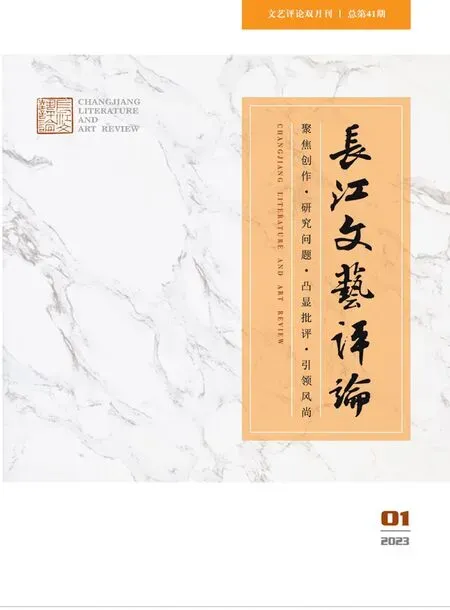围城之下女性生存的社会棱镜
——《春潮》电影文本解读
2023-09-01韩明明
◆韩明明
电影《春潮》自上映以来,以女性生存为焦点环绕众多社会话题与热点问题引发公众的广泛讨论与争议热潮。电影海报的宣传语借德国著名心理学家伯格·海灵格的名言开宗明义地为这部女性作品定下主题基调:“你和母亲的关系,决定和世界的关系。”影片从内到外,从剧情到现实每一丝毛孔都表露着女性题材影片的独特文艺气质。画外人与画中人汇聚女导演、女演员、女记者、女社工、女学生等多重女性主体身份与原生家庭为核心的多层女性经验,构成女性视域下女性群体生存图景的多元交叉与视野融合。
电影的成功之处在于导演自带“女作者电影”的标签,颠覆传统电影以男性为性别属性的“凝视”主权,转换男性与女性“看”与“被看”的主客体视角,将原生家庭中的男性存在作为讨论、审视、评判的客体对象,从而推进两性关系的社会思考成为作者、演员、观众三位一体的反思中心。整部电影以母女关系为核心,展开不同历史时期三代女性游离于血缘纽带之间“寻父认母”的情感曲折与心灵挣扎。影片以克制、冷峻为叙事基调,节奏平缓,通过中、近景,私人空间与公共场域频繁交错的镜头语言表现人物主体,放大人物情绪,营造母女之间相爱相杀的深刻矛盾与伦理困境。透过复杂多样的女性伦理情感,细腻隐秘的女性身份叙事,自然互文的女性意象表述形成多元化女性经验的社会成像,从而追溯女性群体在时代、历史、国家、社会、家庭多重交织的巨幅图景下复杂的生存困境与深刻的现实反思。
一、母性谱系的关系断裂与情感异化
“女性谱系”是法国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吕西·依利加雷女性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概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在《与母亲的近身接触》—文中首次探讨女性谱系的存在问题,将“原始的弑母”视为“社会与文化运转的基础”。[1]因此她认为女性之间存在独立的女性谱系,首先表现为基于血缘上的女性关系即以母亲为轴心的直系支脉,囊括母亲、外婆、曾外婆以及女儿、孙女、外孙女等多重伦理身份。并进一步指出母女之间和谐的关系延伸至整个女性群体中能够从社会层面为女性营造爱的空间。女性能够通过女性谱系确证自己的多重身份以及重新发现被男权文化遮蔽的女性历史。因此,女性谱系中以母女关系为主导的母性谱系,成为女性谱系中的重要一环。时代背景的风云变幻、历史成因的错综复杂、家庭伦理的盘根错节形成母性谱系多重层面的矛盾交织,往往导致原生家庭中母女之间的关系断裂与矛盾冲突。在母女伦理之战中,伟大的母爱往往变身为可怕的母爱。
拉康认为,主体间性是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交互影响。[2]母性谱系的断裂表现为母女之间主体间性的关系制衡与伦理罅隙。影片的叙事结构以母亲顾明岚与女儿郭建波之间七次矛盾冲突为主要线索渐次铺陈展开,两代人身居同一“巢窠”之下却表现为肉体“在场”的零度冷漠与精神“缺席”的对话空白。电影的开头选择以家为背景的私人空间中宣告母女水火不容的银幕首战。女儿郭建波“闯入”母亲与合唱团正在排练的家中,故意在“公众视域”下抽烟的“私人行为”,引爆了母亲言辞激烈的极度不满。女儿表面上沉默无言,却在母亲转身后狠狠地将烟头按在饺子皮上发泄情绪,并故意打开厨房水池下方管道的阀门制造“水漫金山”企图破坏母亲的排练,报复得逞后欢快地甩动着胸前的围巾。母亲拥有这个家的“空间”主导权,而女儿却始终是这一“空间”无声的破坏者和权威的挑战者。第二次冲突表现为母女两代人生与死的价值观冲突。住在楼下的王阿姨是母亲顾明岚的闺蜜,一生命苦,老伴去世养女不孝,母亲欲尽友人之义主动张罗其安度晚年事宜,可不想老妇人承受不住世间困苦故意自杀,这令母亲内心悲愤难以接受。母亲眼中的“最好安排”却被女儿质疑自己的好心与逝者意愿相背离。致命的打击是闺蜜的死震颤了母亲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认同。在母亲眼中“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女儿却更尊重个体的主观意志。生命认知差异与价值观念冲突早已在母女之间分裂成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第三次冲突上升为职业道德与国家意志的个人叩问与价值认同。饭桌上母亲的老伴周叔叔肯定女儿身为记者坚持正义真言、暴露黑暗的人格魅力与高尚操守,却被母亲贬斥为拿着国家粮干着批评揭露“吃里扒外”的勾当。母亲愚昧的“爱国”致使她是非不分,价值认同的偏差更是令双方拒彼此于千里之外。第四次“战争”爆发在母亲同学聚会的醉酒之后。前期的铺垫交代了原生家庭矛盾是多年来母女之战的核心问题,女儿的父亲始终是这场战争烟雾的罗生门。他是女儿心中无法忘却的至爱,是母亲心中无法释怀的仇恨。爱与恨难以忘记,反复提起,在母女之间相互撕裂、彼此伤害。女儿是父亲血脉的延续和生命的承载,却成为母亲一生无法逃避的伤痛。母亲借酒意发泄积蓄多年的愤懑,对女儿恶言相加:“我在你们姓郭的家里面,做了一辈子的奴才。我现在老了还要看你的脸色吗?我不欠你们姓郭的,你想我怎么样呢?难不成我要给你下跪,给你磕头,你就满意了是吧。”面对女儿一如既往的无视与冷漠,怒火中烧:“看不惯了吧,你不要看啊,你走了就不要回来,我真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人呢。”关上门后的女儿用手握紧床头的仙人掌,望着掌心斑斑点点的血迹细细地搓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小伤口,就像细数这么多年里母亲插入自己心口的刀伤。第五次冲突以第三代人小孙女的教育问题为导火索,母爱的占有欲与保护欲激起两位母亲的分庭抗礼,也引发了全场中二位的首次正面交锋。母亲再次宣示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空间主导权,“这是我家,我做主”,这激起了女儿作为孩子母亲的强大保护欲,带着女儿叛逆逃离。女儿的出逃和失去外孙女的惶惶不安让母亲决心斩断母女之间的最后一丝温情。第六次战役的打响,从女儿和外孙女的回归开始,母亲策划了对女儿蓄意报复和对外孙女刻意挽留的阴谋,告知九岁的小孙女其“不清不楚”的身世来历,戳穿女儿为保护外孙女所编织的善意谎言,变相抬高自我在外孙女心中“爱”的分量,并郑重地告诉小孙女:“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可以相信,但是你要知道姥姥是爱你的。”面对母亲的霸道强势和无理伤害,女儿躲进厨房,水龙头再次被打开。真正的决裂也是最后的战役发生在母亲彻底倒下之前。隐藏着女儿私密空间的老旧行李箱被母亲无意间翻开,发现女儿珍藏着与父亲有关的一切回忆时,怒不可遏地将其一炬毁之。两人最后一次面对面的对话场域从“私人空间”的家中转向“公共领域”的楼道,空间主场的置位互换使双方由对峙走向对话。“你为什么烧我的东西?你不喜欢那些东西,我把它藏在箱子里了,我在这个家里没有什么是我的,我就那么一点点,你也必须要毁了它。”面对女儿的质问,“战无不胜”的母亲在全片中陷入了唯一一次的沉默性“失语”。
母女关系的断裂是时代的牺牲品,在历史的错位断层下酿成无法挽回的家庭原罪。两代女性成长经验的差异与伦理身份的对立为彼此关系埋下了情感异化的悲剧隐喻。母女之战的轮回伴随着母亲的倒下而隐匿平息,过往伤痕随着女儿在母亲病床前的对窗自白而日渐浮出水面。在女儿的视角中,母亲之“恶”源自于母爱的缺失、母亲对父亲的抹杀和与母亲的“骨肉之争”。自小母爱关怀的缺失使得母亲的形象成为女儿心头的一轮无光残月。被母亲视为“流氓、恶棍、混蛋”的丈夫形象,在女儿的眼中却是“温柔、仁慈”的完美父亲。而母亲之于女儿生命中的存在,是冷淡、虚伪、强势、虚荣、善妒的“暴君”和“杀戮者”,四十年的时间里,母亲从未象征过温暖与爱的港湾,却是家庭氛围的操控者和个人欲望的追逐者,更是试图抢夺自己行使母亲权利的侵略者。自己的存在是母亲绕不过的历史屈辱,是自身苦难的现实见证,但这一切却无法博得女儿根本上的怜悯与同情。暴力与强势的奴役方式只能适得其反,迫使两个血脉相连的人渐行渐远。波伏瓦认为:“母亲和孩子们的关系,要从她的生活的整体形式上来确定;它取决于她同她的丈夫、她的过去、她的思虑、她自己的关系。”[3]在作为妻子与母亲的双重视角中,母亲认为首先丈夫让自己背负了未婚先孕的时代耻辱;其次丈夫婚后的个人“道德问题”让自己持续蒙羞;再之生活的重压与家庭的不睦让她尝透了人世间的艰辛与苦涩,自身原生家庭的不幸让她无法体察与正视女儿对母爱的需求和渴望。女儿与父亲割不断的亲密关系一方面让她发疯般地嫉妒,另一方面又加重了毁灭式的自我异化。对女儿的爱和亏欠更多地转移到关照第三代的主动性抚养、疼爱与呵护上,这也无疑是侧面表达对女儿不露声色的歉意与补偿。波伏瓦对母女关系的复杂性做出如下解读:“对母亲来说,女儿既是她的分身,又是另一个人,母亲既疼爱她,又与之敌对;母亲把自己的命运强加给孩子:这是一种骄傲地承认女性身份的方式,也是一种报复女性的方式。”[4]在这场相爱相杀的冰与火之战中,母亲裹挟着暴烈的控制欲与强势的征服欲行使自己的“善意”,女儿在无声的反抗与沉默的隐忍中日趋同化。伦理立场的迥异与价值观念的偏差在母女主体间的无意识状态下持续发酵成彼此制衡的牵绊和筹码,两性关系的破裂造成母女关系断裂、原生家庭伦理残缺的无数社会悲剧。
二、女性身份的多元建构与本我认知
影片中女性主体的多元身份建构是本片想要引发社会公众思考的一大看点。剧中针对女儿郭建波与母亲顾明岚以及小孙女郭婉婷三代女性角色设定,选择从生理本质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与本我认知主义的三个层面完成伦理身份、社会身份与本我身份在女性谱系中的交织建构,隐喻着女性生存困境的深刻反思与女性本我意识的深层解析。
(一)伦理身份
三代人在女性谱系中形成血缘上牢不可破的中国式伦理关系体征。第一代人顾明岚同时拥有姥姥、母亲、妻子、女儿四种伦理身份,在不同伦理身份与成长经验的交织中呈现隔代亲密、近代相斥的关系表征。作为女儿,她遭受母亲的经济压榨与亲情忽视;作为母亲,她对女儿表现得过分严苛和情感冷漠;作为妻子,她对丈夫充满怨恨和憎恶;作为姥姥,一边对孙女注入慈爱一边企图“教化”。第二代人郭建波兼有母亲和女儿的双重身份,独特的成长经历与细腻敏感的性格特征使其个人谱系呈现两极分化的表征形式。作为女儿,她的半生都陷入在“恋父”与“认母”的精神迷失与灵魂挣扎之中,却始终无力解构与母亲之间的重重阻隔;作为母亲,她毫无保留地向她的女儿释放母性的柔情与光辉,在给予的同时满足自身缺失的心理补给。第三代人郭婉婷作为姥姥的外孙女和母亲的女儿,是两者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世纪灾难中的受害者、幸存者和调解者。一方面她独享着姥姥和妈妈双倍疼爱和关照,另一方面也被迫承受着由上代人的恩怨纠纷所遗留下的过错与伤害。因此九岁的她既拥有符合生理年纪该有的天真烂漫,又有伦理身份催化下被迫成长的世故早熟。女性生理因素所决定的性别属性通过血缘纽带与伦理身份建构成牢不可破的女性谱系,构成多样化的身份原型。时代演进的风云变幻、历史成因的错综复杂给家庭群体中背负多重伦理身份的女性个体招致无处遁逃的生存困境和无法弥补的心灵伤害。
(二)社会身份
影片着意凸显女性由社会工作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完整统一,表达对社会身份建构下女性独立意识的高度赞赏和自我价值的充分肯定。三代女性在不同的社会身份下出色地完成了各自的阶级分工和价值使命。她们是雷厉风行的社区领导者、有良知的社会记者和优秀的在校学生。母亲顾明岚曾经是文工团老师,退休后成为热心的社区工作者。母亲的社会身份属性与工作性质体现出浓厚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和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女儿郭建波是报社记者,将直面现实、披露黑暗、还原真相视为己任,是一心为正义开道,为公平亮剑、为社会号脉、为弱者发声的时代捍卫者。影片中郭建波怒扇猥亵幼龄女学生的变态男教师;作为报社里的一股清流区别于夺人眼球的标题党,甘于做被边缘化的社会吹哨人;不惧生命危险走向现实深处,关注拆迁、怒杀、暴力等社会事件与公共隐患。小孙女郭婉婷是一名成绩优异的小学生,在“以分数论天下”的学校班级中却坚持团结同学不搞歧视,主动和差生坐在一起并成为相互帮助的好朋友。
(三)本我身份
女性本我身份是女性生命本能和内驱力的原始书写,是个人欲望的非理性表达。三代女性通过不同的身世经历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做自己”的强烈反叛精神与本我意识。母亲顾明岚是一个活在历史语境中的女强人。她的极端本我招致了“错爱一生”的家庭不幸和个体异化。年轻时嫁给曾经的丈夫是为了达成当年留在城里的私心;为了离婚甚至不择手段地逼迫女儿成为自己的利用工具、打出“苦情牌”博得同情怜悯以达成目的;为了压制女儿留住外孙女,不顾孩子幼小心灵的健全和成长阶段的健康,怒撕女儿过往伤疤,剖开孙女不知生父的身世之谜。在特殊的时代里坚持离婚和信佛这两项被视为不能触碰的社会禁忌。一面掌握家庭私人空间的绝对主导权,另一面在社会公共领域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甚至晚年的老伴老周于她而言都只是依附者与效忠者的工具性存在。
女儿郭建波的本我带有更多的伤痕色彩。父母关系破裂使自身在情感方面始终游离在“恋父”与“寻母”的安全感之外,形成对男性无意识地依恋、女性认同感缺失以及两性关系的极端不信任。童年记忆中父爱是心灵世界中唯一的柔软之地,母爱却是求之不得的水中月镜中花。波伏瓦指出母爱对少女成长经历的重要性:“当孩子被剥夺母爱温情时,往往对这种温情的需要会在她成年的生活中缠绕她。”[5]影片中女儿对昏迷中的母亲做内心镜像的自我剖析:“有多少夜晚,我都夜不能寐,我想躺在妈妈的怀里。但是大多数时间,我都躺在了男人的身边。”“寻母”不得,只能将情感缺口投射到男性身上求得安慰,走上和母亲同样未婚先孕的老路,吓跑母亲眼中的“好男人”、可以托付终身的结婚对象,宁愿“寄人篱下”与母亲重复日复一日的战争,拒绝美好生活的鲜花之路。“我不,我就是要你看见我现在的样子。”放纵自我,成为母亲命运的复刻悲剧是对母亲变相的惩罚和伤害,同时在与母亲的无休止之战中获得报复性的快意和仇恨性的痛感,也在无形之中招致了女儿伦理身份残缺的身心伤害。个人本我在两段情感中经历了由“伤痛之爱”迈向“治愈之爱”的自我救赎。影片中交代郭建波和作曲家情人的相处模式表现为私密空间里“零对话”的无声状态,忧郁的蓝调音乐和隐秘的昏暗灯光化作人物内心世界与精神状态的写意补白,构成音乐、图像与动作相结合的声像蒙太奇。两人的关系更像是一对理想幻灭者遭受凛冽现实的残酷伤害后相互拥抱取暖、彼此舔舐伤口的失意乌托邦联盟。与盲人按摩师的爱情发生,是男性世界中“寻父”之旅的精神融合,预示着两性关系最终回归琴瑟相调的和谐与共。
小孙女郭婉婷的本我是充满对立冲突的多元矛盾体。首先,原生家庭的破碎使她一方面怀着对幸福家庭的憧憬与渴望,另一方面对现有家庭的残缺极度地敏感和焦虑。面对同学崔英子一家三口的融洽与和睦,眼中流动着满满的艳羡与向往。而面对母亲与姥姥的战争时内心充满恐惧和担忧。影片中小孙女多次用语言和行动表露自己内心情感杂陈的厌恶与嗔怪,例如面对姥姥与母亲的口舌之战直言不讳:“你们说话怎么阴阳怪气儿的,人家崔英子家就不这样。”用故意甩牛奶的方式发出隐含的抗议。家中无休止的车轮之战不知多少次让她从睡梦中惊醒,两位亲人的彼此伤害令她如履薄冰。在本我真实的内心世界里一方面因担心自己唯一两位亲人的离散而惶惶不安,另一方面又发誓要努力充当好姥姥和母亲之间的气氛调解剂。因此听到姥姥和母亲的半夜争吵时,会故意出现转移两者的注意力;发现姥姥生气动怒时会偷偷劝妈妈逃走等等。原生家庭里的隔代矛盾与情感隔膜让她在幼小的年纪里背负了太多不该有的复杂情感和过重的精神压力。其次骨子里流动着两代人的血脉基因,在姥姥和母亲双重影响下成长为两人性格结合的“综合体”。在被姥姥悉心照顾的长久生活中,一方面继承了祖辈的伶牙俐齿和刁钻泼辣,另一方面也兼有母辈的温顺懂事和善解人意的性格优点。最后,不安于现世、追求释放天性的叛逆本真。影片中乖巧懂事、成绩优异的郭婉婷也会逃掉钢琴课在家里肆意撒疯;将象征着圣洁的白鸽刷为粉色,戏称其为拥有翅膀却不能飞翔的“鸽子小姐”,以此暗指母亲和自己“被折翼”的话语权力丧失。
三、女性意象的美学表达与多向反思
(一)女性与自然的互文表征:以“水”化身与以“物”寓人
电影以“春潮”命名,暗含着女性以水为化身的丰富意蕴。首先片中对母亲和女儿两位主人公“以名赋意”的背后,潜藏着“人与水”命运相连的特殊隐喻和母女关系的整体走向。母亲顾明岚的名字中“岚”字的设定,饱含“山”和“风”组合意义。单亲妈妈的角色迫使她承担起家庭双亲的职责异化为“女男人”,生活苦难的繁重和家庭关系的破裂令她负重前行,性情日渐古怪暴戾。母亲本该拥有柔情似水的母爱,却始终如同一座孤耸的冰山呼啸着凛冽的寒风。女儿郭建波名字中的“波”暗指女儿命途多舛的颠沛流离。家庭方面与母亲的关系一如波涛翻滚的汹涌暗潮;工作上自成一股与世俗抗争的逆流力量;在情感方面始终居无定所,随波逐流自由激荡。其次,女性的内心世界与水之间建立起密切的情感关联。当女儿与母亲每每发生矛盾冲突之时,女儿便会陷入深度的障碍性“失语”,通过打开水龙头的方式来排泄内心的愤怒与仇恨。同时水在影片中是纯洁无瑕的皈依象征。为王阿姨夫妇安放骨灰时,母亲主动向女儿提出死后将骨灰撒入水中的愿望,以求身前身后都干干净净、清清白白。最后,水是女性私欲化的自我表达。片中郭建波与情人作曲家浴室的情欲片段,表现水与女性身体的柔美共性,对性欲望的流动写实。片尾的水流象征着治愈亲情“失语”与抚平爱情“伤痕”的心灵之匙。当女儿面对昏迷在病床上的母亲终于敞开心扉,与盲人按摩师相爱之时,大地回暖,尘封多年的冰山开始融解化作一股涌动的细流由室内流向室外,从城市涌向村庄,汇聚成泉奔流入海,预示着两性关系融洽和母女关系溶解的最终走向。
“物”在影片中出现是作为与女性的现实处境与命运轨迹紧密相连的自然意象表达。包括羊、长颈鹿、盆栽花、仙人掌等动植物的多重意象。第一,黑山羊的母性寓意。影片中一只五花大绑、叫声凄厉的黑山羊曾经出现在女儿的梦境里,被全副武装的医疗队伍拖出家中之时转换为母亲的形象。黑山羊在西方神话中象征着不祥的凶兆。在女儿的潜意识里,母亲是一切不幸的万恶之源,是充满敌意的对立存在。第二,长颈鹿的自由隐喻。本该与大自然栖息共生,却被关在动物园玻璃房中长颈鹿,无疑暗喻着片中深陷现实囹圄之境的女性。第三,盆栽花的命运轮回。菩萨吊坠被埋进土里善意的度化让干枯的土地重新开出鲜花,隐喻着女性在经历坎坷与苦难的世道轮回里仍然向善生活的顽强生命力。第四,仙人掌的性格表征。外形被刺包裹、锐利锋芒,内在耐旱持久、生命力顽强的仙人掌,象征着母女二人“外方内圆”的性格特征。这恰恰导致了两人之间以刺示人却秉善行事的相处模式。母亲虽然常常对女儿恶语相加,但依然处处履行母亲应尽的职责和义务。不仅独自将女儿拉扯大,培育成大学生,更是成为社会伸张正义的良知记者。另一方面,主动对外孙女的抚养和照顾、偷偷为孙女攒下读书储蓄是母亲旨在为生存艰辛的女儿减轻生活压力、营造更多的个人空间。女儿对母亲虽心存芥蒂,但骨肉之情仍潜藏在血脉相连的细枝末节里。母亲半夜咳嗽不止,女儿躲在隔壁房间虽不曾露面,但听到声响后迅速起身,暗中关切着母亲的一举一动。在母亲病中昏迷时,守在母亲的病床前默默地为她擦洗梳头。
(二)女性生存的多向反思
影片《春潮》故事讲述的背后折射出时代与历史语境下女性群体背后的一系列社会生存问题。女性由个体生存出发所涉及的成长经历、情感经验与个人意识等多元冲突;关注家庭生存中伦理道德、代际沟通、角色责任、话语权力等多重矛盾;聚焦社会生存下价值认同、性别歧视、信任危机等多层困境。银幕作品对现实问题的投射回归根源性反思,以此归纳为四条结论:第一,家庭伦理问题的多面反思。两性关系的和谐是家庭伦理运行在既定轨道的安全保证。影片将悲剧产生的症结要害溯源至家庭伦理体系的残缺。三代人皆因“缺席”的父亲与“不称职”的母亲而活在上一代的余孽伤痛中。家庭结构中男性主体身份的“缺席”与伦理关系的“空白”,单身母亲责任意识的严重缺失和情感关照的间接忽视,对下一代的身心成长造成无法弥补的精神伤害。
第二,代际沟通的对话机制重建。家庭是爱的港湾,不是敌对的战场。影片中母女二人将彼此最好的一面展露给外面的世界,却把最深的伤害留给最近的亲人。这无疑揭露出当代家庭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代际矛盾、伦理差异、价值观冲突、信任丧失、安全感不足等诸多原因造成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隔膜和情感淡漠。信任与理解是久逢甘霖的雨露,回归爱的本位是消散雾霭的晨光,心灵的沟通与对话是打破黑暗的黎明。时代飞速运转与社会日新月异的喧嚣浮尘下,人与人之间对话机制与信任恢复需要进行迫切性与必要性的关系重建。第三,女性意识的适度矫正。女性追求本我的先锋意识应保持“放”与“收”、“纵”与“敛”之间的中性平衡,过度追逐自我与封闭自我都可能造成女性生存迷失与经验异化。第四,和谐共生的终极追求。和谐是一种超个体生命的存在,这个存在是个体生命、人生幸福以及社会价值的根据。[6]因此女性以个体存在的方式承载着两性关系融洽和谐、家庭伦理稳固和谐、个体与社会的价值和谐、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稳定与发展的共生和谐。这种女性力量以春潮之势在与时代搏击的汹涌澎湃中释放无限潜能。
《春潮》这部影片集中展现了女性在个体、家庭与社会多面之下的真实境遇,深切关注时代变迁下女性群体的生存困境与个体命运的飘零浮沉,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美学意义。首先第三代人的生存走向预示着当代女性伦理困境的自我修复与平复伤痕的和解释然,面对情感颠沛与命运波折保持乐观胸襟与豁达情怀,给予观影者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其次,现实的忧虑反思激励女性群体在男权社会的主导之下争取自我价值认同与建立话语权力机制,加强自我保护与追求权利平等的意识主动性,回溯女性谱系对社会和谐稳定的本初意旨;同时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的发展与完善产生重要的启示意义。再者,女性电影在未来发展的积极展望:进一步丰富女性形象多元化的审美性表达,给予女性边缘化群体的主体性关注,建构女性身份的交叠性叙事,重视女性情感的复杂性抒写等等。最后,活在苍穹之下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人性撕裂的碎片中寻找本我,在情感伤痛的反复中重塑自我。在伦理关系、血缘情感、价值认知由分裂回归融合的对立张力之下,获得道德洗礼与人性升华的巅峰体验,这是当代社会中“崇高感”的灵魂复现。这种崇高感的诞生是时代语境下人们告别伤痛后精神力量的涅槃重聚。它以强大生命力赋予观影者莫大的心灵震颤和信念支撑。
注释:
[1]【法】Luce Irigaray,Sexes and Genealogie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52.
[2]【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页。
[3][4][5]【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I)》,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页,24页,185页。
[6]王杰:《寻找乌托邦——现代美学的危机与重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