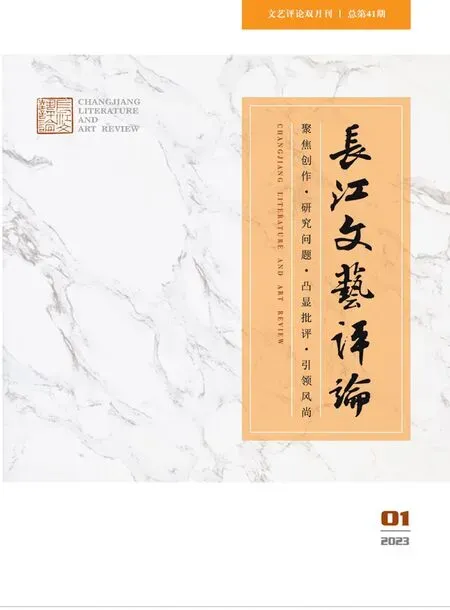乡土记忆、民间书写与诗意想象
——论干亚群散文创作的特色与价值
2023-09-01孙伟民盛凌越
◆孙伟民 盛凌越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王鲁彦、许钦文、许杰等为代表的“浙东乡土作家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作家群体,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学地位。王鲁彦等作家之后,浙东文坛一度冷寂,少有大家名家出现。单说散文创作领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虽有余秋雨这样的散文大家出现,但其作品类型主要为历史文化散文,浙东人事风物并非其书写重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真正赓续了浙东乡土散文创作传统,并在创作技巧、表现内容等方面有所拓延的是浙江余姚籍散文家干亚群。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干亚群便开始发表作品,并在散文创作领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绩。他的创作以书写浙东乡村日常生活及民风民俗见长,其散文具有浓重的地域特点,不仅记录了其有关浙东乡土的个人记忆,描绘了多元立体的人物群像,同时也是在为一个渐行渐远的时代画像。干亚群在其散文中,常以儿童的视角观察世界,并以儿童的口吻叙说观感,整体呈现出一种童稚朴拙的语言风格和纯净明丽的诗意境界。干亚群的散文是近年浙江作家散文创作的重要收获,也体现了浙江当下散文创作所能达到的艺术水准。
一、以儿童视角诉说乡土记忆
漫观中国现当代散文创作,以儿童的视角或口吻进行散文创作,并非自干亚群始。在此之前,萧红、迟子建、刘亮程、李娟等作家都曾大量运用儿童视角进行散文创作。何为儿童视角?有论者表示:“儿童视角,顾名思义,就是用儿童的眼光或儿童的口吻来叙述故事,故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叙述的基调、结构、心理和意识都受制于儿童的一种叙事方式。”“儿童视角作为一种限知视角颠覆了传统的全知全能视角。世界对于处于成长阶段、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懵懵懂懂的孩子来说太高深莫测了,他们只能以自己稚嫩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儿童心灵的稚嫩与视角的晶莹纯净,使本来纷繁复杂的世界呈现出一派活泼清新的气象。”[1]以上论说对于我们了解何为儿童视角及其特点、缘由、功用很有启发。采用儿童视角是一种在情感上更为天真烂漫,在技法上更能强化现实对照的写法及策略,其好处在于创作者能够藉由儿童的视角去观察和表现成年人易忽略的地方。
干亚群在创作时多使用儿童视角,在其散文中常可见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比照。如在《天落水》一文中,作者写道:“父亲说,这是空气里的尘埃。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想了半天也没明白,这水缸里的沉积物与空气里的尘埃居然会连在一起。一场雨洗一次天空吧?”[2]在成年人的认知里,门前的水缸中的“天落水”(“从天上掉下来的水”)即降雨,是一种再普通和正常不过的自然现象,但从儿童的角度看,他们观察自然的方式和理念更为直观、简单或缺乏常规的逻辑,他们很难将水缸中污黑的沉积物和空气中悬浮的尘埃直接联系在一起,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并生发了“一场雨洗一次天空”这样令人叫绝的奇思妙想,从而呈现出一种充满诗意想象的语言美感和富有童趣的表达效果。
此外,儿童因懵懂无知,并不像成年人那样有着种种禁忌或规约,他们对所看到的事物常常感到好奇。比如,关于动物的某些生理现象,本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但成年人对儿童是讳莫如深的。如在《一只三眼皮的猪》一文中,干亚群叙写了有关一头“有着三眼皮”、唤作“小小花”的种猪的记忆,童年时期的“我”看到“小小花”“非常烦躁不安,又是拱栅栏,又是转圈子,嘴里还不停地‘哦哦’”,“一双眼睛痴痴呆呆,三眼皮似乎更深了,要不是外面有一圈白色的眼睫毛,那三眼皮好像要飞进肉里去。更要命的是它把自己的粪便踩得稀巴烂,猪圈里臭气熏天。母亲拿扫帚打它,它没多大反应。母亲继续拿扫帚刺激它,它突然狂怒起来,在一间不足八平方米的圈舍里撒开蹄子,却一连几个趔趄。”从引文可看到,作者对处于发情期的“小小花”的状态描写非常生动细腻,也很有画面感,但她不明就里,对父母看到该场景后的耳语满是好奇。成年人将动物的发情和配种视为不宜儿童目睹的禁忌,但他们却是另外一种表现,“主人们在一旁不知是监督还是帮助,抑或是欣赏,嘴巴里高谈着一些什么,而目光却盯在小小花身上。”[3]
对同样一件事情,以儿童或成年人的视角来看,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比和反差。作家无需更进一步地写明作品想要表达的意义,从成年人与儿童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表现中便可窥得全貌。
二、多元立体的乡土人物群像
在干亚群的散文世界里,浙东乡村中的一切人事风物,或节庆婚丧等风俗,或锄头蓑衣等物件,皆是有独特意义的,都承载了她对逝去的不可回转的童年记忆的留恋与追忆,都是值得书写记录的乡土文化记忆。干亚群在人物描摹上,很能显示其深厚的笔力,这方面的作品很多,代表作如《张先生》《肚里仙》《菊花》《老郭》《最后一位赤脚医生》《阿国看鸭》等。在这些作品中,干亚群延续着其一贯的平静自然、娓娓道来的叙述风格。她笔下的人物常常是一群普通的人,往往是与她同一个村庄的童年伙伴或是工作上的同事。
《菊花》一文中的主人公菊花是作者幼年时的玩伴,作者将菊花从幼年一直写到嫁人后独自操持家庭。读者可通过作者对菊花的行为、话语的写实描摹,充分感受到菊花的性格特点,而她的性格特点也为她之后的人生起伏埋下伏笔。当菊花参加了县越剧团的招考,却迟迟没有收到想要的录取通知书时,“我”觉得“虽然不是我,可我还是感到怅怅然的”。相比之下,菊花则要坦然得多,“说是没考上就没考上,这又不是天大的事,唱戏就是玩玩的。说这话时,菊花的脸挂着淡淡的笑意,那笑渗透着平静。这些年过来,我见过的笑脸不知有多少,有大人物的,有文化人的,也有一些有钱人的。他们虽然有一副很标准的笑容,但几乎没看到过像菊花那种亲切笑意。”[4]作者由菊花在这一事件上的表现以及她那让作者印象深刻的“淡淡的”“渗透着平静”的笑来写菊花的淡然性格,当真应了人淡如菊的古语。
干亚群还在其散文中描写了一些颇为“另类”的人物,其中,尤其值得关注和分析的是算命先生、神婆、赤脚医生、剃头师傅、接生婆等形象。这些身份不一但同属于乡土社会的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关乎村民们的起居、嫁娶、信仰乃至生死,他们在民间生活中发挥着十分特殊且不容忽视的作用。
《张先生》一文着重写了一位身世很苦的算命先生张先生,他十几岁时生病,后又慢慢失明。为了生计,他给人搓绳、磨剪刀,下河捕鱼时又差点被淹死。最后,以给人算命谋生。“天热的时候,他跟许多人一样喜欢坐在桥头上跟人聊天,但更多的时候是听人聊天。那时他忽闪着一对盲眼,愉快地接受着旁人的声音。明亮的月光滴落在他的眼睛里,泛起些许光泽。坐在月光下的他,看上去有种仙风道骨的气韵。一身的长衫在晚风中微微打着褶皱。月亮升高后,大家慢慢散去,有人习惯性地跟他说,天黑,走路小心。他呵呵一笑,我天黑天明都一样。村里人哈哈大笑,一个个散去。”在该文中,张先生曾说道:“这世上每一个人的命是一样的,但运是不同的,它是可以左右的,可以变动的,其实我算的不是命,是运。”[5]与其说这是张先生的叹语,不如说这印证了干亚群关于命和运的思考。
干亚群在《肚里仙》一文中还写到过两位神婆,一位是本村里的“肚里仙”,一位是另一个村的“药王菩萨”。两位神婆据说都有过“生病、禁食等之类的体乏其身”而后“关仙”的经历,她们称能够通阴阳,“似乎什么事都能管”,不仅给人算命,还给人看病,“俨然一个全科医生”。作者在该文中,渲染了“肚里仙”的神秘色彩,但“肚里仙”的结局让人唏嘘,她因患有严重的胃病,竟被草头郎中一针扎死了。当“肚里仙”死后,“我们村里的人感到很遗憾,今后‘关仙’得跑很远的路。”[7]相比之下,“药王菩萨”的灵验体现于“把姑妈家的位置,包括房屋的左右都说得一清二楚,家里还有哪些人也交代得明明白白”。但当“我”发现“药王菩萨”之所以知道这些信息,是因为两位妇女在姑妈“求救菩萨”之前已经从姑妈处问询到了这些信息。
如果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神婆之说是蒙昧的,是需要被批判的对象。但是,干亚群写算命先生或神婆时,不仅表现这些人物的神秘色彩,更是把他们当作普通人来写,而尽可能追溯这背后的乡土文化。
三、“万物有灵”的民间书写
在干亚群的散文中,有很多细腻且富有神秘色彩的民间描写,婚丧嫁娶、风俗节日、自然界的事物在干亚群的笔下是有生命的,有灵性的,甚至有神性的。在清明、端午、七月半、中秋等传统节日里,村民们通过种种活动与已逝的祖先或祭祀的鬼神的精神对话。当谈到清明时,干亚群写道:“村里一直有这么一个传统,亲人过世后的三年里清明一定要上坟,除了在坟前上香点烛烧纸钱外,还要每年在坟上放一堆上圆下略钝的土,有时一看到坟上的土堆就可以知道这是老坟还是新坟。三年满后再不必上坟,但必须在清明那天祭祀过世亲人,村里人称为做羹饭,认为这天阴阳两界可以相会。过了这天,村民就会去‘肚里仙’那里询问亲人在阴界的情况。机灵的‘肚里仙’自然不会忘记说清明节来过家里,家里人又是怎么厚待他,等等。”[8]此外,端午时,要制作粽子,抓黄鳝吃鸡蛋。七月半是阎罗王开地府的日子,所以要做羹饭请祖宗吃。诸如此类的表述都很具有地域色彩,增添了散文的阅读性。
在节日的风俗之外,亦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民间说法,如“河埠头是由男人砌成的,这跟村里腌咸菜时不让女人用脚踩一样,老人认为女人属阴,不可做承载分量的活。”[8]“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一块线板,那是从娘家带过来的陪嫁物,与鞋子、针线一起放在鞋簟里。线板有三个手指宽,一拃来长,上面漆成红色,考究些的,上面还描了些花纹,多些是牡丹花。”[9]类似这样的乡村民风民俗的描写在干亚群的散文中,不胜枚举。对很多读者来说,读到这些有关风俗描写的文字时,常常感到新奇而有趣。而对于干亚群来说,不仅是在记录她个人的记忆,也是在为一个地域画像。
在干亚群的笔下,充满梦幻和神秘色彩的乡村世界也是她着力要表现的对象。藉由儿童视角,干亚群所呈现出的乡村世界除却梦幻和神秘,还表现出一种别样的美感和诗意。《万家的狗》一文中就书写了一条仿佛通灵的狗,“后来,人们发现这条狗非常有意思,它喜欢去生病的老人家门口坐,有时甚至一坐好几天。它不走,说明老人的病情还没有缓解。它走了,有两种可能,要么老人将很快离世,要么老人的病过几天肯定会好转。有人说,这狗成精了,能通阴阳两界。”[10]类似带有魔幻色彩的书写在干亚群的散文中并不罕见,鹅仿佛会说话,牛似乎会思考哲学问题,还有吃完草擦嘴的兔子,甚至于石头铺就的河埠头都有着自己的思考和情感。正是在这种崇尚万物有灵的书写里,读者可以感受到如诗又如童话般的审美体验。
通过干亚群的文字,可见得她记忆中的乡村世界是非常多元的、难以概括的。发生在乡村中的很多事情,其本身就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如果非要说清楚道明白,便会失去很多绮丽且美好的想象。无论成人之于孩童,还是孩童之于成人,彼此的视角和视野是有巨大的差异的,儿童比成人更能感受到来自乡村世界的神秘,而这种神秘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淡化、习以为常。干亚群显然深谙其道,因此,她多选择以孩童的视角叙说记忆中带有神秘色彩的乡村。在她的散文中,也常见到许多没被成人注意到的僻静角落,而这“僻静”之处,也正是干亚群的散文的美感、诗意和纯真的诞生之地,是其散文美学上升至一种独特境界的所在。
四、冲淡平和的诗意想象
漫读干亚群的散文,无论在语言风格,还是在叙述节奏上,其文字很难见情绪的大起大伏,也很少看到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句式,通体呈现出一种温润如水、冲淡平和的朴拙诗意,恬淡如一首质朴无华、秀雅隽永的田园诗。这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散文巨匠汪曾祺的散文风格。虽然干亚群在散文创作上表现出与汪曾祺诸多相近的特点,但又有着很大的差别。晚年时期的汪曾祺的散文创作独树一帜,“读其散文如饮陈酿琼浆,其文字更是让人觉得有着非同寻常的深厚韵味。”该时期,汪曾祺的散文创作整体呈现出“如其步入晚年后在散文中所表露出的旷达情怀,在作品中所展现的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多使用短句的调遣等特点”,并“十分注重诗、文、画等诸多艺术形式的综合运用以及对传统散文的学习和借鉴”。[11]且不论干亚群是否有意效法汪曾祺的创作,但单从作品来看,干亚群在汪曾祺的散文风格之外,实另有探索和发展。
在散文的造境上,干亚群常采用白描笔法。干亚群的散文在景物的描写上,只用寥落数笔,就勾勒出大概轮廓,而这种方式描写出来的景物就创造了一种类似与中国水墨画般清新自然的境界。如《正月十四夜》一文的开头这般写道:“这天,村庄里的烟囱又慢慢热闹起来,从几天前的稀薄恢复到了过年前的稠密,可以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冒着青烟。整个村庄上空蒙着一层淡淡的烟云,青色里裹着一点灰。”[12]干亚群在散文造境上有她自己的策略与认知,她不仅对意象的选取进行过筛选,甚至对意象所属的色系也是有着深思熟虑的。在《蝉》一文中,“梅子雨过后,天开始放晴。放晴几许,屋前的枣树上倏忽传来‘吱’的一声,怯意十足。过后,四周一片寂静,显得刚才那声‘吱’恍恍惚惚。继而,树上的‘吱’开始拖音,慢慢升高,高到数丈后戛然而止。村庄一下子跌入幽静。”[13]环境,尤其是乡村的环境,并不总是如画般安静古雅的,更多时候是嘈嘈切切的,是满富生机的。在干亚群的散文里,她的乡村书写就呈现出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状态。数个“吱”字,两个“静”字可见作者在撰文时语言尽量凝练生动,而语意尽量传神入境。
干亚群的笔下的浙东乡村,无论是人与自然,还是人与人之间都呈现出一种和谐共生、“共同承担”的关系。村民们在长期的农务劳作中早就学会了盘肩,“扁担下的人同一个表情,挂满汗珠的五官跟掰开的棉桃一样僵硬,似乎肩膀上的疼嵌到了脸上。挑扁担的人都有一手绝活,那就是盘肩,将扁担从一个肩头过背转到另一个肩头,两只箩筐在晃悠悠中完成掉头的动作。”[14]人与农具之间形成了一种联结,正如没有农具养活不了农人,没有农人也养活不了农具一样。这让人联想到海德格尔对梵高的名画《鞋》所做的解说:“暮色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眠。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这器具属于大地(erde),它在农妇的世界(welt)里得到保存。正是由于这种保存的归属关系,器具本身才得以出现而得以自持。”[15]农具正是因为农人的使用,而农人正是因为是乡土中国的延续的一部分,因此,作为器物的农具、人、乡村才显示出超越字面意义的形而上的内涵。
干亚群的散文看似质朴无华,但她在作品中浸透了对浙东乡土社会的深沉情感和独特思考,整体呈现出冲淡平和的诗意想象。而读者也常能于这种冲淡平和中读到人生的深层启悟,究其根本,这源自于作家对童年生活的怀念、对乡民乡风的追忆,以及对民间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
结语
品评干亚群的散文是一件有趣的事,在阅读其作品的过程中,一幅多姿多彩、丰富多元的浙东乡土画卷在我们面前逐渐清晰显现。干亚群通过她的笔触为我们勾画出一个更为宏阔的艺术天地,那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在记忆深处无比鲜活的乡土世界。我们被她的细腻隽永而感染,也被她的诚挚纯真所打动。在她对记忆中浙东乡村风物人情的书写背后,涌动着的是她对于故土丰沛且浓郁的情感。她所记录的不仅是其个人的乡土记忆,传承的实是一个时代的风貌,她是在为一个时代画像,蕴含着对乡村未来的追问与思索。从这个层面来讲,干亚群的散文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学价值。干亚群不仅仅是一位散文家,她更是一位民间吟游诗人,她所浅唱的是一曲关于一去不复返的乡土记忆的挽歌。
注释:
[1]陈振娇:《儿童视角自传隐喻——〈芒果街上的小屋〉的民族身份建构策略》,《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2]干亚群:《天落水(外一题)》,《青岛文学》,2012年第7期。
[3]干亚群:《一只三眼皮的猪》,《梯子的眼睛》,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7页。
[4]干亚群:《菊花》,《日子的灯花》,宁波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118页。
[5]干亚群:《张先生》,《给燕子留个门》,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页。
[6]干亚群:《肚里仙》,《给燕子留个门》,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
[7]干亚群:《清明的青》,《给燕子留个门》,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180页。
[8]干亚群:《女人的河埠头》,《给燕子留个门》,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63页。
[9]干亚群:《缝衣针》,《梯子的眼睛》,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91页。
[10]干亚群:《万家的狗》,《梯子的眼睛》,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1页。
[11]孙伟民:《论汪曾祺晚年散文的艺术特色——重读〈昆明的雨〉》,《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7年第4期。
[12]干亚群:《正月十四夜》,《给燕子留个门》,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
[13]干亚群:《蝉》,《梯子的眼睛》,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页。
[14]干亚群:《锄头》,《梯子的眼睛》,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76页。
[15]【德】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