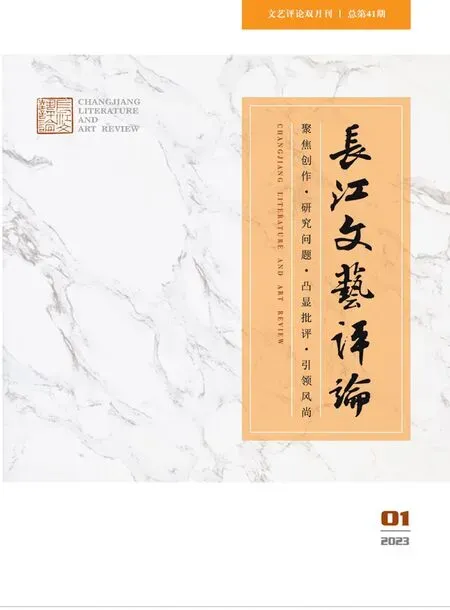论古远清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2023-09-01胡德才
◆胡德才
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虽然至今并未获得官方认可,在国内高校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领域大多暂时将其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邻近学科对待,但世界华文文学丰厚的蕴藏、鲜活的生命力和学界四十余年坚持不懈的推进及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使之被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俨然已成为事实。
有“学术常青树”之誉的古远清年逾八旬完成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这显然有为这一新兴学科作阶段性总结的意味。古先生为该书写的后记题为《人生八十才开始》,他以饱满的学术激情和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无限热爱开启了自己人生的新旅程。年届八十的古先生,两年之内出版了《台湾文学焦点话题》《台湾文学学科入门》《微型台湾文学史》《战后台湾文学理论史》《台湾查禁文艺书刊史》《台湾百年文学制度史》《台湾百年文学期刊史》《台湾百年文学出版史》《台湾百年文学纷争史》《台湾当代文学辞典》等台湾文学研究书系和“世界华文文学三书”:《世界华文文学概论》《世界华文文学新学科论文选》《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古先生令人瞠目的井喷式学术成果使他八十岁开始的人生仿佛一个学术传奇,但造化弄人,古先生传奇式的人生却最终迎来了悲情的结束。仿佛西方古典悲剧的结局,高潮到来,剧情陡转,人生谢幕,古先生蓬勃的学术生命在八十二岁时画上了句号。
2022年12月27日,是古先生告别人世的日子,我和古先生的学界朋友当天都收到了他最后的微信,内容就是即将出版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的清样电子版,那是他最后的牵挂。作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古远清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理论与历史的全面反思与总结
古远清晚年“一个最大的心愿是为世界华文文学这门学科的建设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1]。他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理论与历史的全面反思与总结主要体现在《世界华文文学概论》和《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二书之中。
“世界华文文学”概念最早出现在作家秦牧1986年2月发表于北京《四海》杂志的《打开世界华文文学之窗》一文。但从1970年代末至整个1980年代,学界对台港文学以至世界华文文学的关注与研究,主要是对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的拓展,尚未上升到学科建设的自觉。学界以整合性的视野对世界华文文学进行理论建构、提出加强学科建设的自觉性始于1990年代初期。
1993年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将前五届的会议名称“台湾香港文学研讨会”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并成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标志着国内学界一种新的学术观念开始形成,认识到华文文学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应该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观。同时,学界开始自觉致力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
1999年,陈贤茂主编的四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出版,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史上的标志性成果,陈先生同时在导论中宣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新的学科。”[2]
2002年,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正式成立,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得到有力推进。学会会长饶芃子强调,学会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学科建设”,即“建立学科观念”,把世界华文文学“这一领域的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3]。
2009年,饶芃子、杨匡汉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及与之配套的四卷本《海外华文文学读本》出版,这既是学会推进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举措和成果,也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迈入新阶段的标志。
2021年,古远清出版《世界华文文学概论》,2022年,出版他编选的《世界华文文学新学科论文选》,并于同年完成了《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2023年初出版)的撰写。这三部著作可称为古远清“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三部曲”,一部教材,一部学科论文选,一部学科发展史。古先生试图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理论与历史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其中,凝结着他“对华文文学学科创新和向何处去的追问和反思”。他“希望通过这‘三书’,把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立起来”[4]。其“学术野心”不可谓不大,这“三书”和他持续近十年所编篡的九本《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3—2021)就是他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所做的基础性和开拓性工作。在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史上,古先生的开拓性工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该学科日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古先生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理论与历史的梳理与总结,显示了他开阔的视野、开放包容的心态和求真务实的精神。
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世界华文文学首先在学科命名、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多有分歧,甚至众说纷纭。从学科建设的层面看,“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是两个主要的学科命名。前者所指明确、可操作性强,后者虽有争议但更具时代感和包容性、也为更多的学人所接受。古先生显然倾向后者,他在《世界华文文学概论》和《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里对学科的多种命名进行了一一的辨析,对世界华文文学与周边学科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从追溯生成前史到总结生成经验,进行了全面探讨与总结。在这样全面学术梳理的背景下,古先生阐释了“世界华文文学”命名的合理性和研究对象的包容性。
古先生认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是从中国视角或曰中国本位出发的,”这种命名“不仅与地理因素有关,也与价值观念相连”。[5]而且,华文文学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站在他国的角度看,中国也是海外,因此这一命名不具有普适性。而关于“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名称的内涵,学界一直存在分歧,争议的焦点是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大陆文学是否应包含在世界华文文学之中。古先生认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中国文学不能缺席。”“研究中国大陆文学乃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但从学科的演变来看,“世界华文文学”是从“台港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发展而来,中国大陆文学早已有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已存在一个独立的“中国文学”学科。因此,对中国学界而言,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大陆文学显然不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对中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各国学界而言,研究世界华文文学而将中国文学排除在外,那也是不可思议的。就像国内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者以海外华文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国外的研究者也可能以中国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即使国内研究者,也必须看到,中国文学是海外华文文学存在的背景和不可或缺的参照。正是基于这样复杂的原因,古先生虽然强调应该将中国大陆文学纳入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对象,但“并不是说世界华文文学要拿出巨大的篇幅来描绘中国大陆文学地图,而只是在参照意义上,把它作为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比较的对象”[6]。世界华文文学包含中国文学,尤其对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观照和比较研究更不能缺少中国文学,但不同国度的研究者研究世界华文文学时可以各有重点。这是符合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实际、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也更具有科学性的说法,这样的观点也更能获得全球范围内的华文文学作家和学者的广泛认可。
关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研究对象的另一问题是,华人文学是否应包含其中。有学者认为世界华文文学不能涵盖海外华人的非华文创作,因此,倡议以“华人文学”取代华文文学。古先生认为,华人文学是从族群角度立论,虽然中国人也是华人,但从外交方面着眼,华人概念通常指中国以外有华族血统的世界公民。因此,不宜以华人文学取代华文文学。但古先生认为,“世界华文文学不应固守‘华文’的疆界。华人文学作品不管有无中译本,都应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种研究对象。”因为,海外华人“即使用英文、马来文、日文写作,也不可能完全排除精神文化还乡的可能。”“华人文学的形态,先天就带有某种混合性。”[7]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的确存在交叉、重叠、分化的复杂关系,世界华文文学学科不必拘泥于语言的分野,还应考虑文化的内涵。如果简单地用“一刀切”的二分法,将华人文学排除在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研究对象之外,“那就忽视了这些华裔文学所成长的中华文化土壤,也忽略了海外华人的种族认同,漠视了他们的创作成绩,这在客观上会挫伤海外华人创作的积极性。”[8]我以为,这不是简单的折中方案,而是显示了古先生开阔的学术视野,开放包容的心态,也是他在充分吸收了中外学人的研究成果后,作出的有利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发展的富有探索性、前沿性、前瞻性和普适性的阐释。
古先生在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理论与历史的反思与总结中,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品格的探讨与归纳(国际性、移动性、本土性、边缘性),关于海外华文文学对新中国文学的贡献的论述等,都是富有新意的。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成长与走向成熟的历程,也是世界华文文学作家作品及批评家与批评成果经典化的过程。古先生以文学史家的眼光、开拓者的勇气致力于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与批评成果的经典化,其探索性、独创性的视角和评述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世界华文文学概论》和《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二书中,他都以大量的篇幅来梳理、筛选、总结、评价世界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成果。《概论》中评述世界华文文学作家61人,批评家9人。《学科史》重点评述世界华文文学学科重要学术著作十余部(含文学史、教材、专题学科史及理论著作),创作大家24人,研究名家20人。世界华文文学及其研究涉及广阔的空间和较长的时间,作家、研究者众多,创作与研究成果丰硕,古先生评述的重点、大家、名家有限,自然是精挑细选的结果。当然,对古先生把握的标准、评论的尺度、挑选的结果是否准确、有无遗漏,人们或许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作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学术锐气、首创精神和致力于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成果经典化的努力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值得充分肯定,这也是他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贡献。
二、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料与文献的广泛搜集与整理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和突破,主要取决于创立和完善作为独立学科的理论建构和发掘、整理、呈现比较系统、完备的学科文献资料。其中,理论建设具有引领性,将决定学科发展的高度;资料建设具有基础性,将决定学科建设的厚度。就资料建设而言,三十多年来,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该学科内容涉及面广,资料搜集、整理难度大,整体而言,资料建设仍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薄弱环节。
古远清藏书丰富,博览群书,在学界联系广泛,尤其注重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其学术研究以史料详实见长。他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资料建设的重要贡献,除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深耕台湾文学外,主要体现在他编篡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世界华文文学新学科论文选》和撰写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之中。
古先生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具有非常自觉的学科建设意识和使命感。早在2007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返聘已退休的古先生给学生讲授“世界华文文学”课程,他就跟我建议、商量编篡《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但那时学院、专业尚处于草创阶段,学科建设经费非常有限,我也忙于建设初期的学院行政工作,无暇协助古先生编篡年鉴,这样,年鉴编篡一事虽时常谈起,却都议而未决。直至2013年下半年,古先生告诉我,他已在着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第一册的编篡工作。2014年,《华文文学》以增刊的形式正式印行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3》,古先生就这样以一人之力结束了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没有年鉴的历史。
古先生编选出版的《世界华文文学新学科论文选》既属学科资料建设,也是学科理论建设。世界华文文学学科资料建设难在海量文献散佚世界各地,时空阻隔,处境边缘,全面搜集、钩沉、考辨、汇集困难;理论建设则因学科研究对象的边缘性、交叉性、多元复合性、模糊不定性而难以作出经典的理论建构。迄今的理论成果多为借鉴多学科的各种理论方法对世界华文文学进行多角度的探讨,历史的、美学的、比较的、文化学的等等,不一而足,有分歧,有论争,众声喧哗。随着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日益稳定和成熟,也呼唤着学科理论建构的新突破。
古先生编选《论文选》正是立足于学科理论建设,从四十余年来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宏观论述和理论探讨的学术论文中选择53篇汇集成册,39位作者,分属中国大陆、台港澳和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选文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大体能反映四十余年来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理论探讨中所涉及的主要话题和理论建设的轨迹。该书意在“为世界华文文学这门学科的诞生作见证以及做理论支撑。”[11]作为第一部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理论建设论文选,既是对四十余年学科理论探索的检阅,也是对未来学科理论建设发展的铺垫和呼唤。
古先生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更是开创性的著作,对学科历史文献的系统梳理、评述,对世界华文文学创作大家、研究名家的论评,对学科研究现状的跟踪和对学科发展远景的展望,多有新见。该著作没有流于一般学科史四平八稳的材料罗列,它高屋建瓴,观点明确,材料鲜活,生气灌注,既具学术性,亦有可读性。其中还有古先生搜集和征得的第一手资料或鲜为人知的材料。从学科资料建设的角度看,古先生的《学科史》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立下了一块新的界碑。
三、对台湾文学历史与现状的全方位耙梳与研究
国内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是从台港文学研究起步的,而中国大陆文坛从1970年代末开始关注的聂华苓、白先勇、於梨华等台湾作家,同时也都具有海外身份,也属海外华文作家。因此,由台港文学延伸出海外华文文学,再整合为世界华文文学,有其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必然性,台港澳文学自然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远清并不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台港文学研究的学者,他是从1989年出版《台港朦胧诗赏析》开始进入台港文学研究领域的。自从走进台港文学世界之后,他就沉醉其中而不能自拔。在他眼里,“世界华文文学是一座五彩缤纷的锦簇花园,那台湾文学便是散发着芬芳的一丛鲜花。”他则是辛勤采花的蜜蜂。古先生虽然研究门类宽广,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乃至美华文学亦有涉猎,但“最钟情的还是台港文学尤其是台湾文学研究”。[12]他是著名的台湾文学研究“专业户”,名副其实的台湾文学研究专家。就掌握台湾文学研究资料之全、出版台湾文学研究著作之多、耙梳百年台湾文学历史演变之细,在学界首屈一指。十年前,著名诗人洛夫读到古先生的《台湾当代新诗史》就称赞他:“不论大陆或台湾的诗歌学者、评论家,写台湾新诗史写得如此全面、深入精辟者,你当是第一人。”[13]
古先生是文学史家,尤以私家治史著称,在其七十余部著述中,各类文学史和以史料见长的著述占半数以上。文学史涉及面宽广、需查阅的文献浩繁、前期研究工作量大,学界多以集体项目、分工合作的方式进行,但古先生习惯“单打独斗”,私家治史,扎硬寨,打硬仗,克难关,以一人之力撰写十数部各类文学史,数量上打破了学界个人撰写文学史的记录,创造了“私家治史”的奇迹。其勤勉、执着和献身学术的忘我精神令人敬佩。古先生的台湾文学研究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色。
第一,全方位多侧面深耕台湾文学。
古先生既有《当代台港文学概论》《台湾当代文学事典》《台湾当代文学辞典》等全景式的梳理、论述、反映台湾文学历史发展过程、各类体裁的作家作品、各时期的文学思潮、文学论争、文学事件的综合性著述,更有从文类、文学制度、文学传媒、文学争鸣等多角度撰写的台湾文学史。如《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当代新诗史》《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台湾新世纪文学史》《微型台湾文学史》《战后台湾文学理论史》《台湾查禁文艺书刊史》《台湾百年文学制度史》《台湾百年文学期刊史》《台湾百年文学出版史》《台湾百年文学纷争史》等,其中多数都是开创性的填补空白之作。在传统的以评述作家作品为重点的一类文学史之外,古先生从更多的侧面更完整地呈现百年台湾文学生态、发展过程、复杂关系、经验教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台湾文学研究系列。
苏楠有点走神,她在想象李石磨跟杨小水一起生活的情景。李峤汝以为苏楠无心跟父亲闲聊,赶紧自己支开自己。爹,我去做饭,你跟苏律师好好聊聊。她在旁边,怕爹放不开。
第二,回眸历史与关注当下相结合。
古先生的台湾文学研究一方面以十余部“史”书全方位梳理台湾百年文学史,彰显出他作为文学史家的优势和特点,另一方面他又十分关注台湾文学发展现状,常常直接介入当下台湾文学现场,将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相结合。他的《台港澳文坛风景线》《当今台湾文学风貌》《世纪末台湾文学地图》《分裂的台湾文学》《台湾文坛的“实况转播”》《蓝绿文坛的前世今生》等著作就都体现了这一特点。特别是对台湾当代文坛的宏观鸟瞰、对文学史事件的当代反思、对当下文学现象和热点问题的争鸣等,是古先生台湾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他的《台湾百年文学制度史》《台湾百年文学出版史》等书的历史叙述都截止为2020年,书末的“余论”《台湾文学制度展望》《台湾文学出版面临的困境》等都介入当下台湾文坛。古先生曾独立完成多个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台湾新世纪文学史》《当今台湾文学风貌》《世纪末台湾文学地图》等著作都是课题结项成果。古先生频繁到访台湾,置身台湾现场,订购多种台湾书刊,结交众多台湾文友,在台湾文学世界纵横驰骋,贯通古今,因而成了“台湾通”,进而在台湾文学研究领域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硕果累累,独领风骚。
第三,详实的史料与批评的锋芒并存。
古先生的台湾文学系列研究是建立在丰厚的史料基础之上的。在他的藏书中,以台湾文学资料最为丰富、最有特色,其中包括多种成套的台湾文学书刊。因此,他的台湾文学研究以史料扎实著称。如《台湾文学学科入门》一书由“台湾新文学关键词”和“百年台湾文学大事年表”两部分组成,上编七十页,阐释四十二个关键词,下编一百七十多页,逐年展示1920至2020年百年台湾文学的重要事件,具体到年月日,由此可见古先生做史料的功夫。他的《台湾当代文学事典》《台湾当代文学辞典》也都是以广博、丰厚的史料作支撑的。因此,孙绍振评价说:“古远清所收罗的学术资源之广博和第一手的准确性,使得他的著作具有学术生命力。”他“以其学术资源的系统和丰厚,为台港文学研究在学科基础的建构做出有目共睹的贡献。”[14]但古先生并不是只钻故纸堆的老学究,他是一位关心社会、紧跟时代、耿直敢言、执着求真的学者和批评家。他说:“我从不愿意做纯学术的工作,努力遵循学术与政治、与时代、与社会相结合。”[15]他从事台湾文学研究,有国家民族的大局意识,因此不回避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他甚至提出“用政治天线接收台湾文学频道”[16],虽然他也很重视审美天线、语言天线,如他高度评价余光中的文学成就,认为“能做到诗文皆美,余光中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堪称第一人”[17],并出版有《余光中传:永远的乡愁》等专著。从《台湾文学焦点话题》一书所涉及的众多文学事件,可知文学与政治、与社会、与时代的紧密关系,也可一窥古先生介入台湾文学现场、直面敏感问题的胆识与批评锋芒。
总之,古远清先生勤奋多产,著作等身,是台港文学研究大家,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七十多部著述均为独立完成,因此,他被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称为文坛“独行侠”。古先生确有侠者之风,功底深厚,本领高强,乐观豪迈,仗义执言,但有时也难免固执任性,率性而为,不拘小节。古先生著作中“自我重复”一类的瑕疵也正是其侠者之风的表现,也就可以理解。古远清为台湾文学研究和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创造了多个第一。他是“侠之大者”,是名副其实的学界“古大侠”。
注释:
[1]古远清:《后记》,《世界华文文学新学科论文选》,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版,第653页。
[2]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鹭江出版社1999版,第28页。
[3]饶芃子:《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备经过及学科建设概况——在“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报告会”上的学术报告》,《华文文学》,2002年第3期。
[4]古远清:《后记:人生八十才开始》,《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3年版,第332页。
[5][6][7][8]古远清:《世界华文文学概论》,中国华侨出版社2021年版,第15页,9页,8页,14页。
[9]黄维樑:《古镜记:读古远清编篡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3〉》,《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4》,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1页。
[10]古远清:《编著“年鉴”成了我晚年的一项事业》,《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6》,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39页。
[11]古远清:《凡例》,《世界华文文学新学科论文选》,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版,第1页。
[12]古远清:《序言:研究台湾文学乐此不疲》,《世纪末台湾文学地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页。
[13]洛夫书信,载古远清编注:《当代作家书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95页。
[14]孙绍振:《推荐序:古远清的勇气和学术坚持》,《战后台湾文学理论史》第一册,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版,第3—4页。
[15]古远清:《自序》,《台湾百年文学制度史》,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版,第2—3页。
[16]古远清:《自序:用政治天线接收台湾文学频道》,《台湾文学焦点话题》上册,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版,第1页。
[17]古远清:《当代台港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