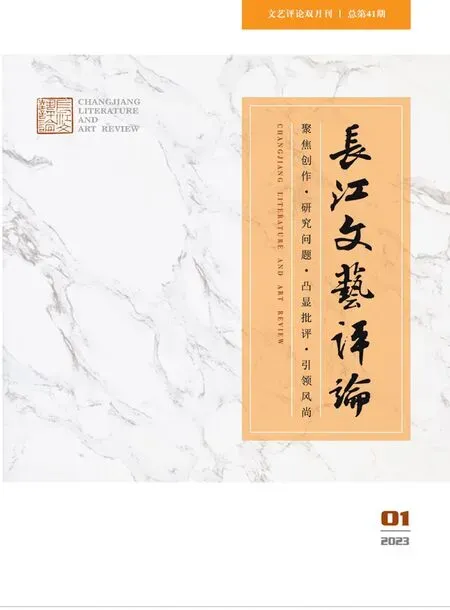历史循环剧或“楚人”宿命史
——何志汉小说《赋圣宋玉》阅读札记
2023-09-01赵黎明
◆赵黎明
《赋圣宋玉》是宜城作家何志汉创作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也是他为鄢地辞赋先祖宋玉正名的倾情之作。小说在楚国日衰、群贤逃离、言路日蔽的历史背景下,以宋玉的出生、读书、入仕、归隐为发展主线,从仕楚曲谏、与奸佞周旋、对百姓倾心关爱、对爱情忠贞不二等维度,多侧面、全方位地展示了宋玉淳朴敦厚、风雅高洁、忧国忧民的崇高形象。它是一部楚人追忆楚人的记忆之书,也是一部楚人对祖国命运痛定思痛的反思之作,倾注了大量的主观情感,也加入了不少的个人体验,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介入性。的确,对中国文学史来说,宋玉不过是一个生于楚地的辞赋家,但对楚人后代而言却是一种特别亲近的存在——不仅出生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还时刻活在他们的血脉、思想和性情中,这或许就是楚之后人如此追念他、怀想他,并当其遭遇无端讥嘲时奋起捍卫的原因所在。
宋玉生地楚之鄢郢,即今湖北宜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八)载:“(宜城)城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隽才辩给,善属文而识音也。”晋习凿齿《襄阳耆旧传》亦云:“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宅,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关于他的具体出生地,一般认定是在城南,即小说所称的“腊树园”,墓葬亦在附近,“乙亥二月,摄官宜城。今考邑志,城南三里有宋玉宅,宅后不数武,冢与毗连”(清方策《修楚大夫宋玉墓垣碑》,《宜城县志》卷九《艺文志上》)。至于全国各地存在多处“宋宅”问题,《水经注》曾做过一个专门的附注:“宜城县南有宋玉宅。按宋玉宅有三,此其里居也;一在归州,从屈原游学时所居;一在江陵,则服官郢都时居之。”[1]郦道元特别强调了作为归田而居的“里居”与“游学”及“服官”所居的不同。小说选择“腊树园”作为故事发生地,显然是吸收了主流史学界的成果。
关于宋玉与屈原的关系,不论是西汉的司马迁,还是东汉的班固,一致认定他为屈原后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艺文志》云:“宋玉……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二书记载都比较简古。尤应引起重视的是宜城籍学问家王逸的注释,其在《楚辞章句》卷八《九辩序》中,载有这样一段文字:“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闇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王注不仅明确点出了其文与屈原的师承关系,还特别强调了宋作《九辩》“闵惜其师”“以述其志”的个人品行,可见二人不仅其文相近,其志也相通,屈宋并称,并非空穴来风。由于秦汉时代相踵,三位史家可信度高,“丘明既没,班马迭兴”(《晋书·陈寿徐广等传论》);“屈宋接武,班马继作”(唐·皎然《讲古文联句》),所以这些论述多为后人采纳,历代鲜少有力质疑者。
不仅未加质疑,历代对宋玉其人其作大加褒扬者大有人在,李白有“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之句(《感遇四首·其四》),杜甫的“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亦广为流传(《咏怀古迹五首·其二》),其他如王世贞《宋玉墓》:“此地真埋玉,何人为续招;秋风吊师罢,暮雨逐王骄;万事才情损,千秋意气消;仍闻封禅草,遗恨右文朝”等等,表达羡钦尊崇之情的作品不计其数。当然,其中也不乏微词相讽者,如“楚国骄荒日已深,山川朝暮剧登临。曾伤积毁亡师道,祗托微词荡主心。江草东西多恨色,峡云高下结层阴。潘郎千载闻遗韵,又说经秋思不任”(刘筠《宋玉·西昆酬唱集》)。对宋玉“祗托微词”而非冒死直谏表达了些微遗憾,但大体还是在正面肯定范围之内的。宋玉的文化形象的根本逆转发生在现代。1942年郭沫若创作五幕话剧《屈原》,先在重庆公演,后在苏联和日本上演,产生了震撼性影响。在这部历史剧中,为了突出屈原忧国忧民、勇于直谏的光辉形象,郭沫若塑造了一个“无耻文人”的反面角色,致使宋玉形象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颠覆。如果考虑到剧本创作时的特殊政治环境和用文学“影射”投降变节的御用文人的特殊政治意图,虚构一个与屈原相对立的反面典型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郭氏并不认为这种处理是一时心血来潮,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当有读者质疑其歌颂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却“冤枉另一个大诗人宋玉”时,他才和盘托出何以贬损宋玉的原因,“宋玉的《九辩》是好文章,写得很婉转,但那和屈原作品的风格完全不同。那正是一些叹老嗟卑、怀才不遇的才子型的牢骚话。虽然里面也有一些高尚辞句,甚至有直接从屈原作品取用的,但整个精神不同。从《九辩》中,我们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爱祖国、爱人民的情感。”[2]他肯定宋玉文学上的成绩,但“讲到品格和在历史上的贡献”,却对“屈宋并称”不以为然,认为“把宋看为标准的风流才子”,“是历史上的定论,或并没有冤枉他”[3]。郭老所列的若干理由中,最主要的一条来自《史记》中的四十字定论,特别是最后一句“莫敢直谏”云云。
针对诸如此类的曲解贬毁,尊重史实的学者对郭提出了质疑,并相继为宋玉正名而发声。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人质疑郭老《屈原》中宋玉形象的可靠性,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有学者明确指出:“郭沫若创作的历史话剧《屈原》中把宋玉写成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但从宋玉的作品中反映出的政治态度并非如此。”[4]近年以来楚地学界更是掀起了一股“正名”风。先是程本兴发表翻案文章,从学术层面对其人格进行正本清源,“宋玉立身本高洁”[5]可谓其立论的主旨所在。后又对其曲谏方式进行辩护,产生了不小的学术影响。“引经据典破万卷,只为宋玉求公平。质疑郭老毁宋玉,阐明赋圣好人品”[6],程先生的这首打油诗道出了他学术努力的动因。何志汉则在国内率先以历史小说的形式,描写宋玉一生行状,复活历史人物。作为宋玉的后人或同为楚人的作家,何志汉的历史叙述,大体追求历史的本来面目,但又没有事事泥古,很多地方加入了一些个人的理解,甚至一些乡党的情感因素,因而不无一种爱深誉切的偏爱之情,这是文学创作的自由度使然。不过,我读这部小说时,注意力并不放在宋玉形象的塑造上,更在意的是文学形象背后的微言大义,即各色人物悲欢离合之中蕴含的历史本质。在我看来,这部小说的真正价值在于它通过宋玉等人物命运遭际的生动描写,揭示了楚国兴衰的历史教训,堪称楚地的“问题小说”,也是一部关于楚人宿命的史诗。
“楚人”有什么样的“问题”?“楚国”经历什么样的“宿命”?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清清楚楚地写在屈原的遭遇里。屈原的故事家喻户晓,屈原的命运令人嘘唏,屈原在传统士人心中是一种神圣的精神符号,它包含了忠君爱国的伦理要求,也包括了九死未悔的士人使命。但在今天看来,屈原的遭遇反映的则是一个政治生态问题,“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贾生列传》)。君王昏聩、奸佞当道、忠信见疑、贤良流离,楚国腐败糟糕的政治名声,不仅在史迁笔下有数处生动描述,专门为之作传的,就有屈原、伍子胥、李斯等等,其他古史如《左传》中也有不少记述,“楚材晋用”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典故。一方面“惟楚有才”,另一方面“楚才晋用”,古已存在的这种矛盾充分说明,楚国的人才流失不是一两个君王的昏聩问题,而是整体的文化土壤问题。楚国历经八百载,问鼎中原数百年,曾有过历史的辉煌,但到屈、宋所处的怀王、顷襄王时代,已经日薄西山,距离“国灭”不足百年了。楚国的衰弱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人才生存环境。纵观《史记》全书,专门就人才与国运关系问题加注“太史公”评论的,只有楚国一国,“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史记·楚元王世家》),可见楚国兴亡根系所在。文学是政治的镜子,也是文化的表征,屈宋形象及其所牵出的伦理冲突正是楚国政治文化的直接反映。其中君臣关系、忠奸结构,在传统文学中一再演绎,乃至成为久传不衰的文学原型。
作为历史延长线上的一个圆点,《赋圣宋玉》无疑承袭了这样一个传统,不过也有新的开拓,在我看来其创新所在就是:以有相同性格的三代楚人的相同遭遇,展示了楚人历史简单循环的可悲宿命。首先我们看看小说的三代苦主:屈原、张鹖与宋玉。作为后二者的老师,屈原正道直行、忠信纯良、文约辞微,“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但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屈子却遇到了因“争宠而害其能”的一帮群小,和“听之不聪”、昏聩无能的怀王,他的下场可想而知,“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只能“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并“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他的弟子张鹖继承其师衣钵,也想以太傅之尊通过教育太子而影响未来国政,然而仍然不被奸佞所容,“有个叫张鹖的,文才出众,因为遭小人暗算,忽然就出走了”,“从此隐身民间,以教书为生”,其结果仍是自我流放,终老乡野;及至宋玉,因为才高八斗,聪明伶俐,而被周石等无赖算计;因为文采斐然,倚马可待,而被顾祺、金丛等奸佞嫉害。具有正面质素的三代师徒,性情相近,品行相若,才学相仿,理当受到朝廷重用,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总是遇到相似的君王、遭逢相同的群小、受到一样的谗言、遭到同样的围攻,收获同样的苦果。史迁笔下的屈氏困境,不仅在屈原那里是打不开的死结,在张鹖、宋玉那里也是找不到出路的泥淖。小说接着司马迁的叙述,以巨大的历史涵括力,描述了几组具有同质性格的文学人物:从楚怀王到顷襄王的昏聩君王,从屈原、到张鹖至宋玉的正直士人,从郑袖到云妃、从上官大夫到顾祺、金丛、倪印的奸佞小人,时移世易,人事变迁,但演出的剧本未变,呼吸的空气未变,人物的性格未变,发生的冲突未变,他们用着同样的动作,在荆楚大地的空间舞台上,演绎着相同的循环闹剧。小说站在长时段的历史高度,描写了宋玉师徒三代人的遭遇,相同历史悲剧的反复演出,不仅对楚国去忠就邪、近奸远贤的政治生态提出鞭笞,而且对楚国历史的深层规律做出了艺术概括,道出了楚国历史简单循环的深刻原因。黑格尔曾刻薄地指出,中国本质上并没有真正的历史,一切的一切都不过是君王覆灭、王朝更迭,不断重复罢了,任何的进步都未从中诞生。这句话初听起来十分刺耳,但放在楚国倒显得恰如其分。在小说家笔下,从屈原到宋玉、从楚王到襄王、从郑袖到云妃、从上官大夫到顾祺,虽然时间仍不断流逝,演员不停更换,但是剧本依旧、动作依旧,历史在那里不过是时间的周而复始、周而复返,任何新的进步都无从发生。我认为小说的价值就在于用文学形式概括了这种历史惰性,指出了这种“历史周期律”的根源所在。
当然,小说并没有让人一味沉溺于循环空转的黑暗历史,而是给出了一道拯救之道,那就是:继往开来,薪火相传,开办教育,将良善的种子传递下去。小说将孩子的教育问题,贯穿在故事的始终,显示了作品的命义所在。教育是小说的一根伏线,也是暗黑世界的一线光明。屈原言传身教影响了张鹖,张鹖设塾授徒传递香火,宋玉身退之后也拿起来教鞭,在家乡办起了学校,“教学子,是天大的要事!”,他暮年的一席话将这种旨趣概括殆尽:
眼看楚国一天天衰落,君王一代不如一代,我这一生是等不到明君了,希望你们能等到。你们不要懈怠,你们等不到,再教好你们的学子去等。教学子就是栽培贤士呀。如果哪一天有了明君,却贤士难觅,无贤可用,岂不遗憾至极!这教学子,乃是天大的要事!
相信未来,寄望未来,并为未来未雨绸缪,培养新生力量,这是宋玉的理想,也是小说的主旨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小说可以称为一部“教育小说”。
此外值得说明的一点是,小说虽然褒扬楚国士子干预现实、批判现实的思想传统,肯定屈原敢于直谏、勇于苦谏的烈士精神,但也对宋玉的曲谏方式进行了某种辩护,认为这是一种不得已的策略选择。“这是通篇微词,这是隐晦的劝谏,这是曲折的劝谏,这是——诡谲的劝谏哪!”“在下的老师曾经说过,对那刚愎自用的君王,直言直语的劝谏,是越来越行不通了,为臣者,须另寻他法。”曲谏方式的选择,只是进谏形式的改变,并没有改变谏诤的本质,所以小说将宋的进谏精神塑造成屈原谏诤传统的补充或发展。不管是司马迁,还是郭沫若,其对宋玉“莫敢直谏”的非难,都有一些脱离实际、苛求古人的成分。在权力利维坦肆虐的先秦时代,面对拥有绝对权威、喜怒无常的君王,普通士子是不敢谏诤也不能直谏的,哪怕曲谏也要冒生死风险,“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楚世家》)……故以“倡优蓄之”的侍臣,最多如东方朔、淳于髡等一样,通过讲讲“滑稽”故事讽喻君王,如屈原那样敢于当面直谏的绝无仅有,这不仅由于其“左徒”的地位,更由于“楚之同姓”的身份,否则后果绝不是“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那么轻松,所以小说肯定宋玉曲谏的合理性,一方面体现了尊重历史事实、不苛求古人的历史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对郭老酷评的曲折回应。曲谏也是谏,关键是谏了什么,谏的效果如何。小说描写宋玉进谏楚王,虽有随声附和的成分,但更多是事关国运民瘼的,比如宋玉即兴创作的《风赋》,就以文艺的曲折形式蕴含了规劝大王归朝勤政之意,“……像是颂扬,怎么又味道不对?宋玉呀,你这个《风赋》……不是个简单的东西!找不出指责寡人之言,怎么又总觉得这里面有指责寡人只顾自己享乐、不顾百姓死活之意呢?”……在小说家笔下,一个关心国家、悯惜苍生而又机敏聪颖的辞赋家文学形象呼之欲出。
大雅久不作,屈宋千古传。屈宋为中国文学奉献的不仅是香草美人、丽词雅句,还有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这一文学遗产的核心部分就是对祖国深沉的爱,对人民真挚的情感,以及对现实的干预精神。《赋圣宋玉》显然萃取了这一楚文化精髓,不仅其所塑造的平民知识分子群像具有这种特质,小说本身也是反思历史、关怀现实之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文学都是现实文学。作为楚人后代,何志汉撰写宋玉的精神传记,目的并不是美化先祖,也不是寄寓闲情,而是用于寄予无限的故国忧思。小说以艺术的形式将先祖面临的历史困境再现于今人面前,既是一种怀念,也是一种期冀,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可谓是奉送给当代楚人的一本“曲谏”之作。小说以高屋建瓴的视野,饱含情感的姿态,勇敢地直面楚国政治文化症候,深刻地总结了千年楚国的历史宿命,给人一种强烈的思想震撼和文化启迪。
注释:
[1]参见【清】穆彰阿、潘锡恩等:《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襄阳府·古迹》,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4—48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3]郭沫若:《谈〈屈原〉剧本中的宋玉》,《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4]黄德馨:《楚国史话》,华中工业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页。
[5]杨斌庆、程本兴:《宋玉立身本高洁》,《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6]程本兴:《宋玉研究顺口溜三首》,《宋玉与宜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