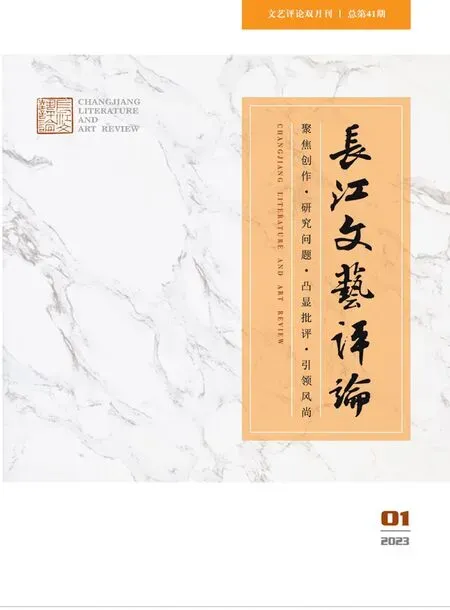巴山渝水诗无尽:重庆长江的诗词想象及其美学特征
2023-09-01王本朝
◆王本朝
一、源远流长:悠久的诗词文脉
“自古西南镇”,“水围巴子国”。重庆古称巴郡、江州、渝州、恭州、重庆府,历来是中国西南版图的锁钥之地。千里泱泱嘉陵江,“含烟带月”小三峡;“蜀中山水奇,应推此第一”之乌江,带着秀美与雄壮,汇入长江。长江劈开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百折千回东流去。
大山大川塑造着重庆独特的自然风貌。山城巍峨、长江浩荡。长江重庆段多激流、险滩、长峡。沿江而下,为它镇守的是涪陵、万州、奉节和巫山。“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七百里三峡为出入巴渝之咽喉,巫山十二峰云霓缥缈,气象万千,给无数诗人墨客以无尽的想象与梦幻。巫山神女,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为幻美的意象。夔州险地,无数游子因江峡所阻,在此慨叹历史烟云,感怀世事沧桑,留下了无数诗篇。“巴渝”和“三峡”,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条璀璨的诗歌长廊。在这里,有李白“思君不见下渝州”的眷恋和“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欢畅;有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感怆,有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深情,也有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缠绵,还有苏轼“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的坚韧,更有毛泽东“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指点江山的豪迈。不一而足。山水滋民风,民风养诗风。诗人们化自然之景于胸怀,融民俗之风于诗律,创造了厚重的重庆诗词传统,彰显了自然之美丽、人性之敦厚和文化之淳朴,激发起世人无尽的欣羡和深远的思索。
人类历史是一部文化的发展史。龙骨坡“巫山人”遗址考古证明,200多万年前的三峡地区就已有人类活动。距今约6000年的“大溪文化”,石斧、彩陶和玉器的使用,表明重庆区域与中国其他文明发祥地,大致同步迈入早期人类文明时代。有文字记载的重庆历史约起于商代,距今3000年左右。当时的巴人在江州,即今天的重庆主城区建立巴国。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后置巴郡,辖治江州。梁朝时置楚州,辖六郡,管制区域与原巴郡相当。隋开皇元年(581年),改楚州为渝州。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改渝州为恭州。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赵惇封恭州王,二月继皇位,赵惇于恭州先后封王封帝,感于双重喜庆,恭州得其嘉爱,而升为重庆府,“重庆”由此得名。宋以后,重庆凭其独特的地理优势逐渐成为重要的商贸重镇,尤其是明清之际大举开发西南,重庆成为了西南重要的商贸物流及文化中心。1891年开埠后,重庆与外部的交流增多,各方面发展迅速,在近现代,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得以进一步凸显。新中国成立后,重庆一直是西南开发建设的桥头堡。
扎根于这片土地的巴人先民创造了重庆悠久的历史,有关重庆的诗词书写,其久远的历史文脉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代。常璩的《华阳国志》辑录有巴地古歌谣,其中有“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形象地展示了巴地的峡江地貌、物产及风俗,让后世感受到古巴民的自然、艰辛与和睦的生活图景,这是较早反映古巴渝地区人民生活的文学记录。巴渝民风质朴,生活平实,重情守诺,在巴渝诗词,尤其是在白居易、刘禹锡等的竹枝词中,都有丰富而传神的表现。
巴渝地处盆地。在唐以前,巴渝就与北方及中原有着诸多联系,从巴地古歌谣中,亦可见出秦晋之风。大水携大山,虽有蜀道之难、江峡之阻,古代巴渝仍可通过长江与湘楚接触,而其中的三峡是巴渝连通外界、汇通四方的重要通道。屈原的《九歌》、宋玉的《高唐赋》对三峡一带的自然与人文就有浪漫想象:“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巫山神女,其曼妙幻影赋予了三峡无穷的神秘魅力。南朝的刘绘、萧纲,北魏的郦道元等,他们创作或辑录的诗作,都有对三峡的描写与抒怀。郦道元的《水经注》借民谣“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在写实的同时,又增添了愁怨情愫,这样,神女幻象与凄哀猿声,就构成三峡诗歌的典型意象。无数游子商旅经三峡出入往来,历江滩绝险,赏万山奇景,听猿声哀鸣,在浊浪沉浮与悲喜交加之中,吟哦出无数壮怀慷慨之作。巴渝北接三秦,东联湘楚,南接夜郎,既有湘楚文化的浪漫深情,又得秦地实诚厚重的文化渗透,伴之夜郎文化的神秘元素,巴渝文化在自成体系的基础上,又有兼收并蓄的特点。从历史文脉看,巴渝诗词发端于春秋战国之际,由巴地古歌谣,见其野气与朴质,由高唐神女的想象,又具多情而浪漫之风。由此,双脉并行,一干双枝,一树繁花。
二、江山风情:地理风貌与历史风骚
独特的地理风貌成就了重庆诗词独特的意象和风格。古今诗词对重庆自然地理的叙写与抒情,主要集中在两江一城,即滔滔嘉陵、浩浩长江和壮观巍峨的重庆城。
嘉陵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通航江段也是蜀地南下进出巴渝的重要通道。嘉陵江曲折蜿蜒于四川盆地的丘陵地带,水势较为平阔,景致最美处在合川以下小三峡一段。李白的“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巴女词》)、陈子昂的“奔涛上漫漫,积水下沄沄”(《入东阳峡与李明府舟前后不相及》)、范成大的“关下嘉陵水,沙头杜老舟。江花应好在,无计会江楼”(《嘉陵江过合州汉初县下》)、王廷相的“苍山冥冥落日尽,古渡渺渺行人稀”(《发白崖》)、王士祯的“云开见江树,峡断望人烟”(《舟出巴峡》),所写皆为嘉陵江上的风光美景。嘉陵江小三峡穿过缙云山,古称巴山,有专家考证过李商隐《夜雨寄北》就作于此,“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不知牵惹起多少读者思亲的绵绵之情。缙云寺又称相思寺,后面有相思崖。民国时于右任登临此地写过一首散曲《温泉望缙云山》:“相思岩下相思寺,相思树结相思子,相思鸟惯双双睡,相思寺自年年翠。”处远而思亲,中国人心中的美好情愫,在千年之后的诗人那里得到回应,这也是中华文化重亲情念旧友的美好见证。
最被诗人反复吟咏的是长江。长江是养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携青藏高原的雪域圣水奔涌而至。到重庆境内,主要呈现为山峡之川,穿切于大山之中,曲折而湍急,经三峡出夔门,迎来的则是“吴楚天地宽”的另一番景致。三峡一带是巴渝先民最早的居所,三峡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走廊和诗歌圣地。古往今来,描写三峡的诗人之多,诗作的数量之大、质量之高,为世所罕见,现辑有九册《夔州诗全集》。寄情三峡的篇章,也是吟咏重庆诗作中最具代表性之作。可以说,吟咏重庆的诗作,近半数成于诗城夔州,而写在夔州的作品,又多为赋咏三峡之作。三峡的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寒猿暗鸟、巫山彩云,萧萧落木、滚滚江涛,这些都被诗人定格成风景画,演绎为情感流,成为无数诗人与读者萦绕心中的三峡梦。为此,诗仙李白写下了“水宿五溪月,霜啼三峡猿”“桃花飞渌水,三月下瞿塘”“巫山高不穷,巴国尽所历”“汉水波浪远,巫山云雨飞”“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等诗句。它们描摹奇险江景,写行旅急切,难掩胸中不畏险途的澎湃激情。诗圣杜甫也有“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瞿塘漫天虎须怒,归州长年行最能”“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众流归海意,万国奉君心”等诗句,体现了一个风烛残年忧国忧民的沧桑诗人形象,展示了诗人博大沉郁的民胞物与情怀。
三峡诗歌,从宋玉的《高唐赋》中走出,在郦道元的“三峡”歌谣中唱响,经由李杜诗篇的洗礼,白居易、刘禹锡竹枝的咏叹,再加上苏轼、苏辙辞赋的铺排,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融入近代诗人的热血,汇流而成刘伯承、陈毅等革命家身上那种负载民族使命的豪迈远行,演绎成吴玉章“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的艰卓砥砺。昔日“满眼荒芜”的荆棘遍故园,是“愁云惨雾,暗淡锁西川”,历史终于迎来千年巨变,“江流石不转”的风景依然,但诗人之笔赋予的则是三峡更美好的意境,面对壮丽山川,毛泽东的“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更是给世界的诗情承诺,显示出中华民族崛起的豪迈与自信。
游历巴渝的诗人,肯定不会忘怀那座守望江边气势恢宏的重庆城。两江襟怀,山势耸叠,重庆筑城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险峻山岩,傍水依山,随山势起伏而层层叠叠,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水之城。山水襟带相映成趣,经诗人之笔而成“城郭大都依壁岸,人家一半住烟岚”的独特风姿,是“江流自古书巴字,山色今朝画巨然”的山水胜景,以及“万家灯射一江连,巴字光流不夜天”的夜景奇观。重庆不仅是一座山水之城,也是一座商贸之城,有“万家灯火气如虹”的繁华,有“自古全川财富地,津亭红烛醉春风”“烟火参差家百万”的繁盛。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港口,还有那“城郭生成造化镌,如麻舟楫两崖边”的富庶。巴渝得山水的滋养、人民的勤劬、商贸汇通的便利,造就了重庆这座千年山水之城、历史之城、财富之城。
滔滔嘉陵、滚滚长江、壮美三峡、巍峨山城,独特的地理风貌经由诗人之彩笔,赋予了重庆山水无限的诗情。
重庆地处内陆盆地,谷深山高,环境闭塞,交通不便,山地多贫瘠,并不占有传统农耕社会的自然优势。但生于斯长于斯的巴渝先民,在与自然相处中养成了勤劳、坚韧、刚毅的品格,形成了自古巴渝彪悍的民风。巴渝也是我国重要的移民走廊,土著与外来移民杂居交融,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民风豁达而质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重庆不一定是开风气之先,但重庆的地理位置和民情物产,却往往成为各种大历史事件重要的回旋举托之地,这也是重庆历史之所以特别厚重的原因。
在重庆的诗词中,有不少书写重要历史事件的诗章。比如钓鱼城军民的抗元斗争,辛亥革命时期重庆顺应历史而动的爱国义举,抗战时期陪都军民同仇敌忾决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以及新中国人民轰轰烈烈参与建设的恢弘场景,在诗词中都有充分的表现。对重要的历史人物,如古代的巴蔓子、秦良玉,近代的邹容,现代的杨闇公等等,诗人们不惜笔墨,追思历史大事件,盛赞历史英雄之伟绩,他们的英名和事迹亦因诗词而传扬于后世。
巴蔓子是重庆重要的历史人物,东周末期(约战国中期)巴国将军。约公元前4世纪,巴国朐忍(今重庆云阳一带)发生内乱,当时巴国国力衰弱,国君受叛乱势力胁迫,百姓备受其苦。将军巴蔓子以许诺三城为代价向楚国借兵平乱。楚国出兵平乱后,遂派楚使索城,巴蔓子认为国家不可分裂,不履行承诺视为无信,割城践约又为国所不忠,于是告诉使臣说:“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遂自刎,以授楚使。楚王感于巴蔓子的忠勇,以上卿之礼葬其头颅。巴蔓子以头留城、忠信两全的故事,在巴渝大地广为传颂。唐贞观八年(634年),因巴蔓子“刎首留城”的壮举和三国时期严颜“宁当断头将军,不当投降将军”的气节,唐太宗赐名忠州,即今天的重庆忠县,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忠”字命名的州县城市。王尔鉴在《巴蔓子墓》中慨赞道:“头断头不断,万古须眉宛然见。城许城还存,年年春草青墓门。”巴蔓子对人民的义举,重然诺而以身许国的忠烈,成为巴渝人民精神人格的象征。
近代革命家杨沧白在他的诗作中也慨叹:“巴蔓古城头,雄关据上游。兵车四国会,日夜大江流。”每当国家民族危难时刻,敢于担负历史责任之精神,从古至今已融入巴渝儿女的血液里。
钓鱼城是重庆历史中一个沉重的符号。钓鱼城在重庆主城百里之外,南宋军民在此以弹丸之地,抗御元军36年,重伤蒙哥,创造了古代军事史上抗蒙防守的奇迹,成为中国古代“忠毅勇武”传统文化精神的象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钓鱼城的怀古诗词不少,爱国诗人文天祥曾以“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发出过自己的追问。对以张珏为首的钓鱼城军民英勇抗敌之壮举,因独木难支而最终失败,诗人的叹息深长而悲凉,也令人不禁回想起历史上那些类似的英雄豪杰。中华文化向来注重道德人格,对这些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牺牲的人们,后世会永远铭记。
在近代革命史上,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就是今重庆巴南区(原四川巴县)人。邹容的《革命军》一文,若“江流出峡,一泻千里”,被誉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吹响了推翻腐朽封建王朝的号角,启蒙了众多仁人志士加入民族救亡的行列。吴玉章评价邹容的勋绩时说:“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而邹容在他的诗作《涂山》里写道:“苍崖坠石连云走,药叉带荔修罗吼。辛壬癸甲今何有,且向东门牵黄狗。”表达的正是献身革命、义无反顾的壮烈之情。现代革命家陈毅在《咏三峡》中有“每到狭窄处,总破一重关”,表达的也是那种坚卓无畏、矢志不移的革命精神。
巾帼不让须眉,重庆自古就多女中豪杰。秦代的巴寡妇清,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实业家。金俊明在《怀清台》中写道:“丹穴传赀世莫争,用财自卫守能贞”,叙写了巴寡妇清的身世,说“其夫得朱砂矿而富甲天下,夫死,妇守其业,以财自卫,人不敢犯,以贞洁名闻天下”。重庆历史上另一位女英雄是秦良玉。明天启年间,永宁(今川南叙永一带)宣抚使奢崇明起兵造反,史称“奢安之乱”。石柱女总兵秦良玉奉命镇压,并在白市驿、马庙、二郎关和叛军激战,大败叛军,活捉统帅。崇祯皇帝诗赞秦良玉奉旨勤王:“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近代爱国女诗人秋瑾在《〈芝龛记〉题后(八章)》中,对秦良玉也有“靴刀帕首桃花马,不愧名称娘子师”的称许。郭沫若《咏秦良玉》中有“石柱擎天一女豪,提兵绝域事征辽。同名愧杀当时左,只解屠名意气骄”之句,对秦良玉作为女中豪杰的勇敢和所创造的业绩发出由衷的赞叹。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成为陪都,不屈的重庆城成为民族抗战的精神堡垒。面对敌人惨绝人寰的无差别大轰炸,“江城怒沸千家火,山月寒轰万壑雷”,重庆儿女则义无反顾,“三百健儿新入伍,悲歌慷慨震危楼”。重庆人民刚毅、顽强,为民族大义不怕牺牲的决绝,也激发着诗人们对侵略者的义愤,对山城人民不屈敌强的歌赞。
在吟诵人文历史的诗作中,还有不少叙写巴渝农事劳作及物象。黄庭坚笔下的春天是“画鼓催春,蛮歌走饷。雨前一焙谁争长。低株摘尽到高株”的繁忙采茶情景。刘天民看到的是“巴田不成井,逐垄细开塍”的农忙和丰收在望。张问陶在友人送橘柚的欣喜中,留下了“涪州朱橘夔州柚,乍解筠笼香一船”的记载。宋永孚的“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明确记录了巴盐开发的历史。赵熙盛赞“酒国春城让白沙”,胡小石感叹“江村地僻足人烟,一饮‘红茅’斗万钱”。这些农事劳作和重庆物产与其他的历史人文一起,构成了重庆物质文明的历史记忆。
三、美学精神:豪迈之气与恢弘之境
古有诗言志、文以载道之说。文章作为千秋功业,承载着构建道德伦理、塑造社会价值之重任。诗词曲赋则多个人的含道映物和生命的澄怀味象,是个体性情、胸襟抱负的发抒流露,“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它以个体性的言说触发共同的人生感受。所以,为文则多为社会请命,吟诗作词则多自我遣怀。但诗词曲赋的个人表达,往往又是应物斯感,受到环境触发,潜移默化,神思勃发,受“水土”“地气”感召,产生一种与地理风貌相似的审美理想。中国文学有南北差异,骏马秋风塞外,杏花春雨江南。不同地域有不同诗风。诗人创作除“情性所铄”之外,还有环境和学养的“陶染所凝”。于是,刘勰有“江山之助”之论,王勃有“人杰地灵”之说。孔尚任也认为:“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冈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凡人不为诗则已,若为之,必有一得焉。”所谓“灵”“秀”“厚”“健”,都是得之山川风土感召而产生的艺术个性。沈德潜说得更为直接,“余尝观古人诗,得江山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其所处之地”。刘师培在其著名的《南北文风不同论》中指出,南方文学倾于浪漫和北方文学偏于现实,均与南北地域水土有关,“北方之地,土厚水深”,“南方之地,水势浩洋”。不同自然山水激发出诗人不一样的怀抱与情感,诗人在咏叹自然山水的同时,自然山水也塑造着诗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人格。
从地质构造看,重庆多高山峡谷、大江长河,多激流险滩、幽谷长峡。行旅之人,在北方是风沙扑面、行道迟迟,看见的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景象,或是“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气候异象。而在重庆一带的江峡之中穿行,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古代出巴渝,要么走陆路,经剑门鸟道,路远途险;要么走水路,从嘉陵江由北入长江,或从宜宾、泸州循长江西来,七百里三峡是必经之途。由于长江穿行于大山之间,回旋跌宕,江随山势,山阻江洄,形成了江面宽阔处数百米、逼仄处数十米的奇观,而且江流中还布满怪石险滩,四季水位变幻莫测。舟行其中,江流平缓处是踯躅回旋,到了峡谷却立马变成江水沸腾,浊浪滔天。涪陵十景中就有“群猪夜吼”,可见滩险与水恶。长江水势受季节影响,冬枯夏涨,古歌谣《滟滪歌》就有这样的描述:“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滟滪大如牛,瞿塘不可流。滟滪大如幞,瞿塘不可触。滟滪大如鳖,瞿塘行舟绝。滟滪大如龟,瞿塘不可窥。”在巴渝连绵的大山之中,如蚁小舟穿行于沸浪之上,诗人内心是复杂的,“扁舟西溯上三峡,千岩万壑争追随,终朝应接已不暇,心目洞骇具忘疲”。面对旅程的凶险,诗人的内心难免忧惧。诗人之心,在与自然的“白帝高为三峡镇,夔州险过百牢关”的体味里,感悟到人生之艰难,既有“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的深沉思念,也有“书报九江闻暂喜,路经三峡想还愁”的乍喜还愁;甚至不乏刘禹锡那“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释然畅达;更有刘伯承那种“海潮东去连天涌,江水西来带血流。壮士未埋荒草骨,书生犹剩少年头”的拳拳爱国之心和洒脱豪迈的青春气概。面对“江间波浪兼天涌”的天险,诗人对人生也有一种超越性体验,产生了无畏险阻、笃定前行、征服自然的崇高之感。
古代出入巴渝者多为宦游之人。观山水之城,历江峡之险,情以物兴,感物咏志。重庆的山川胜境,更使诗人睹物生情,情景交融,心境相通。于是,李白有了“朝云夜入无行处,巴水横天更不流”的超然洒脱,杜甫有了“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的喟然吊古,白居易有了“忧喜皆心火,荣枯是眼尘。除非一杯酒,何物更关身”的平和坦然,以及刘禹锡“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沉重叹息,也间或传来寇准《武陵景》中“武陵乾坤立,独步上天梯。举目红日尽,回首白云低”的相忘自得,白居易“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的农事闲情,以及杜一经“缓步上石来,清风透满怀。此景堪图画,别是一天台”的悠然惬意。
历代诗人吟咏重庆之山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山水诗。山水诗始于魏晋六朝,谢灵运是主要开创者之一,后兴于唐,王维、孟浩然是其大纛。中国诗词中的山水更多的是人格化的表现,山水诗中的自然,往往也是雅静的,体现了恬淡中和之美,表达士人隐逸之心,不乏老庄的虚静和禅宗的透彻,如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而诗人笔下的重庆山水,却有另一番景象和别样的心性。要么是宋玉式的上天入地的诡谲想象,要么是李白般的豪放洒脱;或是陈恭尹那种“通牛峡路连云栈,如马瞿塘走浪花”的激流勇进。照面万山峰丛,扁舟穿行于激荡的礁石缝隙之间,自然虽是可怕的,但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诗人却另生一番心境。他们不是畏葸停步,而是探索前行,在困境超越中获得精神的快慰和力量,在自然伟力面前,诗人也有了阔大而恢宏的人生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曾借词章演绎人生三境界,重庆的诗词曲赋,对三重境界均有一一展现。自然山水的险扼与重负,旅程的逆境滞塞,反而赋予诗人更为强劲的生命力量。
李白东行三峡、杜甫寄寓夔州、苏轼咏叹扁舟,无一不是指向一个精神意象:人生有如江流曲折,难免会遇到激流和险滩,难免会经受峡谷的重重阻遏,只有克服阻遏奋力而为才能冲出峡谷,才可迎来寥廓江天。这是一种何等豪迈的人生情怀!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以及刘伯承、陈毅、毛泽东的诗作中,都体现了面对艰险的勇猛和刚毅。可以说,重庆的自然山水与人文历史对于诗人的影响是巨大而深沉的,传达出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和坚韧意志。可以说,重庆诗词,是一种大诗,是有人生力量和境界的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自然山水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并塑造着诗词的美学精神。它有历史的承传与赓续,也有时代的发展和创新,还因不同情势而有不同侧重。在整体上,它体现出一种坚韧而超越的精神。无论是生存在峡江地区一代又一代的巴渝先民,还是寓居于此、暂驻将行的思乡游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人生渴望,那就是走出去,摆脱自然对人生的拘囿。这既是身处盆地山谷人们的潜意识和现实生活的催逼,也是对外面世界诱惑的想象。即使在天堑变通途的今天,也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在那山川相阻、行步泛舟的时代,更是一个伟大的梦想。沿江而下,穿越江峡之阻,东出夔门,成为巴渝人们内心深处的欲念。巴渝先民是这样,途经此地的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范成大也有同感。巴渝先民东出夔门的历险,多个体命运的蹇塞,成于外物与内心的应和。到了近现代,在邹容、杨沧白、刘伯承、陈毅和郭沫若那里,人生使命和境界已大为不同,出三峡已成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
如果不沿江东行,待守盆地就很难实现人生理想,只有冲出三峡,通向大海,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才能看到生活的希望。因此,重庆有关长江诗词曲赋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言说行走的艰难,慨叹行走的决心,思考着行走的去处。诗人们是一群在路上的梦想者。他们一路惊异于奇丽的山川景致、峡江风光,在猿声哀鸣中抒发远走他乡的惆怅,吟唱出华丽哀婉的三峡思绪,也在激荡的江涛中体会到人生前行的哲理,巫山十二峰不知见证过多少诗人的困惑与精神的成长。
因为江流湍急,因为江峡之险,诗人体验到“处处奇相敌,山山妙不重”,而非“西出阳关无故人”,更少“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的怆然凄凉。江峡虽险峻,青山却多情,神女添玄思,它们也慰藉着旅人寂寞的思乡之苦。由此,巴渝出夔门之诗,并不给人以蹇促逼仄之感,而是高天壮阔、人生天地宽的豁然开朗。诗人们表达自然山水的行旅之思,物以情观、天人合德而彰显出激越的生命意志,在对巴渝人文的历史感怀,追慕豪杰、赞誉先贤而体现出坚韧的人格意志。它们贯穿于历史,凸显于情怀,显现出既慷慨激昂又沉郁恢宏的诗风。山水涵深情,诗文蕴别意。重庆有关长江诗词的丰富书写,有“云从三峡起”“无风波浪狂”的自然感慨,有“不尽长江滚滚来”“江水东流万里长”的豪迈之气,更有“目穷千里大江流”的恢弘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