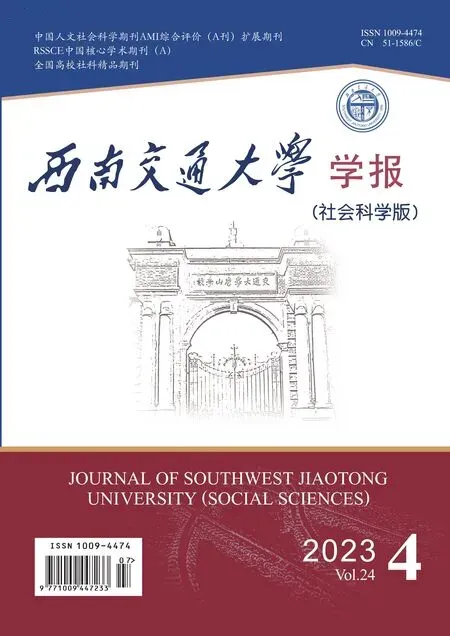新制度主义视野下的体育暴力研究
2023-08-28陈卓李丽芬
陈卓 李丽芬
摘 要: 体育中的暴力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为纠正人们对暴力过于简单化的认识,在回顾体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采用文献资料法、案例分析法,并运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方法,从权力、合法性和环境三个方面,围绕暴力与非暴力的关系、合法暴力与非法暴力的关系、赛场暴力与社会暴力的关系,发现:在权力方面,暴力与非暴力构成核心问题,主要体现为世俗社会对体育暴力的权力控制、体育运动中对暴力的权力控制、体育暴力内部的权力控制;在合法性方面,合法暴力与非法暴力构成核心问题,合法化的暴力具有戏剧性,非法暴力与惩罚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非法暴力行为可能通过合法化过程获得合法性;在环境方面,赛场暴力与社会暴力构成核心问题,场内暴力是运动员与观众的表演互动,场外暴力反映了利益相关者们的诉求表达,社会暴力折射出大众传媒作用下的体育神话。总之,新制度主义视野下的体育暴力涉及到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二元互构,需要从系统的、动态的视角进行综合把握,体育暴力才有可能得到科学对待和有效治理。
关键词: 体育暴力;新制度主义;权力;合法性;制度环境
收稿日期: 2022-12-11
基金项目: 2022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研究课题“高校思政课灌输—启发式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2GXSZ059YBM);2022年度浙江省高等教育研究课题“大学生个体认同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研究”(KT2022076);2022年度浙江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品德三维结构说在研究生现代人格培育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YJG-Z202205)
作者简介: 陈 卓,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德育原理与教育社会学研究,E-mail:chenzhuo321123@163.com;李丽芬,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暴力可谓无处不在,日常生活中也随时可能遇到程度不一、形式各异的暴力事件。暴力在真实生活情境中表现为恐惧、愤怒、激动等情感的交织,这些方式往往与正常情境中的传统道德背道而驰。与其他人类活动方式相比,体育与暴力的关系更为密切。关于体育与暴力的关系,在中西学术界有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命题:体育究竟是降低了暴力,还是增加了暴力?由此进一步引发出的问题是:体育对暴力的控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它又是如何起作用的?最近30年来,我国体育暴力研究热点包括球场观众暴力、运动员攻击行为、足球流氓、球迷骚乱和越轨行为;演进脉络从体育暴力的概念界定、分类等理论研究过渡到对球场观众暴力、运动员攻击行为、足球流氓等问题成因、影响因素及应对措施等方面的研究,进而细化到对体育暴力历史起源、法律规制等具体问题的研究〔1〕。一方面,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许多问题进入关注视野并进一步清晰起来;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更为宏观和抽象视角,往往容易导致“一叶障目”,从而在“体育究竟是降低了暴力,还是增加了暴力”这一经典命题的解释方面仍难取得实质性突破。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将体育置于一个更大的环境(场域)中,分析体育场域中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及其各种复杂的组合,在研究正式规则、程序、规范的同时,也重视为行动者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等。这些正是新制度主义所强调的〔2〕。在新制度主义看来,暴力的起源、形式以及后果是多种多样的,体育场域是一个复杂系统,体育中的暴力具有自身的特性,它融合了暴力与非暴力、合法暴力与非法暴力、赛场暴力与社会暴力等多方面要素。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体育中的暴力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利于从更为宏观和抽象的层面进一步澄清体育场域中与暴力相关的权力、合法性和环境等问题,进而引起体育场域内外诸多方面的重视,从而推动体育改革,有效控制暴力。
需要说明的是,“暴力,首先是身体暴力,是未经他人同意而对他人身体的袭击。‘首先的意思是,我们对非身体的暴力的想象也以身体的暴力为准……对心理的暴力来说,身体的暴力还是参考值,比较标准以这个参考值为准,隐喻从这个参考值中获得其说服力”〔3〕。所以这里所说的体育“暴力”,主要是指身体暴力,至于与之相关的心理暴力、冷暴力、“潜在的暴力”〔4〕等则不在讨论范围之列。
一、权力:暴力与非暴力
权力与暴力都是社会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与前者相比,暴力问题仍然很模糊。阿伦特(H.Arendt)认为:“暴力几乎没有被看成一种独立的现象……如果我们看看关于权力现象汗牛充栋的文献,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发觉,人们之所以没有重视暴力问题,是因为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人士都一致认为,权力与暴力都是一回事儿,也就是说,暴力不过是权力最明显的体现。”〔5〕实际上,权力与暴力关系密切,但又存在显著差别:权力并非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权力可以用暴力或者不用暴力被争取到;权力可以短期地不用暴力或者仅仅用暴力得到维护。但是,从长远角度看,权力不仅通过暴力得到维护,而且與实施暴力这种能力联系在一起〔3〕。新制度主义反对传统意义上的单向、强制型的权力观,强调制度产生和运作过程中权力的层次性和非对称性。诚如费埃德伯格(E.Friedberg)所主张的:“摒弃纯粹否定性的权力观,在不平等交换以及冲突性合作过程的背景之中置换否定性的权力观——不平等交换与冲突性合作,是构成所有集体行动的经纬结构要素。”〔6〕这要求研究者深入到组织场域的各个层面,对权力的来源及其运行方式进行细致地分析。具体到体育中的暴力问题,主要涉及到以下三个层面:世俗社会对体育暴力的权力控制,体育运动中对暴力的权力控制,体育暴力内部的权力控制。这三个方面分别涉及到权力在体育暴力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表现。
(一)世俗社会对体育暴力的权力控制
从传统意义上看,体育和战争紧密相连。古代西方体育中的斯巴达军事体育、角力、拳击、摔跤、击剑、骑士比武等體育项目表现出体育的本真性暴力〔7〕。暴力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并非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是一种价值取向。在古希腊人的道德评判体系中,暴力在更多情况下是披着强权、强力、强势身体的物质外衣〔8〕。时至今日,有些教练仍要求运动员为了团队的利益要甘冒受伤的风险,并常常引用战争的语言和道德规范。这从体育版上常用的话术中可见一斑,例如“海盗队消灭(destroy)爱国者队”“老鹰队埋葬(bury)巨人队”“76人队击败(blow out)网队”“杜克大学队闪电击败(blitzes)维克森林校队”“佛罗里达大学队淹没(swamp)密西西比州立大学队”“俄克拉荷马大学枪杀(guns down)德克萨斯大学长角牛队”等等。运动员给队友的最高评价就是说:“他是一个你想与之并肩战斗的人。”〔9〕在当下中国体育新闻报道中,暴力渲染也随处可见。不少媒体将体育描绘成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捕杀、人类社会你死我活的战争,无论对象是体育人物还是比赛本身,都涂抹上浓厚的暴力色彩。如“仇人相见刺刀见红”“德意志血洗英格兰”“高丽战车碾过巴林”“仅割越南鱼腩三刀”“10分钟玩死阿曼”“森林狼加时‘咬死国王”等等〔10〕。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也无论是什么样的民族和文化,一旦离开了暴力,体育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在很大程度上,暴力是体育活动中获得权力的重要途径。
鉴于此,统治精英阶层对平民大众娱乐消费的关注便成为一种常态,其背后体现的正是世俗社会对体育暴力的权力控制。伊莱亚斯(N.Elias)和邓宁(E.Dunning)记述过爱德华三世(King Edward Ⅲ)在1365年向伦敦市治安官颁布的一项命令:节日中从事“休闲活动”(leisure)的“壮丁”(able bodied man)只允许使用弓、箭和其他经批准的武器参与对军事有益的“体育”活动;那些参加如掷石头、手球、足球这样“徒劳无益”的体育活动的人将承受“监禁之苦”。并不是所有的当局都采取这样严厉的措施,但他们已认识到许可、限定及禁止受欢迎的消遣等行为具有高度的政治属性〔11〕。詹姆斯一世(King James Ⅰ)和查尔斯一世(King Charles Ⅰ)将《论体育》(Book of Sports,这里是在娱乐消遣的最广泛意义上使用“体育”一词的)记入法律,允许“周日礼拜时间之外进行某些受欢迎的消遣”。这一立法受与清教徒进行权力斗争的启发,对他们来说:“若体育活动是服务于一个合理的目的,即作为增强身体技能所必需的消遣,则是可以被接受的;但若是作为不可控的冲动的无意识的表现手段,就值得被怀疑;而如果它成为一种纯粹的享乐,或唤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不理性的赌博本能的手段,那当然就该被严厉谴责”〔12〕。1859年,早期的现代泛希腊运动会上,一群人冲到雅典街头,堵住道路,不让运动员通过,最后警察强行出动为选手们开路,结果踩伤了几十名观众,赛事中夹杂了灾难、嘈杂和混乱,成了一个教训,类似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19世纪,人们基本上是在集市、宴会、丰收日和宗教节日这样的场合举行像拳击、摔跤、足球、赛马以及斗鸡等这些比较有组织性的比赛〔13〕。他们经常遭遇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宗教力量的仇恨或道德关注,滥饮、赌博、暴力、性乱这些被主导力量憎恶的淫荡而具有破坏性的行为,经常伴着这些“原始体育”(proto-sports)比赛而发生。
(二)体育运动中对暴力的权力控制
与其他活动相比,体育具有更为典型的两面性:它既是一个规则明确的领域,暴力带有表演的性质并受到控制,又是一个极易引起隐蔽的愤怒的领域〔14〕。在古老的竞技运动中,对暴力的限制经历了一个漫长而重要的历史发展过程,主要体现在逐渐控制竞技动作、逐渐控制竞技中的冲动。大多数研究都承认运动中允许兴奋和冲动,但同时又必须克制和收敛这种冲动。身体的对抗释放出激情,然而社会主张抑制这种激情,准确地说就是竞技运动中的激情已经被定位,它必须保持在能够被容忍的状态下。换言之,体育运动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于暴力的权力控制过程。16世纪以来的长矛比武,既保留了激烈的搏斗,又不允许真枪实战;既允许冲动,又克制冲动;既具有暴力色彩,又将暴力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就是古老竞技运动史体现出的两个极点。从旧制度时期的竞技运动过渡到现代体育,首先是比赛得到了更为集中的全国性管理,出现了体育联合会制度以及内部民主、等级鲜明的行政管理。其次,制定和实施了一定的规则,大家主动承认和接受了它们。赛场上,明枪暗箭的报复、以牙还牙和放荡不羁的行为大大减少,其影响力也大为减弱。实际上,从竞技运动发展到体育,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随着体育事业的进步,控制暴力行为的努力不断取得成效。
今天体育文化所体现出诸多特征:胜利时刻的狂喜、自己支持的队伍获胜时的盲目自豪感以及从高度兴奋到暴力冲动的人类最原始的情感,这些特征几乎每一样都会让禁欲主义者和极端理性主义者们感到不安。体育可以被看作对社会秩序背离的一个重要征兆和部分原因,这种秩序是建立在对身体抗衡冲动的压抑,以及通过既接受这样的消遣又对其推销并从中“获利”而获得快乐的基础之上的。当代“狂欢”的成分可能已经变化了,但体育依然是社会空间的控制者与被控制者进行斗争的重要场域〔15〕。与过去相比,今天的体育暴力似乎更加猖獗,现场发生的比赛暴力、战术暴力、直接对抗暴力,特别是动作暴力,远比过去强烈和粗暴。而现代体育的初衷恰恰与此相反,正是为了遏制暴力,因而在暴力行为方面加强了控制,特别是加强了监督。与古老的运动相比,现代体育采取了逐渐减少和避免攻击行为的措施,它延续和模仿了古老的运动,但方式几乎是象征性的,用规则进行了约束和改变,研究者认为这是暴力消失后的一种补偿形式:现代体育把追求“危险”的快乐和原始野蛮的幻觉建立在回避危险和野蛮的基础上,在表面的直接对抗和抑制阻挡冲动之间进行了复杂的调剂。正像一份分析报告指出的那样:“生活变得不再危险丛生,但也变得更为乏味。面对这种变化,体育应运而生,成为一项非凡的社会创举。它抛弃了很多危险的身体接触所带来的快感,但同时也保留了一部分战斗的快乐。”〔14〕体育既抑制了暴力又给人以使用暴力的幻觉,它几乎始终对危险动作进行着控制,成为一种想象与现实相结合的运动。
(三)体育暴力内部的权力控制
进一步深入下去可以发现,体育中的暴力系统内部同样体现出权力控制的特点。一方面,体育中的暴力分布与社會中的阶层分布呈现对应关系。经济收入较低的阶层通常会选择像拳击、摔跤、举重、赛车、保龄球、美式台球以及摩托车赛等项目,其中大部分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暴力性和不确定性,且需要力量及胆识〔9〕。与之相对,高尔夫球、网球、排球、游泳、滑雪、马术、舞蹈和田径等体育项目中很少或完全没有暴力出现,它们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受到受过良好教育和经济条件好的参与者们的青睐,这些人对待暴力的态度与工人阶级是截然不同的〔9〕。实际上,受到一种确定的社会训练的所有行动者共同拥有一整套基本的认识模式,从互相对立的形容词组合中获得一个客观化的开端,这些组合通常用来划分和形容差别最大的实践领域内的人或物。这些区隔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施行,是因为整个社会秩序都在支持它们。对立的网络是以统治者(“精英”)与被统治者(“大众”)之间的对立为原则的,大众是偶然的和混乱的、可互换的和数不清的、软弱的和无能为力的大多数,只有统计学上的存在,这些对立存在于高(或崇高、高级、纯粹)与低(或平庸、平淡、卑微)之间,精神与物质之间,细腻(或精致、优雅)与粗俗(或粗糙、肥胖、粗野、粗暴、粗鲁)之间,轻(或敏捷、轻快、灵活)与重(或缓慢、笨重、迟钝、艰难、笨拙)之间,自由与被迫之间,宽广与狭隘之间,或在另外一种维度上,在独一无二(或稀罕、不同、高雅、唯一、特别、独特、异常)与平庸(或无名、平凡、中等)之间〔16〕。
另一方面,体育中的暴力折射出社会阶层的伦理观和审美情趣。这一点与新制度主义对文化—认知性制度要素的关注是一致的:“关注制度的文化—认知性维度,是社会学与组织研究的新制度主义最显著的特征。”〔17〕布尔迪厄(P.Bourdieu)以橄榄球为例进行了分析。橄榄球集中了大球(或小球)游戏和格斗的民众特征,它拿身体本身当赌注并且准许对身体暴力的一种(有部分节制的)表达和对“自然的”体质(力量、速度等)的一种直接利用,因此它与典型的民众配置有关,这些配置包括崇拜男子气概和喜欢争斗、不惧怕“接触”、耐得住疲劳和痛苦、有团结意识(“伙伴”)和节日意识(“第三个下半场”)等。虽然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橄榄球被注入一种美学—伦理学的内容,尤其是来自统治阶层的成员以及有意无意地表达这些成员价值的知识分子,这种注入有时会导致人们从事这种运动。对坚韧品质的追求、对男性美德的崇拜——尽管这种崇拜有时夹杂着对暴力和角斗的一种唯美主义态度——导致把初级球员的深层配置提到话语的层面。而这些球员几乎不大擅长言语表达和理论化,在教练、经理和一部分记者的教导下,他们具备了原始的和服从的力量(“好小子”)、驯服于被赞颂的民众力量(克己、忠于集体等)。但贵族主义的重新阐释在传统上依靠与中卫的战术相关的“勇敢”价值,使它在现代橄榄球的现实中显示了它的局限性,现代橄榄球在比赛和训练技术的合理化、球员的社会招收和观众扩大化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给予前锋的战术以主导地位,人们越来越以最隐晦的工业劳动(“干苦差事”)或短兵相接(“有责任感的人”)这类语言谈论这种前锋的战术〔18〕。
二、合法性:合法暴力与非法暴力
新制度主义区分了组织的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技术环境是这样一些环境,在其中组织的一种产品和服务得以生产并在一个市场中进行交换,这样的组织因为对其生产系统实施有效且充分的控制而获得回报。制度环境是那些以具有完善的规则和要求(如果其中的个体组织要想获得支持和合法性就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和要求)为特征的环境〔19〕。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组织的要求常常是不一致的:前者要求效率,后者常常要求组织耗费资源去满足合法性。体育中的暴力同样面临着合法性的问题。本雅明(W.Benjamin)批判了所谓“神圣的暴力”,他要人们区分合法的暴力与非法的暴力〔20〕。有些暴力是体育本身的一部分,如拳击手会互相殴打,橄榄球运动员会尽可能用暴力阻挠对手,冰球运动员会发生身体冲撞。在比赛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运动员也常常会发生受伤事件,这些规则范围内的暴力被称为“运动暴力”,通常情况下它都会令比赛终止。这其中也有重合的部分,有些场上暴力似乎也在规则承认的范围之内;对犯规、不必要的冲撞和规则之外的打斗也都会有相应的惩罚。这一切构成了一个连续的光谱,柯林斯(R.Collins)将它们概括为:(1)合法化的暴力,(2)犯规,(3)阻挠比赛继续进行的打斗。情况(1)属于合法暴力,情况(2)和(3)属于非法暴力〔21〕。沿着这一光谱,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合法化的暴力具有戏剧性,非法暴力与惩罚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非法暴力行为可能通过合法化过程获得合法性。这三者在逻辑上处于一种不断深化、逐级递进的关系。
(一)合法化的暴力具有戏剧性
暴力源于人类的天性,“一部文明史也就是人类同自己的暴力倾向作斗争的历史”〔22〕,斗争的成果之一就是一定意义上的暴力合法化。一种文明形式通过它用以定义暴力地带的方式和方法形成自己的特色:暴力地带是这样的一些领域,在其中暴力是被禁止的、被允许的或者是必要的,或者这些可能性有规则地被联系起来。任何关于暴力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都必须从这个社会事实出发,因为任何对暴力的谈论都是在或多或少被认为不言而喻的“地带”或者被承认的合法地位范畴的背景下进行的。可以说,任何对暴力合法地位的确立或解除,都涉及(被允许的、被禁止的、必要的)暴力有前提的、专门的地带,无论是为了改变暴力,还是为了根据现实的问题探讨和巩固暴力〔3〕。暴力的合法性是一切研究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逻辑起点。谈论文明问题时是这样,讨论体育问题时同样如此。人们常用“男子气概”来解释运动暴力,它在社会文化中被理解为攻击性或支配性,在生理特征上则被理解为过量分泌的睾丸素或是结实的肌肉,不管从哪个角度理解,这些体育暴力都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在新制度主义看来,运动暴力的这种“天然”合法性实际上来源于一种戏剧化的作用,其核心是制度的文化—认知性要素。合法化的暴力是具有戏剧性的暴力,正因为如此,观看虚构或人造的暴力有时会令人愉悦,但观看真正的暴力(例如播放关于屠杀或暴力伤害的格外真实的影片)却不然。体育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戏剧冲突,它通过竞争生产兴奋和娱乐。体育比赛中自发产生的细节是无法预测的,但是,能够发生的事情是被预先规定的程序所设计好的。比赛是所有冲突中最具有舞台性的,之所以选择这种形式,是因为它能够产生戏剧性。人们制定并修改规则,用来将行动控制在特定的形式中,这些决定通常是为了让比赛产生更多的戏剧性,如在棒球比赛中,投手丘高度降低,好球区缩小,都是为了让运动员更容易打中;足球比赛中引入了越位规则;篮球则加入了三分球,并缩小了防守方能够阻挡篮板的区域。体育是真实的生活,这愈发引人入胜,但人们对这种真实生活进行了最大可能的人工组织与控制;体育超越了真实的生活,其冲突形式更加纯粹,更加集中,因而也就比普通事件戏剧性更强,从而也令人更加满足〔21〕。从这个意义上说,体育奠基于现实社会而又超越现实之上构建了一种神话,这种神话自成一体,将一部分暴力戏剧化,从而使其具备了合法性。
(二)非法暴力与惩罚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
新制度主义主张把研究重点放在不同层次运行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上,以及对利益结果的影响上〔17〕。就非法暴力与惩罚的关系而言,过去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完善惩罚手段和降低非法暴力行为的发生概率,现在则首先关注两者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非法暴力是惩罚的对象,无论是犯规还是打斗都是如此。首先,对于犯规行为中的暴力,人们往往采取修改规则这样的做法,以防止失控的暴力。橄榄球中对不必要的暴力会进行惩罚,例如:从身后攻击对手,或是攻击对方膝盖等脆弱的身体部位;攻击四分卫等特别脆弱或非暴力的选手;阻挠一名尚未接到球的接球手或传球防守队员等。对暴力行为的犯规惩罚措施程度不一,但都会降低犯规方获胜的机会。然而,由于双方都可能发生犯规(对暴力行为的犯规惩罚与越位等普通的犯规惩罚并无不同),这些处罚有可能彼此平衡,所有球员并没有动力去避免暴力犯规。其次,严重的打架斗殴与正常的预料范围之内的犯规行为,其处罚方式是一样的。这些处罚(例如在禁闭区待上几分钟)会影响球队获胜的机会,因此被纳入了进攻和防守策略中(在对方接受处罚而缺乏忍耐时可以采用“高压攻势”,但对方也有策略能够应对“高压攻势”)。因此,冰球的处罚方式包括:普通犯规会被罚下场两分钟;格外粗鲁的动作则会被罚下场四分钟;如果球员的打斗持续了10~20秒以上,裁判就会上来拉开他们,他们也会被赶出赛场,但因双方通常都会被赶出去,而且替补也是允许的,所以这不会为一支队伍创造太大的优势。
另一方面,非法暴力具有仪式性,导致惩罚本身也成为一种策略。首先,就犯规行为而言,在体育这个充满危机与竞争的舞台上,优秀的运动员与队伍都对犯规十分娴熟。在比赛的主要内容之外,时刻伴随着受控的暴力。在篮球比赛中,暴力犯规会导致罚球,虽然罚球得分率很高,在关键时刻也很重要,但通常却并不足以形成足够的优势来奠定胜局。双方被罚球的频率都很高,导致罚球成为常规比赛和策略的一部分,比赛中的一系列行为虽然违反规则,但都在意料之中。犯规处罚等于容许了一种受到保护的暴力形式,所有参与者都心照不宣。正是处罚令暴力成为可能:通过将暴力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运动员克服了冲突性紧张和恐惧。其次,打斗行为也遵循同样的逻辑。柯林斯从微观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棒球比赛中的打斗行为,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一小群愤怒的挑事者实施仪式性的报复和自卫;与他们密切相关的队友带着一定程度的愤怒参与进来,但也是为了控制前者;其他球员集体冲上前来,就像是一场身体碰撞的巨型仪式,混合了团结与敌意。在这些混战中,球员很少会受伤。最危险的武器(球棒)在打斗中几乎从来不会被用到,而是在打斗開始前就被丢下了〔21〕。
(三)非法暴力行为可能通过合法化过程获得合法性
新制度主义反对决定论,主张互构论,主张组织场域的制度环境是片段化的,并且充满了冲突。因为组织有着不同的属性和占据着场域中不同的位置,所以那些制度影响远非是统一的或一致的〔17〕。这样就打破了合法暴力与非法暴力之间的壁垒,为考察后者向前者的转化提供了可能。实际上,合法性不仅仅是合法暴力的诉求,而且也是非法暴力的追求目标,在“使自己合法化”这一方面两者是一致的。不管怎样,即使频繁的温和犯规行为已经被制度化,其本身也无法预测运动员暴力的严重程度。“在人们扩展被允许的暴力或者必要的暴力的领域的地方,有某种事物作为手段进入视线中,以前人们并没有忽视这种事物,而是根本没有把它当成手段考虑。”〔3〕一旦现实的需要被体育场域中的行动者意识到,这些手段就会被发现并被应用。首先,就犯规行为而言,正常比赛与犯规之间的界线部分在于运动员对比赛的意识,运动员会分辨合理的犯规和愚蠢的犯规。合理犯规不仅服务于比赛本身,而且足够富有攻击性,能够恰当地传达出争夺支配权的信息。“小动作”则让人瞧不起,因为它们不够暴力。冰球运动员这样描述道:“要想吓唬一个人,你就得让他吃点苦头,小动作是不行的,勾人犯规、绊人、抱人这种事太廉价了。好的犯规是冲撞过去,前提是你能撞到对方,而他也知道你会撞到他。如果你绊倒他,他既不会受伤,甚至也不会烦心,那他根本不会在意。绊人很愚蠢,唯一需要绊人的时候就是他在你身后或是你错失了球而击中了他的脚。这也很愚蠢,因为在那些情况下你都没好好打球。这意味着对方已经击败了你,你得让他慢下来,才能勾到或抱住他。如果你一开始就能吓到他,他就根本不会出现在这一位置上。”〔23〕
其次,就打斗行为而言,冰球、橄榄球和篮球都有将超出规则的暴力合法化的倾向,冰球经常发生打斗,橄榄球次之,篮球则不常发生运动员之间的打斗。除此之外,棒球并没有太多将暴力犯规合法化的规则(相比之下它对打斗有着相对严重的处罚,例如被罚下场,有时还附带罚款和禁赛,在这一点上与足球相似),却也经常发生某种特定的打斗。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打斗爆发时运动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保护。冰球运动员身穿层层护具,包括头盔和手套等。尽管他们携带了可以当作武器的球杆,但却几乎从来不会在打斗中使用——虽然勾人或举杆过肩都可能引发打斗。通常情况下,在冰球比赛爆发的打斗中,球员会丢掉球杆,并戴着手套互相殴打。这些装备既能保护他们,也能限制他们对另一方造成伤害。此外,打斗者往往很快就会被其他球员包围起来,这些人会彼此推搡,但通常都会限制打斗者的活动范围,令他们难以施展拳脚。穿着冰鞋的打斗者很难踢到对方,也没法像拳击比赛一样大打出手。可以说,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则规定非法暴力的合法性,但它们却在体育现实的合法化过程中走得很远。在理论上,判断非法暴力与合法暴力,具有一定程度上清晰明确、可操作化的标准,但在实践领域,两者之间的界限时常变得非常模糊,以至于有的老师在劝阻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时,干脆使用“野蛮人的游戏”这样笼统的称呼。
三、环境:赛场暴力与社会暴力
新制度主义强调“组织场域”这一概念,主张从以组织为研究中心走向以场域层次为研究中心〔17〕。“场域概念表明一种组织共同体的存在,这些组织具有一种共同的意义系统,而共同体的参与者彼此之间,比起与场域之外的行动者来更频繁地互动,并且这种互动对于场域内的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更为重要。”〔24〕体育场域包含了体育比赛现场以及现场以外的环境,甚至辐射到整个社会。在新制度主义看来,如果仅仅关注运动员在体育比赛现场的表现,就无法了解整个体育场域的复杂结构和真正的运作逻辑。我们需要研究体育比赛的场内暴力,同时也需要研究场外暴力;我们需要关注运动员,同时也需要关注观众和更为广阔的社会。更重要的是,上述几组关系是彼此联系、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因此需要用系統的、动态的眼光来审视他们。具体而言,可以遵循从小到大的逻辑,按照从场内暴力到场外暴力再到社会暴力的逻辑,依次分析运动员与观众的表演互动、利益相关者们的诉求表达和大众传媒作用下的体育神话。
(一)场内暴力:运动员与观众的表演互动
在媒体技术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为什么还愿意花钱去体育现场观看比赛?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只有在比赛现场才可能有运动员与观众的互动表演。“体育及体育自身与它们的氛围是分不开的:体育体验并不能轻易地屈服于将‘体育从‘与体育有关的体验的总体性中区分出来……另外,这些体育的体验……已使自己被混合了,因此它们彼此借用、相互映照。”〔25〕体育及其体验以这样的方式变得难以区分,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界限相应地也被打破了。如果想充分分享体育比赛,就需要实时经历那些扣人心弦的瞬间,仅仅是观看录像或是从新闻中得知结果,则意味着错失了绝大部分情绪体验:离开了紧张感的累积,也就不会有胜利时的狂喜;失败时的失望也是人们为了体验这些时刻而愿意付出的代价;更有甚者,这是一种集体情绪体验——正是周边的回响与观众们互相浸润的姿态,令支持其中一方的体验变得更加有趣,哪怕最后并未取胜,而最终胜利的时刻更是会成为铭记一生的记忆。这就是为何在一场众人翘首以盼的比赛发生时,观众们会挤满整个运动场,哪怕座位很糟糕,哪怕在电视上明明能看到更好的视角,他们依然会选择去现场观战。所谓球迷体验,并不是仅仅看到比赛而已,而是那种戏剧性的情绪被现场有着同样爱好的众人所放大的感受〔21〕,与其说这是一场体育比赛,不如说它是一种互动表演。
在互动表演过程中,运动员与观众之间的纽带能否建立起来,取决于人们能否怀着深深的感情、带着一种风格与分寸感,来共同欣赏一场毫无瑕疵的仪式。在体育竞赛中,表现和展示构成了一个主要因素,它提醒人们去注意游戏、仪式和戏剧间原先所存在的联系。参赛者不仅仅是在竞争,他们还在表演着一种强调共同价值观的仪式。仪式需要见证人,需要通晓表演规则与内在含义的热情的观众。观众观看比赛不仅不会破坏体育的价值,而且能使体育比赛更趋完善〔26〕。合法化的暴力不仅不会破坏双方的关系,反而是加深双方感情的润滑剂。观众与运动员面对着同样的戏剧节奏,事实上,正是因为能够体会到集体紧张感,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情绪并将其转化为集体兴奋和团结感,人们才会愿意去现场观看比赛。因此,观众与运动员在同一时刻陷入打斗也并不奇怪,这一点在不同的体育项目中都成立。观众暴力有几种形式:(1)观众冲到场内,或是从远处向运动员投掷物品;(2)观众跟运动员打起来,尽管这很罕见;(3)观众在比赛中互相打起来。心理学测试表明,在观看橄榄球和冰球比赛后,球迷们的好战性会增强,但在观看健身或游泳比赛后却不会如此〔27〕。球迷们会跟随特定比赛中所产生的情感波动,而恰到好处的暴力就是对比赛的延伸,只有当暴力被认为是故意的时,球迷们才会变得富有攻击性。如果受伤被认为是一个意外,球迷就不会表现出攻击性,也许还会反过来为受伤的对方球员鼓掌〔21〕。
(二)场外暴力:利益相关者们的诉求表达
体育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很多方面,最主要的两类当属运动员和观众,场外暴力是他们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方式。就运动员的场外暴力而言,这种暴力是否由场内暴力引起目前尚无明确结论。常识告诉我们,人们如果习惯了在体育中使用身体威胁和暴力,那么在体育以外的事情上,他们也会很自然地在面对冲突时做出同样的举动。运动员很容易被人冠以“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之类的形容词,这是一个社会现实。在感到自己的男子汉尊严被挑战时,运动员可能很难不出手进行报复。然而,运动员一旦出手反击,也很可能被认为是过去在体育之外养成的文化修养问题。引起暴力的可能不是体育运动,导致运动员选择暴力性体育的是运动员的修养或本性。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年轻男性喜欢用体育来证明他们的男子汉气概,任何对其男子气概的挑衅都会让他们起身反抗,否则他们会在同伴面前颜面扫地。根据美国的调查数据,运动员所犯的罪行多数是家庭暴力。几乎在每一个案件中,家庭暴力都是关于从事暴力性体育项目的男性运动员虐待他们的妻子或女友的事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辛普森杀妻案〔9〕。但是,从总体数量上看,大多数在赛场上有暴力行为的运动员在场下并没有继续暴力行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我们一定能够从法庭记录和新闻媒体有所了解。但目前的研究还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还没有掌握运动员家庭暴力案件的全部数据。除非暴力行为发生的过于频繁或超出人们的控制范围,否则多数家庭都不愿意将其公开,而多数女性也不想就此提出控诉。
就观众的场外暴力而言,有几种观众暴力可能始于运动场或与比赛相关,但最后却外溢为场外暴力,并发展出独立的路线。这包括政治暴力、胜利与失败骚乱等〔21〕。2013年6月27日凌晨,巴西在联合会杯半决赛中2-1战胜乌拉圭。球场内成为欢乐的海洋;球场外不远的地方却是另一番景象,愤怒的民众们继续走上街头,高举着“反对世界杯”“反对奥运会”的标语和真枪实弹的警察对峙。足球从来都标榜与政治无关,但在当时的巴西,联合会杯却成为了一个民众向外诉说的平台,写满了无奈。“民众不到被逼无奈之时,根本没有必要上街要求更好的交通、卫生、教育和安全服务,因为这些要求应该都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他们反对的不是世界杯球赛本身,而是被权钱腐化的世界杯〔28〕。这次巴西骚乱是一场政治骚乱,也是一场较为少见的胜利骚乱,因为体育的胜利反衬出政治的失败,因而没有带来庆祝反而招致抗议。在现实社会中,由于体育神话的意识形态功能,人们更多看到的胜利骚乱往往与庆祝暴力相伴生,这是狂欢暴力的一种形式。胜利骚乱可能与失败骚乱具有同样的破坏力,而且胜利骚乱要常见得多。胜利骚乱严重时有可能会发展到攻击权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缺乏传统的受到限制的庆祝方式。缺乏制度化的场所来让人们温和地享受破坏性的“道德假期”,正是导致暴力升级的原因之一;大众传媒格外关注运动员自己的庆祝,这也是原因之一。后者正是我们接下来要分析的内容。
(三)社会暴力:大众传媒作用下的体育神话
在现代社会,经由电视“景观化”(spectacularization)的体育以及明显增长的体育观众数量,都成为组成体育文本自身欲望的一部分,它们与体育的惯例、调停和体验纠缠在一起。很多时候,体育已经成为一种表演,所有表演都包含双重意识,经由此,实际执行的动作被置于该动作潜在的、理想的或记忆中的原始模式的精神比较之中。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比较是由动作的观察者做出的,不过最核心的并不是外部观察,而是双重意识。“一个运动员可能会意识到他(或她)自己的表演,将它与其心理上的标准相对比。对某些人来说表演永远是表演,某些观众即便是当(间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自己就处于表演中时,也将其识别和确认为表演。”〔29〕在体育场域,通过大众传媒的力量,表演者的这种双重意识在一個相当广泛的范围内被再现。拥有多重机会看到自己、看到自己正被看、看到违背某些常规标准做某事,这类似于福柯(M.Foucault)所分析的那种人类主体的监视与规训。它们不仅适用于专业运动员,也适用于体育的各方利益相关者,从教练和营销商到电视评论员和导演,再到赞助商和粉丝,概莫能外。正如段义孚(Yi-Fu Tan)所说,在体育场内,虽有明确的空间和角色“界限……观众会全身心地参与他们尽可能参与的活动”〔30〕,当我们通过媒介将体育场域的概念延展到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和街头的时候,我们可能“全是参赛者”(Players All),并且经常渴望变成媒介体育文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人们总是把与日俱增的观众暴力归咎于现代体育的暴力性及对比赛的过分认真的态度,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观众暴力的盛行来自他们对待体育的不够认真,因为他们不尊重规则和习俗,这些规则和习俗既应约束观众,也应约束比赛者。对幻想的攻击既来自运动员与组织者,也来自观众。运动员急于表现出自己是个娱乐工作者(一部分目的是使他无愧于自己的高薪),就否认体育的严肃性。组织者鼓动体育迷们成为狂热的党徒,即便是在诸如网球这样一些原先以礼仪为准则的运动项目中,情况也是如此。电视制造出一批留在家里的新观众,并使“现场”观众成了参与者,他们拼命争着进入摄像镜头,挥舞旗帜时不是为了评论比赛场地上的活动,而是为了吸引摄像机的注意。优势体育迷们会做出更冲动的举动使自己闯入比赛,比如冲入比赛场地或者在一次重要的胜利后捣毁体育馆,这类越轨行为不断地出现,损害了体育比赛所制造的幻觉。打破规则就等于打破了魔力。参赛者与观众之间界线的消除就像剧院中演员与观众之间界线的消除一样,阻止了人们暂时中止怀疑,并因此破坏了有组织的体育运动的代表性价值〔26〕。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体育形成了一种现代媒体包装下的体育神话,甚至可能催生出一种新形式下的体育狂欢。在《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中,波兹曼(N.Postman)总结道:“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31〕波兹曼特别提醒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不要遗忘了赫胥黎的警告,就体育中的暴力而言,我们不要忽视了大众传媒作用下的体育神话,让暴力披上合法化的外衣表演出一幕幕滑稽戏。
四、结语
体育中的暴力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关于暴力的产生、性质及影响,以及暴力与权力、合法性和环境的关系,本文目前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初步的雏形。在新制度主义视角下,体育暴力呈现为一个多角度、多面向、综合化、立体化的系统,暴力与体育的关系更为全面地展现出来。体育场域中的暴力与非暴力问题、合法暴力与非法暴力问题、赛场暴力与社会暴力问题也逐渐清晰起来。首先,体育中的暴力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在其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是权力。从表面上看,基于身体的此在性、不可化约性,与其他社会活动相比,体育看起来似乎更为公开透明。但是,体育场域中的身体不仅具有自然属性,同时还具有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32〕。围绕暴力与非暴力,仍然可以看到世俗社会对体育暴力的权力控制、体育运动中对暴力的权力控制、体育暴力内部的权力控制。协调体育与暴力之间的关系,需要发挥制度建设在体育改革中的积极作用,正确处理与权力的关系,划清合法暴力与非法暴力之间的界限,通过制度建设消除体育场域中的非法暴力,这是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其次,新制度主义视野下的体育暴力研究,强调制度的合法性,重视制度的文化—认知性要素。合法暴力与非法暴力的界限从理论上看是明晰的,但在现实的体育活动中,通过社会整体价值观的灌输—启发双向运作机制,非法暴力有可能转化为合法暴力。在现代社会,体育活动中的人并不是机器和工具,而是具有独立人格、自由个性和理性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只有建立在个体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制度的文化—认知性要素的积极作用,让每一个体育场域中的行动者都能对体育暴力形成科学全面的认识,并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旦裁判和教练的脑袋里对上述暴力问题有了清楚的认识,暴力行为发生时,处罚就会容易裁定。犯规者会立即被禁赛或处以罚款,但对于多数运动员来说,被禁赛的效果更好。允许暴力的教练和队伍也会被处罚,直到他们意识到这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风险。最后,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环境的重要作用,体育场域中的暴力不仅仅涉及到运动员和裁判员,它也是整个社会的组成部分,牵一发而动全身。体育对暴力的控制并非如人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可以迁移到运动之外,体育中的暴力正日益被其他利益所挟持,不应夸大体育对暴力的干预作用,其对暴力控制带有明显的局限性〔33〕。在现实中,一旦与更为宽泛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有些人就会更不愿参与讨论体育暴力问题。然而,职业体育必须明白减少暴力是符合它们自身利益的,他们必须成为反对暴力斗争中的领导者,而不能对此袖手旁观。社会也应当着手解决暴力问题,体育中的暴力行为可能会成为新闻头条,但是暴力行为同样存在于商界、职场和教育领域中。如果在处理暴力问题时综合考虑经济、政治、文化或教育缺失等问题,源自体育场域的反社会行为的发生几率就会大大降低。
参考文献:
〔1〕石 岩,高 桢.我国体育暴力研究热点、演进脉络及发展趋势〔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7,(6):1.
〔2〕陈 卓.新制度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大学校际体育竞赛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6,(8):94-101.
〔3〕雷姆茨玛.信任与暴力:试论现代一种特殊的局面〔M〕.赵蕾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05,165,213,226.
〔4〕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84.
〔5〕Arendt,Hannah.Macht und Gewalt〔M〕.München:Piper,1970:36.
〔6〕费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M〕.张 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93.
〔7〕张洪安.古代西方体育的本真性暴力及其“去暴力化”〔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5,(1):46.
〔8〕于 华.古希腊竞技体育中暴力因素的文化学解读〔J〕.体育学刊,2011,(5):43.
〔9〕伍 兹.体育运动中的社会学问题〔M〕.田 慧,译.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1:279,218,279,281.
〔10〕朱才威.体育报道须剔除暴力语言〔J〕.新闻战线,2014,(4):108.
〔11〕Elias,N, E.Dunning.Folk Football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Britain〔C〕∥N.Elias, E.Dunning.Quest for Excitement: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sing Process.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176.
〔12〕Weber,M.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M〕.London:Unwin University Books,1930:167.
〔13〕Clarke. J, C.Critcher.The Devil Makes Work:Leisure in Capitalist Britain〔M〕.London:Macmillan,1985:53.
〔14〕维加雷洛.体育神话是如何炼成的〔M〕.乔咪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48,146.
〔15〕大卫·罗.体育、文化与媒介:不羁的三位一体〔M〕.吕 鹏,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8.
〔16〕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下册)〔M〕.刘 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741.
〔17〕斯科特.制度與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M〕.姚 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65,222,223,224.
〔18〕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册)〔M〕.刘 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29-330.
〔19〕斯科特,迈耶.社会组织部门化:系列命题与初步论证〔C〕∥鲍威尔,迪马吉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姚 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33.
〔20〕Benjamin,Walter.Reflections:Essays,Aphorisms,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M〕.New York:Schocken Books,1978:277-300.
〔21〕柯林斯.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M〕.刘 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02,299-300,306-309,300-301,324-325,327-331.
〔22〕陈嘉放,邓 鹏.文明与暴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前言”9.
〔23〕Faulkner,Robert F.Making Violence by Doing Work:Selves,Situations,and the World of Professional Hockey〔C〕∥Daniel M.Landers.Social Problems in Athletics: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Sport.Urbana,Il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6:99.
〔24〕Scott,W Richard.Conceptualizing Organizational Fields:Link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al Systems〔C〕∥Hans-Ulrich Derlien,Uta Gerhardt,Fritz W.Scharpf.Systemrationalitat und Partialinteresse.Baden-Baden: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1994:207-208.
〔25〕Rinehart,R.E.Players All:Performances in Contemporary Sport〔M〕.Bloomington,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8:7.
〔26〕拉什.自恋主义文化:心理危机时代的美国生活〔M〕.陈红雯,吕 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97-98,102.
〔27〕Arms,Robert L.,Gordon W.Russell,Mark Sandilands.Effects on the Hostility of Spectators of Viewing Aggressive Sports〔J〕.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1979,(43):275-279.
〔28〕许 可.巴西骚乱:反世界杯 更反腐化〔EB/OL〕.(2016-09-26)〔2022-04-20〕.http://sports.qq.com/inside/37.htm.
〔29〕Carlson,M.Performance:A Critical Introduction〔M〕.London:Routledge,1996:5-6.
〔30〕Tan,Y-F.Space and Context〔C〕∥R.Schechner, W.Appel.By Means of Performance:Intercultural Studies of Theatre and Ritual.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243.
〔31〕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 艳,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185.
〔32〕陈 卓.体育场域中的身体:自然、社会与文化属性〔J〕.社会科学论坛,2018,(5):196-213.
〔33〕刘 龙.体育与暴力关系的研究争议与辨析〔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7,(5):20.
Research on Sports Viol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CHEN Zhuo, LI Lifen
Abstract: The sports violence is an important and complex topic. Based on reviewing the process of sports development, the paper is about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sports violence in terms of its origin, forms, characters and influences, to correct peoples oversimplified thinking of violence. The research is conducted with literature data, case analyses and the theory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iolence and non-violence, between legal violence and illegal violence, and between violence in competition and that in socie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violence and non-violence constitute the core subject which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power control over sports violence from the society, the power control of sports violence in activities, and the power control within the sports violence it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itimacy, legal violence and illegal violence is the core subject that legal violence can be dramatically changed, that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illegal violence and punishment, and that illegal violence may become legal through the process of leg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violence in competition and that in society is the core subject. Violence in the court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layers and audience, violence out of the court reflects the expression of demands of stakeholders, while violence in society reflects the sports myths in current media effect. In short, sports viol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involves the binary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which needs to be comprehensively grasped from a systematic and dynamic perspective in order for sports violence to be scientifically treated and effectively managed.
Key words: sports violenc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wer; legitimacy;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責任编辑:陈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