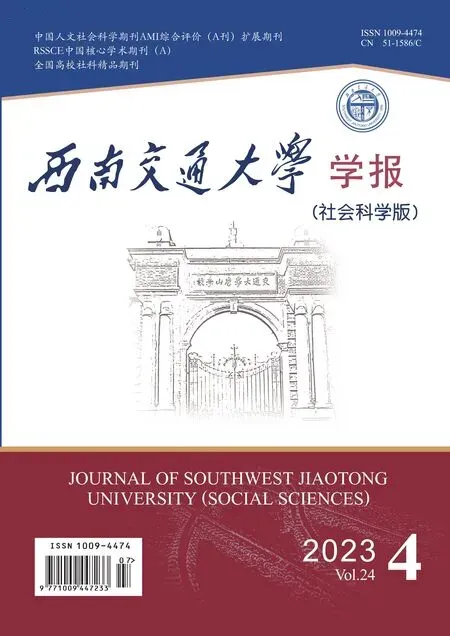道器之间:近代思想视野下的铁路、中国与世界(1875—1936)
2023-08-28叶舒宋桂杰
叶舒 宋桂杰
摘 要: 在近代铁路思想的演进中,既包括对铁路筹划、主权、债务以及建设等具体内容的探索,也包含对“道体器用”“物质与精神”等精神指导思想的讨论。从道器关系的角度看,中国近代铁路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等人从“器用”的角度阐述修筑铁路带来的利益,认为存在“道体”统一其上;甲午海战后,随着铁路主权论与瓜分中国论的出现,康有为等人对洋务派思想产生质疑,统一的“道体”分裂为中国与西方两部分;五四运动后,铁路作为西方物质文明的产物,被梁漱溟、李大钊等人拿来与东方精神文明进行对比,由此展开的物质与精神之争使得西方的“道体”衍化为追求“科学精神”的欧美道路以及探索革命与改造思想的苏俄道路,铁路也由此成为承载科学精神、社会主义的重要载体。
关键词: 中国铁路史;道;器;洋务派;维新派;革命党人;欧美道路;苏俄道路
收稿日期: 2022-08-29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代江苏铁路转运业研究”(2022SJYB2129)
作者简介: 叶 舒,扬州大学苏中发展研究院讲师、中国大运河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与中国铁路史的研究,E-mail:3031710084@qq.com;宋桂杰,扬州大学苏中发展研究院教授、长江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道器之间”,语出朱熹《答黄道夫》:“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1〕,朱子还说过:“然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尝离乎器,道亦只是器之理”〔2〕。這两句话看似矛盾,实则均是对《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3〕的衍生性阐释道与器,用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易经》中的全文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上即形体以上,即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体以下(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形体本身)是有形的,即器。。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器物、知识与观念的传入,中国人对“道”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王国维就指出:“臣窃观自一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4〕。基于王国维“道出于二”所谓“道出于二”,是指近代中国人的指导思想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思想讲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亦或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但在近代西方思想观念传入中国并对国人产生深刻影响之后,国人的指导思想出现中与西、新与旧之间相互碰撞、杂糅的情况。此即王国维所谓的“道出于二”。的论述,学术界围绕近代中国“道”的变化、道器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详见罗志田《近代中国“道”的转化》(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由器变道:补论近代中国的“天变”》(《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8期),《道出于三:西方在中国的再次分裂及其影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李欣然《道器与文明:郭嵩焘和晚清“趋西”风潮的形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8期),等等。。
古语有云:“器以载道”,器物是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是“道”在物质形态方面的表现。铁路作为西方工业革命的代表性器物,自19世纪末被引进至中国后,影响了近代中国思想的发展。目前学术界关于近代铁路思想的研究较为丰富如朱从兵《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朱从兵《严复铁路思想初探》,载黄瑞霖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年;王志勇《论梁启超的铁路利权思想》,《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第2期;朱从兵《一个言官的尴尬——赵炳麟的铁路筹建思想与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4期;朱从兵《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事业的艰难起步》,北京:群言出版社,2006年;苏全有《论杨度铁路思想的理性特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马陵合《借款可以救国?——郑孝胥铁路外债观述评》,《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朱从兵《晚清宫廷的思想动态与铁路兴办(1865-1889)》,《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3期;王昉、张铎《民国时期铁路规制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基于1912-1937年中华全国铁路协会刊物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1期;黄庆林《论岑春煊的铁路建设思想及其限度》,《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等等。,关涉到相关人物对于铁路筹划、主权、债务以及建设等方面的认识等内容,但梳理、总结近代铁路思想中物质与精神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殆仅见此,本文拟在梳理近代铁路思想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不同阶层对中国与世界的认识,揭示铁路思想中物质与精神部分的内在关联。
一、道体器用:铁路与洋务运动时期“富强”说的生成
19世纪70年代末,清廷内部展开了是否修建铁路的争论,李鸿章、薛福成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与王韬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都阐述了修筑铁路给西方国家与中国所带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铁路的修筑确实促进了西方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实力的发展,但也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压力与胁迫。中国需仿行西方国家的做法,在境内自主修筑铁路,以此实现富强。这本质上是在“道体器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所提出的一套经世致用的救国理论。
李鸿章等洋务派认为修筑铁路是西方富强的秘诀之一,他们将铁路、轮船、电报等实用性的器物“空间化”所谓器的“空间化”,根据罗志田先生的说法,是指王韬、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对于西方科技产物(例如铁路、轮船、电报等)在西方与中国的应用与影响(即器物在不同空间的应用问题)的认识。在此,罗志田先生认为在道的“空间化”之前,还存在器的“空间化”。,主要从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层面论证其给西方国家带来的益处。例如1876年晚清著名政治家、洋务派代表人物丁日昌1876年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就指出:“日本前本弱国,自设轮路、电线、开矿、练兵、制器后,今乃雄踞东方”〔5〕。再如1881年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与醇亲王奕譞来往的函件中也肯定铁路促进了西方各国军事实力的提升李鸿章的原话为:“五十年前,西洋诸国尚无铁路,迄今纵横交错,为路至数十万里。其铁路与军实之多少,彼此若势均力敌,遇有争端,不轻发难,而和局即可长保,势使然也”。。在社会经济层面,他们认为铁路促进了西方国家商旅贸易的发展。1878年,近代外交家、洋务派代表人物薛福成在《创开中国铁路议》中指出美国开通铁路促进了当地商业贸易、社会经济的发展,“即如美邦新造,四千年前尚无铁路,今通计国中六通四达为路至二十一万里。凡垦新城辟荒地,无不设铁路以导其先;迨户口多而贸易盛,又必增铁路以善其后”〔6〕。19世纪90年代,清末实业家、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在《铁路篇》中也认为西伯利亚铁路的开通促进了俄国商业贸易的发展郑观应的原话为:“俄国所筑西卑里亚(西伯利亚)之铁路,不日可成……有此铁路,不遇二十日可到。就通商而论,其地贯欧、亚洲之北境,将来各国行旅,多出其途,俄人即可坐收其利”。。
当然,李鸿章等人在论述铁路给西方国家带来变化的同时,也注重分析修筑铁路涉及的国际关系问题。1880年,薛福成在《代李伯相议请试办铁路疏》中就论述了日本、俄国在边境修建铁路对中国边防造成的威胁:“即如日本以区区小国,在其境内营造铁路,自谓师西洋长技,辄有藐视中国之心。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恰克图等处,又欲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中国与俄接壤万数千里,向使早得铁路数条,则就现有兵力,尽敷调遣,如无铁路,则虽增兵增饷,实属防不胜防”〔6〕。同年,洋务派骨干之一、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奏请清廷筹造铁路事宜时,也论述了日、俄两国在中国边境修筑铁路的举措给中国带来的压力与威胁刘铭传的原话为“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铁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非畏我兵力,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将不测。日本一弹丸国耳,其君臣师西洋之长技,恃有铁路,动逞螳螂之臂,藐视中华,亦遇事与我为难”。。
面对西方国家在中国边境修筑铁路的举措,他们给出的应对之策主要包括两个:一是中国应牢牢掌握修建铁路的主动权。1875年,近代启蒙思想家、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王韬认为一旦中国自造铁路,对中国有觊觎之心的国家就会有所忌惮:“火轮铁路,电气通标,亦无不自我而为之。凡泰西诸国之所眈眈注视,跃跃欲试者,一旦我尽举而次第行之,伸彼无所觊觎艳羡其间,此强中以驭外之法也”〔7〕。另一個对策是将西方的富强之道“移植”到中国。薛福成就提出中国要仿行西方修筑铁路的方法,以此作为实现中国的富强之道:“今泰西诸国,竞富争强,其兴勃焉,所恃者火轮舟车耳……是故,中国而仿行铁路,则遐者可迩,滞者可通,费者可省,散者可聚”〔6〕。
当然,他们不仅关注铁路筹划、主权、债务以及建设等方面的内容,也在思考“道体器用”“中体西用”等理论问题。李鸿章在《妥议铁路事宜折》中就认为轮船、铁路等既能促进中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符合天地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迩者中国仿造轮船,亦颇渐收其益。盖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朴而精,风尚由分而合,此天地自然之大势,非智力所能强遏也”〔8〕。薛福成在《创开中国铁路议》中也指出西方诸国修筑铁路实现富强的做法符合天地自然发展的大势:“迄于今日,泰西诸国,研精器数,创为火轮舟车,环地球九万里,无阻不通。盖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朴而精,风气由分而合。天地之大势,固如此也”〔6〕。
这实质上是在“道体器用”的框架下提出的“中体西用”理论。正如王韬在《杞忧生易言跋》中所说,“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舟车、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焉。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9〕。虽然这一时期有人注意到西方也存在道,并且指出西方之道与东方之道的异与同例如1877年郭嵩焘在出使英国时期所写的日记中就指出,“往册所载,国家有道,得以兼并无道之国。自古皆然,如英人兼并印度,人多言其过。吾意不然,印度无道,英人以道御之,而土地民人被其泽者多矣,此亦天地自然之理也”。再如王韬在《原道》中也指出,除了中国有圣人之道外,西方、印度等国也皆有其道。“耶稣教则近乎儒者也,天主教则近乎佛者也,自余参儒、佛而杂出者也。顾沿其流犹必溯其源,穷其端犹必竟其委,则吾得而决之曰,天下之道,其其始也由同而异,其终也由异而同”。,但在“道体器用”“中体西用”的思想框架下,多数人仍然强调“道出于一”。正如王韬在《原道》中所说:“天下之道,一而已,夫岂有二哉?……天下之道,其始也由同而异,其终也由异而同……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10〕。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人们围绕是否修筑、如何修筑以及修筑铁路后对中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等问题,大致在中国传统的“道体器用”的框架之下提出了一套“中体西用”的方法。“中体”与“道体”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道”是唯一、绝对的本体,是超越性的最高实在。在儒学体系中,“天道”“仁道”“天理”均是表征本体的术语。因此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道”即为本体。近代以降,西方的科技、经济以及制度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冲击。对此,洋务派提出了一套“中体西用”的理论。“中体”,即主张以中国传统思想(包括“道”)为本源,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为应用。,既包括李鸿章与薛福成所认为的“天地自然之大势”,也包括王韬提出的“道则备自当躬”。它根源于中国的传统观念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一些著作当中已出现“天地之势”“天地自然之大势”之类的词语。如南宋程公许的《试阁职策问》就说:“然王公设险以守其国,素具于习坎之彖辞,而重门击柝以待暴客,黄帝、尧、舜已有取乎豫备之义。则因险以为守,固天地之然之势,而事以制变,亦有国者之所不可忽者乎?”清代王萦绪在《八卦阵论》中也指出:“即河图之数,合而为十,五、十居中,田与阵则分其四面阴阳之数,为四阵四隅耳。比皆天地自然之势,圣贤当然之理,非别有神奇不测之术也”。,可以对器进行总结与指导。在李鸿章等洋务派人士看来,“西用”与“器用”则是指能给中国带来富强的铁路。
二、“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铁路与甲午—辛亥时期危机意识的出现
甲午海战后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开始意识到虽然修筑铁路促进了西方世界的繁荣如1895年6月30日,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指出:“美人铁路如铁钢丝,五里十里,纵横午贯,而富甲大地”。再如梁启超在《瓜分危言》中也认为铁路的修筑对提升国家力量有重要作用:“俄国势力所以未充者。一由于西伯利亚之铁路,工程浩大,久而难成。二由于东方未得不冰口岸。苟得此二者,则俄之力已将奋飞矣”。,但只会造成“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维新派代表人物、保皇党领袖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就认为铁路的开通反而导致土耳其国力的式微:“土耳其为回教大国……于是俄割其黑海,波斯割其科托……六大国君废其君而柄其政,为之开议院,筑铁路,于是土不国矣”〔11〕。另一位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论湘粤铁路之益》中更是发出“今日之世界,铁路之世界也。有铁路则存,无则亡;多铁路则强,寡则弱”〔12〕的感慨。可见,他们不仅观察到铁路给西方强国带来的富强,也注意到铁路对世界弱国衰败产生的作用。
维新派关于铁路与世界关系认识的变化,与西方强国进一步侵蚀中国领土密切相关。由于中国存在被西方国家瓜分的危险,激发了杨度、梁启超等人对国家危亡与主权问题的思考,由此出现了铁路主权论与瓜分中国论。1899年,近代启蒙思想家、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瓜分危言》中指出:“故质言之,则铁路割地之快刀也(英俄协商,亦以铁路权为题目,盖名为占认铁路,实则瓜分土地也)”,“要之,欧人于中国认定一语为宗旨,曰铁路之所及,即权限之所及,故争之不遗余力焉。就中国而言,则铁路所及之地,即为主权已失之地”〔13〕。1905年,清末“宪政专家”、维新派代表人物杨度在《粤汉铁路议》中也指出:“近得美国留学生秘密消息,谓美政府因俄国提议瓜分中国,美政府自筹。此时铁路尚未修成,运兵不便,故暂主保全中国领土。俟铁路成后,再行瓜分。则此路之危尚复何等!”〔14〕并呼吁:“夫粤汉铁路之关系,归于外人之结果,可使湘粤鄂三省为东三省之续。故不争废合同,则中国危亡。若谓争废合同,致生外交之困难,为足危亡中国者,此大误之说也”〔14〕。
与此同时,面对西方国家运用铁路侵蚀中国主权、瓜分中国的做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洋务派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出于对国家危亡与主权问题的担忧,他们开始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的辩证关系,其对于“中体”与“道体”、“西用”与“器用”的认识均发生重要转变。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他在该书中从国家主义的思路出发,指出李鸿章学习西方修筑铁路、希望以此实现中国富强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15〕。
在梁启超看來,甲午海战后,中国人已从学习西方的器物、技艺逐步转变为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铁路的重要性也因此逐步让位于兴民权、设议院等政治举措。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也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船坚炮利”,与他所提倡的“立科以励智学”的变法措施紧密相关:“近者英之得印度、缅甸,俄之得西伯利至珲春,法之得越,皆筑铁路以逼我三陲矣……人皆惊洋人气象之强,制造之奇,而推所自来,皆由立爵赏以劝智学为之”〔16〕。
在“器用”发生变化的同时,维新派对“道体”的认识也跟着产生转变。一方面,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注意到在西方“船舰利炮”的器物之上,还有更为根源性的事物存在。另一方面,他们杂糅了中学、西学的部分概念,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最早发生转变的是谭嗣同,他在《报贝元征书》中,一方面指出李鸿章等人所举办的兴修铁路等事宜并未触及到根本;另一方面,对于洋务与变法之间的关系,他形象地用道器关系进行阐述,认为器既然已经发生变化,道也要跟着产生转变:
来语:“将讲洋务之术尚未精,必变法以图治欤?抑中国圣人之道固有未可尽弃者欤?”……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哉……中国数十年来,何尝有洋务哉?抑岂有一士大夫能讲者?能讲洋务,即又无今日之事。足下所谓洋务:第就所见之轮船已耳,电线已耳,火车已耳,枪炮、水雷及织布、炼铁诸机器已耳。于其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固宜足下之云尔。凡此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17〕。
1903年,近代著名翻译家、教育家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否定了陆九渊、王阳明关于“格致无益事功”的思想,在明确了西学格致之道及其与陆王心学的不同之处后,他认为虽然修筑铁路的确是富国强兵的必要之举,但须先了解器物背后的西学格致之道:
惟是申陆、王二氏之说,谓格致无益事功,抑事功不俟格致,则大不可。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然而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救之之道,非造铁道用机器不为功;而造铁道用机器,又非明西学格致必不可。是则一言富国阜民,则先后始终之间,必皆有事于西学,然则其事又曷可须臾缓哉!〔18〕
在道被“分解”成中国、西方之际根据罗志田先生的叙述,至少对古代中国士子而言,“道”是普适于天下即全人类的。近代以降,洋务派、维新派人士发现既然西方自有其“道”,则中国的“道”也就成为时人心目中“道”的一个部分了。可以说,随着“西学”在近代中国的确立,传统的“道”便正式被空间化了,即被分解成中国与西方两个部分。,时人开始将中国与西方的相关概念进行杂糅。例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与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佛家的极乐世界思想相结合,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理论;并且认为铁路具有冲破时空阻碍、使不同区域的交流更加密切的特点,可以作为实现大同世界的具体手段〔19〕。谭嗣同在《仁学》中将中国古代仁的思想与西方的以太、电气等科学概念相杂糅,提出了仁学的概念;并在讨论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威胁中国主权的现实问题时,认为可以通过修筑欧亚大铁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从而体现仁学以及仁政的思想:“若虑俄国之扰也,则先修欧亚两洲东西大铁路……且夫弭将废之兵端,保五洲之太平,仁政也”〔20〕。
虽然该时期洋务派所倡导的“中体西用”说在清末思想界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1〕,但从谭嗣同、康有為以及严复等人的论述中不难发现他们已开始突破原先的“道体器用”“中体西用”思想。在“道出于二”的过程中,一方面,他们对于原先的“中体”产生质疑;另一方面,他们仍相信“器用”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方法,谭嗣同的“器体道用”谭嗣同的原话为:“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的序言中指出,“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然……故方今竞新之势,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者死”。均是如此。这也体现了在清末西学浪潮的冲击下道器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三、道器再变:铁路与民国思想界的新变化
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关于铁路的认知发生了新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第一,更为理性地看待铁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认为它不仅给西欧带来富强,也见证了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第二,认为铁路是西方物质文明的产物,且西方物质文明与东方精神文明差异较大;第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些人开始注意到修筑铁路对社会主义国家所产生的影响。
民国成立后,社会各界对于铁路在西方国家作用的认知出现了新变化。原先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造成的影响后,改变先前的观点,宣告“科学万能论”的破产。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铁路推动西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距,在欧洲国家引发了铁路罢工:“科学逾昌,工厂逾多,社会遍枯亦逾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我们留欧一年,这罢工风潮,看见的听见的每月总有几次。其中最大的,如九月间英国铁路罢工,那里是两个团体竞争,简直就是两个敌国交战……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22〕。
与梁启超思想的转变几乎同时,以胡适与李大钊等人为代表、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学人也开始对中西文化进行归类与比较,并积极探索西方文明背后的精神问题。1928年,近代著名教育家钟鲁斋在《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中指出以铁路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崇尚物质与科技,铁路即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外在表现,并认为西方物质文化与东方精神文化存在较大差异:
在性质说来,就是中国文化是偏于精神的文化。西方文化,偏于物质的文化……所谓东方式的文化,都是精神的,更显而易见呢。西洋人则注重物质……自从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用之开矿,用之工场,酿成十九世纪的工业大革命来。什么史提芬之火车,毕尔之电信,麦柯尼之无线电信等等。弄到欧美的世界,是物质世界〔23〕。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论述了以铁路为载体的西方物质文明对中国产生的重要影响,认为中国要跟上世界潮流,必须改变原先的文化观念李大钊的原话为:“吾侪日常生活中之一举一动,几莫能逃其范围,而实际上亦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例如火车轮船之不能不乘,电灯电话之不能不用,个性自由之不能不要求,代议政治之不能不采行。凡此种种,要足以证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滔滔,殆不可遏……余既言之,物质的生活,今日万不能屏绝勿用。则吾人之所以除此矛盾者,亦惟以彻底之觉悟,将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扫荡,期与彼西洋之动的世界观相接近,与物质的生活相适应”。。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认为以铁路为代表的西方物质文明与中国传统生活差异太大,主张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要看到其背后所具有的科学精神:“所以我们东方人看西方东西,那异点便刺目而来……譬如最初惹人注目的枪炮、铁甲舰、望远镜、显微镜、轮船、火车、电报、电话、电灯……就是样样东西都带着征服自然的威风,为我们所不及。举凡一切物质方面的事物,无不如此……西方既秉科学的精神,当然产生无数无边的学问。中国既秉艺术的精神,当然产不出一门(模)一样的学问来”〔24〕。中国现代思想家与哲学家、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虽然非常反感将东西文明进行简单的归类与对比,但也认为以往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仅是触及到以铁路为代表的表浅层面,尚未深究器物背后的精神问题:“今日最有毒的妖言,莫如说西洋的文明是物质的、唯物的,而东方的文明是精神的……西洋近代文明,千头万绪,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尽,就是用人的智慧来征服自然界的困难。空间的困难,有汽船、火车、电车等等工具来征服他们……我们只看见那表现人的智力的物质的器械,而看不见那物质的器械所表示的精神”〔25〕。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开始关注铁路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情况。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中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除去一大部分的有土农夫,凡大资本的企业,铁路矿山、轮船公司、承办运输事业、大规模的制造工业、大商店,收归国有,在人民会议代表人支配下,照常办理”〔26〕。此外,一些报刊杂志也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铁路建设问题。1933年,刊载在《东方杂志》的《苏联工业建设现状》通过铁路建设状况观察到苏联的工业化路径:“在当时苏联的经济是建筑在两块方向不同的基石上:社会主义性的大工业、铁路、矿穴等等,与商品资本主义性的农村经济”〔27〕。
以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目睹帝国主义与军阀混战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压迫后,主张运用阶级分析法团结铁路工人。陈独秀在《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实行》中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将铁路作为掠夺中国的武器,与军阀阶级共同奴役工人群体;共产党要团结无产阶级进行罢工运动,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阶级陈的原话为“我们要明白外国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的武器,第一是关税,第二就是铁路了……如唐山罢工是反对英人与杨以德,陇海罢工是反对洋管理,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是反对曹锟吴佩孚……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故劳工运动首先反对帝国主义;同时在国内的政治机关,也不得不反对军阀阶级,合这两种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阶级——便是国民运动”。。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我们看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28〕。
可见,时人对于学习西方方面的认识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学人在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討论中,认为应当学习欧美国家的“科学精神”;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则转向学习马列主义与苏俄模式。对“道”的认识在经历了前一历史时期的裂变后,大体形成中国与西方两部分。而随着民国时期思想界出现新变化,国人对于西方的道也有新发现,进一步分裂为欧美与苏俄两部分关于“道”在民国时期特别是在北伐前后所产生的新变化,罗志田先生在《道出于三:西方在中国的再次分裂及其影响》中有详细的论述。参阅罗志田《道出于三:西方在中国的再次分裂及其影响》,刊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从西方物质文明中引申而来的“科学精神”,就是“道”在民国时期的“变体”。1932年,著名化学家蒋明谦的《西方文化的侵入与中国的反应》在回顾以往探索救国道路的基础上,提出物质与精神之争与道、器之争的本质不谋而合:“第三期自1895至1918,外患为丧失铁路矿山等权及划分势力范围。中国至是始放弃整军从武,而整兴实业,改革政治制度……即至到了现在,还有许多人还在鄙夷西方文明为‘物质文明,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文明,与三、四十年前所谓‘东方尚道,西方尚艺的思想完全同一鼻孔出气”〔29〕。梁启超也认为传统中国重道轻器的做法,使得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非常容易忽视其中的科学精神梁启超的原话为:“我们几千年来的信条,都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一类话。多数人以为:科学无论如何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我大胆说一句话: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两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科学精神是什么?我姑从最广义解释:‘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
随着国人对西方文明认识的逐渐深入,他们日益意识到精神文明并非东方所独有。正如著名文学家林语堂在《机器与精神》中所说,“物质文明并非西洋所独有,精神文明也非东方的奇货……因为有机器文明的人,未必就没有精神文明,我们知道这句所谓机器文明的话,还是五十年前中国人心理中的一件事。那时的中国人只看见西洋人火车、轮船、电报、枪炮等显而易见的文明,故谓之机器文明”〔30〕。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现代民族运动之总动向》中认为当时讨论的“工业化”问题既涉及铁路、机器以及工厂等物质文明,也包含五四时期时人所强调的精神文明:
我们这样说,似乎有与清末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的说法相同了。他们都是主张要铁路、机器、工厂的。张之洞在武昌曾举办了许多新式工厂,最近行将通车的粤汉铁路,是在张之洞时就着手修筑了的……后来到了“五四运动”,有人以为不惟西洋物质文明我们该学,并且非先学其精神文明不可……今日照我们说的“工业化”,是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也有,而以物质为根据。如有了某一种的物质文明,则某一种的精神文明不叫自来〔31〕。
另一方面,伴随着学人对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反思,以陈达材、阎一士为代表的、深受辛亥革命与北伐运动影响的政界人士开始从思想与文化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曾任黄埔军校秘书处秘书长的陈达材在《物质文明》中,分析了西方国家对于工人阶级的压迫并对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提出质疑:“工厂彻夜作工,火车、轮船通宵不息……物质文明进步之价值与私产制度殆成不可两立之势”〔32〕。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爱国人士阎一士在《社会主义与中国物质文明之关系》中认为铁路作为西方物质文明的产物,成为欧洲国家侵蚀中国主权的工具,由此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社会主义在欧洲,虽不始于资本集中时。然其旗帜鲜明,实基于此,碻系一般学者之定论。换言之,物质文明之程度愈高,社会家之呼号愈烈,以为劳动家耗竭汗血,均为缙绅做嫁衣裳……至若我国,凡多百仰给于外货……几段铁道,更是半主权,不称国家营业……而欧美社会家不平之声浪震到亚洲,我国人士苦于旧思想之缚束,闻此新奇,遂相与附和而揄扬之〔33〕。
社会主义的实现,不仅要靠团结无产阶级进行罢工运动,对他们进行思想、精神层面的改造也是非常必要的。正如陈独秀在致著名哲学家张东荪的信件中所说的那样,“只知开发物质文明,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即令各省都开矿筑路,也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34〕。此外,1920年刊载在《解放与改造》上的《物质生活上的改造方针》与《精神生活的改造》二文也指出要对包括铁路工人在内的无产阶级的物质生活进行改造〔35〕,但仅仅在物质上改造工人是远远不够的,也要用社会主义对他们的精神生活加以改造,因为“如果精神改造了,物质生活就不能维持现状,自然的要趋于改造。精神生活的改造,可以算是物质生活改造的花。物质生活的改造,可以算是精神生活改造的果”〔36〕。
四、结语
诚如胡适在《建国问题引论》中所说,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的各种救国运动,均是要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即“怎样解决中国的种种困难,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立脚,可以过安稳日子”〔37〕。无论是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等人所秉承的“道体器用”“中体西用”思想,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冯友兰等人对欧美文明与社会主义的认识,铁路一直是国人试图解决当时所面临问题的工具之一〔6〕。在近代中国铁路思想的发展历程中,既包括对铁路筹划、主权、债务以及建设等具体层面的内容的讨论,也包含关于“道体器用”“物质与精神”等思想问题的探索。
总体说来,国人对于“器用”(指如何运用有形的事物)的认识大致经历了“重视—质疑—重新审视”的变化。洋务运动时期,鉴于铁路在政治军事与社会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修筑铁路被认为是救国的重要手段。甲午海战后,虽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仍旧关注铁路的主权问题,但其在救国方面的重要性被兴民权、设议院所取代。五四运动后,铁路作为西方物质文明的产物,被梁漱溟、李大钊等人用来与东方文明做对比;另一方面,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也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修筑铁路的问题,并提出运用马克思主义团结铁路工人举行罢工运动。
与之相应,国人对于“道体”(指依据各种观念形成的指导思想)的主张则大致经历了“隐而不显—分裂—再分裂”的阶段。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等人认为在“器用”之上还存在“道体”进行统一指导,并认为“天下之道,一而已,夫岂有二哉”。甲午海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洋务派“器用”说的质疑,使统一其上的“道体”裂变为中国与西方两部分。五四运动后,胡适、李大钊等人在关于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争论中实质上又形成了对西方“道体”的新发现,即裂变为追寻“科學精神”的欧美道路以及改造思想的苏俄道路,铁路也由此成为承载科学精神、社会主义的重要载体。
参考文献:
〔1〕郭 齐,尹 波,点校.朱熹集(5)〔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2948.
〔2〕黎靖德,编.杨绳其,周娴君,校点.朱子语类(3)〔M〕.长沙:岳麓书社,2020:1768.
〔3〕梁国典,主编.易经〔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81-82.
〔4〕王国维.论政学梳〔C〕∥方 麟,选编.王国维文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741.
〔5〕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348.
〔6〕薛福成,著.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07,136,107-108,107.
〔7〕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0:393.
〔8〕李鸿章,著.李鸿章全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1553.
〔9〕任 清,编选.唐宋明清文集(2)〔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1903.
〔10〕王 韬.弢园文录外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2.
〔11〕康有为.康有为全集(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73.
〔12〕谭嗣同.论湘粤铁路之益〔J〕.湘报,1898,(19):73-74.
〔13〕哀时客.瓜分危言(再续前稿)〔J〕.清议报,1899,(17):1049-1052.
〔14〕杨 度.粤汉铁路议〔J〕.新民丛报,1905,(14):33-35.
〔15〕梁启超.李鸿章传〔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55.
〔16〕康有为.康有为全集(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70.
〔17〕谭嗣同,撰.何 执,编.谭嗣同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2:208-215.
〔18〕广 来,选编.近代名家名人文库——龚自珍·严复〔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42-145.
〔19〕康有为.大同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03.
〔20〕谭嗣同.清末民初文献丛刊·仁学〔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7:94-96.
〔21〕陈旭麓.论“中体西用”〔C〕∥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35-40.
〔2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7:12.
〔23〕钟鲁斋.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J〕.沪江大学月刊,1928,(13):8-9.
〔24〕梁漱溟,讲演.陈 政,罗常培,编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24.
〔25〕胡 适.我也来谈谈东西文化〔J〕.微音,1926,(27):10-12.
〔26〕李大钊.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C〕∥李大钊.守常文集.上海:北新书局,1950:198.
〔27〕志 远.苏联工业建设现状〔J〕.东方杂志,1933,(2):38-40.
〔28〕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C〕∥徐 辰,编.宪制道路与中国命运——中国近代宪法文献选编(1840-1949)(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175.
〔29〕蒋明谦.西方文化的侵入与中国的反应〔J〕.独立评论,1932,(22):16-18.
〔30〕天水,杨健,选编.林语堂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79-80.
〔31〕冯友兰.中国现代民族运动之总动向〔J〕.社会学界,1936,(9):259-260.
〔32〕陈达材.物质文明〔J〕.新潮,1919,(3):32-36.
〔33〕阎一士.社会主义与中国物质文明之关系〔J〕.太平洋,1922,(4):6-9.
〔34〕周月峰,编.新青年通信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624-625.
〔35〕周佛海.物质生活上的改造方针〔J〕.解放与改造,1920,(1):7.
〔36〕周佛海.精神生活的改造〔J〕.解放与改造,1920,(7):9-10.
〔37〕胡 适.建国问题引论〔C〕∥何卓恩,编.胡适文集·政治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30.
Between Dao and Qi: Railways, China and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Thoughts (1875—1936)
YE Shu, SONG Guijie
Abstract: I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railway thought, there have been discussions not only about the railway planning, sovereignty, debt and construction, but about the spiritual guiding ideology such as “Dao Ti Qi Yong (Principles as the essence and objects for the practice)” and “matter and spir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tween Dao and Qi,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railway thoughts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During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Li Hongzhang et al. expounded the benefits brought by railway construction from the angle of “Qi Yong”, and believed there was still a unity of “Dao Ti”. After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awareness of railway sovereignty and the threat of partitioning China, Kang Youwei and others questioned the thought of the Westernization Group. The unified thoughts of “Dao Ti” wer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Chinese thoughts and the Western thoughts.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railway, as a product of western material civilization, was compared with Easter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by Liang Shuming, Li Dazhao and oth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material and spirit made the western “Dao-Ti” thoughts evolve into the Europe-American way of pursuing “scientific spirit” and the Soviet-Russian path of exploring revolution and reforming ideology. The railway has thus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socialism.
Key words: China's railway history; Dao; Qi; Westernization Group; reformists; members of a revolutionary party; the Euro-American way; Soviet- Russian path
(責任编辑:武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