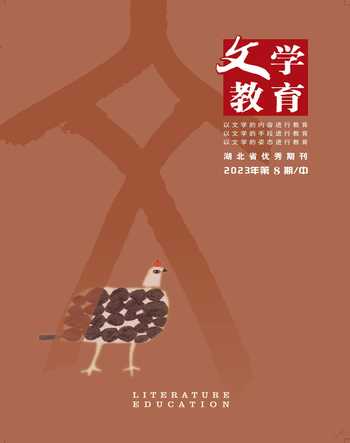辛格《旅游巴士》的多元文化与身份书写
2023-08-22李蕊
李蕊
内容摘要: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是美国当代犹太作家的杰出代表,被誉为“20世纪短篇小说大师”,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犹太性作为辛格写作的典型特征,不仅体现了他对于犹太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同时也传达了其对于犹太民族命运和前途的忧虑。本文从后殖民文化批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旅游巴士》中涉及的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对立冲突,旨在研究多元文化语境下犹太民族的身份困境及自我异化,探明他者视域下的犹太形象,挖掘辛格的犹太书写的深刻内涵,进而探寻犹太民族的生存之道,为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旅游巴士》 多元文化 身份认同 犹太性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是著名的美国犹太裔作家,被誉为20世纪“短篇小说大师”,推动了美国文学的发展。凭借充满激情的叙事艺术,辛格于197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植根于波兰犹太人的文化传统,生动描述了具有普世性的人类境况。尽管辛格一生中多数时间居住在美国,但他坚持使用意第绪语写作,借此“界定他的文化身份,同时使之成为连接他和波兰犹太社区生活的牢固纽带”(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2018:7)。辛格的作品以别具一格的叙事艺术洞察历史与现实,关切人类的普遍困境,不仅体现了他对于犹太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也传达出对于犹太民族命运和前途的忧虑。辛格的大多数小说描写东欧犹太人在二战前后的精神状态,披露纳粹集中营的创伤记忆对于犹太人生活的影响,他也影响了我国改革开放后一批作家的创作。
《旅游巴士》作为辛格后期的短篇小说作品,聚焦二战后犹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关注犹太性,凸显了其写作的典型主题——逃离与回归,揭示了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犹太人面临的身份危机与生存困境。《旅游巴士》讲述了美籍犹太作家“我”在一次为期12天的西班牙巴士之旅中的相关经历,“我”乘坐的旅游巴士规定游客每天都要换座位,由此“我”先后结识了维尔霍夫夫妇以及玛特伦母子。维尔霍夫夫人是二战集中营出来的难民,也是犹太人,为了嫁给丈夫,改信信教,但婚后并不幸福,婚姻濒临破裂;维尔霍夫先生是苏黎世的一家瑞士银行行长,外表绅士,具有典型的银行家气质,鉴于妻子的犹太身份,婚后开始关注犹太新闻,非常厌恶妻子;玛特伦夫人是亚美尼亚人,丈夫去世后,同儿子马克共同生活,物质富裕;马克年仅14岁,但处事颇具成人风范,精明干练,计划周详,想要移民美国。
一.文化他者与二元对立
“他者”和“自我”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他者的存在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先决条件,“他者的‘凝视促进了个人的自我形象的塑造”(张剑2011:120)。移情指“我们具有确认其他人正在想什么和感觉什么的能力,并且以适宜的感情回应他人的思想和感情”(Baron-Cohen 2011:11),这为解决不同民族间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的冲突对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小说中的旅游巴士作为公共交通工具,构建了一个流动的空间,为不同民族人群的聚合提供了可能,旅行的过程也是多元文化融合的过程,但不断出现的民族对立和文化冲突,致使巴士这个具有文化载体功能的临时命运共同体一步步走向幻灭,呈现二元对立的状态。小说中的二元对立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对立,第二种是犹太人内部的对立。
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矛盾焦点是维尔霍夫夫人,她是在非犹太世界中受压迫的犹太人代表,她与丈夫的对立冲突是小说故事发展的主线之一,主要通过叙述者“我”的描述展现。维尔霍夫夫人是小说中唯一经历过二战集中营迫害的犹太人,丈夫的不理解导致夫妇二人婚后冲突不断,她称丈夫为伪君子,指控所有人都是反犹太主义者,她痛恨她的丈夫,谴责其吝啬自私,最终在旅游途中遭受到丈夫的毒打后,决定与其决裂,登上火车,离开了这个移情脆弱的社群。维尔霍夫先生眼中的妻子言语恶毒,是一个购物狂,他对于犹太群体存在刻板的消极印象,在与“我”的交谈过程中,他提及了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话题:“一个民族在世界各国游荡了两千年,还可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然后又回到祖先的发源地,重操祖先的语言,这难道不奇怪吗?(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2018:570)”尽管读了很多有关犹太民族的书,但他“还是不清楚什么是犹太人的本质”(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2018:570)。个体间移情理解的障碍导致了两性关系的疏离,20世纪的人们在经历众多人性残酷的历史事件后,“对不幸人群表现出漠然、麻木而不是有意义的移情关切”(罗媛 2012:49),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维尔霍夫先生对于妻子的正常移情能力也遭受到文化冲突的腐蚀,这也就注定了他与妻子这段跨族婚姻终将以失败而告终。
维尔霍夫夫人和巴士上的其他乘客间也存在冲突,巴士每一次停留,她都会去大肆购物,故意错过巴士的集合时间,让一车人等候,而她却毫无歉意,这引起了其他乘客的不满,进而上升到了对犹太群体的不满与偏见,而“我”作为犹太人的一员,也被迫承担她的过错。人们认为是“集中营和流浪彻底摧毁了她的神经”(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2018:571),导致其性格的缺陷,但却忽视了二战后,以维尔霍夫夫人为代表的经历集中营迫害的犹太群体的心理需求。辛格笔下的“二战”犹太幸存者们大都“感情脆弱、多愁善感、感性多疑,而且还对生活悲观失望”(乔国强 2008:46),维尔霍夫夫人这一受创的女性形象揭露了集中营经历给人们带来的心灵与身体上的巨大伤害,人文关怀的缺失是维尔霍夫夫人最终选择登上火车的原因之一。通过对维尔霍夫夫人的描写,辛格试图唤醒人们对现实世界中更多有此经历的受害者给予关怀,打破二元对立的壁垒,倡导不同民族间多元文化的融合,跨越边界,“认可差异、包容差异、尊重差异和沟通协商将是在当前的后殖民语境中实现少数族理想所必经的第一步。(生安锋 2011:97)”
小说中不仅体现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揭露了犹太社群内部潜在的冲突与对立,“犹太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樣,并不是只有一个声音,一张面孔;受过迫害并不意味着获致美德,在有的情况下,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只一纸之隔”(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2018:14)。作为集中营的受害者,维尔霍夫夫人将身心的创伤、婚姻的不幸强加于“他者”,故意迟到,给其他乘客的旅行带来不便,加之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移情匮乏,导致对立冲突,其悲剧是一系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维尔霍夫夫人种种歇斯底里的表现体现了经历集中营迫害后人类表现出来的“移情脆弱性”(罗媛 2012:44),“多年的怨恨、伤害(通常是冲突的结果)会导致移情腐蚀,更持续的神经性因素也会导致移情腐蚀”(罗媛 2012:33),集中营的创伤是维尔霍夫夫人遭受移情腐蚀的开端,而婚后丈夫的指责则是致使其移情腐蚀进一步加深的神经性因素,持续的冲突使她逐渐关闭了对他者的移情能力,一步步走向施害者而非受害者,“受害者与迫害者的界限在移情被屏蔽后变得不再清晰”(罗媛2012:55),正如叙述者“我”所说,“夫人,您的所作所为对犹太人的伤害,超过所有反犹主义”(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2018:582)。“我”作为犹太人,却并不参与任何犹太宗教的活动,在旅行途中对维尔霍夫夫人的遭遇,一直保持旁观者的身份,缺失“视角换位”,局限于自我的信仰系统与认知模式,无法肯定与包容其身上异质性的存在,导致人际之间移情理解的不足,在被玛特伦夫人问及身份构成时,“我”却回答不上,陷入身份焦虑,而这也是造成“我”对维尔霍夫夫人移情匮乏的原因之一。而马克虽然拥有犹太血统,但并非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小说中对于马克的形象描述迎合了传统的犹太人形象,唯利是图、精于算计,千方百计撮合“我”和他的母亲,想让“我”成为他的继父,从而达成其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目的,而“我”对于马克的作为,持否定批判态度,他和他的母亲玛特伦夫人一样,对于维尔霍夫夫人的遭遇选择了漠视,以自我中心主义为导向,这些犹太人内部的冲突与不团结现象折射出二战后犹太民族的思想混乱和精神危机。
二.犹太性、逃离与回归
犹太性是犹太人特有的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是带有犹太民族情感和民族身份的意识和文化。而辛格作品中的“犹太性”主要是指“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与犹太文化或宗教相关联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心理机制以及任何能表现犹太人的生活、性格、语言、行为、场景等特点的东西”(乔国强2008:68)。犹太民族作为“少数族”(生安锋 2011:123),总是同“逃离”与“回归”的命运息息相关。
小说中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身上都体现出逃离意识,“我”想要逃离失恋带来的伤痛,逃离玛特伦母子的纠缠与控制,逃离因民族身份带来的困扰与不便;维尔霍夫夫人想要逃离集中营经历带来的身心创伤,逃离不幸的婚姻,逃离异化的社会;维尔霍夫先生想要逃离怨天尤人、总是令他蒙羞的妻子,逃离这段濒临破灭的跨族婚姻;玛特伦夫人想要逃离儿子的管控,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马克想要逃离身份的禁锢,逃离现有的生活,成为美国公民。小说的结尾写到“我”和维尔霍夫夫人在一辆驶向比亚里茨的火车上不期而遇,这暗示了犹太人的寻根理念以及回归传统的主题。犹太教作为犹太传统的重要部分,“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犹太人与生俱来的存在方式,二战后很多犹太人由于对上帝的怀疑与指责而失去信仰,然而他们发现自己与犹太教传统间的脐带是割不断的”(程雪芳 2012:139),正如维尔霍夫夫人那样,她为了婚姻幸福,改信新教,丧失了信仰,变成了精神上没有归宿的边缘人,犹太性逐渐衰退,这是对犹太传统文化的一种背弃,但最终在旅游途中与丈夫彻底决裂后,她决定“回去找犹太人的上帝”(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2018:583),同时她的丈夫也提及维尔霍夫夫人曾“试图与苏黎世的犹太团体建立联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2018:571),也曾去找拉比辩论宗教问题,这些细节表明维尔霍夫夫人从本质上无法隔断犹太民族的宗教传统,其犹太性的最终回归具有必然性,是对犹太传统文化的一种反思与恪守。
《旅游巴士》这部短篇小说蕴含辛格对犹太民族以及整个世界的深切思索,不仅反映了其尊重犹太文化传统、回归犹太民族本性的犹太伦理思想,同时也揭露了二战后犹太民族的身份焦虑及生存困境,这不仅是犹太民族的问题,也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其历史意义之厚重、社会意义之深刻耐人寻味。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现代犹太人需要珍视犹太身份,探明生存的意义。只有不同民族追求自我对陌生他者的移情与理解,借助“视角换位”理解他者眼中的世界,欣赏和尊重他者的认知视角,才能实现跨民族的融合,共同建构一种包罗万象、尊重差异、抵制压迫的文化。
参考文献
[1]Baron-Cohen, Simon. Zero Degrees of Empathy: A New Theory of Human Cruelty. London: Penguin Group Inc., 2011.
[2]艾薩克·巴什维斯·辛格. 辛格自选集. 韩颖等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3]程雪芳. “论辛格《旅游巴士》中的二元对立与身份错位.” 湖北社会科学, 2012(7): 136-139.
[4]乔国强. 辛格研究.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5]生安锋.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张剑. “西方文论关键词 他者.” 外国文学, 2011(01): 120-129+161 -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