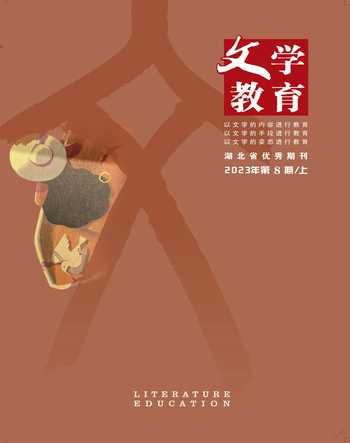苏童小说中的南方阁楼
2023-08-22金雯
金雯
内容摘要:尽管苏童的短篇小说《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与其代表作品相比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但作者在两篇小说中对于“阁楼”这一叙事空间的构造独具匠心,值得深探。在苏童笔下,阁楼不仅成为女性主人公的生活场所,也区隔并连接起了世俗与神圣、时代与个体,支撑起了小说中的女性书写。从“阁楼”这一空间入手,能够窥见苏童在叙事技法上的巧妙,体会其对人性剖析的深刻,也能探寻苏童小说与古典文学作品的深刻联系。
关键词:苏童 阁楼 《妇女生活》 《另一种妇女生活》
作为苏童先锋转型时期的作品,《妇女生活》与《另一种妇女生活》弱化了先锋性,强化了现实意识,延续了在《妻妾成群》中对于女性形象的细致塑造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刻理解。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苏童在书写“一种”与“另一种”妇女生活时,都选择了二层阁楼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空间,这绝不是偶然。设置“阁楼”不仅为主人公提供活动场所,更划分了上下、内外两重空间,形成“看台效应”,也连接起个人私域与宽广的时代背景。而对女性空间的设置自有其传统文化资源,中国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后花园”这样的女性空间,由此可以看出苏童小说与古典文学的联系。
一.阁楼上下:“看”与“被看”的多重结构
苏童所选择的二层阁楼这一建筑形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是一个悬空的、单独存在的空间,也仍然构筑于市井之上,与世俗保持着密切联系。通过这一场所的设置,作者能够划分阁楼上下两重既相互隔绝又彼此联系的空间,产生“看台效应”。《另一种妇女生活》讲述酱园中两种不同的女性生活:简氏姐妹遵从父亲家规,幽居于阁楼中,过着数十年如一日的“守贞”生活;而楼下酱园中的三位女店员则代表着“嘈杂尘世”。最终,个体意识觉醒的妹妹简少贞在酱园女店员的逐步“诱导”下摆脱了姐姐的束缚,走出阁楼追求自己的婚姻,而姐姐则在阁楼中自杀身亡。在这个故事中就暗含着多重“看”与“被看”结构。
最小也最明顯的一层“看”,是楼下酱园的女店员对楼上简氏姐妹生活的观察。简氏姐妹幽居的阁楼悬在酱园之上,酱园店员“对此充满了猎人式的心理”[1],会以各种方式获取简氏姐妹离群索居的生活细节,满足自身窥视欲。而店员们在“看”简氏姐妹的同时,自己也成为整条香椿树街居民的观看对象,由此构成另一重超越阁楼上下、发生于阁楼内外之间的“看”。香椿树街的居民既关注着阁楼上幽居的简氏姐妹,也旁观着酱园三个女店员之间的争执。人们抱着一种看好戏的心态以各种渠道获取店内“丑闻”以供消遣:或是直接围观,或是在街上拉住路过的店员刺探消息,有好事的妇女干脆直接把店员拉到自己家里。先是店员杭素玉与店主任之间的暧昧关系在香椿树街不胫而走,接着群众的议论又使事态不断发酵,最终导致了杭素玉之死。
在故事中的两重“看”与“被看”之外,还有一重范围更大的、小说内外的“看”,那就是作者、读者对整个故事中人物群像的观察。香椿树街的居民起初千方百计从店员粟美仙处打听消息并传播,获得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在凶杀案发生后又认为粟美仙是害死杭素玉的间接杀手,在其背后指指戳戳。而这些好事群众其实也是杀死杭素玉的凶手。这不禁让人想到鲁迅作品中以咀嚼他人痛苦为乐的庸众,可见群众的围观在文学作品中总不缺席,并且永不过时,总能够反映人性纵深处的险恶,引人深思。
“看台效应”之外,苏童还以阁楼区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楼上是相对单纯、带有超脱性的女性世界,楼下的寿衣店、酱园则代表着世俗、欲望和死亡。然而这两个空间又不是泾渭分明的,悬浮的阁楼看似与市井隔离,然而它的低矮又决定了它难以避免时代的烙印与世俗生活的侵扰,这个企图保持神圣的世界必然会向泥泞的市井倾斜并最终崩塌。《妇女生活》中的三代女性在时代大趋势对人性的改造下逐步摆脱浪漫与幻想,最终由箫完成了向俗世的彻底回归;《另一种妇女生活》中的简少芬也在店员顾雅仙锲而不舍的“进攻”下跟随其走出阁楼,结束守贞。而外部世界对阁楼逐步“侵入”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女性的挣扎、逃离,和最后不得不“陷落”的宿命般的结局。作者正是利用低矮的阁楼这一空间不动声色地展开了女性的挣扎与悲剧的命运循环。
二.阁楼内外:个体与时代的剥离
苏童笔下的阁楼往往狭小逼仄,再加之南方气候的潮湿闷热,更是充满阴郁气息,象征着束缚与围困。《妇女生活》和《另一种妇女生活》中除了简少贞之外的所有主人公都曾试图“逃离”阁楼,唯一坚守阁楼的简少贞最后在阁楼中自杀,也可看作另一种形式的逃脱。而这些女性又无一不在出逃后重返阁楼,作者利用她们的出逃连接起了阁楼内外两个空间,展现出狭小阁楼之外宏大的时代背景:抗日、大炼钢铁、知青下乡……而她们的回归又使翻天覆地的中国社会与一潭死水的阁楼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见那些深刻改变中国社会的历史大事件反映在这些女性身上也不过人生中转瞬即逝的浅浅涟漪。
苏童对时代背景的处理是有其特殊性的,他并不对小说的社会背景作过多描述,而更专注于叙述阁楼内女性的个人生活。尽管小说也给出了故事发生的具体年份,但和历史真实并不对应。例如,电影明星阮玲玉死于1935年,但在小说中却死于1939年。苏童对自己这一“低级错误”的解释是,他在有意模糊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2]。由此可以看出80年代末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对政治的有意疏离与对人性的皈依。历史在文学作品中不再成为叙事赖以生发的源头,而淡化为人物存在的一种氛围。
当然,苏童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对社会历史作出一定的展示,小说还是隐约展现了抗日、大跃进等深刻影响中国社会面貌的历史大事件,并且也有“资产阶级寄生虫”“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差异。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小说很容易就能处理为主人公离家争取自由,反抗压迫等主流题材。但苏童笔下的主人公们都很软弱,她们无一例外在出走后又返回明知是泥潭一般的生活,越陷越深,自甘堕落。况且她们的逃离最初为的也不是什么宏大的目的,而是私人化的需求。可见作者没有以阶级视野去观照、划分、塑造人物,他遵从的始终是人性的逻辑。
在《妇女生活》中有一个“巧合”:芝和箫都曾以楷模身份出现在同一份报纸上。芝投身白水泥试制生产,她在水泥工地的照片登在《解放日报》上。作为水泥厂中的先进技术员,她出于阶级考虑嫁给了邹杰,但进入工人家庭之后又产生种种不适应,最后仍然回到阁楼中母亲“小资”的生活中去。十六年后,箫自愿报名去农场插队的光荣事迹也被发表在了《解放日报》上。作者在文中说“箫的选择充满了时代意识”[3]。而箫去了农场之后才发现劳动强度远远超过自身承受范围,不惜以患上风湿性关节炎为代价获得返城机会。后来作者在描写已经怀孕的箫干家务活儿的场景时捎带了这样一句话:“从窗户门缝里挤进了一九八七年热闹的街市声,但是箫对外面的世界无动于衷。”[4]时隔十六年,母女二人都出现在报纸上,又共同以自己的人生为曾经的光荣事迹作出了颇带反讽意味的注解。“箫的经历与她的同时代人基本相似”[5],这看似虚构的巧合故事之下,其实是人性的惯常。
苏童在阁楼中展现了小的个人与大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人的命运固然受到时代社会的影响,但在历史之外,还有那些隐藏在阁楼内非常私人化的、亘古不变的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社会变动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是非常个人化的,没有什么崇高意义。日本入侵对于娴的最大影响不过是孟老板抛弃了她,而知青下乡对于箫来说也不过是一个逃离家庭的借口。这显示了更普遍的人之常态:极少有人是出于非常弘正崇高的目的去做出与所谓时代潮流、历史趋势相契合的人生选择的。大多数人是自私、胆怯的,被卷入历史都是出于眼前的、切实的利益,或是出于从众心理、青春冲动。当历史神话被淡化为一种氛围,个人被从中分离后,个体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便得到了更为深刻的关注。我们会发现,最终对人起支配作用的还是物欲、情欲等人本身的诉求,历史也许不过是为人欲望的施展提供不同的舞台而已。
三.古今流变:“阁楼”与“后花园”的深刻联系
随着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向空间方向的开拓和跨学科研究的兴起,文学与建筑空间的关联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现代文学研究视角的多样使我们得以重新挖掘古典叙事作品中女性空间的内涵。而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文学与空间关联性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是女性与特定空间的关联,这一空间往往是私家园林。
园林中女性的在场已经得到许多建筑学者的探讨,在《中国园林》上就刊登了诸多研究园林与女性关系的文章[6]。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也有共通之处,概括而言,尽管男性才是园林的设计者,但女性也深刻影响了园林这一空间的设计。例如,园林中设置专门出口供女性出入,临街以高墙相隔,有非常严密的男女、内外之分、活动空间比较狭小……这些都和礼教对女子的约束有关。
“后花园”作为大户人家的私家园林,是一个能够包容女性敞露内心的临时性场所,因而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重要的女性空間。在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还魂记》中,杜丽娘常年被礼教禁锢身心,在后花园的自然美景中产生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原来这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桓。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院!”[7]在游园归来后,杜丽娘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会,醒后思念成疾乃至香消玉殒,最终还魂复生,与柳生终成眷属。这个“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奇幻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不仅是因为缠绵悱恻之“情”,更是人们对“情”之下所显示的自然人性舒展的向往。可见后花园不再仅仅是才子佳人爱情生发的场所,更是促使女性生命意识觉醒的空间。
而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女性意识在“后花园”中的觉醒已经不仅仅止步于对爱情的追求,更表现为同性之间的相互体恤与对个性解放的向往。大观园是作者刻意营造的、较为单纯的女性空间,少有男性与长辈介入的女性“青春王国”,在这样一个礼教控制的临时“盲区”内,众姊妹们表现出了各自鲜明的个性,流露出对美好感情的向往,并显示出了女性之间的互相扶持与谅解。而“抄检大观园”的发生让阴云笼罩上了这一世外桃源式的女性空间,表明女性的个体诉求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终归会受到礼教钳制。以这一事件为转折点,众姊妹们都逐渐走向各自的悲惨人生轨道,贾府也迅速败落。
总的来说,后花园作为封建时代大户人家供家中内眷游玩的半敞开的生活空间,是封建女性难得可以进行社交的公共区域,也是隐秘的情感私域。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成为积极介入到叙事中的空间意象。这个半封闭的空间不断对女性进行暗示与言说,逐步打破了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缄默。苏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后花园这个精心营构的女性空间置换为更平民化的阁楼,可以看出其对古典文学的继承。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女性的活动空间是大户人家的“后花园”,而在20世纪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女性显然不可能居于私家园林。在《妇女生活》和《另一种妇女生活》中,苏童便以南方阁楼作为女性生存空间。尽管树影幢幢与繁花似锦褪去,但后花园与南方阁楼两个空间却有共通之处。首先,二者都具有一定的隔绝性。后花园以高墙与外界相隔,阁楼则以悬浮离于市井,都是比较纯粹的女性生存空间,较少有男性介入,也远离世俗生活。其次,是活动范围有限。古代女子由于出行不便加上礼教约束,在偌大的后花园中活动范围仍然受到限制。而苏童小说中的女性虽然已经获得自由出行的权利,却又因某种坚持自愿困守于狭小的阁楼。最后,是半封闭性。尽管两个空间都有隔绝性,但都留下了一定的开放通道。古时有男性逾墙入园,后花园因此能够成为半公开的社交场所。苏童小说中也会有人沿梯而上进入阁楼,因此才有女性向世俗、欲望的陷入。
阁楼作为后花园的现代变体,在苏童的女性书写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狭小封闭的空间可以使女性内心细微情感被放大,更利于表现幽微的人性。开放的通道又让外部世界能够介入其中,唤醒女性的个体意识。女性在阁楼中受到禁锢,也在其中沉思并苏醒,阁楼由此成为女性精神空间构筑的起点。从“后花园”到“阁楼”,这一女性空间的变化不仅体现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更显示了文学书写的流变。
在《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中,“阁楼”不仅是作为背景的一处场所,更是一个能够支撑起女性主题的特殊空间。它既能够显示作者的叙事技巧,也能展现作者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独特理解与对女性的深刻认识。正因为南方阁楼的设置,作者才得以在如此短小的篇幅内,通过有限的人物与情节全面深刻地把握“妇女生活”这一宏大主题。由“阁楼”这一角度切入,是对苏童小说中女性形象阐释的一次突破,也能够帮助我们把握苏童小说叙述风格,管窥苏童从先锋小说走向后先锋的小说创作转型特征。
参考文献
[1]苏童.妇女生活//妻妾成群.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2]苏童.另一种妇女生活//妻妾成群.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3]吴士余.中国小说美学论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4]汤显祖.临川四梦[M].朱萍,编.北京:中华书局,2016.
[5]韩子勇.苏童:南方的植物[J].小说评论,1992(05):46-48.
[6]丁帆,陈霖.略论今年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一种“他塑”[J].学术研究,1995,(03).
[7]王德威.南方的堕落与诱惑[J].读书,1998(4).70-80
[8]张学昕.苏童小说的叙事美学[J].呼兰师专学报,1999(03):53-57.
[9]葛红兵.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J].社会科学,2003(02):107-113.
[10]吴若冰,杜雁.中国古代私家园林女性心理及空间行为探析[J].中国园林,2018,(03).
注 释
[1]苏童.另一种妇女生活//妻妾成群.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125
[2]周新民.生命意识的逃逸——苏童小说中历史与个人关系[J].小说评论,2004(02):35-41.
[3]苏童.妇女生活//妻妾成群.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93
[4]苏童.妇女生活//妻妾成群.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104
[5]苏童.妇女生活//妻妾成群.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94
[6]吴若冰,杜雁.中国古代私家园林女性心理及空间行为探析[J].中国园林,2018,(03);李佳芯,王云才.基于女性视角下的风景园林空间分析[J].中国园林,2011,(06).
[7]汤显祖.临川四梦[M].朱萍,编.北京:中华书局,201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