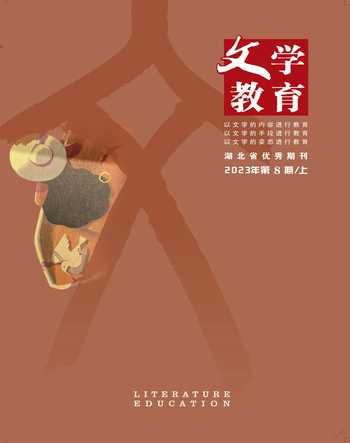迟子建小说集《一坛猪油》里的城市与乡村
2023-08-22李霏
李霏
内容摘要:《一坛猪油》是一部以城市和乡村为背景的小说集。迟子建以乡下人的眼光审视城市,既看到了城市经济的发达,人民生活的富足,又发现了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同时,她以城市人的眼光观察乡村,展现景美、人美、情美的乡土魅力和其存在的不理想面。迟子建的城乡书写从最初的“乡村崇拜”转为客观地诉说城乡现状,虽然乡村存在一定的缺憾,但是它仍为人类心灵的安抚地。
关键词:迟子建 《一坛猪油》 城市 乡村
《一坛猪油》小说集是迟子建小说编年系列(1985-2010)的最后一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2004-2010年迟子建创作的以《一坛猪油》《采浆果的人》《野炊图》等为代表的12篇小说,《一坛猪油》小说集在迟子建作品集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展现了迟子建创作风格的新转变,由“童话般”书写转向社会现实书写。在迟子建的笔下,城与乡是这部小说集的两大书写空间,她笔下的城市与乡村书写具有双重性特点。在写作视角上,她站在乡村审视城市,站在城市遥望乡村。在激进的城镇化进程中,作家没有把城市和乡村二元对立起来,而是在城与乡的比照中,谋求城乡的健康发展。
一.以乡下人的眼光审视城市:躁动与生机
《一坛猪油》小说集收录的作品创作于2004-2010年,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动态更新且持续发展的状态,城乡一体化快速推进,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时代浪潮下,城市文明以势不可挡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推动社会转型,为了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民进城,城乡交流进一步加强。1964-1981年迟子建在乡村生活,后来由于求学和工作等原因一直居住在城市,与生活空间随之变化的是迟子建写作态度从早期完全抵触城市转为逐渐接受城市。1990年迟子建来到哈尔滨,她说,“最早来到哈尔滨,我没有自己的屋子,所以工作写作之余,特别喜欢在街上闲逛。我走到每一个地方,都觉陌生,因为这不是我生活的领地,我感到孤单,虽说哈尔滨是座美丽的城市。”[1]迟子建作为城市的“外来者”,面对陌生的城市她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但是,定居并了解哈尔滨的过程中,她也亲身感受着在城市生活的优势,享受着城市提供给她的更高的发展平台,“我对哈尔滨,从最初的隔膜到现在就是水乳交融了,你在这座城市当中了解它的历史、文化、风俗等等一切,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在升温,对它有了表达的欲望。”[2]迟子建心路历程的变化使得她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从最初的有“隔”转变为水乳交融,对城市的态度由“谈不上爱”转为“亲”,并于1998年定居在哈尔滨。融入城市的生活经历为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城市自然而然地走进了作家笔下。迟子建笔下的城市可分为“有名”城市和“无名”城市,“有名”城市指有具体名字的城市,如北京、兴林和塔里亚等,“无名”城市即没有具体名字的城市。在《一坛猪油》小说集中,无论是有名城市还是无名城市,作家都消隐城市个性而刻画城市群像,集中展现城镇化中城市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客观说明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的城市“通病”。当飞速发展的城市与逐渐落后于时代的乡村发生碰撞时,迟子建多以乡下人的眼光审视城市,在冷色调的诗意书写中展现城市的喧嚣、堕落与生机。
迟子建以乡下人的眼光审视城市,这是带有较强的作家主观感情色彩甚至是个人偏好的创作。相较于沈从文审视城市的“偏激”视角,迟子建审视城市的目光是温和的、客观的,她既写出城市的问题,也肯定城市的先进之处。一方面,迟子建笔下的城市充溢着喧嚣与黯淡。1990年迟子建初到哈尔滨,她既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又要适应完全异于乡村的生活模式,诸多因素使她丧失了对城市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她当时的内心是游离于城市的,她看到城市喧嚣之下的罪恶与沉沦,异变的人类欲望。她从细微之处着笔,由外及内的暴露城市弱点,控诉优美环境的不再,谴责城市人们无休止的欲望。在《蒲草灯》等篇目中,迟子建笔下的城市肮脏逼仄,街巷散布着废纸片,遗落着果皮、粘痰,空气里弥漫着鱼腥气、街边厕所的尿臊味。相较于描绘城市整体环境的光鲜亮丽,迟子建深入刻画城市隐蔽处,关注生活在城市边缘人们的生活环境。与环境恶化随之而来的是城市欲望的泛滥。“20世纪90年代,城市文学开始从审美现代性的视角阐述城市生活,城市成为欲望的符号,城市文化演变成一种“物”的文化。”[3]遲子建笔下的城市欲望滋生,欲望诱导人生悲剧的轮番上演。色欲的引诱下,在《蒲草灯》中警察嫖娼,助长了当地的妓女行业;局长嫖娼,甚至侵犯民女邹英,导致邹英不堪耻辱,含恨而死。金钱横行的城市中,物欲使城市人唯利益至上,行人还需要“付费问路”;《野炊图》里的冯飚说:“这世道的人只认金元宝,银锭子!”[4]更是对物欲城市的正面批评。
另一方面,迟子建笔下的城市又充满了繁荣和生机。迟子建发掘城市闪光点,描绘城市的高楼大厦和一片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象,迟子建肯定城市是一个生活富裕的所在,因为它满足了现代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需求。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作为主体不断发展前进,城市的地理优势和政治职能使城市优先享受到国家政策效益,从而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为城市人提供了富足的生活条件,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完整的基础生活设施,这在迟子建的小说中都有所表现。在关于城市的侧面描写中,城市经济发展前景更为明朗,城市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百雀林》中的明瓦进城后赶上县里公路管理站增编,凭老兵复员政策,成为正式工人,明瓦的姐夫二歪离开乡村到城市开种子店,二歪的外甥到城里学美发,明斋做厨子……不仅如此,城市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资源配置。城乡卫生资源配置不平衡,具体表现在城乡卫生费用、基础卫生设施、医疗卫生管理体制和医疗保障体系等方面。《百雀林》里的王琼阁得了股骨头坏死,要从小城镇远赴到蚌埠、赤峰和丹东等大城市看病,小腰岭镇和青峰村无法医治的病人被转到城市里的医院接受治疗,由此形成了乡村到城市看病,小城市到大城市看病的普遍现象。而在迟子建关于城市的正面描写中,可以看出城市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一坛猪油》小说集中,水果店、百货商场、饭店、棋牌室、茶馆、理发店等场所频繁出现,高楼、马路、吉普车、自行车早已普遍,码头上的客船和货船生意繁忙。过年时的火车票价格高昂,但是仍然一票难求,列车上的乘客们惬意地吃烧鸡、猪手,喝小酒、嗑瓜子。《五羊岭的万花筒》中城市餐馆在夏季有炝拌木耳、卤八角花生米、水晶猪皮冻等新式菜品,饭店一天走三五箱啤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二.以城市人的眼光观察乡村:感动与反思
迟子建小说编年系列共四卷,包括《北国一片苍茫》《亲亲土豆》《花瓣饭》《一坛猪油》。在迟子建小说编年系列前三部作品中,她笔下的乡村是一片不受尘世凡俗侵扰的理想之境,乡村人也一直以正面形象出现,而在编年史系列最后一部《一坛猪油》小说集中,迟子建的城市生活经历使她获得了一种审视乡村的全新视角,即以城市人的眼光审视乡村。作家的创作风格发生变化,她理性看待并接受城市文明,不再采用以往“乌托邦”式乡村描写手法去展现完美无暇的乡村,而是在表现乡村美的同时,审慎地落笔于乡村的恶俗之处。从城市反观乡村,乡村并非从前印象里的那般完美,而是善恶并存。《一坛猪油》小说集中作家笔下的乡村,充满诗情画意又含有众生苦态,她对落后于时代的乡村人充满同情,在诗化语言中诉说他们的悲痛命运,使人在凄婉中感动,在温情中反思。但总的来说,迟子建对待乡村的态度是亲近的,乡村虽然充满恶俗但仍是心中的清净之地,是人类精神的安抚地。
迟子建与沈从文一样,笔下的乡村书写是美丽的,都用诗意的语言表达淡淡的哀伤,氛围凄婉唯美。《采浆果的人》中白云、青草、土地、野果等意象在作家的笔下可爱动人,又因乡村远离城市,既无“三废”污染,也无噪音骚扰,空气新鲜,土地肥沃,草木茂盛,这是一片美丽宜居的乡村。正是在这种似真似幻的乡村里,塑造了如邹英(《野炊图》)、紫云(《花牤子的春天》)、苍苍婆(《采浆果的人》)、黑妹(《塔里亚风雪夜》)等农村人物形象,她们有着乌溜溜的大眼睛、漾着笑意的嘴角、秀丽的脸庞。乡村人不仅长相靓丽,而且精神风貌淳朴自然。《塔里亚风雪夜》中李贵是迟子建笔下理想的乡下人形象,他为了不弄脏保洁员刚拖完的地面,脱鞋走进银行;身处消息闭塞的小村庄仍关心民生国事,为汶川大地震捐出自己仅有的一百零五块钱;他还连夜坐载蜂箱的车赶到城里看奥运开幕式;最后却在向税务局检举商家不开发票的路上发生车祸。李贵乐观地直面生活苦难,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乡村大自然中,作为乡村养育出的后代,李贵富有同理心,善良真诚地待人,不畏惧世俗的眼光,忠于内心,勇敢热烈地生活。但是这些农村人物的故事结局大多是充满悲剧色彩或者具有深沉意味,使人感慨命运无常,又领略到乡村的牧歌情调。
迟子建不仅以赞美的眼光欣赏乡村,同时,也以反思的眼光审视乡村滞后处。周晓扬曾评迟子建“不回避东北那片寒冷土地上的贫困、苦难和丑陋。”[5]原始乡村环境孕育出了淳朴的乡村民风,但乡村也无可避免地存在落后低俗的一面。长期居住在城市的迟子建注意到乡村的滞后处:存在缺憾的乡村环境和乡下人身上的劣根性。缺憾的乡村盛行封建迷信,这阻碍了乡下人接受科学文化的意识。在小说《西街魂儿》中,宝敦被炸山采石的声响吓到惊厥,以徐队长、宝敦妈为代表的乡下人们,他们相信封建迷信,愿意去找巫医“治病”,认为邮票可以“招魂”,治愈身体的疾病。而从北京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的张以菡则痛斥她们:“你们真够愚昧的,孩子病了不去看医生,去找巫婆!”[6]——表达了作家对农村愚昧现象的批评。村中的沼气池因年久失修,在高温环境爆炸导致张以菡身亡,但是西街镇的乡下人们不能客观地理解并接受科学现象,把张以菡的死归为是她不贡献自己邮票,所以宝敦的冤魂藏进粪池,索了张以菡的命。此外,乡村同城市一样,存在情欲和色欲泛滥的现象。村民们经常开关于两性的低俗玩笑,乡下人口中所谈论的大多都是男男女女的事情,女性之间担心对方勾引自己的丈夫,男性之间担心妻子与村里其他男人发生不正当关系。《花牤子春天》里的花牤子强行侵犯紫云、小寡妇、陈六嫂,堕落的陈六嫂在乡村干起了妓女行当,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们在城市嫖娼,染上性病后又带回乡村。
三.迟子建笔下城市与乡村的关系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工业化进程,我国的城乡关系总体经历了城乡分治、二元对立体制局部瓦解、城乡统筹和城乡融合四个阶段。小说集《一坛猪油》展现了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中国城乡关系发生变化:从二元分治转向城乡统筹,这种变化使迟子建看到城乡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进步与不足。《一坛猪油》小说集里的城乡书写以中国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个十年作为社会背景,反映城市版图不断扩大,城市人挤占乡下人生存空间的过程。城乡关系是不平等的,城市更具有侵略性;但城乡又绝非是二元对立的。“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 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 才能相互支撑。”[7]城乡相互支撑,促进彼此成长是作家理想的社会状态,但是迟子建发现,现实城乡关系的融合是艰难的。对于如迟子建一般的精英知识分子们来说,这种“难融”是一道较为容易跨过的障礙,即使最初的他们来自乡村,她们依然可以很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但是对于平凡的小人物来说,他们没有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城乡的“融合”是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人类的心灵最终归依到哪一方?迟子建最终选择了乡村,这既是她的“乡土情结”,也是拥有过几十年城市生活经历的乡下人迟子建最后的家园抉择。
城与乡的融合仅停留在表层空间的流动,在迟子建人文主义目光的注视下,其实城乡深层次的、心灵层面上的融合依然是难以实现的。“新时期以来,城市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并成为现代化进程的导引方向,这个显著事实直接引发了由乡入城的现象。”[8]在城市居住多年的迟子建愈发清晰地认识到城乡难融之处,作为一名精英知识分子,迟子建融入城市的过程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乡下人来说,融入城市的过程是对自身内里的“撕裂”,这种“撕裂”带给他们身体上的疲惫与精神上的混沌,来自底层的乡下人,经济能力与观念转变都有所欠缺,致使乡下人无法选择自己理想中的城市生活,只能被动地等待城市生活的筛选。《雪窗帘》里来自农村的老妇人坐火车不会换卧铺票,她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床位,在冰冷的板凳上独坐整夜;老妇人不会坐火车折叠椅,向列车员求助却换来不屑的眼神和刻薄的话语,车厢上的城市人用凑热闹的心态看完这一场闹剧却无人施以援手。城市人傲慢地咄咄逼人,乡下人畏缩怯弱,乡下人被城市排挤在城外,这是一堵无形的城,一座隔在城市与乡下人心里的墙,这座城墙仅仅依靠外部力量是行不通的,只有城乡从心底接纳彼此才能真正地打通这座无形之墙。城与乡在空间上是流动的,城市人会到乡村进行劳动改造、走访调研、收浆果等,对于走入乡村的城市人来说,他们的心灵世界仍属于城市,乡村对于城市人只是出于目的性需要而短暂停留的地方。但是对于进城务工的乡村人来说,他们的精神世界已然受到城市影响并发生动摇与改变,他们渴望在城市扎根但没有能力在城市定居,最后又尴尬地重返乡村。《百雀林》里的农村小孩周明瓦在十一岁时被养父接到城里生活,起初明瓦成家立业,人生顺意,甚至他还帮助农村亲戚们在城里打工,后来在一系列变故之后,明瓦却无奈地返回乡村任职养鸟员,依靠明瓦生存的农村亲戚们也陆续失去了城市的工作,被迫返回乡村。乡下人进城后很难在城市扎根,他们只是完成了一次从农村到城市,或长或短的空间流动,而非长久的驻足生活。
面对城乡难融的境况,虽然乡村充满缺憾,但是在迟子建笔下它仍为人类救赎之地。迟子建笔下的乡村是非理想化的,帶着缺陷和伤痛,迟子建认识到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纵情声色、金钱本位、享乐主义等负面欲望已经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无法根本性的剔除。而乡村也染有这些不良风气,迟子建笔下的乡村也出现色情、重利和虚荣等道德“失范”的问题,但是乡村的可塑性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因为乡村人正视个人欲望,不逃避犯下的错误,及时自省,适时改正。迟子建基于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体验建立了一个人类精神家园的栖息地,这是承载着人类美好希望与真诚大爱的土地,这片土地就落在乡村。迟子建把乡村构想为生长真爱之地,真诚的爱可拯救人精神的堕落。小说《一坛猪油》中,“我”和丈夫老潘是地道的农村人,即使长时间分居异地,仍夫妻恩爱,感情坚定。“我”的儿子蚂蚁也从小成长于农村,偶然机会认识了来自林场河对岸的苏联女孩并一见钟情,他勇敢地游向河对岸的苏联,只为追寻真爱。乡村能够孕育并生长出真正的爱情,这种真爱救赎人们的精神。与之相反,城市无法生长真正的爱情,来自城市的崔大林为了与来自大城市的女教师程英结婚,偷走“我”的戒指,程英也为了一枚昂贵的戒指嫁给自己不爱的人,这是一对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脆弱的婚姻关系,绝非爱情。迟子建构想的这片真爱生长之地,更是自我救赎之地。《蒲草灯》中在城市犯罪的“我”逃回乡村后,重获心灵的归属感和熟悉感,相较于城市阴暗潮湿的环境,乡村充满阳光,有大片的草原、金红的晚霞、米黄色的麦子和绚丽耀眼的葵花,较之对城市冷色调书写的不同,作家选用大量暖色调事物打造放松的乡村环境,使“我”恍然意识到自己的罪责,最终“我”擎着象征爱与希望的蒲草灯去自首。“我”在城市自首的念头是出于对法律惩罚的恐惧,这是被动的救赎,而“我”在乡村自首的念头是受到乡村来自精神上抚慰过后的结果,这是一种真正的、真诚的人心灵上的救赎,但是只有在乡村,人才能做到心灵上的平静。
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城镇化正处在现代化的宏大进程里,与传统乡村道德伦理、生活生产联系最为密切的村民们,也面临时代与社会的转型。如何让值得珍视的乡土情感在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以某种新的形态保存下来值得现代人深思。迟子建在《一坛猪油》小说集中向外界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现代性一直都是二者共同追求的目标,一个截然二分的社会状态是不健康的,迟子建希望城和乡能够相互支撑走向美好;但是在很难进行理想融合的当下,人类应当为自己选择一个可以依靠的心灵港湾,那就是择乡村而依。迟子建对乡村充满信心,在她看来,乡村在未来不仅会像城市一样,是生活舒适自由的所在,乡村还依然是人心灵的栖居之所,是值得依赖的精神富饶的家园。迟子建对乡村充满壮丽丰满的信心与期待!
参考文献
[1]董雨阳,陈渌,迟子建.从他乡到故乡——迟子建永远温情的文学世界[N].黑龙江日报,2013-05-16.
[2]王志艳,迟子建.迟子建长篇新作《烟火漫卷》:献给哈尔滨的一首长诗[N].新华网,2020-09-10.
[3]于小植.“城市主体”建构及其限度——论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烟火漫卷》[J].文学评论,2021(06).
[4]迟子建:《一坛猪油》[M].第1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5]高平.小小的北极村 世界的北极村——迟子建文学创作的文化人类学简释[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6]迟子建:《一坛猪油》[M].第8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7]刘彦随.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地理学报,2018,73(04):637-650.
[8]范耀华.论新时期以来“由乡入城”的文学叙述[D].华东师范大学,2007.
[9]杨艺嫄.迟子建小说创作流变论[D].长沙理工大学,2015.
[10]桂璐璐.迟子建城市小说创作论[D].安徽大学,2015.
[11]郑学鹏.迟子建小说对家园的寻求[D].华南理工大学,2015.
[12]仲秋云.论迟子建小说的苦难书写[D].江南大学,2019.
[13]李培林.李炜.陈光金.田丰.新成长阶段的中国社会建设——2010~2011年中国社会发展形势分析与预测[R].第1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