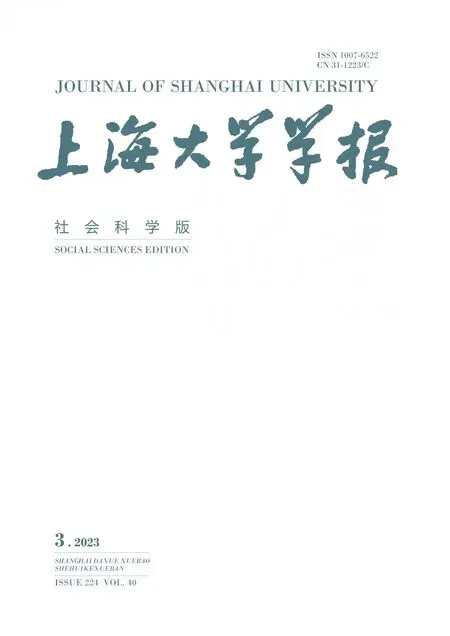“以道驭技”:电影工业美学的技术伦理路径
2023-08-18韩贵东
韩贵东
(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学部,辽宁 大连 116024;中国科幻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引言:电影工业美学与技术伦理的出场
陈旭光在《“电影工业美学”的阐释与延展》一文中提出,电影工业美学理论“接着讲”还需要对伦理批评的维度进行再拓展。他认为:“归根到底,电影是人的电影,强调电影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与资本的关系,在生产过程中,各司其职,在其位谋其政,构建和谐、高效、合理、合规的‘共同体’,这从伦理的角度看,就是一种伦理关系,属于伦理学命题。因此,电影工业美学的伦理维度思考,也是一个值得拓展的空间。”[1]诚然,电影与伦理学的关系命题已经成为学界与业界共同探赜之焦点,而电影工业美学不仅将电影生产的各个环节交还给了伦理承诺的底线,更是将电影与人、社会、市场等的关系以伦理的标杆和尺度加以判断与衡量,不但具有伦理属性,还必然与多种伦理观念交融、碰撞、共生并形成一种有效性的互文关系,乃至于形构双向、多元、共生化的理论场域。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讨论“艺术对话(aesthetic conversation)”的问题时认为:“艺术对话,就好像一个人和自己的对话,这种对话既能被自己感知,同时也对这个人有所影响。”[2]如此,对于电影工业美学伦理维度的考察自然成为一项开放性的议题,其与伦理学的对话亦是一种完全可容纳差异、包含共性、存证特殊的意义生成过程。当然,在伦理维度的审视之中,电影工业美学涵盖的内容要义依旧是美学之本位的思索,但其延展性的理论阐释与现实创作新思,可能已溢出了美学问题本身,或可成为电影工业美学之伦理学转向的一次契机。
毋庸置疑,电影是有关“人”的电影,也是社会发展与市场资本包裹中的工业化产品,抑或是影院银幕、网络媒介之中的电影,但不可忽视的恰在于电影自始至今的技术性要求。自默片时代至数字技术电影盛行于银幕之上的当下,技术的催促成为电影工业迭代与创新的一个翘板。“在当下电影生产的全产业链运作过程中,技术性要求越来越高,技术素质、科学素质成为导演的一种重要素质和基本能力。这对于当下导演,特别是与时代同体共生的新力量导演而言,成为他们必须适应的一种生存环境,也就是说——一种‘技术化生存’。”[3]正如陈旭光所言,对于电影工业美学建构的关键对象——新力量导演而言,技术生产与技术化的风格转向已然成为一种必然。如此便意味着,电影工业美学与技术层面的联结具有更为广阔的谈论天地。当然,对于电影工业美学之中技术化问题的思索已在其前期理论争鸣中有过讨论,尤其是电影工业美学与技术美学的并包关系。一些学者在探讨电影工业美学理论源头时,曾追溯到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①海德格尔技术化的探求为电影工业美学涉及的技术概念提供了某些理论思考,参见[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下)》,孙周兴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中有关技术美的反思与批判性意见,尤其是其“技术对自然的解蔽、催逼”,进而以“艺术介于技术”重新审视主体性审美认知等议题,最终获得“有可能在形成的人类技术高度发展社会背景下,产生出类似‘诗意的栖居’的社会美学意境和内涵”的结论。[4]诚然,这种对于电影工业美学与技术之美思考的维度是可行的。不过,略显遗憾在于其只是止步于对技术的本体思考或美学判断,且大都来自主观性的经验。毋庸讳言,从技术的角度观察电影工业美学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姿态,倘若批评的视野往前再迈一步,则会有技术之善的道德发问,即技术伦理的一种路径。何为技术伦理?德国技术哲学家阿明·格伦瓦尔德(Armin Grunwald)认为:“技术伦理学的任务范畴,是要解决伴随科学和技术进步而必然出现的种种规范和原则的不明确性问题。”[5]因此,在与技术产生联系的过程中,那些与电影技术有关的问题一旦陷入被遮蔽的状态,电影工业美学理应能够达成或厘定此种规范的目的与范畴。退一步来说,如果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追问能够左右电影工业美学的某种遐思,那基于现象学视域下的海德格尔技术之道德哲学发问应当更能够影响电影工业美学的再阐释。原因恰在于海德格尔的技术伦理思想不是学理旧规,而是一以贯之的摆脱技术“座架(Gestell)”,实现人之本质的目的,即抵达“人之为人”的彼岸。
“电影工业美学应该葆有伦理的底线。无论怎么强调电影的工业品质、视听效果、类型化生产、体制内作者的制作、制片人中心制、票房指标、对受众和投资人负责等,在这些原则要求之余,都有一个最低限度的伦理承诺。”[6]在某种意义上,电影工业美学的伦理承诺即是实现对“人之目的”本身的一种祛蔽,即不必因现实技术的“促逼”或“摆置(Stellen)”而走向自我以及群体异化。这种伦理的承诺需要召唤技术伦理出场,且应是贯通性、整体化、多维度的伦理牵引与道德要求。只是讲究技术美学或许不能够走出人之本质遭受侵蚀或创伤的技术窠臼,也难以形成抵御技术庸扰的屏障,自然也就无法达成有效性的电影工业美学诉求。因之,电影工业美学的技术伦理路径建构既是对原有内容的补充与再拓,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技术尤其是热衷电影数字技术的当下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思考窗口。
一、电影工业美学之“善”:技术异化的伦理“揭蔽”
技术哲学家奥特加(Ortegay Gasset)在技术存在论中进一步阐明了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文化关怀。面对海德格尔将技术认定为一种真理显隐的方式,奥特加则将富有内在善的“人之为人目的”的技术与人之美好生活的具体实践相联结。从生活实践的意义来看,技术的使用是科技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正因为技术革新之中出现了诸多有争议性的话题,并且一次又一次冲击着文化存在的形态,才使得人们在对技术进行狂热化追求的同时,开始对视觉文化中的技术跃迁葆有伦理道德维度的考量,也对当下电影工业美学的登场提出了更为真实化的技术道德之问与伦理诉求。正如德国文化理论学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在其作品《记录系统》中所提及的那样: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前进与媒介样式的发展革新息息相关,甚至媒介的形式递进成为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与根本性的缘由。而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逐渐完善与代际更迭,人类文化形态所遭受的正是“哥白尼式的转折”,而这似乎也导致“文字文化最终丧失支配地位并可能退出历史舞台”。[7]在如今充斥人们感观世界的审美文化具体样式之中,文字逐渐被视觉文化所取代,而观众也在视觉文化的享受之中,渐次将自己对于技术的推崇提到生活之内,因而,掌上电脑、穿戴装备等技术化产品的革新也导致人们思维知觉等具体形式得以改变,并在一种潜移默化的技术场域之中产生多重异化的可能性。马克斯·韦伯在谈及伦理问题之时,首倡责任伦理的概念,他认为“我们必须明白,一切伦理性的行动都可以归于两种根本不同的、不可调和地对峙的原则: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8]电影工业美学的多个维度都是对于“负责任创新机制”的一种贯彻,无论是其生产体系、制片人中心制、剧本医生等皆可以诠释责任伦理的内涵。不过,对于电影工业美学的技术伦理路径而言,应当避免人之本身沦为技术的附庸,即需要完成对技术异化诸多问题的伦理“揭蔽”,从而使电影之技术彰显负责任之善的伦理意义。
“当下导演,必须适应数字技术、互联网语境下的‘技术化生存’,技术影响、制约、改变、形塑着电影导演的创作思维和想象力。”[9]回到与电影有关的数字技术追问,当下抑或元宇宙未来憧憬之下的电影工业美学不单是强调技术化生存的意义,而是理应对技术性的伦理问题有所预设。从技术发展的角度而言,无论是今之诸多导演尝试的“120帧、4K、3D、CG、面部动作捕捉(Facial Motion Capture)”等技术,抑或是元宇宙时代混合与交互的多重技术迭代,例如与之相关的扩展现实技术(VR、AR、MR、XR)、720°全景沉浸数字孪生(Digital Twin)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区块链技术、大数据云计算、脑机接口穿戴设备、光线追踪等一系列技术,抑或是Web3.0 发展以及数字藏品/NFT(Non-Fungible Token,指非同质化代币)等媒介技术的发展赋能,皆在一种可以想象的视觉景观思索中,成为人之主体生活的必然选择。但是,与之俱来的问题在于,如上所述电影数字技术或其他媒介技术的发展不是单一化的,其表现为一种多维、综合、联结的技术支撑。这也就意味着,技术之间充斥着复杂的缔结关系或异化之状,并不能只是对技术化的实际应用关注,而是需要混合、能动、多维的技术伦理忧思。进一步而言,“媒介技术就是人类同外部世界进行合目的、有规律地变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一种中介性手段”。[10]作为人之主体与客观对象认识的中介,电影数字技术成为人们认识客观存在与改造个体自我的有效手段。如此,便有了一种媒介技术进化的认知,一如保罗·莱文森(PauI Levinson)所言:“有了技术之后,人就变了,人就从进化的产物变成了进化和变革的生产者,就从现存世界的理解者变成了新世界的创造者。”[11]其对于技术更为广义化的认知,直接将技术与客观环境与人类实践中的主客体做了别具张力化的有效界定。因此,无论电影工业美学之中的技术发展呈现怎样的潮水流向,都需要首先思考技术与人之间建立何种关联。质言之,电影数字技术与人之间存在何种伦理关系,往往影响着当下乃至以后技术是否成为人们良好生活的选择或将走入一种“人之本质目的”的电影工业美学之技术生命体认。
诚然,在当下的生活日常中,电影媒介的发展、认知始终会沿袭着技术化的逻辑意向,无论是在早期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马歇尔·麦克卢汉,抑或是尼尔·波兹曼看来,媒介技术既充当人们感知体系形构的关键凭证,又是人们内在心灵认知与体悟的必要存在中介。当然,这种技术的认知,还包含着技术对于人之主体生活干预之外的一种“控制论”倾向,技术对于人们思维表达、行为约束以及生活日常的渗透,早已经使得人们对于技术的关注走向了上述异化的论调。不过,这些基于电影、网络等媒介技术的认知,还未呈现出媒介迭代升级过程中的“人之主体性意识”表达。好在电影工业美学的提出恰逢其时,本就顺应了这种技术化的倾向,“‘电影工业美学’与理性美学、技术美学、现代设计美学、工业美学等理论资源具有某种渊源性或交叉互文性,与好莱坞电影工业生产特性或好莱坞电影美学有一定的相关性或相似性。但其根源是中国本土,作为一种本土化的批评理论,它是中国电影生产实践的总结和提升”。[12]正是在此思考中,电影工业美学始终以内在承继、外在扬弃的开放化态度,展现其对技术异化中人之能动性的有效反馈,促成了人本主义的人性化技术发展趋势。在这层意义上,电影工业美学既是他者经验的一次巡礼,又是自我真实的一次复盘,与其说其提供了一层技术美学审视的维度,倒不如将其延展的可能放置在更为宏大、宽阔的技术伦理现实之思中。这一将人类非完美性、人类理性与人类需求性作为媒介技术演化、升级之补救内因、自然环境与逻辑归宿的思考,[13]为我们寻得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电影媒介与人之道德良性化发展、共促、并行的路径,从而更好地解决技术主义对人之主体介入而产生异化的某些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工业美学作为技术对人之本质异化伦理“揭蔽”的一种认知,合乎“以道驭技”之善的技术伦理要求吗?对此问题的回应,首先应当考量电影工业美学是否意味着“道”这一学理层面。《庄子·天地篇》有言:“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14]其意在于那些一味追求机械化的人,断然有投机取巧之事由、行径,而投机取巧的人必然存有钻营、投机之心。人一旦有了此时的“机心”,便可能丧失以往的自然性或天道,也正因此,老子很早便在《道德经》里提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5]当然,老子并非全然拒绝技术的使用,而是将技术的要求重返一种所谓的“天道”,即自然的状态之下。面对技术使人步入“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价值判断境地,人之本质已然在技术充斥的生活此在中被遮蔽,以至于需要一种共识避免人之异化。老子在“复归于朴”中达成对于技术使人异化的方法论建构,这种自内而外省思的方式本就是一种摒弃奢求、去泰悟道化的技术伦理策略。自“技合乎道”至“技进乎道”再至“以道驭技”,渐次呈现对于“以技驭道”、技术异化症候的一种伦理规范方法。在“以道驭技”的伦理思考中,电影工业美学的导向之“道”更为精细、准确地指向电影创作的各个环节。“电影生产者应该秉承电影产业观念与类型生产原则,在电影生产中弱化感性、私人、自我的体验,代之理性、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方式,游走于电影工业生产的体制之内,服膺于‘制片人中心制’但又兼顾电影创作艺术追求,最大限度地平衡电影艺术性/商业性、体制性/作者性的关系,追求电影美学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16]如此,理性化、标准化的工作之“道”自然也就为技术之于电影之“道”提出了具象化的要求,服务于电影艺术的技术理应成为一种协助性意义的存在物,而非电影艺术主体本身。诚然,电影工业美学所倡导的均衡性关系也适用于技术之道。在希腊文字的表达中,“技术”(technik,tech-nology)这一词汇的源起本就来自“技艺、几微”。[17]16技术作为存在论意义生成中的现象,其本质自然含有更为丰厚的缘构性,如此意味着电影工业美学之中的技术意义不单单是达成数字技术电影景观飞扬与上升的目的或手段,更应在此思索中成为人之重塑或再造的方法,即“更有力、更深刻的参与塑成人的历史境域”。[18]因之,电影工业美学之中的技术审视,需要充分认识到“技术之道德”的诉求,“技术之伦理”的必要,或可尝试构建一种“技术与人良善关系”的道德策略或伦理约束机制,从而真正实现技术伦理之异化问题的揭蔽与规避。
二、电影工业美学之“喻”:“技术景观”的伦理警惕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在其电影研究中认为,哲学不再是凌驾于艺术头上的唯一真理者,他认为要将艺术本身的艺术真理归还给艺术,因为“艺术自身就是真理的进程”。[19]电影工业美学所强调的“技术化生存”为电影艺术的创作指明了发展方向,并行之有效地提供了技术生成电影视觉文化意义的合理方式,但值得警惕的恰在于电影数字技术以一种混合化、多样态的技术存在影响着人之主体性、现实与虚拟边界、记忆存留等伦理忧思。电影数字技术的显隐如若成为观众视觉观看视野的延伸,数字技术则如海德格尔所言演化成了一种“座架”,是一种“胁迫与强制”,其结果自然变成“对象物”的生成,以至于人本身也自然成为“对象物”。如此,电影艺术自身就难以成为巴迪欧所言及的真理,更无法行之有效地演化为真理之进程。这种技术本体观念已经影响了人们对于电影的观看形式与方式。在消费主义市场产业化的制导逻辑之下,技术对于电影作为商品属性的升值有着巨大的催化效果,但并不意味着技术可以超越电影艺术或凌驾于其之上,渐次转化为一种实在体。面对技术化甚嚣尘上的发展态势,电影工业美学需要在技术化生存的议题之中,追问银幕内外技术伦理所表现的具体问题,达成极度技术景观体验使人丧失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谓的“灵韵(Aura)”的伦理警醒目的,重返人之主体性的意义探寻,毕竟“人存在于世的主体性思考是伦理问题构成的关键”。[20]
康德说:“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的人格中的人性和其他人格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仅仅看作是手段。”[21]这意味着无论何时人都应当认识到“人是目的”的意义与价值。电影工业美学观照之中的“人”既包括创作者身份,也包括消费者身份,导演与观众同样需要注重“人之为人目的”的“人之主体性”数字技术观,不能够且不应当沦为技术之力的附庸。从20 世纪60 年代起,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提出景观社会的概念,伴随着艺术文本意义与技术存在之间的博弈,“景观(Spectacle)”逐渐成了一个具有批判性的词汇,“景观”意义的延伸表达逐渐在德波的个人理解中演化为一个与商品视觉文化有关的概念,因而他提出“商品社会被所谓的景观社会取代,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政治生活一类概念,开始被空间和日常生活等概念取代”。[22]35这种数字技术电影所形成的“景观”文化的飞扬,是否意味着“意义场域虚设”的商榷,这才是数字技术电影使人陷入伦理迷思的关键。“世界将变成影像的集合,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影像为中介。”[22]3实际上,居伊·德波的观点自20 世纪60 年代至今的现实导向意义仍值得人们反思。当下数字技术的迭代已经超越了20 世纪媒介技术初生破壁的样态,人们不但难以挣脱技术之网,甚至无法摆脱景观的锁链。这种视觉图像景观化的发展趋势无异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所指明的“全景监狱”,[23]人之主体性身份指向了被规训的可能,进而导致主体性意义的迷失与消解,自影像的景观变为规训下商品化的个体,深陷技术景观造成的视觉之魅中,而难以回归伦理至善的自我。这种思考并非是危言耸听,的确有电影工业美学技术化生存关注中的案例来佐证。无论是对《速度与激情7》中保罗·沃克CG 技术换脸的先前思考,抑或是李安导演“120 帧+4K+3D”的技术实验,再到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的3D 长镜头以及路阳等诸多新力量导演技术化的具体表达等等,均如此。另外,凭借体外可穿戴设备不仅实现了VR 虚拟现实的“高保真”观影体验,还进一步打破了银幕内外的真幻界限。人工智能剧本写作业已经成为影像生成的一种可能,似乎电影艺术变成数字技术“宰治”的对象。倘若“数字化的幻象成为统治”,[24]主体不仅丧失了自我主动选择的能力,一再被技术景观化的商品循循善诱,“崇拜”或“膜拜”图像,渐成为他者技术营造的幻象,可能致使主体自我的消解,不仅导致判断力缺失,步入伦理道德底线消弭的境地,更何谈陈寅恪所言“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25]
诚然,电影工业美学的技术生存态度除却人之主体性的伦理思索之外,还应当回应技术景观导致现实与虚拟边界逐渐模糊的“伦理弱感”问题。安德烈·巴赞在其经典著作《“完整电影”神话》中认为“电影与完整无缺的再现现实是等同的”。[26]伴随着电影数字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由早期影像本体论中可知“我为看的主体”转向为不知“我在电影之外看”的伦理焦虑。当电影数字技术作为手段,例如VR/AR/MR 等技术使电影内容本身的表现更具真实性、富有沉浸感、实现天马行空之曾经不可为的浪漫想象或残酷未来时,人们对于技术构成的“超真实”则判断为一种“真实”。加之高帧率(HFR)、高动态范围(HDR)+广色域(WCG)+4K/8K 的技术化辅助,以此实现超高清视野观看,人们误以为由技术生成的视觉真实感等同于主体生活世界的真实性,这便模糊或混淆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甚至自觉沉浸于这种技术勾勒的数字景观之中,一味贪求数字技术视觉体验的极致快感,从而丧失真实的伦理判断。殊不知电影数字技术营造的景观无非是“拟态环境”创造的“拟像”再现。正如对当下元宇宙的批判一般,不能够把元宇宙世界开放化的自由感体验当成是实现了自由之身,人们即便沉浸于3D、VR 影像之中,但依旧被各种穿戴设备所束缚与规训,肉身仍然处在封闭的空间之内。另外,还需警惕的在于,电影数字技术一旦创造了上述视觉景观体验的快感化接受,便容易陷入一种盲目追求快感而理智消除的伦理消费陷阱之中,甚至寄希望于技术视觉之幻来达成自身的欲望追逐,由此忽视生活现实而陷入虚无主义的囚笼。
当然,此类视觉技术景观体验的快感需要重思技术复制现实的伦理困局。正如德籍韩裔哲学家韩炳哲对于当下视觉复制的判断一般,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层次洞察当下的视觉文化形式,人们已经能够看到眼下媒介形式多元化所构成的有关视觉文化转向的某些可能,而这无疑给予大众影像视觉生产的无限复制观感体验,并对大众的生活产生审美的围堵,由此造成伦理道德的诘问。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一再提及“灵韵”走向消散的质变,电影数字技术对于现实的复制,尤其是所营造的“快感化现实”是否也意味着“膜拜价值让与展示价值,从而使艺术原有的原真性与其灵韵消散了”。[27]技术生产的复制影像与原有的真品本就是逐渐离散的关系。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复制而来的“拟像之物”带有现实的形式或样貌,但其作为现实复制的客观存在本就遮蔽了现实。因此,其文化性或者符号表达丧失了本有的真实,而只是以一种“失去摹本的仿真式‘类像’(Simulacrum)”[28]存在于视觉景观体验之中。难怪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盖棺定论道:“虚拟空间不是一个有别于现实空间的另一种空间,而是世界自我投映所借助机制的拓展,它具有前所未有的实效性,并促生了一个新的假象视域。”[29]人们如果将电影数字技术营造的景观当成真实经验本身,甚至自“技术景观之物象”导向生活,反而进入了“无我之境”的“伦理弱化”地带,最终既无法获得真实性的生活意义,也难以把自己作为解决现实困厄的方法。电影工业美学的阐释恰需要重新厘定电影数字技术生成的虚拟之像与真实存在之间的伦理边界,不能够将虚实之间的界限抹平,混淆类像与自我的现实性伦理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工业美学技术化生存的伦理忧思或许还将指涉有关记忆伦理的议题。简言之,电影数字技术对个体或群体过往记忆的找寻与复现能够达成伦理的某种审视。王国豫认为:“除了对技术的自然科学——技术式以及经济方面的观察外,还必须注意技术在社会心理以及社会伦理方面的影响,并有必要重现‘灵魂所具有的巨大的道德力量’。”[30]电影数字技术如何勾连记忆伦理,又将产生哪些伦理警醒,从而导致技术在记忆的社会伦理维度产生困惑呢?毋庸置疑,在数字技术化生存的时代,人之记忆已经能够被技术所呈现,我们将大量生活痛苦或美好的记忆填充进大数据的质料之中,记忆复现的媒介也已由文字、图像变为数字信号,原有的历史时间线性记忆已经被改组为随时随地的数字技术记忆集合,而一旦记忆被技术景观生成更意味着记忆的持久性或永恒性。当电影数字技术介入记忆时,斯蒂格勒所谈论的“通过模拟和数字技术才得以彻底实现”的“记忆的工业化”[31]已经不再是想象。阿维夏伊·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记忆的伦理》中不仅确证了“存在记忆的伦理”,[32]还具体指出了记忆伦理之中选择性遗忘与记住的道德责任等问题。电影数字技术建构了人之历史时空中的记忆,让观众仿佛回到过去之时,但也模糊了线性记忆应该有的自然规律。概言之,技术所设定的记忆不过是一种“伪记忆”,其确实具备过去的轮廓,但并非自然之道的记忆本身。当电影数字技术营造的记忆成为消费主义市场逻辑下的技术景观商品,记忆也就具备可复制性与保真性,但这种“永久性的在场”只是成为资本规训的手段与利器,并非是线性自然记忆的模样。更何况,面对何为良好生活的发问,如果没有遗憾或将陷入无趣的生活之地。换言之,人类生活福祉的实现恰在于记忆遵循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如此才会更为珍惜、把握美好与苦痛皆有的当下,不至于走进电影数字技术的虚空记忆中。因之,电影工业美学的拓展亟须对技术化生存的策略进行伦理导向的规约,尤其是面对“技术景观”化发展的趋势,不仅警惕人之主体性意义丧失的可能,还需在现实与虚拟的边界地带,重返人之记忆自然性,重树伦理道德的界碑。
三、电影工业美学之“法”:道德物化的伦理规制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之“座架”需要按照某种特定规则进行摆置,而人作为自我意识主导的灵活性行动者,在技术座架的驱使之下逐渐为了完成任务而沦陷自我或丧失思考,陷入僵化、形式化、片面性的技术境地。因此,技术座架具备“强制性和规范性”。[33]电影工业美学技术化发展的未来也必然存在技术座架的催促与胁迫。为了摆脱技术座架的束缚,自然需要寻找一套能够驾驭座架的道德之法或伦理之善的理路,释放出被压制的德性答案,聆听来自技术忧思中的伦理声音。正如海德格尔对于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一般,“但是何处有危险,何处也就生成着拯救”。[17]32这意味着技术之困的答案似乎来自技术本身。换言之,技术如果抵达伦理之善的境地,或将重新散发闪耀的光芒。问题正在于如何实现电影工业美学技术生存中的伦理之善?道德物化的路径或许是一种理论与实践兼顾的尝试。
从时间线性发展的维度来看,传统意义上的技术伦理在递进过程中表现为有效针对性的缺失,其难以适应多变的技术发展,尤其是“会聚技术”的出现,并导致实践意义逐渐消解。与此同时,荷兰技术哲学家彼得-保罗·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提出了技术物作为道德之行动者的理论构想,即道德物化。尽管在某种层面,其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具有混淆性,但维贝克的道德物化伦理实践,或可以为电影工业美学技术伦理路径提供方法参照。“技术物成了内在的道德实体,这就意味着设计者可以以一种物质的方式从事伦理活动:对道德进行物化。”[34]维贝克的这一观点不是承认技术物的主体性,而是将人与技术之物形构成“道德行动者共同体”,技术之物存在自由化与指向性的意义,可以充当道德调解的角色。因之,参照此种论断,为解决上述讨论中电影工业美学技术生存的人之主体性伦理困惑,或可以在电影观看、电影生产等技术化环节中,使技术之物例如头戴VR 设备、3D 眼镜、视频盒子等承载一定的伦理价值。换言之,在技术之物的产品设计阶段就应当考量其伦理意义的内容,保证其使用环节具备伦理化的意旨。如此,面对虚拟与真实边界模糊或混淆的伦理困厄,技术之物便能够在具体的实践中有效发挥道德行动者的功用,实现应有之义的伦理预警或提醒,完成对电影技术产品使用者行为的伦理规约与道德牵引。
当然,维贝克并非纸上谈兵,他提出了一套道德物化得以实现的具体方略。先由设计者的道德想象(Moral Imagination),进入扩展建构性的技术评估(Augmenting Construc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再于情景模拟(Scenario Method)方法中得以实现。如陈旭光所论:“想象力,是指人的一种心灵能力或主观能力,是为世界创造新意义的一种精神能力。爱因斯坦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是知识进化的源泉。艺术领域也是如此,艺术家的艺术原创力突出表现为艺术想象力。”[35]从想象力构建的维度来看,电影工业美学呼唤“想象力消费”时代的到来,而于技术伦理的层次思考而言,或将需要一种与“艺术想象力”遥相呼应的“道德想象力”。道德物化的实现即来自技术之物设计者的道德想象力。这要求设计者在先前的设计阶段既能够根据自身主观经验完成对于技术物道德调节的想象,又能够设身处地地进入不同使用情景,并进一步预测技术之物如何塑造或影响使用者、观看者的主观意识与行为表达,最终将此道德想象反作用于技术之物的设计之中。目前,头戴VR 设备虽然可以确保人们影像观看体验的沉浸感,但就道德物化的视域而言,其伦理之善的未来仍旧任重而道远。另外,扩展建构性的技术评估机制对电影工业美学建构系统化、良性化的道德技术物有所启发。所谓扩展建构性技术评估是对起源于20 世纪末荷兰等地传统的建构性技术评估的升级,其将技术的发展纳入进化论的视野观。该评估机制认为技术的前进与市场或政策的环境有较大关系,而在设计阶段如果可以预测技术发展的未来环境,就能够避免被市场或政策淘汰的技术生产,这就为与技术有关的发明者、生产者、消费者各个层面提供了平等对话的可能,以此使得技术之物成为利益共有客体,从而避免了技术被消费时所包含的技术压迫道德焦虑。当然,对于扩展建构性技术评估的考察还需要兼顾各个层面的因素,但电影工业美学的拓展或可在技术评估的层面尝试建立属于自身的技术评估程序,以此更有利于电影技术化生产的未来性走向。
实际上,电影工业美学的技术伦理思考不仅要在实践层面强调道德物化,还需要在多维度的意义商榷中秉持“负责任向善”伦理态度。自马克斯·韦伯开始,对于伦理责任的关注已经使得诸多技术哲学家纷纷建构自己的伦理思想。汉斯·萨克瑟(Hans Sachsse)在20 世纪70 年代初期出版了责任伦理标志性的书籍《技术与责任》,不但归纳了韦伯责任伦理的概念,还将这一责任的内涵归还给技术,建构了个人对于技术富有责任化的洞见。随后,德国技术哲学家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在1979 年的《责任原理——工业技术文明之伦理的一种尝试》中再次对于技术的意义完成了以责任为核心的关键阐述。作为电影工业美学技术伦理的进路,尝试以一种“负责任向善”的技术伦理原则来达成一种共识,似乎可以提供具体而有效的答案参考。电影数字技术的演化、迭代即便有其自身的进化规律与逻辑主导,但是先进技术的出现与落后技术的退场根本上来自人之主体的责任性,也就是“负责任之善”的思考。这本就为电影数字技术的出场与发展导向了症候式解答的伦理出路。或许,只有基于负责任道德向善伦理目的的人之主体认知,才能使电影工业美学中的影像数字技术与人或客观实存形成一条良性、同构化的发展进路。当然,在电影数字技术的演进过程之中,技术的革新必然会带来差异性丛生的伦理新样态。电影数字技术表现自身合理性与工具性的同时,其自身内在的依存机制或将更为有效、便捷地帮助人物实现视觉审美提升、文化娱乐享受等功能,但不容忽视的恰在于其存在的技术伦理缺陷,即价值理性的失衡。这将在影响人们客观选择的同时,或呈现为一种突发、异变的工具特质。如此,更需要建立一种责任性的伦理约束机制,使得电影数字技术在真正服务于人的同时,还能够在一种逆转中不断朝向技术的伦理至善目的。因之,秉持“负责任向善”的电影数字技术伦理关键,将能够在技术更迭、逆转的演进中,为电影工业发展提供一种人之主体性德性选择的方向性伦理规约,进而把握电影技术的发展方向,走出伦理困境,进入道德向善之地。
结语
从历史和当下的双向维度而言,无论是海德格尔、阿多诺,抑或是米切姆、斯蒂格勒等哲人在对技术本质追问的过程中,仿佛自有光芒。他们对技术表达态度,探究内在,重勘旨归,如此便意味着真理被放置于“闪耀的光辉处”。在这层技术目的的探赜中,尽管阅尽了电影技术带来的人之异化可能,反思人之主体性消弭的困境,体悟虚拟与现实边界模糊的伦理之忧,也在技术勾勒的记忆中回到过往之地,但不得不说,我们同时探求到了技术与人类美好生活的联结关系,寄希望于道德物化的技术行动者,从而确证技术问题背后伦理答案显现的可能。
电影工业美学的建构之所以能够朝向一种系统化、本土化、未来化的发展路径,恰恰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开放性、包容性、共促性。元宇宙时代的来临,已经使技术整合性发展成为必然,同时对电影工业美学的未来化面向,提出了新的技术思考空间。而面对元宇宙未来的美好蓝图,还需要及时地想象一种不可为之可为,即保持技术自身与人之间均衡性、和谐化、良善共生的技术伦理关系。尤其是在当下的生活日常中,需要始终怀有未来主义的伦理忧思,以负责任道德向善的技术伦理关怀或“以道驭技”的技术伦理建构完成对于电影工业美学中电影技术问题的干预与重估。以此,为电影工业美学的再拓展赋予开放化考察的伦理意义,从而祛除技术之困,真正获得人之主体性的伦理至善。不仅如此,其他文学艺术形式也皆应在创作思考中“把个人经验和历史经验相融汇,将自我反省和历史反思相结合,从一个极为有效的角度达成了对20世纪中国历史、人性异化等问题的透视与审问”,[36]从而实现人之主体与社会的共同的伦理至善之境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