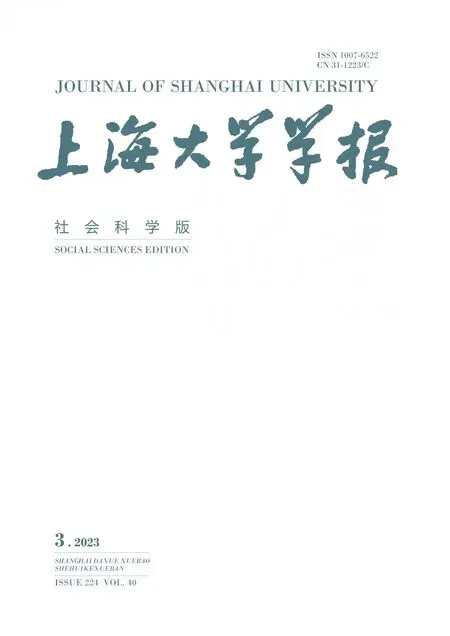电影工业美学的伦理命题
2023-08-18袁智忠,蒋峰,2
袁 智 忠,蒋 峰,2
(1.西南大学 新闻传媒学院,重庆 400715;2.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电视学院,成都 610037)
电影工业美学是当前国内被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电影美学观念。陈旭光在《电影工业美学研究》一书中阐释其立场时指出:电影工业美学承认电影的本体与功能都是复杂多元的,是艺术与工业、产业的复合体,因此在电影生产中最大限度地平衡电影艺术性/商业性、体制性/作者性的关系,追求电影美学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结合新力量导演群体的创作,它的美学原则有商业与媒介文化背景下的电影产业观念、制片人中心制观念、类型电影实践、“体制内作者”的身份意识等;在方法论立场上,它是电影理论“中间层面”的研究,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具有观念革新意义和实际操作指导性意义等等重要思想。[1]10-13
不难看出,电影工业美学在繁荣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方面具有一种宏大愿景和务实理想。对电影工业美学的持续深入研究和探讨,于中国电影工业以及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科学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毋庸讳言,电影兼具技术、文化、产业、商品、艺术等特性,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反映着人的价值愿望并参与各类社会关系的构建。由此来看,人类的电影工业生产活动也必然具有丰富的伦理意蕴,而秉承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方法论、认识论,对其存在的伦理规范与伦理失范进行正反两方面的前瞻性探讨和伦理审视,对于增益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发挥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如笔者曾指出的,“随着西方工业化、商业化思维不断渗透进影像作品,在我们积极推动电影产业升级的同时,资本的血液大量地浸染和输入,加之缺乏相应的制度和伦理规训,影像打上了‘金手指’式的‘非道德’标签。它们解构崇高、消解社会主义道德观,贩卖‘肉感’‘大腿’,突出‘暴力宣泄’。这种带有‘原罪’的影像使得人类陷入更难以把控的道德困境”。[2]可见,电影工业美学在倡导对大众文化、工业美学、技术美学、实践理性美学等理论的运用和疆界的拓展中,其如何能够促使工业体系下的电影生产在满足社会伦理、道德要求的基础上趋利避害,显然是一个极富张力的问题。
由于现代工业体系下的电影产业链十分强调工业化生产、技术化呈现和大众化接受三个层面,因此,在电影工业美学的伦理命题探究中,本文将从生产伦理、技术伦理和传播伦理三个方面展开。首先,生产伦理聚焦于生产制作层面的伦理问题,探究电影工业生产目的和生产手段的伦理取向,并结合当前的电影工业生产实际思考其在道德价值层面的表现。其次,技术伦理聚焦于影像技术层面的伦理问题,探究影像技术对电影艺术表现力的拓展及其与人的现实世界的生存互动等方面彰显的伦理价值,并警惕其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最后,传播伦理聚焦于电影映后的传播消费等层面,重点探究在工业体系下的观众接受、文化批评和营销传播三个维度中,应遵循的道德原则和力求彰显的伦理精神。
一、生产伦理:践行从“手段善”到“道德善”的伦理诉求
《易经·系辞上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3]古圣先贤将主导世间有形之物运行的一般规律或抽象概念称为形而上者,而组建、构成有形之物的具体手段和物质本身称为形而下者。由此类比,电影作为一种有形之物,对其审美规律进行一般总结和抽象概括的电影美学,可以说是一种形而上学,而对其生产创造进行工具开发和实践运用的电影工业,便是一种形而下学。所以,电影工业美学在研究思路上可以说是一种运用自下而上的美学研究路线,对电影工业的生产流程及其作品进行审美研究,最终归纳和概括出一般美学原则的一种电影美学观念建构。直观上看,艺术创作强调的个性化、独特性和超功利性,与工业生产追求的标准化、规范性和商业性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存在。但对电影艺术来说,它的诞生本身便基于放映机、摄影机等工业化产品的出现,且影史早已揭示,每一次电影技术上的进步最终都更有利于电影艺术的表现,如声音、色彩、虚拟数字影像等技术的出现。可见,艺术与工业之间的二元关系在电影艺术中有着更为复杂而辩证的表现。因此,如何从生产伦理的层面看待这种二元对立又辩证统一的矛盾关系,是电影工业美学中的一个重要伦理命题。
首先,从伦理的视角看,电影工业之于人的电影生产活动是一种“手段善”。在元伦理学中,“善”是事物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主体需要、实现主体欲望、达成主体目的的效用性,且根据这种效用性,又可以将其划分为“目的善”和“手段善”等。所谓“目的善”,即事物其自身而非其结果就是人们可欲的,能够满足人们需要,成为人们追求的“目的善”;而“手段善”乃是事物自身作为人们追求的手段,而其结果才是人们所追求的“目的善”。[4]198-199电影工业作为一种物质生产方式,其自身并不是人们追求的目的,但电影工业的进步,能够不断优化电影生产流程,丰富电影艺术的表现形式,对其合理运用后产出的电影作品能够给人们带来愉悦感、幸福感等审美享受。无疑,这一结果是人们所追求的目的之一。因此,从伦理学的角度看,电影工业之于人的电影生产活动是一种“手段善”。以当今全球电影工业实践最为成功的美国好莱坞为例,它不但使美国大片具有一种全球化的吸引力,还在体制机制上形成了一套保障其源源不断生产的高超管理技巧(如制片人中心制、明星制、剧本医生制等)。然而,作为“手段善”的电影工业也受到了社会学理论家和电影理论家们的高度警惕。20 世纪70 年代出现的电影装置论者就指出:“好莱坞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一体的‘装置’(apparatus),它通过把精神分析和意识形态的引诱及媚惑相结合,从而对每个观众产生影响。”[5]24在道德层面,部分影片就存在表现性爱、毒品、暴力、犯罪等内容时,过于强调视觉刺激和欲望消费等伦理失范行为。因此,在伦理规范上,电影工业作为一种“手段善”,只有在具体运用中进一步落实为“道德善”,才具有更大的社会性意义。
所谓“道德善”是“一种对于目的的效用性——不过不是对于某个人的目的的效用性;而是对于社会创造道德的目的的效用性”。[6]亦即,“道德善”所满足的主体是社会,是某种行为及其品德满足社会创造道德的需要、欲望、目的的效用性。毋庸讳言,电影工业生产出的文化商品以营利为目的,但文化商品一旦进入社会,便不能不与他人产生联系,产品也就具有了社会性,此时它就要接受来自社会伦理规范的相应约束。因此,作为“手段善”的电影工业,只有被合理的运用,产生的结果满足社会创造道德的需要和目的时,才符合社会对它的伦理期待。基于此,便可以通过对电影工业在电影生产过程中的运用,来判断它对社会是有正道德价值,还是负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判断,进而有利于人们规范和促进电影工业的发展。
譬如,国内正在进行的“电影工业4.0”建设便具有一种正道德价值,因为它有望解决影视制作中的诸多行业痛点。影视制作人成文曾指出当前的行业痛点,即“中国影视行业摄制更像作坊制而非工业化,生产过程靠人工协调,各环节缺乏协同;层层分包产生高价低质,真正用于摄制的资金不到总成本的一半;制作过程不透明,投资人事实上被排除在影视主控团队之外”。[7]而“电影工业4.0”是以5G 网络、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应用为引领,通过提供先进的影视场景基地服务、智慧拍摄方案制定服务等革新电影制作流程,能够实现电影制作的标准化、规范化、流程化。这一工业体系建设使电影生产制作过程更趋透明化,便于投资者、制片人以及相关监管部门把控电影资金流向,促进电影资金的合理运用,进而有利于电影生产环节的公平正义,这便是一种正道德价值。
再如,民族电影工业的崛起利于国产大片的发展,使其能在国内市场有效抵御好莱坞电影带来的文化冲击,发挥出守卫民族文化阵地的重要作用。英国学者吉尔·布兰斯顿曾指出:“我们不能简单地一味颂扬好莱坞在管理和商业上的成功而对此视而不见,那么做意味着忽视好莱坞为了加强自己的优势所经常采取的残酷手段,忽视好莱坞在影片制作的各个层面与政府的强力联合。”[5]18诚如是,当好莱坞电影席卷全球的时候,它带去的不只是娱乐,还有美国式的价值观、文化观、生活方式,等等。然而,这些好莱坞电影中的美国文化又何尝不是被精心粉饰之后,才展露出“美好”或“理想”的一面。这种极具诱惑性和欺骗性的文化输入,对其他民族、国家而言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它容易使人放大对自身社会现状的不满,转而片面渴求一种美国式的文化生活,却不知道美国同样存在各种严峻的社会问题。所以,在好莱坞电影中这种精心粉饰后的价值观实际裹挟着资本主义的霸权文化。
近年来,国产电影得益于电影工业的升级,涌现出了《流浪地球》《战狼》《红海行动》《长津湖》《金刚川》《奇迹·笨小孩》《独行月球》等一系列现象级的新主流大片,它们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相较引进的美国大片已经占据上风。这些新主流电影充溢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有力地构筑起了一道守卫自身价值体系的文化长城。可见,一个强大的民族电影工业体系能够保证自身民族电影的大片化发展,进而在全球化浪潮中,抵御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大集团资本主义的文化扩张。当然,最令人期待的是电影工业的标准化、规范化、流程化制作,能够实现全球电影资源的融通,而不是一种单向度的文化输入。如中美合拍片《长城》就使中国的文化资源与全球最先进的电影工业相结合,有力地促进了优秀文化资源的全球共享,这显然也是一种正道德价值的体现。
在负道德价值方面,则要警惕电影工业中可能出现的制作僵化、内容拼贴、文化底蕴丧失、破坏生态等负面价值。电影作为一种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文化商品,尤为看重文化创意。而电影工业强调一切都要按照流程走,避免超出流程范围的额外举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扼杀艺术创作中的自由性,从而造成创意僵化。《长城》作为合拍片,最终并未达到双方期待的效果。从媒体对主创人员的访谈中,可以看到在“制片人中心制”的管理模式下,管理者严格遵守工业生产的流程化,致使剧本创意与导演个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并成为其失利的原因之一。再如,在电影制作中一味追求电影工业带来的视效刺激,而忽略将视效融入观众认同的文化表达,亦会造成审美怪异和资源浪费。针对国产影片《封神传奇》,有网络媒体评论道:“《封神传奇》的技术迷恋虽然值得肯定,大资本势必要带来更加精致的画面和视觉享受。但创作者忽略的问题在于,一个东方式的故事,是否应该用西方的视觉风格来呈现。”[8]无疑,创作者罔顾文化底蕴和史实,光靠单纯的视觉刺激,最终难以令观众实现审美认同和情感共鸣。此外,亦有如《无极》《鬼吹灯之云南虫谷》《情癫大圣》等影片在拍摄地置景时,存在破坏自然生态环境、遗留大量建筑垃圾等有悖生态伦理的不道德生产。
总的来看,在生产伦理层面,工业体系下的电影商品化生产与艺术性表达既二元对立,又辩证统一。但在伦理诉求上,电影生产者对电影工业的运用,应当将其从“手段善”落实为“道德善”,以保证在符合社会道德需要的基础上,合理地追求商业利润。
二、技术伦理:警惕影像技术制造极度体验的消费陷阱
德国哲学家汉斯·约纳斯认为:“现代技术,不同于传统技术,是一个有计划的活动,而非一种占有;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状况;是一个动力学的推动因,而非一个工具和技巧的库存。”[9]换言之,现代技术相较于传统技术,有了更多的能动性,它不但全面参与人们的现代生活,还在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选择。技术在电影中的运用同样如此。在电影工业发展中,数字图像合成技术是支撑影像内容生产的重要技术创新。诸如LED数字虚拟特效棚、动作捕捉、Moco 特效以及3D 扫描等拍摄制作技术的运用,使得以科幻、魔幻等为代表的奇幻大片,以战争、古装等为代表的史诗巨片,以及以游戏与电影融合而生的影游融合电影等都成为当下重要的商业类型片。虽然,技术本身无所谓善恶公正,但其具有的伦理性在于“它作为人的一种现实活动形式,既具有目的指向性,又具有客观效果的利弊权衡选择性,内在地存在着深刻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性关系,它表达了特定的价值理念,承载了特定的价值关系”。[10]基于此,便涉及一种伦理张力:一方面是技术拓展了影像的表现力,给观众带来更丰富、全面的沉浸式娱乐体验;另一方面是工业化生产对这种沉浸式体验的极度追寻,存在引发个体生理失衡的风险。因此,如何理性看待技术在影像表达中的运用,亦是电影工业美学中的一个重要伦理命题。
首先,技术在拓展影像表现的疆界、丰富电影的艺术类型、强化电影的人文功能、满足观众的想象力消费需求等方面具有正道德价值。想象力是人类自身最富创造性的一种精神生产力,但对想象的真实呈现却不能不受现实条件的制约。远古人类曾借助文字以神话的形式展现着自身的丰富想象力,直至电影的诞生才使这种文字想象能够以视听的形式进行具象呈现,如梅里爱的《月球旅行记》(1902)就首次尝试表现人类遨游太空的冒险经历。但由于过于明显的舞台布景和特效设计,影片还难以以假乱真、令人信服。至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乔治·卢卡斯在拍摄《星球大战》时,成立了工业光魔电影特效公司,自此开创了电影特效行业的新时代。此后,随着数字计算机的不断发展,数字影像合成技术进一步使虚拟影像创作变得便捷且多元。因此,十分依赖视觉特效的科幻片、灾难片、魔幻片等类型电影迎来了发展机遇,成为全球大集团电影公司每年争相打造的重量级电影产品。如21世纪初,以《哈利·波特》系列和《指环王》系列为代表的魔幻片,就凭借亦真亦幻的魔法世界给人带来超强的视觉震撼,引发制作热潮。同样,在科幻电影的创作中,技术除了使影像更加逼真外,还在文本层面为其提供科学依据。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们探索宇宙奠定了科学基础。以合理的科学假象为根基,大量的科幻电影应运而生,讲述人类探索太空的故事,如《流浪地球》(中国)、《独行月球》(中国)、《阿凡达》(美国)、《E.T.外星人》(美国)等。这些影片在内容上展现出的人类科技成就和未来科技发展,都给人带来极大的视觉震撼与心理愉悦。另外,面对潜意识中可能发生的外星威胁,科幻电影也用人类战胜外星人或与其和谐共存的叙事理念,给人带来心理安慰,突出电影的人文功能。
其次,在电影与世界关系的认知层面,电影也能以其强大的叙事能力,具象化探讨现实世界中科技发展面临的伦理问题,从而具有正道德价值。现实世界中,似乎每一次重大的科学发现或技术进步,都让人欢欣鼓舞,使人类自我中心意识进一步膨胀,但人类社会对科技进步带来的伦理风险,则缺乏认真反思。基于电影工业体系生产出的奇幻类影片则肩负了这样的伦理重任,比如,《头号玩家》揭示了虚拟世界体验具有遮蔽或取代人的现实世界的生存危险;《未来战警》描绘了科技给人类社会带来身体异化的恐怖景象;《哥斯拉》讲述了由于人类的核能滥用而引发的生存灾难;国产影片《刺杀小说家》也探讨了人被科技掌控后所面临的生存危险,等等。面对这些潜在的伦理隐忧,一般的科学论述总是难以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而电影或文学作为一种感性的艺术表达形式,则能够在给人带来审美愉悦的同时,进一步使人深刻反思相关伦理话题。对此美国文学理论家凯瑟琳·海勒就指出:“科学文本善于揭示为特定方法提供理论背景并保证其实际效力的基本假设,文学文本则善于揭示与观念转变和技术创新紧密相连的文化、社会要素及其表征,两者结合才能将变化的故事讲得合情合理,生动丰满。”[11]
最后,在技术运用引发的负道德价值方面,则要警惕电影生产过度追求极度体验可能产生的伦理失范风险。陈旭光指出:“新力量导演无法回避消费主义和以商业性、世俗性、娱乐性、流行性和大众参与性为特点的大众文化的影响,大部分作品中追求着视觉的狂欢和图像文化的冲击力,追求着以娱乐至死的游戏拼贴化表现方式来迎合主流市场,创作呈现出娱乐化、游戏化、商业化的发展趋势。”[1]139可见,在电影工业体系中,部分创作者总是不断瞄准影像的极度体验消费,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商业化发展战略方向之一。所谓极度体验的商业化,是指电影生产者为了使电影持续不断地吸引受众,而有意识地借助技术不断发掘电影与观众可能存在的互动点,渴求在最大限度上刺激观众的神经。如美国科幻动作片《硬核亨利》全片以主人公亨利的第一视角,展现他在追逃过程中与对手发生的枪战、追车、跳楼、炸飞机等惊险动作。观众则在第一视角的强同化作用下,直面影片中的血腥、暴力、惊险等场面。亦有新闻报道,2020 年5 月4 日,俄罗斯的两名儿童疑因模仿蜘蛛侠从11 楼跳下死亡。[12]有学者曾指出:“虚拟现实技术为现实的人创造了一种赛博空间的生存方式,高仿真的人物设计、场景虚构,不但存在使人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拉锯的风险,同时,由于它提供了一种体验禁忌、恐惧与刺激的最为安全的方式,因此也孕育着与色情、暴力和犯罪相关的游戏体验。”[13]可见,对这一追求极度体验的影像表达在伦理层面要予以重点审视,要警惕受众可能存在的技术迷失,并给出相应的伦理举措,从而避免个体与社会脱节,避免个体在技术中沉醉,避免逼真体验造成生理失调等导致的伦理悲剧。
美国电影研究学者罗格·F.库克指出:“随着数字化技术对电影的提升,对人的感觉神经中枢体系的影响就越激烈,也导致了人们在认知层面上的对应变化。”[14]针对电影工业美学对技术美学的强调,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对于更前卫、更具刺激性、更能激发人的生理欲望的电影工业技术运用,是否使人类面临着比以往解构经典、调侃崇高、媚俗搞笑等异化现象更为危险的生存模式?这些都需要予以伦理审视。
三、传播伦理:尊重“为己利他”的市场经济道德原则
广义上看,电影传播伦理涉及整个产业链,是围绕电影制作者、传播者、受众以及电影文本内容、电影传播媒介、社会效果等要素而搭建的关系伦理系统,是基于电影文本生产、制作、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涵盖了实体、规则、关系等多个环节和价值取向。本文在此主要聚焦于电影的传播消费等环节,对工业体系下的观众接受、文化批评和营销传播三个层面涉及的相关伦理命题予以探讨。
第一,在接受伦理上,理想性的伦理诉求是使观众在电影中体验到一种精神上的幸福感。在伦理学中,幸福是善待自我的道德原则,作为一种至善,它“是对一生具有重要意义的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的心理体验,是获得了对于一生具有重大意义的利益的心理体验”。[4]1219-1220但幸福与快乐并不等同,快乐有正常、健康和非正常、病态之分,如酗酒、吸毒、沉迷声色的快乐便是一种非正常、病态的快乐。所以,“快乐未必有利生存和发展;幸福必定有利生存与发展”。[4]1219工业体系下生产出的影片,作为一种满足大众精神性需求的文化商品,在诉诸观众的心理体验上,往往以娱乐为第一诉求。为了娱乐,部分影片不惜利用低俗、庸俗、媚俗的情节满足人的低级感官享受,也会利用色情、暴力等情节无限度地制造感官刺激。显然,这些致力于此的影片,带给观众的都是不健康的快乐。因此,在电影工业美学的观念下,电影产品带给大众的体验,如何能够超越简单的感官娱乐,而让人体验到一种精神上的幸福感,便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命题。
关于幸福的实现律,学者王海明在《新伦理学》中提出欲、才、力、命、德五要素是幸福实现的充足且必要条件,它们与幸福的实现成正比,[4]1339-1354并将幸福的实现律归结为一个等式:
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当电影成为一种工业体制下的文化商品时,获取利润往往是投资者的根本商业诉求。美国学者理查德·麦特白就认为:“好莱坞‘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共生关系对于理解它的商业美学至关重要,商业美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动机上的机会主义。”[15]这种机会主义在电影影像的欲望性生产中便可见一斑。从幸福体验的角度看,影像中合乎情理的欲望刺激,虽然能够提高人们的精神需求并有机会得到更多的幸福,但是由于欲望与幸福实现成反比,这种欲望刺激越大,幸福实现同样也越困难。诸如,影像中过度激发感官刺激的性爱描写、缺乏正义诉求的单纯暴力展示以及纯粹满足攀比心理的消费特写等非正常的、病态的欲望表达需要被警惕。因为,这些可能激发部分自控能力较弱的群体成员不惜铤而走险,采用极端暴力的手段来满足被影像激发出的欲望,这势必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
对于才、力、命、德这四个实现幸福的正相关要素,我们亦可从受众与电影主人公进行想象性认同的审美体验中,窥视到工业体系下的电影内容生产应遵循的一些基本价值取向。不难发现,无论是美国的好莱坞大片,还是近年来的国产大片,打造各种英雄成为影片的重点表现对象,如国产电影《战狼》《长津湖》《中国机长》《烈火英雄》《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独行月球》等,美国电影《超人》《蜘蛛侠》《蝙蝠侠》《复仇者联盟》等。这些影片中的英雄人物具有如下的成长历程:首先,这些英雄无疑都有绝佳的潜在天资,只是影片一开始常常不会表现出来而已;其次,他们在影片中都需要肩负起拯救众生的职责,这种职责决定了他们必然要进行一段艰苦奋斗的努力征程;再次,从命运的角度看,表面上他们可能是不幸的,但时势造英雄,这种不幸的遭遇恰恰成为激发他们潜能的重要环境因素,他们也必然在这种磨难中获取最终目的的胜利,进而成长为令人崇拜的英雄;最后,英雄们可能会牺牲,他们的牺牲则彰显出其无私利他的崇高道德品质。当然大部分好莱坞电影结尾是大团圆式的,这样也满足了观众期待英雄永生的世俗愿望。这些英雄人物无不体现出了天资高、肯努力、命运好、品德优的幸福正相关要素。当电影观众沉浸在影像中,便能实现与英雄主人公的想象性认同,进而产生一种模仿、崇拜、向往英雄的正向道德价值冲动。因此,从受众的幸福实现的角度看,电影工业体系下的电影生产活动,在内容层面不能一味追求影像对人的非正常欲望的满足,而应注重使观众在与主人公的认同中,能够经历到欲与才、力、命、德相一致时产生的完美幸福体验。这样才能在满足自身商业利益诉求的同时,为社会创造更多的道德价值。
第二,在批评伦理上,文化批评主体应当尊重为己利他的市场经济道德原则。当前,受消费主义文化主导,电影创作呈现出娱乐化、游戏化、商业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世俗性的电影美学追求,也是商业电影屡受传统精英意识文化批评的聚焦点。对于这一问题,需要从规范伦理学的角度加以辩证看待。电影工业体系下的电影生产活动在性质上首先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而在市场经济伦理中,为己利他原则是经济活动中最基本且恒久的原则,它是可以在各类行为关系中实现利益一致和两全的行为。但传统的电影文化批评在道德立场上秉承的更多是无私利他的社会传统道德总原则及其理论,即儒家、墨家和康德以及基督教所代表的利他主义思想强调的只有无私利他的行为才是道德的、善的。显然,这一道德立场与经济行为中的道德立场存在一定的冲突,因此,传统批评难以发挥出切实有效的指导性作用。由于中国电影产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市场利润的支撑,因此对商业电影的批评不能忽略利而只谈义。
但是,也要清晰地意识到,集体主义和无私利他虽然不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却可以是市场经济行为者从经济人转变为社会人时需要遵循的道德原则。“不难看出,一个人作为社会人如果对无私利他原则遵循得越好,无私利他的行为越多,那么,当他是经济人时,他对为己利他原则遵循得便越好,从而他为己利他的行为便越多而损人利己的行为便越少。”[4]680这也似乎从伦理学的视角解释了为何陈旭光将“‘体制内作者’的身份意识”作为电影工业美学的原则建构和表征之一的重要原因。因为,“体制内作者”的身份意识能够保障创作者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原则的认同。无私利他作为符合社会需求的最高善原则,亦能从体制内作者的人格中得以显现,从而在他们从事电影生产的活动中做到为己利他的行为更多,损人利己的行为更少。
第三,在营销伦理上,电影工业体系下的营销传播亦应遵守为己利他的市场经济道德原则。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审美需求是一种较高层次的需要,据此也就意味着,满足审美需要的电影并不是大众生活中最迫切、最依赖的一种心理需求。而电影营销采取的策略,恰是要将这种审美需求与大众的各类迫切的现实需求相结合,进而使大众产生迫切的消费冲动。由于电影的营销传播诉诸人的现实需求,因此便存在一种伦理张力,即当它能以审美需求满足人的迫切现实需求,使人产生一种愉悦感、幸福感,此时具有正道德价值;而当它不能以审美需求满足人的迫切现实需求,使观众产生一种受骗感、失落感,此时具有一种负道德价值。所以,当部分影片通过偷票房、买票房制造虚假票房优势,鼓动粉丝盲目造势宣传,打擦边球捆绑优质资源营销等不正当手段给观众制造一种迫切需求,结果在审美趣味上并未满足大众的现实需求时,便给观众带来受骗感,从而形成信任危机。此外,工业体系下的高效率整合营销传播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够快速维护社会道德规范,也能够快速解构社会道德规范。同样,针对那些过度迎合大众流行文化,利用性、暴力等感官刺激吸引受众的电影,这种高效传播则可能对社会道德体系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在电影审查阶段,要仔细评估该类电影可能触发的负道德价值取向。
四、结语
邵牧君曾说:“电影作为文化商品,更主要的矛盾是商业与道德的矛盾。”[16]诚如是,电影工业体系下的电影生产,将电影视作一种文化商品,总是力求通过满足大众的欣赏趣味来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因此影像中的欲望生产不可避免。但人的欲望总是无止境的,当个人不受限制地追求欲望,最终带来的是相互间的侵犯和奴役。所以,道德作为一种人类为了达到利己目的而创造的害己手段,它能够在整体意义上求得更大的善和防止更大的恶。而对电影工业美学相关伦理命题的探究,则力求在整体意义上构建出电影工业伦理的观念。这一伦理观念将以电影工业活动中涉及的伦理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和审视这一活动中的各类伦理关系和伦理行为,揭示并树立其应具有的伦理精神、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以期建立一套电影工业伦理规范和价值评判体系。
从前文所述,便可窥见电影工业伦理对电影工业活动的一般性价值诉求:第一,在生产伦理中要肯定电影工业之于人的电影生产活动是一种“手段善”,但这一“手段善”只有落实为“道德善”才能对社会具有更大的伦理意义,像“电影工业4.0”建设对生产中公平正义的推动、国产电影工业体系的崛起对民族文化自信的建立等都是其“道德善”的具体体现。第二,在技术伦理中则要辩证地认识电影工业体系下的影像技术运用,一方面其能够拓展影像的表现力,给人带来更丰富、全面的沉浸式娱乐体验;另一方面则要关注这种对沉浸式体验的极度追寻,存在可能引发个体生理失衡的风险,因此,在工业化生产中要警惕影像技术制造极度体验的消费陷阱。第三,在传播伦理中要注重在接受层面能使观众在观影中体验到一种精神上的幸福感;在批评实践、营销传播层面则要尊重为己利他的市场经济道德原则。综上可见,电影工业伦理作为主体把握电影工业活动的一种伦理实践精神,它能更好地约束和调节人们的电影工业行为,进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善和防止更大的恶。同时,它也在理论层面与电影工业美学紧密呼应,对于促进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整体建设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