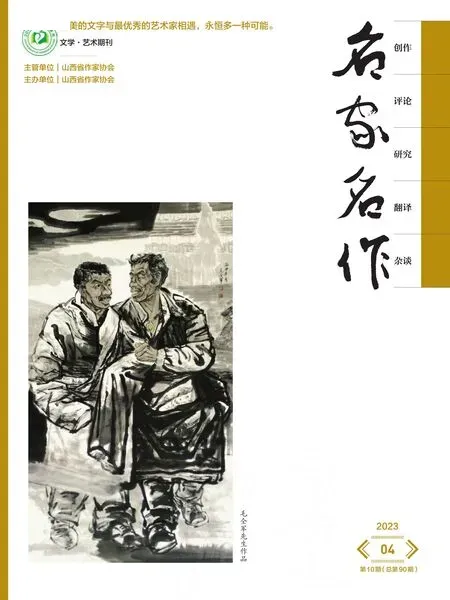困境与突围
——试析毕飞宇小说《推拿》中的苦难叙事
2023-08-14蒋明宇
蒋明宇
一、选题缘由与创新性
自 2000 年以来,毕飞宇的小说创作迎来了一次爆发期,这一期间他创作出大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创作风格日益趋向稳定。
毕飞宇的小说在文学形式和主题上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既有传统小说的文学艺术性,也有新颖的探究人性和社会现象的思想内涵。《推拿》[1]这部小说是极具代表性的,不仅是当代文学的一部代表作,更展现了作家毕飞宇对于日常生活和社会人情深刻的关注。作品中对真诚追求的揭示,体现了作家思想逐渐成熟和深刻的趋势。特别是小说对盲人按摩师这一社会特殊群体进行的细致描写,不仅在情节设置上给人以起伏和震撼,而且在刻画残障群体“苦难”生活方面更是入木三分,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此外,小说中不同角色面对困境时的“突围”行为也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社会价值和伦理研究价值,引导我们更加深入地反思社会问题的本质,并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
关于毕飞宇的小说,在文学创作方面,现有的研究重点在于其叙事手法、创作意识以及创作风格的转变;在社会伦理方面,较多关注点在于文中有关盲人群体的描写。
本文在分析研究已有学者理论的基础上,从全局化的角度入手,综合文学艺术价值与社会伦理价值,结合文学社会学、苦难美学等文学理论,从多个角度对《推拿》一书中盲人群体遭遇苦难时的行为进行分析,总结小说中的苦难叙事特点,展现盲人这一群体在困境与突围中的艰辛,从而在总结小说文学价值的同时分析其社会价值。
二、试析小说中的困境与突围
(一)事业上的困境与突围
在《推拿》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维生手段,这个群体是由“沙宗琪推拿中心”的一群盲人推拿师组成的。虽然这些推拿师都是盲人,但他们技艺高超,以中医推拿为维生手段,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治疗服务。这些推拿师们并不以个体为中心,而是以整个群体为主人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有所不同,他们深谙中医推拿之道,并将其作为自己生存的基础,这种特殊的群体生活方式也引起了人们对别样社会生活的思考。
小说的开篇,描述了按摩师沙复明的一段工作场景,他通过听声音、摸钥匙、闻味道,判断出来客的卡车司机身份,并据此对客人的病症做了准确判断,给客人来了一次满意的推拿,客人却留下一句“还是你们瞎子按摩得好”。从精确的判断、熟练的手法可以看出沙复明作为盲人在背后付出的艰辛,为了在众多推拿、按摩馆中占一席之地,他不仅练就一手好的推拿功夫,更是练就了在黑暗中“察言观色”的本事,而卡车司机的最后一句话不仅质疑了他的推拿技能,更触及了他内心深处的脆弱。情节的最后沙复明把脸对着卡车司机,强调他做的是推拿而不是按摩。沙复明站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始终不曾动摇,并用最好的服务回应了这句轻浮的话语,背后是他面对苦难的顽强。
叙事文的构成有四个层次:表达的实质、表达的形式、内容的实质、内容的形式[2]。这一段内容是以叙述沙复明推拿为主要形式,而内容的实质则是透过一段叙事,展现沙复明为了在社会上立足所付出的艰辛,而他对于客人最后一句话的回复,表面上仅是解释推拿不同于按摩,实质则是他面对他人的轻视,为自己职业尊严做出的抗争。
第一章故事叙述的是推拿师王大夫的故事。他从孤身一人打拼,到后来结识了盲姑娘小孔,为了赚钱成家,王大夫将积蓄全部投入股市,最后血本无归。王大夫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看不见的手”一词,股票市场的变幻莫测受操控于背后“看不见的手”,这里似乎还有言外之意,王大夫的手对于他自己而言也是看不见的,王大夫用看不见的手挣来的钱被股市中“看不见的手”卷走了。
王大夫听收音机这一叙事场面,用听觉的表达形式传递出王大夫积蓄流失的事实,表达的实质是盲人群体面对新兴事物的无所适从,对于时代变化、新潮迭起的不适,他们往往因为自身的特殊身份而被裹挟在时代的潮流之中,无法真正获得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和能力。
沙复明与老同学王大夫是众多盲人推拿师的缩影,两人都有各自的事业,尽管做着相同的事,但是有着不同的人生追求。毕飞宇着重描写的是推拿师们娴熟的技巧,异于常人的能力如听觉、嗅觉等,而这些能力的养成并非一朝一夕,都是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与锻炼得来的。在每个盲人的事业中,往往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却又有着更大的风险及更小的机遇。
(二)感情上的困境与突围
王大夫出生的时候是全盲,他把温情都寄托到了他的弟弟身上,把痛苦的感情留给了自己。他反复在精神上折磨自己,认为正是自己失明,所以家里才要的弟弟,他和家人十分宠爱弟弟。弟弟在溺爱之下,变得十分叛逆,甚至瞧不起自己的哥哥。弟弟欠下的赌债要王大夫去还,王大夫不惜用菜刀割伤自己,他认为一切家庭问题的源头都是自己失明,认为一切的源头都是自己瞎掉的眼睛。王大夫十分痛苦,这种痛苦不仅仅来自赌债带来的财务压力,更是源于对家庭、社会和人性的认知。为此,王大夫不断挣钱,试图用钱来赢得尊严与亲情,殊不知这些东西并不能被简单地用金钱来衡量。
王大夫在亲情中不断挣扎,在爱情中也深陷泥沼。王大夫的女友小孔也是盲人,家里不同意再找一个王大夫这样的全盲,于是她和王大夫私奔来到南京,进入了沙复明的推拿馆工作。在工作之余,小孔瞒着所有人和自己的父母斡旋,在这种关系中痛苦不已。王大夫和小孔的苦难更具有复合性,不仅在事业上,更在亲情与爱情中交杂。
除了基层的推拿师,沙宗琪推拿中心的合伙人张宗琪虽“身居高位”,却也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痛苦,因为他的继母曾说过要毒死他,所以他对于吃到口中的食物都非常谨慎,从小形成了多疑的性格,对任何感情关系都存在怀疑,以至于这种性格最终让他痛失了爱情。
每个盲人推拿师的感情和常人一样是多样的,有亲情、爱情、友情;却又是不一样的,有复杂、痛苦、多疑。小说中的每一位盲人按摩师,主要的感情纠葛、性格缺陷,都是因为“盲”而产生。他们的内心世界是一个凄苦的、残缺的世界,因此是十分渴望健全的[3]。他们希望能拥有健全的亲情,如王大夫的苦心付出;拥有健全的爱情,如小孔的进退回旋。他们都曾试图突围,却又局限于自身,最终却好似张宗琪,陷入困境苦苦挣扎。
(三)人生中的困境与突围
相比一出生就失去光明的人来说,还有一种人与之相比承受着更大的痛苦,那就是后天致盲的人。他们本来可以看见这个世界,但是突然有一天又失去了这一切,剩下一片黑暗,他们经历了两个世界,两个世界的中间是无尽的苦难。小马曾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有着无限的希望和美好的未来。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失去了看世界的能力。这对于小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经历了从光明世界到黑暗世界的巨大变化,这种体验令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痛苦,在治疗的过程中,他一次一次燃起了希望,却最终都破灭了。
第一次的困境是小马自杀后被救活,代价是在脖子上留下了一条骇人的疤痕。第二次的困境是精神上的压抑,在推拿中心里面他爱上了被他称为“嫂子”的——王大夫的女友小孔,小马对小孔深藏隐秘的情愫,是一种对母亲的依恋,这种爱是见不得光的,又具有青年荷尔蒙式的激情[4],在伦理与欲望的裹挟中,他找到了洗头女小蛮,把错位的爱施加在了小蛮身上。朱光潜在《谈美》中探讨艺术与游戏的相似性时写道:“他聚精会神到极点,虽是在游戏却不自觉是在游戏。本来是幻想的世界,却被他看成实在的世界了……全局尽管荒唐,而各部分却仍须合理。”[5]从小马自杀失败,到工作时对小孔的幻想,最后把小蛮想象成小孔,对人生的极度厌弃到自暴自弃,是他面对苦难做出的误入歧途的抵抗。
推拿中心的女技师都红是半路入行的,在此之前她曾是学音乐、弹钢琴的。在一次演出中,都红表演很失败,但是台下却响起了掌声,主持人站在她身边说“可怜的都红”是靠着全社会的好心人支持才“鼓起了活下去的勇气”,都红今天的演奏就是为了“报答”。都红内心十分疑惑,自己什么时候亏欠了社会,她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残疾被众人利用,她的音乐被用来烘托他人的“爱心”,从此都红放弃了音乐。社会的同情和怜悯让极具天赋的都红自尊心受挫,并在成年后陷入不断重复的创伤梦魇中,无法进入新的生活[6]。后来在推拿中心的都红,因为事故失去了大拇指,变成了“残疾人中的残疾人”,当其他推拿师纷纷慷慨解囊的时候,她却决定主动离开这里,与放弃音乐梦想的那一刻相似,在这里她因看不到出路感到绝望,她担心自己在感激里活一辈子。
小马与都红是相似的,他们的人生都经历了重大的转折,都经历了“两个世界”,与其他的盲人推拿师一样,失明是他们人生中绝大多数苦难的根源,他们尝试了许多办法,不论是从正面的应对还是逃避式的离开,面临苦难的突围一刻也没有停止。
三、小结
在史铁生的小说中,苦难在个体生命中的本质性存在是有寓言意义的,因为他还原的不是个体如何去应对生活中的苦难境遇,而是当苦难成为一种生命的本原后,应当以怎样的精神去飞升和超越[7]。而在毕飞宇的这篇小说叙事中,也将苦难作为生命的本原,每一个盲人按摩师自失明起就陷入了苦难之中,但有关精神的飞越与升华涉及不多,甚至展现了许多盲人按摩师的负面精神。
沙复明和张宗琪为了争“老板”地位的明争暗斗、小马为了爱欲的放纵与堕落……毕飞宇以一个特殊群体的特殊视角,人际关系的复杂、利益至上的寒凉,在盲人的感受下越发显得赤裸而残忍。
人总是希望世界中善与恶是明确区分开的,因为人有一种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评判[8]。但在《推拿》的叙事中,善与恶是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物之中的,人物形象因此而丰满。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五类[9]。在沙宗琪按摩中心这个社会圈子里面,盲人有沙复明、张宗琪这般争当老板的需求,有王大夫这般寻求尊严的需求,也有小马这般渴望爱情的需求。无一例外,他们都是在与自己的苦难斗争的人,在矛盾发展中展现不同的性格与特点。
伤害、疼痛是毕飞宇小说创作的主题[10],《推拿》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实施“伤害”的武器恰恰是人们最平常、最普通的目光。盲人生活中的苦难无处不在,由出生到死亡,伴随一生的黑暗作为最基础的苦难,对盲人的人生不断产生连锁反应,各类苦难接踵而来。对于苦难叙事的审美,不能将其异化。王朔说:“世界上最无耻、最阴险、最歹毒的赞美,就是用穷人的艰辛和苦难,当作励志故事去愚弄底层人。”苦难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那些经历过苦难的人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的成长和收获,但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决不是值得吹嘘或者美化的。苦难是人生中难免会遇到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够美化它,却也不应当在面对的时候失去希望和信心。相反,苦难可以成为我们窥视人生的窗口,从中得到更深刻的思想反思和精神上的成长与发展。
文学从创作到消费是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文化过程,这一过程不能不受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制约,而浸润着社会的思潮,反映着社会的风貌,直接或间接地回答社会问题[11]。《推拿》并不是一部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一味抬高盲人形象、贬斥主流社会的批判性质的小说,它反而通过描写盲人在面临苦难中的所作所为,真实地展现出盲人的日常生活,让读者看到盲人们不仅有乐观、活泼、积极、自尊自爱的一面,当然也有存在问题的一面。
《推拿》以苦难叙事展现小人物的困境与突围,从而以小人物写出命运之重,以日常生活呈现时代之重,这是其文学与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价值所在。《推拿》主要通过盲人推拿师的故事来呈现小人物的困境和挣扎,以此反映出社会的现实问题。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命运和独特的境遇,在竞争激烈的按摩行业中奋斗、追求生存和发展。这些小人物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劳作之中,寄托着对生活和未来的渴望,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苦难。小说中的这些人物故事不仅仅是为了呈现生活的困境,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他们在苦难之中持续追求自我价值以及捍卫尊严的勇气和决心。他们通过坚韧的信念和努力实现自身价值,从而突破命运的束缚,赢得自由和尊重。以此反映出时代变迁中小人物面对命运洪流所做出的抗争和突围。
除此之外,《推拿》所关注的日常生活细节和社会人情也给予读者强烈的现实感受。小说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现代的人际关系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和价值观念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社会学研究价值。
综上所述,《推拿》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对现实生活和社会问题的反思与表达。作者用真实的情感和细腻的笔触展现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生活困境,从而引领读者思考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和社会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