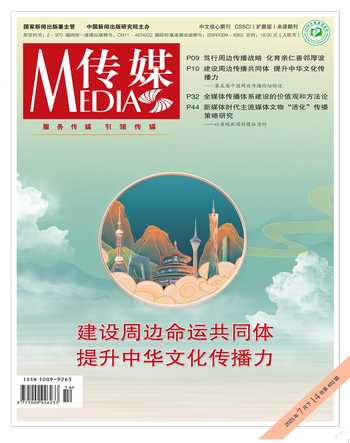跨境铁路的周边传播理论功能浅析
2023-08-13陈沫武思权
陈沫 武思权
“传播”(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与“交通”(Transportation)存在与生俱来的紧密联系。从物质交往来看,造纸术和印刷术传遍世界之前,人类社会的信息和物质交流主要依托于水陆交通。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提及了“路”对沿线国家的影响,但侧重于承运的货物而非本体。从中国交通银行史来看,其因“多为赎回京汉铁路之故”而得名,但不止“铁路”,其他如“电线、邮政、轮船”等也包含在“交通”一词中,其英文定名为“Bank of Communication”,可见“交通”与“传播”的意义是统一的。若从词源上追溯,据雷蒙·威廉斯考证,Communication一词在20世纪之后,新闻、广播才逐步替代交通运输成为讯息传输和社会联系的主要手段,并逐渐衍生出“传播媒体”的概念,而17世纪之前,传播主要用于指代“道路、运河和铁路”等通讯设施。
传播从交通的意义中分离后,麦克卢汉则重新关注到了“路”。他用“世界因货物运输的媒介——铁路和飞机的革命性而改变,而非货物本身”来说明“媒介是人的延伸”,特别强调了路的媒介属性。此后,施蒂格·夏瓦、约翰·杜汉姆·彼得斯等万物皆媒论学者,认为铁路本身及其建设与使用过程对社会互动、政策施行和文化交流均具有裹挟性的“媒介逻辑”。
跨境铁路是天然的跨国媒介
铁路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跨境铁路更能体现出周边传播的特征。党的十八大报告到二十大报告都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和“效能”。不可否认,传统的国际传播主要依靠跨国媒介,但“跨境铁路”是周边传播的重要补充。周边传播理论认为,狭义的周边传播指“国家在主权辖区边界两侧进行的综合性信息传播活动”,且具有“主题多样性、渠道立体性、效果直接性、适度接近性”等特征。如果将边境线作为内外周边的分野,那么国门口岸就是周边传播最为集中的场域,连接内外的交通方式就勾连起相邻国家间的周边传播。可以说,铁路的交通属性决定了其具有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媒介功能,跨境铁路自然也具有跨国传播媒介的天然属性和功能。这种天然性不仅超越了现存的以实际受众为中心的跨国媒介的界定范围,更创造性地以地缘、语言和文化为机缘将跨境铁路演变成了国际文化交流折扣最低的周边传播媒介。
正如传播不能只依靠媒介存在,周边传播也不能只依靠跨境铁路的存在而产生。跨境铁路和列车是给过境国家人民带来的最直观、也是最有效的信息。但最具有扩散和传播功能的还是跨境铁路上的乘客和货物,他们本身携带的“信息”既包含人文因素,也包含科技因素,当然也包括语言、知识和风俗习惯等文化信息因素。因此,无论是国际旅客联运上搭载的乘客,还是国际班列所运输的货物及其公司,都可以被称之为广义上的“传播者”。周边传播理论认为,近则似,似则通,传播的边际效用随空间距离增大而递减。也就是说,在周边国家之间穿行的国际铁路,周边传播功能最强大。离列车始发地越远的国家,跨境铁路或列车的传播功能越低。例如,中蒙跨境铁路上大部分乘客为蒙古族,和蒙古国在文化、语言上基本相同,相互间的传播几乎畅通无阻。而不同区域的跨境铁路乘客则呈现不同的人口特征,差异化的传播主体无疑会降低包括跨境铁路在内的所有跨国媒体传播的效能。借由跨境铁路向外周边传播的“信息”所抵达的人群和目的地即可理解为“受众”。与其说这是“信息”的跨境传播,不如说是个体借由跨境铁路直接同外周边的主体完成了面对面的人体传播或物体传播。这些“信息”不具有新闻的时效性特征,传播内容的可控性提高,存在固定的流动方向(即固定的边民往来和商品运输),且品质稳定。在铁路建设和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中国标准、中国方案”即为“传播效果”,相比于传统跨国媒体的效果检测需要许多间接的测量指标,跨境铁路的效果“可观可感”。2021年底通车的中老高铁让老挝民众直接体验了中国高铁运行的速度、安全和便捷,而铁路全线采用的中国技术、标准和运营模式,更是对“中国形象”持久感知起着潜移默化的效应。
跨境铁路勾勒了外交的“他周边”
周边传播理论中,边缘不仅仅指代圈层内的“地理周边”,还包括以认同而存在的“影响力周边”。跨境铁路也可以被区分为地理意义上的“跨境”和影响力意义上的“跨境”。因此,跨境铁路的建设不仅是中心国家对周边国家经济周边和市场周边的延伸,也是文化周边和外交周边在物质层面的投射。
从国际史来看,克里斯蒂安·沃尔玛尔曾说:“欧洲各国发展了它们的鐵路,而美国铁路发展了它们的国家。”在世界列强的殖民史和向第三世界的扩张史上,铁路成为必备的工具,它通过“垄断路权”,侵略“国家主权”,进而维护“殖民霸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欧美列强跨境铁路的建设史,就是对弱小国家的侵略史和文化与价值观的传播史。
晚清朝廷主权的丧失就是以铁路的失控为标志的。而铁路本身不仅改变了旧中国的社会面貌,还为列强进一步侵略和掠夺中国提供了交通基础。1865年起,列强从勾结清政府筑路事务入手,逐步掌控中国。如果说军事侵略是一种恶意的周边传播,作为媒介的跨境铁路就是其周边传播半径的“延长器”和周边传播进程的“加速器”。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后,借助地缘优势在六年间修建了将我国东北、朝鲜、日本甚至苏联链接起来的跨境铁路网。此时,跨境铁路作为运输武器、物资、军队、劳工的媒介,成为“战争输血管”,铁轨的延伸象征着势力范围和政治霸权的扩张,无论是铁路本身,还是其运送的物资,都是国家意志和价值观的物化。而当时的非洲、印度和中南半岛都被帝国主义瓜分并殖民,铁路的建设也如火如荼。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收回了列强巧取豪夺的中国铁路主权,并以其他国家建设的铁路网为基础,开始建设自己的跨国铁路(见表1)。中国不仅在沙俄建设的中东铁路和日本建设的辽朝铁路基础上拓展革新,也在中国南部、西部等地以边境口岸为核心进一步拓展建设。截至2022年,中国已经同6个国家联通了13条直接跨境铁路,其中有9条国际旅客联运铁路,另有通向6个国家的5条铁路正在规划建设中。如今,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依托周边口岸建立了六大跨国经济走廊,并布局中南半岛铁路网、新亚欧大陆桥和第三亚欧大陆桥(见表2)。恰如中国外交部原部长王毅所说,“铁路修到哪里,中国的影响力就能延伸到哪里”。

在周边传播理论中,中国在海外援建的铁路可视为远离本土的“传播飞地”。作为国家周边传播的海外根据地,铁路将“周远”转化为“周边”,并随之启动“晕染模式”下的新一轮周边传播。当中国在中南半岛铁路网的逐渐形成、中国援建的匈塞跨境铁路通车、中国援建的非洲铁路网更加完善以后,跨境铁路区域内的通达系数、经济活力和公共外交的潜能都会被整体和成倍地激活。
跨境铁路承载的文化属性与战略价值
跨境铁路主要是为了连接、疏通和加强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据统计,截至2022年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6.5万列,运输货物超过600万标箱,货值3000亿美元,中欧班列不仅承载了大量的货物,实现跨国贸易的高效和快捷外,同时赋能了多边口岸的经济建设。此外,跨境铁路也可以促进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网络。在跨境铁路沿线的城市,跨境铁路的建设和运营也可以带来就业机会和商业机遇,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跨境铁路的速度和运力也在不断提升。正如网速的提升实现了社交媒体传播效果的优化,跨境铁路运能与运效的提高也突破了时空限制,强化了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发展。
跨境铁路对周边国家的文化交往影响更加深远。跨境铁路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文化媒介。1903年,俄罗斯控制的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通车后,大批俄国移民随之涌入未开发的黑龙江省,抢占中国大量土地和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俄国文化元素。因此,当年的中东铁路可以说对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入侵。但是,这种“被周边传播”的过程,也塑造了当地社会独特的“内周边”社会风貌。哈尔滨火车站或许是铁轨的终点,但更是下一阶段“内卷模式”周边传播的起点。铁路沿线以哈尔滨为龙头延伸出一个囊括工商、矿产、航运和金融等产业的经济合作体——“中东铁路经济”,刺激当地从人烟稀少的小农社会快速發展为“中俄合璧”的国际大都会。十月革命后,苏联控制了这条铁路并由此将共产主义传入中国。作为这条“红色丝绸之路”最紧密的周边圈层,铁路沿线率先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的独特场域。在这里,马列主义从思想开始逐步渗入语言、习俗等文化领域,进而在经济、交通和城市规划等方面逐渐强烈地显现出相应的意识形态。
综上所述,跨境铁路的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媒介属性同样强烈。跨境铁路具有的承载性、连接性、制度性、企业性功能使其成为一种广义的社会“媒介”。以路为媒,化界为埠,跨境铁路不仅可以在现实中有效发挥附加的周边传播价值,也可以在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周边外交战略实施、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周边传播理论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7ZDA28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编辑:钱尔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