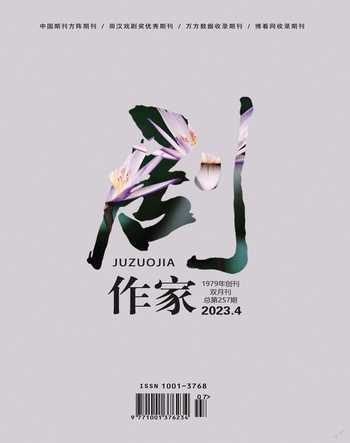刘萤与龙江剧音乐
2023-08-09张继昂
张继昂
摘 要:刘萤(1924—2007)是我国老一辈资深戏曲作曲家,一生致力于戏曲音乐的创作与研究,是龙江剧剧种音乐的奠基人和主创者。他数十年孜孜不倦、潜心探索、勇于实践,为龙江剧音乐留下了可贵财富。今天,我们对他的作品及创作理念进行研究,并做出客观、中肯和理性的评价,这不仅关系到刘萤本人,同时也是为了龙江剧音乐的未来发展和繁荣,为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新兴戏曲剧种音乐在新的文化生态环境下的创作规律和基本特征,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从而为丰富、充实我国戏曲音乐的理论宝库做出贡献。
关键词:龙江剧;音乐结构;创作理论
一
刘萤是从事龙江剧音乐创作的第一代作曲家之一,曾先后为七十余出龙江剧剧目作曲。他的重要贡献在于:依据中国戏曲音乐的基本特征和普遍规律,通过创作实践,从宏观上对龙江剧剧种音乐的总体框架进行了精心和全方位立体式架构,归纳起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母体音乐进行科学分类,形成龙江剧剧种音乐的唱腔系统
唱腔是剧种音乐的主体,是抒发情感、刻画人物的主要手段。龙江剧音乐的前身是二人转、拉场戏音乐,而作为曲艺(走唱)音乐的二人转音乐演变为戏曲(剧)音乐,其唱腔主调的确立是第一要务。为此,刘萤在对母体音乐进行科学分析和归纳后,于1962年提出了龙江剧“三种唱腔系统(嗨腔、柳腔、帽腔)”的构想[1]。在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后,现在看来此一提法是适时和富有艺术眼光的。它的主要特征如下:
1.系统性。三种唱腔系统,全部涵盖了二人转、拉场戏唱腔音乐。(1)嗨腔。包括“双玩意儿”全部主要唱腔曲调,是二人转音乐的主体。如【胡胡腔】【喇叭牌子】【文嗨嗨】【武嗨嗨】【抱板】等,可作为龙江剧唱腔未来发展的主体或一部。(2)柳腔。是拉场戏的主要唱腔曲调,主要包括【红柳子】和【穷生调】曲牌。其音乐已初具戏曲音乐的形态特征。如【红柳子·排字句】以叙事见长,而【红柳子·苦悲迷子】则长于抒情,可成为龙江剧音乐的基本曲调。(3)帽腔。即二人转的“小帽”音乐,多是民歌小调。可作为主体唱腔音乐色彩的调剂而运用于以上两个腔系中间。
2.鲜明性。三种唱腔系统完整地体现了广义二人转音乐的风格特色。母体音乐风格的鲜明、独特为龙江剧音乐浓郁的地方色彩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也使后续音乐风格的发展有了本源。
3.丰富性。二人转的唱腔曲调历来就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之称。其曲调种类繁多、色彩纷呈,既有【武嗨嗨】【四平调】【三节板】等叙事性曲调,【文嗨嗨】【悠武嗨】【红柳子·苦悲迷子】等抒情性曲调,同时又有【胡胡腔】【喇叭牌子】【打枣】等载歌载舞的曲调。如此丰富多彩的曲调,为日后龙江剧唱腔音乐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1980年,龙江剧进入“归路”(进一步规范)的发展阶段。此时,刘萤在三种唱腔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地提出了以【四平调】【穷生调】作为唱腔主调,以【红柳子】【文嗨嗨】【武嗨嗨】等曲牌为辅助曲调,以及要进行“四定”(定腔、定调、定板式、定过门)的构想[2]。并通过《结婚前后》《双锁山》《皇亲国戚》《邻居》等剧目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二)确立龙江剧音乐的结构形式
对于一个新创建的地方戏曲剧种来说,确定其唱腔音乐整体的结构形式,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而采用和形成怎样的、体现何种美学原理的结构模式,是体现一个剧种音乐成熟的重要标志。为此,在龙江剧创建初期(1961年),省委召开了“加强龙江剧创造座谈会”,会上提出了运用曲牌联接、板式变化或两者相结合的戏曲音乐结构。刘萤参加并主持音乐部分。而在1980年的“归路”研讨会上,刘萤又进一步提出龙江剧音乐的结构形式是“以主调贯穿联接并融合辅助曲调的板式变化與曲牌联缀相结合的音乐体制”,即综合体作为未来的结构形式。可以说,综合体的提出具有前瞻性,是在对板式变化体和曲牌联套体之利弊权衡后做出的理性选择。
鉴于综合体的复杂性,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刘萤主要先进行了板式变化体(以下简称板腔体)的创作与实践。
首先,通过一定时间的实验与演出,形成了齐全的主体板式。如慢板、中板、原板、快板、紧板和散板等。并对每一种板式基调的形态特点都一一进行了规范。如【四平调】中的中板,为一板一眼四分之二节拍,中速,上下句结构。每句四小节,上句落音为mi(3),下句落音为do(l),甩腔落sol或la(5或6)。
其次,对一些附属板式如导腔、搭腔也进行了创作尝试,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对于一些程式性的、具有结构功能的腔句,如留腔、甩腔(半终止)、切腔、蹾腔、锁腔(完全终止)等,使其逐步在创作中形成龙江剧特色的艺术形式。
最后,进行各种基调的板式变化及成套唱腔的实践。1.单一基调的板式变化。如《结婚前后》一剧中董雷演唱的“结婚至今整三天”唱段,就是以【穷生调】为基调,由中板、慢板、中板和紧板加甩腔构成。2.同一唱腔系统不同基调的板式变化。如《李双双》一剧中李双双演唱的“我身边走出了孙喜旺”唱段,是以【文嗨嗨】和【四平调】为基调,由【文嗨嗨】中板、【四平调】中板、【四平调】紧板、【四平调】散板、【文嗨嗨】慢板加帮腔等构成。3.不同唱腔系统、不同基调板式连接的成套唱腔。如《皇亲国戚》一剧中杏花、窦皇后演唱的“憨郎他滴滴鲜血往下淌”唱段,由【红柳子】散板、【武嗨嗨】紧板、【哭迷子】散板、【哭迷子】原板、【花四平】慢板、【四平调】中板、【花四平】中板(锁腔止)等构成。是一段不同唱腔系统(柳腔与嗨腔)不同基调板式联结的成套唱腔。
(三)反调唱腔的初步尝试
综观我国属板腔体结构的戏曲剧种音乐,一般都有两个唱腔系统。如梆子腔有花音和苦音(秦腔),皮黄腔有二黄和反二黄(京剧),评剧则有正调和反调等。反调唱腔的出现,是由于伴随着剧种的发展,剧目内容的扩展,剧中不同个性、身份人物的增多,以及戏剧矛盾冲突的尖锐和剧中主人公内心感情的起伏、多变等因素,原有的单一唱腔已不适应戏剧情节的发展,故反调唱腔应运而生。为适应龙江剧的发展,刘萤则进行了龙江剧反调唱腔的创作实验。如《映山红》一剧方秀云演唱的“湘江千里日夜流”唱段,就是由“反四平”中板和紧板构成。诚然,这方面的实例不多,但剧种创建的初期就已考虑到龙江剧应有反调唱腔系统,其设想是难能可贵的。
(四)以母体音乐为基础,创作龙江剧板腔体“大慢板”唱腔
刘萤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相继在一些剧目中创作了一定数量的“大慢板”唱腔。如【红柳子】慢板(《红云岗》英嫂唱“忆当年我的爹爹欠租难偿遭残害”和“点着了炉中火放出红光”唱段)、【穷生调】慢板(《蝶恋花》杨开慧唱“绵绵古道连天上”唱段)和【花四平】慢板(《花香蜜甜》金梅唱“苇沙河里的水为什么不平静”唱段)等。
这些唱段共同的特点有:1.富于歌唱性和旋律性,抒情性更强;2.板起板落,曲调连贯,起伏婉转;3.词曲交织,形成更为细腻的“小腔弯”;4.句幅较长,有长大的拖腔。与原早期的慢板唱腔(眼起板落,曲调简约,语言型旋律色彩较浓)相比,大慢板唱腔将原来慢板的抒情性功能提高了一个层次,表现剧中人的内心感情和刻画、塑造人物的音乐形象更为深刻。
“大慢板”唱腔的出现,对于自然形成的地方戏曲(亦指清末民初崛起之民间戏曲)剧种音乐而言,一般要在剧种音乐成型后的一段很长时间后才会出现,而且打着鲜明的专业音乐创作印记。如评剧,从剧种音乐形成的1910年至20世纪的50年代末,其抒情性的板式就只有“正调慢板”(还包括“反调慢板”)。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由专业音乐工作者在掌握了评剧唱腔传统规律并进而突破其规范,以及吸收外来因素的情况下,才逐步创作形成了“凡字大慢板”“正调大慢板”“反调大慢板”“越调大慢板”等。与此相比,刘萤创作的龙江剧“大慢板”唱腔,无疑是超前的。它的出现,丰富了龙江剧的唱腔音乐,使龙江剧音乐的戏剧化程度有了进一步提升。
但平心而论,与其他古老且比较成熟的剧种音乐比较,龙江剧“大慢板”唱腔还有进一步锤炼和完善的地方。如唱字的节奏还应进一步展宽;一些词组(句逗)应考虑形成富有特色、更为细腻的短小行腔;句幅还要加长、舒展;甩腔也要扩展、延伸。使之旋律起伏有致,节奏松紧得当,色彩对比更强烈,具有更浓烈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
(五)男女分腔的实践与探索
戏曲演唱的男女分腔,是戏剧音乐特有的命题。对于老的、自然形成的剧种来说,是一个颇为棘手的课题。有的剧种解决得好,且很完善(如京剧);有的至今仍处在解决之中;而有的则在专业音乐工作者成为创作主体后才真正得到解决。
对于龙江剧音乐来说,男女分腔也是创作中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按照刘萤的说法,主要是通过同腔同调、同腔异调、异腔同调、异腔异调等四种方法解决,但重点解决同腔同调的男女分腔。几十年来,刘萤通过在《阮文追》、《紅云岗》、《寒梅花》(柳腔)、《李双双》、《结婚前后》、《邻居》(嗨腔)、《花香蜜甜》、《映山红》(花四平)等剧目的实验中,如男女都用“大嗓”(即艺术真声声型),那么在分腔上则采用男女在自然有效音区上相差四五度的方法,使之发挥各自富有光彩的音域。而如男声是“大嗓”,女声是“真假声混合声型”,为了发挥女声的优长,则在创作上大体处在同一活动有效音区。可见,刘萤在男女分腔的创作实践中是不拘一格的。至于一些二人转传统的分腔方法,如搠尾巴调、平着唱、走矮腔等,在创作中都适时而又灵活地运用。可以说,其男女分腔总体上是成功的。当然,截至目前,该实验还有一些需改进的部分。如分腔如何保持唱腔曲调的风格特色,即分腔时如何稳定唱腔曲调(特别是下句旋律和落音)中具有体现其韵味、风格特征的乐汇和音调,仍是在实践中须进一步解决的课题。
(六)创作理论建树
刘萤是一位有一定理论素养的龙江剧专业作曲家,具有较丰富的戏曲音乐创作经验,且能将此归纳、概括和抽象出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在与他长期的工作接触中,我们会不时听到他对其创作经验及实践感受的阐发。本人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个部分。
1.节奏说
主要是指板腔体音乐创作。他多次谈到,板腔体各不同板式的区别,从本质上讲是节奏型态的不同。如“慢板”“中板”和“快板”,各自有不同的节奏型态,从而导致不同的表现功能。道出了板腔体音乐作为戏剧性更为强烈(与曲牌体比较)的音乐之核心问题。
2.布局说
在刘萤参与创作的七十多出剧目音乐中,大多数是他一人独立完成的。他常说,一个剧目的创作,在唱腔的安排上,要有统一筹划和整体布局,不能平分秋色。哪个场次是音乐表现的重点部分,哪个是一般部分,哪个只是过场戏一笔带过,都要事先安排好。重点部分的唱段,一定要下功夫多着笔墨重点渲染,最大限度发挥音乐的特长(一般为抒情性唱段)。一般部分多为过场戏的非重点部分,虽不一定是重点唱段(多为突出语言特性的叙事性唱腔),但也要写好。布局说体现出作曲家对大型剧目音乐创作的整体驾驭能力。
3.“稳定与变化”说
在龙江剧音乐创作中,如何处理好稳定剧种唱腔风格与变化发展的相互关系,刘萤曾多次讲过一个“二十三字口诀”,即“头变尾不变,尾变头不变,两头不变中间变,上下四五度移”。以下做一简要分析。
(1)“头变尾不变”。就一个唱段或一个曲调而言,“头变”就是对曲调的开头旋律进行发展变化;“尾不变”则是对该曲调的结束部分包括调式、旋法、落音、节奏等维持原样和不变动。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保持唱腔曲调不走味和又有变化、有新意之间的关系。
(2)“尾变头不变”。“尾变”即对一个唱腔的终止(或半终止)部分曲调进行发展变化;“头不变”则是曲调的开头部分保持原有框架不动。
(3)“两头不变中间变”。可做两种理解:一是较长、较大的唱段(套腔),二是较单一和短的唱腔曲调。起始和结束部分保持原来的曲调特征,而中间部分则进行发展变化,或旋律方面,或节奏方面,或速度力度方面等等。就一个长大的成套唱腔而言,“两头不变中间变”既稳定了剧种唱腔音乐的风格,又有变化和对比;既完成了戏剧所赋予音乐的表现任务,又给予了充分的空间使音乐发挥其优长及功能,以满足欣赏主体审美愉悦的需求。
(4)“上下四五度移”。“移”即“移位”(严格移位和自由移位)。即唱腔曲调最体现其风格、韵味的部分,在另一个音区“再现”。诚然,“移位”是我国传统音乐经常运用的一种变化发展旋律的手法,但刘萤则将此发扬光大。
以上“二十三字口诀”,可以说是刘萤长期从事戏曲音乐和龙江剧音乐创作的经验总结和概括,也是他的得意之笔。其对于后起之龙江剧音乐创作工作者,应该说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指导价值。
二
刘萤的龙江剧音乐创作,特别在第一阶段(1960—1982),其贡献不可磨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并取得了可观成果。但另一方面,业内人士对其创作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
(一)剧种音乐风格与母体音乐
剧种音乐风格,既是一个抽象、笼统的概念,又是一个具体的、能从听觉感受到和体验到的概念,实际是一个韵味、特色与母体音乐亲缘远近的问题。虽然,一个剧种音乐的风格体现在各个层面(演唱的发声、演唱形式、润腔,乐队伴奏和主奏乐器的演奏技巧、风味等),但主要的具体表现则是唱腔的某一曲调在调式、旋法、节奏、特性音级、特征乐汇(音调)等诸要素反映母体音乐形态特征的程度上。
平心而论,在刘萤创作的作品中,不乏有音乐风格较为鲜明和成功的唱段(大多存于【四平调】和【花四平】中),但确也有一些唱段,演员和同行人士感到韵味不浓,离母体音乐较远。何故?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从具体的唱腔形态特征入手深入分析和探讨。
1.“柳腔”。“柳腔”是以【红柳子】为主要曲调。凡熟悉二人转、拉场戏音乐的行家都知道,传统的【红柳子】曲调是角调式。尽管其【红柳子·苦悲迷子】的下句甩腔落低音la(6),但紧跟其后的衬腔则落mi(3);而【红柳子·排字句】上句落do(l),下句则落mi(3)。故总体上,【红柳子】是一个角调式个性很鲜明的曲牌。但刘萤创作的【红柳子】唱腔,则将其下句落音改为do,不少甩腔也落do音。虽然大段唱腔中间,有时出现突出mi和la音的旋律片断,但审视整个唱腔旋律的调式个性,是以宫调式占主导的。为此,调式、调性的改变,势必导致旋法、音调、特征乐汇等体现母体音乐风格、韵味诸形态特征及表情意义的变异。
2.“嗨腔”。众所周知,“嗨腔”中的主要曲调是【武嗨嗨】,而【武嗨嗨】是商调式。在二人转众多常用曲牌中,与【武嗨嗨】同宫系统的曲牌还有【胡胡腔】【喇叭牌子】【文嗨嗨】【抱板】等。尽管其中个别曲牌为其他调式(如【文嗨嗨】为徵调式,【胡胡腔】为商宫混合调式),但作为一个严密的结构整体,它们是由商调式来贯穿的,故“嗨腔”的主导调式应是商调式。而正是商调式,以及它的各种跳进旋法和极具色彩的特征乐汇和音调等诸多因素,形成了“嗨腔”热情、高亢、火爆、爽朗的风格特色。
笔者在对刘萤创作的“嗨腔”许多唱段反复吟唱并深入分析后,感到以【文嗨嗨】作为“嗨腔”的主调进行板式变化是值得商榷的。这其中主要是板式变化基本曲调的曲体结构应是上下句。因为上下句结构的唱腔曲调可塑性强,便于进行各种变奏,而【文嗨嗨】从音乐上是“起、承、转、合”四句体(由四个小分句构成)结构形式。一般讲,以四句体结构的曲调进行板式变化难度大且缺乏可变性,故我国传统戏曲音乐凡属板腔体的梆子腔和皮黄腔诸剧种唱腔基本曲调(如梆子腔的【二六板】【二性】,皮黄腔的【原板】)的曲体结构,都不是四句体而是上下句体。此外,由于【文嗨嗨】是徵调式曲牌,容易在创作中将商调式曲牌(如【武嗨嗨】)的一些很有风格特色的衬腔、大过门弃之不用,从而使展现传统“嗨腔”音乐的风格特色大打折扣。
3.关于【穷生调】。【穷生调】又称【盘家乡调】【擀面调】【靠山调】等,在传统拉场戏中,是仅次于【红柳子】的主要唱腔曲调。它的基本曲调的形态特征是上下句带甩腔曲体结构。其落音为第一番上句落re,下句落低音sol;第二番的上句落mi,下句落sol;段落结尾甩腔常落mi音。近年来,甩腔落音也有落在sol音的。为此我们可以认定,【穷生调】的基本调式为角调式或角徵混合调式。但我们吟唱和品味刘萤创作的以【穷生调】为主调的唱腔时发现,其旋法、音调、落音离传统的【穷生调】相距较远。如甩腔大部分落do音,其旋律音调与【打枣调】的终止乐句颇相似,这样,在择调上选用【穷生调】的意义已失大半。当然,传统的【穷生调】带有一定程度的泣诉、哀怨之感,有“穷生”气质。但在选用时,完全可以在保留其特征乐汇、旋法和落音的基础上做适度调整,而且在演唱上也可以弥补。
刘萤是处在龙江剧剧种创建初期从事音乐创作的作曲家。此阶段应是一个构成剧种音乐风格诸要素(音阶、调式、旋法、落音、音调、节奏、音色等)逐步积累的阶段,而且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在与观众的互动中被认可。否则,初期的音乐创作离母体音乐很远,那么其后续的发展时期——第二、三代音乐创作者其作品所体现的龙江剧音乐风格,将会演变成何种样子,那是不言而喻的。
(二)结构形式
龙江剧唱腔的结构形式,是刘萤几十年音乐创作给予关注度最高、着力最多的部分。深入分析和思考,笔者感到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1.板式变化“度”的把握问题
以变奏为原则进行板式变化的音乐创作,可以說是刘萤最为熟悉,且最得心应手的领域(因此前其长期从事评剧音乐创作)。综观他的作品,一方面产生了一定的音乐成果和积累了较丰富的创作经验;但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个在板腔体音乐创作中对板式变化“度”的把握和分寸掌控的问题。下面是从他创作的许多唱段中整理出的进行板式变化的唱腔曲牌:
①【红柳子】【穷生调】柳腔
②【文嗨嗨】【武嗨嗨】【喇叭牌子】【锔大缸】等嗨腔
③【月牙五更调】【合钵调】帽腔
④【四平调】【花四平】四平调和花四平类
如此众多的曲调都要做板式变化,需要吗?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值得深思。众所周知,在我国属板腔体戏曲音乐结构的剧种中,只有皮黄声腔的剧种音乐是两个声腔系统(西皮、二黄)。其他如梆子声腔诸剧种音乐,都是单一声腔的板腔体音乐。当然,作为一个剧种音乐,其唱腔丰富多彩总比色调单一要好。但丰富多样,总要有一个“度”,特别在剧种音乐形成的初期。从中可以看出,在此期间,其音乐创作就有“期望过高,摊子过大”的欲求。此外,既然“嗨腔”和“柳腔”已各自形成一个唱腔系统,那么在“嗨腔”的成套唱腔中,就不宜插入【红柳子】曲调。否则两个腔系相互交叉、包容,将缺乏腔系自身的稳定感,淡化了各腔系风格的鲜明性和独立性,从而显得杂乱而无章法。这与京剧西皮套腔中一般不会夹入二黄腔曲调是同一道理。
2.曲牌体问题
在刘萤的七十多部龙江剧音乐(唱腔)作品中,真正按照组曲原则,即将若干曲调按一定规范相互联缀构成的唱段较少。这表明,刘萤更多地关注于板式变化体的音乐创作。
二人转音乐的结构形式是曲牌体,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我国,大凡其剧种母体是曲牌体音乐(多为源于民间歌舞类型的剧种),那么,其剧种音乐形式的初期,一般都沿袭母体音乐的结构形式。其有两个优长:一是体现对母体音乐的继承性,便于风格的稳定和积累;二是能将更多的母体曲调纳入到结构的框架内。可见,龙江剧音乐在其形成初期的时间内,搞曲牌体音乐创作,有其规律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当然,这种曲牌体已不是原来母体音乐那种结构模式,它应是更高级、更有规范和章法的戏剧化的曲牌体音乐。鉴于曲牌体音乐所具有的歌舞性(边唱边舞)特征,故初期编演一些且歌且舞的小型剧目(两小戏、三小戏),以及选择一些二人转曲目作“拆出”或“拉开场”演出处理作为龙江剧的剧目积累,对后续发展是大有益处的。回顾这段历史,现在看来,当初的曲牌体音乐创作时间短、作品少,建院初期就忙于板腔体音乐创作,显然是有些操之过急了。
3.对综合体的思考
刘萤在龙江剧音乐的整体架构中,对唱腔的综合体结构形式提出很早,说明其起点很高。从资料显示,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演变:一、初期(1961—1962),运用曲牌联缀、板式变化或两者结合的戏曲音乐结构形式;二、中期(1962—1980),进行板腔与曲牌综合使用实验;三、后期(1982—),以主调贯穿、联结并融合辅助曲调的板式变化与曲牌联缀相结合的音乐体制。
以上三个时期综合体的提出,有的是刘萤亲自提出的,有的则是在他参与下拟定的。
应该说,从理论上讲,搞综合体无可厚非。但也应看到,综合体的结构形式在传统戏曲音乐中是否客观存在在理论界是有争议的。而我们认为的一些剧种存在的综合体音乐,在一些权威人士看来,其实不是综合体音乐——要么是以板式变化为主,以某些曲牌联缀为辅的结构形式;要么是以曲牌联缀为主,一些曲牌做相应的板式变化的结构形式。前者仍属于板腔体,后者则仍属于曲牌体。其运用的难度在于两者的均衡和互融一体。故此,笔者认为,尽管龙江剧是新剧种,但仍应遵循由简到繁、由点到面、逐步积累和全面铺开的发展轨迹,先搞曲牌体,待有一定积累后转入板腔体的实验创作。最后曲牌体和板腔体创作有丰厚的经验逐渐聚集后再搞综合体的创作,这样才能水到渠成。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刘萤当时的良苦用心,想在尽短的时间内把龙江剧音乐搞成一个成熟、完善,至少与评剧音乐比肩的戏剧化音乐。
从中国戏曲音乐史的角度,新兴剧种音乐创作是一個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全新课题,无章法可依循,刘萤对此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其成果、经验和贡献是不可抹煞的。他留下的七十余部作品,对于已进入第二个五十年发展历程的龙江剧剧种音乐艺术及后辈的龙江剧音乐专业创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注释:
[1]刘萤:《龙江剧音乐概述》,《中国戏曲音乐集成·黑龙江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4,第644页
[2]刘萤:《谈龙江剧音乐》,《戏曲研究》第八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第174页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 王彩君 刘心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