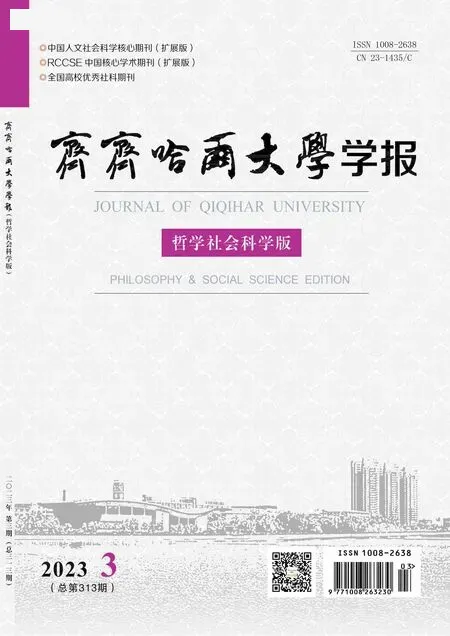迟子建研究述评
2023-08-08巴德玛拉
巴德玛拉,杨 春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74)
从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迟子建就以温情诗意的创作风格、硕果累累的创作成果和近四十年来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一直被许多学者、专家跟进研究,成为了中国文学界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2008年10月,迟子建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学界对其研究进一步加强。创作研讨会、学术论坛频频召开,如2008年12月20日,西北大学召开了“大学教育与西北大学作家群现象研讨会”;2009年6月30日,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审美文化与龙江文学研究中心举办了“迟子建、阿成文学创作研讨会”;2015年10月21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和文学院主办了“迟子建创作三十年研讨会”;2016年11月13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召开了以“苍凉与诗意”为主题,围绕迟子建文学创作为讨论的“第十季喻家山文学论坛”等。还有一些学者围绕迟子建的文学作品出版了研究专著,如从琳编著的《生命向着诗性敞开——迟子建小说的诗学品质》(吉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宋秋云编著的《极地·远方:迟子建文学创作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和李会君编著的《迟子建的乡土世界与叙事精神》(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据知网查询,通过答辩的迟子建专题研究的硕、博论文有三百余篇,与获奖前对比,近年来对于迟子建的研究视域进一步拓宽,作品中的许多问题得以新一轮的探究。
一、迟子建研究视域的拓展
(一)关于迟子建生平与创作历程的研究
迟子建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学者们对其生平、家世、成长经历以及创作历程的研究进一步升温。如方守金在2002年出版的《北国的精灵——迟子建论》的基础上完成的《文艺学与民间情怀》,对迟子建的生平、成长经历、创作历程、创作题材、小说传达层面以及高超的写作技艺进行了高度概括,使之凝练集中。刘明真根据迟子建公开发表的自述、访谈以及国外访学交流,写作发表了迟子建2022年之前的生平、家庭结构、学习经历、作品发表、婚姻状况、获奖情况、创作经历中的思想变化等有关情况的“迟子建文学年谱”[1]。在上述研究成果中,有的百密一疏,或存在争议之处,但对于学者更为深入地了解迟子建,对于推动迟子建研究,是有重大参考价值的。
(二)关于迟子建小说中的地域文化背景研究
许多学者对于迟子建文学创作中体现的鲜明地域色彩给予了高度关注。如孙胜杰在《迟子建小说中的“河流与女性”母题论》中,详尽分析了河流对迟子建的影响,认为河流不仅在迟子建创作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还被迟子建不断加工处理,以更为丰富的内涵参与到其小说叙事中,成为其文学创作的重要情结和形成了区别于他人的“迟子建风格”。[2]喻超,李丹梦在《记忆、认同与想象——文化记忆视野下重读迟子建长篇小说》中论述了“东北”作为记忆的场域来说,是迟子建小说拓展创作空间的平台和彰显地域文化色彩的重要标识。[3]赵栢欣在《“冻土上的生活之流”的地域风貌呈现——论迟子建小说中的地域文化特色》中阐述了东北这一特殊的地域环境不仅是迟子建在小说创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而且成为其建构小说艺术世界中的关键因素。[4]陈琛的硕士论文《论东北文化视域下的迟子建小说创作》(陕西师范大学,2015),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宗教信仰等角度,论述了东北地域文化不仅为迟子建提供了创作素材与源泉,成为其写作的积极动力,而且也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另如张瀚尹的硕士论文《新世纪以来迟子建小说的地域书写研究》(江南大学,2021),讲述了新世纪以来迟子建书写场域逐渐延伸到东北都市,将目光聚焦于东北大地,破除了传统地域书写的限制,深入发掘乡村世界,让读者感受到了东北文化,对当代地域书写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关于迟子建生态观的研究
迟子建创作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迟子建的生态观逐渐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有许多学术文章发表。如卓睿在《从“皈依者”到“拔拂者”——生态视域中的迟子建小说人物形象转变》一文中,依据迟子建生态小说中勾勒的人物形象,充分肯定迟子建的如下生态观:作家们要敢于直面目前生态危机的情况,找寻构建和谐的路径。同时,要对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变化保持高度敏锐,将生态忧患意识自觉植入文学作品中,在应对生态危机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文学的作用。在他看来,迟子建通过持续地创作实践,塑造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表达了生态美学的性质,推动了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理论的发展。[5]汪树东在《论迟子建近期小说的生态书写》中,围绕迟子建近期创作的《群山之巅》《空色林澡屋》《候鸟的勇敢》三部小说,进一步论述了迟子建生态书写出现的新变,并将绿水青山的生态观念真正落实到了文学写作中。[6]李昭明,王卓玉在《论迟子建小说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中认为,乡土经验和丰富的童年经历造就了迟子建独有的生态观,并在其日后的创作历程中逐渐达到“多位一体”的生态主义思想。[7]李智伟在《迟子建作品中的生态意识》中论述了迟子建主张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理念,她竭尽全力将笔触伸向河流、森林、山川,动物,以悲伤基调的生态意识力图唤醒当代人民群众淡薄的生态意识,从而维护人们所剩无几的静美原乡。[8]李敬巍、纪秀明在《基于现代文明之上的生态构想——生态批评视阈中的迟子建小说创作》中联系迟子建“人与大自然是部分与整体的共融”的主张,进一步阐明了迟子建要在基于现代文明之上传达人与自然至纯关系的生态诉求。[9]另有多篇硕士论文,如耿丽霞《女性视域下迟子建小说的生态观》(西北师范大学,2012)、丛领《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的迟子建小说》(东北师范大学,2013)、褚紫玲《生态美学视域下的迟子建作品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7)、李冬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生态美学意蕴研究》(南京林业大学,2018)、廖思琦《人与自然的双重变奏——生态伦理视域下的迟子建小说》(西南交通大学,2019)等,亦从多重角度,论述了迟子建对生态环境的思考,对生态系统的重视,深入分析了迟子建构建的文学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进一步阐释了女性视域下生态观的价值以及意义。
(四)关于迟子建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
随着迟子建研究热度的不断提升,迟子建与其他作家的比较,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内展开。在与外国作家的比较方面,盛永宏比较分析了迟子建与哈代作品中各自地域的民间信仰,认为在两位小说家笔下,能够感受到对乡土人情的类同书写和地域上的历史传承,以及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有着较为相似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10]刘佳文通过对迟子建《白雪乌鸦》与加缪《鼠疫》的比较,认为两位作家都是以“鼠疫”作为描写对象,虽然对“死亡”话题有着截然不同的阐释,但是能够从两位作家的作品中感受到“向死而生”的生命哲学。[11]龙咏熹通过对川端康成“雪国”与迟子建笔下的“北极村”系列小说比较,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对迟子建产生了重要影响。迟子建“北极村”系列的小说不仅吸收了《雪国》的“感伤主义”,而且在“乌托邦空间建构”、“女性形象设计”、情爱世界的书写等方面对其多有学习和借鉴。但迟子建并非照搬川端康成,在学习川端康成的基础上,她为小说贯注了鲜明的“中国文化”元素,打造出了贴合时代背景的“北极村”系列小说。中国文学在借鉴外国文学的过程中,迟子建笔下的“北极村”理想国对《雪国》的成功借鉴为当代中国文学领域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文学写作经验。[12]这方面值得注意的论文还有田洁的《论灾难文学中的“英雄”形象——以加缪<鼠疫>与迟子建<白雪乌鸦>为例》[13]、胡作友、朱晗的《迟子建VS莫里森:转型焦虑及其文化启示》[14]、李慧的硕士论文《东方之美——迟子建与川端康成创作的审美比较》(湖南师范大学,2011)、刘晓蕊的硕士论文《吉本芭娜娜与迟子建小说中“死亡主题”的比较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017)、李勇兵的硕士论文《从生态批评角度比较<使女的故事>和<鸭如花>》(上海交通大学,2020)等。在与国内作家的比较方面,值得注意的成果有:李旺在《书写鄂温克——乌热尔图、迟子建比较论》中指出,迟子建在创作《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过程中离不开乌热尔图的影响,其写作风格和情节设置与乌热尔图的小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迟子建和乌热尔图通过文学创作给读者塑造了最广为人知的鄂温克族形象。[15]刘艳在《童心与诗心的女性书写——萧红、迟子建创作品格论》中,认为迟子建的文学创作深受萧红的影响,尤其是迟子建在塑造意象的过程中与萧红的《呼兰河传》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呼兰河传》中的“胭粉豆花”意象甚至在迟子建《东窗》里竟以循环往复的形式多次出现。更值得关注的是,她们浑然天成的童心和诗心的女性书写能够突破一般作家很难超越的“物的限制”。[16]林超然在《寒地黑土文学叙事的双子星座——迟子建与阿成小说对读》一文中,结合迟子建与阿成的小说指出,迟子建与阿成不仅在小说题材到形式存在极大的相似性,而且在小说中都保留了“寻根”的传统。虽然两位作家都坚持用诗性的语言表达作品的内容,但是阿成相较于当今的迟子建,文字却没有了往日的刀斧痕迹。[17]李会君在《从浪漫抒情到生态叙事:迟子建对鲁迅乡土小说的继承与开掘》一文中,认为迟子建的乡土小说借鉴了鲁迅乡土小说的地域叙事方式,在鲁迅乡土小说的叙事策略上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开掘和创新。迟子建不仅坚持着鲁迅的人道主义立场,而且将乡土叙事的宗旨拓展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真正凸显了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的生态精神。[18]另如何梦洁、杨晖在《生态批评视野下阿来与迟子建创作的相似性——从“山珍三部”与<候鸟的勇敢>谈起》一文中,围绕自然书写、意象构建、生态观等多个角度展现了阿来的“山珍三部”和迟子建《候鸟的勇敢》在创作方面存在高度的相似性。两位作家基于现实的基础上,在揭露人性阴暗的同时,也发掘了人性的真善美,并从生态角度给予“文学即人学”新的诠释。[19]徐夏敏在硕士学位论文《沈从文、迟子建边地小说比较研究》(湖南大学,2017)中,从二者建构边地文学的角度出发,在时代背景、文化身份、叙事艺术等方面比较论述了迟子建与沈从文之间的异同,展现了边地创作者们力求缩短边地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差距,期待更多的文学创作者参与边地文学的写作,构建边地文学的全新格局。上述比较研究,极大程度地拓宽了迟子建的研究视域。
(五)迟子建作品在世界各国的译介与影响研究
迟子建在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其作品在世界各国的译介与影响研究,也成为学界研究热潮,涌现出的代表性成果有:褚云侠的论文《“神秘”极地的本土性与世界性——迟子建小说的海外传播与接受》和韩聃的论文《想象与重生:迟子建作品在日译介与评说》。褚云侠依据自己归纳整理的迟子建作品在海外译介的现状,全面细致地探讨了迟子建作品在海外受到“热译”和“冷评”的原因。日本对迟子建小说的翻译虽然略晚于其他国家,却是对迟子建小说研究最多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对迟子建小说的研究还仅停留在文本细读和简单地评述。尽管迟子建小说的海外译本数量位于国内其他作家前列,但对其的研究却远远落后于其他作家。这种“热译”和“冷评”的原因也暗示着东西方认知视角的差异;此外,迟子建小说中的超自然想象这一“神秘性”对其小说在海外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这种“神秘性”让海外读者没有意识到作品中的其他更有价值的议题。[20]韩聃在其论文中,着重以日本学界对迟子建作品的研究概况为主,深度分析了日本学界重点关注迟子建的生活经历对其后来文学创作的影响,进一步揭示迟子建作品当中塑造的意象与其生活场域的内在联系;另外,韩聃在褚云侠的研究论文基础上发表了新的观点。在他看来,迟子建作品的“神秘性”对于日本读者而言早已不是“神秘”体验。通过查阅《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与考察相关的神社、古迹,可以发现日本人早在五、六千年前就有“万物有灵”的思想,所以迟子建的作品在被解读过程中被赋予了“神秘性”以外的全新意义。[21]上述研究成果,能够更好地了解海外学者与读者眼中的迟子建文学,为推进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迪。
二、迟子建研究议题的深化
作为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和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迟子建,其作品究竟有何独特之处?从作品之中到底反映了怎样的文学精神?迟子建笔下的“北极村”理想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什么深受中外学界的关注?自是迟子建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探讨和解决的主要问题。值得肯定的是,在近些年来的迟子建研究中,这些问题得到了深化。
(一)关于迟子建作品的思想价值
近年来,迟子建作品当中的思想价值被诸多学者从多方面进行了深入地解读。迟子建早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即已开始了她重新反思传统文化,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反思与温情批判的过程。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把目光聚焦于鄂温克族的百年历史,“怀着‘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开启了一个‘复魅’的自然空间”[22];表达了对当今生态现状的忧虑以及鄂温克族深厚的历史意识,透露出生态思想的深层内涵。汪树东结合道家思想,认为迟子建能够巧妙地运用道家的反智主义、福祸相依、返归自然的思想来塑造人物形象,小说中的弱智者、精神病患者也正是道家思想的关键承载者。对道家思想的一脉相承,使得迟子建小说更能传递出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与物同情的特色思想。[23]郑孝萍、王乐为认为,迟子建借助作品当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呈现了其“生命共同体”概念,完成了她对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启示。她坚决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并在作品中将传统人文主义和生态人文主义形成二元对立,有选择性地继承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的优点,将其优点补充为生态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准则,从而建立起以“爱自然”为核心的和谐共生的人文精神,为处在生态危机中的人类敲响了树立生态环境意识的警钟。[24]李德南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论述了迟子建作品的思想性,认为迟子建运用大量笔墨去书写社会的失范,是基于人性中的算计性思维、现代人的心理世界和“共同体”生活的缺失,这就极大延展了小说的批判深度。更为重要的是,迟子建的思考从创作《候鸟的勇敢》之前一直在深化,她敏锐地观察到文学在现代和文明之间扮演的角色,作品中也多次出现“共同体的召唤”。他结合滕尼斯、利奥波德、让-吕克·南希对于共同体的论述,更加证实了迟子建的思考在当代文坛中达到了新的高度。[25]迟子建之所以能够得到学界持续地关注,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她的文学作品,既厚植了乡土情怀,又能站在道家思想的立场去发掘传统文化底蕴;既呈现了鄂温克族璀璨悠久的历史,又以其历史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善与恶。可以说,就是这些要素在作品的思想价值方面,确立了迟子建在中国文学领域的地位。
(二)关于创作特征与审美个性
关于迟子建作品的创作特征,国内外学者持有不同看法,或曰“浪漫主义”,或曰“女性主义”,或曰“新历史主义”,或曰“现实主义”,或曰“理想主义”,或曰“生态女性主义”,或曰“生态美学主义”,或曰“寻根文学”。在近些年来的研究中,不少学者从迟子建的创作历程和作品基调概括了其创作特征。王昕初以迟子建早期作品《伪满洲国》为例,分别从历史观、时间观、历史的主体论述了《伪满洲国》的新历史主义。迟子建将“民间历史意识”融汇到了文本之中,挖掘平凡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以平凡人的口吻去重述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从而达到给读者重新认识史实的目的。她还通过故事中每个人物的偶然性经历,来获取民众集体记忆,在革命历史主义时间观的基础上来回穿梭于新历史主义的时间观。最后,她运用新历史主义中的“反英雄”特点去塑造人物形象,尤其以“王金堂”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不仅让整部作品具备了真正的民间意识,而且让读者感受到了历史的真实。[26]李会君认为,迟子建通过诗意的文学语言和叙述视角的灵活运用,使《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思想内容与情感基调保持了高度一致,让读者能够感受到真正的语言美、意境美和儿童视角下的“童真美”。生态美学主义在她早期作品《原始风景》《北极村童话》中已初露端倪,只不过她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将生态美学主义发挥到了极致。[27]王振滔则结合迟子建文学创作历程,认为迟子建小说的浪漫主义表现在人性论的基础上。虽然迟子建小说中的人物有肮脏、丑恶的一面,但是她并没有以讽刺的态度竭力批判。与之相反,她在宽容和理解人性丑恶的同时,也发自内心地想要消解、感化人性中的阴暗成分。此外,王振滔还探讨了近年来“浪漫主义”研究的新动态,佐证了迟子建的小说与当今浪漫主义恰好能够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与共鸣。[28]
关于迟子建作品的审美个性,易瑛在《民间信仰影响下沈从文、迟子建对“神性”生命世界的构筑》一文中认为,迟子建继承了民间信仰中“巫文化”背后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她通过对古老“巫文化”的探寻,在作品中凸显人性美所散发出的“神灵之光”的美学风格,并深情地建构了一个“人神合一”的精神家园。而鄂温克族古老的民间信仰文化驱使她对至今尚存的巫文化产生追溯和思考,狩猎文化中的“万物有灵论”也使得《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人物兼具人性与神性色彩。[29]尹文雯注重研究迟子建的散文作品,在散文整体基调和意象的基础上认为,迟子建的散文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既有古典美学范畴中的“闲适”,又有当代美学范畴中“悠然”的审美理念。迟子建对童年生长的乡土环境的温情书写和对雪、月亮、花等意象的细致描绘,凸显了散文“伤怀之美”的美学格调。[30]刘秀哲在《乡土记忆与文学想象——迟子建文学创作的文化表征》一文中认为,迟子建的写作超越了传统乡土文学的范畴,乡土在其笔下承载的内容逐渐变广,承载人类的苦难生活的同时,又能演绎出独有的诗意和浪漫。与此同时,她对乡土民俗的书写是其文学创作中的核心要素,复刻了鄂温克族独有的文化记忆,体现了迟子建特有的审美个性和人文主义精神。[31]
(三)关于作品的叙事方式与结构特色
对于迟子建作品的艺术特色研究,尤其是对于其叙事方式与结构特色的研究,是近些年来迟子建研究的一个热点,在《文学评论》《当代文坛》《文艺评论》《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中,有数篇相关论文发表。王丽娟在《异族人生景观的深情观照——略论迟子建乡土文学中的“非汉族”书写》一文中论及,迟子建《北极村童话》《白银那》《微风入林》《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五部小说,呈现出迟子建乡土文学中的“非汉族”书写,这种书写模式为当代乡土文学小说提供了全新参照范例,填补了中国乡土文学史对边地少数民族叙述的缺口, 拓宽了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领域。[32]刘艳在《童年经验与边地人生的女性书写——萧红、迟子建创作比照探讨》一文中以萧红和迟子建的童年经验作为切入点,论述了童年经验为她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并对作品形成了一种最强的先在意向结构,直接影响了她们对于边地人生的女性书写。她们在基于童年经历的基础上,在边地场域搭建起了特有的艺术世界,为当代文学的写作与研究提供了丰厚的样本。[33]刘秀哲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民俗传统与审美文化》一文中认为,民俗不仅为迟子建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资源,而且增强了文本意蕴。《额尔古纳河右岸》以苍茫北国的文化场域为时代背景,借助民俗生活、民俗形式与民俗意象为载体,全方位、多层次地给读者呈现了鄂温克族的百年历史。迟子建在书写鄂温克的同时,由对“民俗的静态式书写转向了动态性直观”,并在拓展性的陈述过程中将时代性特质赋予给民俗,揭露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乡土窘境,进而展开对当下现代文明社会的省思和对人类心灵憩园的探寻。[34]
在关于迟子建作品的叙事与结构研究方面,值得重视的成果还有,陶维国、徐变变将儿童视角视为迟子建小说中最重要的叙事策略。迟子建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从儿童的视角来洞察一切、描绘人物或阐述事件的,而淳朴真挚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是驱动迟子建坚持以儿童视角作为叙事策略的深层内因。这种叙事方式在迟子建的创作中的不断复现,也是其小说结构的重要元素。[35]郑坚尝试以浦安迪的《叙事学》和热奈特的叙事视角为理论基础,运用传统文学叙事的角度解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文本,并同时使用分析法、比较法、归纳法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学叙事对迟子建小说的叙事角度和叙事方式等内部结构和文体形态等外部结构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从而阐述迟子建的作品在中国古典文学叙事基础上进行的继承和革新。[36]欧芳艳认为,在迟子建研究中,其长篇小说的叙事结构问题很少被提及。迟子建长篇小说的叙事结构大致可分为多线并置式结构和U型结构两种模式。通过时间线观察迟子建小说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其构思的叙事结构,不仅承袭了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大团圆”的模式,还与民间信仰影响下的世界观念和作家对人生的感悟紧密结合。多种因素的交叉相融,使其文本呈现出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因此,通过考究迟子建长篇小说的叙事结构,静观其作品人物的发展轨迹,可以考察迟子建小说对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结构的承袭和灵活变换。[37]李涵认为,从内容构成还是叙事结构上分析,风景书写在当今小说创作语境中大幅缩减。值得研究的是,“从创作发生学角度、具体风景书写的呈现”来观察,迟子建小说几乎都表现出与自然、风景的紧密相连,风景书写在迟子建小说中重复出现。风景不仅构成了迟子建文学创作的由来,更成为支撑她的生命观与写作观的内核,同时,她的原始自然观成为了批判当今文明社会的主要思想基石。迟子建小说的风景书写弥补了当今文学创作中的风景缺位,显现了风景书写所表现的诗性韵味与浪漫主义。[38]这些紧扣文本、结合叙事学的有关理论,得出的上述见解,可谓更为精准地捕捉了迟子建作品的叙事特点,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迟子建的创作艺术特点和审美个性。
三、关于迟子建新作的研究
迟子建在2008年10月荣获茅盾文学奖之后,又陆续创作了《白雪乌鸦》《群山之巅》《烟火漫卷》等长篇小说。对迟子建的新作,也已有许多研究成果发表,其见解主要集中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体现了迟子建新的艺术追求与自我突破
如欧阳澜、汪树东从艺术追求角度认为,《群山之巅》开启的“屏风式”结构、“块茎式”人物群像以及“强化的”意象叙事等,侧面反映出迟子建作品的艺术新质,并且使古典美学绽放出绚丽之花。迟子建有意回避了现代社会中的浮躁气息,继承了古典小说中的美学意蕴,连接了前现代和后现代的艺术桥梁,量身定制了其乡土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展现出不同以往的美学特色。[39]徐勇与王迅认为,“乡镇写作”对于迟子建而言,不仅是试验场域、还是城乡之间、全球化与边缘化交织互融的“模糊地带”。她在“乡镇时空”背景下思索着世界与自身关系的新起点,创造了混沌和诗意的辩证结合,达到了现代性视阈下乡镇叙事的美学高度。[40]
(二)迟子建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形象研究
如欧芳艳认为,迟子建小说被学界逐渐关注以后,“老女人”形象是其小说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并在她后续系列的小说中形象逐渐饱满丰腴,为构建女性形象谱系起到关键作用,造就了迟子建独特的文学创作模式,成为迟子建小说创作与时代发展互动性的标志性符号。[41]卓睿认为,从《额尔古纳河右岸》开始,迟子建生态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从皈依自然的弱者变为拔拂生态的强者。她以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塑造出了鲜明对比的人物形象群谱。[5]陈培浩认为,迟子建在新作《烟火漫卷》中,塑造了“黄娥”这一神采奕奕的人物形象:她率真淳朴的个性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审美魅力的自然之子的形象,对匍匐挣扎在现实城市生活中的人们有着引领作用。迟子建塑造的“黄娥”形象,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谱系进行了扩充和丰富。[42]
(三)迟子建文体方面的突破
如张学昕认为,迟子建对中篇小说的文体越来越得心应手。《候鸟的勇敢》文本内核简单利落,故事情节循序渐进,内容之间保持紧密联系,挣脱了结构的束缚,将中篇小说的文体优势展现了出来。[43]在李遇春看来,从《树下》到《群山之巅》,她不断在往“海洋”文体美学的方向发展,以至于小说文体成为一种空间诗学。通过中短篇小说中的诗学因素互相渗透,从根本上也使得迟子建长篇小说的文体美学更为成熟。她通过多年的小说文体实践将现实的“具象”提炼为抽象理论,破解了多年来困扰我们的文体美学难题。[44]
四、迟子建研究中的争议
迟子建进入文坛以来,在得到学界认可的同时,也不乏争议。尤其是获茅盾文学奖之后,大家为她庆祝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批评声音也越来越多。
(一)关于迟子建艺术成就的争议
史玉丰认为,迟子建温情的写作风格与题材的重复书写使她陷入了惯性创作思维,限制了她对生活的理性发掘和对整个世界的深度思考。她的小说结构不仅较为零散,而且模式化倾向使文本无法经受住整体审视,给人一种窥一斑而知全豹的阅读感受。[45]王博雅认为,迟子建在中短篇小说中对“善”的表述不足,过分强调“善”的作用,造成了一种失真叙述,损害了小说的真实性。[46]而黄明智与史玉丰也达成了一致。黄明智认为,细读迟子建的作品,会给人一种雷同与公式化的感受。固定的人物形象和温情的书写风格,不仅没能让迟子建看清生活的本质和复杂的人性,而且降低了其作品的审美意蕴和思想深度。究其原因,也许是她还缺乏对现实生活的深切体会,使她无法做出真实的分析与判断,从而只能在文本基础上不断重复故事模式。[47]程小强在史玉丰和唐小林对迟子建文学批评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度创新,梳理了像迟子建一样存在创作症候的一批知名作家。他认为,造成迟子建“创作重复”的现象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源于迟子建为文观的偏差、写作能力的不足和对现代主义的过度迷恋;二是批评界不负责任地对其过度吹捧,加重了“创作重复”的痼疾。[48]
(二)关于迟子建新作的争议
迟子建获奖之后发表的新作,在广受好评的同时,亦有学者指出了其不足之处。欧阳澜,汪树东认为,《群山之巅》在精神探索层面并没有达到突破。无论是塑造民间小人物的人性特质,还是对当下社会的批判,迟子建依然在最擅长的写作模式上“原地踏步”。她没有用辩证的角度去分析民间市井小民的形象特点,未探索到人生真正的本质,所以在精神探索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49]于京一认为,《群山之巅》中过于流露的忧伤在破坏小说情感基调的同时,又极大影响了小说的叙事,造成整部小说在整体结构、发展节奏、情感基调上零散破碎。[50]于小植认为,《烟火漫卷》中的小人物与城市主体没有建立起紧密的联系,缺乏历史的连贯性和厚重感。同时,将《烟火漫卷》放置于现当代文学中宏大的“哈尔滨叙事”和城市文学史中进行勘察,发现小说在建构城市主体上存在局限和弊端,对城市主体的表述存在偏差。[51]
迟子建研究中出现的上述争议,不论是否准确,都是值得学习借鉴的。迟子建研究中存在的争议,不仅能够提高文学评论界的积极性,而且有助于读者能够更加辩证地看待迟子建作品的特质和蕴含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