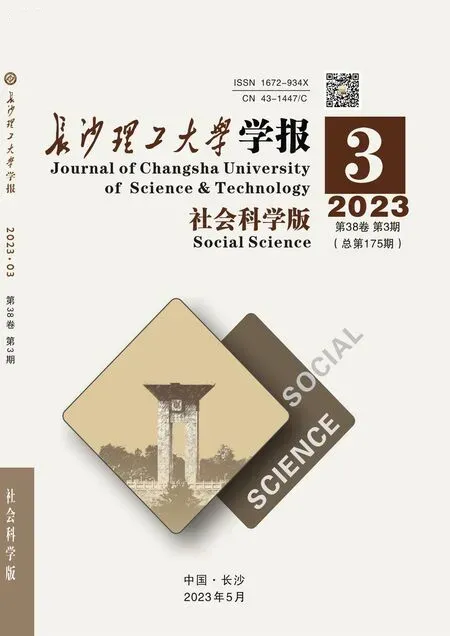农业转基因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知识架构:殖民医学及其遗产
2023-08-07韦敏
韦 敏
(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由于研发技术的日益丰富,农业转基因(转基因的绿色技术分支)具备了复合性状,也由此负载了更多准药用和药用成分。基于这种研发趋势,农业转基因研发者和推广者认为,这类产品可有效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但现实证明,实践效果与理想存在差距。农业转基因所试图参与的全球卫生治理,其知识论奠基于西方殖民医学,因此当代的全球卫生治理与殖民医学在知识和方法论上存在连续性和相似性。加上农业转基因研发者和推广者与全球卫生治理初创者在角色和组织模式上的趋同,使得与农业转基因相关的全球卫生治理遵循着殖民医学及其延续所塑造的作为遗产的知识和方法论。本文根据历史发展进程依次论述:殖民医学及其延续性实践留下的知识论遗产;农业转基因进入全球卫生治理的历史背景;农业转基因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所折射出的这一遗产的内在局限性等内容。农业转基因参与的全球卫生治理疏离生活世界中的既存秩序和真实需求,反映出自身与生活世界的抵牾,这种抵牾既源于殖民医学及其遗产所筑建的知识架构本身的缺陷,更肇因于这一架构根植于的“全球科学”实践模式。
一、殖民医学与当代全球卫生治理的兴起和发展
殖民医学是发达国家在殖民过程中创制的集合了医学技术、规范、卫生治理理念与方法的综合体。殖民史虽然已终结,但殖民医学的方法、理念、规范、框架仍影响着公共卫生实践,如殖民医学中对他者的“弱者想象”成为了全球卫生治理的实践基础和修辞动力;殖民医学中对常见疾病的消灭和预防使全球卫生治理重视利用“适度技术”进行疾病干预;殖民医学及其延续利用“成本-效益原则”核算卫生干预的成效,推动着现代循证公共卫生对伤残调整寿命年等健康经济学核算工具的征用;等等。
殖民医学的目的是控制和预防疾病,以确保在留住殖民者的同时确保原住民的健康和殖民地的生产力。为实现此目标,殖民医学从最初的疾病勘察模式演化为疾病干预和控制模式[1](P101),并从关注个体转向关注群体。关注总体性的群体意味着抛却对群体内部异质性的考量。干预的必要性和确保生产力使殖民医学以及殖民医学在当代的延续体——全球卫生治理,均涉及对地点的选择,即需要对哪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干预是存在政治性考虑的。
殖民医学时期重要的治理主体之一洛克菲勒基金会(简称“洛基会”)长期关注传染病的控制和消灭,它曾研发出黄热病疫苗,并在20世纪20年代用蛔虫药成功控制了十二指肠虫病,又于1938年击退了入侵巴西的冈比亚按蚊[2](P461)。洛基会主要选择亚非和拉美地区的殖民地,也就是在洛基会有战略性利益的地区进行投资。健康、生产力、疾病控制,这些关注点促使殖民医学优先选择自上而下的“垂直干预”项目,如针对多种疾病或疫情的“根除运动”。
根除模式在当时是通过有意忽视疾病的社会根源,并将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放在次要位置,实现了在短期内应对黄热病、疟疾等热带疾病[3]。垂直、自上而下、根除的理念在二战后得到了巩固。二战后兴起的世界卫生组织(简称“世卫组织”)也延续了这些在他们看来“已被历史证明为有效的”范式开展全球卫生治理。
通过运用源自殖民医学的知识架构不断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世卫组织逐渐确立起自身的领导地位。如1947年,面对埃及霍乱,世卫组织阻止埃及邻国进行的不必要的检疫,还提供了补液治疗、环境卫生保障、疫苗接种等服务。早期,世卫组织规划的项目大多是为了集中解决单一问题,包括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免疫接种,尤其是针对儿童天花、麻疹和脊髓灰质炎的疫苗,以及通过杀虫剂的大规模喷洒、清洁水运动、物理隔离对结核病、疟疾、麻风病等进行预防、治疗和根除。
这些任务的阶段性胜利进一步强化了利用单一实体性要素(如疫苗、补液剂)进行干预的做法和“银盘思路”[4]。“银盘思路”认为,只要有强有力的资金和政治支持,依赖军事化的指令结构,以技术为中心,通过低成本投入便可以消除大部分疾病。立足于根除方法、实体性要素和“银盘思路”的做法,世卫组织最终有效控制了雅司病,并成功剿灭麦地那龙线虫病(1986年)、脊髓灰质炎(1988年),忽视与其他健康项目进行融合和协调的殖民医学范式及其现代变体最终被视为可以所向披靡[5]。
但也是因为殖民医学范式及其现代变体,以及对技术性方案的过度迷恋,世卫组织在剿灭疟疾中遭遇了失败[3]。疟疾是一种深嵌于社会情境中的疾病,农耕模式、灌溉设施的使用、劳动力分布和人口迁移特点等,决定了疟疾的消除不可能仅仅依赖于技术性手段。世卫组织在应对疟疾的溃败中感受到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基础设施建设和初级卫生保健投入的重要性[6]。
于是,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开始尝试开辟全球卫生治理的新途径。1978年,两个机构召开了阿拉木图初级卫生保健国际会议,会议共识浓缩在《阿拉木图宣言》(简称《宣言》)中。《宣言》的重要主题之一是:适当的技术——运用于资源匮乏环境的公共卫生和医学工具应当是适当的[7](P88)。适当主要指技术对农村人口的可及性。另一主题是发展综合性初级卫生保健——社区内人口能普遍获得的基本卫生保健。但在后来的实践中,选择性初级卫生保健(有选择地将关联性不强的卫生干预措施打包)代替了综合性初级卫生保健,目的是绕开卫生和疾病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因素,聚焦于成本低廉、短期内易于监测的指标和结果[8](P73)。这一做法推动了垂直干预在卫生领域的再次流行。
典型的选择性初级卫生保健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1982年发起的GOBI-FFF项目,该项目把相关性不强但符合一定标准的若干措施集结在一起。这些措施包括:对早期营养不良儿童进行监测(G);在治疗腹泻时使用口服水疗法(O);倡导母乳喂养(B);用疫苗接种的方式预防6种主要疾病(I);使用食品补充剂(F);有计划的生育(F);让女性接受教育(F)[7](P88-89)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选择这几项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在促进儿童发育方面,这些措施具有显著的成本-效益优势。
GOBI-FFF项目为全球卫生治理带来了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深远影响。首先,项目设计者也曾考虑过其他干预项目,如控制疟疾、防控轮状病毒、干预维生素D缺乏症等,但设计者最终认为GOBI-FFF项目最有可能在个体、家庭和社区层面带来直观的、容易感受到的死亡率下降的感受。这使得对短期可见性效果的渴求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风格和旨趣。然而,GOBI-FFF项目无法迫使现有卫生系统改革,因为GOBI-FFF项目实现目标的前提是——不改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不优化初级卫生保健的供给机制[7](P88-89)。
GOBI-FFF项目最终在世界范围内成功推广了口服补液疗法和营养补充剂。口服补液是联合国机构通过成本低、效益高的纵向项目进行结果导向援助的一个早期成功案例。但结果导向会使纵向项目占主导,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横向方法[8](P116)。而成本-效益原则本身也存在争议:基于成本-效益的分析是以占有稀缺资源为前提来实现结果的最大化。这一前提有时会强化已经存在的不平等。成本-效益原则还因为“以市场逻辑为中心的赋值”,容易让人误判什么是技术的“适当性”:人们往往根据功利主义立场判定适当性,而忽视了每一种被称为成本的事物都暗含有对特定价值的偏好[9]。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影响日渐广泛,最终渗透至全球卫生治理,卫生治理活动逐渐转向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于是,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成本-效益核算、公共开支、通货膨胀等经济知识就被赋予了优先性,被用作标准来评估哪里出了问题、哪里需要改变。相应地,医学、社会学、人类学、环境科学等能够反映生活世界既存秩序的知识就被边缘化了。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采取的新自由主义,促使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推出了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它把过早死亡和健康生命年损失相结合来衡量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这是个有争议的标准。伤残调整寿命年是一种价值观依赖的、权宜性的核算方法,该方法背后隐藏的价值观是:为多数人提供微小的收益要比为少数人提供大的收益要好[10]。此外,DALYs还把人类应对疾病的能力排除掉了,这就改变了“疾病负担”这一概念的内涵。
盖茨基金会这类非国家行为体也在为殖民医学及其延续注入新治理范式。基金会的资助范围包括卫生保健、清洁水、卫生设施和农业发展等,对创新型技术方案尤其偏好,如支持营养强化作物[8](P141)。历史上,盖茨基金会通过控制科研经费,把研究引向其偏爱的方向:追求技术的奇异性、构建强调进度和结果的激励体系、严格的绩效考核、组织大量短期和可测量的活动、设计过量的指标,这些做法降低了其他卫生治理主体研究和实践的独立性[1](P52)。因基金会的资金实力和影响力,它会扭曲世卫组织等正式机构的议程[8](P104)。盖茨基金会这些提供卫生服务的富裕者们并不对政府、法定机构负责,也不与之合作,这不仅带来效果问题、重复问题和问责问题[11],而且更加使得基金会根据自身兴趣施行资助的纵向项目盛行。
殖民医学以及二战之后延续殖民医学范式进行的卫生实践,在半个世纪之前就为当下全球卫生治理景观创造了权威、定下了基调[12]。总结起来,殖民医学及其之后的卫生实践,锻造了一种作为殖民医学遗产的知识架构,即:有关全球卫生治理的垂直、自上而下和根除思路;对狭义结果评价的偏好;对单一要素的强调;对进度的迷恋及这种迷恋带来的结果主义导向;对可视化、可量化目标的偏好;坚信技术之于治理的充分性;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卫生治理方案的情境无涉性;将疾病视为无需社会回应的自然实体;认为被治理对象只是治理方案的被动接受者[13];非国家行为体介入全球卫生治理。
二、农业转基因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历史背景
(一)杜鲁门总统的“第四点计划”与二战后农业援助的兴起
1949年,杜鲁门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美国外交政策需要增加“第四点计划”:“大胆启动新规划,将科学和工业进步带到落后地区,帮助它们发展。”[2](P462)“第四点计划”的性质是,让美国专家将技术和知识传授给不发达地区,使后者形成发展的能力。美国尤其重视三个领域的技术援助,其中两个为:以粮食为主的农业发展及公共健康和卫生。“第四点计划”提出时,二战后的和平建设时代拉开序幕,彼时,发展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课题。美国不希望这些国家被纳入他们所反对的共产主义阵营,而是能被纳入美国所构建的世界秩序。为此,美国政府准许非政府组织作为执行“第四点计划”的重要主体。
“第四点计划”的推行地点主要是邻近共产主义国家的亚非拉地区,有显著的地缘政治考虑,而非出于真实的发展需要。美国政府选择被援助地区的具体原则有:有重要的外交意义、援助规模较小、被援助国同意合作、对技术援助有一定需求、有必要的技术使用能力[14]。“第四点计划”提出后,美国政府动员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洛基会、福特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一同行动。洛基会在殖民医学时期长期与亚非拉地区打交道,拥有丰富经验,积累了技术和知识,被美国政府委以重任。这意味着在殖民医学时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开始更深入地向农业援助和农业-医学结合的领域挺进。
(二)殖民医学和二战后援助性农业:实践主体的同一
洛基会在20世纪30年代便根据科学慈善的理念,在第三世界开展殖民医学实践的同时进行农业援助,首要目的是推广美国商业化农业,其次才是出于利他动机。洛基会出于政治和经济考虑,即为了以更加温和与人道的方式控制拉美,进而维护自身在墨西哥的经济和石油利益,将墨西哥选为新型农业技术试验地。“第四点计划”问世后,洛基会加强了对于墨西哥的小麦育种研究,牵头成立了墨西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以“绿色革命”为历史背景,为墨西哥提供高产小麦以缓解饥荒的同时,通过在哥伦比亚、印度等国建立育种合作计划,将育种科学带入国际领域。
墨西哥农业项目成功后,包括洛基会在内的国际性组织开始信奉“神奇的种子”观,将优质种子视为农业发展的关键。在洛基会看来,农业发展援助归因于食物问题,该问题又可以被进一步回溯至“农业产量”这一可被独立出来的议题,而农业高产可通过基因修饰实现。这种还原论思维客观上导向了对“卓越(excellence)上游研究”(基因修饰技术在彼时属于卓越技术)和“技术优先论”的倚重[15](P17)。洛基会为延续在拉美的成功,继续在菲律宾成立了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IRRI的核心却未言明的宗旨:一是将农业研发和推广中的等级结构延续下去;二是将实验室的同一成果推广到所有农耕环境。为实现这两点,IRRI在成立后不久便开始有意识地将基因改良作为首要研发手段。
最开始,IRRI的研究是家族式研究(family research)。家族意指:在IRRI水稻研发中,菲律宾的研究者甚至农民都会参与种子培育,并与西方背景的研究者保持密切沟通。家族式研究是自下而上的、回应情境和农民需求的、能够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去中心化和等级化的,而不是国际化网络、更注重实验室的。但后来IRRI逐渐抛弃家族研究,一是希望作物研发简单高效,这时通常利用基因工程手段加入稳定表达的性状;二是IRRI的研发人员以及其背后的洛基会、福特基金会等,希望研究回到自上而下的模式,以维持研发者权威和技术的奇异性。这一转变造成研究活动对还原论和单一要素的强调:只有在这种视角中,IRRI营养强化作物的优越性论证才能成为可能,这时,被强化的营养素是一种作物优势,该营养素对应的生理症状的缓解是作物的社会医学功能。
从IRRI时期起,概念验证(proof of concept)开始逐渐占据主导,概念验证是用教科书式的、理论的、基于思维的,而非立足实际情境的方式来验证种子的功效。在概念验证中,种子“神奇”与否只需关注被强化的营养素,即单一要素本身的生化功效如何。IRRI围绕大米的分子生物学育种为农业转基因起到了示范作用:如何将实验室研究的成果成功应用于多个地点,而不考虑地理差异和政治环境,仅仅凭借生化、基因特点就确保效用[15](P18)。
(三)从IRRI到CGIAR:管道模型、简单高效的技术育种、想象救助对象、生物强化理念、量化评估等在农业育种领域的巩固
CIMMYT和IRRI的工作使得洛基会和福特基金会、世界粮农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下定决心在1971年组建国际农业研究机构网络(CGIAR),在更大范围内推动区域农业生产。CGIAR比IRRI更强调回到上游研究,追求卓越的上游研究将转基因技术视为关键手段[15](P25),因为当时的CGIAR认为,开发具有技术奇异性的研究可以增加机构影响力[15](P131)。上游研究强化了CGIAR的“管道创新模型”:从前,农民是育种下游阶段适应性研究的合作者,现在成为了技术和种子类产品的“用户”。
鉴于加碘盐和维生素A补充剂等“基于要素”的卫生类垂直项目的成功,国际营养议程将注意力转向微量营养素的供给[15](P38)。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根据“全球疾病负担”将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确认为风险因子,并开始用DALYs评价微量元素补给带来的健康收益。于是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营养投资被列入优先项,到世纪之交,营养投资和干预开始负载一系列可度量的目标,以匹配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15](P32-33)。千年发展目标要求用量化的、可视化的方法度量所有任务的完成度,其下8个子目标中,一半目标的达成需要依靠农业提供充足的营养。2005年,千年发展计划由于在中期审核时感到失望,国际性机构决定考虑通过农业-营养-健康模型,而非原来的工业补充剂-营养-健康模型来促进健康。CGIAR有联系农业-营养-健康的历史经验,一些有食品价格分析背景的经济学家来到CGIAR位于世界各地的育种中心,成功劝服他们根据成本-效益原则研究在植物育种中添加营养性状的可行性[15](P38)。
我没有答话,我真的对颖春说的这些东西有些烦了,但颖春仍然兴致勃勃的,回到家,饭也不吃,觉也不睡,而是把我按在沙发上坐下说,老公,今晚我们好好合计一下我们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我闭上眼睛说,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我想睡觉了。颖春那一下突然跳了起来,她一把将我从沙发上拖了起来说,孙东西,你怎么这么没长进呢?从小你父母送你读书做什么?
对于CGIAR,生物强化研究还涉及对“用户”的概念化,CGIAR把试图干预的对象统称为“穷人”。事实上,需求群体内部存在差异[15](P131)。CGIAR在不细分目标群体的同时,延续了IRRI的两种做法:一是不对生物强化产品进行人体效能研究,即不去确定农产品发挥预设功效的程度,主要是为了吸引投资者(效果不理想的产品将失去吸引力)[15](P54);二是在现实中根据非医学标准有选择性的强化特定营养素。尽管缺铁和缺碘问题突出,但维生素A依然比铁、碘受到了更多关注,因为补充铁碘难以带来短期的、可视的成果,不便于监控,且铁和碘的摄入和生物利用受多种因素影响,削弱了用单一指标衡量的可能性[15](P71)。
(四)从CGIAR到HarvestPlus:农业转基因通过“概念验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和“银盘思路”的再现
2000年,世界粮农组织提出“充足食物的权利”,为营养获取加入了人权视角。这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食物、健康、照料”框架的旨趣相近。之后,国际性组织的注意力和资源分配依循“目标导向”思路,希望营养供体能通过一种规模效应,而不是基于特定地方的可引发食品体系持久变化的方案[15](P37),来快速达成缓解营养不良的目标。基于这一背景,CGIAR开始有意识地巩固农业转基因作为新型营养供体的角色。
CGIAR在2001年发起“挑战项目”,挑战之意在于,项目有时间限制、受独立监管,且有巨大影响力、指向CGIAR研究目标的、需要基于广泛的合作关系来推广研究成果[15](P95)。一共有10个挑战项目,其中之一是“利用农业技术增进穷人健康:生物强化作物抗击微量元素缺乏”。这不仅意味着CGIAR进入了人类健康这一他们不擅长的领域,也意味着CGIAR开始回应把健康视为发展工具的全球发展议程。世界银行等机构和新自由主义理念,将经济学意义上可测量的单元向全球健康和发展领域的嵌入,进一步促使CGIAR使用可被独立和重复的目标来度量研发成果的效用[15](P133)。
生物强化早年的做法是使作物适应土壤,如培育富铁作物来适应缺铁土壤,适应性研究涉及很多变量,且需要自下而上的研发思路。CGIAR则认为,农业转基因能消除由基因-环境交互以及收获后损失带来的不确定性,育种便有了可预测性和可控性。在将生物强化作物等同于农业转基因后,CGIAR便可以将生物强化构建为自上而下、包含有中心指令的农业转基因研发项目。这类项目耗资巨大,而“挑战项目”的赞助者也更愿意赞助单笔金额大的纵向项目,以提高自身影响力。纵向项目的盛行致使农业-营养联姻的横向项目难觅踪影。
2004年,CGIAR的生物强化研究更名为HarvestPlus,Plus有跨学科之意。跨学科的表述能调动大规模的资本提供者对研发的投资,而跨学科的协作使研发呈现专家网络主导的局面,专家网络对以往家族研究网络的彻底替代,重现了殖民医学和全球卫生治理时代的“银盘思路”:在孤立复杂的现实因素的前提下,投资于上游活动,可以通过简单因果通路和垂直项目的设计,依靠指令性系统,以及下游可量化结果,产生最大化的成果[15](P130)。CGIAR跨学科性质和专家网络的形成带来的另三个影响是:促成了公私合作(技术精英和资本提供者均可能加入网络);压缩了技术选择的讨论空间;地方行动者被边缘化[15](P126)。最终,生物强化研究使通过农业实现健康的方式围绕通用性、中心化、还原论的原则达成了共识。
(五)HarvestPlus:农业转基因进入全球卫生治理的直接动力
盖茨基金会成为了HarvestPlus最大的赞助人[15](P39)。该基金会在20世纪末成立时,所受到的支持来自两个先锋型NGO,这两个机构横跨医学和农业。而盖茨基金会也跨界于健康治理和新型农业,施加相似的治理模式于两个领域。盖茨基金会决定赞助HarvestPlus,既是作为投资策略的一部分,以分散投资风险,也是出于对技术性方案的坚信,“我们一直以来的目标是应用科学和技术来解决‘穷人’的难题”[15](P102)。此外,洛基会秉持策略性慈善的原则,注重以低成本来提供公共品,以获得影响力,因而也邀请慈善家投资HarvestPlus。
HarvestPlus中心化的设计压缩了关于技术选择的讨论空间。对于该项目的恰当性,长期以来存在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最有效的营养问题干预方案是完善种植系统和保证饮食多样化。HarvestPlus项目实施者不认同这一“短期内看不见成果、成果难以量化”的思路。而对于“营养补充剂和强化食品也可以缓解营养素缺乏”的看法,HarvestPlus认为这两种方法需要安全稳定的食物传输系统、适当的社会架构和持续的资金支持,只有生物强化作物这种独立于社会因素、基于要素的方法是可行的[16]。
HarvestPlus还最终巩固了成本-效益原则和DALYs在农业-营养联姻领域的地位。专家组全部为经济学家的“哥本哈根共识”对世界发展涉及的重大问题(大多为医学和营养问题)进行经济学排序,越靠前的问题越在投资上具有成本-效益优势。2004年“哥本哈根共识”把为营养匮乏者提供营养素排在第二位;2008年,“哥本哈根共识”将通过营养素强化解决营养不良(主要是维生素A和锌)排在首位,投资的收益程度用DALYs来表示[15](P131)。
HarvestPlus在任务上呼应于“哥本哈根共识”,HarvestPlus主席Howarth Bouis是擅长食品价格分析的经济学家,他推动了该项目将所有研究成果的评价限制在经济学范畴内。HarvestPlus根据世卫组织的CHOICE(即选择最具有成本-效益优势的干预措施)理念,以及“如果挽回一个伤残调整寿命年的费用低于当年该国国民人均收入,这种干预措施就是十分经济有效的”这一标准,运用DALYs研究不同作物、不同营养成分在改善隐性饥饿和营养不良上的表现。
HarvestPlus还呈现为“围绕一个想法的联盟”[15](P127),即HarvestPlus并不是根据真实世界评估农业转基因可能发挥的功效。从研发起点看,HarvestPlus清楚知道达到营养目标很难,因此常常借助概念验证,而概念验证只是表示制造技术的可能性。富铁大米便是概念验证的产物。概念验证将事物内部的规范性、政治性和社会性问题翻译成实证科学问题[15](P136)。从研发终点看,HarvestPlus的目标远离研究地点,针对的是想象中的人群。HarvestPlus研发的农业转基因有两个目标:从长期来看的成本-效益优势以及对农村人口的可及性。对群体的指向性使得HarvestPlus关注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追求的是遥远而模糊的目标。HarvestPlus缺乏经验性评估,惯于对远方人口进行抽象,如HarvestPlus最大赞助者盖茨基金会就将农业转基因救助的对象统称为“穷人”。
三、“殖民医学及其遗产”与“IRRI到HarvestPlus时期”对农业转基因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方式的影响
从IRRI到HarvestPlus时期,殖民医学和当代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诸种范式影响了作为“营养-健康-农业”新型联合体的农业转基因,这些范式塑造出了几种研究机制:研发网络替代家族研究客观上对指令系统和垂直干预提出要求;对干预对象的想象和建构;追求技术本身的卓越性;征用成本-效益原则和DALYs进行效用评价;概念验证的盛行;策略性慈善背景下卫生治理实践者向自身利益倾斜以及这种倾斜造成的对被治理者真实需求的漠视;对其他卫生干预方法的拒斥。这些方面共同导致农业转基因的应用往往疏离生活世界既存事实、秩序和习惯。21世纪以来,若干种农业转基因在不同程度上展示出以上研究机制及其内在局限性。
(一)维A补充剂和黄金大米:想象的患者和缺少经验性调查的成本-效益分析
长期以来,印度被发达国家和国际性组织认定其维生素A匮乏问题突出,儿童群体尤其严重。于是,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定期向印度分发维生素A补充剂。2001年,印度阿萨姆地区约30名儿童以建议剂量服用补充剂一段时间后死亡。后来对死因的判断是:这些儿童摄入了过量的维生素A。根据1999年印度医学研究会调查数据,在被西方世界认定存在临床意义上患维生素A缺乏症的阿萨姆地区儿童中,仅有0.3%有毕脱斑(bitot spot,眼睑处白色三角形斑,是表明缺乏维生素A的症状之一)。而在流行病学中,0.5%是判定人群具有临床意义的维生素A缺乏症的分界线。组织和实施这一高剂量维生素A补充项目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阿萨姆当地政府受到指控,两者在缺乏流行病学调查和证据时,贸然将维生素A补充量由原来的每剂2毫升提高到每剂5毫升,导致了过量维生素A摄入及其引发的毒性效应[16]。这一事件肇因于源自殖民医学时期的对弱者的想象,以及这种想象在当代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变体:“想象和建构的风险人群(population-risk)”。
黄金大米是可以合成维生素A前体物质β胡萝卜素的农业转基因,它承担维生素A补充剂的使命,是现代卫生治理所强调的口服补液在农业产品上的翻版,但黄金大米在印度的推广绕开了阿萨姆儿童死亡事件的双重警示:刻板而顽固的对弱者的想象和设定,以及贸然的技术介入。在黄金大米推广中,为论证其优越性,研发者根据20多年前国际调查结果“6个月至5岁儿童是严重缺乏维生素A的群体”这一对被救助者的设定,进行了事前成本-效益分析,结论是:黄金大米在印度市场化后,每年可带来的健康改善值在0.001 6万到8 800万美元之间,研发投资回报率在66%到133%之间,收益将显著大于成本[17],2002-2012年在印度推迟十年使用导致142.4万伤残调整寿命年的损失[18]。
(二)加纳转基因豇豆:卓越科学、管道模型与策略性慈善对农民需求的否定
豇豆是低成本优质蛋白质来源,有近2亿非洲人以豇豆为主食。但豇豆仍是一种仅限于被当地人种植和使用的孤儿作物,商业公司并不重视豇豆。豇豆长期受“豆野螟”这种害虫的攻击,致使西非豇豆的总产量每年损失20%到80%。为“保障非洲农民蛋白质摄入”的营养目标,澳大利亚科研机构运用自称“唯一可能抗击豆野螟”的技术方式,即利用转基因技术使豇豆表达毒性蛋白,并制定审批和监管内容[19]。
抗豆野螟豇豆引入非洲,更深层的背景与洛基会的新型慈善理念有关。洛基会知道,生物技术公司不愿意出钱将基因修饰技术应用于豇豆等农民自种自吃的孤儿作物,因为难以盈利。于是洛基会建议生物技术公司将相关转基因性状捐赠给发展中国家研究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开发对应于孤儿作物的转基因种子[20]。洛基会还动员美国国际开发署、英国援助(UK Aid)这样的大型机构、各类生物技术公司、美国高校等,以集结更大力量来推进转基因技术和产品在全球范围的应用。之于加纳转基因抗豆野螟豇豆,它利用的原始基因cry1AB来自孟山都公司。该公司认为,捐赠cry1AB的使用权能帮助公司挽回点声誉,且不会造成太大经济损失,因为非洲不像亚洲和拉丁美洲那样有较大的转基因市场。
在抗豆野螟豇豆项目开展过程中,到访过加纳的研究者、商人、官员都承诺农民生活将因新技术产品的到来而改善,源自对技术研发管道模型的信赖和对真实需求的漠视,他们都没有再回来过。事实上,加纳一些农民在这种新豇豆来到之前,已经开始通过间作豇豆控制虫害,效果较好[20]。转基因技术并非是治理豆野螟的唯一方法。从保证产量的角度,即使在豆野螟存在的情况下,加纳豇豆也足以喂饱全国人口。加纳农民最关心的其实是“收割后的损失”。他们认为,这一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提高的那部分产量不仅没有意义,还会造成豇豆价格下跌,最后烂在地里。加纳农民的首要需求是:能有更多资金来建造存储设施,对种子和农机设备进行补贴,创造新的豇豆加工方式以扩大销路、创造更多附加值[20]。
(三)乌干达转基因香蕉:“概念验证”的幽灵和非国家治理主体的技术偏好
东非高地蕉是乌干达人的重要主食,但它几乎不含维生素A等营养素。昆士兰科技大学农业技术专家研发出含有维生素A的“金色香蕉”。盖茨基金会为该研究提供了近1 000万美元的资助。盖茨基金会于2003年启动了总额达1亿美元的“全球健康探索大挑战”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征集并资助创造性的研究计划,目的是探索具有技术奇异性的方案,以应对发展中国家的重大健康问题。该项目中第9单元是“农业与卫生治理的结合”:在主食中增添经过系统优化的、具有生物可利用性的营养素。乌干达含维生素A东非高地蕉是入选项目。
但种植这种转基因高地蕉要求农民施更多肥料,并维持一定的播种间距,因为新品种对养分和光照要求很高。然而,种植高地蕉的大多是贫农,他们买不起更多化肥,拥有的土地也很有限。鉴于此,乌干达一些贫农便不选择转基因香蕉,继续种植传统香蕉[20]。非国家卫生治理主体虽有良好初衷,但他们陷入了倒置的境况:首先根据“概念验证”的逻辑设定某种理想技术品类,并基于高度理想化和简化的管道模型,认为技术的奇异性与技术在现实中的效能之间存在必然的演绎关系。盖茨基金会从21世纪初开始,多次凭借自身技术和资金优势,利用农业转基因广泛介入全球卫生治理,强化了对技术性方案的偏好和“银盘思路”,使农业转基因介入的社会痼疾以特定的问题化方式被凝视、呈现和剖析。
四、结语
全球卫生治理作为医学实践,它所依赖的医学范式承袭的是西方殖民医学及其延续。而殖民医学及其延续内在的局限性,造成了农业转基因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实践时,治理实效与治理初衷的背离。这些局限性涉及:一是强调纵向的垂直干预,这带来了家族式研究的盛行,能够联合异质性力量的横向项目被边缘化,以及卫生实践主体对生活世界的失察,最终造成农业转基因在进入地方情境时的突兀甚至无效。二是通过概念验证的方式过度凸显单一要素的功能,这不仅引发了通过农业转基因进行全球卫生治理时对技术奇异性的追求,更使得全球卫生治理实践偏离了对健康状况背后结构性因素的审查。三是对成本-效益原则以及对伤残调整寿命年等具有学术争议概念的过度推崇,带来了评估“实质善”时的思维陷阱。四是对短期的、可视的、可量化目标的重视,使得全球卫生治理实践被囿于工具理性框架中,而忽视了对影响健康状况关键变量的考察。五是选择性初级卫生保健盛行后对相关性不强的一揽子计划的倚重,使卫生实践的审慎性和协调性不足,往往以低成本为标准,抓取一些操作性强的干预手段。基因编辑技术的兴起让单碱基和基因组编辑成为可能,生物反应器的问世又让农业与医学的深度融合成为发展趋势,农业转基因将超越单一营养素的供给,更广泛地介入全球卫生治理。在尊重并认同作为智识努力的农业转基因的基础上,需要反思与超越农业转基因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时所根植的知识框架。而这一框架在根本上是20世纪全球科学的产物。全球科学是形成、编撰于西方世界语境的知识和方法论体系,该体系始终坚持并实践一种统一的、单一的科学理性。全球科学在现代呈现为与权力相对应的干预世界的实践形式。对全球科学的批判性反思,也是在倡导去殖民化的科学和认识论,提升科学实践的开放性和民主程度,推动技术研发对生活世界的倾听和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