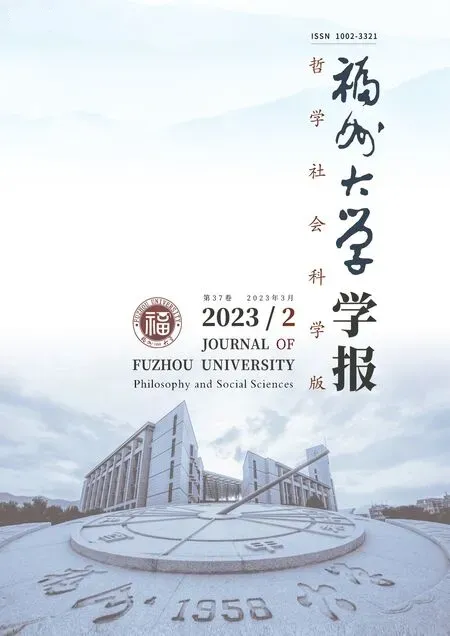清代册封琉球与赐封妈祖关系探究
2023-08-07赖正维马例文
钱 宁 赖正维 马例文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福州 350117)
妈祖为东南沿海民间广为信奉的航海保护神,以护佑行船平安著称,由于灵应显著,福荫广被,自宋以来历代统治者均有赐封。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历史上首次册封妈祖,赐号“灵惠夫人”。宋代共赐封妈祖13次,最后一次在开庆元年(1259),朝廷赐封妈祖为“灵惠显济嘉应善庆妃”。至元十五年(1278),元朝占领福建,元世祖赐封妈祖“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元代共赐封号妈祖8次,最后一次为至正十四年(1354),加赐妈祖“辅国护圣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明代共赐号2次:明洪武五年(1372),因为妈祖庇护漕运,朝廷首次赐号妈祖“昭孝纯正孚济感应圣妃”;永乐七年(1409),因为妈祖庇护郑和下西洋官兵,朝廷再赐妈祖“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明朝结束时,妈祖赐号增加为14字,但仍为“天妃”。
入清以后,朝廷对妈祖的褒封为历朝之最,封号增加更是达到14次之多。赐封事由有平乱助战、护佑册封使、利济漕运、保护堤防等,其信仰活动的功能得到延展。赐封形式主要有增加妈祖封号和御赐牌匾两种。清代首次赐封是在康熙十九年(1680),沿用了明朝14字封号。此后清廷历次加封,每次惯例增加四字。同治十一年(1872),因为保佑漕运,朝廷最后一次赐封妈祖。此时,妈祖已经晋封为“天后”,封号达64字,可谓尊崇至极。(1)徐晓望:《妈祖信仰史研究》,海风出版社,2007年,第315-319页。值得关注的是,清代14次增加妈祖封号,有3次与中国册封使远渡琉球王国关系密切,朝廷因妈祖庇护册封琉球活动有功而赐号,或御赐牌匾。这对妈祖信仰在琉球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清代一共出使琉球8次,其中册封使上奏请求朝廷赐封妈祖的就有6次。册封使请封妈祖的行为不仅在文化层面上促进了中琉两国的交流,同时也反映了妈祖信仰在朝贡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有关妈祖信仰与琉球关系的研究,迄今中国与日本学界大多聚焦于三个层面。第一,琉球册封航路上的妈祖信仰及祭祀活动,如林国平《使琉球与海神信仰》(2)林国平:《使琉球与海神信仰》,《第六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社,2000年,第520-530页。、张文绮《明清册封琉球使者的妈祖信仰》(3)张文绮:《明清册封琉球使者的妈祖信仰》,《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1期。、仲原善秀《册封使的遭难与天后宫》(4)仲原善秀:《册封使的遭难与天后宫》,《历代宝案研究》第6、7合并号,湘京书屋,1996年,第57-66页。;第二,妈祖信仰及其祭祀活动在琉球的传播和嬗变,如钟建华《明清时期妈祖信仰在琉球的传播与式微》(5)钟建华:《明清时期妈祖信仰在琉球的传播与式微》,《八桂侨刊》2022年第1期。、李宏伟和阳阳《琉球王国妈祖祭祀活动之研究》(6)李宏伟、阳阳:《琉球王国妈祖祭祀活动之研究》,《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2期。、谢必震《试论明清使者琉球航海中的海神信仰》(7)谢必震:《试论明清使者琉球航海中的海神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1期。;第三,妈祖信仰与琉球女神信仰的比较及其相关研究,如徐晓望《琉球与福建的女神崇拜比较》(8)徐晓望:《琉球与福建的女神崇拜比较》,《第五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海洋出版社,1996年,第477-489页。、郑国珍《琉球进贡使者多神崇拜习俗的由来及在榕与之相关的史迹考》(9)郑国珍:《琉球进贡使者多神崇拜习俗的由来及在榕与之相关的史迹考》,《第五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海洋出版社,1996年,第368-387页。、窪德忠《中国文化与南岛》(10)窪德忠:《中国文化与南岛》,第一书房出版社,1981年,第237-254页。。然而,有关清代14次赐封妈祖,其中3次与册封琉球的相关研究还未遑展开。因此,本文拟在对明清册封使录、妈祖档案史料、《清史稿》《历代宝案》《球阳》等中日文献资料研读的基础上,考察清代赐封妈祖与册封琉球之间的关联,揭示妈祖信仰在中琉朝贡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
一、康熙五十八年(1719)册封琉球与妈祖入官方“春秋二祭”
琉球是位于中日之间太平洋上的岛国,明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派遣行人杨载作为使节出使琉球,建立正式的藩属关系。直到清光绪五年(1879)琉球被日本吞并前,五百多年间两国关系都十分密切。每当国王即位,琉球均请求明清朝廷派遣册封使前往册封:“琉球国凡王嗣位,先请朝命,钦命正副使奉敕往封,赐以驼钮镀金银印,乃称王。”(11)赵尔巽:《清史稿》卷五二六,中华书局,1977年,第14618页。明清共遣正副册封使43位,共册封琉球23位国王。明太祖还派遣福建东南沿海善于操舵的船民移居琉球,作为琉球从事朝贡贸易所需的航海商贸人才,史称“闽人三十六姓”。福建移民在琉球久米村建立了上天妃宫。此后,琉球王府也在那霸建立了下天妃宫。每逢朔望节庆,琉球人都要供奉天妃。万历三十年(1602)来到琉球的日本僧人袋中良定在《琉球神道记》中记载:“世人皆称此神为菩萨……此菩萨为海神之最,以妃位相配也。此神于海中对往来商船扶危济困,德行足以配天,故名曰天妃。”(12)袋中良定:《琉球神道记》卷五,加藤玄智编,明世堂书店,1943年,第64页。可见妈祖信仰已逐渐成为中琉文化交流的纽带。
中琉之间航程漫长,约两千四百余里,当时受航海、造船技术等客观条件限制,迷航、触礁、遭遇风暴频发,应对方法稍有失当就会酿成船毁人亡的惨祸。根据日本学者赤岭诚纪统计,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至清光绪二年(1876)的约五百年间,中琉之间的航道上共发生441起船难,其中进贡船就有85起,死亡1 835人。(13)赤岭城纪:《大航海时代的琉球》,冲绳时报社,1988年,第39-40页。使团在途中一旦遭遇海难,只能祈求神灵保佑,同时尽力与风浪搏斗,逃出困境。海上的艰险导致所有册封琉球使团人员都笃信海神,并将平安往返琉球都归功于海神的庇护。
在册封琉球的航海过程中,使团供奉的海神以妈祖为主。妈祖救助海难、护国庇民的传说经过历代口耳相传,民间已经奉其为海洋保护神。明清朝廷先后在长乐闽江口广石澳和福州亭江怡山院两地设立妈祖庙,以供册封使出行前祭祀。册封使团先要准备谕祭海神文,焚香祭祀妈祖及其他海神,出发前将神像恭请上船,到达琉球后置于琉球妈祖庙供奉,事毕回国时再请神回船。此外,册封使回到福州后,必定到妈祖庙进香和还愿,出资兴修当地庙宇,并留下对联或题刻等。回京后,向皇帝奏报其路途中受到的海神庇护,请求皇帝赐予封号或祀典,以回报海神襄助。明朝册封使将妈祖信仰当中“庇佑航海”的一面广为传播,如嘉靖十三年(1534)册封正使陈侃在其《使琉球录》中著有一篇《天妃灵应记》,详细讲述其出使途中船上“用闽人故事,祷于天妃之神”一事(14)陈侃:《使琉球录》,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0年,第35页。。册封副使高澄亦著有《天妃灵异记》。万历七年(1579)册封使谢杰在《琉球录撮要补遗》中也载道:“航海水神,天妃最著。”(15)夏子阳:《使琉球录》,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0年,第277页。郭汝霖、萧崇业、夏子阳等册封使也各自留下有关妈祖护佑航行的记载。明廷从万历年间起,固定事先准备祈报海神祭文两道,夏祈与冬报祭文内容大致对称。册封使出洋前官祭天妃遂成为惯例。但明朝未曾因为册封琉球事而赐封妈祖。
康熙二年(1662)册封使张学礼、王垓虽在出海前在长乐梅花所祭祀天妃,在琉球天妃宫献上一面“中外慈母”匾额,归来亦修葺庙宇,“置金冠、悬匾、答神惠也”(16)张学礼:《使琉球记》,台湾文献丛刊第292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1年,第9页。,但因为南方沿海战乱,册封使团出行草率,未曾得到清廷的重视,也就没有下赐谕祭海神文。
清朝对妈祖的尊奉始于康熙十九年(1680)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请封。当时清朝新定三藩之乱,试图以尊奉妈祖重聚人心,赐号“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但未有春秋常祀,供品也仅敬献“少牢”,低于国家祀典的“太牢”。而后历代册封使经历艰险往返于中琉之间,平安归来后向朝廷积极争取官方祭祀活动,讨请匾额,为妈祖等海神加封。
清代首次因册封琉球事为妈祖请封的是汪楫和林麟焻的册封使团。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任命翰林院检讨汪楫、内阁中书舍人林麟焻分别充任正、副使节,册封琉球尚贞王。此次册封是三藩之乱后的首次册封活动,中琉双方皆予以重视,康熙还下赐御笔“中山世土”匾额给琉球。汪楫、林麟焻使团出行十分顺利,当年六月十三日从五虎门放洋出发,六月十六日即抵达那霸,为历届册封使抵达琉球最快者。两人圆满完成了册封活动,并前往久米村上天妃宫祭祀妈祖,但册封使团返程即遭遇风暴,汪楫在《使琉球杂录》卷五“神异”中记载:“二十八日一鼓,飓风大作,云垂水立,一帆如夹雪壁中,虽预为之防而四夜三昼不止,浪欲翻天,舟行忽拍云端,忽落渊底,跳掷奔腾,不可名状……祷天妃许为请春秋祀典,风稍定。”(17)汪楫:《使琉球杂录》,引自《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 (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805-807页。林麟焻也在《敕封天后志序》中写道:“逮夫典礼事竣,方图反棹,而狂澜汹涌,澎湃滔天,樯撼舟横,维楫为之断裂,震荡漭沧,四无足恃。倾危间,十难一全之势。舟中人咸谓惟神可祷以无咎。倾者少安,裂且不坏,然而淼淼巨浸奔蹴,却迷天日。夜来帆影,不意昏黑漂泊之顷,恍有二火晶光熠耀桅舰之前,私幸有赫神灵于昭于天,差可借以无恙。”(18)林清标:《敕封天后志》,乾隆戊戌年(1778)刊本,第16页。
正是因为此次历险,汪楫对于妈祖信仰更加推崇。而作为莆田人的林麟焻,更是积极为妈祖请奏褒扬。二人向康熙帝上书详述出使遇险经过和得到天妃保佑一事,提议举行春秋二祭祭祀妈祖:“有此三异可验神功,乞敕下礼臣议春秋二祭,着令地方官敬肃奉行,则海疆尽沐神庥,履坦无非圣泽矣。”(19)汪楫:《使琉球杂录·册封疏抄》,第875页。然而礼部认为天妃级别与黄河神相同,没有举行春秋二祭的先例。康熙据此驳回上奏。说明清初妈祖祭祀品级不高,还没有得到统治者的充分重视。
虽然康熙拒绝了汪楫和林麟焻的上奏,但此后关于加封妈祖的提议一直没有停止过。康熙二十三年(1684),施琅收复台湾,又以平乱助战为由请求加封天妃,但仍被驳回。“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请封天妃之神,礼部不准行,但令致祭。上曰,此神显有默佑之处,着遣官致祭。”(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1页。
康熙五十八年(1719),徐葆光、海宝作为正副使节前往琉球册封尚敬王,此次航行往返皆十分顺利。徐葆光《中山传信录》记载,封舟往返均没有遭遇风暴,触礁之险也因呼神获救而免。册封使团将出使顺利一事归功于“天妃默佑”,在琉球即前往上天妃宫行香拜祭。回国后,徐葆光和海宝再度请求朝廷赐予妈祖春秋二祭的地位:“自前平定台湾之时,天妃显灵效顺,已蒙皇上加封致祭。今默佑封舟,种种灵异如此。仰祈特恩许著该地方官春秋致祭,以报神庥。”(21)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台湾文献丛刊第306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2年,第30页。礼部答复:“今天妃默佑封舟种种灵异,应令该地方官春秋致祭,编入《祀典》。”康熙五十九年(1720)八月初六,康熙皇帝最终批准了妈祖入祀典,地位与山川岳渎之神同等,春秋二祭遂成为惯例。(22)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第31页。此次赐封标志着妈祖从民间信奉的神明跃升为朝廷官方推崇的正神,这与康熙年间诸位册封使的努力请封是分不开的。
二、乾隆二十一年(1756)册封琉球与首次赐号妈祖“诚感咸孚”
妈祖信仰的官方地位得到显著提升是在雍正年间,雍正三年(1725)九月,巡台御史禅济布、给事中景考祥上奏为妈祖请封,列举康熙六十年(1721)朝廷平定台湾朱一贵起义时,福建水师得到妈祖庇佑的种种事迹,但误将民间传说康熙年间妈祖已“加封天后”一事掺杂其中,雍正批准后,妈祖受封天后一事就此得到官方承认(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3页。。雍正朝共赐封妈祖3次,雍正四年(1726),皇帝为天后宫颁赐匾额“神昭海表”,湄洲、厦门、台湾各处天后宫均悬挂朝廷赐匾。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因护佑堤坝修筑一事,下赐“福宁昭泰”匾额给浙江海宁海神庙。同年,福建总督郝玉麟上奏请赐福州南台天后宫匾额:“查福建省城南台地方,襟江带海,商船云集,旧有神祠为万民瞻礼之所,臣等不揣冒昧,恳求圣恩,俯照湄洲等处,并颁御书匾额,敕令春秋祭祀。”(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43页。雍正下赐“锡福安澜”匾额给南台天后宫,从此福建省城官员均在此祭祀妈祖。
妈祖在康熙十九年(1680)成为清廷官祀神明,而康熙五十九年(1720)在册封使徐葆光和海宝的奏请下,妈祖已经获得了春秋二祭的礼制,然而郝玉麟认为还不足以体现妈祖的地位,又奏请希望各省官衙领衔祭祀:“其各省会地方,如曾建有祠宇而来,经设立祀典之处,并请降旨一例举行。”(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45页。于是在雍正十一年(1733)后,清廷下令全国凡建有天后宫的省城,均由总督、巡抚带头执行春秋二祭,极大推动了妈祖信仰的发展。(26)徐晓望:《妈祖信仰史研究》,第216页。清廷对妈祖态度的转变,一方面是由于雍正本人对道教的极力推崇,另一方面在于收复台湾以后,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联系日渐紧密,海峡往来航船及沿海水师官兵皆祭拜妈祖,清廷也就顺应变化,将妈祖的地位相应提高,收拢人心。
乾隆二年(1737),福建总督郝玉麟上奏,因台湾官员兵士往来两岸得到护佑而请封妈祖,妈祖被正式册封为天后,并加封号“福佑群生”。乾隆帝即位后,对佛道二家都采取推崇的政策,因此赐封妈祖达16次,为历朝最多者,特别是首次因册封琉球事为妈祖增加封号。
乾隆十六年(1751),琉球王尚敬薨。乾隆二十一年(1756),翰林院侍讲全魁与翰林院编修周煌奉命出使琉球,册封尚穆王,六月初六例行在怡山院谕祭妈祖,颁赐祭文。清朝前四次谕祭海神文的内容基本一致,海神祭文的撰写还比较笼统,仍沿用明朝祭祀多个海神之例,没有专门祭祀妈祖。
然而,全魁、周煌使团此次行程航路颇为凶险,接连遭遇风暴和触礁,清廷首次以租用民船代替官造贡船,船身亦不坚固。据周煌《琉球国志略》记载,使团于二月初九日出京,十四日抵达姑米山下,“适当暴期,波浪兼天,舟身震撼,呕逆颠仆者无数”。只得在原地顶风坚持,但之后海面情况继续恶化:“延至二十四日夜,台飓大作,椗索十余一时皆断,舟走触礁,龙骨中折,底穿入水。”(27)周煌:《琉球国志略》卷七,台湾文献丛刊第293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2年,第170-171页。危难之际,使团看见桅杆顶上出现亮光,海面隐约浮现灯火,恍如有神明显灵。之后,船只稍微向右倾斜,滑脱礁石,得以安全,使团众人皆认为是妈祖显圣。册封使团历经艰辛才得以到达琉球,二百余人全部生还,二号船则漂流到浙江永嘉。因船只在路上遭遇风暴,贡船受损,货物被打湿,影响到随船水手和兵丁携带货品在当地贩卖的收入,导致使团在琉球还发生了清兵向琉球方面勒索的骚动。回国后不久事发,全魁、周煌险遭革职,犯罪兵丁数人被处决。(28)曾焕棋:《清代琉球册封使研究》,榕树书林,2005年,第185页。但册封使事大体顺利,全魁、周煌使团还捐资在姑米山(久米岛)修建了琉球第三座妈祖庙,请琉球人从福州购买神像,并赠银两、对联、匾额,以纪念脱险生还一事。久米岛天后宫至今尚存。(29)球阳研究会:《球阳》,角川书店,1978年,第337页。
乾隆二十一年(1756)十月二十一日,全魁、周煌使团完成册封,登船返回。十一月初七日出海,因为风暴又回到琉球。次年正月三十日再次出发,二月十三日抵达福建五虎门,“一路风恬浪静,险阻无虞”(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66-68页。。由于全魁、周煌使团在海上颇多周折,回程时,两位使者专程至怡山院行谕祭海神礼。(31)周煌:《琉球国志略》卷五,台湾文献丛刊第293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2年,第147页。此外,两位使者上奏礼部《请加封谕祭疏》,首先是为妈祖争取加封,其次是请求另作妈祖祭文两道,或在祭海神文内明确祭祀妈祖。周煌解释其缘由道:“臣等兹役,自闽海往还,祈神获佑;窃疑封号尚袭前明,即谕祭文内但云‘海神’,不言‘天妃’。敬沥微忱,乞加封号,并请明颁谕祭;俱蒙圣慈俞允。崇报益隆,名实悉称,典礼周祥,超轶千古矣。”(32)周煌:《琉球国志略》卷七,第168页。
乾隆二十二年(1757)五月十四日,皇帝同意礼部所奏。六月十八日,礼部奉旨,乾隆皇帝赐封天后“诚感咸孚”(33)周煌:《琉球国志略》卷七,第171页。。又规定以后祭拜妈祖,行三跪九叩之礼,礼节愈加隆重。由于全魁、周煌册封使团的请封,天后得到了“诚感咸孚”四字加封,这是清廷第一次因册封琉球事而加封妈祖,并且清廷对福州怡山院的天后祭祀也更加重视,此后琉球使团所发祈报祭文,不再是笼统献给海神,而是专门献给天后,妈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嘉庆五年(1800)册封琉球与赐号妈祖“垂慈笃祜”
嘉庆年间,清廷对于康、雍、乾三朝尊奉妈祖的制度有所继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早在嘉庆即位之初,就下诏给福建巡抚姚棻,要求他向福建沿海各天后宫敬奉藏香:“近来闽省兵丁等过洋,屡有遭风失水等事,殊为可悯。因思该省天后庙久著灵验,或地方官平日不能虔诚供奉,以致未迓神佑,著发去藏香一百炷交与该督抚,于天后降生之原籍兴化府莆田县地方及濒海一带各庙宇,每处十炷,敬谨分供,虔心祈祷,以迓神庥而静风涛,将此谕令知之。”(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121页。
嘉庆皇帝对于妈祖信仰的重视,与嘉庆年间海盗频发、东南沿海水师巡航频繁有关。沿海禁令放松后,商船和渔船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无论官民皆尊崇妈祖,反映了台海两岸愈加密切的经济、军事往来情况。
嘉庆朝赐封妈祖活动共5次,其中与琉球册封使团有关的共3次,分别是嘉庆五年(1800)因册封使赵文楷、李鼎元出使一事增加妈祖封号,嘉庆六年(1801)加封妈祖父母,嘉庆十四年(1809)应册封使齐鲲、费锡章之请,下赐“昭佑孚诚”牌匾。
嘉庆五年(1800)增加妈祖封号一事与往年相比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并非以往由归来的册封使请封,朝廷在使团远渡琉球之前就已经拟定好了封号,这也是清廷首次因册封琉球事主动下赐妈祖封号。嘉庆帝在当年的正月二十九日下诏,鉴于沿海“兵船及商船往来,均赖神力庇佑”,应该再增四字封号。(3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123页。嘉庆五年(1800),翰林院侍读赵文楷、李鼎元分别充任正副使,册封琉球尚温王。使团临行前,为求得天后庇护,朝廷不仅下令翰林院撰写祭文,交此次册封琉球国正使赵文楷,赍往福建敬谨致祭,并且加封天后“垂慈笃祜”四字神号。册封使团未出行前就到东四牌楼天后宫进香,祈祷平安。同年二月二十八日正副使出京,抵达福州后,四月十三日前往南台天后宫祭祀天后。据李鼎元《使琉球记》记载:“恭奉谕祭加封天后文出城,至南台之冯港。主祭者正使,陪祭者余与将军、巡抚、都统、司道等官,皆朝衣。”(36)李鼎元:《使琉球记》,台湾文献丛刊第292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1年,第148页。可见祭祀礼仪之隆重。
五月初五,册封使团在福州怡山院谕祭海神,等候出洋。五月初七使团出发。开舟前,船队迎请妈祖和拏公神像上船,行三跪九叩之礼,又命令道士作法:“取旗祝之,噀以酒。合口同言:‘顺风吉利。’”初十船队行至赤尾屿附近,遭遇风暴,船只有倾覆的危险:“午刻,大雨,雷以震,风转东北。舵无主,舟转侧,甚危。”琉球接封大夫梁焕建议船队退回五虎门改日再出发,但船只陷在风暴中进退不得,赵文楷、李鼎元两人只得就地向天妃祈祷:“因与介山(赵文楷)潜焚藏香,跪祷于天后曰:‘使者闻命,有进无退,家贫亲老,志在蒇事速归!神能转风,当请皇上加封神之父母。鼎元自元旦发愿,时刻不忘,想蒙神鉴!’祷毕,不半刻,霹雳一声,风雨顿止。”(37)李鼎元:《使琉球记》,第159页。
使团于五月十二日抵达那霸港,册封使在琉球期间多次前往天后宫祭拜。赵文楷、李鼎元出使琉球期间,嘉庆皇帝十分关心使团的行程。当得知他们于五月十三日安全抵达琉球,嘉庆帝下诏发送大小藏香各五炷给闽浙总督玉德,令其前往厦门天后宫行香致谢,并祷祝该使团能平安归来。(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143页。当赵文楷使团返回后,嘉庆皇帝又特意“发去大小藏香各十枝,著玉德于接奉后即代朕祀谢,用答神庥”(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157页。。
嘉庆六年(1801)正月,回到京城的李鼎元一直记挂曾在旅途中祈祷妈祖一事,专门上奏疏吁请清廷晋封天后的父母。妈祖父母从宋朝受封以来,历朝统治者均未再加封。嘉庆五年(1800)元旦,李鼎元在北京祭祀妈祖时就产生了这一想法:“凡天下受敕封为正神者,率褒及其父母;况天后由孝女成神,后殿不祀其父母而祀三官,失其本矣。”(40)李鼎元:《使琉球记》,第235页。此次他又在上书中称:“窃念天后以孝女成神,志或未尽,似应追封崇祀以迓神庥。谨按,后父名愿,宋初官都巡检,宝祐五年因教授王里之请,后父封积庆侯,母封显庆夫人,后兄以及神佑皆有锡命,此后未经加封。合无仰恳皇上天恩,特赐褒封在于天后行宫行殿设位崇祀,以答天后孝恩,即以昭圣朝锡类之盛典。”(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166页。
其后,清廷奉旨封天后之父林愿为积庆公、天后之母为积庆夫人。据《南平县志》记载:“嘉庆六年十一月间,奉旨天后父母制造神牌安奉,春、秋致祭。”(42)蔡建贤等:民国《南平县志》卷十一,祠祀志,1985年,第597页。圣旨规定,此后各县凡有天后宫处,都必须祭祀天后父母。妈祖信仰的孝义一面也得到了官方的褒扬,清廷对天后的信仰更推进了一步。不仅主动新增封号,还在册封使赵文楷、李鼎元的奏请下赐封妈祖父母,这表明嘉庆帝对于妈祖信仰的虔诚之情要超过其他清代皇帝。这一点从嘉庆皇帝历年对全国各地天后宫的修缮以及嘉庆十七年(1812)在皇宫御苑里修建“天后惠济神祠”等举动中也同样有所体现。(43)徐晓望:《妈祖信仰史研究》,第237页。
嘉庆年间的另一支琉球册封使团是嘉庆十三年(1808)的齐鲲、费锡章使团。齐鲲、费锡章使团于当年五月初三出洋,前往琉球国册封尚灏王。路途中两次遭遇风暴,回返福州时船只失控几乎撞山,但最终都得以脱险,“初九日放洋,十五日进五虎门,十七日早至福建省城。通省官民无不讶为神速。此皆赖圣主洪福,天后默佑。是以来去大洋前后均系七日,两次猝遇风暴俱蒙化险为平”(4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192页。。齐鲲、费锡章次年回国后上奏嘉庆帝,请求在褒扬妈祖的同时,对陪同上船供奉的水神陈文龙、拏公也一并给予赐封。陈文龙是南宋时莆田人,抗元英雄,死后被视为水神,俗称“水部尚书”。拏公相传是宋代邵武府拿口镇人,传说因试毒挽救村民而殉难,被视为海上淡水的保护神。二者都是闽江下游流行的水神信仰,祭祀中经常作为妈祖的陪神。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汪楫出使起,拏公就与妈祖一起被奉置于贡船上祈求平安,而陈文龙首次出现则是在齐鲲、费锡章使团,被放置在二号船。有鉴于上述原因,嘉庆皇帝下诏称:“陈尚书、拏公于该省南台各有专庙,据该处耆民人等吁求御书匾额等语,此次册封琉球使臣海舟往返平安迅速,实昭灵贶,兹发去御书匾额三分,着张师诚接奉后即于各该处敬谨悬挂,以期环海永恬,普邀神庇。”(4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194页。下赐“昭佑孚诚”牌匾给福州怡山院天后宫,南台尚书庙、拏公庙也得到了御匾。嘉庆十四年(1809)的加封是陈文龙和拏公首次与妈祖同享下赐匾额的待遇,反映了清廷对册封使出发地福州水神信仰的重视。
四、道光十八年(1838)册封琉球与赐号妈祖“泽覃海宇”
道光朝对于妈祖的尊崇与嘉庆朝基本保持一致,共赐封妈祖6次,其中2次与册封琉球有关。道光十八年(1838),册封正使林鸿年、副使高人鉴出使琉球,册封尚育王。林鸿年册封使团未有类似《使琉球录》的著述传世,因而探求使团在海上航行和在琉球活动的详情较为困难。后任册封使赵新的子孙在刊行《续琉球国志略》时记载道:“缘乾隆间,有翰林院侍读周煌所著《志略》,齐北瀛太守有《东瀛百咏》,而林勿村中丞所著录者未见。恐钜典煌煌,散佚无考;故定著《续琉球国志略》。其义例,悉仍前志云。”(46)赵新:《续琉球国志略》,台湾文献丛刊第293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60年,第337页。
这说明林鸿年使团的册封使录早在清末已经无考,然而其册封活动始末亦散见于《历代宝案》《中山世谱》等典籍之中,幸好赵新《续琉球国志略》一书对道光十八年(1838)册封活动情况有所补充,因故如今仍然能够考察到林鸿年使团请封妈祖的部分情况。
道光十八年(1838)二月十日,林鸿年使团从北京出发,四月二日抵达福州,从福州人金广发和邱大顺手中选定商船两只作为封舟。人员规模相较以往册封使团有所缩减,且受乾隆年间兵丁骚乱事件影响,使团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在福州期间,林鸿年等人检阅封舟,谕祭天妃及陈文龙,准备出海。四月二十七日正副使首先奉“谕祭天后海神祈文各一道,诣闽安镇怡山院虔诚致祭毕,即便放舟”。(4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251页。本次出使,祭文内容相较以往更为隆重,而且列出了所有和航海有关的封号称呼妈祖,而与漕运、堤防有关的封号则从略。五月初四,林鸿年使团出洋,五月初九抵达那霸港。八月初三,林鸿年使团册封琉球王世子尚育,宣读道光皇帝诏书,而后,册封团将道光皇帝御书“弼服海隅”匾额颁赐尚育王,完成册封典礼。林鸿年使团在琉球共160天,受到了尚育王的隆重接待。林鸿年使团谢绝赠礼,并将册封结余240万贯钱全部交给琉球国王赈恤民众。此举赢得了琉球上下的一致称颂。林鸿年还在琉球积极从事文化交流活动,作《谕劝惜字纸》,劝诫当地人建立焚字炉,珍惜书籍纸张。(48)球阳研究会:《球阳》,角川书店,1978年,第460页。
道光十八年(1838)十月十二日,林鸿年使团完成册封任务,与琉球方面的两艘谢恩贡船一起返航。因护封游击周廷祥在七月二十七日病逝于琉球,尚育王表奏“封舟西返带柩回闽”,赠银五百两。(49)冲绳县教育委员会:《历代宝案》校订本,第12册,卷167,冲绳县教育委员会,2000年,第255页。二号封舟由副使高人鉴临时统领,但行至那霸外海时触礁,船体受损,被迫返回那霸修整,十月十四日另行启航。其余船只则正常归航,经由南杞山、定海,于十月十九日入五虎门。正副册封使“恭祭天后海神后,即于十月二十八日进省”(5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256页。。十月二十八日,使团从福州南台岛上岸,册封活动至此结束。安全返京后,林鸿年、高人鉴奏疏《恳请再加天后等神封号颁匾事》,疏中提及册封使团回程时,“两次猝遇风暴,正在汪洋万顷之中,人力莫施,举舟惶悚,臣等虔诚祈祷,皆获化险为平。舟人佥谓神助圣朝,宣灵赞顺,同声欢颂,感凛万分。伏查天后之神在我朝,夙昭灵贶,叠荷加封,此次转危就安,显应彰著合无。”(5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260-262页。因此请求皇帝给予妈祖和随船的尚书公陈文龙、拏公一起颁赐。礼部议称:“此次林鸿年等封舟内渡,两次猝遇风暴于危险万状之时,俱得默邀神助,借以化险为平。仰见圣朝盛治遐敷,百灵效职。而天后之宣显赞顺,神佑弥隆。应请如该使臣等所奏天后旧有封号恩赐再加晋封,以昭灵应而答神贶。”(52)蒋维锬:《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1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100页。道光皇帝遂按照嘉庆年间惯例,颁发三道御书匾额:
“福佑瀛壖——写赐福建省天后庙请讨扁一面”;“海澨昭灵——写赐福建省陈尚书公庙请讨扁一面”;“利济心敷——写赐福建省拏公庙请讨扁一面。”(5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260-263页。
其后,闽浙总督桂良与福州缙绅于道光十九年(1839)十月二十日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将匾额献给天后宫等庙宇。关于加封天后一事,道光帝“谕旨晋封‘泽覃海宇’四字”(54)赵新:《续琉球国志略》,第299页。。
此后的咸丰朝是给予妈祖封号最多的时期。咸丰皇帝共赐封妈祖10次,给予四字封号5个,分别为“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使得妈祖的封号长达62字,已经超过了黄河神金龙大王的40字,体现了天后在当时所有水神中的崇高地位。咸丰也为妈祖下赐过匾额,咸丰七年(1857),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南北物资运输只能依赖海运,因此咸丰帝给福州的天后宫、尚书庙赐匾:“风恬佑顺——写赐福建闽县天后宫庙扁一面”;“效灵翊运——写赐福建闽县陈尚书庙扁一面”。但咸丰年间没有册封琉球,道光十九年(1839)的赐封是清朝最后一次因为册封琉球事而给妈祖增加封号。
五、同治五年(1866)册封琉球与最后一次赐匾妈祖诸神
同治五年(1866)赵新、于光甲册封使团是中琉交往史上最后一支册封使团,此后日本加紧了吞并琉球的进程,并最终使之灭亡,晚清彻底失去了对琉球的控制力,也不再有朝贡活动。本次使团出行虽未争取到再度给妈祖加封,但同治皇帝应册封使之请下赐了牌匾。同治朝共赐封妈祖5次,例如同治四年(1865),应五口通商大臣崇厚请讨,同治皇帝下赐“赞顺敷慈”牌匾给天津天后宫。(5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329页。同年,闽浙总督左宗棠上奏请同治皇帝下赐匾额“慈航福普”(5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327页。,还调用福建水师作为出使队伍,准备护送册封使出洋。同治七年(1868),下赐匾额“德施功溥”给福建船政天后宫。同治十一年(1872)因海运顺利加封妈祖“嘉佑”后,清廷鉴于妈祖封号过长,不再为天后增加封号。尽管停止新增封号,朝廷给天后宫赐字题匾的现象依然常见。
同治五年(1866),清廷最后一次派出使团册封琉球国王尚泰,礼部在下达册封颁赐详情时,明确按例颁发谕祭天后文:“向例正副使远涉海洋,赐给谕祭海神文二道,谕祭天后文二道,赍往福建致祭。此次应颁给祭海神祈报文各一道,谕祭天后文二道,书名天后封号,于怡山院天后宫举行致祭。祭文由内阁撰拟,交封使赍往致祭,其香帛、祭品该地方官备办,照例核销。”(5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335页。
赵新等人于同治五年(1866)正月从北京出发,四月底抵达福建。赵新等同福建巡抚徐宗乾选募商船作为封舟,当年五月十三日,使团谕祭妈祖。此次谕祭文与道光十八年(1838)的不同点,在于列举出了妈祖的全部封号。(58)赵新:《续琉球国志略》,第300页。之后,使团从福州南台开船,在五虎门候风时,副使于光甲还专程到闽江出海口的亭江怡山院祭拜天妃。六月初九开洋,六月十八日到达琉球近海,因为黑潮涌入港湾,赵新等人被迫在海上漂荡了整整三天。赵新在《续琉球国志略》中记载此次遇险经历称:“午后,黑云陡起,海色如墨,一舟皆惊。臣等谨焚香,默祷天后、尚书、拏公并本船所供苏神各神前。入夜,墨云四散,仰见星光,阖舟额庆。”(59)赵新:《续琉球国志略》,第336页。使团最终在六月二十一日傍晚抵达那霸港。七月二十日,赵新等人祭奠琉球已故先王尚育,八月二十七日,宣读册封尚泰王的敕书。使团于十一月初十从那霸港出海回国。赵新使团在琉球的逗留时间只有138日,是历届使团当中最短的,而且频频要求降低接待供应,减轻琉球方面的负担,这与琉球末年经济疲敝的实际情况有关。(60)曾焕棋:《清代琉球册封使研究》,第317页。除了出洋时的险情外,使团从琉球归来途中也遭遇不顺。赵新后来在上奏中称:“又于十一月初十日自球反棹放洋,是夕,复遇暴风,巨浪山立,越过船头,船身几没,复触礁沙,势极危险。臣等复于神前虔祷,化险为平。”(6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342页。
赵新使团抵达琉球时,照例将妈祖等诸海神恭迎上岸,供奉在天后宫。使团在琉球多次到天后宫参拜妈祖、陈文龙、拏公。每次参拜均发布公告,张贴辕门,以示隆重,回国之前再将妈祖及诸位海神请回封舟。使团从琉球归来后上奏为妈祖等海神请讨匾额,同治皇帝由臣下代笔赐匾:“惠普慈航——写赐琉球国使臣赵新请讨天后庙用扁一面”;“朝宗利济——写赐琉球国使臣赵新请讨尚书庙用扁一面”;“恬波仰镜——写赐琉球国使臣赵新请讨拏公庙用扁一面”;“仁周海澨——写赐琉球国使臣赵新请讨苏神庙用扁一面”。(6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352页。
妈祖、水部尚书陈文龙、拏公都是清朝册封使传统祭祀的神明,而“苏神”则是第一次出现在赐匾的范围内。苏神又名苏臣、苏王爷,本名苏碧云,据称为明朝天启年间人,隐居不仕,晚年移居海岛,为来往海船指引平安,死后成为闽南一带信奉的行船之神。因赵新在遭遇风暴时也向苏神祈祷,于是在上书中请求给苏神一并赐匾,得到皇帝准许。至此闽南水神也被列入了随船祭祀的范围之中,但遗憾的是此后再无琉球册封使团。
光绪五年(1879),日本吞并琉球,清廷册封琉球国王一事便告结束。福州本地陪祀水神盛况不再,南台天后宫和怡山天后宫相继衰落。(63)徐晓望:《妈祖信仰史研究》,第252页。不过清廷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华侨出资赈灾下赐“波靖南溟”匾额给南洋福建会馆为止,仍然对妈祖有所赐封。光绪年间赐封7次,以赐封台湾各地天后宫和奖励赈灾为主。宋、元、明三朝统治者各赐一匾,清朝则多达40余次,仅同光二朝就有20次。晚清赐匾虽多数由南书房代写,并非御笔,但也体现了清廷对于赐封妈祖的重视。
六、结语
清代对于妈祖的崇敬程度相对于以前的朝代可以说是迅速提升,无论是对妈祖封号的增加还是下赐匾额的数量,都要远胜于前朝。妈祖跃升为“天后”,成为官方最为推崇的海神。一方面与康熙年间收复台湾后对东南沿海的经略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清朝重视中琉朝贡关系有关。妈祖的64字封号里,有12字与册封琉球相关。从康熙年间汪楫、林麟焻等人请求让妈祖入国家祀典并行“春秋二祭”开始,到乾隆年间全魁、周煌请求另作谕祭海神文祭祀妈祖;嘉庆时期赵文楷、李鼎元请求加封天后父母,齐鲲、费锡章请求一并赐封妈祖的陪祀水神陈文龙、拏公;道光年间林鸿年、高人鉴最后一次为妈祖请求封号;同治年间赵新请求再增加对苏神的祭祀等,妈祖地位在清朝逐步提升,琉球册封使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册封使请求册封妈祖的事由,大多因为他们在漫长的航路途中遭遇风暴,最终有幸脱身。也有人因航行十分顺利,在顺风条件下快速往返中琉之间,感叹行程如有神佑。在科技条件尚不发达的年代远渡重洋,经历生死劫难,又或是平安行船未遇劫难者,自然会将原因归功于“神明护佑”,在当时而言是一种朴素的情感表达。加之福建在中琉贸易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福建籍的船工、水手,还是琉球负责朝贡事务的闽人后裔,都笃信妈祖。册封使在路途中容易受到随船人员和琉球人的感染,从而认同妈祖信仰,在完成册封使命后为妈祖争取赐封。明代册封使谈论神异话题受儒学影响,对妈祖信仰还多少持有保留态度,如嘉靖十三年(1534)册封使陈侃就在《天妃灵应记》开头写道:“神怪之事,圣贤不语;非忽之也,惧民之惑于神而遗人道也。”而清朝的册封使则更为推崇妈祖,而且闽籍册封使在其中作用明显,康熙二十二年(1683)副使林麟焻、嘉庆十三年(1808)正使齐鲲、道光十八年(1838)正使林鸿年、同治五年(1866)正使赵新,他们自身就是福建人士,对妈祖文化有着深刻的认同。例如首请将妈祖列入春秋二祭的林麟焻出生于莆田,认为自己是妈祖的子孙后代,回到乡里后也亲自为《天妃显圣录》作序。齐鲲出生于福州,对福州地区的水神信仰较为了解,于是首次请求将水部尚书陈文龙、拏公也与妈祖一并颁赐等。封赐妈祖活动的提升也与帝王的态度有关,笃信妈祖的雍正、乾隆、嘉庆、咸丰等皇帝在位期间,赐封的力度都有极大的提升,清廷以增加封号和颁赐匾额两种形式,维持着妈祖在海神信仰当中的权威,借以安定沿海地区。
琉球册封使请封妈祖不仅提升了妈祖的地位,更是通过册封活动将妈祖信仰远播琉球,对琉球社会亦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天后地位不断提高,册封使在进行活动的过程中更加严格遵守对神明的尊奉,例如举行谕祭仪式、迎送神像上下船、拜谒天后宫行香等,将这些仪式也一并带到了琉球。琉球的妈祖信仰就以三座天后宫为中心长期延续,与两国的朝贡贸易紧密相连,成为古代中琉两国政治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