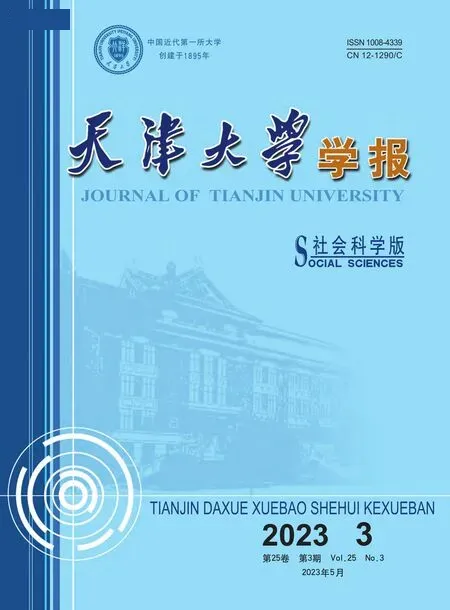梁思永与中国田野考古学
2023-08-07李鹏
李 鹏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350)
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考古学是一门有别于传统金石学的新学问。考古学的新,主要表现在它是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开展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并以田野考古所获取的资料为研究对象,是考古学的基本特征。回首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发展历程,这是一门立足于田野,不断运用新方法,贡献新资料,参与重建中国古史,被友邻学科与社会公众广泛接受与认可的新学问。史语所考古组,尤其是他们在殷墟十五次发掘中所奠定的“殷墟传统”[1],无疑代表了中国考古学百年来主要的发展方向。
尽管也有学者指出,在中国考古学的创建与发展历程中,还存在着诸多殷墟以外的“暗流”传统[2]。但不可否认的是,史语所考古组的成立与殷墟发掘,对此后中国考古学发展道路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在以往论及“殷墟传统”的相关著述中,最受关注的考古学家,无疑是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其实奠定“殷墟传统”的,还有另一位不容忽视的考古学家——梁思永。
梁思永,1904 年生人,原籍广东新会,是梁启超的次子。他于1924 年在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后,至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 年夏取得硕士学位,随后回国加入史语所考古组,先后主持并参加了昂昂溪、热河、小屯、后冈、城子崖、西北冈王陵等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取得了以三叠层为代表的多项开创性学术成果,1948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0—1954 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工作至病逝。作为中国第一位接受过考古学专业训练的考古学家,他为中国田野考古学之科学水平的提升,尤其是田野考古方法的革新与工作制度的建设,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称为“中国科学考古第一人”。
一、 三叠层的揭示
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梁思永在安阳后冈所揭示出的仰韶、龙山和小屯殷墟文化的三叠层,是他最引人瞩目的贡献。对于这一发现的价值与意义,学界已有较多相关论述。如尹达认为,这个发现是打开中国考古学中关键问题的一把“钥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对于中国的考古学工作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夏鼐[3]认为,三叠层的发现,“第一次依据地层学上的证据,确定了仰韶和龙山两种新石器文化的先后关系以及二者与小屯殷墟文化的关系,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一个关键性问题”。安志敏[4]认为,这一发现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开始跨入成熟阶段的显著标志”。黄景略、张忠培[5]认为,这一发现“为纠正安特生提出的仰韶文化混乱概念和龙山文化早于仰韶文化的错误认识奠定了基础”,同时张忠培[6]还将这一发现作为中国考古学分期的六大标志之一。陈星灿[7]则认为,这一发现使从考古学上追踪中国文明的起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是解开中国古代文化之谜的钥匙。
简言之,三叠层的学术意义与价值,可大致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就其对中国文明起源等重要学术议题所产生的影响而言,这一建立在科学地层学基础上的考古发现,为厘清仰韶、龙山、殷墟这三种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二是从支撑三叠层这一重要考古发现背后的理论方法来看,科学地层学成为之后在中国考古学界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方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三叠层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对于梁思永揭示出三叠层的原因,除尹达等少数学者外,学界的讨论仍相对较少。考虑到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会影响到我们对梁思永的学术贡献,以及中国考古学史上相关问题的判断,因此有必要分析这一重要发现背后的原因。
对于梁思永揭示出三叠层的原因,最早由尹达[8]撰文指出,他认为这“决不是偶然的机运”,而是和梁思永“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还有“深刻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学力”是分不开的。梁思永之所以能“把后冈这样复杂错综的堆积关系找出清楚的眉目来,找到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锁钥”。主要是因为他曾经参加过“小屯村殷墟的发掘工作”,“对殷代的遗物遗迹获得了具体而深入的认识”。同时他对仰韶文化遗存亦有相当研究,曾具体分析过山西夏县西阴村的陶器,并写成了《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中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书。此外,他还是龙山遗址的发掘者和整理者,对龙山文化的遗存十分清楚。正是以殷墟、仰韶、龙山这三方面的具体认识为基础,再通过精细的发掘工作,才取得了这一划时代的重大贡献。张忠培[9]在论述科学地层学的来源时也认为,这是由于思永先生从考古实践中创立了这一考古发掘方法,考古实践才是梁思永创立这一方法的原因。
尹达是中国本土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他与梁思永共同参加了诸多的田野发掘工作,对梁思永个人以及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状况,是具备充分了解与切身体会的。张忠培则对中国考古学史与考古学理论有着深入的研究,他在一篇论述中国考古学史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考古学是从国外引进的。总之,尹达和张忠培对于梁思永的求学与工作经历,以及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状况是足够了解的。但令人稍感困惑的是,这两位考古学家都未将梁思永揭示出三叠层的原因,与他的留学经历相联系,而是归结于他所亲身参与的田野考古实践与研究。他们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判断?欲消除这一困惑,有必要对梁思永的相关经历进行综合考察。
在后冈三叠层的发现之前,梁思永在国内有过两次重要的田野发掘。最早的一次是1930 年在黑龙江昂昂溪遗址的发掘。对于这次发掘的具体情况,他在报告中写到:“文化的遗存就出自这黑沙层”,“黑沙层本身并没有分层次”,“所有的幺石器石片都是地面上的采集,因为这缘故,……我们却不能绝对地确定幺石器与墓葬的关系”[10]。这段文字至少透露了两点信息:一是他在这次发掘中,地层划分的依据是土质土色所显示的自然层;二是他已将出土物的位置信息,与其年代关系的判断联系起来。这种考古地层学的方法,与同时期国内其他考古学家所采用的地质地层学方法相比,是更为科学的。对于以上两点推论,亦可从他对李济在西阴村遗址所用发掘方法的评价中得到佐证。而他所用的理论方法,应当源自其留学时所师从的考古学家基德尔[11]。
1931 年的城子崖遗址是第二次发掘,梁思永通过解剖地层关系,详细分析了城墙的建造、废弃年代与过程。在当时而言,这不仅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发现,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次科学地层学的成功运用,使得当时史语所考古组的同仁接受了这一理念方法。从昂昂溪到城子崖,梁思永的发掘理念与方法,实际上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是在当时的考古学家群体中所产生的影响却大不相同。这说明即便是一个先进的理论方法,也需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逐步得到认可与接受,乃至进一步发展。而凭借这两次发掘,梁思永可以当之无愧被称为科学地层学在中国最早的实践者、探索者与传播者。
在城子崖发掘后不久,梁思永即发现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那么,这一重大发现究竟应该归功于哪些因素呢?这个问题恐怕只有梁先生本人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我们只能基于现有资料略作分析。梁思永在《小屯、龙山与仰韶》一文中写到:“吴金鼎先生1930年秋季在山东龙山镇城子崖发现了龙山黑陶文化的遗址。于是小屯、龙山与仰韶的问题由此而产生。……我们所得的证据就是考古学上最实在最简单的地下自然的层次”[10]151。通过以上表述可以看到,梁思永认为地层的发现是“最实在最简单”的,但三叠层的问题,却是由于城子崖的新发现而产生的。说明相较于地层上的发现,他本人更看重由城子崖这一新发现所带来的新问题。这大概是如果没有城子崖的发现在前,仅凭他对后冈遗址三个地层间关系的判断,是无法在殷墟、龙山与仰韶这三种考古学文化之间建立联系的,那么三叠层的学术价值与意义也就无从谈起。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作如下判断:如果说借助专业学习而来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可以帮助梁思永把某一单个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与清理的话,那么如梁思永所说,正是城子崖的考古新发现,才产生了在仰韶、龙山和殷墟这三个考古学文化之间建立联系的新课题。又因为梁思永在仰韶、龙山、殷墟这三个遗址,都有过田野实践或考古研究,才使得他对当时中国境内最主要的三种考古学文化,获得了相对全面的理解。
从学理上分析,梁思永留学期间所学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主要是依据欧美的考古资料归纳总结而来的。尽管在考古学的一般规律上,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建设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与参考价值。但由于二者在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地方性差异。那么对于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资料,就只能依据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在田野实践中摸索本土道路,积累本土经验。比如对于中国独具特色的土木建筑结构体系所造就的土(软)遗址,在欧美就相对缺乏直接经验可资借鉴,只能由本土考古学家自主探索。所以,如果梁思永仅凭他留学时所学到的考古学理论方法,而缺少了中国的田野考古实践这一环节,结果恐怕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三叠层的重大发现,应是以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梁思永留美期间所学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二是他在美求学时就已经开始的,对中国考古资料的持续研究;三是他回国后持续开展田野实践,所积累的本土经验;最后,其实还可以加上城子崖发掘,这一“偶然的机运”。这一点也证明,考古学是一项集体事业,极少有哪一项成就是独属于某一考古学家个人的。当然,如果缺少前面三方面的准备,也绝不可能抓住最后这个机会的。可见,幸运的基础是专业素养与持续探索,偶然的背后恰恰隐藏着必然。
二、 田野考古工作制度
田野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问,在田野考古工作中,除必要的理论方法外,还需要有一套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对日常的田野考古工作加以规范与引导,否则就难以保障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回顾中国田野考古学发展的历史,在城子崖、小屯、后冈、西北冈王陵等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梁思永逐步改进和创建了多项田野考古工作制度。这些制度不仅为当时的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指导,同时也为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后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补充、修订与完善,又逐步发展成为当今中国田野考古工作制度的一部分。
对于梁思永在田野考古工作制度建设方面的贡献,曾参加过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谈到,正是“由于他的参加,才把殷墟的考古发掘提高到应有的科学水平,才把殷墟发掘工作中存在的混乱局面澄清。……当时在考古发掘的方法上,思永先生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使中国的青年考古工作者逐渐积累了比较丰富的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经验”[8]。上述回忆,主要述及了梁思永对考古发掘方法的改进,并着重强调改进后发掘方法的科学性。所谓澄清“混乱局面”,一方面是说,梁思永所引进和发展的考古地层学,相较之前地质地层学影响下的发掘方法更科学。另一方面指的是,他对田野发掘制度的若干改革,诸如遗址发掘的作业方法,测绘坐标与方向的规定,以及考古资料的记录方法等具体细节,都进行了科学化和规范化改进。
同样参加过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夏鼐回忆到:“小屯殷墟发掘工作的头几年,参加的人都是没有受过正式的考古田野训练的。大家都在黑暗中摸索,想从尝试和错误中获取经验和教训。……自从梁先生参加工作后才加以整顿,面目一新,他费了很大力气来改进田野考古方法,拟定各种记录表格,组织室内整理工作,训练年轻的工作人员,使一切都逐渐纳入正轨”[12]。“自(梁思永)加入殷虚(墟)发掘团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的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在野外工作中,能注意新现象,发现新问题。主持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时,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遗漏细节”[3]。夏鼐的回忆,主要概括了梁思永改进田野工作制度的若干方面,如发掘、记录、整理方法,以及组织工作、人才培养等。表明当时梁思永对田野考古工作制度的改进,除发掘方法以外,还包括其他内容。
与尹达同为殷墟考古“十兄弟”的考古学家石璋如,则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将梁思永所创立的田野考古工作制度,概括为“双”“一”“象”“多”“轮”五字,即双站制、一元制、现象制、多址制、轮流制[13]。应该说,这五项制度的概括与总结全面而准确。考虑到这些制度与当下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制度,仍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下文试以这五项制度为纲,将其创立时的初衷,与时至今日的传承发展情况,逐一进行比对。以期重新认识梁思永在中国田野考古工作制度建设上的贡献,并找出相关工作制度的发展脉络,获得更加准确的信息。
所谓双站制,即在一次田野考古工作中,在田野考古工地与所在地的城镇,分别设立两个工作站。其中设在田野的工作站,地理位置靠近田野考古工作地点,但仅提供食宿功能。而设在城镇的工作站,则可在休息日,为考古工作人员提供休息、洗浴、写信等功能,作为田野工作间隙的调剂与休整之所。如此设置,可以节省工作日在路上所消耗的时间与精力,改善原先只在城镇设一个工作站的弊端,从而提升田野考古发掘的效率。
梁思永所创立的这一制度,是从当时的田野考古工作实际出发所做的调整,目的在于提升田野工作效率,同时兼顾考古工作者的休息权,可谓既创意十足,又饱含人文关怀。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活条件的改善,田野考古工作站的条件,已经普遍得到较大改善,站点的选择也更为灵活。但从我国长期以来的田野考古工作条件,尤其是广大基层考古工地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实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都基本采用了与双站制一脉相承的田野考古工作制度,并且往往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其精神内核——在提升田野考古工作效率的同时,兼顾考古工作者的基本权益,则是始终一致的。
一元制,即田野考古工地由此工地的负责人统筹指挥,主持考古发掘的全部工作。考古工地上诸如探方的布置,遗迹单位的编号,照片等数据资料与档案的管理等,皆由负责人统一安排。而且每天各个分区负责人所作工作记录的复写本,都要上交给工地负责人作统一整理。这一制度的确立,避免了各个分区由不同负责人分别负责所导致的混乱局面。
在现行的国家文物局制定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中,还可以看到这一制度的延续。如第三章“考古发掘单位和领队职责”第十条“领队职责”就有如下之规定:“考古发掘项目实行领队负责制。(一)主持制定发掘方案、文物保护预案,组织各项发掘准备工作。(二)按照考古发掘执照许可内容调整发掘方案,主持发掘工作,协调各技术系统的运作,确保各项工作严格遵守本规程……”[14]。从现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制度,对于工地负责人(领队)的要求,尽管在具体内容上有变化,但其核心要求,由领队统筹整个发掘工作,还是延续了梁思永一元制的思想。
现象制,是对考古发掘工作与发掘资料记录工作的规定。当时的发掘方法为探坑制,探坑是进行考古发掘的基本工作单位。探坑的方向,以指南针进行标示,同时坑壁要保持直立整齐。在不同深度所发现的考古现象,要分别用平面图加以记录。待探坑发掘至底部时,要绘制该探坑的地层图。另外,如果有考古现象超出探坑的范围,还要用开支坑的方法找出该现象的范围,并进行发掘。总之,考古现象是发掘与记录的核心要素。
如今,中国的田野考古学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当时的考古现象、探坑,变成了现在的遗迹单位、探方(沟),标示方向的指南针也变成了三维测绘坐标系统。但现在规定探方(沟)是考古发掘的工作单位,堆积单位是考古发掘的最小作业单位,可以看到与原有现象制诸多的相通之处。综合来看,与当时的发掘方法与资料记录方法相比,现在的制度规定,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改进,表明梁思永当时所创立的制度,仍在传承中不断发展。
多址制与轮流制是密切相关的两项规定。多址制即多个负责人同时发掘几个相互关联的遗址,以方便互相比较。这在当时既为了方便多个遗址之间进行比较,同时也是有意识尽快培养能够担当主持工作的人才。轮流制即在田野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即转入室内整理工作,待发掘报告完成后,再接着去做田野工作。这样就能实现田野不停地发掘,同时发掘报告也能连续出版。
这两项制度,在当时主要是为了在田野考古上取得更多的成果,并尽快培养更多的人才。在今天看来,这仍是非常科学合理的田野考古制度。比如多址制的背后就暗含着超越单个遗址的,更为宏大的课题意识。积极培养年轻的考古人才这一传统,也一直延续至今。至于轮流制,则对于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考古报告积压问题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除石璋如所概括的五项制度外,梁思永在城子崖发掘时还对用工制度提出了要求。根据《城子崖》发掘报告记载,在1930 年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中,梁思永倡议“每坑所需工人应减至最低限度”。“仅派两人同作一坑,一锨一镢合作;掘至深及二公尺,因坑旁积土翻运困难,乃再增一人;至三公尺后,每坑增至四人;再深即用辘轳,常增至五人;但如果再增,则不见效率之增进”。说明当时他已经发现了在不同发掘进度下,每个探坑用工人数与发掘效率之间的边际效用规律。采用新的用工方法之后,“各工队虽不甚固定,但每人有固定之工作,快慢极易比较,且有充分立足之处,可以自由活动,故效率增大”。通过上述用工制度上的调整,既取得了比之前更好的效果,又使得工人得到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这种用工方法,即便在当下,也有借鉴意义。
综上,梁思永对田野考古工作制度的改进与创制,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增强田野考古工作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主要包括发掘、测绘、记录等工作;二是保证田野考古工作的秩序性,主要体现在以一元制为代表的组织工作上;三是提升田野考古工作的效率,包括工作站的设立,发掘工作的安排,以及用工制度等;四是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保障考古工作者的基本权利,并在田野实践中培养人才。总而言之,这些制度在保证科学、严谨、专业的同时,又极富创造性,同时饱含人文关怀。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它既使“考古发掘提高到应有的科学水平”,又“使一切都逐渐纳入正轨”。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制度中的很多内容都传承至今,并逐步发展成为当今中国田野考古工作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 资料整理与发掘报告
一项完整的田野考古工作,除需要运用科学的发掘方法,进行规范的发掘作业与资料记录以外,还需要对发掘资料进行必要的整理,并最终完成发掘报告的编写与发表。如果说田野发掘与资料记录,是为了获取考古资料,那么在此基础上,对考古资料进行初步整理,并最终以发掘报告的形式,向学界与公众公开发表,则既可实现对考古发掘资料的永久保存,又可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基础研究资料。在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发展史上,梁思永在田野考古资料的整理与发掘报告的编写方面的工作,起到了道夫先路的作用。
安志敏对梁思永最早的资料整理工作——西阴村陶器的整理与研究,有如下评述:“对第四探方的1 万余片陶片进行了深入分析。由于缺乏能够复原的完整器形,乃就陶片的质地、口沿、器底和柄把的形式分类叙述,对于它们在地层中的分布、变化作了详细的统计,并用图表予以表示……是最早的一份田野考古分析报告。……整理、分类、统计以及对比研究的方法,都具有示范的作用,对后来考古报告的编写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以类型学的方法研究古代器物,在中国近代考古学著作中应属最早的代表”[15]。
除前述的西阴村陶器整理外,梁思永所做的相关工作,还包括对昂昂溪、热河、城子崖、后冈等遗址出土遗物的整理。通过对这些工作进行综合考察,本文将他的资料整理原则与方法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以出土位置(地层关系)作为断代的根本依据,这一原则体现在他所撰写的考古报告中。他曾指出:“断代根据过于偏重于制法,而制法究系推测,一直有飘渺之感。断代最可靠之形制又被忽略,总之断代离开地层是难事”[16]。第二,重视完整器,在系统整理资料之前,首先要对器物碎片进行拼对复原。第三,从质地、形制、大小、颜色、外部装饰、加工方式等方面,对器物进行分类,并挑选典型器作详细介绍。第四,运用统计方法,对器物的年代、类型、数量、组合等进行分析,并以图表的形式加以展示。这些基本原则与方法,与同时代的考古学者相比,是更为科学合理的。这些原则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后来者所继承,因此可以称得上是奠基性的工作。
资料整理工作,既是对前一阶段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又是为后一阶段的报告编写工作进行必要的准备。考古报告的重要性,就体现在无论是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还是资料整理工作,最终都需要以编写完成的考古报告呈现出来,成为整个田野考古工作的总结。对于梁思永在考古报告编写上的贡献,李济在中国第一部考古发掘报告《城子崖》的序中写到:“关于编辑的事,梁先生经历了好多困难,但他都能想法子满意的解决了。报告集的体例大部分都是梁先生创制出来的”。说明梁思永对于这部中国最早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的体例,有创制之功。
除了编辑城子崖发掘报告,梁思永还单独撰写了昂昂溪与热河的报告。此外,他的遗作《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还从方法论层面,提纲挈领地对报告的编写进行了论述。透过这些文本,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他的报告编撰思想与方法。梁思永所编辑的《城子崖》报告基本框架包括:城子崖遗址及其发掘之经过,城子崖地层之构成,建筑之遗留,陶片,陶器,石骨角蚌及金属制器,墓葬与人类、兽类、鸟类之遗骨及介类之遗殻,附录。他独立撰写的《昂昂溪史前遗址》(以下简称《昂昂溪》)报告,基本框架包括:调查的缘起及经过,东三省及附近各地的石器时代遗存,挖掘的经过,挖掘,墓葬、墓葬里的人骨架,文化遗存、石器、骨器、角器、陶器,结论,图版。《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以下简称《热河》)调查报告的基本框架包括:查不干庙,林西、陶器、石器,双井与程家营子,赤峰、赤峰北砂窝中出土遗物、赤峰东砂窝中出土遗物,补记,图版。
《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篇提纲式的文章。文中指出,考古报告并没有一定格式,报告的繁简基本上以田野材料的繁简为准。根据发表材料的多少,又可分为包括全部材料的“正式报告”与只包括重要材料的“简报”。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工作目的(如普遍性调查、抢救性发掘、有目的的调查或发掘等),工作人员,负责人,工作情形及发掘经过;二是遗址的环境(含地理位置、交通路线、地形地貌、周围景观等),遗迹(包括时代特征、构造、功用),出土物的叙述(主要是有代表性的遗物);三是总括扼要的叙述各时代主要的遗物,遗址所代表的时代及文化特征,本工作所解决的问题及所引起的问题;四是附录,其目的在于节省正文的篇幅,并保持行文的完整性,主要包括出土物登记表(列举出土位置、形状、质料、尺寸、纹饰等),墓葬登记表(列举出土位置、形状、尺寸、结构、人骨架数目与放置情形,随葬物等),专家报告书(含人骨的体质人类学报告,动物骨骼研究报告,植物遗存研究报告,陶器、金属器成分的分析报告,石器用料的岩石学鉴定等);五是图版,主要包括地图(含遗址位置图,遗址平面图,总图、分图、剖面图等);器物图、照片(器物图可表现器物的结构,照片则形象逼真,二者可相辅为用)。
通过对《城子崖》《昂昂溪》《热河》这三篇报告的框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这三篇报告皆有发掘(调查)的缘起与经过,遗址环境,遗迹现象,地层关系,出土物信息的介绍等内容,同时皆附有图表、照片、器物图等。梁思永在《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一文中,对自己的编撰思想与方法进行方法论层面的概括与总结时,也与他之前的编撰实践基本一致。这表明梁思永的编撰思想与方法,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与稳定性。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城子崖》报告的编辑过程中,除报告的体例外,他主要是在自己所负责的部分,体现了自己的编撰思想与方法,而对于其他合作者,则给予了充分的尊重。比如吴金鼎撰写的“陶片”部分;董作宾、郭宝钧撰写的“陶器”部分;附录中董作宾所作的“城子崖与龙山镇”则采用了不同的器物分类、分析方法,并在古文字、古文献、历史学的研究等方面,都体现了与梁思永的不同之处。这说明,梁思永的考古报告编撰思想与方法,在当时的影响还相对有限。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梁思永的考古报告编撰思想与方法对后世的影响,则不可谓不深远。夏鼐的《田野考古方法》一文中,对于发掘报告具体内容的认识,就与梁思永的《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基本一致,只是进一步将其概括为序论、正文、结论、附录四部分,这说明夏鼐对于梁思永的编撰思想与方法是认可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是1956 年夏鼐在中科院考古所见习员训练班授课时的讲稿,后来又被收入了《考古学基础》(科学出版社,1959 年)一书,其影响之广度,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另外,从现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相关规定来看,“发掘报告内容主要包括:遗址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既往工作;发掘工作经过和发掘方法;文化堆积与分期;遗迹与遗物;编写者的认识;有关专业技术报告等”[14]9。也可以看到,这与梁思永的总体框架仍有较高的契合度。
简言之,梁思永资料整理工作的原则与方法,为后来者提供了科学的示范与有益的启示。而他的考古报告编写实践,以及编撰思想与方法,也为之后田野考古报告的编写提供了经典的范式。尽管随着田野考古实践的持续推进,相关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各种手段方法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相关工作已较之前有所调整与优化。但如前所述,梁思永的奠基性工作与思想方法,已成为后来者进行调整、改进,乃至超越的基础。
四、 结 语
前文所述,主要是梁思永对于中国田野考古学最具基础性影响的几个方面:一是立足于本土的田野实践,进行科学地层学的实践、传播与发展,并取得三叠层这样的重要发现;二是对田野发掘制度的若干改进与创制;三是对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工作的奠基性贡献。
其实还有很多他对于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贡献,是本文所未论及的。比如他对殷墟建筑遗存的准确辨识,纠正了“殷墟淹没说”。他所主持的西北冈王陵发掘,对于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具有示范意义。从史语所考古组到中科院考古所,他既是草创时期的奠基人,又是过渡阶段的传承者与重建者,对中国考古学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田野考古工作一如既往地坚守,以及对田野考古人才的培养。在殷墟发掘的田野考古工作中,他培养和训练了以殷墟考古“十兄弟”为代表的,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考古学家。在考古所任职期间,他组织和领导了青年干部的培训工作。而他在田野工作中所体现出的那种“拼命三郎”式的奉献精神,已成为中国考古人的精神基石,激励着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风餐露宿、青灯黄卷,以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学术志向、顽强的工作作风坚守考古事业。
总之,梁思永对于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影响,是基础性与全方位的。他在田野工作与学术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创造性,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坚守田野,为考古事业奉献终身的敬业精神,则成为永远的精神丰碑,留待后人瞻仰与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