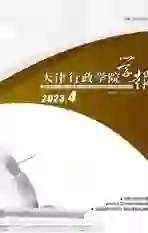论政府数据开放中公民参与权的立法完善
2023-08-04王春业曾幸婷
王春业 曾幸婷
[摘 要] 政府数据开放是数字政府构建的重要基础,其完善的制度构建与高效的数据利用离不开公民的有效参与。立法实践中公民参与权的设置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公民参与权权利范围模糊、程序性权能单薄致使实质效能受限、权利救济不足等,其原因是权利立法层面的基础逻辑不适用、权利内容不充分及救济意识与制度的缺位。政府数据开放中公民参与权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多重价值,其公民视角可为当下政府数据开放提供民主的制度引导、高效的治理路径与公正的法治价值。公民参与权的落实与发展亟待更多的立法关注,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制度应当构建公民参与充分的数据开放秩序与相应管理机制,在转变传统立法逻辑、细化公民参与的实体性原则与程序性规则及构建充分的救济制度上作出立法层面的完善。
[关键词] 政府数据开放;公民参与权;立法逻辑;权利救济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23)04-0052-12
随着学术界对政府数据开放的探索从价值意义转变到开放质量与利用上,公民参与政府数据治理的重要性得到更多關注 ① ,在世界范围的开放政府运动中,公民参与权已作为一项正式权利写入国际协议、国家宪法和具体立法中。在我国,公民参与政府数据开放是宪法赋予的公民参与权在政府数据治理中的具体体现,“以权利为核心的参与”设计是各领域公民参与实效性的重要保障 [1] ,也是政府数据利用主体抽象权益在立法层面的具体化 [2] 。从权利外在形式看,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三者常组合表达,以此构成公民参与权外在形态的应然权利体系 ② ;从权利内部结构看,公民参与权可以细化为资格准入阶段的参与资格享有权、实质利用阶段的意见表达权与获得处理反馈权,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政府数据开放的地方立法中包含了对公民参与权部分或全部权能的表述。
然而,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实践中为公民参与预留的制度空间并不充分,导致公民参与的范围、程度、作用不尽如人意。2022年《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指标体系)》指出,“各地数据开放工作更多侧重于发展数字经济的目标和面向大中型企业,而对于其促进数字社会发展的作用尚未给予同等重视”,这种功利主义倾向既造成政府数据开放“利用主体单一,利用成果数量少、质量不高”等问题,也让公民在商业场景下的信息弱势地位延续到了政府数据的行政场景,不透明的数据处理与空白的参与方式进一步削弱政府公信力。
学术理论中公民参与权利的受认可度不断升级,实践中公民对政府数据的利用率却很低,溯源立法层面,这一现状映衬出下列问题的探讨价值:一是参照立法期待,研究既有立法文本,梳理地方实践中公民参与权落实存在哪些共性问题;二是如何从立法视角审视分析在共性问题背后的原因;三是如何通过对公民参与权利的体系性诠释和整体性保护,推进其在法律实践中得到有效实现。
一、政府数据开放中公民参与权立法现状审视
近年来,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数量持续增长,从2017年至2022年五年间增长近十倍 [3] 。相较于平台开放实践的稳步推进,政府数据开放立法进程呈现“中央立法滞后、政策文件推动、地方先行先试”的特征 [4] ,其中涉及公民参与权的法律法规内容极少,在参与权权利范围划定、实质效能发挥与救济路径设置等问题上亟待立法回应。
(一)公民参与权范围模糊
公民参与权范围模糊根源在于数据开放范围的不确定,政府数据开放范围受两方面影响:“政府数据”概念划定影响整体开放范围,有限开放标准划定影响可开放范围。
1.模糊的概念划定影响公民参与权的最大行使范围。“政务数据”“政府数据”“公共数据”三者共存的情况在学术研究与立法实践中屡见不鲜。
在中国知网上分别以三种表达为关键词搜索,近半数文献使用“政府数据”,其次为“公共数据”与“政务数据”,对“政府数据”又常作扩大解释以包含其他两者 [5] 。在立法实践中,中央政策中常两两并列使用 如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与2022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分别出现了公共数据与政府数据、政务数据的并用。 ,地方层面则三者混用,政府自行选择与设定三者含义 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新发布的公共数据管理办法中规定公共数据包括政务数据和公共服务数据,《北京市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办法 (试行)》则与之相反。
从纷繁的定义表述上可以感受到政府数据概念的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仅指政府机关掌握的数据,广义的包括公共事务职能组织与公共服务运营单位拥有的数据,这两种定义间存在一定立法空白,行政机关有权决定该范围数据的开放与否。出于权利本位的固有思维与对责任承担的规避,开放机关往往最小化解释政府数据概念,实则极大限缩了公民参与权的可行使范围。
2.不明朗的开放标准影响公民参与权的实质范围。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分为“无条件开放”“有条件开放”与“禁止开放”,后两者是对公民参与权行使范围的直接限制。涉及“三密”、危害公益或第三方利益及违反法律法规为“禁止开放”标准已成共识,“有条件开放”则存在诸多立法表达。
仅有少部分地方规定了较明确的开放标准,如上海、青岛、日照等以数据安全、处理能力、时效性或持续性要求为标准设定有条件开放的数据,有些地方则以抽象表达“安全有序”为受限开放的要求 如《杭州市公共数据开放管理暂行办法》开放机制中规定“未明确开放的,应当按照安全有序的要求,列入受限开放类”。 或者在措辞表达上,选择裁量空间充沛的“可以”有条件开放而非“应当” 如《日照市公共数据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 ,更有甚者仅规定“应当优先开放”内容,回避了对开放条件的具体描述 如《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2021修正)》第20条规定了优先开放内容,全文并未提及其他开放条件。 。此类笼统的表达凸显政府在数据开放中的绝对权力地位。
3.开放数据更新的时滞性影响公民参与权的有效行使。开放部门未及时更新而将本该开放的内容划定为有限开放或禁止开放,或有些数据应当进入开放目录而未进入。对于此类情况,地方实践中主要采取定期评估更新、公众提出需求两种解决方式。政府数据属性多样、迭代速率不一,加之开放部门能动性不足,导致很多地方规定的周期性更新流于形式。我国政府数据更新可分为动态更新与静态更新 动态更新包括实时更新、每日更新、每周更新、每月更新、每季度更新,静态更新包括不更新、不定期更新、每年更新、每五年更新、每十年更新、按需更新等。 ,其中动态更新占总数的32.56% [6] 。 分析全国86个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更新频率,可以发现以年为更新周期的比例最大,实时更新仅占13.79%,且仍有11.49% 的平台没有提供数据更新频率的信息 [6] 。除了更新缓慢,缺少面向公民的统一更新频率标准也是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问题之一
如烟台市在其公共数据开放指南中规定“烟台市大数据局不定期编制并公开《烟台市公共开放数据目录清单》”。 ,不定期更新意味着即便保障了更新速度,公民参与的有效性也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二)公民參与权实质效能受限
公民参与权实质效能的保障主要依靠意见表达权与获得处理反馈权两项程序性权能的紧密结合。现行的相关规定存在三个方面问题。
1.公民的需求表达途径单一且为单向沟通模式。为实现“需求导向”的数据开放,不少地方尝试以利用主体对开放目录的异议机制收集公民需求意见,包括更新周期、内容勘误、其他需求等内容。但总体而言,当下公民对数据需求表达的途径是单一的,法规内容多为原则性表达或简单的反馈时限规定,方式多为事后且无法律效力的网页反馈提交、不定期需求问卷收集。数据需求的表达主要依靠公民的单向沟通,少有地方规定数据开放机关主动对需求进行周期性收集,这意味着公民需要准确描述需求内容并及时关注政府不定期发布的数据需求公告,才能完成一次完整的数据需求沟通。对于收集到的数据申请,数据开放机关拥有审核权,如有地方规定公民提出的申请需达到“申请频次高”的程度才可进入后续审核环节如《温州市公共数据共享开放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35条。 。
2.公民的评价反馈系统并未实现赋能数据开放服务质量的真正作用。信息服务质量的评价通常采用主观感知的方式,即由作为用户的公民所感知的实际服务水平决定 [7] 。因此,公民在参与过程中对数据服务的评价是优化政府数据开放服务功能的有力素材。然而,地方立法并未重视公民在参与过程中评价的意义,内容上未作专门规定,实践中则将数据开放机关收集公民反馈的义务转化为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自主选择开设的项目。目前仅有57.47%的平台提供用户互动交流渠道,其中以上海为代表的较成熟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提供了可用性、及时性、满意度、准确性四个维度的打分机制,也有很多平台虽提供评价渠道,评论数与评分数均为0 [6] 。可见,由于缺乏政策及立法的支持,平台用户交流渠道难以形成反馈的完整链条和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且难以发挥公民评价系统的真正作用 [8] 。
3.公民获得反馈权缺乏系统的制度支撑。对于公民发出的数据需求申请或服务评价意见,地方实践中最具体的规定仅限于数据开放机关作出答复的时限规定。时限规定确保了公民参与过程的“事事有回应”,但在立法逻辑上并不能保证“事事可解决”,开放机关所作答复的内容翔实程度、对问题的解决程度、公民获得反馈的满意程度等才是更立体的评判标准。实际的状况更为复杂,如数据开放机关并非数源机关、公民申请开放的内容需要主管部门进一步审批、申请开放的内容需要多个机关协同配合等,公民对用户端服务的反馈意见更需要技术部门的专业支持,这意味着完善的制度安排与组织统筹才能进一步保障参与公民的价值表达能够在最终的数据开放中获得考虑和采纳,这些在当下立法实践中并未体现。
(三)公民参与过程中权利救济不足
地方立法实践主要体现为公民参与过程中的两种待救济情形。一是对数据提出正当需求而未被满足的系列情形,如公民对某项数据提出申请与修正请求时,多数地方立法规定了相关责任主体作出答复的时限,少数地方规定了公民对答复有异议时可申请大数据主管部门的复核 如《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2021修正)》第21条。 。二是当相关机关不履职造成公民参与权益受损时,公民可以通过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大数据主管部门等进行投诉举报来维护自身权益 如《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2021修正)》第29条。 ,举报成功且非责任豁免情形下可责令违法违规机关限期改正,对逾期不改者通报批评或给予处分。从形式上看,这两种救济情形既可使公民在参与过程中合理的数据诉求得到反馈与复核的双重保障,也可在违法违规情形出现时以上级或外部力量约束数据开放机关。
然而,实际情况是救济制度依然缺位。一是政府数据开放立法仍呈现“轻事后”的态势。一方面,能够在立法中完整包含两种救济情形的地方少之又少。受公共服务说影响,许多地方立法并不承认公民在参与过程中对政府机关的不履职有问责的权利,仅由上级机关或主管部门进行全权监督,因而也未设置投诉举报的相关内容。另一方面,即便地方立法具备较完整的救济路径,其制度细节上仍待推敲:如平台反馈、投诉举报均不具备明确的法律效力,数据开放部门与数据提供部门的混用会加剧实际追责的困难,仅针对正确性而非合法性的复核并不能在法律层面保障公民参与权的有效救济等。
二是立法中并未给公民在参与过程中遭遇的不平等对待预设救济路径。现阶段的治理强调价值的实现而忽视公平利用问题,直接表现为政府数据利用主体主要集中在具有技术和资金优势的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等 [9] ,“平等”似乎成为公民参与面临的最大挑战:政府以营利为目的设定主体资格限制 如《福建省政务数据管理办法》第32条。 或者政府直接参与收益分配与盈利,导致竞标模式下只有专业性强且资金雄厚的企业主体获得数据;在少数授权或独家授权的情况下,被授权的主体可能不当提高数据产品的定价,侵害公民作为消费者的权益;将公民与企业置于形式公平的竞争环境下,本身就是实质公平的失衡。当公民遭遇此类规则设置的不平等时,往往无法诉诸有效的救济渠道。
二、政府数据开放中公民参与权立法不足的症结诊断
科学完备的法律是权利得到有效保护的重要前提,在立法层面存在的问题势必辐射到法律实施的诸多环节。政府数据开放中公民参与权存在的问题应从立法层面进行源头审视,在立法底层逻辑、权利内容设置与救济制度构建上进行深入分析。
(一)立法逻辑的错位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地方立法逻辑主要有法定义务说与国有财产说 [10] ,两者都未考虑政府数据开放中公民参与的特殊性与必要性,在理论逻辑中缺乏公民视角。
1.政务公开与政府数据开放的重叠:限缩公民参与的权利基础。在立法逻辑上,政府数据开放的制度设计很大程度沿袭政务公开制度的法定义务说。虽然学界对政务公开与政府数据开放采用相同制度进路有反对之声 [11] ,但出于节约立法成本与保持行政审慎姿态的目的,立法实践中常刻意模糊两种制度的边界。在立法内容上,有地方政府直接规定数据开放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 山东省、浙江省、合肥市、佛山市、中山市、贵港市、南京市、济南市、台州市、湖州市的相关立法均有此类规定。 ,违法性认定中也有地方立法参照政务公开保留了行政机关不予处理的相关权利 山东省、济南市、中山市的相关立法均有此类规定。
。
在法定义务说下,政府数据开放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对政府的监督权为基础,属于行政机关对公众负责的单向法定义务,实践中常出现行政机关反客为主的情况。一是公民虽然在制度形式上具有积极地位,但事实上只能在政府履行义务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在立法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行政机关身兼运动员与裁判员身份,以传统裁量权与新型算法技术手段把控合法合规界限,使公民陷于不利处境。二是知情并不是公民在数据时代的最终诉求。以外部知情权、监督权制约公权力效力有限,制约公权力、提高政府透明度也不是政府开放数据的唯一目的,挖掘数据经济价值、重塑互联网时代民主路径、共建共享数字政府治理才是公民参与政府数据开放的初衷所在,这些权益诉求远超知情权与监督权的范围,暴露了以政务公开路径发展政府数据开放的局限性。三是以权利保障为基础的制度,逻辑上会因权利行使不充分而影响制度效力,即公民是否有意愿、有能力行使知情权影响政府数据开放的成效,这一逻辑转移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治理责任,也超出我国公民的数据治理参与能力,不能真正实现政府数据开放制度保护公民自由与权利的立法预期。
2.数据权属国有化的排他性:消解公民参与数据收益的初次分配。国有财产说提出将数据资源视为有价值的国有资产,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调配,提高其利用效率,促进社会总体福祉的增加。国有财产说以易于操作、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特征受不少地方政府青睐。即便中央立法对数据权属的归处进行了刻意留白、在数据产权制度中淡化了数据所有权概念,地方实践中仍出现了将政府数据定性为国有资源的立法表达 福建省、山西省、深圳市相关立法均有此类规定。 ,或即便没有明文规定,也在执行中肯定了这一逻辑 最典型的是依申请开放中的限制条款,政府的变相主导权巩固了对政府数据的垄断优势。 。
从公民视角看,国有财产说的成立需要审视其合法性。一是基于所有权的特性,该学说的合法性要建立在政府数据中公民个人权属的完全排除上,这一点可由两种思路进行否定。第一种思路是将政府数据类比普通国有资产,政府处理个人信息进而生成有价值的数据集合的行为不能等同于政府投入资金开发天然滩涂的行为,因为数据是公民个人行为“留痕”产生的,加工数据获得的劳动成果达不到绝对财产权的高度。并且,承认国有财产说等于间接承认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企业获得数据所有权,这个推论有悖于过往的司法审判,也易造成数据的垄断。第二种思路是基于个人信息的双重属性主张公民权益,个人信息具有财产属性与人格属性是学界共识,匿名化处理只能剔除其人格属性,剩下的个人财产属性被数据所继承,因此,政府很难将政府数据视为纯粹的国有财产。
二是政府数据国有化能否对抗个人数据中的隐私权是存疑的。当前政府采取的做法是在数据处理中用“个人信息与数据的二分”限制数据源头端公民的权利,回避隐私权与信息权的侵权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对个人信息与数据定义的核心差异在于个人信息可识别而数据不可识别 [12](P55) ,政府通过技术手段达到个人信息匿名化,意味着政府内部个人信息的保护终端仍是技术规制而非法律规制 [13] ,
然而,匿名化处理本身仍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匿名化处理的标准制定、再识别的风险规避及技术上的可操作性等。事实上,政府通过匿名化处理不能排除公民隐私泄露的绝对风险,却绝对排除了公民参与数据处理过程的权利基础。
(二)权利内容的不足
立法逻辑中政府对公民地位的有意弱化使其在立法内容中回避了对公民参与权权利内容的细化。一方面,当前立法缺少对公民参与权权利内容的规范化、体系化表达,直接导致公民参与权权利范围模糊、需求表达与整体评价渠道不通畅、有效反馈的获得无保障等问题;另一方面,与公民参与权权利内容的不足同时出现的是公权力的过度膨胀,在实践中则表现为数据开放机关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无须承擔明确的法律责任,也无直接动力保障公民参与权的实质效能,导致公民参与过程屡屡碰壁。
未被细化的权利往往由数据开放机关的公权力所替代,加剧了政府控制数据的权力与公民参与权利的失衡。事实上,这种失衡贯穿数据开放全过程,如在个人信息收集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如果出现“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可以“不需取得个人同意”就处理个人信息,换句话说,政府在收集信息时可以以“有权采集”来跳过公民的“知情-同意”。此处“有权”包括主体有权与依据有权,两者应当同时存在 [14] 。然而,鉴于公权力的扩张性和强势传统,现实中政府数据采集对“有权”存在选择性执行问题,出现许多超越权限甚至是无权的采集行为,采集端的违规违法采集屡见不鲜 如公共机构要求采集辖区进出人员婚姻登记数据,地方高校广泛采集师生指纹、人脸等生物识别数据进行考勤管理等都是富有争议的公共信息收集。 。公民在信息收集阶段不仅没有参与的话语权,甚至常陷于被动收集、强制收集、重复收集的处境。
公权力膨胀在数据开放阶段最主要的形式为政府对标准设定的裁量权。在现实场景下公民要获得政府开放的某项数据,至少要经过政府的两次审视:该数据是否涉密或敏感;该数据是否出现在开放目录中 [15] 。政府在这两次审视中都拥有不小的裁量空间,公民仅拥有无具体内容的“被听取意见”权。具体来看,政府在数据开放中的裁量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划定涉密或敏感信息的裁量权。涉密和敏感的数据不予开放是共识,此类数据经依法匿名化、去标识化等脱敏、脱密处理或经相关权利人同意后也可以成为普通数据。实践中政府能够自主决定是否对涉密或敏感信息进行技术脱密、脱敏处理,对处理标准具有制定权,最终完成处理的数据也由政府决定开放与否。这意味着一旦信息初始涉密或敏感,无论后续经过如何安全处理或随时间变化不再涉密或敏感,政府仍对其流通拥有绝对控制权。这类数据并不在少数,包含就业、市场、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行业,这些与公民息息相关的数据因政府的绝对控制而无法接纳公民的参与。二是开放目录制度的裁量权。目录制度是政府数据开放的重要制度载体,是保障数据服务灵活性与效率的管理机制,通过目录的查询,公民可以快速、实时、动态知晓可使用的数据。然而,在公民参与权落实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仍拘泥于政务公开的法定义务说模型,忽视公民对政府开放数据获取和利用的权利义务关系 [16] 。目录制定权限的分散,更进一步赋予地方政府较大的裁量空间,并且只提供公民在目录范围内的数据选择权,数据能否进入开放目录则由政府决定。这意味着即便内容并不涉密或敏感,政府仍可以自主决定开放内容,打造强势的“卖方市场”。
(三)救济制度的缺位
公民参与权两条救济路径的不完善与平等参与保障的不充分暴露了既有立法中救济制度的缺位,这一点与学界关于政府数据开放公共服务说相呼应。公共服务说是指政府开放数据的行为是在为社会提供一种公共服务,是从权利保障机制这一传统行政法治建构轨道逐渐转向寻求更优数字治理效果的另一种功能主义建构思路 [17] 。但这一建构思路冲击了公民参与权救济的权利基础,大幅限缩了其制度构建的财政支持,甚至未达到该学说预期的公益服务效果。
1.公共服务说限制了公民诉权。将政府开放数据定位为提供不特定的社会公共服务,意味着政府不开放某项数据造成的损害也没有特定性,公民在开放过程中得到的利益是不可诉的反射利益而非主观利益,基于此,政府不予开放数据的行为不具有可诉性 [18] ,公民也失去法律所能提供的最有力的救济途径。政务公开制度中规定了公民可以通过复议、诉讼等救济途径寻求救济,而政府数据开放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中仅规定了社会主体的监督机制及内部申诉机制。制定机关依程序作出一定处理,但不受其他国家机关的外力约束,这种模式显然不具有强制性,其制约效力可想而知。
2.公共服务说伴随沉重的行政成本与激增的责任风险,进一步压缩救济制度构建的可能性。公共服务首先应当是无偿且安全的,加之政府数据的开放建立在大量行政资源消耗之上,不仅需要培训职工、购买技术和升级网络基础设施,还需要外部计算机和设计团队的技术服务支持 [19] 。因此,作为一项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地方财政能力是政府开放数据价值生成的核心环节 [20]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中央立法迟缓,具体实践以地方政府为主力,财力、人力都是欠缺的,导致不少地方政府在为公众赋能与发挥商业价值间选择了后者。同时,将政府数据开放视为公共服务,政府不仅要保证被开放数据的实时动态更新,还要承担数据开放之后可能带来的诸如“马赛克效应”等政治、法律和社会风险。在公共服务说下,政府开放数据范围愈广则财政成本愈高,开放程度愈深则安全风险愈大,对公民参与权救济制度的构建更加有心无力。
3.公共服务说并未带给公民参与政府数据开放预期的话语权。公共服务说认为政府要以更积极的方式去追求公共利益与行政效率,使公民权利的空间不再限缩于指定的权利范围。相较于法定义务说,公民从被动的权利捍卫者转变为积极的服务消费者,参与过程更侧重于共享数据本身的经济与社会价值。然而,公共服务说与法定义务说一样缺少为普通公民发掘数据经济效益的直接动力,即便借助“服务消费者”这样市场化的概念,政府主导提供的也极有可能是“卖方市场”,打造的公共服务也有既定的、专业性要求更高的“受众”。事实上,消费者在数字经济环境下本身不是强势角色,公共服务说并不能为公民带来预期的话语权,对其权利保障也无更多支持。
三、加强政府数据开放中公民参与权立法的价值分析
公民参与的正当性是法律条文、政策文件与学术讨论的通识。政府大数据治理中公众参与权的事实基础在于公民在大数据治理中的角色不仅是数据的来源端,也是数据的使用端,公民参与是政府数据再利用的重要环节;公民参与权的法理基础是由于政府数据是政府以财政支出为代价取得的资源,纳税人支付了数据挖掘与数据处理的成本,作为纳税人的公民是这些数据真正的所有权人 [21] 。结合这两种论证,公民应当享有对政府信息的知情、参与及监督的權利。
然而,逻辑论证的正当性并不能成为落实公民参与权的直接动力,政府数据开放不仅是对已有数据进行工具化的技术附加,形成数字技术层面的开放,更是在数字法治政府下对政府理念、机构、职能、流程再造的法治化进程,公民参与背后的民主意义、公平价值与社会影响应当受到更高关注,即进一步考察政府数据开放中公民参与权利的积极作用与独特价值,通过深化对公民参与意义的认知,形成推动公民参与权立法进程的根本动力。
(一)政治价值:消弭法律授权明确性弱化造成的正当性危机
科技的发展与行政任务的专业性、复杂性激增冲击了代议制民主框架下行政的“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滞后的立法因难以穷尽行政权的活动边界和具体情形而选择抽象笼统的目的式条文表达,赋予行政机关宽泛的技术性、政策性和程序性裁量权限,“法无授权不可为”的传统行政理念受到冲击,法律授权的明确性逐渐弱化。在这种背景下,应当确立公民参与权以强化现代行政的正当性。
民主性是数字政府建设的根本属性,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基于政府行动透明、公民政治参与及政府与公民之间协作的民主进程的创新。事实上,“用之于民”一直是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2015年,《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指出,数据发展的总体目标是“构建以人为本、惠及全民的民生服务新体系”,要“利用大数据洞察民生需求”,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 [22] ;2016年,《公共信息资源开放试点工作方案》强调“坚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做起”,进一步促进“信息惠民”;
2022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数字政府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数据治理的成果要“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法律法规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相继出台,构成政府数据治理一体化管理制度的重要部分,强调了信息时代公众的合法权益及国家机关在信息数据处理活动中应尽的安全监管职责。在数字政府建设的民主基调下,政府数据治理以公平惠民为目标,具体实践“以公民需求为导向,以保护公民隐私权、合法信息权益为底线”;学术界也逐渐认识到公民是数据消费者及权益待保护的弱势者,保障普通公民获取政府数据的权利是政府数据开放的民主基石。
民主性不仅是法治层面的要求,也是政府数据治理实践的现实问题。政府数据是指政府产生、收集和拥有的数据,这些数据来自政府机关依法行政的工作日常、第三方依法提供的资源及职权之外依法生成的数据库等,是基于用户行为、用户内容、用户数据生成的,最原始来源仍是公民。在政府数据的开放过程中应当回答这些问题:在政府数据必然包括个人数据的情况下,公民可以免费获取哪些基本数据服务?政府数据资源的内容提供者的正当权益应当如何保障?
(二)经济价值:提升政府数据开放利用的精准度与效率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对其开发利用应当是政府数据开放制度的优先目标。单纯地批判政府数据开放中政府机关对企业的偏爱是片面的,回避对公民参与的实质价值的追问,也无益于改善行政机关在鼓励公民参与问题上的三无态度——无动力、无意向、无效率,应当看到公民在挖掘政府数据经济价值层面的独特贡献与潜力。
1.公民参与有利于提升政府数据开放的精准度。目前市场和社会对开放数据的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存在开放数据数量不多、容量低、颗粒度粗、质量不高等问题,实时动态、高颗粒度、高容量数据集的开放极少。这种现状一方面是政府机关在技术与人力物力上的不足导致,另一方面是由于供给与需求的不吻合。政府数据开放既需要充分了解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也需要依赖众多利益相关者实现对数据的价值挖掘与有效利用。公民是政府数据开放中最广泛的参与者,既基于规模产生的价值潜力巨大,又能在制度设计上带来工具性的好处,即利用公民的经验和知识来满足公民最紧迫的需求 [23] 。但当下无论从公民在信息时代的角色定位、权利基础,还是行政视角下政府数据治理的发展特性来看,都未能实质性地达到公民角色的预期定位。正确看待公民在政府数据治理开端的价值与信息权属,才能将公民真正纳入数据红利共创共谋的大局,摆脱数据治理功利主义倾向;也只有将数据背后公民的鲜活个性与多样需求纳入政府数据的治理,才能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高效利用与精准转化,提升公民在正式政治参与、合作规划和预算编制、作为公共产品消费者的市场参与三种参与机制下的能力 [24] 。
2.公民本身是兼具创造力与生产力的数据利用主体。国内外学者通过不同范围的社会调查证明公民参与程度能够影响政府数据的治理成效,即便是敏感的隐私保护领域,公民参与共治也有利于防范政府开放数据伴随的风险,提升政府服务功能 [25] 。一方面,完善的公民参与机制能让公民通过分析政府开放的数据,提高其监督政府管理、有效表达意愿的能力,防止政府按照自己的偏好恣意行事;另一方面,适当的政府激励与官方平台能够促进公民参与政府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各国均有不少成功案例,如丹麦开放的公共设施数据被用于开发公共厕所显示网站;
韩国某网站将国民养老金数据中的公司信息可视化,提供公司年薪、人数、劳动力等数据,便于求职者了解就业信息;我国公民个人开发上线的以“为公众提供住房周边危险源的查询服务”为宗旨的“危险地图”等。部分城市举办的面向个人的鼓励政府数据利用的作品大赛中也成果非凡,如深圳开放数据应用创新大赛中呈现不少有价值的个人作品。
(三)社会价值:缓解信息化时代的社会群体性焦虑
伴随着现代行政高度专业性、技术不确定性、决策信息不对称性及价值结构多元性加剧,信息的透明度越来越低,公民在商业场景下对算法歧视、算法垄断、算法黑箱的警惕与抵触,随着政府数据运营者身份的确立,衍生到政府数据开放的场景之中。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越过知情同意获得保障公益所必需的相关数据,政府收集与积累的数据更加庞大,激发了公民对信息权益的自我保护与对政治生活参与的强烈欲望,当公民参与欲望的强烈与参与制度的不完善产生矛盾时,就会造成舆论的规模升级与非制度化的公民参与。这种非制度化的公民参与具有参与动机多元、行为过程非理性及参与后果消极的特征 [26] ,加之对数据开放风险的非自愿承担性与自身合法权益的受损,极易驱使公民在恐惧心理支配下发起群体性事件。
在制度层面正确设置公民参与权是政府数据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抓手。政府对数据实施的一系列处理行为是有权机关行使公权力行为,政府对数据的收集、转换、存储、开放等过程兼具裁量权与主导支配地位,就此而言,政府数据治理属于行政法规范的范畴 [27] ,应当遵循行政控权理念与其他一般原则。在政府数据开放过程中巩固公民参与地位有利于推动法治进程。一是强化行政机关在平台机制下的公共属性和职能,为企业私权力发展划定合法合理范围。公平原则是行政基本原则,即为达到结果的公平,相同情况作出相同安排,不同情况下应当作出有差别的安排。政府打造数据共享平台,为公民与企业提供形式相同的参与通道。在数据活动中,公民与企业在资金、技术、数据资源上存在巨大差别,法律的平等地位反而造成实质的失衡局面,过分强化企业大平台私权力,使公民权利受到限缩是当下我国数据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二是开放透明的政府数据治理有利于保护公民在信息时代的各项权利。当下政府对数据进行全流程、闭环的、无接触的管理,公民知情有限,监督边缘化,出现侵权时申辩无力、救济不畅,为数字官僚主义、数据独裁、数据垄断留下诸多法治隐患 [28] 。政府数据治理的封闭性是造成公民产生权利焦虑的重要制度性原因,保障公民的参与机会有利于降低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民生的决定在后續阶段的落实难度。
四、政府数据开放中公民参与权立法完善的路径指向
大数据时代下公民参与权的政治、经济、社会三重意义催生了权利保障立法的强烈动力,结合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实践中公民参与权现状背后的基础逻辑不适用、权利内容不充分、救济制度长期缺位等问题,应当在转变立法逻辑、细化权利实现内容及构建充分的救济制度上作出立法层面的完善。
(一)转变立法逻辑
政务公开的权利保障模式无法满足数字时代公民全面发展的需求,传统的国有自然资源排他授权开发途径更是一刀切式地排除公民的应然权益,这两种在既有法律制度上衍生的政府数据开放理论逻辑在立法之初就显露对公民参与的重视不足。应当在后续的立法逻辑探究中进行改变。一是拓宽公民参与的权利基础,从知情权、监督权到公共数据权与数字发展权,公民享有向行政主体请求开放政府数据资源以平等获取和使用的权利 [29] ,也应当享有数字时代基于人权平等发展的机会权利。二是明确政府数据权益分配中的公民参与,即便基于数据价值理论,公民并未参与数据的生成与处理环节,个人信息在处理中转变为不受公民个人所控的数据,数据仍以人为记录对象,以人为最终主题,公民也以人的集体身份保有参与政府数据开放的合法地位。
坚持公民参与不仅是制度层面的完善,更应是政府数据开放的底层逻辑,即数据资源应当由人民共享,政府肩负推动数据价值实现的社会责任。基于此,有两种逻辑模型值得借鉴。一种是数据信托语境中的政府数据开放模型。全体公民作为公共数据的“真正所有人”即信托人享有使用和获得信托财产增值利益的权利,政府仅为公共数据的“形式所有人”即受托人,为了公共利益而负有控制、管理和保护作为公共信托资源的公共数据的职责和义务 [30] 。这种理论视角给予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公民发展的权利保障,也重新定位了政府在数据开放中的双重角色:既保护管理信托客体——政府数据,也效力于信托人——公民。另一种是基于公平利用权构建政府数据开放模型。与权力导向或利益导向的制度设计不同,公平利用权概念下的政府数据开放注重利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致力于形成利用主体与开放主体间相互促进又相互约束的互动结构 [31] 。这一模型的优势在于在政府数据开放制度建设初期就着重从数据“开放—利用”维度完善相应规范体系,而无需对政府数据权属进行仓促规定。在利用为重心的制度构建下既能保障政府数据利用主体的权益与理性预期,也可约束与指引开放机关的行为,从而在双重意义上提升制度理性,充分释放该项制度实践的经济和社会效用 [32] 。
法定义务说与国有财产说在实践中仍有各自优势, 如更强的操作性与更好的适应性等,应当在调适的基础上逐渐结合新的理论模型,才能确立起与政府数据开放利用完全匹配的指导思想。
(二)细化权利内容
政府数据开放并非一个价值无涉的封闭过程,尤其在中央立法滞后、地方实践先行的情况下,必然带来多元的价值碰撞与行政偏好,压缩公民参与的制度空间。立法中零散笼统的表达更为公民参与权的落实增加了难度,也易让政府数据开放的相关规范被片面划定为政府裁量范围,加剧公权力的膨胀。因此,对公民参与权权利内容作明确和体系化的规定是立法完善的关键之举,权利细化应当兼具实体性原则与程序性规则两方面。
1.在立法原则层面强调公民参与的法律地位。一是在立法目的上可以增设诸如“保护公民参与政府数据开放合法权益”的表达,增强政府数据开放立法的权利保障属性,为公民参与权各项权能的细化落实提供总领性依据,强调政府数据开放中的公民视角,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民主进程。二是在利用主体上强调公民与企业组织的平等性,将如“保护社会各主体公平利用政府数据的权利”的表达设为必要内容,使其出现在地方政府数据开放立法的总则部分,强调政府数据开放的公平性,既为公民的平等参与提供指引与保障,也为公民未能平等参与政府数据开放情境中的事后救济提供法条依据。三是在立法中體现权利与权力制衡互动的原则,防范行政机关的过度裁量权。政府数据开放中的公民参与权应当与公权力交互制衡,约束行政机关在其法定开放职责内的乱作为或不作为行为,避免对公民利用政府数据的公平环境与合理预期造成破坏,从而真正促进政府数据开放制度的理性化、规范化运作。
2.在具体规则上增设公民参与权内容的专门规定。一是明确政府机关定期收集公民数据需求、评价反馈的职责。以需求为导向的政府数据开放应当配备常态化、周期性的需求收集机制与评价反馈机制。二是细化开放机关作出反馈的流程标准。就权利性质而言,获得处理反馈权是指公民享有要求行政机关对其所提出的意见与建议给予合理处置及反馈答复的程序请求权,蕴含四重规范内涵:公民有权知悉其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政府数据开放过程中如何被处理;公民所提意见和建议应当获得必要程度的尊重;公民提出的合理意见应当被行政决定所采纳;公民有权要求行政机关公开说明相关意见和建议不被采纳的理由。因此,除了反馈时限,更应规定数据开放机关所作答复的内容翔实程度、对问题的解决程度、对合理意见的采纳程度、对不采纳部分的解释标准、公民获得反馈的满意程度等以促成公民与政府良性互动 [33] 。三是保障公民参与政府数据开放的标准制定环节。如政府数据开放目录确定过程中,应当确保公民有能力一定程度影响目录内容,依照公民实际需求开放相关数据;制定脱密、脱敏数据的按期开放制度,经过安全处理的数据依法有序开放,以程序性制度规制政府裁量权界限。
(三)构建权利救济制度
虽然公共服务说限制了公民对政府不予开放数据行为的诉权,但可在立法层面构建公民参与权救济的其他路径。
1.通过行政复议实现权利救济。相较于既有制度中的复核,行政复议跳出了行政机关自行设定的规则而对规则本身的合法性进行基础性审查,能够进一步保障公民平等参与政府的数据开放。不可诉不等于无救济,也不意味着完全排除行政复议的可能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采用权益救济功能说,逻辑上可复议性的范围应大于可诉讼的范围。在行政复议范围规定中也包含兜底性条款——“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最新修订草案中也增加了“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申请复议这一新情形,这是政府数据开放可复议性的有益信号。
2.完善内部申诉机制实现权利救济。我国部分地方立法中已有内部申诉机制的雏形,如通过数据开放平台对有误数据提出异议,对侵犯个人隐私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提出申诉等,但在申诉主体、申诉范围、申诉流程与申诉反馈上暂无统一规定,可以在立法上对此进一步完善。同时可借鉴域外经验,设置专门的督察机构接受并处理公民对政府数据管理机构的投诉,并在公民与管理机构之间进行调解,以确保公民的相关权利得到尊重 [34] 。权利救济制度的构建还应当解决救济成本问题,即解决公共服务说下政府数据开放的行政成本问题。一方面,应当重视数据利用的效能,盘活政府数据开放制度的经济效益循环 [35] ;另一方面,允许政府在开放数据时收取适当费用以弥补边际成本,如对商用价值较高的数据,可以纳入有偿开放的范畴 [36] 。
五、结 语
数据积累和技术运用带来了不平等的权利关系,普通公民在数字时代商业场景下常处于数据鸿沟的弱势地位,这种局势很难不随着政府数据的开放而衍生到行政场景中。因此,保障公民的积极参与应当成为政府数据开放制度构建的重中之重,这是制度完善的诉求、政府公共属性的应然职责,也是大数据时代对公正、民主的重要价值关切。受既有立法实践的影响,政府数据开放制度中存在立法逻辑错位、权利内容不充分、救济制度长期缺位等问题,需要政府结合社会变革在立法逻辑上改变传统观念,在权利内容上进一步完善政府数据开放中公民参与权的实体性原则与程序性规则构建,在救济制度上开辟行政复议渠道、完善内部申诉机制、解决救济制度的立法成本问题。
政府数据开放应当考虑国家权力作用和利益刺激等因素,制度运行初期为推动数据的阶段化高效开放与利用,在规则设计中引入权力导向与利益导向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当下的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治理中存在一定的功利主义倾向。但如果该项制度过分倚重权力和利益而展开,忽视公民个体在其中的合法权益与潜在作用,则会偏离数字法治建设中民主公平的初心,与大数据时代对算法正义的追求背道而驰。公民在政府数据开放中的参与程度是公民在数字法治共建共享共治实践中扮演何种角色的直接体现,是人本原则下数字公民身份转变的显性指标。正是基于此种意义,法治建设中我们更应当重视政府数据开放制度的公民视角,致力于在立法层面完善公民参与权的制度细节,既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也以此约束、指引行政机关在政府数据开放中的裁量权,以权利制约权力,提升制度理性,充分释放数据的经济和社会效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法治建设。
参考文献:
[1] 朱兵强,白家亮.影响公众参与环保实效性的制约因素及建议[J].环境保护,2021,(11).
[2]吕富生.论私人的政府数据使用权[J].财经法学,2019,(6).
[3]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城市指数(2022年度)[R/OL].[2023-06-20].http://ifopendata.fudan.edu.cn/report.
[4]武亚飞.大数据时代公共数据开放立法研究[J].科技与法律,2022,(6).
[5]刘 权.政府数据开放的立法路径[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
[6]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湖北省数据治理与智能决策研究中心.中国政府开放数据利用研究报告(2022)[R/OL].[2023-05-12].http:
∥imd.ccnu.edu.cn/info/1046/12620.htm.
[7]王 琳,杨 莹,邱均平.基于公众感知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信息服务质量評价体系研究[J].情报科学,2022,(11).
[8]瞿忠琼,鹿艺鸣.探寻公众感知的本质与迭代逻辑[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4).
[9]高秦伟.数字政府背景下行政法治的发展及其课题[J].东方法学,2022,(2).
[10] 黄贤达,高绍林.论我国公共数据开放的双重路径与规范重塑[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
[11]宋 烁.政府数据开放宜采取不同于信息公开的立法进路[J].法学,2021,(1).
[12]马长山.数字法治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2.
[13]程 啸.论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权利[J].中国社会科学,2018,(3).
[14]王真平,彭箫剑.政府数据采集的法治路径[J].图书馆,2021,(12).
[15]孙丽岩.政府数据开放范围裁量权的法律控制[J].法学家,2022,(5).
[16]朱 峥.政府数据开放目录制度的问题及其应对之策[J].情报杂志,2021,(12).
[17]王万华.论政府数据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关系[J].财经法学,2020,(1).
[18]邢会强.政府数据开放的法律责任与救济机制[J].行政法学研究,2021,(4).
[19]黄先海,虞柳明,戴 岭.政府数据开放与创新驱动:内涵、机制及实践路径[J].东南学术,2023,(2).
[20]宋迎法,嵇江夏.政府应急管理中开放数据的价值生成模型研究——基于31个省级卫生健康部门网站的定性比较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3).
[21]付宇程.政务大数据治理中公民权利保护的国际经验[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22]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EB/OL].[2023-04-25].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05/content_10137.htm
[23]OECD.Open Government: The Global Context and the Way Forward[R/OL].[2023-06-01].https:∥doi.org/10.1787/9789264268104-en.
[24]Davies T.Open Data,Democracy and Public Sector Reform:A look at Open Government Data Use From data. gov.uk.[D].Oxford:University of Oxford,2010.
[25]袁 靜,刘晓媛,臧国全.用户参与共治:政府开放数据隐私风险治理的新思路[J].图书情报知识,2022,(6).
[26]王洛忠,阚 萍.政府决策过程中非制度化参与:现实挑战与治理对策[J].新视野,2014,(2).
[27]李 涛.政府数据开放与公共数据治理:立法范畴、问题辨识和法治路径[J].法学论坛,2022,(5).
[28]何 渊.政府数据开放的整体法律框架[J].行政法学研究,2017,(6).
[29]朱 峥.政府数据开放的权利基础及其制度构建[J].电子政务,2020,(10).
[30]冯 果,薛亦飒.从“权利规范模式”走向“行为控制模式”的数据信托——数据主体权利保护机制构建的另一种思路[J].法学评论,2020,(3).
[31]丁晓东.数据公平利用的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J].法学研究,2022,(2).
[32]王锡锌,黄智杰.公平利用权:公共数据开放制度建构的权利基础[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2).
[33]袁 莉,李 霞.开放政府数据用户参与过程重构——情境、鸿沟与使用[J].现代情报,2023,(6).
[34]OECD.The Role of Ombudsman Institutions in Open Government[R/OL].[2023-06-01].https:∥www.oecd.org/gov/the-role-of-ombudsman-institutions-in-open-government.htm.
[35]陈 美,郝志豪,曹语嫣.我国地方政府开放数据制度评价与运行效果研究[J/OL].[2023-06-27].图书情报工作,https:∥doi.org/10.13266/j.issn.0252-3116.2023.08.002.
[36]尹博文.政府数据有偿开放理论的法治建构[J].新疆社会科学,2023,(1).
责任编辑:陈文杰
On the Legislative Perfection of the Right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Open Government Data
Wang Chunye, Zeng Xingting
Abstract:
Open government data is a cruci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government, and its perfect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efficient data utilizatio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effective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establishing the right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legislation, such as the vague scope of the right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limited substantive efficiency caused by thin procedural power, the lack of right relief, and so on.The reasons for these problems are the in-applicability of basic logic at the legislative level of rights, insufficient rights content, and a lack of relief consciousness and system. The right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open government data have multiple values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its citizen perspective can provide a democratic institutional guidance, an efficient governance path, and a fair rule of law value for current open government data. As a result, more legislative attention is required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ight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Chinas open government data system should build an open data order and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mechanism with full citizen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improve it at the legislative level by changing traditional legislative logic, refining substantive principles and procedural rule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constructing an adequate relief system.
Key words:
open government data, the right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legislative logic, right reli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