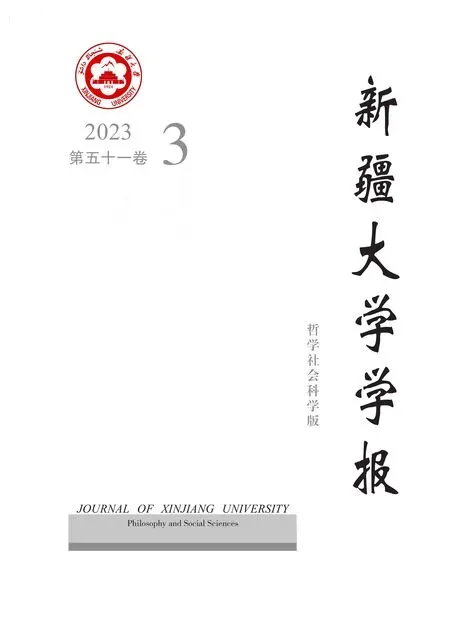“样子”的助词化及其句法语义效应*
2023-08-03白雪飞
白雪飞,赵 彧
(1.上海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200234;2.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中文教育学院,上海 201620)
一、引 言
先看一组例子:
(1)他拿针的样子倒很灵巧。(戴厚英《流泪的淮河》)
(2)天色阴暗,乌云低垂,仿佛又要下雪的样子。(魏巍《东方》)
例(1)“样子”是名词,有词汇意义,不能删除,“拿针的样子”是定中关系,例(2)“样子”相较前者,意义相对抽象,可以删除,“仿佛又要下雪的样子”很难分析为定中关系。再如:
(3)六路车早班的最后一趟还没回来——还要等半个钟头的样子。(阿累《一面》)
(4)剩余的放在冰箱保存,吃个三天样子都可以。(《炒个什锦菜过年吧!》《扬子晚报》2016-02-12)
划线部分可以抽象为“数量结构+(的)样子”,表示的都是说话人的推测,为什么附上“样子”后就可以表示推测?另外,张谊生指出近代汉语中存在着诸如“样、状、相、态、貌、势”等一批用来描摹对象的某些典型形状、表情、外貌等外在特征的词,它们在现代汉语中大致有两种发展趋势:其一可以后附在词、短语或小句后发展为摹状助词,①参见张谊生《当代汉语摹状格式探微》,《语言科学》,2008年第2期,第156页。其二经过双音化保留在现代汉语中,可以称之为摹状名词,如“样子、架势、趋势、形势、情况、状况”等。洪波指出“具有相同语义内容的语言单位受到相同的句法语义因素的影响,会发生方向相同的虚化”[1],即所谓的“平行虚化”,而摹状名词除了本身的语义差异(有的语义还比较实在,有的有自己的语域)外,语法化的程度也不尽相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语法化层级,这其中“样子”的语法化程度最高,句法语义以及语用功能都得到扩展,而有的词意义还比较具体,没有创新用法。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先分析“样子”的助词化过程,再研究助词“样子”的语用功能,最后分析摹状名词的语法化程度及其带来的句法语义效应。
语料取自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BCC 现代汉语语料库以及网络报刊等,均标明出处。
二、“样子”的助词化
(一)叙述语境到推测语境
“样子”作为复合词最早见于五代时期,仅在《祖堂集》中见1例。例如:
(5)众参,师云:“若有白纳衣,一时染却。”于时众中召出一僧,当阳而立。师指云:“这个便是样子也,还有人得相似摩?”众皆无对。(《祖堂集》卷十)
这个“样子”是有实际指称内容的名词,即“供人效法、模仿的榜样或式样”,充当宾语。宋代以后,“样子”开始多见,有和五代基本相同用法,句法相对自由。例如:
(6)你不晓得底,我说在这里,教你晓得;你不会做底,我做下样子在此,与你做。(《朱子语类》卷十三)
(7)後之人此心未得似圣人之心,只得将圣人已行底,圣人所传於後世底,依这样子做。做得合时,便是合天理之自然。(《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由“供人效法、模仿的榜样或式样”可以泛化为呈现的景象、状态或情形、情况。例如:
(8)“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这个便是好恶样子。(《朱子语类》卷二十六)
(9)你若不恁地,后要去取敛那地来,封我功臣与同姓时,他便敢起兵,如汉晁错时样子。(《朱子语类》卷九十)
例(8)句“样子”充当名词性中心语,例(9)句“样子”表示“情形义”,附在小句“如汉晁错时”后,这是叙述语境,“样子”还是客观意义,不能删除,去掉语义不完整。由具体的样子发展为抽象的样子,这是隐喻的泛化结果。至明以后,不仅这种用法增多,而且“样子”语境扩展了,由叙述语境扩展到推测语境,说话人的态度也涉乎其中,“样子”表示说话人的主观判断或者推测,获得了主观性的表达功能,由抽象的样子发展为基于样子的推测,这是转喻的结果。例如:
(10)连吆喝,递吆喝,这个枷再不见松,只见越加重得来,渐渐的站不住的样子。(《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七十四回)
(11)三人进了门,只听得房间里地板上“历历碌碌”一阵脚声,好像两人扭结拖拽的样子。(《海上花列传》第五十五回)
(12)见西上房里,家人正搬行李装车,是远处来的客,要动身的样子,就立住闲看。(《老残游记》第二十回)
上述三例,“样子”用在由前提而结论的推论语境中(前提是“这个枷再不见松,只见越加重得来;房间里地板上‘历历碌碌’一阵脚声;家人正搬行李装车”,结论是“渐渐的站不住;两人扭结拖拽;动身”),重新分析为助词。“样子”是对结论成为事实的或然性推测,体现了言者的主观情态,句法地位降级,成为句末的附属成分,可以删除。如:
(10)’只见越加重得来,渐渐的站不住。
(11)’只听得房间里地板上“历历碌碌”一阵脚声,好像两人扭结拖拽。
(12)’家人正搬行李装车,是远处来的客,要动身,就立住闲看。
综上,“样子”完成了“具体的样子→抽象的样子→基于样子的推测”的虚化过程,这与我们的认知有关,我们总是以具体的来表达抽象的。“样子”的推测义也是认知与语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e)的结果,“样子”由“供人效法、模仿的榜样或式样”可以抽象化为“参照标准”,标准是心智中既有认知域,是潜在的,以此为语义基础,说话人将当前认知域与既有认知域的标准进行比较,由于结果是或然的,充满着不可确定性,因而是推测,“样子”的这一语义演变过程是推理到指称(in‐ference become reference)的过程。
(二)小句结构到数量结构
“样子”用于推论语境表示言者的主观判断或者推测一直延续至今,孙利萍把“样子”的这一用法称为样态助词。①孙利萍《两岸华语后置标记“样子”的语用差异及其成因》,《中国语文》,2017年第4期,第410页。例如:
(13)话才说完,杨魁便精神跃跃的要想争辩的样子,忽然韩毓英、哈云飞叉手上前。(《续济公传》第一百九十六回)
而把推论事件用于推论数量,就是估量(估量是对量的推测),句法范围得以扩大,这是动态活动与静态数量之间的范畴隐喻(categorical meta‐phors)现象。“样子”用于估量在清代已见用例。例如:
(14)更见方翁如此壮健,虽是六旬年纪,面貌却是四十余岁样子,随与女儿翠花商议,欲将其送方翁为妾,以报周全之德。(《乾隆南巡记》第四回)
(15)文命细看那夫人,年纪亦不过十几岁样子,心中暗暗称奇,便问夫人捉妖之法。(《上古秘史》第一百十一回)
上述两例,数量结构与“样子”紧邻共现,语义上有两种理解:一是修饰关系,“样子”表示“模样”,“四十余岁、十几岁”就是这个“样子”,“样子”也就是“四十余岁、十几岁”;一种是依附关系,“样子”表示估量,“四十余岁样子、十几岁样子”即“四十余岁左右、十几岁左右”。可见,表示年岁的数量结构是“样子”由名词过渡到助词的中间环节。当数量结构表示非年岁时,“样子”就成为助词了。例如:
(16)穿宅过院,径至后园,另是一座小院落,花盆,橘筒,也有五七样子。(《歧路灯》第三十四回)
(17)那的有果子哩。是前几年时,自己做的油酥四五样子,桔饼、糖仙枝、圆梨饼十来样子。这几年就断截了。(《歧路灯》第八十三回)
(18)我们相别不到一年,倒像过了好几十年的样子。你的面貌比先前瘦了好些,却觉得神采飞扬,容光照耀,比从前更是不同。(《九尾龟》第二十二回)
(19)由一小门进去,里面方方的一个天井,三层一座花台,满花台都是海棠,开得十分可爱。最上台上一棵梧桐,遮着半边天的样子。(《续济公传》第一百四十二回)
“样子”后附的既可以是概数形式,也可以是确数形式,与数量结构的组合可以是粘合式,也可以是组合式。朱德熙指出“数量词是体词,但是同时又有谓词性,因此除了作主语、宾语和定语之外,也能做谓语”[2],张敏也认为“数量结构虽是体词性成分,但也有谓词性”[3]。由推论事件到推论数量,“样子”的助词属性没有发生变化,这是基于事件与数量都具有述谓性(predicative)的类推。
三、语用分析
推测是根据一个或几个已知判断得出另一个判断的思维过程,推测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样子”是说话人对必然或实然无法做出准确的认识,而是“对情境的可能性作出判断”[4],体现为认识情态。认识情态内部存在等级强弱之别,Palmer 指出“语言中一般存在三种与认识情态有关的判断,即表达不确定的推测(speculative),表示以可得到的证据为基础的推论的推断(deductive),表示以常识为基础的推论的假设(assumptive)”[5]。推断是唯一可能的结论,推测是可能的结论,假设是合理的结论。“样子”表推测,逻辑上的或然与事实可能相符,可能不符。例如:
(20)忽然迎面来了姨太太老九,手里捧着一个很饱满的皮夹,是要出门的样子。(茅盾《子夜》)
推理形式“要出门的样子”在逻辑上是或然的(可能出门,可能不出门),事实上也是或然的。少数推理形式在逻辑上是或然的,在事实上却是实然的。例如:
(21)金全礼的车子开到工地,老丛已笑眯眯地在那里站着迎他。看他神情,知道他要来的样子。(刘震云《官场》)
推理形式“他要来的样子”在逻辑上是或然的(可能来,也可能不来),但在事实上是实然的(金全礼的车子开到工地,老丛在那里站着迎他,所以他来了)。“样子”表示对事件进程的推测,形成的语篇模式是“S1推测依据,S2推测结论”,总是依据在前,结论在后。例如:
(22)天空阴沉沉的,彤云密布,像是要下雪的样子,使座上更增添了一种低沉懊丧的气氛。(刘斯奋《白门柳》)
(23)到这里,只听见李冬青在外面说话,似乎要进来的样子。(张恨水《春明外史》)
(24)佩芳吃完饭,赶着洗了手脸,又来绣花,凤举就戴着帽子,拿着手杖,仿佛要出去的样子。(张恨水《金粉世家》)
上述三例,根据“天空阴沉沉的,彤云密布”“听见李冬青在外面说话”“戴着帽子,拿着手杖”等,可以推测出“像是要下雪”“似乎要进来”“仿佛要出去”,结论是不确定的,其中“像∕好像”等词经历了类似义到推测义的引申,①参见李小军《相似、比拟、推测、否定——“好像”“似乎”“仿佛”的多维分析》,《汉语学习》,2015年第2期,第5页。与“样子”构成“像∕好像……的样子”的同义框式强化形式。“样子”附于数量结构后表示估量,估量其实是对量的推测,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数量结构+(的)样子”表达的主观量既不是主观大量,也不是主观小量,而是主观游移量。例如:
(25)昨天傍晚六点钟样子,警卫听到林总办公室的报警后,冲进林总办公室。(文丽《表姐表妹》)
(26)走了十里路的样子,他们才分了手。(梁斌《红旗谱》)
(27)到了蔡家,约有了七点半钟样子。(沈从文《冬的空间》)
(28)民警和汽车城有关人员对夫妻俩进行劝导,大约1 点样子,他们被成功劝了下来。(《高价拍来展位遭限牌生意冷 二手车老板夫妇欲跳楼》《钱江晚报》2014-04-01)
所谓主观游移量,是指“说话人认为非确定的数量,是一个基于数量结构为中心上下浮动的游移的量”[6],反映了说话人的思维过程。“六点钟样子、十里路的样子、七点半钟样子、1 点样子”是以“六点钟、十里路、七点半钟、1点”为中心上下浮动的量,可能略多,也可能略少,因而是游移的。量的不同体验是心智的产物,语言反映心智,心智上拿捏不准反映为量的游移,结构中还有一些像“大概、大约、约莫、估摸、差不多”等“可能”类情态词同现帮助表示或然判断。“样子”发生了去范畴化现象,句法位置粘着,只能后附在事件小句或数量结构后,语义上没有指称内容,语法上是表示说话人主观推测的助词。
四、虚化差异与句法语义效应
摹状名词在现代汉语共时层面呈现出不同的虚化程度。首先,语义伴随着语法化程度的加深,会变得越来越抽象,除去“样子”在现代汉语中发展为推测助词外,“模样、光景”也产生助词用法,“表示约略的情况,用在表示时间、数量的结构后面”[7]。例如:
(29)今天早晨五点钟模样,农民们攻进了黄老虎的住宅,她正躲在床角里发抖。(矛盾《蚀》)
(30)下午两三点钟光景,深秋的太阳还是很有热力,她背上汗湿了,衣服贴在脊椎的那道沟槽上,挺直的脊背只腰肢扭动,我紧跟在她后面。(高行健《灵山》)
张爱玲指出“‘光景’除了发展出了助词用法,还语法化成一个表示推测语气的认识情态副词”[8]。“样子、模样、光景”由名词发展为助词,句法地位降级,成为句末的附属成分,都经历了“具体的样子→抽象的样子→基于样子的推测”的虚化过程,语境也从叙述语境扩展为推测语境。而汉语中诸如“情形、情况、架势、趋势、状态、状况、相貌、外貌”等一批摹状名词主要还是以表达词汇意义为主,用来指称事件发展的动向或刻画人或物的外在形状,它们句法位置较为自由,没有虚化为助词的句法语义条件,语境也还是叙述语境。其次,内部的虚化差异还体现在一系列句法语义效应上。
(一)修饰语
根据摹状名词有无实际所指内容,可以分为名词与助词两种用法。例如:
(31)他的脸红了,显出微醉的样子。(吴强《红日》)
(32)小姐低头沉吟的模样虽然残缺不全,可却生动无比。(余华《古典爱情》)
(33)家里有我新买的韩国泡菜方便面,感觉很好吃的样子,要不要尝尝?(六六《双面胶》)
(34)大家抬起脑袋来看,天真阴沉。有人把胳膊伸在外边,看有没有雨掉在上面。“没下。”“像要下雨的模样儿。”(穆时英《油布》)
前两例“样子、模样”有具体的词汇意义,可以替换为“状态、情形、架势”等,而后两例“样子、模样”具有语法意义,表示主观推测,就不能用其他摹状名词来替换了。两种语义的差别也体现在句法上,前例“显出微醉、低头沉吟”属于同一性定语,整体就是“样子、模样”的内容,“样子、模样”也就是“显出微醉、低头沉吟”,可以从定中关系变成同位语关系,而后者“很好吃、要下雨”是“样子、模样”的宿主(host),不可以变成同位语关系。如:
(31)’他的脸红了,显出微醉这个样子。
(32)’小姐低头沉吟这个模样虽然残缺不全,可却生动无比。
(33)’*家里有我新买的韩国泡菜方便面,感觉很好吃这个样子。
(34)’*像要下雨这个模样儿。
后两例“样子、模样”是推测小句末尾的标记成分,句法上可以删除,而前者“样子、模样”是中心语,不能删除。例如:
(31)”*他的脸红了,显出微醉[的样子]。
(32)”*小姐低头沉吟[的模样]虽然残缺不全,可却生动无比。
(33)”家里有我新买的韩国泡菜方便面,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34)”像要下雨[的模样儿]。
(二)数量结构
表层形式上实义的摹状名词与虚化后的助词虽然都可以出现在“数量结构+(的)___”的句法结构中,但句法结构与语义关系都有不同。例如:
(35)我今天晚上在那儿看见了一种光景,让我非常地厌恶。(托马斯·哈代《还乡》)
(36)经过多方面征求意见,反来复去的研究,从十九种图样中选择和确定加工三种样子。(《人民日报》1956年)
(37)黄克诚的三师,距林彪也就20 里左右。梁兴初的1 师更近,就10 里样子。(张正隆《雪白血红》)
(38)等她换了衣服,拿了些钱,来到红房子西餐馆的时候,已是七点钟光景。(王安忆《长恨歌》)
前两例“光景、样子”有实际指称内容,“一种、三种”是对“光景、样子”的客观计量,“光景、样子”也可用“情景、式样”等进行同义替换;后两例“样子、光景”没有指称内容,而是表示估量,句法上是后附的,“10 里、七点钟”不是对“样子、光景”的客观计量,“样子、光景”也无法替换为“情景、式样”。划线部分虽都可以作删除或插入量度义形容词等句法操作。例如:
(35)’我今天晚上在那儿看见了一种[光景]。我今天晚上在那儿看见了一种坏的光景。
(36)’选择和确定加工三种[样子]。选择和确定加工三种厚的样子。
(37)’梁兴初的1 师更近,就10 里[样子]。梁兴初的1师更近,10里远的样子。
(38)’已是七点钟[光景]。已是七点钟晚的光景。
但在语义上就显现出差异,“一种光景、三种样子”和“一种、三种”在语境中是等值的,“10里样子、七点钟光景”却不等于“10里、七点钟”,而是表示“略多于10 里∕七点钟”或“略少于10 里∕七点钟”。可见,在共时层面上,“样子、光景、模样”发生了功能分化,有名词与助词两种用法,它们与其他摹状名词相比,在句法与语义上呈现出较强的功能扩展趋势。
(三)篇章回指
摹状名词因为语义内容实在,可以在话题链结构中进行回指。例如:
(39)当晚他把那位青年送来了——顺便说一句,好人有一辆汽车,非常之小,样子也很古怪,像个垃圾箱的模样。(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
(40)这些狗长得娇小玲珑,憨态可掬,模样特逗;而且性格温顺、聪明伶俐,善解人意,使人赏心悦目,所以特有人缘。(《报刊精选》1994年)
上述例句中,“样子、模样”都具有回指功能,分别回指话题“汽车、这些狗”的样子与模样,而已经虚化为语法成分的“样子、模样”用在句末,表达语法功能。此外,能否进行关系化也是判定摹状名词是否发展出语法功能的重要指标。关系化是对一个述谓结构进行降级处理,关系化后成为一个降级述谓结构,不再具有原先述谓结构的特征。如:
(41)做好一套样子,发动学员自己仿做。(《人民日报》1952年)
(42)刘嘉麒花白头发,两道寿眉已微微长出模样。(《人民日报》2002年)
普通话中关系从句标记是“的”,对摹状名词进行关系化可以得出下列句子。如:
(41)’做好的一套样子已经被学员仿做了。
(42)’两道寿眉已微微长出的模样令人难忘。
而已经虚化为助词的“样子、模样”就不能再进行关系化了,这说明摹状名词内部产生了分化。例如:
(43)我们随着那个孩子,又走了一里路样子,来到沟边上。(《人民日报》1965年)
(44)到了十二点钟模样,我假定已经睡过一夜,现在天亮了,正式地披衣下床。(丰子恺《半篇莫干山游记》)
加入“的”构成的“走了一里路的样子、到了十二点钟的模样、躺了小半年的光景”并不是关系化形式,与原式只是组合式与粘合式的区别,这里“的”并不像关系化时具有强制性。
五、结 语
现代汉语中,“样子”发生了去范畴化现象,句法位置粘着,可以后附在事件小句和数量结构之后,语义上没有指称内容,语法上是表示主观推测的助词。“样子”附于事件小句后表示对事件进程的推测,附于数量结构后表示估量,表示的是以数量结构为中心上下浮动的主观游移量,说话人对事件小句或量的必然或实然无法做出准确的认识,是确定性较低的或然判断。助词“样子”是经“具体的样子→抽象的样子→基于样子的推测”发展而来的,这是隐喻与转喻共同作用的结果,“样子”的推测义也是认知与语用推理的结果。摹状名词内部存在不同的虚化层级,其中“样子、模样、光景”虚化成为句末助词,与实义的摹状名词有修饰语、数量结构与关系化等一系列的句法语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