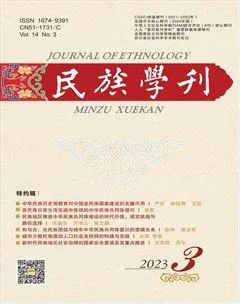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进路
2023-07-31袁娅琴李良品
袁娅琴 李良品
[摘要]
土司制度是明清王朝国家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政治基础,也是保障边疆地区稳定的必备条件。明清时期国家主导、上下互动、多元共治,无疑是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路,为王朝国家制度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历史、治理经验,对新时代国家层面的制度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认为,制度治理不仅要以国家为主导,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双向互动,而且需要“多元共治”。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在变革制度、完善制度、维护制度、督查制度等下功夫,实现国家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方面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增强国家制度治理的权威性。探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的进路,寄望于助力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土司制度;国家治理;进路;制度治理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3)03-0134-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土归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9ZDA18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袁娅琴(1993- ),女,重庆酉阳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北京 100081 李良品(1957-),男,重庆石柱人,长江师范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学和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重庆 涪陵 408100
制度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立足于“制度”,关键在“治理”。本文的所谓制度治理,即“按照制度治理意识办事、依据制度治理规律办事、运用制度治理规则办事”[1]。制度治理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明清时期通过土司制度治理土司和土司地区就属于制度治理的典范。明清中央政府具有“一统天下”的宏大视野和长远目标,这不仅为不断丰富完善国家制度、加强国家治理取得重大成效,而且為保持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推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做出巨大努力。明清中央政府的制度设计、统治手段与监督体系等国家治理措施,为国家权力在土司地区的延伸、深入与下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取得了应有的成效。
近十年来,学界虽对土司问题研究给予了极大关注,相关成果如雨后春笋,但学界漏逮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相关问题。迄今为止,学界与本文完全一致的成果仅有笔者关于中国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的论文1篇[2],另与主题相关的著述有5篇,或探讨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或分析土司承袭制度与国家治理,或研究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这无疑是学界之憾。我们认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不断完善新时代中国制度体系,强化中国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功能,从而推进“国家之制”向“国家之治”转化,这不仅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最基本的制度逻辑,而且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逻辑。因此,探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进路,能够助力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国家主导下的土司制度
明清中央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体现了统治者在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意志和决心,它主导着中央政府与各地土司的关系,决定着土司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趋势。
(一)主导土司制度治理的顶层设计
明清时期王朝国家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不能脱离土司制度。边疆地区制度治理效果的优劣与好坏,根本上取决于土司制度的顶层设计是否科学,土司制度的制订是否完善。明清统治者充分认识到,土司制度的建设、丰富和完善是有效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关键,因此,土司制度设计是土司制度治理过程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的核心问题,明清中央政府一直将土司制度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几种分项制度的设计掌控在自己手中。
一是土司职官制度。明清时期各地土司虽然是世袭土官,但同样也是朝廷命官,土司职官职衔和品级的设置、各地土司职官的赋权、土司职官的铨选与考核、土司职官的管控与制衡、土司职官的监督与违法处置、土司衙署的权力构建与丧失等内容,均为土司职官制度,这些被中央政府在顶层设计时一直牢牢控制着。
二是土司承袭制度。土司承袭制度是土司制度的核心,是明清中央政府管理土司地区的关键,也关系到土司政权和土司地区的稳定。土司承袭制度包括承袭法规、承袭程序、承袭文书、承袭次序、承袭方式等具体规定与实施、以及土司承袭过程中有“冒袭”“夺袭”“争袭”等违法之“袭”,针对承袭过程中的弊端,朝廷制定了相应的惩罚制度。这些举措的制定始终被明清中央政府掌控着,也就是说,土司承袭制度在明清中央政府对土司制度治理过程中,既不断丰富完善,又始终控制着制度的制定权,在民族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三是土司朝贡制度。土司朝贡制度是土司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明清中央王朝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土司朝贡属于王朝国家与各地土司间的“官方贸易”,它体现了各地土司的国家认同、政治归附和地方权力机构臣服。明清时期各地土司向中央王朝贡献珍稀物品、地方特产,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且体现了各土司对中央政府承担的一种特定的政治义务和对王朝国家的认同。因此,中央政府对各地土司的朝贡日期、朝贡人数、朝贡物品、回赐物品、接待等级、款待用膳等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不允许土司违反规定。
四是土司法律制度。明清政府制定成文的土司法律制度,经皇帝批准后施行,并通过《大明会典》《大清会典》《礼部志稿》《钦定三部则例》《大清会典事例》和《钦定大清会典则例》等颁行,对各地土司的职衔、承袭、铨选、征调、贡赋、抚恤、考核、赏罚、升迁、裁革等具体规定,构成了土司法律制度,并在土司地区具有普遍法律效力。土司法律制度形成了一个结构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中央政府始终利用这套体系约束和管控各地土司。
五是土司征调制度。明清中央政府规定各地土司服从征调、保境安民等义务以及土兵军事组织体制、军事领导体制、兵役制度、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军饷制度、军事法规制度等军事制度。土司制度是土司征调的前提和基础,土司征调是土司制度的根本与基石。明清时期各地土司兵是一支非常重要而十分活跃的武装力量,土兵既要服务于土司自身的统治,又要成为明清中央王朝军事力量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此外,土司制度治理还涉及土司教育、土司礼仪、土司安插、土司分袭等制度,中央政府在制度治理过程中也不断补充和完善各项具体的制度,逐渐构建起系统的、规范的、有效的土司制度体系。
(二)主导土司制度治理的制度执行
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土司制度是王朝国家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和赖以运行的基础,是王朝国家保障土司地区长治久安的条件。但是,土司制度是“死”条款,是供国家治理者运用的,需要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生效力、产生效果。土司制度的优劣好坏,归根结底要看在土司制度治理过程中的效果。土司制度是否成熟与完善,归根到底要由国家治理的成效来检验。因此,土司制度的基础是实施治理,实施治理的过程是制度执行,由谁来具体执行又成为土司制度治理的关键。土司制度是制度治理的依据、尺度,同时也是手段和工具。中央政府一手掌握着依据和尺度制定权,一手掌控着依据和尺度(即制度执行权)。
一是对土司承袭过程中相关问题的执行。明清政府在处理土司承袭问题时,根据法规和土司地区实际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灵活处理具体的土司承袭问题。在对土司“世袭”与否的问题上,明清政府的处理极具灵活性。明代中央政府是以土司“世袭”来抚绥边疆,如广西田州知府“岑伯颜,即岑间,由世袭土官,洪武元年赍前朝印信率众归附复职,洪武二十年授田州府知府,长男岑永通授上隆州知州。洪武二十六年岑坚故,钦准承袭,患病,长男岑祥备方物、马匹赴京朝觐,告替。永乐三年十二月奉圣旨,准他替职。钦此。”[3]208这或许是因为“明自中叶而后,抚绥失宜,威柄日弛,诸土司叛服不常,仅能羁縻勿绝”[3]2的原因。明代又以土司是否“守法度”来决定是否让其世袭。如永乐元年二月奉圣旨:“见任的流官知州不动,这董节是土人,还著他做知州,一同管事,不做世袭,他若不守法度时换了。”[3]8-9清代土司承袭,除了遵守王朝国家的相关法令之外,清王朝又对有些土司执行分袭制度,或承袭一个虚衔,并无实权。如《清史稿》卷一百十七“贵州土同知”条载:“其不管理土峒者,正六品、正七品土官各一人,正八品土官三人,正九品、从九品土官各二人”。[4]3414-3416采用这些举措来限制土司权力,以此增强国家对土司地区的管理。
二是对土司承袭过程中贪官腐败问题的执行。袭职程序的不统一导致贪污官吏钻法律制度的空子,如有的流官勘合人员在土司承袭过程中不肯为土司应袭子弟保堪,需有土司行贿后方才受理,这就导致土司不能袭替,进而引发土司叛乱。明代中央政府重新制定土司承袭程序,嘉靖九年(1530)颁布的《土官袭职条例》就是用来规范土司袭职程序的明文规定。为避免勘合官员的受贿行为,嘉靖十年(1531)规定,土司承袭事宜,须“令镇守抚按会行三司”[5]441-442。嘉靖四十五年(1566)进一步细化:“勘报过一年者,行巡按官查究;二年以上者,听吏部径自查参”。[6]31从上述规定来看,中央王朝对勘合人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并没有制定实质性的处罚措施。勘合官员的受贿行为导致诸如潞江线贵、陇川岳凤、蛮莫思哲等土司附缅。对此,陈善的《土官袭职议》[7]862-863针对勘合人员的贪污行为,提出将袭职程序通告各土官衙门,严格规定了勘合期限,建议对骗财的勘合人员和主动行贿的土司做出相应处罚。时至清代,流官需索土司依旧:“官吏贪污,为清代边政紊乱之一原因……至于官吏贪污,在上者虽严行禁止,但鲜见成效;且边地衙门索费,视为规例。其他倚势凌人,种种苛索,在所难免,禁亦难禁。高宗时因知胥吏之藉故贪污,乃根本免除若干地方土民之纳粮。此虽为善政,然究非制止贪污之良策也。”[8]78-79可见,清代制度治理也存在巨大的弊端。
三是对犯罪土司的制度治理。明清中央政府对犯罪土司的治理皆有法律可依。《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详细载有“职官有犯”“请发充净军”“纵军掳掠”“略人略卖人”“越诉”“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官员袭荫”“徒流迁徒地方”“盗卖田宅”“违禁取利”“私越冒度关津”“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恐吓取财”“诈教诱人犯法”“盗贼捕限”等条文,均是明清中央政府在土官土司犯罪制度治理方面的具体条款。这些内容是土司制度治理的基础,对土司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王朝国家的长治久安起着保障性的作用。
(三)主导土司制度治理的结果运用
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建设是相对成型和稳定的制度治理體系,可以运用于土司职官、承袭、征调、朝贡、纳赋、文教、礼仪、分袭、安插等土司专项制度的治理和践行中。土司制度治理的要诀,就是要根据土司及土司地区当时的实际,科学合理地运用土司制度,采取多种方式方法,对土司及土司地区的一系列问题实行具体而有效的管控、调整和巩固,使之达到有效治理的状态,并将制度治理所取得的结果运用于土司是否继续履职与承袭?是否接受奖惩、抚恤与升降?从现存历史文献看,土司制度治理过程中,一方面在加强土司制度体系的建设,一方面进行土司制度治理,并按照国家意志运用其结果,以实现王朝国家的“大一统”。
一是关于土司承袭的结果运用。著者查阅明清时期重要文献,发现记载土司家族内“争袭”事件的次数较多,其中《蛮司合志》7次,《土官底簿》6次,《明史·土司传》11次,《明实录》18次,《清史稿·土司传》3次,合计45次,说明各地土司争袭事件在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时有发生。从表面上看,土司争袭是因为“土司常有多妻,嫡庶之争,为其乱源,又兼妇女可得承袭,为祸更大”。[9]但究其实质,土司争袭的根本原因有四:[10]第一,土司制度赋予的土司特权是明清各地土司争袭的直接原因。“土司所到之处,土民皆下跪迎接,土司出,其仪卫颇盛,土民见之,皆夹道伏。即有谴责诛杀,惴惴听命,莫敢违者。”[11]在土司制度下,土司是土司辖区内的“土皇帝”,是一切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和土民的最高行政长官,拥有财政、行政、法律等诸多方面的特权。第二,土司承袭制度本身存在着承袭者众多和无序的两大弊端。土司权力诱惑太大,导致很多人在土司承袭上仍“不讲规矩”。第三,土司袭职过程中虽然有相关部门的保结文书,但在实际操作中,流官渎职疏慢和随意索贿,不为土司保结,导致一些土司长期不得袭职,以致“土官子孙承袭,有积至二三十年不得职者”[12]273,这就更加助长了土司争袭的可能。第四,朝廷官员不依法办事,不按照承袭次序,造成土司争袭。明清中央政府针对各地土司夺袭事件不断健全和完善土司承袭制度,加强土司及土司地区治理。
二是对于土司违法的处理。明清中央政府不仅强化律例约束土司,并依法处理违法土司。《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均有针对土司违法后的惩罚法律条文。如《大清律例》禁止土司越界活动,若土司与“土人”需要远赴外省,必须呈报官府而后出行。清王朝严格规定土司、土人出行时间、路线、地点,不许擅自逗留,土司违反即革职,“土人”违反按律处罚。清政府对土司延幕也有明确规定:“私聘之文武土官,及失察之该管州、县,交部分别议处”,[13]550对土司公聘延幕和私聘土幕的规定十分明确,特别是私聘土幕还要照违令私罪律罚俸一年。这些规定彰显了王朝国家对土司及土司地区的管控更加严格,治理更加有效。
二、上下互动中的土司制度
明清时期是秦汉以降土司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最为密切的时期,也是中央政府与土司地区互动最为频繁的时期。王朝国家通过“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路径,由此形成上下互动。
(一)土司制度与土司权力的一体性
明清时期对土司制度能够起到决策作用的无疑是以皇帝为核心而形成的朝廷,即中央机构,这是土司制度治理的最高决策层,皇帝处于土司制度治理的塔尖,是土司制度的最终决策者。土司制度不仅是王朝国家和土司地区管理机构以及制度规范的统一体,而且是王朝国家制度治理与各地土司实际权力的统一体。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要求地方流官按土司制度治理各地土司,让其有效实施权力。如《滇事杂档》中“前迤南道道台胡某办理车里宣慰卷”云:
伏思边吏治边,固以协体制为急务;而尤首以安边为急务,盖协体制犹虚而安边乃实也。若边不安而尚有何体制之可协乎?盖各边情形不同,总须因地制宜,宜则边安,不宜则边不安也。故有不能不协体制以安边者,亦有不必尽言体制而边始安者……然则边吏治边总以安边为主,而安边尤以因地制宜为主。有不能不协体制以安边者,即以协体制为安边也;有不必尽言体制而边始安者,即以安边为协体制也。[14]
这主要凸显了朝廷命官对土司制度与治乱安边的认知。在土司制度下,王朝国家将权力委派给行省和府州厅县以及土司机构,以便让各级机构代行土司地区治理的权力,最终实现在国家主导下土司制度与流官、土司的实际保有权力的一体性。
(二)地方流官与各地土司的共同性
王朝国家通过行省以及府州县、土司等地方官员分层分级管理土司地区事务,这是土司制度治理的主要执行者。明清时期有土司的省份,其行政官员设置和土司制度治理惯例,都是采取分层分级形式,分为行省总督、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府州厅县流官、土司计五个层级,并共同治理土司地区。
各地流官作为治理土司地区的执行者,他们在执行王朝国家政策和法规的同时,不仅要求各地土司必须效忠供职,自觉肩负起抚夷安边的职责,而且强调各地土司必须肩负起与地方流官共同治理地方社会乱象的责任。时任临安府知府认为:“土司土舍为朝廷藩篱,边外有事,即须调练防堵;而本境地方夷民人等,遇有为匪不法,重则送州县本管官究办,轻则自行惩处,务使夷民安业,地方安静,方为无忝厥职”[14],“设立土司土舍,原为约束夷民,干御边圉,该土舍所属夷民不能差遣,安用土司为耶?”[14]换言之,作为边疆地区的土司,对外要拱卫王朝、捍衛边隅;对内要安抚夷民、缉匪捕盗、收纳钱粮,遇到不法行为和社会乱象,必须共同治理,实现“变乱为治”的目标,以充分体现府州厅县流官与当地土司共同治理土司地区的重要性。道光二十三年(1843),“镇康太爷又将勐捧、邦东数户,私许送与莽戛,招兵数千抢杀自家百姓,不分皂白,不管客家,乱抢乱杀”以及“景星潜逃入境”的情况,永昌府移请镇康土州转“饬令耿马土司就近查拿务获解府”一事,[14]更说明地方流官期望土司与其一道治理乱局,以达到“拨乱反正”之目的。
(三)中央政府与各地土司文化认同的一致性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各地土司相对于中央政府基本上居于弱势群体。因此,中央政府必然引导各地土司自觉接受主流文化,起到对国家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和土司地区各族民众经过长期博弈,最终被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诸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等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举贤、节俭等思想以及法家的君主集权、依法治国等思想,应该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让土司地区在国家主流文化引领下,实现文化认同的一致性。这些主流文化无疑是土司地区各族民众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始终处于统领地位。
明清中央政府通过创办儒学、社学、义学、书院等各类学校以及地方民众修订族谱、制订乡规民约等举措,引领土司地区各族民众学习儒家文化,以使土司及土司地区各族民众自觉接受国家主流文化,服从中央王朝统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乡约对土司地区各族民众的文化引领作用。如清代乡约朔望宣讲的内容以《圣谕六条》《圣谕十六条》和《圣谕广训》为主,这些圣谕其实是忠孝伦理道德的具体化,反映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15]嘉庆《临安府志》载有:“每遇朔望,齐集乡之耆老、里长,宣读《圣谕广训》,务使乡曲愚民共知鼓舞向善。”[16]125-126该志对宣讲《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的记载颇为详细,将乡约宣讲时间、场所、仪式、内容、教育形式及相关奖励办法等记载得十分清楚。乡约宣讲的对象主要是包括土司地区各族民众,主要目的在于化民成俗,纠正不良风气,减少犯罪行为,稳定社会秩序。从土司及土司地区各族民众的层面看,他们通过创办土司学校、学习儒家文化、参加科举考试、修订家乘族谱、制订乡规民约等形式体现对国家正统文化的认同,如湖北利川土司覃氏家族编纂的《覃氏族谱》“家规”序言中有“家之有规,犹国之有制。制不定,无以一朝廷之趋;规不立,无以为子弟之率”的记载,反映了各地土司将国家主流文化深深地融于自己日常生活之中和置于当地族群心目之中。这些“规训”堪称土司家族谱牒的精华,该族谱的序言及正文条款尽显教化族群之用意,不仅可以看出它明显受清廷“圣谕”的指导而撰写,而且也是乡村社会族群在对国家正统文化认同后的产物。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所宣扬的主流文化,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土司地区各族民众只能接受。在王朝国家主流文化引领下,中央政府通过政权经略、土司制度、创办学校、建立卫所、人口迁移、土兵征调、土司朝贡、劝民农桑等直接或间接的多种形式,经过中央政府与土司及土司地区各族民众频繁的接触和碰撞,引导土司地区各族民众与王朝国家之间在文化认同、价值趋同等方面相互借取,尤其是通过土司制度治理,加强土司地区各族民众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推动土司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多元主体共同管理土司地区
“多元共治”是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这种治理以土司制度治理为基础。它既是明清中央政府在土司制度治理实践中形成的新要求、新思想,也是王朝国家土司制度治理实践探索的经验总结,属于明清时期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制度创新。
(一)“多元共治”思想及土司制度治理体系
“多元共治”并不是西方行政管理思想,而是我国封建社会早已有之的国家治理思想。“多元共治”思想其实也是一种理论,它比较契合明清时期王朝国家的土司制度治理。“多元共治”理论散见于我国古典文籍之中。如《荀子·君道》:“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孔子家语·贤君》:“吾欲使官府治理,为之奈何?”这些语句都蕴含了我国先秦时期哲人们的治理思想。《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也体现了我国先秦时期传统社会的多元共治思想。明清时期很多学者也提出“人君与天下共”等主张,这也蕴含着共治思想。[17]我国古人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深入观察和对实践生活的认真总结,将“多元共治”思想运用到国家治理中,并得到充分验证。从历史上的“管理”到后来的“治理”,再到“多元共治”,其意涵由单向控制、管控向互相协作治理转变,即包含治理主体的多元趋势,不断吸纳社会各方力量积极主动参与,不再仅限于政府这个单一治理主体。土司制度治理权力运行模式的转变,不再强调以往自上而下的单维治理模式,而是注重上下互动、多维协调的治理过程。[18]明清时期王朝国家的传统社会不仅存在多元共治思想理念,并在土司地区基层社会结构中呈现出多元共治的形式。
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治理体系可总结为“一个中心、两个主题、三大目标、四元治理、五项内容”。即以“土司制度治理”为中心,围绕“确保土司制度治理有效”和“确保土司地区长治久安”的主题,以“加速土司政治一体化”“加强制度治理网状化”“践行土司地区治理地方化”为目标,以“官方基层组织、官民共建基层组织、土司宗族组织、民间绅士阶层”为单元,以“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为治理内容而形成土司制度治理体系。政府机关、里甲团练、乡约饮酒、土司宗族四方共同治理,以行政命令、告示章程、乡规民约、宗族族规等为治理主要依据,形成了明清时期王朝国家独具特色的土司地区多元共治协调机制,并在土司地区逐渐实现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图景。
(二)土司地区“多元共治”举措
作为王朝国家重要组成部分,土司地区肩负着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推动土司制度治理历史进程的重任。为此,多元共治成为明清时期王朝国家制度治理的必然选择,通过多元治理思路和模式,可以解决国家与地方、中央王朝与土司、土司与土民等多方面的利益诉求矛盾,整合多方资源,改进治理方式落后等,最终以多元共治的方式整体加快推进土司及土司地区治理。
1.官方基层组织
明清时期王朝国家在土司地区省份的官方组织机构有府、州、县等官吏设置,形式多样,或土流并治、土流分治,或土司统治,或卫司同城。在土司地区基层社会的组织设置也不尽一致:广西壮族土司地区以哨为单位的基层组织编制,广西瑶族土司地区以里、堡、城头、化、布、哨、团、甲等为单位的编制;[19]川西北则以改土设屯的卫所(如土千户所、土百户所)为单位,湖广都指挥使司则有以九溪卫所管辖麻寮所的建制……它们同样具有土司性质,但在基层组织设置时则是因地制宜。如麻寮土千户所:
明洪武时,设麻寮所隘,正副千百户三十二名,世守土,赐铁券,封武德将军。本朝顺治四年,顺丞王安边至澧,各所隘投诚披剃,仍因明制,赏给方印号纸。雍正十三年,诸蛮向化,献土缴印,该千户为千总、百户为百总,颁给敕书一道,扎符一张,令其子孙世袭,如有年力精壮,准其随营效用,才具优长者,照以武职升转。[20]481
即麻寮所为一所四厅的武职,计设千总六员,把总二十六员,其基层组织设置,在隘设百户,汉、土杂用。明清时期在一些土司地区推行社制、里甲、保甲、乡约、牛丛等制度。
明清中央王朝把县以下的基层社会治理权交给这些小土司的同时,使他们受制于流官,便于乡村社会的稳定。如清光绪年间广西巡抚李某就有禁革土司地方科派告示[21]58-59,其碑文揭露了广西土司统治下的壮族地区,“土官遇事科派,不恤民艰,而汉属文武衙门”,也随便“需索使费”,致使土司辖区民不聊生的惨况。因此,广西巡抚出告示坚决制止这种现象发生,这有利于维护土司地区社会稳定,属于制度治理土司地区的案例之一。明清中央政府既有对土司和流官的管控,也有土司对辖区的治理,当然也不乏以里甲、保甲、团练等为代表的官方基层组织对土司地区基层的治理。通过对官方基层组织制度治理情况的考察,既彰显了王朝国家在制度治理过程中权力在乡村社会中的渗透与下沉,也体现了土司地区基层社会中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构成与彼此协调。
2.官民共建基层组织
王朝国家在土司地区的官民共建基层组织是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组织,这种组织主要有官方组织的民间化与民间组织的官方化两种情况[22]76,其主要作用在于协调土司地区的官方与民间,以共同治理土司地区。从土司地区的实际情况看,明清时期官民共建基层组织主要有乡约、社学、社仓等,它们是土司地区官方基层组织的配角,充当教化乡民、赈灾济贫、维护社会秩序的角色,是对明清时期土司地区里甲、保甲和团练等基层组织相关职能的补充与完善。明清时期土司地区官民共建基层组织有三个特点。一是官办性。社学、乡约、社仓等属于官民共建基层组织,具有官治的传统。如社学是明清中央政府督促创建起来的,“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23]185,社学必须贯彻执行中央政府的办学宗旨。二是强制性。官民共建基层组织是一种强迫的组织,如社学的学习内容、教师选擇等具有强制性。三是变异性,主要体现在乡治系统的变异和宣讲内容的变异。特别是乡约的变异更为明显,明代乡约的本质是让乡里百姓“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24]105,而清代乡约则成了宣传贯彻统治者理念(如康熙《上谕十六条》、雍正《圣谕广训》等)的一种工具。如清政府规定:“凡直省州、县、乡村、巨堡及番寨土司地方,设立约处所。推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择朴实谨慎者三四人,以为值月。每月朔望,齐集耆老人等,宣读《圣谕广训》、钦定律条,务令明白讲解,家喻户晓。”[25]尽管这种空洞乏味的说教在土司地区并未真正发挥其职能,但对于土司地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起到一定的协调作用。
3.土司宗族组织
明清时期土司宗族组织在土司制度治理土司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因为在各地土司治理辖区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他们必然会利用土司的权势,凝聚宗族力量,互相照应,抱团发展,因此,聚族而居的土司宗族组织为土司辖区基层治理履行职责和义务创造了必要条件。我们认为,在一个土司宗族共同体中,族长或族正是核心人物,而任现职的土司是当仁不让的族长。在明清时期土司地区,建立了以族长权力为宗族核心,以族谱、族规、宗祠、族田为手段的严密的土司宗族社会人际关系。当时土司宗族组织大多是通过族规、祖训等来调整土司宗族关系,维持宗族内部的秩序和尊卑伦理,进而起到维护和加强土司家族统治的作用。土司宗族组织之所以有着很强的内聚力,是因为它有着相互联系、控制力强的宗族内在结构。土司宗族组织的各种功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障宗族成员的各种基本需求,因而土司宗族组织对于族众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基本上可以信赖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社会群体组织。[26]50
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多元共治”,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这种制度治理具有多元性。但我们必须清楚,国家地方行政机构、地方基层组织和土司宗族组织三级治理体系的融合不够。随着各地土司运用权势、掌控资源、维护辖区统治的需求不断扩大,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野心不断膨胀,中央政府与各地土司的利益冲突便逐渐显现出来,而时常发生土司叛乱事件。即由于府州县行政机构、官方基层组织、官民共建基层组织以及土司宗族组织四者之间制度治理体系不融合,未能产生联动,所以导致土司制度治理效果不佳。只有府州县行政机构、官方基层组织、官民共建基层组织以及土司宗族组织四者之间构建土司制度治理共同体,才能真正实现国家主导、地方负责、社会协同、土司宗族参与的国家治理格局的目标。
四、结语
综上可见,明清时期国家主导、上下互动、多元共治,无疑是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路,为王朝国家制度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历史、治理经验,对当下新时代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认为,制度治理不仅要以国家为主导,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双向互动,而且需要“多元共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实质性、决定性的作用,制度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因此,必须加快推进制度治理,让制度治理成为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程中,必须推进和加强制度治理,因为制度治理不仅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最基本的制度逻辑,而且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逻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应该在变革制度、完善制度、维护制度、督查制度等方面下功夫,实现国家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方面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增强国家制度治理的权威性。
参考文献:
[1]温宪元.制度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N].深圳特区报,2014-03-12.
[2]李良品,韦丽芳.中国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的三个问题[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06).
[3](明)佚名.土官底簿[M].北京:中国书店,2018.
[4](民国)赵尔巽.清史稿[Z].北京:中华书局,1977.
[5](明)方孔炤.全边略记·卷7[Z]//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明)申时行.明会典·卷6[Z].北京:中华书局,1989.
[7](明)刘文征,古永继点校.滇志[Z].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8]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M].重庆:正中书局,1944.
[9]佘贻泽.明代之土司制度[J].禹贡,1936(11).
[10]莫代山.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争袭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09(06).
[11](清)周来贺.桑植县志·杂识·卷8[Z].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
[12]李良品,等.二十五史西南地区土司史料辑录[Z].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13]张荣铮,等点校.大清律例[Z].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14](清)胡启荣,黄中位,辑.滇事杂档·照抄前道胡办理车里宣慰卷之“照抄禀覆中丞稿”条[Z].道光十三年至道光二十七年(1833-1847)抄本.
[15]李良品,等.清代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社会教育述论[J].民族教育研究,2011(05).
[16](清)江浚源,纂,杨丰,校注.嘉庆临安府志[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
[17]江必新.关于多元共治的若干思考[J].社会治理,2019(03).
[18]孙逸啸.论明清时期长江沿岸码头城市多元社会治理的法秩序——以上海、武汉及重庆为例[J].江汉大学学报,2018(02).
[19]都安瑶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都安瑶族自治县志[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20]鹤峰县史志编纂办公室.容美土司史料汇编[Z].鹤峰县史志编纂办公室,1983.
[21]广西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
[22]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D].蘇州:苏州大学,2001.
[23](清)张廷玉.明史·卷69[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4]朱元璋.大诰续编·明孝第七[Z]//吴相湘.明朝开国文献(一).台湾“内政部”,1966.
[25]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18·礼部·风教·讲约一[Z].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26]李良品.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
收稿日期:2022-10-12 责任编辑:丁 强
猜你喜欢
杂志排行
民族学刊的其它文章
-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作用
- On the Building and Practice of a Social Support Network for the Urban Ethnic Minority Floating Population: A Case Study of “Ethnic Homes” in Guangzhou
- The Early Practice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Visual Ethnodanceology
- Core Issues in the Philological Study of Ethnic Literary Integration History in Ancient Southwest China
- A Study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Evolution Trend of Red Revolutionary Tourism Symbiosis Atlas in Sichuan Province
- A Development Model for the Homestay Industry in Qiang Area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Based on a Survey in Wenchuan County, Aba Prefe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