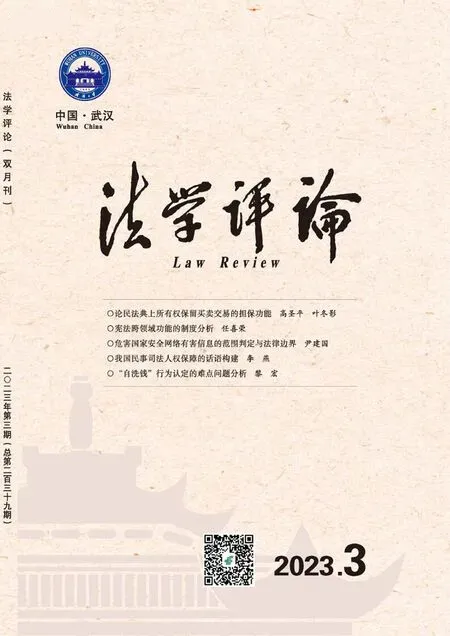专利授权伦理审查的制度重构*
——从“科技向善”到“专利向善”的法律安排
2023-07-31刘鑫
刘 鑫
作为专利授权实质性审查的重要内容,对于发明创造的伦理审查是可专利性判断中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确保“科技向善”伦理追求在专利制度中有效贯彻,实现“专利向善”伦理目标的重要制度安排。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明确给予成员国基于社会公德或公共利益需要,在其本国境内对危及人类与动植物生命或健康以及危害环境的发明创造或技术成果不授予专利权的例外,到各国在专利制度中专门设置的专利授权公序良俗条款与伦理例外规则等以道德考量为主要内容的相关规范,伦理问题不仅是专利授权审查活动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难题,同时也更是国际条约与各国立法中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我国《专利法》也并不例外,公序良俗条款和伦理例外规则自我国《专利法》颁布之初,便以专门条文的形式被予以明确规定,为专利授权伦理审查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
然而,随着技术变迁及相应产业革新的不断深化,我国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机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一方面,专利技术产业化运营的持续推进,使产业利益与政策日益成为专利授权审查的主导因素,而专利授权伦理审查却日渐式微,在实践中甚至还呈现出了以最大程度减少乃至消除对于发明创造伦理审查为目标的“伦理最小化”的实用主义倾向;(1)See Matthias Herdegen, Patents on parts of the Human Body Salient Issues under EC and WTO Law,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Vol. 5, 2002, pp.145-156.另一方面,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成果的不断涌现,使道德范畴中出现了诸多规范和原则不明确的问题,而在对这些新兴科技成果进行专利授权审查时,则会使技术伦理层面的规范和原则的不明确问题,逐步进入到由产业利益所主导的“伦理最小化”的专利审查实践当中,并在其中造成严重的伦理迷失。(2)参见[德]阿明·格伦瓦尔德:《技术伦理手册》,吴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鉴此,为破解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专利伦理难题,有必要以新兴技术中饱含伦理论争的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为例进行分析,深度挖掘社会公众的实践需求,探寻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日渐式微的深层诱因,并在此基础上从内容与程序两个层面入手,展开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机制的立法重构,以实现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标准的精细化及具体运行的规范化。
一、“伦理最小化”思潮下专利授权伦理审查的日渐式微
在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是对发明创造进行授权审查的法定标准,而不违反公序良俗、不属于专利法排除的客体范畴则是其中的伦理性限制条件。二者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给出了专利授权审查的客体要求,虽不能在形式上实现授权范围与排除范畴的“无缝”拼接,但二者并不存在逻辑上的空隙与重叠,因为二者之间实质上是法律一般条款与特殊条款的关系。(3)参见崔国斌:《专利法:原理与案例》(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6-57页。其中,正面性的法定标准对于专利授权范围的一般性要求,应是专利授权中的一般性审查条款,而与之相反的限制条件则是基于社会公德、公共利益的特殊性伦理考察,是专利授权的特殊性审查条款。由此,从法律效力位阶来讲,相比于专利授权中的一般性审查条款,特殊性的伦理审查条款应具有适用上的优先性。但随着专利技术产业化运营的日渐兴盛,传统的专利授权审查制度尤其是其中的伦理审查机制受到了极大冲击。在产业利益驱动下,要求最大程度地减少乃至消除对于发明创造伦理考察与道德衡量的“伦理最小化”思潮开始冒头并逐渐扩散开来,使本身具有优先效力的伦理审查机制在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越来越不被重视,相应的伦理标准与道德约束也随之流于形式。这不仅导致专利授权的公序良俗要求常常被人们所忽略,也致使专利授权的伦理例外规则在实践中被一再突破。
(一)专利授权审查“伦理最小化”的价值溯源
从专利权排他性财产权的本质出发,专利授权活动本身就具有高度的伦理相关性。这是因为专利权的授予势必会造成私人对于发明创造或技术成果的独占,并由此带来知识垄断的社会争议,(4)See Daniel J. Hemel, Lisa Larrimore Ouellette, Beyond the Patents-Prizes Debate, Texas Law Review, Vol. 92, 2013, pp. 303-382.与此同时,它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引起对后续创新活动的阻碍。如若技术方案本身存在较大的伦理问题,专利权的授予还会将其中的伦理问题移转,并进一步加剧专利授权的伦理争议。诚如科学与技术不受限的推进会引发现代化的人造风险,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伦理考察与道德衡量的不足同样也会导致制度风险。然而,基于专利技术产业化运营的利益诉求,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却出现了一系列“伦理最小化”的观点与思路,主张在专利授权审查中回避伦理考察与道德衡量,以保证相关发明创造或技术成果的可专利性,并以专利权的授予为专利技术产业化的持续推进提供必要的支持与保障。
在专利授权审查“伦理最小化”的支持者看来,专利的授权审查活动乃至整个专利制度实践都是“价值中立”的,应保持专利制度的客观性及其单纯的技术色彩,并最大程度地回避其中的伦理问题,使包括专利授权审查在内的全部专利制度实践活动都远离道德层面的非议与论争。(5)参见胡波:《专利法的伦理基础——以生物技术专利问题为例证》,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2期。然而,在实践中,专利授权审查的“价值中立”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只是理论层面上的一种不成熟的假设。这是因为法律制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不能脱离伦理道德的影响。(6)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专利制度当然也并不例外,整个专利制度的演进历程都深受社会伦理环境与道德氛围的制约。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道德传统下,专利授权审查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必定有所差异,那种源于人们对自身理性和对科学技术理性过分自信的“价值中立”观点是脱离现实的。专利授权审查“价值中立”所促成“伦理最小化”无非是科学技术至上论和科学技术万能论等盲目乐观主义情绪的一种不适当的扩散蔓延。(7)参见吴翠丽:《科技伦理:风险社会治理的应对之策》,载单继刚、甘绍平等:《应用伦理:经济、科技与文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
除此之外,专利授权审查“伦理最小化”论者,往往还会以专利授权查审活动对于伦理问题的“有限影响”进行辩护,他们认为发明创造与技术成果的伦理审查只影响到专利授权与否,一项发明创造或技术成果即使通过专利审查获得授权,如若其他法律中有禁止性规定,该专利技术也无法在实践中被予以应用,而如若该发明创造或技术成果因道德原因不被授予专利权,也并不能阻止这一有害技术的实施。(8)参见陈桂荣:《公共健康视域下专利伦理审查机制的问题与对策》,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但是,必须要特别注意的是,伦理审查是专利授权审查制度的社会责任彰显。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其对自然、社会以及对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干预日益深化,相应的技术伦理要求随之同步提高。专利授权审查中对于伦理道德问题的考量无疑也应被高度重视,不能因其效果与影响的有限性就对其予以否定,相反,更应对其予以强化,并在使专利授权质量得以改善的同时,也使专利授权审查中的伦理问题获得应有的规制。(9)See R. Polk Wagner, Understanding Patent-Quality Mechanism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Vol. 157, 2009, pp. 2135-2174.
(二)专利授权审查“伦理最小化”的实践映射
在“伦理最小化”思潮的影响下,伦理审查在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日渐式微。专利法中针对技术伦理问题延展而设置并应在专利授权审查中优先适用的伦理审查机制不断地被人们所怠忽,无论是原则性的公序良俗条款,还是具体性的伦理例外规则,都不能被予以充分的贯彻与适用。尤其是在专利技术产业化运营的巨大利益驱动下,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的“伦理最小化”趋势日盛,不仅专利授权的公序良俗要求被日渐忽略,专利授权的伦理例外规则也被不断突破。
1.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对公序良俗条款的日渐忽略
公序良俗作为民事法律制度中为维系人类社会共同生活而限制法律行为之内容的一般性规范,滥觞于罗马法并为法国、德国民法及其他近世诸民法所承继。(10)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所谓公序良俗,即包括“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两个层面的内容。(11)参见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其中,公共秩序,系指社会之公安与公益;而善良风俗,则难以给出确切含义,应就特定环境下整个民族之意志决定之,不能囿于某一特殊情形。(12)参见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但无论是公序所指称的公共秩序还是良俗所指称的善良风俗,均具有浓厚的国家与社会伦理色彩。(13)参见谢潇:《公序良俗与私法自治:原则冲突与位阶的妥当性安置》,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6期。而这也决定了公序良俗在民事行为与民事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及其在民事法律规范中的最高原则属性。(14)参见杨立新:《中国民法总则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0页。由此,进一步从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框架来看,公序良俗实质上就是在权利产生阶段弥补禁止性规定不足的一项概括性条款,是针对法律行为内容进行的“内容审查”。(15)参见于飞:《民法基本原则:理论反思与法典表达》,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然而,不能否认的是,条款的概括性在很大程度上却也意味着具体内容的不明确性,虽说公序良俗这种不确定的开放性,得使法律能够随着价值理念的发展及社会伦理的变迁而演变进步,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充分彰显出其在适用中不易涵摄的本质属性。(16)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
在专利制度中,以秩序底线和伦理底线为表征、以非特定当事人利益为保护重心的公序良俗原则也同样是制度运行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17)参见于飞:《公序良俗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区分》,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我国《专利法》在“总则”第5条中便确立了公序良俗原则对于专利制度的引领,即明确将不违反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作为专利授权的消极要件。与此同时,《欧洲专利公约》《德国专利法》《瑞士专利法》《日本专利法》《韩国专利法》等诸多国家或地区的专利制度中也都专门设置了类似的公序良俗条款。但是,由于公序良俗内涵的不确定性,这一伦理层面的考量往往缺乏具有可操作的具体标准,因而也就流于形式,并不能真正发挥其秩序底线和伦理底线的效果。而且,以工业应用为基础的传统发明创造及技术成果大多也并不存在太大的伦理道德问题,这也就进一步加剧了实践中人们对于公序良俗条款的忽视。直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第四次科技革命中生物技术的持续发展,以及逐渐开启的具有伦理争议的生物技术专利保护,才使人们意识到了专利授权审查中的公序良俗需要。(18)See Hannah Mosby, Biotechnology's Great Divide: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ent Law and Bioethics in the Age of CRISPR-Cas9, Minnesota Journal of La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19, 2018, pp. 565-606.然而,基于长期以来专利授权审查偏重于对发明创造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等可专利性积极要件的考量,以及公序良俗条款在实践中的形式主义运作,虽有现实需要,公序良俗条款却也难以立刻被予以充分适用。与此同时,加之以新兴技术产业发展中经济利益的巨大驱使,也使人们在趋利本性下诱发了对于公序良俗条款的“选择性遗忘”,进而导致专利授权审查呈现出“伦理最小化”的实践模式。
2.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对伦理例外规则的不断突破
伦理例外规则是为缓解专利授权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规定对特定技术或方法不授予专利权的一种制度设计,其实质上是对违反公序良俗一般性条款情形的一种具体化列举。易言之,专利授权审查中的公序良俗条款和伦理例外规则是一种从一般到特殊的关系,二者分别是对专利授权审查中伦理要求的概括式界定与列举式规定。纵观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专利制度对于专利授权审查中伦理考量的规定,可以发现,除去日本、韩国等公序良俗条款的单一概括式立法,包括《欧洲专利公约》《德国专利法》《瑞士专利法》在内的很多国家或地区的专利制度都在公序良俗条款的一般性规定统领下设置了专门的伦理例外规则,对相关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进行具体列举。我国《专利法》也不例外,在原则性公序良俗条款的之下于第25条规定了科学发现例外、智力规则例外、诊疗规则例外等6种具体的不授予专利权的例外情形。当然,也有相当多的国家在专利制度中并未设置专门的公序良俗条款,仅以伦理例外规则对不授予专利权情形的具体列举来实现对专利授权的伦理考察与道德衡量,例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俄罗斯民法典》(知识产权部分)以及《南非专利法》所采取的就是这样的立法模式。相比之下,公序良俗条款的一般性规定统领下的伦理例外规则无疑是更为合理的立法模式,在确立专利授权审查的一般性伦理要求的同时,也对有违伦理的具体情形进行了明确的列举。(19)参见刘鑫:《“科技向善”倡议下专利伦理评价机制研究》,载《中国科技论坛》2021年第6期。
在各国的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由于对公序良俗条款重视的普遍不足,各种立法模式下的专利授权伦理审查实质上都以具体性伦理例外规则为基础,并无太大差异。唯一的不同,只存在于各国在具体规则中对于伦理例外设定类型与数量的差异。虽然这其中各国的立法设计有所区别,但科学理论与发现、智力活动的规则与方法等关键性的内容都无一例外地被设定为伦理例外的对象。除此之外,还必须要格外关注的是,作为当今世界专利制度先行者的美国,虽未在专利制度中专门设置一般性的公序良俗条款与具体性的伦理例外规则,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对于专利授权审查的伦理限制与道德要求,其在早期实践中由实用性标准下的判例法将有悖公序良俗的发明创造排除。(20)参见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3-44页。早在1817年美国法官便在判例法中将实用性标准解说为“对社会有益的用途,即不能有损道德、健康或者社会良好秩序”。(21)See Bedford v. Hunt, 3 F. Cas. 37 (C. C. D. Mass. 1817) (No. 1, 217).与此同时,相关的伦理例外规则也由判例法所确立,涉及自然现象例外、抽象概念例外、自然产物例外、商业方法例外等。但在后来由于道德判断的主观性以及道德标准的变化性,美国司法实践中逐渐将道德要求剔除出实用性标准,仅要求发明创造具备最小的现实价值即可。(22)参见[美]J·M·穆勒:《专利法》(第3版),沈超、李华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页。例如,其中的商业方法例外已于1998年在轰动一时的“富道银行案”(23)See State Street Bank &Trust Co. v. Signature Financial Group, 149 F. 3d, 1368 (Fed. Cir. 1998).中被废除,商业方法也就此成为了美国专利授权的客体范畴,并随实践发展在判例法中形成了专门的“机器或转换”的审查标准。(24)See In Re Bilski,545 F.3d 943,88 U.S.P.Q.2d 1385 (Fed. Cir. 2008).无独有偶,伴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美国专利授权范围日益扩张,其他的伦理例外也存在被突破的巨大风险。而且,这一情况也并不仅仅存在于美国,专利授权范围增大是当下全球的发展趋势,其他各国法律所明确规定的例外规则也在被不断吞噬,失去了原有的约束效力。例如,对于基因技术的专利授权即开启了生命物质的法律保护,其对诸国专利制度中科学发现例外以及美国判例法上的自然产物例外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25)参见刘鑫:《基因技术专利化的问题、争议与应对》,载《电子知识产权》2021年第8期。而对于人工智能算法或软件的专利授权则往往会陷入对数据算法予以专利保护的漩涡,形成对专利制度中数学算法、智力活动方法、计算机软件等相关例外规则的挑战。(26)参见刘强:《人工智能算法发明可专利性问题研究》,载《时代法学》2019年第4期。
二、新技术时代强化专利授权伦理审查的现实必要性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变革,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并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以及态度,但在它为我们带来巨大社会福利的同时,一系列突破传统伦理准则与道德限制的社会风险也随之席卷而来。(27)See Daniel Berdichevsky, Erik Neuenschwander, Toward an Ethics of Persuasive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Vol. 42, 1999, pp. 51-58.作为科技研发与应用的重要保障机制,专利制度在发挥其促进新技术研发的福利效用的同时,也面临着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制度变革压力。通常说来,一般性的制度适用问题通过法律释义的方式即可克服,但新技术所引发的伦理性问题,对专利制度而言却并不是一个能够轻而易举化解的难题,尤其是在当前深受“伦理最小化”思潮影响的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机制之下,相关伦理问题的解决愈发困难。从生物技术专利授权审查中的生命伦理争议(28)参见肇旭:《生物技术专利授权要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1页。到人工智能自主发明创造专利授权审查中人工智能能否作为“发明人”的伦理讨论,(29)See Erica Fraser, Computers as Inventors - Leg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Patent Law, SCRIPTed: A Journal of Law, Technology and Society, Vol. 13, 2016, pp. 305-333.与新技术相关的各种伦理难题接踵而至,无一例外地都掀起了激烈的社会论辩与学术争鸣。在“专利向善”的伦理目标之下,有关强化专利授权伦理审查的声音也由此不绝于耳。
之所以在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新技术的专利授权审查中会出现严峻的伦理难题,究其根本而言,是由这些新技术在研发与使用过程中所衍生的道德矛盾、价值冲突等技术伦理问题延伸而来。(30)参见庄友刚:《科技伦理讨论:问题实质与理论自觉》,载《观察与思考》2017年第3期。虽说在伦理争议突出的技术领域中,研发工作开始之前便会进行相关的伦理审查以防控技术风险,但是其所能排除的只是诸如“人兽杂交”“人类克隆”等存在明显社会危害或严重伦理冲突的少量部分,而大部分兼具福利效用与伦理挑战的技术研发并不会受此阻滞。如若相关技术成果被提出专利申请,则势必会将原本的技术伦理问题引入到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之中。不仅如此,一旦这些具有伦理争议的发明创造或技术成果通过授权审查被授予专利权,它们的流通速度就会随之加快、传播范围也会随之扩张,相关的伦理问题更会被予以成倍放大。概言之,由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专利伦理难题,归根结底,是不断涌现的新技术中所蕴含的技术伦理问题在专利授权审查中的延伸与扩展,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我们在新技术时代摒弃专利授权“伦理最小化”观念,并强化专利授权伦理审查的现实需要之所在。
(一)新技术自身伦理争议在专利审查中的延伸
对于一项新技术而言,与之密切关涉的伦理议题即在于,该技术能否造福人类、能否保证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和谐相处,相应地,在科研活动中人们也就时刻都面对着“能做什么”和“应做什么”的伦理衡量。(31)参见陈爱华:《科学伦理的哲学审思——基于认识论维度的追问》,载单继刚、甘绍平等:《应用伦理:经济、科技与文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如若该项技术进入到专利授权审查之中,这种“能做什么”和“应做什么”的道德选择也就演变成了“能否授权”以及“如何授权”的一种法律判断、一种政策考量,当然也更是一种伦理抉择。(32)参见刘鑫:《论专利伦理》,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12期。而这种技术伦理争议在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进一步延伸的情况,在当下新技术不断涌现的过程中更是表现得极为突出。尤其是对于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这些伦理争议较为严重的新兴技术而言,一旦专利授权审查被开启,它们原本的技术伦理问题即刻便会转变为可专利性判断中的伦理衡量难题。其中,生物技术专利授权审查中的伦理争议主要体现在权利客体层面;而人工智能生成发明成果相关的专利授权审查伦理难题则主要体现在权利主体层面。为此,不妨分别以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为例,对新技术自身伦理问题在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的延伸过程予以详细阐释。
1.生物技术伦理问题在专利授权审查中的延伸
自基因技术等一系列生物技术产生以来,对相关技术的道德非议就从未停止。从生物技术侵蚀自然秩序所引发的人的“非人化”争议,(33)参见李宏伟:《现代生物技术伦理价值冲突的哲学思考》,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6期。到“人造生命”合成生物“设计”与“重构”过程中关于权利主体、技术标准以及责任承担等方面的伦理诘问,(34)参见李真真、董永亮等:《设计生命:合成生物学的安全风险与伦理挑战》,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年第11期。与生物技术相关的伦理争议此起彼伏。随着生物技术研究与应用的深入,对其进行专利保护的要求日益强烈、相关实践日渐增多,而这也使得专利制度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也越来越复杂。(35)参见曹新明:《知识产权制度伦理学初探》,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诚然,一直以来理论界都认为对生物技术予以专利授权是存在巨大伦理风险的,尤其是其中的基因等生命物质,给予它们以专利保护更是有失伦理妥当性,(36)See Graham Dutfie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Biogenetic Resources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 Earthscan Press, 2004, p.3.但是生物技术开发与应用中的高昂资金投入和巨大市场风险却诱使人们开启了给予生物技术以专利授权的实践尝试。(37)参见李崇僖:《再探基因尃利問題:美國經驗省思》,载《月旦法學雜誌》2014年第1期。虽说对于生物技术而言,专利保护是最为适宜且最为有效的制度模式,却也是伦理问题最为突出的,生物技术开发与应用过程中所凸显出的伦理争论不仅不会有所消减,甚至反而会演变为对于专利制度设计合理性的道德非议。(38)See Anna Kingsbury, Patenting Life: Human Genetics, Ethics and Patent Law, Yearbook of New Zealand Jurisprudence, Vol. 3, 1999, pp.89-116.因此,在给予生物技术成果以专利授权时,促进产业发展并不是评判的唯一标准,还需进行必要的伦理限制,以应对生物技术专利授权审查中的伦理争议。(39)See Emanuela Arezzo, Gustavo Ghidini, Biotechnology and Software Patent Law,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11, p.87.
2.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在专利授权审查中的延伸
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而言,伦理问题的本质即源自其脱离人类控制与干预的自主性,这既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早先技术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同时也更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道德风险之所在。人工智能这种独立自主的工作能力,不仅带来了技术后果的不可预见性问题,同时也引发了技术控制层面的一系列法律挑战与伦理难题。(40)See Matthew U. Scherer, Regul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Risks, Challenges, Competencies, and Strategies, Harvard Journal of Law &Technology, Vol. 29, 2016, pp. 353-400.具言之,人工智能独立自主的运行模式无疑使其具备了替代人类的潜质,尤其是人工智能自主生成发明创造与技术成果的出现,更彰显出其代替人类进行智力创造活动的能力。虽然这其中具有诸多造福人类社会的有益之处,但如若出现人工智能危害人类的情形也势必会造成颠覆人类伦理观念的严重不良后果。随着人工智能生成发明创造与技术成果的日渐增多,给予其专利授权的呼声与诉求也愈发强烈,而人工智能技术运行后果之伦理风险的难以预测和控制的问题,也会进入到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并成为重要的考量因素。(41)参见刘鑫:《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专利法规制——理论争议、实践难题与法律对策》,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但在人工智能生成发明成果的专利授权审查过程中,承担技术后果与控制伦理风险的发明人往往难以识别,专利权的授权却又是由发明人的识别为开端的。(42)See Ben Hattenbach, Joshua Glucoft, Patents in An Era of Infinite Monkey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anford Technology Law Review, Vol. 19, 2015, pp. 32-51.自主进行发明创造的人工智能并不具有主体资格,既不自己申请专利、行使权利,也无法自己承担法律责任以及不利技术后果所产生的社会责任。(43)See Liza Vertinsky, Todd M. Rice, Thinking About Thinking Machines: Implications of Machine Inventors for Patent Law, Bos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Science &Technology Law, Vol. 8, 2002, pp. 574-613.由此,人工智能技术运行中所存在的伦理困境也就完全体现于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之中,并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专利授权审查的伦理难题。
(二)专利授权对新技术中伦理问题的扩展效应
通常来说,一项发明创造在被赋予专利权以前,对于发明人来说往往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而当其通过审查获得专利授权之后,发明创造就具备了以权利形态参与产品流通和市场竞争的能力。(44)See Justin Hughes, The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Georgetown Law Journal, Vol. 77,1988, pp. 287-366.如此一来,发明创造本身所固有并延伸至专利授权审查之中的技术伦理问题,也会随着专利产品的流通而不断扩散,进而形成对于技术伦理问题的扩展效应。技术本身是中立性的,更是盲目性的,单纯的技术探索、发明创造往往只是“实验室里的革命”,即使存在伦理问题,即便对人类有害,也并不能产生实质的影响。而如若这些技术成果、发明创造在“伦理最小化”思潮影响下通过专利审查并被授予专利权,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不仅会将技术伦理问题带入相关市场形成市场风险,更会引发社会性的伦理挑战,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成困扰。
1.专利授权会导致新技术中所蕴含的伦理问题转变为市场风险
作为一项基于市场需要而建立并存在于市场环境中无形财产权制度,专利制度一般被认为是对市场回报机会的一种奖赏。(45)See 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1996, pp.119-122.而对于具体的发明创造而言,专利权的授予则不仅是相关技术成果商品化与市场化的开端,同时也是相关技术研发与应用的产业化起点。易言之,发明创造在获得专利授权后,相关技术产品在一定期限的排他性生产与销售权利的保障下会被更完整、也更安全地投放市场,使发明人收回成本、获取收益的同时,也加快了技术成果的市场流通与扩散,推进产业化进程。(46)参见[苏丹]卡米尔·伊德里斯:《知识产权: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曾燕妮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原本技术成果中存在的技术伦理问题也会随着专利权的授予,附着于专利产品之上,并在专利产品的快速市场流通乃至产业化运营中不断发酵,甚至转变为相关市场运行的伦理风险。以生物技术为例,专利授权无疑可以推动转基因食品和基因药品等先进发明成果的迅速市场化与产业化,但同时也使相关技术中蕴含的伦理问题被引入到市场与产业运营的层面。如若不对其加以充分的伦理衡量,其影响范围则会从技术层面的伦理争议扩大到市场层面伦理风险与安全隐患。(47)参见胡加祥:《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法律思辨——“无罪推定”还是“有罪推定”》,载《法学》2015年第12期。不仅如此,从国际市场来看,对于生物技术相关发明创造的专利授权也将引发更为严重的市场风险。由于生物技术大多为少数发达国家所掌控,赋予这些技术成果以专利权,实质上也就是给予了它们在相关市场上的垄断性地位,并由此形成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权力,相应地,伦理风险与安全隐患也会因这种国际市场结构不平衡性而进一步加剧。(48)参见刘鑫:《专利权益分配的伦理正义论》,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9期。
2.专利授权会致使新技术中所蕴含的伦理问题演变为社会困扰
作为一项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私人财产权制度,专利制度本身就是一种以利益平衡为基础的法律架构,旨在实现激励技术创新和满足社会知识产品供给两种诉求之间的理想平衡。(49)参见黄玉烨:《知识产权利益衡量论——兼论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新发展》,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而专利授权审查则向来都是以私人权利与公共利益间的协调作为第一要旨的。(50)参见云昌智:《诠释全球化下法律伦理与社会利益的平衡之维——张晓都<专利实质条件>之评析》,载《电子知识产权》2003年第10期。易言之,专利授权不仅仅是对私人权益的法律确认,同时也需要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全面地考察与衡量。而技术成果自身蕴含的伦理问题无疑也是社会公共利益考量中的重要内容。虽然如此,原本技术成果中存在的技术伦理问题却并不会在这一社会层面的利益衡量中有所消减,其只是专利授权与否的一个伦理指标。如若相关发明创造或技术成果通过审查并被授予专利权,该发明创造或技术成果本身所具有的技术伦理问题也会随之延展,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并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安全与伦理问题,一旦规制不力,甚至会产生数量巨大且广泛影响的、远远超过个人所能理解和掌控范围、严重威胁健康与安全的公共风险。(51)See Peter Huber, Safety and the Second Best: The Hazards of Public Risk Management in the Court,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85,1985, pp.277-337.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其自主生成发明创造与技术成果的能力使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发明人”的角色,但无论是专利审查机构还是专利司法机关都无法给予人工智能以明确的法律定位。(52)See Ryan Abbott, I Think, Therefore I Invent: Creative Computers and the Future of Patent Law,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Vol. 57, 2016, pp.1079-1126.如若给予这些发明创造或技术成果以专利授权,势必会使其技术本身蕴含的技术后果的不确定性与主体资格的不具备性等伦理难题扩大化,形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制约,带来无法预测的社会风险,使技术层面的道德难题演变为影响社会安全与秩序的伦理挑战。
三、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机制的精细化设计与规范化运作
面对由新技术伦理争议所延展并由“伦理最小化”思潮下公序良俗条款被日渐忽略、伦理例外规则被不断突破所诱发的实践性伦理难题,应在专利授权审查的制度安排中做出回应,完善专利授权伦理审查的相关制度构造,一方面在内容上展开精细化提升,既使公序良俗条款所昭示的内容能够被充分地具体化,不至于再被轻易忽怠,也使伦理例外规则能够与时俱进、动态完善,以自身的及时更新来应对实践的冲击与突破;另一方面在程序上进行规范化安排,通过创设伦理审查专门程序,使伦理审查成为专利授权审查中常态化的运转环节,以此改变目前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对发明创造或技术成果伦理审查的旁落局面,化解专利授权审查中的伦理难题,实现专利授权审查机制对“科技向善”以及“专利向善”等社会伦理道德要求的充分反映与有效保障。
(一)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机制的精细化设计
1.公序良俗条款的具体化阐释
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对于行为或事项进行合法性评定的核心在于,对该行为或事项与社会伦理道德契合程度的判断,即应以合伦理性为标准进行相关行为或事项是否为公众所普遍认同的权衡与检验。(53)参见甘绍平:《伦理学的当代建构》,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版,第416页。但对于具体行为或事项是否符合公序良俗要求的判断,往往并不能仅基于社会的普遍伦理道德观念与规范而有效展开,而需将这些普遍性的伦理道德观念或规范的内容进行具体化,与相关行为或事项的具体场景相结合,并由此映射出社会伦理道德观念或规范在其中的具体表征。
所谓公序良俗内容的具体化,即意味着对于实践中公序良俗原则或条款适用情形的类型化。这既是公序良俗内容具体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处理实践中公序良俗原则或条款适用难题的常用策略。基于公序良俗原则在适用范围上的普遍性,以及在适用中保持本土性和时代性的具体要求,民事法律制度对于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往往采取类型化的策略。(54)参见李岩:《公序良俗原则的司法乱象与本相——兼论公序良俗原则适用的类型化》,载《法学》2015年第11期。因为这样一来,符合公序良俗特征的各种复杂法律关系能被合理分类,使其趋于明确也便于区分,从而使法官依据法律关系的“同理性”对同一类型的案件做出相同或相近的裁判。(55)参见李双元、杨德群:《论公序良俗原则的司法适用》,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3期。与此同时,也使法官在衡量公序良俗的过程中,能够尽量抛弃其主观好恶等个人因素,从而最大限度的实现相关案件裁判的伦理正义。(56)参见戴孟勇:《论公序良俗的判断标准》,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3期。在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公序良俗条款类型化的具体表现虽与民事法律活动中有所不同,但类型化对于专利授权审查中的公序良俗条款而言也是实现其概念与内涵具体化的重要手段与必要策略。通过对实践中专利授权审查公序良俗要求的类型化区分,不仅可以使公序良俗条款所包含的内容被更为具体地界定,也能为专利授权审查实践工作的具体运行提供必要的参考与依据。
基于专利授权审查中伦理问题的技术原生性,在对专利授权审查中公序良俗条款进行类型化的过程中也应以特定技术的伦理表征为基础进行类型划分,而不能不加思索地依据民事活动中以具体事项标准展开公序良俗原则类型化的模式,进行专利授权审查中公序良俗条款的具体化。虽说专利权的授予是具有技术普适性的,只要符合专利授权要求的发明创造或技术成果都能获得专利授权,并无技术领域层面的直接差异。但必须承认的是,不同技术领域中发明创造或技术成果生成的具体方式与难易程度并不相同,因而它们对专利授权的基本立场与诉求也各不相同,尤其是在研发投入和周期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更会使不同技术领域中发明创造或技术成果的专利授权范围存在一定区别。(57)See Emanuela Arezzo, Gustavo Ghidini, Biotechnology and Software Patent Law,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11, pp.9-10.相应地,专利授权审查中公序良俗条款的具体含义与作用方式在不同技术领域的发明创造或技术成果之上也有所差异。例如在传统的机械工业中,发明创造与技术成果大多是机器与装置的存在,公序良俗条款对其的要求是不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而在伦理争议较为突出的新兴技术领域中,以公序良俗原则为基础的伦理审查无疑要求更高,公序良俗条款的内容也须更为详细的具体分类。在生物技术领域中,公序良俗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不违反人类生殖道德、不危害国家生物安全、不侵害个人生物信息三种类型;而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而言,公序良俗的具体内容则涉及人工智能不扰乱人类社会秩序及不危害人类生命安全两个层面。此外,在其他技术领域中也是同样,应依照公序良俗内容类型化的一般策略,从不同技术领域的特征与伦理诉求出发,以不同的技术类型为标准实现公序良俗条款之不确定概念与内容的具体化。
2.伦理例外规则的动态化诠释
从基因技术专利到商业方法专利,专利授权审查中的科学发现例外与商业方法例外在技术与产业的利益驱动下被逐一攻破。不仅如此,未来对于人工智能算法的专利授权也势必会造成对数学算法例外、智力活动方法例外的严重冲击。为此,展开专利授权伦理审查中伦理例外标准的动态化设计无疑是很有必要的,不仅有助伦理例外规则的完善,也更能为专利授权伦理审查工作的有序进行提供有力保障。
专利授权审查中伦理例外标准的动态化运作,实质上就是在伦理例外规则所列举的具体项目之下,结合新技术及相关产业发展的情况对这些项目进行的一种定期性的解释与完善,使专利授权审查中伦理例外规则能够更好地与实践相契合。科学技术飞速的更新换代,针对其中伦理问题而在专利授权审查中设置的伦理例外规则也应与时俱进,通过采用定期更新的动态性伦理例外标准的方式予以回应。诚然,在基因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剧烈技术革命面前,伦理例外规则不断呈现出被突破甚至颠覆的情形,但必须注意这些技术变革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其对规则的突破与颠覆也不是即刻发生的,而是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技术变革的发展过程中,一开始并不会形成对专利授权审查中伦理例外规则的完全突破,只会对其构成一定的冲击。如若在此时就以动态性的伦理例外标准与之相匹配,专利授权审查中伦理例外规则的效用便可得以有效保障,即使最终发生技术上的质变并形成对原有例外规则的突破,在不断更新的动态性的伦理例外标准的保障下,人们在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也不会因此手足无措,而对于伦理例外规则的完善也会提供更为全面的参考与借鉴,从而实现伦理例外标准动态性诠释对相关规则创造性作用。(58)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页。
实践中,对于专利授权审查中伦理例外标准的动态化运作,应根据具体伦理例外项目的特点,并结合相关技术与产业的发展现状,由专门机构以“细则”“指南”或“建议”的形式进行定期性的规则释义与内容更新。在具体的标准制定中,应充分考量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发展特点与未来趋势,采用逻辑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多种法律解释方法对相关规则进行释义。当然,对这些伦理例外规则的解释也应在合理的范畴之内,不能超越规则文义之“预测的可能性”。(59)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第2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页。不仅如此,基于科学技术的飞快发展,伦理例外标准的更新周期也应相应缩短,使之真正的“动”起来,将动态化运作落到实处。具言之,对于专利授权审查中伦理例外规则的定期性解释,亦即动态性伦理例外标准的建构,主要有两种路径可供选择:一是以专利授权审查中的伦理例外规则中所列举的具体项目为基准,分别从科学发现例外、智力规则例外、诊疗方法例外等具体的例外类型出发,分析各个例外类型在适用中存在的技术风险与实践挑战,为它们的适用设置详细的标准,并定期予以完善;二是专门以特定技术或产业所带来的伦理问题为基础,以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与产业划分为标准探究对于伦理例外规则的冲击及其潜在的突破风险,制定以诸如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特定技术或产业为专题的伦理例外标准,并根据技术或产业的革新而不断更新。其中,前者是从专利制度中伦理例外规则的具体项目类型出发的,是一种对法律规定适用的具体解释,在实践中往往会以“法律实施细则”的形式存在;而后者则是从特定技术或产业的划分出发的,是一种对技术或产业问题的法律释义,在实践中大多表现为“特定技术与产业的专利授权审查指南或建议”,例如“生物技术专利授权审查指南”“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审查的指导建议”等等。二者在关注重点上各有侧重,在具体内容上也有所交叉,但在实践适用中却并不冲突,两种路径的并行无疑会使专利授权审查中的伦理例外标准更为全面、更为具体,也更有利于指引实践,从而充分发挥专利授权审查中伦理例外规则的现实效用,彰显专利制度的伦理理性。
(二)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机制的规范化运作
1.在程序运行顺位上将伦理审查机制设定为实质审查启动的第一步
通常而言,一项发明专利申请被受理后即进入到偏重于形式的初步审查环节,通过初步审查后专利申请即被公开,并在特定时间内须经申请方才启动实质审查,并同时从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等可专利性积极要件,以及不违法反公序良俗、不触及伦理例外等可专利性消极要件两个层面展开对专利申请的实质性审查,唯有积极和消极要件都能满足的申请,才会被最终授予专利权。在当下“伦理最小化”倾向的影响下,专利实质性审查中的可专利性积极要件日益成为专利授权与否的核心标准,伦理性的消极要件逐步失去了其应有的效力。虽然这样能充分满足新兴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诉求,却往往会引发深远的道德困境。正如专利授权审查中缺少与科学界互动,会由技术水平差距而引发专利质量问题一样,(60)See Beth Simone Noveck, Peer to Patent: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Open Review, and Patent Reform, Harvard Journal of Law &Technology , Vol. 20, 2006, pp.123-162.专利授权审查中对伦理道德问题的关注不足,也会因缺乏道德衡量而造成专利技术的伦理争议。为此,应改变专利实质审查中可专利性积极要件与消极要件的平行运作模式,提升公序良俗与伦理例外等伦理审查的程序顺位,将其设置为实质审查的第一步,使实质审查中的可专利性消极要件恢复其应有的效力,避免专利授权审查中爆发出不应有的伦理道德危机。
提升公序良俗与伦理例外等伦理审查的程序顺位,将伦理审查设置为实质审查的第一步,即以公序良俗与伦理例外等消极性的伦理考察要件作为专利实质审查的第一道门槛,如果不能跨过这道门槛,实质审查就会停止,相应的专利申请随即便会被予以驳回,而不能进入到下一个审查流程。(61)参见赵晶:《专利审查过程中“伦理审查”之初探——由两件明胶专利引发的思考》,载《中国发明与专利》2013年第3期。申言之,在程序运行顺位上将伦理审查机制设定实质审查启动的第一步,实质上就是使专利授权审查中特殊性的伦理性审查条款,相比于一般性审查条款的优先性得以在程序层面被予以充分实现。这既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法律效力位阶原理的重要践行,也是对专利授权审查中伦理审查程序的有效完善,在改变实质审查中的可专利性消极要件被日渐忽视之实用主义错误的同时,也使专利授权审查中的伦理难题得到有效应对。
2.在程序运转方式上以价值衡量标准展开对专利申请的伦理审查
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机制的规范化运作,不仅意味着伦理审查机制在专利实质审查中程序运行顺位上的优先性,还须在程序运转方式上对专利申请中的伦理审查进行标准化与等级化设定。这是因为对于事物或行为的伦理评判本身就会由具体实践情形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化的价值等级顺序。(62)参见[德]尼采:《论道德的谱系》,赵千帆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54-55页。当代著名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对于伦理正义两个原则的归纳中,将确定与保障基本的平等、自由作为第一条正义原则,利益、财富的平等、合理分配则是居其下位的第二条正义原则。(63)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0-61页。在专利授权伦理审查中,伦理正义的实现也势必存在着价值衡量上的等级顺序,因而为保障对专利申请所进行伦理审查的充分性与科学性,有必要以其中各种伦理价值的等级顺序为基础设置专门的伦理衡量标准,力求在程序运转方式上达到专利授权审查应有的伦理理性要求。
不同于专利权配置中公平与效率间左右摇摆的伦理价值取舍,在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安全与秩序的价值追求才是最趋近于正义的道德选择。(64)参见刘鑫:《我国专利制度的伦理挑战及其应对策略》,载《深圳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易言之,在对专利申请的伦理审查过程中,安全与秩序是最为核心的伦理要求。由此,在设计专利授权伦理审查的价值衡量标准时,也应以人类社会的安全与秩序为基点而具体展开。对于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体而言,社会的安全与秩序是保障生存、实现发展的根本前提。因而,以安全与秩序为导向的专利授权伦理审查价值衡量标准,在本质上无疑也是以保障个体在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为宗旨。基于此,应以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实践需求为出发点,展开专利授权审查中伦理价值衡量的标准设计,在无害于个体生存的基础上,追求有益于个体发展的更高等级的伦理价值,并通过对人类生命健康、社会稳定有序等具体考察要素进行价值衡量的标准等级排序完成相关程序的合理设置。
根据专利授权伦理审查中从对人类生存无害到对人类发展有益的价值位阶,可以创设出四项价值衡量的具体标准,按照价值等级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无害于生命健康、无害于生态环境、有益于国家安全及有益于社会进步。其中,前两项是关涉人类生存的、最为基础的价值衡量标准,重点关注人类根本生命健康权益的维护,以及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实践中主要涉及食品、药品等与公关健康相关专利申请的安全性与稳定性评判,以及专利申请中生态环境危害性问题的预防与制止等具体情景下的价值衡量;后两项则是事关人类发展的、极为关键的价值衡量标准,着重考察专利申请对于国家利益与社会公益的影响,并以其对于国家安全与社会进步的推进效果作为价值衡量的实践标准。毋庸置疑,由无害于生命健康、无害于生态环境到有益于国家安全、有益于社会进步的顺序,依次展开对于专利申请的伦理价值衡量,是相对合理且相对全面的程序设计。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无害于生命健康、无害于生态环境、有益于国家安全、有益于社会进步这四项价值衡量标准还相对概括,在实践中应根据伦理审查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在每一价值等级的衡量标准内部展开进一步细化与完善,并形成一系列的次级衡量标准,从而在专利授权审查中建构起更为详尽,也更具可操作性的伦理价值衡量标准。
3.在程序运作机构上建构起体系化的专利授权伦理审查组织框架
为实现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机制的规范化运行,仅仅明确程序顺位、设置价值衡量标准还远远不够,尚须在此基础上推进道德衡量机构的体系化。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德衡量机构的体系化是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机制有序运行的基本条件,也是伦理审查工作常态化运转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只有设置了健全的道德衡量机构体系,才能确保伦理审查机制被作为专利实质审查启动的第一步予以开启,也才能保证对于专利申请伦理审查的价值衡量由专业的机构和人员负责开展,从而使伦理审查能够真正成为专利授权审查中固定环节,并使其能够真正在实践中常态化地有序运转。
在专利授权审查中,对于专利申请中发明创造的伦理审查,从专利制度的时间结构来看,其无疑是一种基于专利制度伦理要求而进行的事先道德衡量;但就发明创造生成的时间结构而言,这一过程却是对于技术成果的一种事后道德评价。基于此,在专利授权审查中,专门化的道德衡量机构在形式上主要有从专利制度本身出发的事先道德衡量和以技术伦理问题为基准的事后道德评价两种模式。其中,从专利制度本身出发的事先道德衡量模式,即是在专利行政审查机关中负责实质审查的各个技术审查部门内部设置专门的道德衡量机构,由专职人员对进入实质审查的专利申请进行第一步的伦理审查;而以技术伦理问题为基准的事后道德评价模式,则是仿照生物医药等研究领域中对相关技术研发或实验进行伦理审查之伦理委员会的机制设计,在专利行政审查机构之外,设置由专业人员所组成的伦理委员会,并由其进行对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程序开启前的道德评价。(65)参见张金钟:《生物医药研究伦理审查的体制机制建设》,载《医学与哲学(A)》2013年第5期。毋庸置疑,前者是较为高效的模式选择,但内部性的机构设置也注定了其缺乏对于伦理疑难问题的应对能力;而后者虽能通过专业化的道德考察给出合理的伦理判断,却会带来专利授权伦理审查的成本增加与效率下降。鉴于此,为使两种模式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缺点获得最大限度地规避,在体系化道德衡量机构的具体设计中,应尝试将二者有机融合,形成以内部机构伦理考察为主、外部伦理委员会伦理评判为辅的专利授权审查伦理审查机构体系。
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机构体系的具体安排与运行架构如下:进入实质审查环节的专利申请,一般由专利行政审查机构中负责实质审查的各个技术审查部门内部设置的道德衡量机构进行伦理审查,如若发现专利申请中存在初步审查中未能完全筛除且相对较为明显的对于伦理原则的违背,直接驳回该申请;如若专利申请中并不存在与专利制度伦理要求相悖的情况,则应将该专利申请推向实质审查的下一环节。但如若专利申请中存在重大伦理争议,内设性道德衡量机构难以抉择,则应将该申请递交给外部的相关伦理委员会进行更具专业性的伦理评判,首先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展开分析讨论并给出专家意见,在此基础上还应将专家意见公开披露并进行社会听证,使社会公众能够充分参与到涉及重大伦理争议的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活动之中。经过社会听证后,伦理委员会如若给出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制度的伦理要求最终意见,专利行政审查机构则驳回该申请;而如果伦理委员会最终认定该申请符合专利制度的伦理要求,则由专利行政审查机构开启对该申请进一步的实质审查。如此一来,通过内设性道德衡量机构与外部性伦理委员会的合理分工协作,便可从机构体系层面上完成对专利申请伦理审查的运行架构设计。但在实践中,要想切实保证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有效进行,还须在机构体系有序建构的基础上,对内设性道德衡量机构和外部相关伦理委员会的具体安排予以进一步明确,并以此真正实现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机构的专门化设置与体系化运转。
四、结论
作为专利制度运行的起始环节,专利授权审查与技术创新之间是存在循环影响的,技术的进步促使了专利授权审查机制的演进,而发明创造经过审查后的专利授权则是技术发展与革新的一种指征。(66)参见文家春:《专利审查行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载《科学学研究》2012年第6期。在这其中,发明创造或技术成果上所存在的伦理问题,往往也会延伸至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之中,并嬗变为制度运行层面的伦理难题。而这也正是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伦理难题的本质来源。一旦饱含伦理争论与道德非议的那些发明创造或技术成果通过审查被授予专利权,伦理难题也就不再是制约专利授权审查机制运行的技术伦理问题,而会演变成影响范围更广、强度更大的市场风险与社会困扰。然而,为适应专利技术产业化发展需要,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却出现了以清除技术伦理阻碍为目的的“伦理最小化”思潮,致使相关的伦理难题不仅得不到有效遏制,甚至还呈现出不断蔓延的趋势,并在具体制度层面映射为公序良俗条款的效力迷失与伦理例外规则的界限混沌,突出表现为人们在实践中对公序良俗条款的日渐忽略,以及对伦理例外规则的不断突破。为此,有必要强化伦理审查在专利授权审查中的重要地位,首先应在伦理审查内容上做精细化提升,既要从不同技术领域的特征与伦理诉求出发,参照公序良俗内容类型化的一般策略实现专利授权审查中公序良俗原则具体化,也要积极推进专利授权审查中伦理例外标准的动态化,以新兴技术的本质特征与运行方式为基础对伦理例外规则进行适当且及时的解释,并根据实践中伦理例外规则所受到的冲击与突破,对伦理例外规则中的具体内容与标准进行定期的修正与完善。在此基础上,还应从程序层面入手,将伦理考察机制设定为实质审查启动的第一步,以价值衡量标准化的模式展开对专利申请的伦理审查,并逐步建构起以内部机构伦理考察为主、外部伦理委员会伦理评判为辅的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机构体系,使伦理审查成为专利授权审查中常态化的运行环节,确保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机制的有序运转,从而实现“专利向善”的制度伦理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