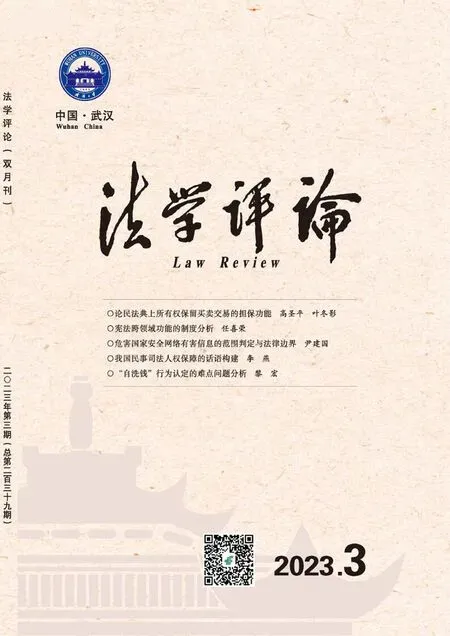清代法典编纂理念之沿革
——以刑典为中心的考察*
2023-07-31黄雄义
黄雄义
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2页。中华民族历来有着浓厚的尚典传统和丰富的编典实践。回顾史上诸朝,国家强盛往往同法治相伴而生,是为“必有一代之典,以成四海之治”。(2)《大明会典·御制大明会典序》。满清虽系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大一统政权,但在法典编纂上有着不绌于前世的执着与热忱。尤其是其刑典,远绍唐律,近承明律,创律例合编之体例,清末之修又兼融西法而开启中华法制近代化之路,“是故论有清一代之刑法,亦古今绝续之交也。”(3)《清史稿·刑法志》。终清一朝,刑典经历了多次大型编纂。每一次编纂,对先圣前作多有传袭,在体例内容上又有新的变化。这般“变”与“不变”,须归因于法典背后繁复的理念更迭。由不同帝王主导的法典编纂,在理念上虽因同一王朝的共质性和连续性有着诸多肉眼可见的一以贯之,但也存在或多或少之差异。只不过相较于刑典渊源、律例关系等内容的备受青睐,编纂理念的演变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4)对于清代刑典之编纂理念,大多是关注清末修律时的理念巨变,只有少数成果涉及到顺、康、雍、乾四朝的刑典编纂理念及其流变。因此,本文拟通过缕析清代刑典的数次编纂,对个中核心理念钩玄提要,以冀对把握清代刑典的形成流变规律、总结中国古代法典的编纂经验乃至启示当代法典编纂事业之功成有所助益。
一、顺治律:效法明律以应急
顺治四年,清廷颁布《大清律集解附例》,即“顺治律”。这部法典是清朝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具有“开基立国”的特别历史意义。它的制定历时数载,先后经过了多番讨论与磨勘,正如沈家本所言:“是此书经始于二年,校定于三年,刊成则在四年也。”(5)(清)沈家本:《寄簃文存·顺治律跋》。即便如此,顺治律的完成速度总体上是相当之快的,这得益于背后核心编纂理念的推动。它从一开始就切实贯彻了“效法明律以应急”之意,是满清统治者为了应对开国之初稳固统治的迫切之需而无奈仿照明律制定的一部专制刑典。
顺治律的“应急”性,需要结合顺治初年国家所处的历史境遇来审视。清人入关之后,在治国理政层面面临着多重领域的不同乱象。择其要者,主要包括政治乱象、社会乱象和军事乱象。就政治乱象而言,彼时的政治时局明波荡漾、暗流涌动,满族虽定鼎燕京并祭告天地以绥中国,但要在根本上取得正统的统治地位仍存在难以突破的无形壁垒。中国古代历来存在一种“华夷之辨”的族群观,“戎夏不杂,自古所诫”(6)《唐会要》卷五十六。说的即是此理。这一观念在政治统治上体现为“华夷分治”,刻骨铭心般地将“华”与“夷”置于两种截然不同的位置。明末清初的鸿儒黄宗羲有言:“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7)(清)黄宗羲:《留书·史》。黄氏将“华”与“夷”的关系,较之于“人”与“兽”,其对满清的态度可见一斑,关键这代表着很大一部分汉人的真实想法。因此,“当满族入关建立清王朝之际,它面临着中国历史上有史以来最严苛的华夷之辩的政治文化背景”,(8)白文刚:《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8页。它所代表的“以夷统华”,可以说是对汉人族群自尊的踩踏蹂躏。就社会乱象而言,明末本就罹患天灾,战争频仍进一步加剧了清初的社会混乱和国之凋敝。彼时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客观地记录了其所闻所见。葡萄牙传教士孟儒望在中国副省的年信中写道“上帝要惩罚他们”,“数不清的人们忍饥挨饿,世风腐化堕落,瘟疫肆虐整个王朝,饿殍遍野。残忍的匪徒蜂拥而起,无恶不作,他们抢夺一切有用的东西,吞食一切可吃的东西。人们举家乞讨,四处流浪,眼前遍布的死亡景象使他们感到晕眩和震惊。”(9)[美]柏里安:《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毛瑞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页。百废待兴,急需加强国家治理以复原正常的社会秩序。就军事乱象而言,顺治帝虽迁都北京形成一统山河之势,但在全国范围内仍广泛存在南明军队、农民军等多股敌对的军事势力。这些乱象之间彼此杂糅互合,形成了一股考验满清统治能力的“急流”。稍有不慎,满清积数代之力所致的不世之功即可能谈笑间灰飞烟灭。
王朝更迭之际,面对种种乱象所形成的“急势”,由新朝加速定律是一种颇为有效的破局之道。刑律的颁布,既可以宣示新政权之诞生,亦可借其构筑新的统治秩序,是为“天下之程式”。(10)《管子·明法解》。顺治初年,从中央到地方,有很多深谙国家治理之道的汉臣纷纷上书请求定律。顺治元年五月,顺天巡按柳寅东奏请安民,指出:“民值乱离之后,心志彷徨。……宜速定律令,颁示中外,俾民不敢犯,而祸乱自清矣。”(11)《顺治朝实录》卷五。同年八月,刑科给事中孙襄条陈刑法四事,其中之一就是定刑书:“刑之有律,犹物之有规矩准绳也。今法司所遵,乃故明律令。就中科条繁简、情法轻重,当稽往宪、合时宜,斟酌损益,刊定成书,布告中外。”(12)《顺治朝实录》卷七。顺治二年二月,刑科都给事中李士焜又奏言:“古帝王制律,轻重有伦,情罪允协。今者律例未定,止有杖决二法,重者畸重,轻者畸轻。请敕部臣早定律法,务期援古酌今,详明切当。”(13)《顺治朝实录》卷十四。又有原任淮扬参议道的杨槚奏言:“又立国之初,定律为先。乞敕法司衙门,酌古准今,按罪定刑。”(14)同前注。同年五月,福建道试监察御史姜金允奏言:“明慎用刑,重民命也。我朝刑书未备,止用鞭辟。……请敕部速行定律,以垂永久。”(15)《顺治朝实录》卷十六。这些奏疏其实主要释放出三条关键信息:其一,新朝根基不稳,社会处于一种动乱状态,各地已滋生出很多犯罪行为;其二,要解决动乱问题,必须抓紧定律,“速定”“早定”“速行”等语,凸显出事之急切;其三,加速定律有一条捷径,那就是效法暂用的明律,这是“援古”“酌古”暗含的题中之义。“说白了,迅速制定新律,不过是全盘接受明律的另一种表达而已。”(16)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24页。
对于臣下关于定律的建言,原本对主政中原就处于懵懂状态的满清统治者基本保持了信任和支持的态度,并确立了“效法明律以应急”的核心编纂理念。这也是他们为了获得真正的政治认同“以建万年不拔之业”而必须采取的法制策略。早在顺治律颁布之前,顺治帝和摄政王多尔衮就已明令暂用明律。“世祖顺治元年,摄政睿亲王入关定乱,六月,即令问刑衙门准依明律治罪。”(17)《清史稿·刑法志》。同年十月,顺治帝在回复刑部左侍郎党崇雅时亦强调:“在外仍照明律行,如有恣意轻重等弊,指参重处。”(18)同前注。对明律的适用,不仅有利于为司法戡乱提供法律依据,也为满人熟悉刑典的基本结构和整体内容提供了契机。在正式编纂刑典的过程中,顺治帝与多尔衮又多次申明“效法明律”的理念。顺治元年八月,“摄政王谕令法司会同廷臣详绎明律,参酌时宜,集议允当,以便裁定成书,颁行天下。”(19)同前注。顺治二年,顺治帝对刑科给事中孙襄关于“修律但宜参酌同异,删除繁冗,不必过为纷更”(20)《顺治朝实录》卷十六。的意见表示认可。顺治三年五月,顺治帝在《御制〈大清律〉原序》中再度强调了定律的理念,即“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21)《大清律例·世祖章皇帝御制大清律原序》。种种迹象都表明,清廷自始就以明律为样板,整个定律的过程也是在“详译明律”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从顺治律的制定时间和具体内容来看,也切实表明在编纂过程中深入贯彻了“效法明律以应急”的理念。满清在入关之前的立法经验极其匮乏,是如顺治帝自认的“俗淳刑简,所着为令,鞭扑斩决而已”(22)《清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五。。其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制定出一部体例完整、内容齐备的刑典,既表明当权者对这部刑典有着急切的需求,也说明其必定“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充分利用了既有的汉族刑典。查顺治律的体例结构、律文内容,相较于大明律,仅删除、移动、微调、增加了个别条款。其中,删者如“漏用钞印”“钞法”“伪造宝钞”;移者如“漏泄军情大事”“信牌”;调者如“蒙古色目人婚姻”改为“外番色目人婚姻”;增者如“边远充军”。时人对此知之甚明,“大清律率依明律,如云依大诰减等,则明初有大诰,国朝未尝有大诰,宜改正”,(23)(清)杭世骏:《订讹类编续补·义讹》。“且夫大清律者,盖从大明律”。(24)(清)黎元宽:《进贤堂稿·理筠绪录序》。甚至有人断言:“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25)(清)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康熙二十八年,刑部尚书图纳在题本中亦曾坦承:“至若《大清律》一书所载诸事,有仍袭前代之旧文而于本朝之法制绝不相蒙者,如群王、将军、中尉亲自赴京者治罪等项,其类尚多。”(26)(清)吴坛:《大清律例通考·奏疏》。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来看,顺治律整体照搬大明律无疑,实乃大明律之翻版。
二、康熙则例:因时制宜以求治
顺治律的固有弊病,注定其难以“垂之奕世”,“子孙世世守之”(27)《大清律例·世祖章皇帝御制大清律原序》。终究只是虚浮之言。及至康熙年间,面对刑事司法乃至社会时势的显著变化,顺治律滞后的缺陷被无限放大,修律已然势在必行。顺治十八年,“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详考太祖太宗成宪,斟酌更定,汇集成书”;(28)《康熙朝实录》卷二。康熙七年,“命刑部酌定见行则例,详晰分款,陆续进览”;(29)《康熙朝实录》卷二十六。康熙九年,“命大学士管理刑部尚书事对喀纳等将律文复行校正”;(30)同前注。康熙十八年,“特谕刑部定律之外,所有条例,应去应存,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详加酌定,确议具奏”;(31)同前注。康熙二十八年,“特交九卿议,准将现行则例附入大清律条”。(32)同前注。然修律活动虽频,但终康熙一朝始终未能重新颁行律典,只是刊刻通行了《刑部现行则例》。鉴于已有将《刑部现行则例》编入刑典的实际行动,条例后来也发展成刑典的重要构成部分,故仍将其视为刑典编纂的一项重要成果。相较于顺治律的“效法明律以应急”,《刑部现行则例》的编纂理念已有明显变化,它更注重法的适应性,追求立足于客观实际,是为“因时制宜以求治”,是清代立法从简单搬用明律走向以本朝实际为依据的起点。(33)参见郑秦:《康熙现行则例考——律例之外的条例》,载《历史档案》2000年第3期。
康熙帝关于修法的圣谕,深刻体现了“因时制宜”的基本理念。康熙十八年,康熙帝在修例时曾明确强调:“国家设立法制,原以禁暴止奸,安全良善,故律例繁简,因时制宜,总期合于古帝王钦恤民命之意。”(34)《康熙朝实录》卷八十四。此谕清晰直接地呈现了皇帝本人的立法思想,那就是国家法制必须要因时制宜。更深而言,亦与钦恤民命高度契合。“民命”时有改易而非一成不变,若要恤民命,就应在国家法制层面不断调整。在同一道圣谕中,康熙帝对于复设条例以及修改条例的原因的阐释,也充分体现了“因时”之义。“向因人心滋伪,轻视法网,及强暴之徒,凌虐小民,故于定律之外复严设条例,俾其畏而知儆,免罹刑辟。乃近来犯法者多,而奸宄未见少止,人命关系重大,朕心深用恻然。其定律之外所有条例,如罪不至死而新例议死,或情罪原轻而新例过严者,应去应存,着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详加酌定,确议具奏。”(35)同前注。也就是说,之前增设《刑部现行则例》是因为当时社会治安差,必须用严法来训儆暴徒;而今重新酌定条例,是因为近来犯法作乱的人较多,基于人命关天的考量而适当损益。前后修例都是基于具体社会情况。康熙二十三年,在纂修大清会典时,又谕:“逮朕御极以来,恪遵成宪,率由弗渝。间有损益,亦皆因时制宜,期臻尽善。俾中外群工,知所禀承,勿致陨越。”(36)《康熙朝实录》卷一百十五。言下之意,他恪守祖宗成宪,对律例的每次修改都希望完善先祖之制,是出于因时制宜的考量。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制定和修纂《刑部现行则例》。及至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已走至人生最后关头,他借亏空钱粮一事晓谕诸臣,总结了六十余年来的治国经验,其中一条就是:“御极以来,尝思事多变易,皆难预定,惟宽平公正、因时制宜,一切未尝预执已见。”(37)《康熙朝实录》卷二百九十九。这番自我总结表明,自康熙帝临御天下始,都始终秉持“因时制宜”的理念。
相较于顺治律的“应急”,这一阶段在立法上的“因时制宜”更多为了“求治”。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根本还是在于国初乱象的渐趋消散以及政权的日益稳固。如果说,顺治帝“没有作出多大变化地沿袭了亡朝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以系统的方式促进了他们自己的第一流精英人物的出现”,从而有力地解决了入关之后面临的一系列急迫性问题;那么康熙帝则是初步“实现了他们最珍视的愿望,消除了怀疑的气氛以及在中央政权与地方官吏(已亡王朝曾深受其害)之间的严重分离”,使得统治重点从“暂时性地稳局”转移到“长久性地安定”上来。(38)参见[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9页。康熙帝多次提及自己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宏图大愿。诸如“务使物阜民安,政成化洽,以庶几于古帝王协和风动之治”(39)《康熙朝实录》卷四十一。“国家致治,首在崇尚宽大,爱惜人才。俾事例简明,易于遵守,处分允当,不致烦苛,乃符明作惇大之治”(40)《康熙朝实录》卷四十三。等语,皆体现了其求天下大治之决心。无规矩不成方圆,若要“求治”,必先依赖于法制。而法制秩序之构筑,通常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预设成法,追求“万世不易之典”和“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一种是因时立制,世轻世重,追求“淡妆浓抹总相宜”。相较于第一种方式的绝对固化,因时立制在自由度和灵活性方面无疑更具优势。它讲求根据背景时机和客观需要来立法,更能调和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的矛盾以实现长治久安。
《刑部现行则例》的体例和内容,亦都呈现出鲜明的“因时”特色。从体例上来看,其门类划分虽仍遵循着“名例、吏、户、礼、兵、刑、工”的基本顺序,但未将这些作为大类名目(如吏律、户律、刑律),而是将里面的具体构成部分作为名目,如“职制”“公式”“户役”“田宅”“婚姻”“仓库”。每一名目下设的条例,也不受律文的限制且有自身的专属题名。如,“名例”之下有“十恶干连不赦”“年幼免流”“反叛奴仆入官”等条例。“有清一代,大概只有《则例》中的条例是每条皆有名称(或标题)的。”(41)苏亦工:《康熙朝〈刑部现行则例〉的修颁时间、传本及特色》,载《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3期。这样的设计既便于司法适用,也便于随时删改修纂。从内容上来看,很多条例均系因时而设。一方面,有大量因司法案件所修纂的条例。如,“反叛奴仆入官”例,由“刑部将叛犯侯满英家仆张兴等交送总管内务府等因具题”而奉旨修定。(42)沈厚铎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丙编第三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8页。另一方面,不再局限于明律明例,而是增添了诸多满族特色。既设计了“旗下徒流折枷号”“旗下人入官”等诸多与满人旗民相关的条例,亦使用了“固山大”“管旗”等大量的满文术语。关键还在于,《刑部现行则例》的内容和体量并非恒定,它的产生、发展乃至消亡仍严格遵守着“因时制宜”的基本原则。康熙十九年正式颁行之后,仍时有新例产生,(43)光绪年间曾任刑部尚书的薛允升对《大清律例》中的条例来源进行了逐一考证,其中不乏康熙十九年后所定之条例。如,康熙四十八年,基于宁古塔将军题发遣人犯骚达子在配打死齐兰保一案,就产生了新例,附于“徒流人又犯罪律”之后。是为雍正帝所说的“有未经校刻者”,(44)《雍正朝实录》卷三十四。“的确具有‘因时著定’的特点”。(45)参见沈厚铎:《康熙十九年〈刑部现行则例〉的初步研究》,载韩延龙主编:《法律史论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44页。客观而言,志在因时制宜的《刑部现行则例》,有力规范了清初的社会秩序、推动了国家治理高效化,也为后来的律例合编奠定了基础。
三、雍正律:析异删繁以画一
“如果说康熙修律开启了清律从基本承袭明律到自我创制和发展的转型,那么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雍正律,则无疑是这一转型的阶段性成果。”(46)姚宇:《康熙四十六年修律进呈本的发现及初步研究》,载《清史研究》2021年第5期。历来以勤政著称的雍正帝在临御之后,“绍守丕图,深怀继述”,(47)《大清律例·世宗宪皇帝御制大清律集解序》。深感刑狱治法之重,毅然决定继续康熙年间悬而未果的修律工程。雍正元年八月,雍正帝“乃命诸臣将律例馆旧所纂修未毕者,遴简西曹,殚心搜辑稿本进呈”。(48)同前注。修律臣工在既有修律成果的支持下,于雍正三年进呈成稿,后于雍正五年刊行。相较于顺治律和康熙《刑部现行则例》,雍正律的核心编纂理念有了新的变化,即“析异删繁以画一”。它实质上是对顺治律和康熙则例的系统全面梳理,聚焦解决律例彼此抵牾和文字表达繁冗的问题,希冀通过内容统一化和形式简约化的双重升华,实现刑典整体“画一”的核心目的。
“析异删繁以画一”编纂理念的确立,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在着手制定雍正律时,清帝国的刑典其实已经存在前后不一、繁简失序的严重弊病。雍正元年正月,雍正帝在御极之初即谕令按察司:“朕惟国家考定律例,所以弼教,非以厉民,是故严立刑书,防其或罹于法。……今或情例相违,牵合文法,以纳民于网。或有两例并见,辄上下其手,以自遂其私。安得无冤狱哉?”(49)《雍正朝实录》卷三。这道圣谕在揭示律例本意在于弼教的同时,毫不避讳地肯认了律例存在“情例相违”“两例并见”等突出问题,表达出雍正帝决心修律的圣意。同年秋七月,又有巡视东城御史汤之旭上奏:“律例最关紧要,今六部见行则例,或有从重改轻,从轻拟重,有先行而今停,事同而法异者,未经画一。乞简谙练律例大臣,专掌律例馆总裁,将康熙六十一年以前之例并大清会典,逐条互订,庶免参差。”(50)同前注③。雍正帝对此予以认可,刑部对汤御史所奏内容也议覆“应如所请”。(51)《雍正朝实录》卷十一。对于刑典庞杂的破局之道,关键就在于修律,使“向之抵牾而歧异者,咸讲若画一,无复有疑义之存”。(52)(清)薛允升:《读例存疑·序文》。
待修律拉开帷幕后,雍正帝对这一编纂理念又多有重申。雍正三年五月,雍正帝发布上谕:“又念律例一书为用刑之本,其中条例繁多,若不校订画一,有司援引断狱,得以意为轻重,贻误非小。”(53)《清通志》卷七十六。此处的“繁多”,应有两重意蕴:一者是指条例的数量很多,调整的法律关系相互重叠但设计的法律后果又参差不一;二者是指条例的表达复杂冗长,其“一大特点是过于具体,以致于概括性、抽象力不强,适用面较窄”。(54)同前注,苏亦工文。如《刑部现行则例》的“免死养亲”例,字数就多达三百余字。上谕表明,雍正律的制定初衷,就是要将律例校订画一。雍正帝不舍昼夜地将所纂全稿逐一详览,并“著九卿会同细看”,也切实体现了对“画一”理念的深入贯彻。同年七月,在新律颁布前夕,又谕大学士:“今律例馆纂修律例将竣,着吏兵二部会同,将铨选处分则例并抄白条例,逐一细查详议。应删者删,应留者留,务期简明确切,可以永远遵守。”(55)《雍正朝实录》卷三十四。这是要求将律例、抄白条例、(56)抄白条例,是指未经校刻的刑事条例,这种条例由部内抄白存查,遇事引用,外官无由得知。参见《雍正朝实录》卷三十四。相关部门的则例进行比对,视具体情况行删留之举,目的就是要保证“简明确切”。九月,为庆祝新律刊布内外,雍正帝亲作《大清律集解序》。此序对编纂理念的陈述更为直接。“朕以是书民命攸关,一句一字,必亲加省览。每与诸臣辩论商榷,折中裁定。成析异以归同,或删繁而就约。务期求造律之意,轻重有权;尽谳狱之情,宽严得体。”(57)《大清律例·世宗宪皇帝御制大清律集解序》。“析异以归同”,自是找出律例之间的冲突之处,使之趋于相同一致;“删繁而就约”,则是删减重复的内容以及过于冗长的文字,使之简约明了。双管齐下,确保新律齐整画一。
既然最高统治者视之甚重,负责修律的臣工自当一以贯之。雍正律成书后,律例馆总裁官、吏部尚书朱轼曾在奉表上进时有云:“常蒙天语叮咛,德洽好生。悉体圣心仁爱,源流长远,仰睿鉴之精明;义类繁多,经宸衷而画一。”(58)(清)吴坛:《大清律例通考·奏疏》。个中之意,就是他在修律的过程中经常蒙受皇帝的叮咛指导。而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破解“义类繁多”的难题,使原本存在抵牾或歧义的律例得以“画一”。在另一份奏疏中,他又回顾了制定雍正律的工作历程:“臣等奉命遴选纂修臣纳海、金瑛等,逐条考正,重加编辑。其律后总注,会萃旧文,刊订讹误,期于简切著明。又详校定例,篡入四百八十六条,恭缮进呈。皇上亲加鉴定,其中详略经重未协之处,悉蒙朱批一一改正。”(59)同前注。“逐条考正”“刊订讹误”“详校定例”等一系列动作,其实都体现了对既有律例的全面梳理,是对“析异删繁以画一”理念的全面贯彻和生动呈现。
经此编纂而成的雍正律,在整体一致性、内容精确性、表达简洁性等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进步。首先,雍正律将顺、康、雍三朝以来的律文和条例进行了整合。其中,律文及律注“颇有增损改易”,(60)同前注③。有删除者、有并入者、有改易者、有增入者,总计四百三十六条;条例亦统筹删改并分类附于律后,分为原例(累朝旧例)、增例(康熙年间现行则例)、钦定例(上谕及臣工条奏定例),总计八百十有五条。如,“无官犯罪”律后本附有明代旧例,雍正三年奏准“今无舍人、舍余,亦无运炭、纳米、带俸、差操等例”,因此将此条删去。(61)柏桦编纂:《清代律例汇编通考》,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3页。对律例删改增移的过程,实质上是就是去除矛盾、协调一致的过程。其次,雍正律增加了总注和小注,使律例的内容指向更加精准。总注源自于康熙年间修律的创意,其定位本就是为了疏解律意,“务期异同条贯,不致引用伪误”。(62)(清)吴坛:《大清律例通考·凡例》。康熙三十四年二月,时任律例馆总裁张玉书曾在题本中表明这一点:“臣等汇集众说,于每篇正文后,增用总注疏解律意,期于明白晓畅,使人易知。”(63)同前注。小注则是指律例正文中用括号注明的内容,主要是对相关法律概念进行解读。如,“别籍异财”律后附条例“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许分财异居。(此谓分财异居,尚未别立户籍者,有犯,亦坐满杖。)其父母许令分析者,听。”此例括号中的小注系雍正三年増入,(64)(清)薛允升:《读例存疑·户役》。指出即便是形式上没有别立户籍但实质上存在分财异居行为的,也属于本例的规整范畴。再者,雍正律使用的文本表达更为简洁。如前所述,《刑部现行则例》的文本表达相当繁冗,甚至很多条例都列明了其源头圣谕和案件。如,“科场作弊”例,有“上谕谕礼部:朝廷选举人才,科目最重”等语;(65)同前注,沈厚铎主编书,第505页。“逸出投归”例,有“奉旨:据徐元善寇乱从出贼去,遵法投监,情有可矜”等语。(66)同注,沈厚铎主编书,第501页。在雍正律中,这种现象基本消失不再,诸多条例堪称“立法之善”,“或隐合古义,或矫正前失,皆良法也”。(67)同前注③。
四、乾隆律:随时酌中以尽善
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长足发展,清帝国的刑典已然成为一部形式相对严谨、内容较为齐备的法典,构成支撑帝国统治秩序的坚实法制梁柱。然刑罚本就世轻世重,“非谓一成而不可变易也”。(68)(清)薛允升:《读例存疑·总论》。面对帝国刑典存在的种种新旧问题,乾隆帝未选择固步自封,而是在御极之后即“重加编辑”,(69)《大清律例·御制大清律例序》。并于乾隆五年以《大清律例》之名颁布宇内。对于《大清律例》之编纂,乾隆帝是本着追求极致完美的精神来推动的。他希望从根本上革除既有刑典的大小弊病,通过适时修纂让律例总是处于一种“宽严得中”的状态,从而达到“至公至当”的“尽善”境界。得益于这一理念的促进,清帝国的刑典渐趋完善,并塑造出一套颇具自身特色的稳定样式,“律、例体制定型,相辅相成,清律走向成熟。”(70)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乾隆五年仲冬,乾隆帝为新成之《大清律例》所制的序文,清晰表明了他对刑典编纂的真实想法。这篇御制序文先是逐一肯定了列圣为刑典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然后有云:“朕寅绍丕基,恭承德意,深念因时之义,期以建中于民。……揆诸天理,准诸人情,一本于至公,而归于至当。”(71)《大清律例·御制大清律例序》。在乾隆帝看来,此前列圣之刑典各有千秋,但律例宽严本无定数,必须“因乎其时”,切实根据现实需求来决定宽严轻重。他期待在充分结合时势的基础上,融合天理和人情,真正做到“建中于民”,制定出一部至公至当的完美刑典。对于新修成的《大清律例》,他也确实颇为自信。以至于在颁布的第二年,当奉天府府尹吴应枚建议更改其中个别条文时,他表现得极为反感,认为该刑典是大臣“斟酌重修”和他本人“详加厘定”的上乘佳作,严厉斥责吴应枚“竟奏请酌改三条,夫以已定之宪章,欲以一人之臆见,妄思更易”。(72)《乾隆朝实录》卷一百五十二。
乾隆帝对“因时”的坚持和对“至当”的执着,与其个人的履历和性格密切相关。一方面,深受祖父康熙和父亲雍正的影响。乾隆帝自幼备受祖父康熙宠爱,“随侍宫中,朝夕承欢,不离左右”,(73)(清)乾隆:《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四余室记》。故其理政风格与康熙帝较为相似。而如前所述,康熙帝在修律方面向来推崇的理念就是“因时制宜”。雍正帝生前虽严设刑罚禁令,但在遗诏中特意强调:“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74)《雍正朝实录》卷一百五十九。这显然也构成乾隆修律的正当性支撑。另一方面,乾隆帝是个完美主义者,历来追求文治武功样样皆全。晚年回忆治国功绩时,他曾自信直言“况朕临御六十年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及拓士开疆诸实政,彰彰可考”,更是自号“十全老人”。(75)《乾隆朝实录》卷一千四百八十七。当这种帝王个性上的完美主义运用于国家法制设计,自然会执着于追求法典的“尽善尽美”。乾隆初年主导修律的内外臣工深秉此意。在群臣看来,雍正三年刊行的律例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比如,条例滞后的问题,有“先经定例而后经改易者,或前例未协而后亦未经改易者”;(76)同前注。总注多余的问题,“意在敷宣,易生支曼,又或义本明显无事,笺疏今皆不载”。(77)同前注。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核心就在于“因时而变”,基于乾隆朝当下的客观情况对滞后的律例进行全面修改,使其“折衷尽善”。
然不管法律制定得多么完善,亦只是一时之气象,伴随时间的推移难免漏洞渐显。为了从根本上保证《大清律例》的“随时酌中”和“止于至善”,乾隆帝还煞费苦心确立了定期修例机制。颁行伊始,期限定为三年一修。乾隆十一年,经内阁等衙门于遵旨议复御史戴章甫条奏案内议定改为五年。薛允升在《读例存疑》的自序中亦曾指出:“凡条例之应增应减者,五年小修一次,十年及数十年大修一次,历经遵办在案。”(78)(清)薛允升:《读例存疑·自序》。只不过这一机制主要是围绕条例设置,至于律文,往往被视为经世不易的祖宗成宪,不予或极少修订。在修例机制的推动下,终乾隆一朝,《大清律例》在乾隆五年颁行之后又先后经历了多次修订,“乾隆一朝纂修八九次,删原例、增例诸名目,而改变旧例及因案增设者为独多。”(79)同前注③。但这种因时修例亦非毫无限制,必须具备相当之必要性且经层层把关和筛选,否则“情伪微暧,变幻百出,若事事曲为逆亿,虽日定一例,岂能遍给乎?”(80)《乾隆朝实录》卷六百六十三。通过定期修例,乾隆律得以与时俱新,法律的滞后性问题大多能在修例的过程中得以有效解决。
综观乾隆律,较之前人之作,着实更为周详齐备,可谓有清一代最为完善、最具代表性的刑典。“高宗运际昌明,一代法制,多所裁定”,(81)同前注③。此言不虚。一方面,法典的结构更为科学合理。乾隆律确立了律例合编的最终体例,即“律文+条例”,在每一条律文之后将所有相关条例附后。附例不再区分“原例、增例、钦定例”等繁杂的类别,而是统称为“条例”。雍正律中的“总注”亦被删除。总注作为一种解释性表述本就不宜与律例同列,附于律后“易生支蔓”,但若对“律义有所发明,实可补律之不逮”者,则可改造为新的条例。如,“谋杀人律”后附条例“谋杀奔脱邂逅致死”即由总注改编得来。这一体例沿用到清末,未曾有变。另一方面,法典的内容更为简洁应时。据笔者统计,仅乾隆五年颁行的《大清律例》,对原律例的修改便多达531处,修改方式含括增加、修正、合并、移附、删除等多种。经此大刀阔斧地重新编辑,帝国刑典无疑是经历了一次“洗礼”。以“给没赃物”律后附条例为例,变革甚大,其中既有因时删除者,又有酌中改定者、增加者。在乾隆五年之后的修例工作中,刘统勋等臣工仍格外重视对“新旧不符、词意重复、文义未甚明晰”等问题的查漏补缺,也注重及时将基于司法案件产生的新条例纂入例册,即“因案修例”。(82)黄雄义:《清代因案修例的现象还原与性质界定——兼论其对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启示》,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2期。体例结构和律例内容的双重变化,有力印证了“随时酌中以尽善”理念的深入运转,促成了刑典“条分缕析,伦叙秩然”的宏远目标实现。
五、宣统律:兼采中西以图变
乾隆之后的百余年,帝国刑典处于一种高度稳定的状态,是为“仁宗以降,事多因循,未遑改作”。(83)同前注③。在这过程中,旨在“随时酌中”的定期修例机制日渐废弛,最后一次官方修例定格在同治九年,但亦不过遵照前次小修成法。迨至清末,内忧外患,传统法制既频受冲击又颇受质疑,清廷无奈之下遂思变法,妄图以制度上的妥协让步换取统治上的长治久安。作为清末变法修律的重要成果,宣统二年颁布的《大清现行刑律》《大清新刑律》,(84)鉴于《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均颁布于宣统二年,现行刑律又是改用新律的过渡和预备,故本文将其统称为“宣统律”。可谓新风毕显。究其根源,还是宣统律的核心编纂理念发生了显著变革。相较于之前多部刑典,宣统律的编纂不仅需要考虑律例本身的各式漏洞,还需要考虑来自于国门之外的诸多因素。故此,修律必须“兼采中西”,在变革中寻求延续统治的良策,妥善处理好“变”与“不变”的玄妙关系。
清末修律始于光绪、成于宣统,在这过程中,光绪和宣统二帝多次表明“兼采中西”之意。早在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出使大臣伍廷芳“请变通成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此事奏请光绪帝:“至改订刑律,请饬该大臣博考西律及日本新例,酌拟条款,咨送妥商。”(85)《光绪朝实录》卷四百十七。光绪帝表态支持,批示“并依议行”。同年四月,光绪帝颁布史上著名的《定国是诏》,谕令内阁:“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86)《光绪朝实录》卷四百十八。这一谕令其实确立了变法的根本准则,既要以圣贤义理之学为根本,又要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修律作为变法的重要内容,对这一准则自当严格遵守贯彻。光绪二十八年,光绪帝有感于西国在华纠纷日繁,再次谕令内阁:“着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87)《光绪朝实录》四百九十八。此谕之发布,意味着清廷正式启动修律,其背后也蕴含着“兼采中西”的深意。其一,被委以重任的沈家本和伍廷芳,本就具备中西学的双重知识背景;其二,光绪帝是要求结合“交涉情形”来“参酌”各国法律,意即还是要以中国为本;其三,立法目标是“中外通行,有裨治理”,那么新修刑律的内容当然要体现中西合璧。
宣统帝入承大统后,不忘先帝遗业,积极督促法部和修订法律大臣详慎斟酌,“不容稍事缓图”。宣统元年,宣统帝明令“新刑律限本年核定,明年颁布”,同时在谕令中指出:“惟是刑法之源,本乎礼教。中外各国,礼教不同,故刑法亦因之而异。……今寰海之通,国际每多交涉,固不宜墨守故常,致失通变宜民之意。但只可采彼所长,益我所短。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庶以维天理民彝于不敝。该大臣务本此意,以为修改宗旨,是为至要。”(88)《大清宣统政纪》卷七。这道谕令将“兼采中西”的修律宗旨和理念阐释得极为明晰。一方面,中国的纲常礼教是国粹国本,修律必须要予以坚持和传承;另一方面,受客观形势影响,国际交涉事务日益繁多,修律也要随时而变,注重吸收借鉴西国法制的长处。只有中西结合,方能做到“传粹固本”和“通变宜民”相统一。
皇帝之外,肩负着修律使命的一众大臣,兼受着东西法学的双重浸润,内心既有对中国礼教的执着与不舍,又有对西方法治的沉迷和神往。沈家本历来主张“兼采中西”,“以‘折冲樽俎,模范列强’为宗旨的《大清新刑律》是他立法的目标”。(89)李贵连:《沈家本评传》,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250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沈家本奏修订法律情形并请归并法部大理院会同办理,在奏折中呈报:“臣与馆员参考古今,拟准齐律之目,兼采各国律意,析为总则、分则各编,令馆员依类编纂,臣司汇核对。”(90)《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修订法律情形并请归并法部大理院会同办理折》,载高汉成主编:《〈大清新刑律〉立法资料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他将南北朝时期的“齐律之目”和西方“各国律意”并行,编纂理念呼之欲出。同年六月,在《奏拟修订法律大概办法折》中,沈家本又提出修律务必要“参考各国成法”,主张购买各国法典图书和聘请外国法律专家。是后,他在修律工作中不遗余力地贯彻执行,“乃徵集馆员,分科纂辑,并延聘东西各国之博士律师,藉备顾问。”(91)同前注③。及至刑律分则草案告成,沈家本在奏折中再次指明了修律宗旨和理念:“是编修订大旨,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延之礼教。”(92)沈家本:《修订法律大臣沈奏进呈刑律分则草案折》,载《云南教育官报》1908年第12期。由此洞见,泰西之新说虽甚受沈氏青睐,然传统礼教亦为其所倚重。有着深厚旧律功底的沈家本,深知中国旧律的重要价值,也深知编纂新刑律只有兼采中西,才可能克服礼教派官僚带来的巨大阻力。
对此问题,法部主官也不吝表态。法部尚书戴鸿慈有言:“讲求新政,以长驾远驭之资,任启后承先之重,允宜采取各国之法,编纂大清国法律全典,于守成、统一、更新三主义兼而有之。”(93)同前注,《法部尚书戴鸿慈等奏拟修订法律办法折》,第15页。在戴尚书看来,编纂大清国法律,兼有“守成、统一、更新三主义”。其中,“守成”当指延续传统,“更新”当指借鉴西法,“统一”则蕴含博采整合各国法典、糅合中西之意。继任尚书廷杰,也不赞同一味仿效西国,曾上奏:“惟中外礼教不同,为收回治外法权起见,自应采取各国通行常例。其有施之外国,不能再为加严,致背修订本旨,然揆诸中国名教,必宜永远奉行勿替者,亦不宜因此致令纲纪荡然。”(94)《钦定大清新刑律·奏疏》。廷杰认为,从收回治外法权的目的出发,在刑律中吸收外国立法经验固然应当,但也不能因此完全否定中国名教。尽管对中西法制怎么融合、中西元素孰多孰少等问题存在着明显分歧,但二者在新刑律中缺一不可已然是清末法律专家们的共识。
循此编纂理念而成的宣统律,彰显出鲜明的时代风格,是中国刑法近代化的里程碑之作。其中,《大清现行刑律》“为改用新律之豫备”,(95)《大清宣统政纪》卷三十四。在很多方面已有实质性突破。在体例层面,“芟削六部之目”,不再按“吏户礼兵刑工”排列,直接将各律例归于名例、职制、公式等三十。在内容层面,新修律删除了一些过时滞后的条文,即“因时事推移及新章递嬗而删者”;添入了一些近代刑法的元素,即“其缘政体及刑制迁变而改者”。比如,删除和移改比附援引的相关律例,“不列比附之目”,释放了向西方罪刑法定主义转型的鲜明信号。相较之,《大清新刑律》的进步性更为显著。一方面,对传统刑法的改革力度更大,对西方近代刑法的借鉴更为全面系统。新刑律的体例发生了颠覆性改变,摒弃诸法合体而专注刑事,又分为总则和分则两编,每编各章的内部次序严格遵循着西方近代刑法的排列逻辑。新刑律的内容对西方刑法亦多有移植,“尤其是德国、日本的刑法典的内容”。(96)参见李秀清:《法律移植与中国刑法的近代化——以〈大清新刑律〉为中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3期。另一方面,考虑到皇帝和礼教派官僚的底线,新刑律在一定程度上赓续了礼教传统。除卷首服制、卷中侵犯皇室等条文之外,卷后所附《暂行章程》,主要是想为干名犯义、亲属容隐等封建伦理纲常“施以援手”,以期发挥“沟通新旧”之效用。但刑典的传统色彩已弱化颇多,否则礼教派官僚不会别置一喙,纷纷上书斥责新律动摇国本。短短十年间,帝国刑典已焕然一新。
六、结语
从顺治律、康熙则例,到雍正律、乾隆律,再到宣统律,清帝国的刑典始终处于一种相对稳定而又适时变化的状态。在这过程中,每一部刑典在保持基本共性的同时也洋溢着鲜明的个性。归根结底,还是缘于其背后主导的编纂理念不尽一致。顺治律颁行于立国之初,顺治帝为了更好地应对国内急势以巩固新生政权,不得不选择“详绎明律”;康熙则例制定于清廷统治稳固之后,康熙帝得以有时间和精力来充分考虑满清特色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律例的因时制宜以求大治;雍正律修成于帝国积累上升之际,历来以严谨勤政著称的雍正帝,着力于全面梳理既有律例以达整体画一之效;乾隆律动议于康乾盛世的“高光时刻”,自信于文治武功面面皆全的乾隆帝,立足时势全面推进,追求刑典的尽善尽美、至公至当;宣统律面世于危亡之秋,即便是贵为九五之尊的光绪帝、宣统帝亦得仰人鼻息,在兼采中西展现变法姿态的同时,希图以变求存,延续满清已摇摇欲坠之统治。在不同编纂理念的指引下,帝国刑典虽前后相承,但在体例结构、制度内容等方面又取舍不一、走向互异,最终呈现出的样貌自然也是同异互见。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兼具,恰恰又体现了“法先王之法”和“法因时而化”相结合之意蕴,值得今人寻思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