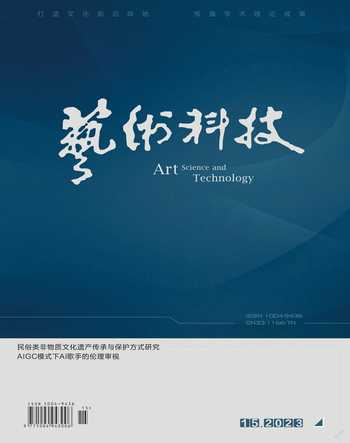可供性视角下短视频对流行音乐的影响研究
2023-07-30罗驰
摘要:流行音乐的发展与媒介形态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如今短视频已成为现代人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基础媒介,尤其是以抖音和TikTok为代表的短视频APP,作为一种新兴的音乐平台逐渐显现出巨大的影响力,对流行音乐产生了深刻影响。文章从可供性理论视角切入,发现短视频作为承载、传播流行音乐的新载体,其可供性渗透于流行音乐的赏用与创作过程中。短视频的技术可供性通过人与环境互动的物质介质即用户界面进行表达,引导平台用户的音乐赏用决策,在选择架构机制的作用下,用户与平台的沟通是被结构化的,用户的能动性受到了限制。TikTok的“合拍”特色功能便是以这样一种体现适模板性的限制性创意方式使普通用户快速上手,实现了用户与内容、用户与平台的互动。短视频的媒介可供性通过再媒介化改变了流行音乐时长和速度的创作趋势。在短视频生产实践中,各媒介之间不断彼此复制和取代,流行音乐在此成为再媒介化的对象,并按照短视频的封装规则被改造。一方面,为了符合短视频媒介的物质特征和符号特征,热门歌曲“缩水”的趋势愈发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夜核”风格的加速版歌曲以更大的信息密度与短视频一同猎取用户逐渐紧缩的注意力资源。由此可见,短视频平台正在重新定义流行音乐。
关键词:可供性;短视频;TikTok;流行音乐;音乐行业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15-0-03
1 背景
1.1 短视频与TikTok
短视频不仅是当下的一种热门媒介形态,更是许多人不可或缺的信息窗口,由此成为全民化的应用。在我国的短视频市场,抖音稳坐头把交椅,而在国际市场,抖音的“远亲”TikTok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了短视频的代名词,改变了大众接收和生产视听内容的方式,其中也包括流行音乐。
TikTok与抖音同宗同源,使用逻辑一致,市场表现相当,平台内流行趋势也常有映射,甚至“抖音摧毁流行乐坛”这一话题在欧美地区也存在镜像版本,可以说短视频影响流行音乐已成为全球化的传播现象。鉴于欧美地区音乐产业比中国更完善和发达,且相关数据更易观测记录,因此本文以TikTok和欧美流行乐坛为主要研究对象。
1.2 可供性理论
可供性(Affordance)是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在其专著《视知觉的生态学进路》中提出的核心概念,之后得到了广泛的跨学科应用。可供性是环境的一种资源,揭示了环境与有机体之间的一种互惠关系[1]。在传播学领域,社会可供性和传播可供性是两个常用概念,前者强调环境(媒介)对个体的引导和限制,后者关注更抽象的事物,如社会地位等。具体到社交媒体的可供性,学者们的视角取向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高/低阶可供性、想象可供性及通俗可供性[2]。
2 技术可供性引导音乐赏用逻辑
从1927年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手》开始,音乐与影像便实现紧密的有机结合,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文娱生活。如今,短视频这一强刺激的媒介形态更为迫切地榨取音乐的情绪传达能力和“耳虫”特性,以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让音乐的重要性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为了提高用户在音乐内容上的参与度,平台将技术可供性融入人与环境互动的物质介质即用户界面,通过定义选项的数量、呈现方式和默认值等,引导用户的决策。在这种“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机制的作用下,用户与平台的沟通被结构化,用户的能动性也受到制约。
2.1 以歌会友:音乐作为模因游戏
TikTok依赖用户生成内容(UGC),为此平台必须充分调动用户积极参与产用一体(Produsage)实践,而音乐则是其达成该目标的特色基础设施。从可供性角度来看,为了以音乐为线索连接起用户与社区,创造便利的音乐使用环境,TikTok将音乐元素贯穿于用户界面的各个环节,引导用户关注、使用音乐。
通常,视频的声音部分内嵌于画面,只供听觉读取。而TikTok将音乐以文字、音符图案和唱片拟物图标的形式外化,并配以动效诱导点击。歌曲作为公约数将相关视频作品统摄于音乐详情页下方,底部的“Use this sound”(拍同款)按钮让用户得以直接选中该段音乐进入预录制界面。录制开始后,音乐将同步播放,此时用户可以以音乐作为相对固定的脚本,实时调整拍摄画面以贴合音乐。
这类以音乐为线索的视频归档和制作逻辑强调了听觉的主导地位,体现了TikTok强化音乐的存在感、力推音乐挑战的技术可供性。音乐挑战是触发病毒式传播的常用手段,它的玩法通常是使用同一音乐和话题标签演绎类似的情节或主题,并鼓励用户分享和接力,如舞蹈、对口型假唱和换装表演等。它可以被看作是音频模因(Audio Memes)的跨媒介叙事,群体归属感在其中产生,原本以视觉形态居多的模因在TikTok上呈现出听觉转向的趋势。音频模因的使用逻辑,一是依靠特定歌词来传情达意,如通过对口型使自己成为某段Punchline(妙语)的表达者;二是借助音乐的旋律和節奏起伏来推进故事情节,如卡点进行画面切换;三是利用音乐的风格和氛围为视频叙事做铺垫,如画面随歌曲的跑调过渡到滑稽情节。
2.2 一起合拍:音乐作为众包项目
适模板性(Templatability)是TikTok技术可供性的另一种表现,指的是用户和平台之间的互动会导致特定的审美倾向、内容生产方式和引流策略,最终成为模板。模板背后的机制与选择架构类似,在给予用户一定自主性的同时,限制了创新性,即限制性创意(Circumscribed Creativity),让普通用户得以快速上手成为内容生产者。
2020年10月上线的合拍(Duet)功能是TikTok极具特色的限制性创意的体现。使用者在播放其他视频的同时同屏录制自身视频,然后二者合成新视频。合拍功能实现了用户与已有内容、用户与平台的互动,为具有适模板性的衍生视频提供了生产工具,广泛用于音乐传播。第一则视频类似于“创作动机”或“行动号召”,向所有感兴趣的用户发出合拍邀请,通过将两段或多段音乐表演结合,实现跨时空合作。这种用户深度参与的音乐赏用逻辑可以被看作一种协作式的音乐制作模式,将当下所处的场所变为即兴音乐(Jamming)的协作空间。一条原始视频可以引发无数次合拍,产出无数新的音乐,形成类似众包创作的效果。这些原本由专业设备和软件包揽的流程,现在通过TikTok就能完成,有效克服了数字空间中创意劳动的不稳定性。
3 媒介可供性改变音乐创作逻辑
麦克卢汉开启了“媒介即讯息”这一理解媒介的新视角[3]。媒介物的独有特征,就是将不同的元素组合在一起,并将其他元素转化为媒介。媒介的生成,便是可供性的实现或者呈现[4]。在麦克卢汉思想的基础上,再媒介化(Remediation)理论被提出,以重新审视媒介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新旧媒介都采用直接性(Immediacy)和超媒介性(Hypermediacy)的双重逻辑改造彼此和自我改造[5]。
短视频生产实践便是一个上演了多重媒介化的舞台,各媒介之间不断彼此复制和取代,流行音乐在此成为再媒介化的对象,并被按照短视频的封装规则改造。最终,新版本的歌曲成为选项被放置于界面。在短视频媒介中,音乐不再按原作者意志进行设计编排、等待被人品鉴、融合音律文学等科目的艺术内容,而是变成一种新的工具和媒介。
3.1 分秒必爭:单曲时长越来越短
音乐是基于时间的艺术,歌曲的时长是媒介技术变迁影响音乐创作的首要指标。回头看向20世纪初唱片工业的黎明时期,78转黑胶唱片只能单面播放3分钟左右,许多经典歌曲为了装进有限的时长,选择删掉第一段主歌,直接从副歌部分开始录制。磁带和CD等技术的进步延长了单曲时间,直至后来,又有了一首歌绵延十几分钟的概念专辑。而近年来,短视频的强势似乎正使音乐回到速战速决的时代。据统计,从2013年到2022年,Billboard Hot 100(美国公告牌百大单曲榜)上的歌曲平均时长由3分50秒降至3分25秒,两分半以内的热门歌曲数量占比在10年间从1%飙升至9%。
进入互联网时代,内容创作者越来越依赖平台,如Spotify一类的音乐流媒体平台甚至已拥有能够影响消费决策的能力。播放越多收益越多的流媒体法则使流行音乐越来越短。随着TikTok成为新的影响力更大的音乐平台,为了符合短视频媒介的物质特征和符号特征,热门歌曲“缩水”的趋势愈加成为必然。
虽然自2022年开始,TikTok逐渐向用户开放10分钟的视频发布长度,但目前平台上的大多数内容依然为15秒到1分钟,“短平快”已成为短视频用户的使用习惯,迫使短视频音乐必须在最初几秒内抓住用户的耳朵。无论是主歌、副歌还是桥接段落,最好能拎出一段完美适配短视频容量,配合造梗并鼓动用户跟风挑战,引发病毒式传播……这几乎成为如今流行音乐创作不成文的规则。
3.2 疯狂节拍:加速歌曲再度流行
如列夫·马诺维奇所言:“媒体与计算机融合,所有媒体都被转化为可供计算机使用的数值数据……简言之,媒体成了新媒体。”[6]一切内容进入短视频媒介都自动变为可编程的数据,进而被算法分析和操控。新媒体对象的多变性(Variability)意味着同一首歌可以被剪接、叠加、变速和变调,创造出众多迥异的版本。在TikTok曲库中,混音版、饭制版与官方版同时在列,并随着用户的编辑使用不断生成新的版本。其中,加速版歌曲在TikTok推动下的复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
短视频中常见的经过加速处理、极具喜剧效果的热门音乐Oh No,其实采样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流行女子组合“香格里拉”(The Shangri-Las)所演唱的Remember (Walking in the Sand),但是两者在TikTok上的使用量有万倍之差。英国女歌手雷伊的歌曲Escapism也有相同的境遇,其加速版在TikTok上的使用量超过70万次,是原版的两倍之多。目前,TikTok上“#spedup”(加速)主题标签的浏览量超过200亿次,Spotify为此专门推出了歌单,这足以证明短视频用户对快节奏的热爱。越来越多的加速版歌曲以超越原版的关注度在TikTok上流行开来,甚至倒逼许多唱片公司发布了官方的加速版本。
对此,加速版歌曲的流行或许可以理解为加速社会在音乐媒介形态上的表征,实际上,这种以加速为基础的制作方法由来已久,其正式名称是“夜核”(Nightcore),起源于2002年的挪威。TikTok高速运转的信息流界面让用户可以快速滑动屏幕刷新短视频,在数秒内阅览大量内容,加速版歌曲则在更短的时长内容纳了更多的歌词和情感,相称的信息密度使两者得以有效结合。加速版歌曲的紧凑节奏和如同吸入氦气般的花栗鼠声调十分抓耳,正好与短视频一同猎取用户逐渐紧缩的注意力资源。任何人都有能力制作夜核,这与短视频低门槛、高度自定义、鼓励创作和表达的理念不谋而合。加速版歌曲的众多特质使其与短视频平台异常适配,可以说,本属于数字亚文化的夜核开枝散叶于大众媒介是用户与平台在短视频传播的疯狂节拍上达成的合议。
4 结语
20世纪初叮砰巷沿街兜售的乐谱,代表了流行音乐和大众传媒的一场巨大变革,它曾经是流行音乐的产业中心。如今,便利的音乐制作软件和媒介平台使所有人都可以作歌、发歌,流行音乐行业在短视频平台上再现了当年曼哈顿下城第五大道叮砰作响的繁荣景象。而短视频音乐不仅成长为近年来全球音乐产业中最具有商业价值和发展潜力的细分产业链之一,更使短视频平台成为强大的内容传播平台,再造了流行音乐行业的样貌。
吉布森认为,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依存性和价值的两面性客观存在。例如,悬崖既有在边上行走的可能性,又有坠落下去的可能性。精细的选择和精细的区隔、快速的占领和快速的遗忘、广泛的机会和广泛的牵制……这些都是行业变化的一体两面。
有任性者如英国歌手阿黛尔,她宣称不会为抖音一代创作歌曲,呼吁取消专辑内随机播放的设置,希望用户从头到尾完整地收听专辑,但只此孤例具有特殊性,难以概括流行音乐行业的全貌。更多的人依然摇摆于是否拥抱新商业逻辑的难题。也许TikTok并没有摧毁流行乐坛,只是“何为流行”的问题,正由TikTok重新定义。
参考文献:
[1] 罗玲玲.技术与可供性[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85.
[2] 张志安,黄桔琳.传播学视角下互联网平台可供性研究及启示[J].新闻与写作,2020(10):87-95.
[3]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6.
[4] 胡翼青,马新瑶.作为媒介性的可供性:基于媒介本体论的考察[J].新闻记者,2022(1):66-76.
[5] 乔伊·大卫·博尔特,理查德·格鲁辛.再媒介化:理解新媒介[M].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0:5.
[6] 列夫·马诺维奇.新媒体的语言[M].车琳,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25.
作者简介:罗驰(1994—),男,贵州铜仁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媒介文化与流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