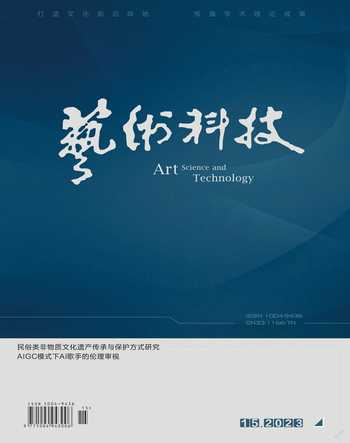论土在综合材料绘画中的运用与表现
2023-07-30张传鼎
摘要:古希腊哲学家克塞诺芬尼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土,土是世界的本原。”土孕育着生命,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是覆盖在地球上的生命之毯,土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我国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是构成世界的五行元素,正是有了这五种元素,地球万物的生命才会生生不息。而在这五种元素中,土元素至关重要。女娲造人的神话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其深深扎根于民间土壤,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共识和集体意识。土凭借重要性和易获取性,成为许多艺术家使用的绘画材料。文章从土性材料入手,首先考察土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并回顾早期艺术史上用土性材料创作的艺术品。其次,探讨土性材料的物质属性、视觉效果和文化特征,阐述一些著名的使用土进行创作的综合材料绘画大师,如安塞尔姆·基弗、让·杜布菲、塔皮埃斯等,分析他們在艺术实践中如何处理和使用土,总结艺术家使用土性材料的方式。最后,探讨土在综合材料绘画中的审美语言和文化价值,并逐步探索材料背后的精神属性。希望能为相关主题研究和艺术创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综合材料绘画;土性材料;物质属性;精神属性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15-0-03
1 土性材料成为艺术创作媒介的历史
汉代郑玄对先秦古书《周礼》注释指出:“万物自生焉则曰土。”在先秦文献中,《管子·地员》比较全面地讲述了我国古代土壤的颜色、性质与结构。同时,在自然材料中,土性材料相较于其他材料更容易获得,正因如此,世界各地的许多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将“土”作为重要的艺术创作媒介。而以土作为艺术创作的媒介,在中国艺术创作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清晰的发展脉络。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发现,在绘画中使用综合材料作为媒介的行为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媒介和材料都是自然界中的现成品。黏土是最早用于绘画的材料之一,当时人类就使用土作为基本的原材料发明了原始陶器。已知的主要用作日常器皿的陶器包括:山东潍坊的龙山文化“黑陶蛋壳镂孔高柄杯”、陕西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三鱼纹彩陶盆”、河南仰韶文化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等。当时的“艺术家”通过在陶器上绘制简单的图案来反映日常生活。彩陶的颜色可分为红色和白色。红色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铁,而白色颜料主要由高岭土烧制而成。
2 综合材料艺术中以“土”为媒介创作的国外艺术家
20世纪初,以毕加索为首的立体画派将现成材料引入绘画创作,打破了传统绘画方式的桎梏。传统的绘画方式是在二维平面进行绘画并追求三维的空间感、立体感和真实感。之后,通过用真实的物体取代他们的绘画内容,这批艺术家消除了作品的二维性,进入了三维空间。这一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综合材料艺术的发展和视觉艺术语言的进步。它给绘画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打破了传统媒介的枷锁。受主流思潮的影响,许多艺术家尝试用各种材料进行艺术创作,材料的发掘逐渐走向多元。土性材料因取材简单、视觉效果突出、文化内涵丰富而广受艺术家的青睐。
法国画家让·杜布菲是20世纪的一位伟大的综合材料绘画大师。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让·杜布菲开始在他的绘画中使用土,以前西方绘画中很少有艺术家使用黏土和沙子。在颜料中加入一种或多种物质,形成一种以人工色彩填充物为基底的特殊效果,呈现出多样化和斑驳的纹理,具有明显的明暗变化。他强调,艺术要像儿童一样,追求率性的天真和野蛮的大胆。艺术家打破了传统的绘画惯例,试图将疯狂的力量与史前艺术的丰富意象相结合,画面充斥着神秘感和原始性。艺术家使用原始粗犷的笔触,通过丰富的想象,在画面中呈现出神秘的、模糊的、畸形的人物形象。例如,《毛皮的帽子》的纹理令人回味无穷,让人联想到微观世界中的生物细胞或是浩瀚宇宙中的星河。
安塞尔姆·基弗是德国新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世界上声名显赫的艺术家之一。基弗的作品以深刻的观点和思想著称,形式和意义也非常独特。正如著名美术史学家阿森纳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怪僻而孤独的欧洲天才,创造了一个被自知之明和怜悯之心拯救了的世界,令人深刻反思的、最终充满希望的景象”[1]。安塞尔姆·基弗大多针对德国的历史和文化进行绘画创作,在他的画作中,沙子、土壤和尘埃填充的大地彰显了大地的意义,这些材料的使用让基弗的艺术作品具有强烈的物质感。在基弗的作品中,土出现的频率很高。与其他材料相比,土留下了更深刻的历史印记。在绘制尺幅巨大的画面的过程中,艺术家利用直接粘贴稻草和沙土的方法打造“废墟”场景,然后再利用各种工具进行反复打磨,这时土的形象如同经历过二战一样斑驳残损,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战争、死亡、毁灭等内容。基弗的画作似乎是一个经历了一场灾难的受害者。他的作品反映了战争对德国造成的破坏,以及在这个环境中存在的希望,引导德国人在战后深刻反思这段特殊的岁月。例如,《女神的巨人》这幅尺幅巨大的作品,就使用了亚麻布和黏土等材料,强调了德国历史的厚重感和深度。
20世纪西班牙画家塔皮埃斯是世界级“非形式主义”画家的代表,他强调材料和媒介的重要性,致力研究各种材料的质感和表现手法。20世纪50年代,塔皮埃斯开始在画作中使用沙子、黏土、大理石粉和布料等材料。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像个疯子一样思考如何使用我新发现的材料,并创作了一系列连贯而有意义的作品,生动地描绘了我当时所面临的问题”[1]。非形式主义强调材料和媒介的重要性,以及绘画的过程和随机性。艺术家非常重视材料本身的艺术价值,致力打破传统绘画的固有形式,抛弃了传统的对艺术美的理解,充分挖掘材料物理属性背后的精神内涵。塔皮埃斯也是一位特别喜欢表现“墙”的艺术家,在综合材料绘画中,做墙就要用到土这个媒介,艺术家通过各种技法与途径来强化墙的污秽不堪、支离破碎的视觉效果。艺术家强调:“在残垣断壁中,我见证了一次次战争。”20世纪90年代,塔皮埃斯创作了一件实物艺术作品《双脚》,它主要使用的材料是陶土。艺术家认为材料是传递人的情感的中介,重量会给人一种稳定、坚硬、牢固的感官效果[2]。
3 土性材料的使用方法
3.1 将土作为画面基底
肌理是指物体的表面组织,主要由材料和纹理等要素组成,构成物体的表面形态。一般来说,每种材料都有特定的质感,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质地和图案。画面基底的制作水平决定了画面呈现的最终效果。一般土性材料需要加入其他材料调和运用,如白乳胶、水、树叶、皮革等。当然,也有直接运用土性材料进行绘画创作的,但是需要加入一定数量的黏合剂,以保证作为基底的土不会脱落。土做的基底往往呈现凹凸不平、开裂、斑驳的视觉效果,如安塞尔姆·基弗的作品La Brisure des vases中充斥着大面积的开裂、破碎、粗糙的土,表现的是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土。画面中的“土”透出阵阵凉意,仿佛在诉说着人民心中的痛苦。
3.2 混合与重组
基于土的特征,在与油画进行调和的过程中,需要加入一些黏合剂才能固定在画面上,否则容易脱落。在调和之前,一般会对土性材料进行加工,将其打碎或磨成粉末重组,这样更容易与黏合剂混合在一起,进而更加牢固地粘贴在画布上。我国艺术家朱进在绘画过程中经常利用五色土进行艺术创作。
3.3 挥洒与喷洒
将土性材料直接挥洒在画面上也是综合材料绘画艺术中一种常见的绘画方式,能产生随机的绘画效果,有时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有时则会破坏画面。美国艺术家艾莉森·科特森突发奇想,将土挥洒在空气中形成灰尘进行创作。首先,她用胶水有规律地涂绘画面,然后在绘画之前进行艺术构思,最后按照构思在画面上喷洒灰尘,其代表作为《李和他的灰尘》。
3.4 堆积与实体
将土堆积成艺术品或做成实体的形式大多出现在装置艺术中,在架上绘画,土过多过重会导致画面承受不住,当画面的承受力达到一个临界点时,材料就会从画面上脱落。在装置艺术中,很多艺术家喜欢用土做出实体,如前面提到的西班牙艺术家塔皮埃斯,其代表作《双脚》就是用陶土做出的实体艺术品。我国艺术家宋陈以土为媒介,将各种各样的土块堆积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蜷缩着的婴儿形象,包围着婴儿的土块则象征着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养育人类的土地。
4 土性材料的精神内涵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土地是承载万物的媒介。古代社会缺乏流动性,人们对土地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催生了人们对土地深沉的爱和人与人之间的朴素感情。这种感情代代相传,已经深深融入中国人的血液中。以土入画,无论是在形式上、内容上,还是在情感上都承载着艺术家的文化素养和文化理念。艺术家在创作之前,以本土材料作为创作材料和媒介,材料本身就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创作构思期间,艺术家融入了民族文化符号,赋予创作主题鲜明的民族性。同时,在创作过程中,又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精神。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85美术新潮运动”兴起,西方现代艺术思想涌入中国。1985年,西方综合材料绘画大师劳森伯格在北京举办了个人画展,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的创作媒介、艺术手法、艺术观念深深刺激着那一批中国年轻的艺术家。朱进是一位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也是最早使用“土”作为创作媒介的中国艺术家之一。他对材料的使用非常敏感,尤其是土性材料,他认为土是自然与文明的本原。经过大量实践,朱进找到并研磨出了五色土这种材料。艺术家认为,人类文明起源于泥土,最早的绘画材料也是天然的沙土和矿物质颜料,这些天然的绘画材料蕴含着早期的人类文明。对中华儿女而言,土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物质,更是历史文化的象征符号,所以在朱进的作品中,土这种自然物质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3]。五色土特有的泥土气息、生命气息,作为本土材料更具有显著的民族特征。
1991年,张国龙在德国留学。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张国龙开始尝试综合材料绘画和装置艺术的创作,近20年来,一直使用土性材料作为绘画媒介。他选择了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黄土。对中国人来说,黄土具有涵盖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黄土的色调与中国人的肤色相同,与中华儿女有深厚的渊源,也突出了中国人的风韵。《黄土》系列作品是张国龙以黄土为媒介进行创作的典型代表,他将随处可见的黄土与蜂蜡、白乳胶等材料混合,经过艺术加工和处理,在二维空间中创作出三维的视觉效果。在他的作品中,黄土地欣欣向荣,彰显了东方精神。黄土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材料,但张国龙发掘黄土地的自由物质性,认为它是中国的基础,是文化传承的媒介和滋养万物的母亲,这也赋予他的作品更深层次的意义。
在第十三届全国美展综合材料绘画展中,有很多运用本土材料创作出的艺术作品。在本土材料开发方面,有许多新的收获和创新。例如,张晓华的《九牛图》就采用西藏泥土、牦牛粪、牦牛毛等材料混以油画颜料和白胶创作而成。在画面中,九头牦牛依次从左到右、自上而下地排列。九头牦牛全都是正面的,目光坚毅、神态各异地目视前方,表现出同心协力、群威群胆、患难与共的西藏人民的精神[4]。
5 结语
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艺术作品以土为媒介,土容易获得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受到了广大艺术家的追捧。土是五行元素之一,人们在土地上繁衍生息,土与人的关系极为密切。作为地球上最基本的物质,土无处不在,不可或缺。土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象征符号,深深根植于广大中国人的心中。在现在的综合材料绘画中,有一些画家不懈追寻不同质感的物质材料,不遗余力地寻找新的材料,而忽略了如何表现材料本身的精神属性。塔皮埃斯曾说:“材料本身是没有生命力的,一件艺术品所具有的感人力量并不仅仅取决于材料,因此,艺术家不能忘记,他创作的有效程度是和社会心理状态有关的,因为他的创作终究要被社会所容纳。”
本文通过梳理早期以土为媒介创作出来的艺术品,详细阐述了近代西方绘画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几位以土入画的综合材料绘画大师,浅析了土性材料的使用方式,目的在于更好地挖掘土性材料暗含的文化语言与民族内涵。笔者认为在综合材料绘画创作中,材料作为一种媒介,艺术家应站在物质材料的角度深入思考,在追求材料带来的丰富肌理效果的同时,深挖每个材料背后的精神属性,这样的艺术作品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和深思。
参考文献:
[1] 唐潇雯.不只是土[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13.
[2] 李晶.物性与神思的遇合:综合绘画材料的拓展与艺术呈现[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4.
[3] 庞景.沙土类综合材料在油画中的拓展与运用[D].镇江:江苏大学,2020.
[4] 吴彧弓.多元与融通:第十三届全国美展综合材料繪画展纵览[J].美术观察,2020(1):33-35.
作者简介:张传鼎(1998—),男,山东枣庄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