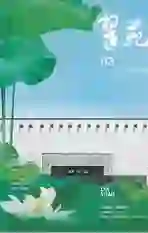《董贝父子》中的伦理困境与道德理想
2023-07-26李玲
1870年6月10日,也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去世的第二天,《每日新闻》的一篇报道中写道:“他绝对是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的小说家,后人将在他刻画的当代生活图景中了解到比史料还要清晰的19世纪生活面貌。”对于狄更斯的作品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马克思早在1854年发表的《英国资产阶级》一文中就曾指出,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和盖斯凯尔等人的小说“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
英国著名批评家利维斯在其小说批评的代表作《伟大的传统》中指出:“狄更斯对自己生活于其间的世界所作的批评,一般都是顺带为之。”然而狄更斯对社会弊端的描绘依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狄更斯在《董贝父子》中塑造了一个拥有巨额财富和尊崇社会地位的伦敦商人形象。作品中虽未过多涉及具体的商业活动,但董贝的商人身份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从董贝的伦理身份切入,围绕其商人身份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以家庭伦理的商业化引发的悲剧来阐发狄更斯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金联结关系的批判。
一、伦理环境与董贝的伦理身份
在《董贝父子》中,伦理身份问题被多次提及。无论是董贝因成功的商人身份享有尊崇的社会地位,抑或是他在家庭生活中强调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身份权威,皆表明身份问题是引发伦理冲突的重要原因。董贝具有多重身份:就血缘关系而言,他是弗洛伦斯和小保罗的父亲;就婚姻关系而言,他是弗洛伦斯的母亲和伊迪斯的丈夫;就职业而言,他是帝国商人,董贝父子公司的领头人。董贝的血亲身份、婚姻身份和职业身份的建构相互冲突,导致他产生了身份认同危机。
狄更斯在谈及《董贝父子》的创作意图时曾说“他要处理的是傲慢问题,正如前一部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要着重描写自私自利”,然而作品产生的实际效果却远远超出了对傲慢问题的揭示,蕴含了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价值观的反思。英国评论家托马斯·杰克逊认为董贝的傲慢是资产阶级“为金钱骄傲”,英国历史学家乔治·扬也指出19世纪中叶的英国是一个“造钱的时代”。作为商业竞争中的胜利者,董贝集资本和权威于一身。董贝不断被强化的商人身份弱化了他家庭成员的身份,进而产生了一系列伦理问题。
董贝的商人身份和商业至上的理念使得他与两任妻子之间的关系皆以获得公司的继承人为目的。董贝与第一任妻子的婚姻不仅没有建立在爱情之上,反而把爱情完全排除在外,正如文中所说,“董贝父子公司经营皮革生意,但却从来不经营心的生意”。董贝把他与妻子之间的婚姻关系看作商业活动中的契约关系。妻子既然签了契约,就要履行为公司生出一个新的合伙人的责任。董贝用商业化的契约关系来维系婚姻关系,也就规避了丈夫的身份所应承担的伦理责任。当为他生下继承人的妻子去世后,他并没有感到难过,而是为董贝父子公司因奶妈的缺失而摇摇欲坠感到愤怒。
董贝与第二任妻子伊迪斯的婚姻更是建立在以获得继承人为目的的交易之上。董贝看上了伊迪斯的美貌;伊迪斯的母亲则看上了董贝的财富,将他比作一个人人都想开采的金矿。然而伊迪斯与董贝逆来顺受的第一任妻子不同,她并不认可董贝的权威。董贝用金钱买回了妻子,却无法买到她的顺从。在董贝为了名誉和社会地位不愿意解除婚姻关系还她自由时,她以与公司经理私奔的形式进行反抗,让董贝的尊严和威信受到致命打击。董贝为公司的延续寻找继承人的努力,却成了董贝父子公司由盛而衰的轉折点。
董贝不仅无法维系建立在交易基础上的婚姻关系,也无法维系与生俱来的血亲关系。弗洛伦斯和小保罗都是董贝的孩子,他们与董贝之间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子关系。董贝需要给予孩子成长所需的关爱和教导,尤其是在两个孩子失去母亲之后。然而在董贝看来,小保罗与其说是他的儿子,不如说是董贝父子公司的继承人。这位刚出生就被父亲称作注定要去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孩子,虽然得到了父亲的关注,却无法得到父亲的关爱。董贝不是在抚育一个孩子成长,而是在为董贝父子公司培养一名合格的继承人。
董贝对小保罗继承人身份的确认,不仅阻碍了他与小保罗之间建立亲密的父子之情,而且还禁止他与任何人建立情感上的联系。董贝对保罗的奶妈波利·图德尔再三强调,他们之间只是纯粹雇佣关系,波利不需要与孩子产生任何感情。董贝把小保罗从出生到成人的时期看作是难熬的过渡时期,他带着让小保罗迅速成长为继承人的愿望,以揠苗助长的方式把他送去幼儿供善寄宿所和布林伯博士学校,让身心俱疲的小保罗过快地走完了生命的历程。
如果说小保罗因为继承人身份被剥夺了与他人建立关系的权利,那么董贝的女儿弗洛伦斯则因无法为公司带来任何利益而长期受到忽视。弗洛伦斯不被称作真正的后嗣,以致董贝要在小保罗的墓碑上写下“心爱和唯一的孩子”的铭文。董贝与弗洛伦斯的父女关系不被认同,这也导致了弗洛伦斯寻求女儿身份认同的过程困难重重。
董贝与两任妻子以及儿女之间的关系皆违背了正常的家庭伦理,归根结底在于他只认同自己的商人身份而规避丈夫和父亲的身份,用商业理念来维系家庭伦理关系。董贝是狄更斯在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宏大叙事背景下刻画的帝国商人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董贝父子》连载之初,就有评论指出:“描述董贝这类的人物简直是当务之急,伦敦的世界里充满了冷漠的、装模作样的、僵硬的、炫耀金钱的人物,想法跟董贝一模一样。”狄更斯在揭示董贝的家庭悲剧时,更希望读者能够以董贝的悲剧为鉴,实现商业社会中对物质财富追求和精神追求之间的兼顾与平衡。
二、身份认同与弗洛伦斯的伦理选择
《董贝父子》贯穿始终的既是董贝为公司的延续不断寻找继承人的尝试,也是弗洛伦斯试图获得身份认同的努力。弗洛伦斯从唯唯诺诺寻求父亲关注的小女孩,成长为可以为父亲带去安慰的精神独立的女性,经历了重重磨难。狄更斯通过孩子的视角,以“一个孩子在探索通向一位严酷的父亲的心的道路”,揭示商业至上的理念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弗洛伦斯在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主要经历了四次伦理选择,并最终完成了伦理身份的建构。弗洛伦斯的身份认同与董贝伦理观念的转变相结合,既表明金钱对维系家庭伦理关系的阻碍,又以家庭领域的悲剧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金联结关系的批判。
小说伊始,作者就以弗洛伦斯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董贝的形象——“蓝色的上衣、笔挺的白色领带、走起来咯吱咯吱响的长靴、一只滴答滴答走得很响的表”。这构成了她对父亲的概念。董贝作为父亲的形象以如此方式呈现,无疑凸显的是董贝的父亲角色在父女关系中的缺失。六岁的弗洛伦斯从未获得父亲的关注,即便是走在街上,父亲也无法将她认出。对于疏离的父女关系,没有比这更为精妙的描绘了。虽然董贝与弗洛伦斯之间的父女关系是既定的事实,但弗洛伦斯作为女儿的身份却从未得到父亲的认同,因为女儿只不过是“一枚不能用来投资的劣币”。董贝完全以商业中的价值来衡量弗洛伦斯的伦理身份,是他无视作为父亲应该承担的伦理责任的表现,也是正常的伦理情感让位于商业价值的结果。
作为女儿的弗洛伦斯希望与父亲建立亲密的关系,但她因长久地被忽视而对父亲充满了恐惧。在希望与恐惧之间,她不断地进行着艰难的选择。弗洛伦斯把母亲的离去当作一次与父亲建立关系的契机,也是她寻求身份认同的第一次尝试。因为在她看来,离她而去的母亲同时也是父亲的妻子,他们同时失去了亲人,对彼此的痛苦应该能够感同身受。共同的情感缺失本可以强化其父女关系,但董贝对妻子并没有感情,所以他不会与弗洛伦斯拥有共同的情感体验。
在弗洛伦斯希望与父亲共享失去亲人的悲伤来建立情感联系的同时,保罗的奶妈波利则希望弗洛伦斯与保罗之间的姐弟关系能够唤起董贝对弗洛伦斯的关注,因为他们都是失去了母亲的孩子。然而波利只看到了弗洛伦斯与保罗事实上的姐弟关系,却没有察觉到保罗因继承人的身份与对商业毫无价值的弗洛伦斯在董贝心中的云泥之别,是无法用姐弟关系的事实来弥补的。尽管弗洛伦斯从未受到父亲的重视,但她对父亲的爱却从未减少。保罗去世后,她又一次鼓起勇气努力寻求父亲的认同,这也是她的第二次伦理选择。弗洛伦斯希望可以与父亲共享悲伤彼此得到安慰,然而董贝却把弗洛伦斯当作与保罗生死存亡竞争中的胜利者,弗洛伦斯不仅无法给董贝带去安慰,反而加剧了他失去继承人的痛苦。
弗洛伦斯第三次寻求身份认同的尝试是与董贝的第二任妻子伊迪斯建立情感上的联系。当董贝为了公司的继承人娶了伊迪斯时,弗洛伦斯则希望通过与伊迪斯维系亲密关系而得到父亲的关注。伊迪斯的美貌纵然是吸引弗洛伦斯的原因,但弗洛伦斯首先是抱着“她将像她美丽的新妈妈学习怎样博得他父亲的喜爱”的目的与她亲近的。这也就解释了刚失去母亲的小女孩为何能开心接受取代母亲地位的继母的行为。在弗洛伦斯看来,父亲必然是因为喜爱伊迪斯才与之结婚的,那么她身上就有自己可以学习的地方。她对伊迪斯的接受与她在孤独的日子里努力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有着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同。
董贝父子公司的破产意味着董贝商人身份的终结,也是弗洛伦斯与董贝伦理关系发生变化的转折点。杰斯特顿在《查尔斯·狄更斯》中指出“只要他想写人物的变化,他准会弄得一团糟,例如写董贝的忏悔”,然而这里董贝的转变却能更好地展现彼时英国的商业环境对人物命运的深刻影响。作为商人的董贝并不缺乏商业道德,他宁愿破产也不愿给他人带来损失的行为是坚守商业伦理道德的体现。然而作为父亲,董贝不仅没有给予女儿正常的关爱,还对其爱的表达和身份诉求不予回应。
破产后的董贝与其说是被失去财富的悲痛压倒了,不如说是被强烈的悲伤与悔恨吞噬了。他深刻地认识到作为父亲,家庭伦理责任的缺失对女儿造成的伤害,以及曾经用商业理念评判一切的标准对家庭的影响。正是这种感受力的产生,让董贝与弗洛伦斯之间的父女关系得以强化,同时暗示着作者对人性和人类社会家庭伦理关系的认识。徐彬认为狄更斯妖魔化董贝的动机不是为了否定帝国商人的社会价值,而在于“对董贝家庭伦理责任的拷问与召唤”。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自私自利,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社会关系被打上市场逻辑的烙印,金钱和价值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精神错乱时的董贝会重复小保罗提出的“钱是什么”的问题,这是小保羅的疑惑,也是董贝曾经有着明确的答案,后来却陷入沉思的问题,也是作者希望读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家庭悲剧的伦理启示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聚焦家庭领域来展现社会问题更是文学家们普遍采用的方式。狄更斯在展现董贝的家庭悲剧时,也为读者展示了贫困家庭中的温馨。在商业竞争中处于劣势的船舶仪器制造商所罗门·吉尔斯与外甥沃尔特·盖伊在贫困的生活中相依为命所表现出的亲情、劳工波利一家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互依赖,都与董贝的家庭伦理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论是董贝无法与两任妻子建立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抑或是无法与保罗和弗洛伦斯之间维系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伦理亲情,归根结底在于他无法把商业活动和家庭生活分离开来,用商业理念来维系家庭伦理关系。
物质资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金钱对任何一个家庭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人们对待金钱的态度却不同。保罗的奶妈波利丢下自己年幼的孩子来照顾保罗无疑是为了赚钱,但她并没有把自己与保罗的关系仅仅看作是现金交易关系。她不仅与保罗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还成了弗洛伦斯的朋友,给她带去了母亲般的温暖。波利不以赚钱为唯一目标,对保罗和弗洛伦斯产生的母爱般的情感,也是对董贝以金钱来维系一切社会关系的反抗与控诉。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天然伦理亲情竟然败给了建立在交易之上的雇佣关系,这无疑是对董贝漠视伦理亲情的巨大嘲讽。
董贝与波利的丈夫图德尔之间的简短对话,也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家庭伦理观。当董贝试图向图德尔再次重申他与波利之间的交易关系时,他对图德尔一切让波利做主的决定感到失望。当董贝认为图德尔家要抚育五个孩子,生活的艰辛让人难以承受时,图德尔却说他最不能承受的是失去他们。图德尔对孩子的重视,与董贝对弗洛伦斯的漠视形成了强烈的对照。狄更斯以图德尔的家庭关系为参照描绘了理想的家庭生活。
商业至上的理念不仅让董贝在家庭生活中拒绝情感的流露,在工作中他也将情感排除在外。当沃尔特为了帮助舅舅还债向董贝寻求帮助时,沃尔特得到了董贝的贷款,然而他发自内心的感谢却遭到董贝的拒绝。董贝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是一个既拒绝情感流露,又不对他人的情感诉求作出回应的人。与董贝不同,沃尔特是一个重视感情的人。他的勇敢、正直、善良赢得了弗洛伦斯的好感,并与之缔结婚姻。与经营董贝父子公司时的董贝不同,沃尔特没有视金钱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他重视情感的价值,家庭幸福美满,事业蒸蒸日上。沃尔特与董贝的对比,既凸显了商业至上理念的危害,又赞扬了以沃尔特为代表的集商人身份与家庭成员身份于一体的具有崇高道德操守的新一代商人。
家庭问题是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问题的核心,《董贝父子》聚焦家庭领域,围绕家庭成员的伦理身份展开社会问题的讨论。董贝无法维系正常的家庭伦理关系,并不是因为其自身道德品质的缺陷,而是资本代替了情感让其无法融入家庭生活。狄更斯以家庭伦理关系的商业化来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商业至上理念对心灵的毒害,以家庭伦理责任缺失引发的悲剧来展现资本主义文明对人性的摧残。破产后的董贝家庭伦理意识的回归以及对弗洛伦斯和沃尔特幸福家庭生活的描绘,寄寓了作者对财富与道德相结合的美好愿景。
作者简介:
李玲,1990年出生,文学博士,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英国文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