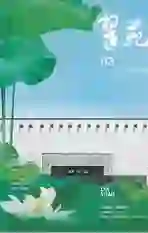浅析青年读者对卡夫卡的解读与形象建构
2023-07-26孙蒨蒨
一位西方学者曾经指出,在读者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热情逐渐消退的当代,有两位作家仍然在被阅读着,一位是王尔德,另一位则是卡夫卡。几乎可以这样说,这两位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当代性”的作家永远不会过气。王尔德因其机智的连珠妙语与当代媒体的碎片化特质相得益彰;而卡夫卡与当代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之间则有着另外一个故事。在群星璀璨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中,卡夫卡的读者数量相当庞大。这里的“读者”指的是一个比较广泛的阅读群体,而非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青年读者以何种形式第一次接触卡夫卡?在读者眼中卡夫卡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作家,与研究者眼中的卡夫卡在哪些方面有出入,因何会形成这样的差别?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能够解释长久以来青年读者对卡夫卡的偏爱。
一、“新概念”与旧概念——为什么是卡夫卡?
卡夫卡在中国,尤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拥有众多的读者,其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超越文学本身的界限的。那么卡夫卡在普通读者心目中是怎样一个形象,他的形象与其他作家是否有区别?这似乎又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要具象化描述卡夫卡在青年读者眼中的形象,这里需要提到一个多年以前曾经是现象级的文化事件——新概念作文大赛。
1998年,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启动。这一赛事有着与当时的传统教育模式迥然不同的理念,即面向新世纪培养新人才,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七所全国顶级高校联合《萌芽》杂志联合发起、共同主办,主张创造性、发散型思维,打破旧观念、旧规范的束缚,打破僵化保守,提倡无拘无束。不得不说,就其效果和影响而言,新概念作文大赛在教育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后的几年内,这一比赛不仅成为了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一批“80后”作家和文化名人崭露头角的舞台,也对当时的语文基础教育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契合了新时代的思想状况和精神需求。随着当时多元化市场经济大潮的涌起,整齐划一的思维模式渐被打破,张扬个性、崇尚自我意识等思想的流行术语渐渐构建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成长于多元开放、思想自由年代的“80后”新青年已经开始摆脱了同质化的思维方式,对人生、社会开始有了个性化的思考。这是韩寒等“80后”作家成长的精神背景。值得一提的是,新概念作文的参赛者及作品中,卡夫卡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的读者对卡夫卡的理解状况。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A卷中有一篇介于短篇小说和叙事散文之间的作文。这篇作品在内容上也是一个“卡夫卡式”的故事,这种现在常见的文体形式在当时看来还是有一定创新性的。作者在其中将卡夫卡描述为一个“孤独、内心充满恐惧,喜欢黑夜的作家,近乎阴沉但确实让人着迷”,作文的女主人公也是有着上述性格特点的人物。事实上,这种性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那一代青少年的审美倾向。
此外,同样参加过这一作文赛事的,后来成为作家和知名文化人物的韩寒也曾表示过他“卡夫卡的东西看多了”。郭敬明也说过:“我没有企图抄袭卡夫卡,而且我也不敢。卡夫卡是让我最为恐惧的作家。” 而获得第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的吴惠子的自我介绍就是:“十九岁的卡夫卡式女孩,喜欢躲在黑暗……沉默健忘……有着错乱的生活方式……”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卡夫卡式的女孩”绝不同于严肃的文学研究中所说的“卡夫卡式”,而更多的是一种与众不同,或者追求众不同的落落寡和的姿态。毫无疑问,这年轻的作者认为卡夫卡和青少年特有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自己一样,“喜欢躲在暗处”“沉默”。 事实上,这样的描述更适合颓废主义插画大师奥博利·比亚兹莱。但卡夫卡在生活态度上与一直向死而生的比亚兹莱相比要积极得多,因为卡夫卡可以和“荒诞”“异化”……等词相联系,却并没有带上太多颓废与绝望的色彩。
主观说来,无论是一度颇有争议的韩寒、郭敬明,还是此后几届的新概念作文参赛作品中那些带有明显青春疼痛文学色彩的作者,他们理解的卡夫卡一般都过于强调其孤独与阴郁的一面。此后,随着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的流行,似乎又给读者眼中的卡夫卡添上了一抹轻飘飘的忧伤色彩。诸如此类的理解确实是 “六经注我”式的,但这也是当时比较广泛的一个文化现象。
二、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现代主义与卡夫卡
为什么是卡夫卡被如此广泛地阅读、接受,并被做了各种“六经注我”式的理解?而与卡夫卡同样复杂、重要,理解的难度也不相上下的其他西方现代主义作家,比如普鲁斯特、乔伊斯,甚至凯鲁亚克等作家,却未受到普通读者同等程度的关注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可读性的问题,卡夫卡的阅读门槛并不高,除三部长篇之外,多为短篇小说,而且带有寓言性;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的是青年读者一般是如何接触到卡夫卡的。
要想弄清楚普通读者,尤其是“80后”一代以及之后的读者,是如何接触卡夫卡的,需要先弄清楚读者是如何接触到所谓的“世界名著”的。中学生除了课本以外的扩展阅读读本之外,还会有语文教师开列的很多选读书目。这里面一般主要是经典的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长篇小说。卡夫卡是少数几个被列在其中的现代主义作家,虽然有一部分是出于应试的目的,但是这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以及塑造作家的形象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另外,在教材中也会选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外文学作品作为课文。其中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曾经有几篇课文涉及到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包括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变形记》、伍尔夫的意识流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百年孤独》节选部分;此外,沪教版语文教材后来还选了卡夫卡另一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一般说来,西方现代派文学进入高中语文课堂,对于学生是有一定的理解和接受难度。但是,语文教材入选作品的多样化,对拓宽学生的視野,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也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即便如此,对于这些作品的解读却未必那么水到渠成。其中《百年孤独》是长篇小说,只能截取很短的片段,学生很难对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有一个整体的把握;《等待戈多》除其本身的荒诞晦涩很难让中学生接受之外,比起小说,剧本的形式也并不是很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至于《墙上的斑点》因其几乎没有情节,对于中学生而言稍显枯燥。因此,真正具有可读性和故事性的,也就只有卡夫卡的《变形记》了。
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自然可以让卡夫卡收获更多直接的读者,但是教学过程中的解读也会对读者造成一定影响。一般中学课堂对《变形记》的讲解大致会是这样一个思路:首先就作者所处时代背景而言,卡夫卡生活在二十世纪初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其思想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的影响,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旨在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成为席卷欧洲的现代人的困惑的集中体现,并在欧洲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卡夫卡热”。《变形记》的写作背景则一般解读为:卡夫卡目睹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特别是他在工伤保险公司工作时,接触了许多被劳动致残而一贫如洗的工人,使他认识到富人的奢侈是以穷人的贫困为代价的,下层人民越来越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卡夫卡创作《变形记》的时代、生活背景。他从个人的、人性的角度去揭示和否定当时的整个社会,其目标是笼统的、抽象的、片面的。
中学课堂教学中关于《变形记》的“标准解读”大致是上述思路,考虑到中学生的接受能力而有意将卡夫卡做了一定的简化与取舍。这一思路直接导向的是《变形记》与“异化”的概念相绑定,学生在此后的很长一段阅读经历中无论在何处见到卡夫卡,后面总会跟着“异化”二字。但是现代主义作品中的“异化”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还是存在差别的,这是中学语文教学一般很难涉及到的。
单纯用“异化”理论来解读卡夫卡的《变形记》,存在着许多问题。无论这种异化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达到极致的劳动分工,还是来自于强大的“超我”的存在。异化既然是由私有制的出现和劳动分工导致,并因人类面临生存困境而不能避免的,那么就会造成这一理论往往在用来解读大部分表现渺小的个人在强大的社会力量面前粉身碎骨的文学艺术作品上,从而忽视了作品的个性。卡夫卡的《变形记》也是如此。
三、文艺青年的朝圣与被诗化的卡夫卡
与其他作家相比,即使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对卡夫卡的形象的描绘往往也是带有明显感性色彩的。以往的研究既会从卡夫卡的犹太人身份、德语写作、法学背景、作品的自传性、与表现主义思潮的关系、异化、荒诞、逻辑的悖谬、后现代等严谨的学术角度去对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和分析,同时也会关注生活在彼时的作家内心的孤独与恐惧、卡夫卡与父亲的紧张关系、个人情感经历与终生未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等感性层面。至于卡夫卡其人,经典的描述包括一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被抛入世界的陌生者”“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相,以毁灭为自己加冕”的“现代主义文学之父”,一位被誉为“欧洲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的孤独单身汉……”诸如此类的描述用近乎诗性的语言勾勒出卡夫卡极为具体且感性的一面。少数读者未必会接触过上述专业的研究论文或专著,但是一般也会通过各种途径感知到卡夫卡即使是专业的研究者也难以抹去的孤独、忧郁和阴沉的底色。上文提到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中的一些现象也能说明这一问题。
对所有读者而言,卡夫卡的作品充满了荒诞、逻辑上的悖谬,是“谜一般”或者梦境一般的。事实上,大多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都很难归纳出一个确切的意旨,自然会“横看成岭侧成峰”。如加缪所言:“卡夫卡的全部艺术在于使读者不得不一读再读。它的结局,甚至没有结局,都容许有种种解释……如果想把卡夫卡的作品解说得详详细细,一丝不差,就错了。”
事实上,作家几乎不可能逃脱被阐释、被重新建构形象的命运。这一现象是普遍的,而卡夫卡则更为特殊。一方面是由于卡夫卡的作品自身存在着很大的解读和阐释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作家本人的经历。我们在学习文学史的过程中不难发现,越是年代久远的作家其神秘色彩往往越强,严谨的研究很难从荷马、莎士比亚的生平去解读其作品,因为荷马、莎士比亚其人是否是历史上某一具体的人,或者是否真实存在过,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对此类作品的解读会更多地关注作品本身。而与之相反,越是晚近的作家,研究者越倾向于从作家本人的经历、性格、心理创伤等私人的一面,去寻找其创作过程中诸多谜题的答案。
作为二十世纪的作家,读者和研究者有大量的卡夫卡的照片、书信,但是这些仍然很难还原一个真实的卡夫卡。与其他作家不同,卡夫卡对自己的作品极其苛刻,甚至临终时嘱托朋友销毁自己的全部手稿。他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病逝之后由好友马克斯·布洛德整理发表的。因此,读者和研究者对卡夫卡的解读之中,很难说清楚其中渗入了多少布洛德个人的思想和情感色彩。虽然在整理和保存卡夫卡遗稿方面,布洛德功莫大焉,但是他对卡夫卡的二次塑造也一直为学术界所诟病。米兰·昆德拉批评马克斯·布洛德以及他开创的“卡夫卡学”,认为他把卡夫卡描绘成一个圣徒,从而把卡夫卡逐出了美学领域。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有一篇《被阉割了的圣伽尔达》讨论了这个问题。昆德拉认为,真正的卡夫卡与布洛德呈现给人们的那个“受难的圣徒”的形象出入很大,当然,真正的卡夫卡应该也与读者心目中的那个敏感、孤独、苍白、昼伏夜出、吸血鬼式的忧郁作家有一定的区别。
正如人们常说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其实,在一千个哈姆雷特产生的同时,还会同时产生一千个莎士比亞。所以,有一千个读者也会有一千个卡夫卡。学者海因兹·波利策在传记《弗朗茨·卡夫卡》中这样写道:“只要人类还在思考、谈论和阅读,他的作品就应该被解读。”作家的被解读是无法控制的,所以,我们的青年读者对卡夫卡的诗性解读也就无所谓正确与否了。
作者简介:
孙蒨蒨,1986年出生,文学博士,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19世纪末英国文学,爱尔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