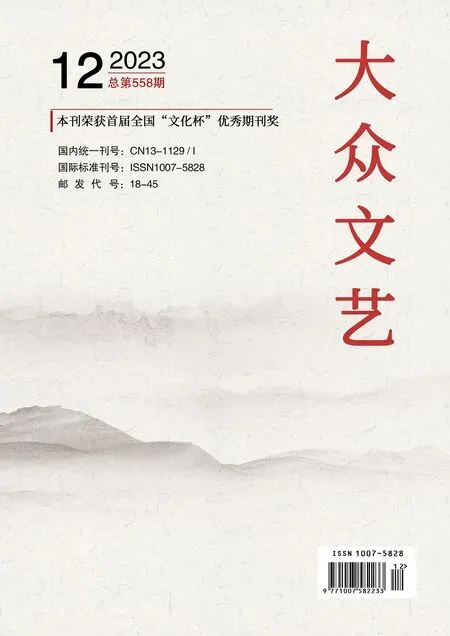清代广州外销花鸟画之写实性探析
2023-07-25吴丽盈
吴丽盈
(广州美术学院,广东广州 510000)
18世纪初至20世纪初,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随之发生的交流也在悄然影响着中国与西方的艺术。在中国,自“禁海令”以来,全球贸易的通道集中在广州这一通商口岸,也因此形成了一股在广州订购中国外销画的热潮。外销画是画师接受外国委托人定制,绘制出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世界的画。外销画呈现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事无巨细的中外贸易过程,满足了西方人对了解遥远神秘的中国生活的好奇心。其中有一类题材——花卉,是欧洲贵族,尤其是贵族女性所喜爱的。花卉纹饰的使用,主要集中在欧洲贵族的昂贵器具上。但除了瓷器上的花卉,外销画中的花卉也不失热度,流传下来的外销画藏品不乏花卉题材的精美画作。这样的艺术形式,借由中国画师之手,在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基础上进行了西方艺术的写实性探究,既结合西方人的审美情趣,又呈现出中西艺术文化融汇的艺术趣味。
一、以花鸟工笔探索写实技巧
本文以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套花卉主题外销画为主要研究材料。这里需要定义的是,由于这一套藏品不是出于生物学意义上再现中国花卉种类的植物图册,而是包含了近乎中国传统绘画元素的花鸟画,比如花、鸟、昆虫等等,因此后文统称这一套花卉题材的绘画为“花鸟画”题材。经考据,这一套花鸟画由赫斯廷斯和他的夫人收藏。“出身军人和政客的赫斯廷斯领主莫伊拉伯爵,后晋升为赫斯廷斯侯爵,于1812-1823年任职孟加拉总督,在此期间,他和夫人收藏了这些画册。1995年,主要是因为画册的印度题材,在英国国家艺术收藏基金会的协助下,大英图书馆购进了赫斯廷斯收藏的这批画集。……至于赫斯廷斯如何获得这些中国画册则不可考。这一系列绘画,应该是出自同一画师之手。”[1]笔者认为,大英博物馆对这套作品出自同一画师的简介有待商榷。外销画出于其商业交易的目的,采取的是流水线的作业形式。[2]只有特别重要的作品经委托才会由画室的主人来独立完成。因此,这组画可能不是出自同一画师之手。对比西方的植物图册类型绘画,这一套藏品有着明显差异。[3]首先,在主题上,植物图册的目的更多在于满足植物学家在中国对植物学研究的需求,尽可能多方位地呈现出植物的根、茎、叶的具体样貌,甚至呈现出了植物的虫害[4]。而这套花鸟画则传达出了中国传统花鸟画中的吉祥寓意。其次,在技法上,以研究为主要目的植物图册,委托人十分强调其准确性。这套藏品将中国花鸟的题材在技法上融汇了西方的写实画法——在纸本上的样式试图摆脱毛笔画法的点染皴擦,转而用西方绘画中的透视原则、颜色深浅的调子来表现明暗。尽管没有了以诗入画的文人花鸟画趣味,却留下了以花鸟工笔为基础探索西方写实技法的痕迹。
一般而言,外销画的套图以12幅为一套,这与西方的计量单位“dozen”有关,即“一打”。这一套藏品部分画作已经流失,只有7幅已收录的作品,分别是《桃花与双鸟》《牡丹与鸟》《梅花与白头翁》《花与喜鹊》《香石竹与蝴蝶》《芙蓉与蝴蝶》《菊花与蚱蜢》。从名字上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前4幅画是花卉与鸟的组合;后3幅是花卉与昆虫的结合。这种组合方式,在19世纪早期,甚至追溯到最早的宋代花鸟画,都是一脉相承的形式。[5]我们再来观察西方艺术史画面中呈现出来的花卉,多不以独立的形式出现在画面中,我们比较熟知的静物画,也不会以花卉和昆虫、鸟类的组合方式呈现,多是以花篮和占画幅非常小的蝴蝶相辅,比如扬•勃鲁盖尔的《蓝色花瓶里的花束》。因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这一套绘画并未在构图和题材上受限于西方绘画。但是在具体描绘所施用的技法上,已经深深受到西画东渐的影响。虽然我们无从考据这位画师如何将传统的花鸟工笔画改成外销画的形式,但是我们可以确定,这套绘画使用的欧洲纸能够说明主人对这套画的珍视程度。这套作品被作为伯爵等级的贵族收藏保留至今,一定是深受主人喜爱的。同时也证明这样的融汇方式是成功的,满足了外销画的商业目的。如若完全按照水墨画法的工笔花鸟与文人意境的呈现,作为西方艺术语境下的艺术鉴赏并不能为这样的喜爱背书。因此,我们大可以根据这幅画所考据的时间——19世纪早期,与之比较当时的花鸟工笔画,从中洞见西画东渐对这套花鸟主题的外销画的影响。外销画中的花卉植物主题,构图、设色都是中国传统工笔花鸟画的典型风格,但却在极力探索着西方写实性的技法表现。
二、欧洲纸特殊的写实性
本文所讨论的外销画均在欧洲纸上作画,不同于数量庞大的水彩通草画。通草画在翻译之初,因其薄如蝉翼的特点,被外国人错译为“rice paper”。而实际上通草纸是从“通脱木”的茎髓中削割出来的植物纤维,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经过造纸工序的纸。[6]通草纸因价格低廉、原材料获取便利、纸张上显色鲜艳等等优势得到了广泛使用[7]。通草纸的使用,给了外销水彩画师们以广阔的发挥空间:在类似中国宣纸的纸面上绘制出西方人喜爱的写实风格。通草纸不同于欧洲纸或者是油画所用的帆布,能够反复叠加颜料,要在通草纸呈现出西方写实绘画所必需的明暗对比,则需要在通草纸的正反两面均敷色,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通草纸不易保存,干燥或潮湿都可能会使原画遭到破坏[8]。大部分外销画室出于商业成本的考虑,除非委托人特别要求,一般不会使用昂贵的中国纸或是进口的欧洲纸。而这一套藏品正是受委托人要求在欧洲纸上作的花鸟画。对比其他的通草纸水彩画,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来欧洲纸的色彩更加典雅且不失耀眼的艳丽。由于欧洲与中国的颜料、纸张等材料在使用上的不同,这一套欧洲纸也给外销画师们带来了绘画上的难度——尽管外销画师们借鉴了外国版画、油画等真实的西方艺术,却仍无法完全复刻西方艺术的写实风格,也因此产生了外销画中西合璧的质朴画风。

图1 《桃花与双鸟》 19世纪早期 欧洲纸水彩画 高40厘米、宽29厘米[1]
三、传统花鸟工笔与西方写实技法结合的探索
(一)独具一格的花卉
《桃花与双鸟》的整个画面中最出彩的便是桃花浓艳的红色。桃花在中国画中寓意着桃花运、大展宏图等。但画幅中桃花的比例,颇有牡丹的艳丽之味。这样的艺术处理,可能是基于画师本身对处理桃花的不熟悉,抑或是根据委托而特意改变。桃花枝干的设色,直白地将枝干的棕黑色以西洋晕色的深浅敷色法呈现出来。这种设色方式在传统工笔画鸟中是少数,仅仅在郎世宁等人的西洋画法的工笔中可见,其余中国传统工笔花鸟画都在尽可能地隐去外部的轮廓线条,即我们熟知的“没骨法”。尽管这幅画最终呈现出的效果更偏向于中国的花鸟画,但是我们在宋代流传甚广的花鸟画中无从找到该样式的踪迹:其一是其水墨晕染的设色,与该画中的精描细绘不尽相同,尤其是文人花鸟画,讲究笔墨酣畅淋漓与一气呵成的意境。[9]而这里桃花的枝干,却清楚地将枝节用精确的西方明暗技法表现出来。桃花应有的花蕊也被忽略了。根据画中所呈现出枝干和叶子的颜色,我们可以推测这是桃花中绛桃品种,绛桃生长区域十分广泛,可以从东北南部延伸至广东、西北、西南地区。画中还有一个非完全写实的部分在新生的枝丫的颜色。新生的枝丫并不会呈现完全的绿色,而是介于枝干与绿芽之间的混合颜色。对于画师最终做出的处理,笔者推测有两种原因:一是枝干与新生枝丫、花卉的绘制由两位甚至多位画师完成;二是画师并未对桃花的盛开进行过严谨的植物学观察,而是采用了临摹的方式,对新生的枝丫和开花的部分进行了想象和创造,使得画面看上去更具生气。在《梅花与白头翁》,梅花的呈现也略显平面化。《香石竹与蝴蝶》中的香石竹,即我们熟悉的康乃馨。其枝叶都符合其植物学特征,但是这香石竹生长的位置却引人好奇——为什么香石竹会长在石头里?且不说突然出现的石头,石头的颜色也是非常罕见的蓝色,这个蓝色和整幅图中的香石竹中别致的一朵蓝色小野花用的是同一种颜料。同样有石头出现在画中的还有《菊花与蚂蚱》,菊花一样是不会长在石头里的花卉。菊花内芯是红色的,外圈花瓣却是黄色的,这样的花卉从来不曾出现在宋以来院体画中,显然这是画师的自然创作。而在《芙蓉与蝴蝶》中的木芙蓉花,其叶子的形态、尚未开放的花苞,几乎是完全还原了木芙蓉的样式,但是却同样缺少了花蕊。呈暗紫色的木芙蓉,经过了画师的调色处理,绘制出了现实生活中很难见到的澳洲芙蓉的暗紫色——木芙蓉在中国生长的种类,并不会呈现出这样的颜色。在这一株花卉中,还有一株待开的百合,增添了整画花卉种类的多样性。
由此我们也可以作一个基本推测:这套藏品所呈现出的写实性,并非真的符合现实中花与鸟的比例,而是基于画师对中国传统工笔花鸟画的结构掌握以及想象性地创造出了西方人喜爱的“写实”画面。
(二)寓意美好的鸟类
《芙蓉与蝴蝶》喜鹊的尾翎的画法,在这幅花鸟画中是独创。我们回观宋代院体画传统的喜鹊画法,多展示尾翎的正面,并且这个正面多顺着羽翎生长的方向顺势而为。而这里的尾翎却用了多个重叠的分叉细致地描绘,这种羽毛形式其实并不符合生物学上的生长规则。《桃花与双鸟》中的鸟虽说在名字上无从考究是什么品种,但是我们从以下证据可以大胆断定是喜鹊。首先,“双鸟”给了我们不少寓意上的线索:成双出现的鸟儿,多在花鸟画中表达好事成双,或是寓意爱情白头到老的美好愿景。相反的,则可能是文人画家对个人精神世界的消极情绪表达。例如李安忠的《竹鸠图》中,仅绘制了一只竹鸠,其寓意便不在于美好祝愿。画中这两只喜鹊相互对视,这样的交流也是喜鹊在中国画中常见的样式。尽管真实的喜鹊头部与尾部的羽毛都是黑色,但是我们从喜鹊的尾翼可以判断这是两只喜鹊——因为燕子的尾翼呈分叉的“Y”字形。这组的喜鹊颜色与样式的特征,也与后一组画中的《花与喜鹊》的样式不谋而合。画师将喜鹊头部的黑色与尾翼的青色相通用,喜鹊的眼部却做了红色处理。生物学上并没有红眼圈的喜鹊品种,但是在纸本绘画上进行艺术处理是十分常见的行为。这一艺术处理在《梅花与白头翁》《花与喜鹊》中都用了相似的处理方式。这里笔者大胆猜测——在同一种颜色背景下,用墨色渲染黑色的眼睛,容易让小鸟的眼睛变得麻木无神。如《桃花与双鸟》图示左边的喜鹊,在青色中用暗色点染眼睛,显然没有右边的喜鹊那样喜庆生动。真正的白头翁头上也并没有这样突出的鸟冠,鸟嘴下的羽毛也并非红色。
对这些鸟类的详细解读,我们会发现外销画师在绘制鸟类时,尽管在主题上延续了中国花鸟画传统的美好寓意,但是在写实技巧上的探索仍在进步中,尚未达到西方委托人所最为推崇的形象上的精确性。
(三)灵动生趣的昆虫
我们对比南宋时期同样是画了蝴蝶的两幅工笔画,以参照外销画中蝴蝶的画法,比如朱绍宗的《菊丛飞碟图》与一幅无款的《晴春碟戏图》[5],我们能明显看到南宋院体流传下来的样式得到了相近的继承:外销画画师沿用了描绘蝴蝶的相同角度,都是蝴蝶的侧面或是正侧面来表现蝴蝶舞动翅膀的活力。但是根据我们对昆虫与绘画的基本认识,外销画上的蝴蝶均不属于现实中的任一品种——蝴蝶并没有类似外销画上这样规则的彩色条纹。很显然这里出现了外销画师的个人创作,一方面外销画师并没有对绘画有着非常极致的追求——他们的最终目的仅仅是为了将这一套绘画销售出去;另一方面,这组画的委托者也不会是需要高度准确性植物图册的植物学家,否则这样的作品是一定不会被委托人照单全收的。那么在《芙蓉与蝴蝶》里的蝴蝶,尽管在生物学的色彩观察上仍失细致,没有做斑斓的点缀,但是在细节上已经极力靠近整画的色彩映衬——蝴蝶翅膀的上部与下部均是芙蓉花的主色调——红色与紫色,并且在蝴蝶的翅膀处,也画出了和鸟儿翎羽般的细致纹路,让蝴蝶的描绘在观感上细节更丰富。《菊花与蚱蜢》里这只蚱蜢的比例显然不符合西方传统意义的透视原则——蚱蜢的身长已经快要超过整朵盛开的菊花;蚱蜢的腹部颜色也充满了想象性的创造,生物学上蚱蜢的外观,要么通体红色,要么通体绿色。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外销画师们对昆虫、石头的创造性描绘、对西方写实技巧的不断探索与呈现,使得这一套外销花鸟画平添几分中国传统花鸟画所不具备的趣味性与想象性。
结语
中国出口的外销画在数量上是非常惊人的,尽管这些外销画究竟从何地产出、出自哪位画师之手,已难以考究。但是我们从成套收藏的珍品做出细致的图像解读,可以从中获取许多有趣的信息:当时的画师们是如何根据已有的艺术材料进行艺术创作,并成功的满足了委托人的要求销售出去。外销画不仅有着十分重要的商业价值,还有非常值得考究的艺术价值——我们可以看到在西画东渐影响之下,中国传统的绘画如何受到冲击,创造出别有风致的中西结合的花鸟画。尽管这些画师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绘画训练,但是其整体表现出的绘画手法和处理方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绘画的学习观——既保留了中国绘画中的主题、构图,又为了满足委托人的需求尽力将画面显现得更加丰富,在色彩的工整写实中表达着体积感,在实情实景的观察中再现着中国花鸟的情趣美与意境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