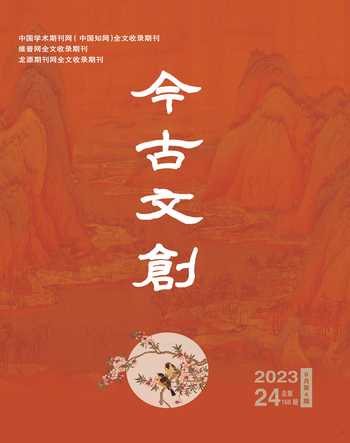论《海上花列传》中的疾病隐喻
2023-07-21俞沈峰
俞沈峰
【摘要】文学中的疾病书写往往不仅是“病人”生理、心理病症的描写,更作为一种隐喻符号,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尤其是晚清—五四小说中,疾病的隐喻功能大大增强,疾病描写背后常隐含着作家对“启蒙/被启蒙”“现代/传统”“巫术/科学”等问题的深层思考。《海上花列传》作为古今转型的标志性小说,其中李漱芳疾病的书写也有着深层的隐喻和丰富的内涵。韩邦庆也借此表达了自己对“传统—都市”转型期间社会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疾病隐喻;《海上花列传》;李漱芳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4-000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4.002
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这座普通的海滨小县城一跃成为中国重要的“大都会”。伴随着这座城市商业发展的,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快速转变,是市民精神、文化思想的转型。商为末的格局被打破,传统社会中宗教、巫术的观念也被所谓“现代性”祛魅思想改变。简而言之,社会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面对社会文化的快速转型,人们一般会有三种状态:完成过渡、正在过渡、拒绝过渡。《海上花列传》主要表现的是前两类人。罗子富、洪善卿等商人已经习惯于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卫霞仙、黄翠凤等倌人也深谙狎客们的心理。港口的开放和贸易的往来让商人们最先接触到外来事物,自然,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最先影响的也正是这些人。而妓女为着生意考虑,被迫地进入现代化的生活当中。洋镜、洋灯已成为她们装点门面的重要物品。“金钱”和“欲望”交织的上海滩十里洋场上,他们是最先完成过渡的一类人。从乡下进城的赵朴斋、赵二宝则是文学史上独特的“乡下人”形象。赵朴斋在花天酒地中迷失自我,从花上海的黑甜乡中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穷困潦倒,只得拉车为生,即使这样也不愿回到乡下。而赵二宝还坚信着“才子佳人”的传说,在以金钱为主导的“妓院圈”中,落得一个被抛弃的下场。这一类人虽然被现代性的浪潮裹挟着前进,被都市的欲望吸引,但本质上他们仍未完全摆脱自己的“乡土性”,是带着“都市想象”进入城市现代化体系当中的。
李漱芳却是《海上花列传》中一个独特的角色。她做了好几年倌人,谙熟人情世故,深知在上海这样的都市中如何经营好自己的生意。生病前的李漱芳也有“几花老客人”;客人看李浣芳“好白相,才喜欢俚,叫俚个局,生意倒忙煞” ①。东兴里的生意一直倒还不错。但同时,她对“真情”与“真爱”抱有强烈的幻想。她不像卫霞仙、黄翠芬那样,已经麻木于,甚至享受于都市中的种种欲望,也不像赵二宝、赵朴斋那样,自觉走入现代化都市当中。李漱芳进入倌人圈多少有些无奈。正如钱子刚所言:
“李漱芳个人末勿该应吃把势饭。亲生娘勿好,开仔个堂子,俚无法子做个生意,就做仔玉甫一个人,要嫁拨来玉甫。” ②
虽只“就做仔玉甫一个人”,但与陶玉甫感情甚笃,“要嫁拨来玉甫”。可惜“倘然玉甫讨去做小老母,漱芳倒无啥勿肯,碰着个玉甫定归要算是大老母,难末玉甫个叔伯、哥嫂、姨夫、娘舅几花亲眷才勿许,说是讨倌人做大老母,场面下勿来。” ③李漱芳不愿做倌人,难以融入都市社会;但她因为妓女的身份又不容于传统社会,无法嫁给陶玉甫。生存在传统与现代社会夹缝中的李漱芳只能闷闷不乐,积郁成疾,得了痨瘵,也就是肺结核。从李漱芳得病的原因不难看出,肺结核不再仅止于一种生理上的疾病,还代表着社会文化上的生存困境,背后有其更深刻的隐喻。
一、“病的李漱芳”与“李漱芳之病”
——现代社会边缘人形象
当时,上海妓女的身份已不止于“性交易”的对象,更扮演着“清客”的陪衬角色,具有重要的社交功能。陪同客人出席酒宴是倌人的“日常工作”。但李漱芳缠绵病榻,常不能陪同她的相好陶玉甫参加商人间的酒宴。因此,韩邦庆给了李漱芳一个特别的出场。在一次李漱芳缺席的酒宴上,她的相好陶玉甫的哥哥陶云甫与其他客人谈起了自己和李漱芳相处的“趣事”,他道:
“啥缘分嗄,我说是冤牵!耐看玉甫近日来神气常有点呆致致,拨来俚哚圈牢仔,一步也走勿开个哉。有辰光我教玉甫去看戏,漱芳说:‘戏场里锣鼓闹得势,覅去哉。我教玉甫去坐马车,漱芳说:‘马车跑起来颠得势,覅去哉。最好笑有一转拍小照去,说是眼睛光也拨俚哚拍仔去哉;难末日朝天亮快勿曾起来,就搭俚舔眼睛,说舔仔半个月坎坎好。”大家听说,重又大笑。④
久病的李漱芳身體虚弱,受不了戏场、马车的吵闹,而且,照相机的光对于她来说,也有巨大的伤害。短短三则旧事,生病的李漱芳的柔弱就在陶云甫的调笑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晚清小说中的疾病被作为隐喻使用时,其审美化功能已消失,疾病不再赋予人物以林黛玉式的病态美,也不具有拜伦式的浪漫化色彩,它是一个与中国古老的病体相一致的隐喻,疾病象征着羸弱、衰败、阻碍、退化、阴暗、死亡和一切消极负面的东西。” ⑤从众酒客“大笑”的反应可以看出,病的李漱芳已经失去了审美上的意义,是作为一个异类与笑话存在的。她虽是倌人,但倌人圈似乎从未正式接受这个“生病的人”。
“在所谓共同的想像和权力话语的策划下,疾病被赋予种种隐喻,而患病的人,即疾病的承载者,则被种种疾病的隐喻扭曲成了被排除在正常人之外的‘他者。” ⑥毫无疑问,陶云甫是都市社会掌握主流话语权的商人,而酒席正是倌人、狎客寻欢作乐的主流场所。作者利用李漱芳的一次缺席,以陶云甫之口介绍李漱芳,自然有其用意。
在这里,马车与照相术是两个重要物什。罗岗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海上花列传》中的“马车”不是指一般的“马拉车”,而是特指西洋敞篷马车。“‘马车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上海拥有了一种新式的交通工具,而且从侧面反映上海市政建设的发展、城市空间的拓展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形成,因为伴随着新式交通工具使用,人群的快速移动必然对街道、市区以及公共秩序的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可能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带来某种不同以往的娱乐和休闲方式。” ⑦可见,马车是工业文明的新产物,更代表着新的秩序与新的生活方式。1839年,“达盖尔法摄影术”出现,这一年也被认为是摄影术出现的元年。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包括上海在内的五座沿海城市被划为通商口岸,为摄影术传入中国开辟了通道。商人正是摄影术的重要传播群体。因其“外来”身份和对当时来说十分新奇的用途,照相术的相关谣言也层出不穷。“照相术发明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其有摄魂的神秘功能。而在照相术传入中国后,中国人也多以妖术视之。” ⑧关于照相术的谣言以“摄魂”“挖眼”为多。李漱芳看到这摄取光影的新技术,运用传统巫术的观念,对照相术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正如王宏超所说:“传统社会是宗教的、巫术的、道德的,现代社会是科学的、技术的、理性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有其‘整体知识,在传统社会中对于技术的理解,多是基于其宗教、巫术的知识视野,而在现代社会中对于宗教等的理解,也常会基于理性的知识视野。” ⑨大家听到陶云甫所讲之事后大笑,一笑陶玉甫、李漱芳你侬我侬关系好,在那些逢场作戏的倌人和狎客眼中,他们就是异类;二笑李漱芳身体差,太过柔弱;三笑李漱芳太过迷信,不讲科学。“理性思想”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 ⑩“祛魅”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陶云甫、罗子富等人已经习惯自己“祛魅的”“理性的”“现代人”的身份,自然要嘲笑李漱芳“落后的”“可笑的”传统思维。可以看出马车和照相术的发展与中国,尤其是上海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也显示出现代性思想在当时的强大影响力。“闹得势”“颠得势”“眼睛光被拍了去”,作者用病的症状来写李漱芳对现代事物的排斥。或者说,李漱芳之病更深层的内涵,是李漱芳传统的、巫术的思维。在“现代性”代表着“进步理性”的语境下,传统观念有着“病”的“柔弱”“落后”的特点。陶云甫口中的李漱芳之病,其实是传统农耕社会之病。
“这一文化(西方强势文化)特征反映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构成了‘海派文学的最大特色——繁华与糜烂的同体文化模式:强势文化以充满阳刚的侵犯性侵入柔软糜烂的弱势文化,在毁灭中迸发出新的生命的再生殖,灿烂与罪恶交织成不解的孽缘。” ?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映衬下,传统农耕文化展现出了病态的羸弱与愚昧,并在这种外来冲击之下渐渐式微了。
二、“浪漫化隐喻消解”
——东兴里“类家庭”模式的建立与瓦解
“从《海上花列传》的都市叙事开始,以‘夜作为一种复杂隐喻的传统文化代表的“家”退居幕后甚至消失。” ?妓女堂子成了狎客、倌人聚集的主要场所,主要叙事空间从“家庭”转变为“妓院”。书中只有倌人的家(堂子),没有了客人的家。而倌人的家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人空间,而是嫖客社交的公共空间和交易的市场了,虽有家的名号,却无家的实质。但是,隐匿在夜的狂欢中的传统“家庭模式”,在生病的李漱芳所住的东兴里,又出现了“类似”的影子。
“长久以来肺结核就与爱情和死亡的想象结合在一起。病人身体的消耗与欲望的满溢往往形成一种吊诡,平添了一层浪漫的色彩。” ?肺结核作为不治之症,不断消耗病人的身体,但不会让病人快速死亡。同时,肺结核的传染性也给照顾肺结核患者的人带来了对自身生命安全的担忧。“患上肺病对于热恋的人来说不仅不会构成障碍,反而会成为爱的试金石甚或催化剂。” ?《海上花列傳》中的疾病书写是围绕着李漱芳展开的。书中不仅写了李漱芳的病,还写了李浣芳、陶玉甫的病。李浣芳在一次夜里出局受凉,李漱芳拖着病躯与陶玉甫百般照看。李漱芳病重,陶玉甫彻夜照顾,最后也累得病倒了。肺病的浪漫化隐喻,本质不在于传染性风险,而在于愿牺牲自身健康与爱人相伴。李漱芳带病照顾李浣芳,陶玉甫因照顾李漱芳积劳成疾,正是围绕肺结核而衍生出的类似于“一起被传染”的真情。在这个“客人骗倌人,倌人骗客人”的都市当中,李漱芳和陶玉甫、李浣芳的真情,自然体现其“反都市化”的一面。
如此真情,让陶玉甫身上肩负着照顾李漱芳的责任。第七回中,罗子富豁拳豁至陶玉甫那,陶玉甫输,要罚酒。代替李漱芳出局的李浣芳不让陶玉甫喝,弄得台面冷清。罗子富觉得无趣,让陶玉甫有事先走,陶玉甫便讪讪地离开了。本来,这种商人间的宴席才是男性的主要社交地,倌人只不过是陪同。但李漱芳的病时刻牵动陶玉甫的心,让“去”东兴里有了“回”的感觉。韩邦庆也在书中用了“归”字来形容陶玉甫去东兴里的行为。?“流动性”是现代都市的一大特征。商人不停翻台、谈生意,空闲的时候便出入堂子;倌人作为狎客的附属,也需要为着狎客的需求不停地被动移动。哪里有生意,就往哪里流动,这似乎成了嫖客、倌人的日常了。但李漱芳因着养病,不能陪同陶玉甫出局;陶玉甫为了照顾李漱芳,经常不顾饭局就往东兴里跑。东兴里变成了类似于家的相对稳定的地方。而且从表面上看,李漱芳和陶玉甫也在无形中建立了类似于“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的家庭模式。只是,这种模式不同于以地缘—血缘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家庭模式,这种因“情”而成的“家庭模式”只能是“类似”。
东兴里这种“类家庭模式”的建构还体现在李漱芳央求陶玉甫娶了李浣芳。李漱芳和李浣芳虽然不是亲生姐妹,但感情极深。李漱芳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便手指浣芳,“俚虽然勿是我亲生妹子,一径搭我蛮要好,赛过是亲生个一样。我死仔倒是俚先要吃苦,我故歇别样事体才勿想,就是该个一桩事体要求耐。耐倘然勿忘记我,耐就听我一句闲话,依仔我,耐等我一死仔末,耐拿浣芳就讨仔转去,赛过是讨仔我。” ?
李浣芳一直是以李漱芳替身的身份出现在读者面前的。陶云甫在李漱芳死后就说:“陆里晓得个李秀姐定归要拨来玉甫做小老母,俚说漱芳苦恼,到死勿曾嫁玉甫,故歇浣芳赛过做俚个替身。” ?李漱芳想让李浣芳代替自己,来弥补自己不能嫁与陶玉甫的遗憾,她心中仍保留着传统的“婚姻—家庭—稳定”思维模式。
只是,疾病的浪漫化的隐喻在李漱芳死后消失了。陶玉甫最后拒绝去娶李浣芳。很明显,让李浣芳与陶玉甫结为夫妻,只是李漱芳的一厢情愿。李漱芳一死,陶玉甫与东兴里的关系就变成了简单的堂子与客人的关系了。前文中说到,李漱芳因困于现代与传统之间而病。李浣芳虽没有生病,但又何尝不是传统、现代两种社会的边缘人呢。李漱芳的美好幻想,并不能因为病死而实现。这种在堂子里建立的“类家庭模式”的彻底瓦解,是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必然。
三、《海上花列传》主题探究
“‘都市狭邪小说作品之所以出现新的价值观念、矛盾复杂的社会心态,甚至一方面得意地享用都市化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自觉地表现出‘反都市化的倾向,正是因为近代上海都市文化还不成熟不完善,人们相关的生活经验十分稀少,不能领会驾驭现代都市的经济内涵和市场生存方式孕育的一套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是都市文化初级阶段的自然表现。” ?李漱芳这一形象带有一定的“反都市性”色彩。但是,她毕竟背负着一个柔弱的身躯。置于现代化的大潮中,她无法回首,走向过去。李漱芳一死,陶玉甫痛哭,哭的是李漱芳,哭的也是李漱芳的生存困境。作者以李漱芳之“死”来探讨新都市人在新道德和新秩序该如何生存的问题。历史转型的背景下,置于迷眼的海上花之中却找不到根蒂的茫然感和轻浮感,和夹于现代与传统之间,无法找到文化认同的生存困境,可能是作者真正想要传达给读者的。
注释:
①②③④??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11-312页,第325页,第325-326页,第62页,第177页,第482页。
⑤谭光辉:《晚清小说中的疾病隐喻与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2期,第82-87页。
⑥查日新、汤黎:《浅析桑塔格对疾病隐喻的文化解读》,《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7期,第79-83页。
⑦罗岗:《性别移动与上海流动空间的建构——从〈海上花列传〉中的“马车”谈开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89-97+123-124页。
⑧⑨王宏超:《巫术、技术与污名:晚清教案中“挖眼用于照相”谣言的形成与传播》,《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第162-171页,第162-171页。
⑩(德)马克思·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三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陈思和:《论海派文学的传统》,《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1-6页。
?吴智斌:《〈海上花列传〉“夜”叙事时空的近代建构》,《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7年第10期,第120-130页。
?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姜彩燕:《疾病的隐喻与中国现代文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81-85页。
?见小说第三十六回。
?樊祥鹏:《近代上海狭邪小说与都市性》,《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30-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