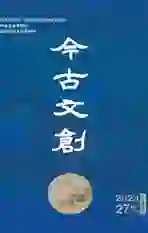《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之异及其意旨探析
2023-07-21周琪儿
周琪儿
【摘要】《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一直是中国清代小说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在研究中运用比较的方法探讨《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的关系,进而可以深化对文本主旨的认识,丰富对文本内涵的阐释。本文在多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南京城市形象建构、叙述视角层级差异、社会理想建构异同三个方面探析两书诗性与理性的不同主题,继而明晰《儒林外史》冷静老练、沉稳圆熟的理性与《红楼梦》酣畅笔墨、畅意襟怀的诗性。
【关键词】《红楼梦》;《儒林外史》;南京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7-003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7.012
一、实与虚——南京城市形象建构
《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都成书于18世纪中叶;《儒林外史》大概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比《红楼梦》第一个较为完整的版本早10年左右;但《红楼梦》的印行在1791年,又比《儒林外史》最早的一本早12年。由是,二书的成书、刊印时间相互交错,基本可以视为同期作品,它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是相同的。两人之于南京的情结虽有不同,但也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土壤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对南京的切实关注或者怀念向往,促使他们将目光投向南京这座城市。由是,两位作者笔下所同构的南京是可以进行对读的。
《儒林外史》中所描绘的南京是写实的、三维的、多角度的南京。书中有关南京的描写与《红楼梦》的蒙眬模糊相比更为直接明确,在全书56回中,有21回直接描写南京,很多回目以当时南京的地点、名胜为回目内容,如“鲍文卿南京遇旧”“萧金铉白下选书”“逞风流高会莫愁湖”“庄濯江话旧秦淮河”等等。《儒林外史》从节日民俗、风景名胜以及日常生活、饮食习惯等对南京这一城市形象进行了全面的塑造。总的来说,小说中有关南京的描写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是客观性大于主观性的,在纪实性的描绘中蕴含着作者对南京的独特感情。
而《红楼梦》中的金陵则是幻想中的审美化的表达方式,是一种若隐若现的情结,是作者情感大于现实,感性多于理性的产物,含蓄地表达作者潜在的深层思想和旨意。从康熙二年作者的曾祖父曹玺来到南京到雍正五年曹頫被撤职,后一年举家离开了南京,曹家在南京大概生活了六十余年。因此曹雪芹是从小在南京长大的,虽然他写作《红楼梦》是抄家落泊回到北京以后,但他的生活记忆是在南京。所以说,《红楼梦》表面上写的是北京,但是是以南京的风土人情、地域文化为背景的,追溯的是自己的童年回忆,学界有说法称“大观园”其实是现实中的南京“随园”化身,而曹雪芹侧面用“金陵十二钗”、在金陵的“甄家”也就将南京符号化、意象化了。因此曹雪芹心中的金陵是幻想远大于现实的,是作为朦胧而诗意的故乡存在的,所以在景物描绘上难免陷入固定写作的程式之中。
例如描写花园,《儒林外史》中是如是描绘的:“面前一个小花圃,琴樽炉几,竹石禽鱼,萧然可爱。”或是“园里合抱的老树,梅花、桃、李,芭蕉、桂、菊,四时不断的花。又有一园的竹子,有数万竿。园内轩窗四启,看着湖光山色,真如仙境。”从中可见吴敬梓舍弃了章回小说长期沿袭的模式化、骈俪化的韵语,而是白描为多,寥寥数笔尽显文人理趣。《红楼梦》中则雕琢更多:“只见正门五间,上面桶瓦泥鳅脊,那门栏窗槅,皆是细雕新鲜花样,并无朱粉涂饰,一色水磨群墙,下面白石台矶,凿成西番草花样。左右一望,皆雪白粉墙,下面虎皮石,随势砌去”“崇阁巍峨,层楼高起,面面琳宫合抱,迢迢复道萦纡,青松拂檐,玉栏绕砌,金辉兽面,彩焕螭头。”包括各个园子的题诗,都走向了浪漫主义的摹写之中,虽然是对大观园的“实地的描画”,实则被传统的美学体验所遮蔽,产生了某种扭曲与异构,在向纯粹的绘画方向迈进的同时,也走向了风景建构的套路。
两人描绘南京的视角也是不一样的:《红楼梦》是贵族的视角,《儒林外史》是更贴近于平民的视角。《红楼梦》中用的有自鸣钟、玻璃镜、孔雀裘、软烟罗,吃的有茄鲞、螃蟹、鹿肉;而《儒林外史》中提及的则是“两边酒楼上明角灯”,玩的是“水老鼠灯”,穿的是方巾、高帽、布衣,吃的则是鸡鸭鱼肉,其中鸭被提及的次数多达41次,更多地体现出了当时南京的民俗民风、礼乐制度以及手工业经济的繁荣。这两个视角之间的阶级差异就导致了两位笔下建构出的南京形象的差异,《儒林外史》中的南京成了理性写实的代表,而《红楼梦》中的金陵成了诗性超验的符号。
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个性化情感的流露与个体经验的表达,《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对南京这一城市的关注与描绘,都集中地体现出这种深刻影响作品视角、内容、思想的创作态度,反映出作家的深层创作心理与文学品格。管中窥豹,吴敬梓笔下的南京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南京,是理性视角下的南京,凝聚着历史与现实;而曹雪芹笔下的南京则是具有梦幻想象的南京,是诗性视角下的南京,充满了象征与情感。因此,南京作为一个地理符号之于两人的精神意义是截然不同的。
二、嵌与隐——叙述视角层级差异
《红楼梦》首先以石头为叙述者,作为主叙述层占了绝大篇幅,而作者曹雪芹则处于超叙述层。全书以第三人称全知记录为主,辅以第一人称现身说法评价。但石头这一叙述者的神话色彩,导致了其可信与不可信的两种情况,更像是作者借以客观表现的主观抒情。并且作者通过在书中嵌套了种种多元的校勘编纂者们,例如空空道人、东鲁孔梅溪等,从而拉开了自己与自己经验世界的距离。石头与作者之间存在着叙事距离,也就带来了小说本身的故事性与神话色彩,更强调了一种间接性与虚构性。《红楼梦》卓然不群之處就在于它能将整体视角与频繁的限制视角相结合,高低、主次叙述层次错落有致,从而形成一种宏大的艺术寓意建构,既冷眼忘穿又热肠挂肚,既可信又可不信,既似真又似梦的杂糅成就了《红楼梦》充满诗性的叙事视角。
《儒林外史》的视角更多的是转换而不是各方杂糅,它的叙述层级是简单的,并没有采用层层嵌套的叙述模式。吴敬梓始终坚持了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在冷静客观的叙述中淡化了叙述者的存在感,例如使用“话说”“只见”等连贯,作者作为第一叙述者并没有与读者隔许多层,这有助于读者以叙述者的上帝视角来总揽全局,增加了叙述的真实性与历史感。作者秉持着一种史家叙事的传统,更近乎暗含褒贬的春秋笔法,更为含蓄蕴藉不明加评说,很好地隐藏了自己的情感,更加客观地呈现历史社会中人物的命运遭际与时代环境,留下足够的空间待读者评述。
所以《儒林外史》采用隐含叙述者、减少介入暗含褒贬的方式,形成了主次两个层级的叙述视角,而《红楼梦》采用了嵌套结构,在多元叙述中产生了三个层次的叙述视角,带来了真实和虚构两种不同的阅读体验。
三、游与讽——社会理想建构异同
在对待仕与隐的问题上,《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因为思想内核的不同导致了同中有异。人们可以看到对于功名利禄、科举取士两位皆秉持着鄙弃的态度,也都在文中指出了归隐这一条道路,但是《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中的“隐”呈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儒林外史》开篇直接塑造了一个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真正的“儒者” ——王冕,宦海浮沉后归隐山林,而《红楼梦》的“隐”则是皈依佛道、寻求“吾心安处”的“隐”,即使后面的“中乡魁宝玉却尘缘”为高鹗所续,也可以从“大荒山”“无稽崖”中窥见一二。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相应的是尼采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一是对外在理性所标画的超越世界的追寻;一是对个体内在情绪的抒发。这两种冲动代表着两种基本的人生哲学观:走向世界,故追求成功;走向内心,故期望超越。故《儒林外史》里对现实世界描绘与宗法伦理结合得比较紧密,而《红楼梦》对世俗生活、城市形象的描绘与对人物命运的描绘基本跳脱出了当时的整个时代背景和社会伦理。
《儒林外史》深入剖析后则会发现作者是以儒家文化传统为内核的。吴敬梓作为儒者,更推崇走向世界,更趋向于寻求“辞确功名利禄方法”,寻求儒家高尚的人格与冲淡平和的襟怀,是一种“圣人”“名贤”的价值态度取向。在面对出处进退的问题时,作者向人们树立了虞博士这一典型的儒者形象。在三十六回中虞博士道:“你这话又说错了。我又求他荐我,荐我到皇上面前,我又辞了官不做。这便求他荐不是真心,辞官又不是真心。这叫做甚么?”苏轼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中有言:“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想要做官,那就去追求,不要因追求仕途而感到不好意思;想要归隐山林,那就去深山老林,也不以为归隐就显得清高。虞博士在这里表明的志向即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欲进则进,欲退则退,他在平凡而琐碎的生活中,既没有陈腐的学博气,也没有傲慢的进士气,更没有无聊的假名士气。他对待一切都极为清醒,心如明镜,他既无虚幻的热情,又无僵硬的理性,襟怀冲淡,自然文雅,是作者笔下塑造出的儒家社会中的真实的理想人格,并成为儒林之中真正的典范。从虞博士这一形象中,可以看到作者儒家精神内核:始终葆有着对社会的忧患意识,有着浓厚的家国责任感和积极的人生理想。
相比之下《红楼梦》则是以道家文化传统为旨趣的。其中贾宝玉对待“仕”的问题采取的是“醉”的态度,即酒神精神,其实质就是于悲剧世界中发掘出备受压抑的允诺与自由。宝玉不愿面对“仕”这一问题的同时又享受着其带来的富贵,如若不是世家大族、代代为官他就不会拥有大观园中自由自在的生活。曹雪芹又何尝不是如此?正是因为社会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无法打破,权利既定的法则无法超越,于是在如此一个悲剧性的社会制度之下,浪漫主义的诗性只能转向个体内在情绪的抒发,这种离弃与否定承接的是对功名富贵乃至人生命运的幻灭感。对现实的厌倦与失望,让浪漫主义的芹卿选择了用“香丘”即理想来表达自我。这个“理想”绝非政治理想,而是文学、艺术的理想与人生的理想的同构。
由此观之,两書在精神内核上的不同也可以回归到主题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诗性与理性的差异。虽然《儒林外史》与《红楼梦》都推崇隐,都认为归隐是当时那个时代最应该选择的方式,但是红楼梦的隐是逃避责任的大观园,是一个不需要考虑任何生存问题的乌托邦,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世外桃源;而《儒林外史》中作者所认可的归隐则是范蠡式的功成身退,这种归隐是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可卷而怀之”为前提的。既然《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关于“隐”的态度以及两位作者一儒一道的思想内核已分析完毕,那么进一步深入则要探究到两位作者在社会理想建构上的差异,而这种理想建构的差异也在文本中通过游世与讽世来得以体现。
东方朔在《诫子书》中提到过“游世”的观点:“明者处事,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与道相从。”游世思想是庄子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也与《红楼梦》的社会理想是契合的,这种观点可以在宝钗称宝玉为“富贵闲人”之时窥见一二。《红楼梦》中的青年男女在逆境之下的对抗都不可以称之为正面反抗,而是摆出一切皆不在乎甚至是逃避现实的姿态以及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寻求个人内心安宁与自洽,来保护一种弱意义的精神生存欲求,这种不对抗在某种程度来说也达成了对抗。所以全书都是以大量的诗意与象征来消解、回避现实的残酷,试图借助哲学的抽象逃往虚幻的彼岸世界,从而获得精神的解脱。曹雪芹不但不谈政治也不讽政治,而是始终持有否定一切政治的思想,所以即便偶有讽刺但也是无关时事痛痒的,并非讽刺小说。也正是因为作者的“游世”之道,《红楼梦》中并没有明确地指出作者自己真正的社会理想,作者自己之于理想也是怀着“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的疑问。这种否定一切政治的结果就会导致灵与肉的双重虚无,大观园也只是乌托邦一样转瞬即逝的存在。
谈及讽刺的笔法,则《儒林外史》足可称之为讽刺小说。鲁迅:“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吴敬梓在全书中贯彻的则是“讽世”的主题。愤世嫉俗激发了吴敬梓的创作激情,使《儒林外史》处处迸发出讽刺的火花,例如范进中举一回极尽讽刺了那个时代读书人的庸俗丑态以及腐朽昏聩的政治制度,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结合起来,用看似喜剧的框架来演绎悲剧的主旨。除此之外作者还直接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作为讽刺对象,寓庄于谐,寓悲愤于嬉笑怒骂之中,在讽刺中多用反讽,不动声色间尽显“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艺术特征。在“讽世”中也明确表达了吴敬梓本人对当时政治制度的忧患意识,并以儒家思想提出解决之道,暗示了作者渴望礼乐重振、制度改造的社会理想,即“讽世”的背后依旧是“济世”的现实主义本色。
依此可见,“游世”就是逃避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冲突与道德准则问题;而“讽世”就是批判现实世界中种种不合理现象并提出解决之道,这两种处事方式也就是两位作者在社会理想建构方面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在《儒林外史》中,诗性是被现实所践踏的,因此作者在叙事中对诗意有所趋避;而《红楼梦》则竭尽全力向超脱于生活之境前进,所追求的是在世俗世界之外找到一个精神家园。因而对《红楼梦》情节自然要更多从形而上的道家立场去解读;而《儒林外史》则致力于揭开世俗的人生百态,于是在阅读过程中就需要读者的阅历并结合作者的时代背景,从而探与作品的意旨。
由是,当面对同样残酷黑暗的社会现实时,《儒林外史》则持以冷静老练、沉稳圆熟的讽世态度,《红楼梦》则以酣畅笔墨、畅意襟怀的游世精神来反抗,在城市形象、叙述层级以及理想建构方面可见其中的差异。所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的叙事过程中,始终不忘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就算时是理想也是基于现实的理想,绝非梦想,力求剖析出生活表面之下的最本质的逻辑来。曹雪芹早已经超越了传统小说物质生存、人生世相的层面,是从人心深处的人文情感或精神诉求入手,追寻的是无法寻觅的香丘。正如林黛玉所言:“我为的是我的心”,其展现出的是文人超越现实世界而寻求精神生存的诗性主题。
参考文献:
[1]李小龙.醉与醒—— 《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之异及其意旨探析[J].红楼梦学刊,2018,(6):166-183.
[2]张国風.双峰并峙,二水分流—— 《儒林外史》《红楼梦》之异同[J].红楼梦学刊,2020,(6):32-44.
[3]甘宏伟.论《儒林外史》《红楼梦》的“功名”与“隐逸”观[J].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2019,(00):160-167.
[4]葛永海.《红楼梦》《儒林外史》中“金陵情结”之比较[J].红楼梦学刊,2004,(02):174-195.
[5](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6](清)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7]陈文新,甘宏伟.站在《儒林外史》的立场看《红楼梦》——从胡适先生扬《儒林外史》抑《红楼梦》说开去[J].明清小说研究,2010,(1):124-136.
[8]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