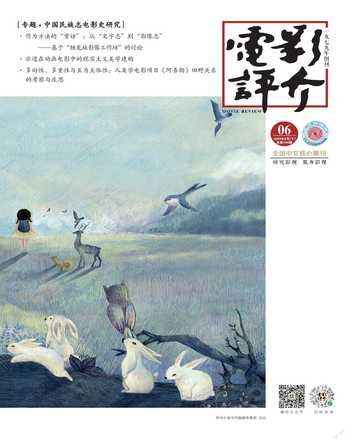歌舞、仪式与饮食:人类学视角下《四个春天》的地方性知识叙事研究
2023-07-06杨丹
杨丹

1922年,由罗伯特·费拉哈迪执导的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在美国公开上映,这部由地质工作者拍摄的记录北美爱斯基摩人在茫茫冰原中捉鱼、捕海象、建冰屋的影片,成为民族志电影的先驱和启蒙。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西南云、贵、川三省以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和东部学人西迁等历史因素,成为民族志影片创作的主要场域,人类学家凌纯声、芮逸夫等学者,曾对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生活进行过实地拍摄和记录。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电影市场出现了诸如《凉山彝族》《芦笙恋歌》《阿诗玛》《苗家儿女》《花腰新娘》《云上太阳》《滚拉拉的枪》等反映西南少数民族信仰、婚姻、传说以及日常生活的优秀影片。在这些影片中,导演运用各种拍摄技巧和蒙太奇手法,将西南少数民族富有地方性的风土民情呈现给观众。
2018年11月至2019年春天,三部贵州题材的电影《地球最后的晚餐》《无名之辈》《四个春天》在全国各大影院公开上映,这部时长1小时45分钟的纪录片不仅人物和素材内容来源于导演真实的家庭生活,就连摄像器材也只是一部尼康D800手持摄影机。《四个春天》自2019年元月作为定档贺岁片公映以来,影片呈现出的悲欢交错的家庭生活、抒情性的故事情节建构、诗意的贵州形象,引起了观众的热烈讨论和情感共鸣。影片先后获得第12届First青年影展最佳纪录片、第5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剪辑两项提名。
导演陆庆屹在《四个春天》一书的后记中写到:“因离家多年,我的审美、思维、习惯已经被重构,这距离使我变成了家乡的旁观者,在不需要与生活角力之后,我有了新的视角去观望故乡的生活方式、人情、风物。”[1]这样看来,除了家庭的温暖,导演想呈现给观众的还有故乡的风土人情。从《四个春天》公映后的社会反响来看,导演对故乡麻尾镇的地方性知识的叙事与认同感塑造是成功的。“地方性知识”是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于1993年提出的概念,格尔兹所说的“地方”不仅空间上与全球、西方、中心相对,在内涵上也与一般性理论相对,格尔兹认为“世界上不同地方所呈现出的艺术和文化是多样性的。”[2]对于那些与地域和民族的民间性知识和认知模式相关的知识,格尔兹倡导要注重用“观察”和“深描”的方法对它们进行研究。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四个春天》是布依族导演陆庆屹用民族志影片的手法,围绕父母日常生活中的歌舞艺术与饮食生活进行叙事,向观众呈现一个西南小城的传统家庭,在现代性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在朴实如诗的日常生活中将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结合与再造、延续与传承的文化图景。
一、地方歌舞承载的时代记忆
陆庆屹导演的家,位于贵州省独山县的麻尾镇,这个小镇是贵州南部布依族的聚集区,蕴含着麻尾悠久历史的民间自创歌曲在当地广为传唱,其中体现布依族青年男女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的情歌《古游》,以其结构短小、节奏明快、情感奔放获得过“多彩贵州”总决赛“铜鼓奖”,第六届西部民歌邀请赛铜奖,首届中国民歌合唱汇演金奖。麻尾的《古游》《表嘛》等布依民歌,是独山县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布依歌舞蹈之乡、书香门第生长的陆家三兄妹,姐姐庆伟读完大学后扎根东北成为国企高管;哥哥庆松曾因出色的音乐天赋十岁时便被中央民族大学招生的老师带去了北京学习;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年少时期的叛逆并没有磨灭导演庆屹对艺术的敏感追求:“音乐在我家是生活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生活的自然呈现。”[3]因此,在《四个春天》中,父母日常生活中的歌舞成了他在影片中“深描”的对象。
(一)颂扬亡者的丧葬歌
《四个春天》在正式叙事之前,有一个45秒的片断,微风吹过的湖面泛起层层涟漪,这是姐姐庆伟去世后亲人们去姐姐坟墓前祭拜时的一帧画面,六个亲人行到画面三分之一处时,影片片名《四个春天》渐渐出现,这个在影片中重复出现多次的湖面,是父母去姐姐墓地的必经之路。导演用姐姐去世时丧葬仪式中的灵堂孝歌作为背景音乐:
“我听过,你贤良的女子,累管当家,正说因你,要此绝去,子母锥心。我身旁,未带有,纸笔和墨砚。她这一生,泪洗人呐,七天夜满。”
丧葬歌是布依族民众在灵堂上以吟唱形式来超度亡灵的歌,其内容包括追溯祖先的故事或追忆亡者生平,讲述做人的道理,以此来寄托生者对死者的哀思,具有重要的道德教化功能。从影片后面的内容来看,姐姐确实是“贤良的女子”,她本应与父母哥哥一起,出现在《四个春天》的首映式中,然而她却“要此绝去”,意外缺席,导演用丧葬歌拉开影片的序幕,姐姐是缺席的,然后在每一个时空里,姐姐却又是在场的,导演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致敬自己的姐姐,也为影片中地方性歌舞的叙事奠定了基础。
(二)充满意趣的布依山歌
贵州的布依族同胞,解放以前是没有自己文字的,人们习惯记事于歌,山歌成了人们传情达意,记载生活的媒介。《独山州志》有载“仲家结婚时,送亲妇幼成群,男女混杂,交饮为欢,歌声达旦。”贵州独山一带的布依族同胞,不仅在岁时节庆、人生礼仪式中唱山歌,日常生产生活的每一个场域,民众都能“随口唱和”。[4]布依山歌以其喜闻乐见的形式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是布依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陆庆屹的记忆中,每逢麻尾的赶场天,很多寨子的人会相约而至,人们赶场的目的不是为了买卖商品,而是為了对对山歌,“镇子四周有不少小块的平地,这对喜欢对山歌的男女来说,称得上得天独厚。一大群男人在一个小山头,女人则在不远处另一个山头,两边你唱我答,一来一往好不热闹”。[5]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现代性的裹挟之下,“打工经济”的浪潮给布依山歌的传承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年轻一代会唱山歌的人已少之又少。
影片《四个春天》中,余姨妈被邀请到庆屹家做客,一脸慈爱的余姨妈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到平塘“对山歌”的情景,满脸的幸福:“哉哦,我们都已经上车了,还着拉回去住一晚上,在那里接着唱。”余姨妈唱道:“春来桃花满树开,一叶小舟荡波来,今天同观西湖景,笑在眉毛喜在怀,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一旁正在剁肉包饺子的陆母也轻声附和着,年轻时,她们都是唱山歌的能手,用廖姨爹的话说:她们的山歌“很捆人”。山歌承载那一代人所有的温情,山歌里有他们的青春和绵绵的情义。父母新年踏青登山,采撷一些春天里生长出的野蕨菜,陆父要陆母到他那边去,他嘴上喊着“喂,过来嘛,打菜莫打那边坡。”尽管破旧的鞋子已经张开了“大嘴”,但心疼老伴的陆父还是选择“我慢慢过去算了”,山上汇合后的夫妇俩,俨然一对正在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他们你唱我和,用山歌传情达意,“打菜莫打那边坡,那边打菜不满箩。”影片中,陆父的老家罗甸,阿哥追求阿妹的山歌是这样唱的“阿哥阿妹情谊长,好像芭蕉一条根,阿哥好比芭蕉叶,阿妹就是芭蕉心”、“燕子双双飞上天,我和阿妹打秋千,阿哥好比芭蕉叶,阿妹燕子云里钻。”这些充满地方特色的山歌,歌词形象生动、旋律简单质朴,给纪录片增加了趣味性的同时,也将贵州少数民族的歌舞文化展示给全国观众。
(三)地方戏与敬酒歌
除了布依山歌,地方戏“独山花灯戏”也在影片中登场了,作为贵州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独山花灯戏”源于正月闹元宵玩灯的习俗,是当地民众最为喜爱的传统戏剧。纪录片中,陆母边做针线边哼唱“独山花灯戏”,尽管陆母打趣说“气不行了”,只唱了“妹呀,在房中绣呀罗裙呀”这么一句,但在字幕上,导演特地标注“地方戏‘独山花灯”,这是一位布依青年文化自信的表现。
敬酒歌出现在一家四口团坐围食的餐桌上,陆母向两个儿子展示敬酒礼仪,她边比划边唱道:“一杯我的美呀酒呀,听见花儿开啰咿,进那门来咿呀,手提我的情谊壶子,今天花儿开咯咿,罚呀酒三杯。”陆父认真地配合着喝下陆母送过来的酒,同桌共餐的儿女,在父母的示范下潜移默化的完成两代人之间的文化传承。
歌舞相伴,音乐与舞蹈总是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对待众人,如果没有合适的语言表达内心的情感,那就放声歌唱、大方起舞吧。影片中除了丧葬孝歌、山歌、敬酒歌、地方戏之外,在山头、在饭桌、在聚会中,父母的《青春圆舞曲》《风雨兼程》《我们举杯》《红河谷》《夜半歌声》《心中的玫瑰》等歌曲将观众一次次带入他们年轻的时候,让浮躁年代的人们不禁想回归那个物质匮乏,但精神富足,自力更生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人们相信爱情和诗歌。影片中,陆母会在陆父的二胡声中翩翩起舞、在踏青的田间地头起舞、在姐姐的墓前起舞……歌舞让他们一次次超越苦难,观众透过一个普通家庭的歌舞艺术,看到的是自己父辈以及一个时代的缩影,反观的则是自己的人生。有观众看完电影后感叹“当下的生活里没有歌,歌是《四个春天》里陆家爸妈唱的那种歌,仿佛具有穿越光阴的力量,是他们的土壤生长出来的歌谣。”
二、地方饮食引发的情感共鸣
“某一个特定的族群对一些特殊的食物已经潜移默化的具有共同的‘口感与‘口味形成带有生理和身体感受的特殊‘味觉。”[6]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在不同民族中,食物已经超越了纯粹的被吃、被消化和被消费的对象,它成了唤醒人们记忆、塑造边界、加强团结的特殊物和特定物。”[7]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的生活活动过程中,对特定的食物会产生一种特别偏爱的嗜好和兴趣,经过当地人的思维活动给“特定的食物赋予一定的人性和相应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传递信息、表达思想感情最容易被接受的东西。”[8]
(一)满载乡愁的腊味与年味
腊肉和腊肠是西南山地民族为延长食物储藏而萌生的生存智慧,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冰箱”已经在民族地区普及,食物储藏的方式已经现代化、多样化,但腊肉给民众所带来的味觉和身体感是市场上的新鲜猪肉所不能比拟的。每近年关,父母便开始不停的询问在外的儿女何时返乡过年,他们会将辛苦喂养一整年的猪宰杀,邻里乡亲帮忙捉猪拉尾“杀年猪”,主人家以一锅热乎乎的“刨汤”答谢至亲好友,大家围坐团食中,“年味”又浓了几分。
新鲜的猪肉,除了献祭祖先,留一部分过年,其余部分会切成条状,抹上盐、花椒、胡椒等香料,放置于大缸之中,腌制一周左右,待盐与香料的味道渗入到猪肉之中后,便开始“熏腊肉”,将腌制好的猪肉整整齐齐的悬挂于密封的“熏房”之中,家庭成员轮班值守,不停的往火塘里添加树叶、树枝、木材,一层层的浓烟被成功的围困于“熏房”之中,猪肉在浓烟的笼罩和微火的熏烤之下,一点点变黑变干,一两天之后,利于长时间保存的腊肉便制作完成。熏制好的腊肉一般被悬挂于家中火塘之上,平日生火煮饭时火塘里所散发出的火苗和烟雾不断的对腊肉进行“再加工”,人们围着火塘吃饭,头顶的腊肉散发着別样的香味。返乡过节的儿女临别时,行李箱里定然少不了腊肉和腊肠。这些承载着多少人乡愁的食物,在《四个春天》中反复出现。第一个春天里,陆父守在一个大铁桶旁吹火、添柴、阅读,在这个镜头中,导演并没有让腊肠或腊肉登场,铁桶像一个待开的盲盒,只有西南的观众才知道盲盒里的“秘密”。导演将镜头转向晚上,陆父微笑着揭开铁桶上的遮盖物,对自己制作的腊肠赞不绝口,“漂亮啊、安逸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熏”腊肉腊肠的场景在影片中重复出现了三次,它们在第三个春天里缺席,是因为姐姐庆伟的离去,让这个家庭失去了“熏”腊肉腊肠的动力,在导演的镜头下,第三个春天的年也就没有前两个春天那么“有味”。到了第四个春天,“燕子绕粱”,父母也逐渐从失去爱女的阴霾中走了出来,他们开始坦然面对燕子的归巢与生命的来去,父母又开始“熏”起了腊肉腊肠。影片中,陆母精心挑选“熏”的腊肉,要送给远方来的客人,满载乡愁的地方食物,已然超出了“吃”的文化功能,它是西南民众赠予至亲好友的贵重“礼物”。
(二)声味相和的共餐与共饮
“声味相和”指音乐舞蹈与饮食活动相结合所形成的一种饮食文化现象,《左传·昭公元年》中,将五味(辛、酸、咸、苦、甘)与五声(商、角、羽、徵、宫)相互关联,认为声与味是相互制约的统一体,因此,古代宴饮活动中常以五声来调和五味,达到“声味相和”。“声味相和”的饮食传统从古代的宴会延续到现代餐桌,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用美食美酒招待客人的同时,习惯用歌声助兴,以表达主家的热情好客,客人在主家的歌声中,一杯接一杯,愉悦地共食。
纪录片《四个春天》中,导演安排了很多一家人的日常共餐的镜头,“组成一个家庭的成员通过一起分享食物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9]每一年春节,一家人团坐围食,边吃边唱,陆母在餐桌上向儿女们演示“敬酒歌”,还不忘趁机让陆父喝上两怀。父母的金婚纪念日,儿女从不同的地方赶回来庆祝,餐桌上,父母向儿女讲述他们年轻时的爱情,那个的年代的日子虽然艰辛,但父母的爱情却是长长久久的。儿女临别时的家庭聚餐中,陆父情不自禁的唱起了《这一生还是你最好》,这是电视剧《金婚风雨情》的片尾曲:“这一生我和你说过爱,直到今天情未了,哪怕岁月淡忘了春天,花香还在你怀抱……”。这个家庭近20年来的变迁、父母的爱情故事以及父母对儿女们的家庭教育,大部分都是在“声味相和”的家庭聚餐中愉悦的完成,原本普通寻常的家庭餐饮活动,因为歌舞被赋予了娱乐性与仪式感,体现了生活的艺术化。除家庭共餐之外,影片中也有亲友共餐的镜头,大家团坐围食中,相互叮嘱要照顾好身体,“虽然吃的没什么,但是一家人在一起热闹。”可见,对于大家来说,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珍惜和享受“在一起”的时光。
三、地方仪式延续的集体认同
除饮食、歌舞文化之外,地方仪式传统在《四个春天》中也有着较大篇幅的叙事。由远古僚人演变而来的布依族民众,每个家户都会在“堂屋”中安设神龛,供奉自己的祖先及神灵,食物是人-神沟通的重要媒介,每逢家中备有好酒好菜,家户长便会向祖先行“供奉”仪式,期望祖先能保佑家宅平安、六畜兴旺。每近年关,布依民众便会举行送灶神、杀年猪、捏血豆腐、打阳尘、安香火、守岁等祭祀祖先和神灵的仪式活动。《四个春天》中,导演多次呈现春节家祭、墓祭等传统仪式。
(一)送别姐姐的丧葬仪式
在第二个春天中,姐姐庆伟的离去,使整部影片的感情基调发生了转变,导演用近六分钟的时间来记录姐姐的葬礼,乌黑的棺木停放在灵堂中,香烛四起,唢呐声声,导演深描了灵堂上的孝歌“我问问,亲慈的苍天,路途惊悚,我妈一生尘土里,养儿艰辛。我本想要留你在,照顾我的家杂,盼呀盼,我泪也流,头戴孝帕。我听过,你贤良的女子,累管当家,正说因你,要此绝去,子母锥心……”送殡仪式上,姐姐的儿子佟畅手捧陆母的遗像走在最前面,庆伟在后面给姐姐撑着黑伞,帮忙抬棺的众人起棺后,人们打翻桌上的香火。下葬仪式中,佟畅双膝下跪,高声“请”妈妈入葬,“带”妈妈回家。这六分钟,是观众情绪最受感染的时间,然而在拍摄过程中,导演却没有太多的情绪表露,只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记录下整个丧葬仪式。那个陪自己到天渠爬山吹风、到林场摘刺梨、到马厩看大马、到小河边抓虾子,温暖了自己整个童年的姐姐的不在了,导演肯定是悲痛的,自确定以父母的日常生活作为拍摄对象以来,导演并不知道,也不愿意,片子中会有一段关于姐姐葬礼的影像,尽管很痛苦,但“当时感觉就是我要记下来,因为记下来之后感觉一家人还是在一起的。”[10]
(二)供奉祖先的家祭仪式
祖先与人有着相似的食欲,对各种美味佳肴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只有让祖先的食欲都得到充分的满足,它才会给人以回报,降福于后代子孙。供奉祖先的家祭仪式贯穿于《四个春天》。在第一个春天里,一家人在小院中准备年夜饭,杀鱼、切肉、炒菜,鸡、鸭、鱼、腊肉等十五个丰盛的菜肴以及水果、饭、酒等被整整齐齐的摆放在神龛前后,陆父点燃香和蜡烛,一家四口围在神龛前“开纸钱”,给祖先磕头之前,陆母认真地为儿子整理好衣领,陆父双手合十,陆母不停地磕头,一家人给祖先行献祭仪式。第二个春节,陆父给桌上的酒杯斟满白酒之后,给祖先行跪拜礼,陆母将一碗碗的菜肴从陆爸爸头上绕过,并开着玩笑请祖先“保佑陆运坤好好的,快长快大,乖乖吃饭睡觉。”其实在第二个春天的开篇里,陆母已经向回家过年的孩子们透露了陆爸爸的身体状况,想来,她心里一直担心着老伴的身体,因此,在给祖先献祭时,陆母玩笑似的祈愿中藏着她对老伴深深的爱意与牵挂。第三个春天中尽管没有春节家祭的镜头,但自姐姐庆伟走后,家里餐桌为姐姐留了饭碗,陆母像日常一样,亲切的叫自己的女儿吃“甜酒煮鸡蛋、煮汤圆”。第四个春天中,家祭的镜头再次出现,陆父陆母开始从失去爱女的悲痛中走了出来,他们开始坦然的面对生老病死。
(三)追忆亲人的墓祭仪式
坟墓是生与死交界处的物化象征,人们把亡者送入坟墓、封住墓口,阻断了人们与死者在阳界的关系,亡者住进了坟墓,这坟墓也就具体代表了阴间地界,坟墓被视为是与祖宗神灵交流的场所。“春节上坟”是人们追忆亲人的一种方式,很多民族称这一仪式为“送年饭”,人们通过向祖先献祭食物来表达对祖先的哀思之情,通过墓地共餐,来实现阳阴两界的团结。《四个春天》中,导演除了在第一个春天里对家族墓祭时族人们烧香、烧纸的献祭仪式场景作了“深描”之外,家族“春节上坟”的传统通过1997年以来,热爱摄像的一家人所拍摄的片子间接性的呈现给观众。对观众而言,“春节上坟”的仪式场景是熟悉的,即便是漂泊的游子,春节时定然也不会忘记给祖先准备丰盛的食物。自第三个春天开始,姐姐的墓地成了影片拍摄的主要场域,一家人在姐姐的墓前修排水沟、种辣椒、种花草、种桃树,以此来表达对亲人的哀思。
结语
“地方性知识是一个特殊人类群体有关他们自身与周边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知识”[11],是一种关于人与生态之间互动的知识与信念从上一代人延续到下一代人的文化传递过程,“是知识接触的结果,在这些接触中,地方与全球、传统与现代复杂的交织在一起。”[12]传统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存在着血缘和地缘联结的生活共同体形式,乡民之间以情感和归属紧密、真实、团结地联系在一起,在向现代社会过渡和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流动的不断加速,乡土社会中的成员从血缘家庭中抽离出来,开始主动或被动的流入大城市,由血缘、地缘联结的传统共同体日渐弱化和分化,“捆扎在土地上”的农民开始“被市场捆绑”,“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市场、交换、契约等形式产生和维持。”[13]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出现了传统与现代杂糅、情感与功利并存在的景象,富有地方传统特色的地方性知识不断的发生变迁,乡村社会如何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找到一种使地方性知识发声的方式,进而走向乡村振兴,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纪录片《四个春天》中,导演将家乡的地方性知识作为影像化表达的重要题材和对象,通过对父母日常生活中自然呈现的歌舞、饮食与仪式的多重叙事为路径,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深描”故乡的风土人情、风俗风貌,影片中呈现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歌唱、出游、探亲、丧葬……“这些似曾相识的纪实段落和细节呈现带来的是集体的回忆与思考”[14],“让观众在大银幕上仪式化地看到‘自己、‘父母以及当今中国‘家的范式及其中所蕴含的苦与乐。”[15]增强了流动性背景下的观众对“家之所在,无远弗届”的深刻理解,让无论身处乡野还是都市的观众,都能在情感上產生共鸣,地方性知识的银屏再现,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另一条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5]陆庆屹.四个春天[M].海口:南海出版社,2019:234,114.
[2][美]克利德福·格尔茨.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论文集[C].王海龙,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56.
[3]马丽琳.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诗意——《四个春天》导演陆庆屹访谈[ J ].电影评介,2019(01):31-37.
[4]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编纂委员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第四卷(民族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71.
[6]彭兆荣.饮食人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18.
[7]杨丹.西方人类学共餐研究脉络与反思[ 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4):50-56.
[8]瞿明安.中国饮食文化的象征符号——饮食象征文化的表层结构研究[ J ].史学理论研究,1995(12):45-52.
[9]杨丹.共餐、食物与爱:人类学视角下的电影《饮食男女》[ J ].电影评介,2021(11):49-52.
[10]陆庆屹,孙红云,张浩.《四个春天》导演访谈[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9(03):63-71.
[11]Per Olsson,Carl Folke.Loc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for Ecosystem Management:A Study of Lake Racken Watershed[ J ].Sweden:Ecosystems,2001(02):85-104.
[12]Nygren A.Knowledge in the Environment-Development Discourse:From dichotomies to situated knowledges[ J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1999(03):267.
[13]戴洁.统一战线与现代国家团结:以社会共同体为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01):22-30.
[14]张静.人类学视阙下《四个春天》的审美特性[ J ].电影文学,2019(12):44-46.
[15]孙红云.真实的家庭劇——评纪录电影《四个春天》[ J ].当代电影,2019(02):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