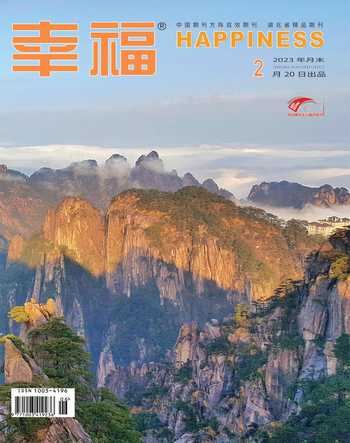捆满铁丝的矮松
2023-06-28赵兴国
赵兴国

六月的校园,和外面的田野一起,陷入一种难以名状的安静。这安静,在天地间弥散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好像烧制瓷器的窑口即将打开,又像是水面上的鱼漂,在轻轻地抖动。
校园里,课间的喧闹,好像被教学楼厅倒计时器上的数字,压缩到窒息的状态。偶尔有老师走过,也是急匆匆的脚步,鞋底敲击地板,发出欻欻的声响,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田野上,昨天还绿油油的麦子,在暖醺醺的南风面前,只过了一晌午,便黄了麦梢,开关献城。往日抽水机艰涩的吭哧吭哧,换成一两声布谷鸟轻快的叫声。田间小路上,匆忙的农人,也只有早上过来,小心翼翼地用粗手指剥开麦穗,把麦粒放进嘴里嚼一嚼,然后若有所思地倒背起手,缓步走远。只剩下风,如海潮般从遥远的天际,一波一波浩荡而来,又浩荡而去。
女人坐在篮球场门口的大理石石球上,好像有一段时间了。我记得我和同事三对三打球的中间,到门口捡出界球的时候,她朝我微笑了一下。我心里虽然有些诧异,可还是礼貌地还以微笑。无意间,我看见风正扯动着她鬓边的细发,轻轻地抖动。
我带着淋淋漓漓一身汗水,正要离开球场的时候,那女人起身拦住我。
“你是赵老师吧?我是浩轩的妈妈。”听女人说出“浩轩”这个名字,我脑际迅疾闪现出一幅画面来,一个五年级的男学生,翻着白眼,站在一株矮松前。
我一边慌忙停下来,一边答应着,大脑也闪电般快速地思索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同时,我也感觉有一点尴尬。一来是自己一身汗水穿着球服,和教师扣脖严领的着装形象严重不符。二来,如果早知道她是有事找我的学生家长,我完全可以暂时不打球,过来处理完她的事,再打不迟。依着我多年的经验,一丁点儿小事,如果处理不好,学生家长便会纠缠不休,需要耗费很多口舌,更不要说她的孩子在学校打架受委屈受伤了。
“你咋不叫我一声呢?让你等我这么长时间,多不好意思啊。”我说。浩轩妈妈说她也没啥事。浩轩妈妈三十多岁的年纪,鬓角已经有几根白发,右手食指上缠着白色的医用胶带。
当我听浩轩妈妈说,是因为彭浩轩同学成绩下滑,才来学校找我之后,我悬着的一颗心,这才安稳放下。她带着一脸不自然的笑,和我说了她家的一些情况。她和丈夫在村里经营着不大不小的一家筛网厂,丈夫常年在外跑业务,她在家带着四五个人守着几台机子制作筛网。因为忙,她大部分时间把孩子交给婆婆看管,连吃带住,上学接送。
“都让他奶奶惯坏了。上一年级那时候,是我看着他,语文数学还都能考90多分。家里干了筛网,我这一忙,就顾不上他了。前几天群里发测试成绩,我这才知道浩轩的成绩这么差。并且,我每次问他有没有作业,他总说在学校就做完了,还经常连书包也不往回拿。尤其是过年的时候,俺们邻居家那个上七年级的小伟,总骑着电车过来找他。那个小伟,爹妈离婚了,法院判的小偉跟着他爹,他爹又给他找了一个后妈。这孩子,也抽烟也喝酒,逃学上网……”
我听浩轩妈妈这样说着,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她口中所说的孩子,我平日里见的太多了。我所在的学校,生源大部分来自周围的农村,能像浩轩妈妈这样,来学校当面找老师谈一下自家孩子的家长,已经是很不错了。更多的,是家长把孩子往校园一送,万事大吉。更有甚者,一部分家长认为:孩子学习好了,是自家孩子聪明;孩子成绩差了,是老师教得不好。
“赵老师,你多费心,该打就打,该训就训,我回家让他爸爸狠狠地治治他。”
我嘱咐她放心,我会在学校尽心管理她的孩子。看着浩轩妈妈远去的背影,我也回教学楼门厅去签退,一路走,浩轩妈妈的那句“该打就打”,一直回旋在我耳边。
“能打吗?啥时候该打,啥时候不该打呢?”我问我自己。
“该”这个字,大概是所有汉字中,最矛盾的一个字,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界定标准。
浩轩这个学生,我从三年级一直带过来,相比之下,是很熟悉的。他活泼好动,脑子灵活,成绩在班里能排到中游偏上一些。他喜欢读书,趁我上课不注意,偷偷摸摸地就读课外书,可是,读书不细致,囫囵吞枣过眼即忘。这也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通病。去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在家上了三个月的网课,回来后,我就发现这个孩子有些变化,具体也说不出,直到今年过了年,到了五年级下学期,我才注意到,他几乎每次都说家庭作业忘了带。我有心惩治一下,可总想不出好的办法。
我知道:打,是肯定不行的。
教育局领导、校领导开会,三令五申不允许体罚。各种大小新闻,只要是有学生和老师发生冲突的,无一例外一边倒地斥责学校老师,口口声声地高喊“保护未成年人”。有的老师因此被降职,有的被调离,有的,丢了“饭碗”。就我,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年逾知天命的老老师而言,能保住自己的“饭碗”,也就“阿弥陀佛”了。
我也知道:不管,肯定也是不行的。因为我的身份是教师,职责就是教书育人。
我曾把我的困惑告诉朋友,朋友用轻快的口吻告诉我说:“冷处理呗,又不是你家孩子。你能安全退休就是好事,多大年纪了,还没活明白吗?”
我知道朋友的“冷处理”是什么意思,可是我真的是没有“活明白”,在我看来,“冷处理”,也是不行的。我总要找一个办法,“敲打敲打”这个“家伙”。另外还有个原因,那就是这个浩轩,在前些日子,把我气得够呛,好长时间,我心中总有一股怨气,散不开,咽不下。为此,我还失眠了两个晚上。
那是一个上午的大课间,我不记得是因为什么事情,正在教学楼的连廊经过,突然,我看到浩轩和另外一个学生,躲在连廊水泥柱子后面,偷偷地往操场上看。在操场上,其他学生都在做课间操。这个浩轩,可也真是淘气,手把着柱子,也不老实,他左手手指把柱子上的展板框撬起来,拨动着,发出“吧嗒吧嗒”的声响。
我见他不做课间操,还破坏公物,心里当时也不知道哪儿就来了一股火气,几步走过去,大声呵斥道:“你有病吗?弄这展板干吗?你弄坏了咋办?”
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用牙咬着嘴唇,反问我说:“老师,你咋骂人呢?”
这话一下子把我问愣了,要知道,教师说脏话乱骂人,这顶“帽子”,可是会把人压趴下的。我说我哪有骂你。浩轩梗着脖颈说:“那我说你有病,你愿意吗?”他那冰冷且尖锐的口气,让我好像受了极大的屈辱一样无法接受,我突然有上去踹他两脚的冲动。可是,这个冲动只是在我身体里跳动着胡乱冲撞了几下,就被我硬生生地压了下去。我说:“你破坏公物还有理了吗?到那边站着去。”
浩轩翻着眼睛看着我,嘴里嘟嘟囔囔地说:“当老师还骂人,还为人师表呢?”然后慢吞吞地迈着脚步,走到楼厅门口的矮松下,扭着身子,极不情愿地站在那儿。而我的胸口,也仿佛被无形的拳头重重击打了一下,透不过气来。
矮松在教学楼门厅前面,大约有两米高的样子。起初,我并没有留意到它,直到那天,我和浩轩同学来到矮松近旁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在矮松身上,捆绑着许多细细的铁丝,形状很像一把伞,伞柄是主干,铁丝是支撑,下端拴住树干,上端斜斜地捆在矮松散开的枝杈上。我想,这铁丝肯定是用来修整矮松枝杈的,迫使那些原本朝上生长的,服从铁丝的拖拽,服从人们的审美意向,而平平地延伸开来,以便于“虬枝婆娑”。我又走近些,用手扶着矮松的枝杈。我看见铁丝有的已经嵌进树皮里面,很多地方,已经生了锈。我用手按了按,枝杈硬挺挺的,很是有力,似乎要把铁丝拽断。铁丝呢,尽管锈迹斑斑,也是绷得紧紧的,坚守着自己的职责所在。我渐渐开始平息的心里,忽然想起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来,再看看身边的浩轩,我竟然一时间有些茫然。
那时候,尽管我有很多话、很多道理要和浩轩讲清楚,可因为下一节有课,我只能忍住,让他回教室上课。上课的时候,我利用学生做练习的间隙,眼睛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瞥向他那里。而他,似乎已经忘了刚才发生的事情,正利用我转身的空档,偷偷看抽屉里的课外书。虽然我想借此发一顿脾气,可是,我还是平心静气地把他的课外书拿出来,放在讲台上,并嘱咐他,认真完成我布置的练习。
摘自《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