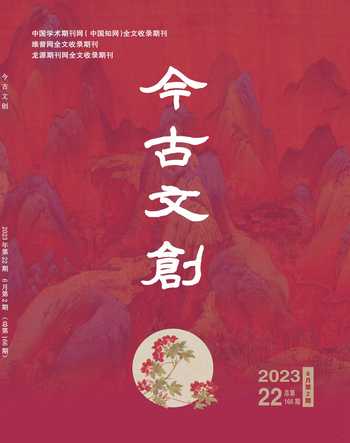文士治生视域下“三言二拍”大运河描写中镇江元素探析
2023-06-25朱琪敏郭展伶
朱琪敏 郭展伶
【摘要】明清时期由于科举竞争激烈、社会心理变化等因素,文士治生现象发展得尤为繁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话本小说“三言二拍”的创作内容与内在倾向。同时,出于冯梦龙、凌濛初二人的生活经历,迎合市场需求,促进故事发展合理性等原因,“三言二拍”中出现了相当的文士治生与大运河元素,其中镇江作为两江汇聚之地,沟通南北之城,常常在“三言二拍”的大运河描写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大运河;文士治生;“三言二拍”;镇江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2-003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2.01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文士治生视域下明清小说大运河描写中镇江元素研究”(项目编号:202210299227Y)的相关成果。
明代话本小说“三言二拍”与大运河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小说中出现较多大运河沿岸的文士治生现象,不仅反映大运河沿岸地区文士治生的繁荣景象,更是从侧面表现了特殊环境下消费市场与社会心理的变化,展现出大运河沿岸的独特民俗风貌。镇江毗邻大都会南京,处于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汇处,人流密集、交通便捷,各地商品、粮食大都需要在此转输,从而造就了镇江在大运河沿岸的特殊地位。这样的特殊地理位置不仅有利于在小说中作为情节发展、地理转换的关键点,也有助于展现运河风貌、迎合大运河流域的读者心理。
一、文士治生与“三言二拍”中的大运河描写
(一)文士治生的词义与表现
“治生”一词曾被记录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后多为历代采用,指通过授徒、游幕、行医、问卜、业农、经商等手段谋生。明清时期,尤其是江南运河流域,出于大运河带来的交通运输便利,大运河流域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人口猛烈增长,从而导致科举人数大幅上涨,科举竞争压力过大,众多士子文人难以通过科举读书安身立命,只能以经商、授徒、游幕等方式维持生活。当然,面对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大量财富,也有部分文人自愿放弃科举道路转而通过经商获取利润与社会的尊重。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交通便捷,市场对商品贸易、教育启蒙、书籍出版的需求较大,因此文人沿大运河进行一系列治生活动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样的景况在“三言二拍”中有着大量描写。如《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家住扬州府城外的赵春儿让丈夫曹可成依仗能写能书的本事做个训蒙先生,“聚集几个村童教学,得些学俸好盘用”;后曹可成欲上京听选,便是雇船沿着运河北上至京。《唐解元一笑姻缘》中唐寅到华学士府上寻秋香时,假称自己“颇善书,处一个小馆为生”,华学士不疑有他,称“我书房中写帖的不缺,可送公子处作伴读”,给了唐寅一个差事。又如《刘小官雌雄兄弟》中刘奇原是随父三考在京的文士,突遇洪灾在运河边被劉公救起,拜刘公为父后便尽心料理店铺生意,未再读书科举。这样的情节描写在小说中并不在少数,其中人物因经营商业放弃科举的行为也并未遭到批评指点,类似的文士治生现象在“三言二拍”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三言二拍”中的大运河描写
经荀德麟(2016)统计分析,“三言二拍”中的故事,虽多为冯、凌二人根据前朝故事改写而成,但故事中的大运河描写并没有因为朝代的不同而减少改变,甚至其中部分经典篇章就是直接讲的运河风物、运河故事。如《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讲述的便是李、黄二人于江南江北两边贩货而产生情愫的故事;《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吕氏为江南常州府无锡县人士,后为了寻子往太仓、嘉定,一路收棉花贩卖;《钱秀才错占凤凰俦》整篇故事的地理路线集中在洞庭与苏州府吴江县的运河水路之上;《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中的地理位置也大致在苏州、浙江之间,交通方式多为运河水路等等。运河沿岸城市的布局同样成为作者详细介绍描写的细节,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许宣等人的房屋、商铺大多都位于桥下、码头附近,《小水湾天狐诒书》《杨谦之客舫遇侠僧》等卷中,房屋、客店也都处于码头边,展现出在大运河流域,尤其江南运河段,为了生活和运输的便利,城内外水系相互联系,商铺住宅沿水系铺陈排列,往来密集的水网构建出城市的大体框架。
“三言二拍”中的大运河描写不仅仅体现在作者多将人物的所处地或故事的发生地设置在运河沿岸城市,更是表现在作者对于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人物谋生方式、出行方式、运河水路境况作了生动详细的描述。譬如大运河作为沟通南北商路、转运粮食的重要水道,也衍生出一些河盗群体,小说不少情节中都表现出河盗的猖獗。《苏知县罗衫再合》中,苏云一行人便是北下至扬州镇江附近因换船之需被骗上了河盗的船只,险些丧命。镇江作为毗邻南京、沟通南北的重要运河城市,自然在“三言二拍”的运河描写当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三言二拍”大运河描写中的镇江元素
“三言二拍”中涉及京杭大运河的故事繁多,而这些故事在人物所处地理位置、情节发生场所中,运河沿岸城市、市镇元素与风貌始终占据着不容忽视的比例,镇江由此在“三言二拍”中成为一个颇具地位的文学元素。对于这一问题,可以采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说明。
冯梦龙的“三言”共写了120篇故事。其中,涉及“镇江”的共9卷,39处;涉及“京口”的共2卷,2处;涉及“丹阳”的共5卷,7处;涉及“润州”的共5卷,7处。除去元素重合部分,涉及镇江元素的篇目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张舜美灯宵得丽女》《杨思温燕山逢故人》《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李公子救蛇获称心》《梁武帝累修旧极乐》《钝秀才一朝交泰》《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计压番金鳗产祸》《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旌阳宫铁树镇妖》《三孝廉让产立高名》《卖油郎独占花魁》《小水湾天狐诒书》《张廷秀逃生救父》《蔡瑞虹忍辱报仇》,共18卷,占总卷数的15%。
凌濛初的“二拍”共写了80篇故事。其中,涉及“镇江”的共3卷,5处;涉及“京口”的共1卷,2处;涉及“丹阳”的共4卷,6处;涉及“润州”的共2卷,2处;涉及“南徐”的共1卷,1处。除去重合部分,涉及镇江元素的篇目为《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大姊魂游完夙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贾廉访赝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共6卷,占总卷数的7.5%。
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与“三言”相比,“二拍”中的镇江元素虽然占比有所下降,但仍旧占据着一定的地位。涉及镇江元素的篇目大多以大运河描写为主,镇江在文中多作为构建运河故事的相关城市,或通过运河交通转换故事发生地的中转站,金山寺这一佛家重地的存在和寺院描绘的热闹景象也使得镇江在涉及妖魔佛道的故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地理元素,可见其在“三言二拍”大运河描写中的重要地位。也正是因为“三言二拍”对于大运河描写的偏爱与对文士治生现象的反映,可以发现,故事中的人物出行,尤其涉及经商、公干等行程,往往多数由水路经过或前往镇江;对于一些发生在运河河面上的故事,也大多将地点设置在京口、扬州等镇江附近的水域。在这其中,为我们看见京杭大运河的沿岸风貌与文士治生现象提供了独特视角。
三、文士治生对 “三言二拍”大运河描写中构建
镇江元素的影响
镇江沟通南北,连接运河长江,又是商品转输要道,人口繁多,在水运发达的运河流域,不管是文士寻找治生途径还是经商中转,都是一个合适的位置,因此其常常作为故事中主要人物汇合的地点。文士治生的特殊背景也促进镇江成为推动情节发展与场景转换的重要地理元素。
《钝秀才一朝交泰》中“钝秀才”马德称“想得南京衙门做官的多有年家。又趁船到京口,欲要渡江”投奔南京也是马德称的文士治生行为,而镇江毗邻大都会南京,津渡发达,成为众多文人士子寻求治生的必经之路与优选地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许宣想治理些营生,也是“教将和去镇江渡口码头上,赁了一间房子”预备做药材生意。《张廷秀逃生救父》中,张廷秀兄弟从京师得到官职返乡,自北往南也需要“顺流而至,只一日已抵镇江……过了镇江、丹阳,风水顺溜”。此外,由于行政区划与官府职责分配的安排,镇江也是古时公干、告状的重要地点,从而在小说中常作为相关地点促进情节发展。这一点在《张廷秀逃生救父》一卷中得以体现,张廷秀兄弟执意要到镇江去的原因在于新按院在镇江,二人要去镇江找按院告状救父,也正是因此,才上了杨洪的奸计,上了一艘伪称“本府理刑厅提来差往公干”的便船,前后也未曾起疑。同时,镇江人口密集,官府事务繁多,水运交通发达;回程的船,为了能够拉客避税,会让官员免费包船,以借其名号。《苏知县罗衫再合》中苏云前往兰溪县做官时找的便是这样的“回头的客座”,后骗取苏知县一家性命钱财的徐能一伙人也是因为有一艘竖着山东王尚书府水牌的船只,方能潇洒得手。
文士治生在小说中的表现除了文士的经商、授徒、代笔等治生活动以外,还包含文士阶层为了治生活动的四处奔走的奔波过程。在文士沿运河奔波的过程中,大运河沿岸城市风貌与民风民俗同时得以展现。镇江、扬州、常州、苏州等沿岸城市往来商船密集,南来北往商人众多,文士聚集,在“三言二拍”中自然成为展现大运河流域民俗风貌的合适地点。《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中,便有对“烧利市”风俗的讲述:
又过了两日,是正月初五,苏州风俗,是日家家户户,献祭五路大神,谓之烧利市。吃过了利市饭,方才出门做买卖。
按字面意思理解,“烧利市”就是有利于买卖经商的意思,也就是说词中风俗最初的产生很可能与商家买卖密切相关。文中金满吃完利市饭后,老门子陆有恩便上门拜年,并带来了库房失窃的线索,确实也对应了“利市”的民俗含义。或许是出于南来北往密集人群的有力传播,在“三言二拍”中“利市”不再是独属于苏州一地的风俗,而成为大运河流域普遍的民俗现象。《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中王生准备离家经商治生时,也“到船烧了神福利市,就便开船。一路无话。不则一日,早到京口,趁著东风过江。”《蔡瑞虹忍辱报仇》中蔡瑞虹随丈夫前往武昌任职,一行人抵达镇江附近的扬州等待前来接取的人,遇见江边有人闹事,下人见奶奶气闷,“今番且借这个机会,敲那贼头几个板子,权发利市。”《卖油郎独占花魁》亦有“若得他回心转意,大大的烧个利市。”这样的口头语。类似的民俗描写放置在镇江等典型的运河沿岸城市,一方面是文士治生环境下现实情况的客观呈现,一方面也存在拉近与读者间心理距离的因素。
李向明(1995)认为,至明代以后,随着刊刻业的发展,文学的稿酬市场开始萌芽,这种近代型文学市场的雏形无疑是一种新的具有蓬勃生机的新形式。大运河流域由于贸易往来繁多,经济繁荣,人口增长,聚集着大量话本小说与通俗文学的读者、消费者。一些屡试不第,或是没有生计的文人也会通过编写小说、话本,将文稿卖给出版商赚取稿酬以养家糊口,这也是大运河流域,尤其是江南流域比较盛行的文士治生方式之一。“二拍”的作者凌濛初,亦是科举失利,家中又需营生糊口,恰逢当时冯梦龙的“三言”在出版后大受欢迎,便应书商要求作“二拍”赚取稿酬。如《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所记:
丁卯之秋,附肤落毛……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编,得四十种……意不能恝,聊复缀为四十则。
在这样的消费市场与创作环境下,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和稿酬,书商和作者常常会在话本小说中增加大运河沿岸代表性城市的曝光度,以迎合消费人群,博取更多的关注。由于经济发达,大运河流域人口受教育程度高,因此文士阶级人口数量较大,随着科举竞争的日益激烈,部分文士不得不从事各类治生活动,奔波于大运河沿岸镇江、常州、苏州等城市,或是沿着运河北上京师寻找出路。像镇江这样连接运河长江、沟通南北的商品转运重要城市,更是聚集着大批客商百姓,为了能够拉近小说与读者间的距离,吸引读者的兴趣,增加阅读的真实感,作者自然会选择在小说中添加鲜明亲切的大运河元素。《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平氏前往襄阳探望丈夫,也是要先“到得京口”,再“上水前进”。《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许宣先是被押发镇江府牢城营做工,又在镇江渡口码头赁了一间屋子预备开药材铺子,随后遇见金山寺的方丈法海禅师,被提点有妖怪缠身;这其中不论是镇江渡口码头还是金山寺,都是大运河流域颇具名气的地方。此外,镇江位于商品运输要道,常有河盗出没,《乌将军一番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中王生遭盗就是在京口附近,这与当时客商的真实经历也是相近的。加上冯梦龙曾人丹徒训导,凌濛初也在大运河沿岸进行治生活动,对于文士治生现象与大运河描写的建构生动贴切,符合读者的消费倾向,从而展现出大运河流域的独特风貌。
在文士治生发展的大环境下,冯、凌二位生长在运河边的作者编写“三言二拍”时有意识地构建了大运河描写,镇江元素出于地理、文化因素,与大运河流域文士从事的坐馆、经商、行医等治生活动密切相关,多次以故事发生地、情节转折地、承上启下等作用出现在“三言二拍”的大运河描写中。通过作者对于故事的改编与对于大运河描写的构建,不仅能够发现文士治生这一社会现象的发展情况与文人生存状态,还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明代消费市场的倾向与社会心理变化,展现大运河流域独特的民风民俗与社会风貌。
参考文献:
[1]徐永斌.文士治生视域下明清江南运河区域通俗文学的兴盛[J].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20,(1).
[2]荀德麟.大运河与中国古典小说名著[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
[3]苗菁.“三言二拍”中的明代故事与京杭大运河[J].明清小说研究,2018,(1).
[4]张俊福.创作论视域下的“三言”“二拍”与大运河[J].明清小说研究,2022,(2).
[5]李向民.中国艺术经济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