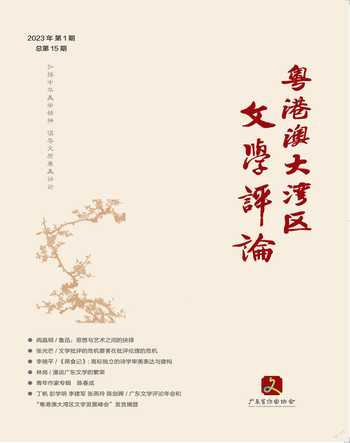假如表面虚空
2023-06-23艾玛
艾玛
大多数读者在打开一部小说时,都希望能读到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感受到些新鲜有趣的人生经验,倘若在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几页,都看不到这种希望,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时间的流水里漂浮着生活的鸡零狗碎,这样的小说不管写得多丰沛、多真诚,可能仍难以避免给人留下平滑、虚空的印象。当人们觉得没意思的时候,阅读往往就被放弃了。所以,能把A Reader on Reading 译为“理想读者”的译者,1应是参透了阅读的偏见与艰辛的。
“在贡布雷,有两个‘那边供我们散步,它们的方向相反,我们去这个‘那边或那个‘那边,离家时实际上不走同一扇门。”小说创作也有两个“那边”,对作家形成严峻的考验,一个是生活“那边”,一个是虚构“那边”。就拿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来说吧。
这部巨著最广为人知的逸事,是它曾被十九世纪法国思想界坐标、文学界的泰斗纪德毙掉过。有人说当年纪德作为伽马出版社的审读员,毙掉《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部,《斯万家那边》,是因为作者在茶点上花费的笔墨太多,(也就是对日常琐事描写得太多)可能也并不是因为茶点,毕竟普鲁斯特在那种叫小玛德琳娜的点心上花费的笔墨,并不比不眠之夜枕上的浮想联翩更多。——“在我的孩提时代,我以为《圣经》里没有一个人物的命运像诺亚那样悲惨,因为洪水使他被囚于方舟达四十天之久。后来,我经常患病,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不得不待在‘方舟上。于是我懂得了诺亚曾经只能从方舟上才如此清晰地观察世界,尽管方舟是封闭的,大地一片漆黑。”所以,《追忆逝水年华》不是从茶点开始的,而是从一只孤枕开始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躺下了却睡不着,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记忆如长河之波翻腾着涌来,如此一夜接着一夜,最终生成了一部令人望而生畏的《追忆逝水年华》。看上去像是呈现了烈火繁花的盛筵,实则是一幅荡尽一切的洪荒图景。纪德在给普鲁斯特的退稿信里给出的理由是,“这部作品里尽是些公爵夫人,不适合在我们这出版。”当普鲁斯特自费出版的 《斯万家那边》大获成功后,纪德写信给普鲁斯特,承认自己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从这封道歉信来看,退稿原因跟作品本身无关,既不是因为茶点,也不是因为公爵夫人,而是作者普鲁斯特留给纪德的印象:“我当时认定您——我要向您坦白吗——是威尔杜兰夫人那边的公子哥……在我们杂志社(《法兰西评论》),附庸风雅、热衷社交的人不受欢迎。”在作为一个作家广为人知之前,普鲁斯特是礼服的扣眼里插着山茶花,或是玫瑰花,在上流社会贵妇人的沙龙里往来穿梭的公子哥。(据说玫瑰花倘若不是自家花园的出产,普鲁斯特就会引以为憾。)所以彼时,纪德大约是没有耐心去读一个沙龙里的花花公子、社交界的“礼仪专家”的絮叨之作的。又过了十年,纪德在日记里写道,“普鲁斯特的书在我看来属于最乏善可陈之列,写得非常平庸。”——这应该是纪德最真实的想法,大约他是真不喜欢普鲁斯特,也或许是真不喜欢《追忆逝水年华》,或者两者皆不喜欢。——尽管他在公开场合多次表达了对《追忆逝水年华》的赞赏,与普鲁斯特本人的通信也多到足够结集成书。纪德曾在《日记》中定义他心中的真正的艺术家,“不是原原本本的讲述他经历的生活,而是原原本本经历他要讲述的生活。”这是一个按生活那边讲述,或是按讲述那边生活的问题,他对《追忆逝水年华》的有些矛盾的态度,大约是有时他把普鲁斯特当成一个按生活那边讲述的作家,有时又把他看作是按讲述那边生活的作家吧。
“我从心底看不起那种只从静谧和懒散所得的智慧。”
不巧的是,普鲁斯特的写作表面上看上去恰好像是拜这两样、至少也是与这两样相似的东西所赐。沙龙公子普鲁斯特为了写作“割断最后的缆绳”,长时间待在他的方舟——巴黎豪斯曼林荫大道102号内一间由软木包裹四壁、一点声音也没有的房间里,或是阿姆兰街44号那间租金昂贵的卧室内,偶尔深夜来访的纪德,最强烈的感受大约就是静谧与慵懒了。——这是他从生活里观察到的普鲁斯特,所以他会抱怨普鲁斯特在小说里堆砌细节,“那么多的细腻描写显得毫无用处……”的确,在捧起《追忆逝水年华》之初,谁都忍不住要感喟:太细腻、太琐碎、也太长了。可是,在普鲁斯特这,细节没有多余的,细节都是入口,只要读者不那么心急,无论是小玛德琳娜茶点、路易十六时代风格的房间、威尼斯花边、凡特伊奏鸣曲、还是斯万夫人胸口上的卡特兰兰花,都能将人们领到往昔岁月中做一番不可思议的漫游。人们称普鲁斯特为细枝末节的搜集者,(他曾从病床上爬起来去沙龙观察上层贵族如何戴单片眼镜,半夜去一位女士家问她二十年前戴过的一顶帽子还在不在,因为他想让斯万夫人戴。)而普鲁斯特则认为自己是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求索伟大的法则”。是啊,撇去生活表面上的静谧与慵懒,才能看到一个在“方舟”上打量洪荒世界的孱弱而顽强的人,以及病床边白木方桌上那支抵抗时间与死亡的笔。“任何事情不首先穿透死亡的概念便不可能得到我的关注,哪怕我什么都不管,处于彻底的休息之中,死亡的概念仍然像自我的概念那样一刻不停地陪伴我。”理解了这些,谁又敢说这部小说的作者只是在搜集生活的细枝末节呢?
萨特可能是那个时代最懂得普鲁斯特的人。
与纪德相反,萨特从普鲁斯特的文字中发现他。“我喜欢普鲁斯特,这是一个逐渐产生的过程。”普鲁斯特的确不是一个让人读了第一页就会喜欢上他的作家。“人是在他写的书中被人发現的。我和你都只是通过普鲁斯特的书来发现他的;我们喜欢他或不喜欢他也是从他的书中来的。人在他的书中现实地存在着,人的价值是从他的书中来的。”——这非常普鲁斯特。普鲁斯特在小说中谦卑地告诫读者,告诫我们,我们不是他的读者,而是我们自己的读者,他不过是像贡布雷眼镜商递给顾客放大镜那样,通过这部著作递给了我们一种阅读自我的方法。如果我们没能在阅读的过程中观察到那个隐秘的自我,那个对不止一人而言的自我,一定是我们忽略了不该忽略的什么。
生活“那边”的情形与虚构“那边”差不多。
日常生活总是给人重复、单调的印象,仿佛水滴总是滴落在同一块石头上,那些耐人寻味的瞬间通常更容易被人忽略、遗忘,因为它们比落在纸上的文字更难捕捉。如果我们像阅读普鲁斯特那样时不时停下脚步,思考、观察我们的生活,也许生活就会向我们展现它更多的不同寻常之处。
今年夏天,岛城海边多了几个核酸检测点,有一处就设在海滨步行道边上的小广场上,这应该是岛城距海最近的核酸检测点了,如果风大一点,又赶上涨潮,排队做核酸时,就有可能被扑上岸来的浪花打湿衣衫。在必须去做核酸的日子里,我总是选择去这个距海最近的检测点。排队等待时看看海,吹吹海风,感觉上会有些不一样。来这做核酸的人很多,有的人来时会牵着他们的狗,把狗拴在海边的栏杆上后再去排队做核酸。狗们很快就熟悉起来,一见面就免不了扑到一块亲昵地打闹。而它们的主人戴着口罩,沉默地将它们拉开、拴好,很快狗一排、人一列地各自归位,共度一段海边时光。
海中有两个小岛,有时它们看上去很近,有时看上去很远,有时干脆隐而不见。不过,不管天气如何,看不看得到那两个小岛,却总是能看到船,大船、小船,以及庞大的货轮,不同颜色的集装箱积木一样牢固堆积在船上,它们来来往往,像个安慰,使人感觉世界还是昨日模样。天气晴朗时,还能看到些漂亮的小帆船, 它们在阳光和波涛之间飘荡,轻巧得像是翩翩起舞的蝴蝶……每一天都不一样的海,不,是每一分钟都不一样的海。看久了,就会发现海边的每一块礁石、每一处弯曲的海岸,也总是在以不同的姿态迎接每一个潮涌。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里写大海,“我拉开窗帘。每个模样的大海停驻的时间从未超过一天。第二天,就是另一个大海了,偶尔也与前一日的大海相像。但我从未见过相同的大海出现过两次。”在《追忆逝水年华》丰沛到令人窒息的细节之中,如今这是最能引起我共鸣的一段。有一天,做完核酸我又顺着海滨步行道往东信步走去,经过了几个沉默的垂钓者后,在一处悬崖边,看见不知谁贴在木栏杆上的一张红色小贴纸,上面写着“体温正常”几个字。这一刻过后的大海,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刚测过体温,且体温正常的海,连它偶尔扑向岸边的大浪,也仿佛是为了逗乐而跟人们开的一个玩笑……这种感觉奇怪而又自然,好像有谁在我们的生活里竖起了一块新布景,日常的事物在向我们演绎什么,我们不知不觉、身不由己地参与其中。普鲁斯特在巴尔贝克看到过蓝色、灰色、火红、暗紫色、甚至粉红色的海,还有马戏团一样的海、城堡般的海、像啤酒或是像牛奶似的海……但当他走进画家埃尔斯蒂尔的画室,他要从画作,从画家笔下的房屋、教堂、水手和船只之间辨认海。他长久地凝视一幅画,然后醒悟过来,“这还是海。”就像在摩西脚下认出金牛,在亚伯拉罕脚下认出羊。
巴尔贝克海边有埃尔斯蒂尔,岛城海边有孙师傅和宋老师。
在任何一个季节,任何一个季节中的任一天,任一天中的任一个时辰去海边,你总能遇到钓鱼的、赶海的,或是佩戴简单的潜水用具只身下海的海碰子,就像普鲁斯特通过埃尔斯蒂尔的画笔重新认识巴尔贝克的海一样,我也要通过这些每日与海打交道的人重新认识身边这片海。孙师傅和宋老师便是他们中的两位。宋老师六十七岁,退休前在一家职业学院教模具设计与制造,主攻外壳注塑模具。他为一款家用医疗器械设计的注塑外壳新颖美观,很受欢迎,热销多年。宋老师每天下午三点左右开车来海边,做完核酸去钓鱼,或是钓完鱼再做核酸。宋老师一人三杆,随身一只小桶,一把小马扎。与其他垂钓者不同的是,宋老师钓到小鱼,会重新放回大海,因而他的小桶里,总是空的。我观察过不少垂钓者的小桶,桶中多是成人拇指大小的鱼,以小黄鱼为多。我童年时在家乡稻田边的小水沟里抓到的鱼,也要比这大、比这多。有次我站在宋老师的空桶边,问宋老师钓到过的最大的鱼有多大。宋老师指了指瞭望塔那,说去年,我在那钓到过一条一斤二两重的黑头。二十年前,我刚来青岛时,一位同事说她小时候,退潮时在海边的礁石缝里常能抓到筷子长的鱼。想起她的话我不由叹了口气,无能怎么看,大海都像是收回了它的慷慨。这时,宋老师望着大海,很有把握地说道:“等水温低下去,十八度以下,大鱼就会多起来的。”这句话里透出的耐心、乐观让我愣住了,听上去像是说天黑前水温就会降到十八度以下似的。彼时刚进入十月,距水温到十八度以下,还有好些日子呢。所以,这位钓到小鱼不会要、知道现在水温高大鱼少的宋老师,真的是来钓鱼的吗?倒更像是在给生活注塑,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倒一个不那么荒诞的如何存在的模呢。
再说说孙师傅吧,孙师傅七十一岁,退休前是青岛造船厂电焊工,参与过全国第一艘浅吃水喷水推进多用拖船的船体焊接工作。(孙师傅说起这个名字有些拗口的拖船时,口气很是自豪的。)傍晚去海边散步,在著名的海滨景点“燕岛秋潮”以东约五十米处的小码头,常能遇到赶海归来的孙师傅。孙师傅赶海所用工具很简单,一艘自己组装的皮筏子,只有一只澡盆大小,皮筏子的一头用白色泡沫板加高,形成靠背。两根八爪竿,一把小鱼叉,潜水服、氧气瓶、小桶什么的,也是少不了的。孙师傅身材高大,小皮筏子上也实在不像是能呆得舒服的地方,所以我一直以为,他和那些后备箱里放着潜水用具、下班后开车匆匆赶到海边的年轻海碰子一样,每次在海水里最多也就耍个两三个小时,就会兴尽而归的。
那个距海最近的核酸检测点会在晚上七点半收摊,有时为了避开高峰期,我会在收摊前赶过去做核酸。有一天,做完核酸,天已经黑了,路灯亮了起来。我往海边走去,老远就见有几个人围在小码头那,脖子前伸,低头看着地上什么,路灯从他们头顶照下来,远远一看,像在演一出舞台剧,有趣得很。我猜应该是有海碰子上岸了,收获大约可观的,否则也不会引起大家围观了。我便也加快脚步,赶紧过去看一看。偶尔,遇到海碰子上岸,碰巧他们有收获,收获还不少,自己吃不完,有多余的要出售,我也会从他们手上买一点,多是小杂鱼、八带、海螺之类,样样都要比从集市上买的更新鲜。我从他们那买小海鲜,也从他们那获得了许多知识,比如,从孙师傅那我知道了如何分辨前海和后海的八带,前海八带色近人类肤色,浅褐色,或是偏灰色,后海八带则偏黑色。据孙师傅说,焯过水后,后海的八带会缩小很多,而前海八带不会。听上去后海八带滑头得很,善于弄虚作假的,而前海八带则是老实的八带,货真价实的肥美。我走过去后,挤进人群,才发现是孙师傅上岸了,他正在整理渔获,一只小盆里装着两条小黑头鱼,小桶里有二十来只八带,孙师傅正把它们五只一组地分装在塑料小盆里。孙师傅一般都在天黑前上岸的,所以以往,我多是在傍晚买了小海鲜后,直接拎回家烧来吃。这个点过了饭点了。我看着小盆里的这些前海八带,心里有些遗憾。我问孙师傅今日什么时候下的海,怎么耽搁得这么晚。孫师傅点了支烟,说下午一点就下海了。我有些吃惊,很难想象他靠这个小筏子在海水里泡了五六个小时。这时,一个戴着口罩、牵着条边牧遛弯的大爷路过,对孙师傅说,“老孙,早上那条偏口不错啊。”孙师傅笑着冲他挥了挥手。我惊讶地问孙师傅,早上您也下海的吗?孙师傅说有时早上也下海。“玩呗。”说着他摇了摇头,叹道:“哎呀现在可真没啥意思。”
那晚我还是从孙师傅那买了一小盆八带,没让他帮着处理,而是按照他教的保鲜方法,把塑料袋扎紧口,放进了冰箱的冷藏室里。第二天中午,我把那几只八带拿出来时,发现它们已经窒息而亡。我松了一口气,洗净后配上白萝卜丝烧了个汤,汤的味道依然很鲜美。喝着汤我突然想起孙师傅的那一声叹息,突然悟到“没啥意思”的可能不是海上,而是岸上。因为岸上“没啥意思”,孙师傅在海上待的时间才越来越长的吧?这很难不让人想到普鲁斯特。普鲁斯特三十五岁前混迹社交场所,“一直过着一种极为可笑的、极为懒散的、极为无聊的浪荡生活。”(斯蒂芬·茨威格语)一夜之间,像是感觉到脱钩的发条马上要敲响丧钟,他一下便把自己从最最喧闹的社交界掷入到最最艰苦孤独的写作之中去。他上了他的方舟,在那似水年华里去漂,一直漂到生命最后一刻。孙师傅、普鲁斯特,是不是又很有些像若昂·罗萨的短篇、《河的第三条岸》里的父亲?父亲买了条小船,他坐上去后,便终日在河里划来划去,再不肯上岸……生活与虚构,就这样无缝对接了起来。
科幻作家特德·姜在短篇《巴比伦塔》里写道,“用(雕花)滚筒在一块柔软的泥版上一碾,就会留下一个花纹印记。滚筒上不同侧面的花纹会留下不同的印记。光看泥版,两个不同的花纹完全可能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可在滚筒上,这两个花纹却紧紧挨在一起。宇宙万物就相当于这样的滚筒。在人类的想象中,天堂和地面仿佛各在泥版的一端,中间横着天空和星辰。可事实上,天堂与地面通过某种不可思议的途径卷成了一个圆筒,在圆筒上,天与地相接相连。” 生活与虚构有如天与地,存在于同一只雕花滚筒上,或者,像是巴尔贝克与埃尔斯蒂尔的画,都以各自的姿态真实存在,彼此错综交错,并无明晰的界限。不同的是,虚构经常会被人叩问,“这可能吗?”“这么写,行得通吗?”而真实的生活则不会。人们会在小说里搜寻逻辑,在生活里则常常忽略逻辑。因为逻辑不可见,不可触摸,它对生活的撞击,也不像一日三餐那么直接。生活博大,像海面一样辽阔,逻辑在生活里形成暗流,却不掀起肉眼可见的波涛。生活里发生的一切,最終都会被人们接受,包括那些看上去似乎不可能接受、看上去似乎无法接受的事情,一旦它们发生,人们最终都会闭紧嘴巴,默默接受下来。
“父亲是一个尽职、本分、坦诚的人……在我的印象中,他并不比谁更愉快或更烦恼。” 作家既然选择描写这样一位平常的父亲,又让他做了一件不那么平常的事——买条小船,抛妻弃子,余生都到河上去漂——就必得给读者一些合理的解释。比如,父亲在这条小船上如何生存?作家没有让父亲像孙师傅那样备几根鱼竿,或是一把鱼叉,而是让儿子做出了牺牲,一辈子都在河边等待父亲,为父亲补充给养。“父亲的出走,却把我也扯了进去。”那河的第三条岸,又未尝不是儿子因为父亲而被牢牢羁绊住、再无别的可能的生活呢!那可真是一种怎么也盼不到尽头的无望的生活,像河的第三条岸一样,只可想象,无从抵达。
不过,普鲁斯特的“第三条岸”却是清晰可辨的,他为我们远远地指认了出来。“青草必须生长,孩子们必须死去。”自然永恒,人生苦短,所有的“那边”密密交织,一代又一代的人拎着野餐篮,踏着青草而来,欢快地享用他们“草地上的午餐”。——蓝中丰富,会有纪德不死的种子与地粮,也会有普鲁斯特的小玛德琳娜茶点……人们正是以这种方式去战胜死亡、战胜时间。
伊朗导演阿巴斯说:“需要一定的胆量,甚至勇气,在银幕上放置空无,什么也不展示。”但在他的电影中,恰恰是那些没有台词的静默、单调的长镜头最能震撼人心,它给了观众时间,去观察、思索,笨拙而又勇敢地模仿上帝审视这世间。毕竟,对于存在来说,绝对的空无是不存在的,绝对意义上的空,就是虚空,而虚构世界的全部秘密,或许就藏在那些平滑的虚空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