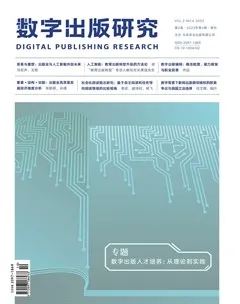要素·结构·功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经济维度分析
2023-06-22张新新孙瑾
张新新 孙瑾
摘 要: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出版经济活动,要提高出版活动经济质量,就要基于高质量发展理念,重塑出版产业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在要素层面,提升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质量,加快提升数据、信息、知识、技术等新生产要素的协同配置效率,用好书号这一特殊要素,优化其配置效率以提升出版物单品种效益;在结构层面,致力于解决出版业结构不平衡、比例失调、内部不协调等问题,实现出版结构的宏观、中观、微观多维重塑;在功能方面,通过出版经济高质量增长,为出版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的实现奠定牢固基础。
关键词: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数据要素;数字出版;出版融合发展;出版经济
DOI: 10.3969/j.issn.2097-1869.2023.04.007 文献标识码:A
本文著录格式:张新新, 孙瑾. 要素·结构·功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经济维度分析:基于提高出版经济活动质量的视角[J]. 数字出版研究, 2023, 2(4): 47-56.
既往研究基于协同论,概括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蕴含文化自信、高质量增长、技术赋能“三位一体”的协同创新发展[1],建构了“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文化—经济—技术三维协同创新理论模型”[2];基于文化视角分析了提高出版活动的文化质量[3];基于技术视角研究了提升出版活动的科技含量[4];本文则基于经济视角,思考和探索如何提高出版活动经济质量,从出版业经济子系统的要素、结构和功能层面进行论述。
1 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属性与经济子系统
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以创新为驱动,遵循经济协同机理,以提高出版活动的经济质量为内核,以提高单品种经济效益为标志。出版创新程度决定发展质量,要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的改善和提升,进而实现出版业整体充分、平衡的发展,最终加快推动包含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产业尽快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以创新为内驱力、以单品种效益提高为主要标志、以高质量经济活动为内核、以“质量、效率、动力”三维变革为路径的出版业高质量增长,对出版产业系统和出版企业都提出了新标准和新要求,需要在审视以往出版系统的要素、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进行出版要素的回归重构和出版结构的多维重塑,以确保出版高质量发展功能的良好发挥。
经济属性,或曰产业属性,是指出版业反映和体现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的性质和特点。经济属性是出版业经济子系统在出版系统宏观层面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出版业的经济属性,体现于静态的出版物和动态的出版活动。从静态视角来看,经济属性是由出版物的商品性所决定的,即:“劳动产品、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5]。从动态视角来看,经济属性包含在出版活动的全过程,出版物的策划、编辑、审校、印制等环节凝结着大量的出版者劳动;出版物的销售过程,是出版者让渡出版物的使用价值以获得价值、实现价值的过程。
出版业经济子系统的构成要素主要有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数据要素、技术要素以及作为特殊要素的书号资源等生产要素,以及分配、交换、消费环节的要素[2]。出版业经济子系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以后,尤其是在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更加显著,具体表现如下:市场在配置出版资源中从基础性作用向“积极作用”[6]角色进行转变,出版机构以市场主体身份参与市场活动,信息、知识、数据、技术、人才等新生产要素配置质量逐渐提升,出版要素市场化配置不断完善,全要素生产率逐步提高,出版物发行渠道不断健全,出版领域市场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推动着现代出版市场体系的日臻完善。
回顾历史,我国出版业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繁荣发展的历程,长期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以下一组数据可以表明这一点:新书品种数从1978年的1.19万种,增长至2016年的最高值26.24万种;重印数从1978年的0.31万种增长至2019年的28.10万种;总册数由1978年的1.50万种增长至2018年的51.90万种[7];营业收入由1978年的7.22亿元,增至2019年的989.65亿元,利润数增至2020年的163.80亿元[8]。
但出版业在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以及主要依靠投入型增长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难题,才能推动出版业向质量更高、效益更好、影响力更大的方向发展。回归到出版业系统的视角来看,这些问题就是集中于要素、结构和功能方面的问题。
出版业发展不充分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从根源上说,这种不充分是要素配置不充分、不合理、效率不高,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较低造成的。生产率,即单位投入得到的产出水平,即产出除以投入。经济学对生产率的研究经历了从单要素生产率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变迁过程:
单要素生产率是指投入单位某一特定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某一类)得到的产出水平,表现为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等。
单要素生产率的问题在于不能全面地反映生产要素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关系,为此,全要素生产率应运而生。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要素(资本、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变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因素”[9]。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是用产出增长率扣除要素增长率(土地、劳动、资本等)所得到的残差(即技术进步),也被称为“索洛残差”法。2020年3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10]中提出五种要素,其中土地、劳动力、资本属于传统生产要素,而技术、数据属于新兴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主要包括技术进步、资源优化配置等。
2 要素向度的回归重构
根据“索洛模型”,经济增长的直接来源包括要素投入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前者属于投入型增长,后者属于效率型增长。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应该从投入型增长转变为效率型增长,即由过去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投资规模扩大实现经济增长,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资源优化配置等来实现高质量增长。所谓要素向度的“回归重构”是指两方面:一方面,出版业高质量发展需不断改造并优化传统生产要素,提高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则要高度重视数据、信息、知识、技术、标准等新生产要素,充分挖掘新生产要素的贡献价值,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切实提高出版业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此外,还需重视“书号”这一特殊生产要素的作用和调控意义。
鉴于土地要素与出版业的直接关联度不大,本文从其他几个要素开展分析:资本要素是指那些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投入到出版物或出版流程的中间产品或金融资产。中间产品是生产另一种产品的物质前提和条件,是指投入出版产品生产过程的实体形态的具有经济性价值的物品,如厂房、机器、设备、工具、原材料等。这些中间产品和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其他生产要素通过配置而进行产品生产。出版业的资本要素主要包括纸张原材料、油墨材料、印制设备等。我国图书出版1978年的图书品种数为1.50万种、总印数为37.74亿册、总印张为135.40亿印张[11],2019年图书品种数为50.60万种,总印数为105.97亿册,总印张为937.60亿印张。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图书出版自改革开放以来至2019年,用纸量增长6.9倍,图书品种数增长33.7倍,总印数增长2.8倍。进一步分析可发现,单品种印数下降较为严重,其经济效益增长是靠品种数的堆积以及原材料的投入增加而产生的,在整体增长的同时,单品种效益在下降。这与前述提及的出版业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标志是单品种效益提高相违背。因此,提高出版物单品种收益,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高资本的单要素生产率,推动出版业的绿色增长、环保型增长,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增长的题中之义。
劳动力要素是指出版从业者的数量和质量,是出版从业者基本劳动力、知识、技能等专业化劳动能力。出版业从业者群体规模的扩大,出版人由“剪刀加糨糊”时代的简单劳动力向专业劳动力、高级劳动力的转型升级,其专业化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升,推动着我国出版业的发展进程。出版从业者职业技能和资格提升的重要标志就是出版职称的设立和完善:2001年,出版从业者职称制度的设立和实行是一个重要标志;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数字出版职称的设立。2016年,北京市首开先河,设立了全国第一个数字编辑职称,以“数字新闻、数字出版、数字视听”“内容编辑、技术编辑、运维编辑”为内核的数字出版“三横三纵”[12]职称序列被正式设立,并于次年被当年的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现为国家新闻出版署)选择性吸收到全国职称中。2023年4月26日,新疆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版系列职称评审条件(试行)》[13](新人社发〔2023〕30号),明确“适用于经国家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图书、期刊、音像、电子和网络等出版单位出版编辑现职岗位从事编辑(包括美术编辑、技术编辑、数字编辑)工作并取得责任编辑证的人员和校对人员”。新疆首次把“数字编辑”列入职称评审范围,并将音像制品、电子或网络出版物列入实践工作量。如果说出版职称、数字出版职称的设立和实施,还是在出版领域对劳动力要素做出提升和认定的话,那么2021年11月《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的发布,则是从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数字素养技能角度,对数字出版这样的新兴职业群体数字技能提出了要求和规定。数字适应力、数字胜任力、数字创造力成为出版从业者提升数字工作效率所必须具备的三种能力。对于5G技术、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数字技术原理的把握和应用,也是出版从业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时代使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出版业高质量增长,对劳动力要素的要求是:践行政治家办出版的准则,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构建由政治素养、专业能力、数字技能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能力体系。出版从业者应提高政治素质,提升政治判断力、领悟力和执行力,以创新能力贯穿和重塑专业能力和数字素养,全面提高选题策划、编校印发等专业技术能力,自觉增强数字适应力、胜任力和创造力、专项数字技术理解力、转化力和应用力所构成的数字技能体系。
上述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属于传统生产要素,下面从数据、技术等新兴生产要素或者是无形生产要素的角度来分析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
数据要素是指对客观事物的性质、状态及关系进行记录的物理符号或符号组合。数据是未经加工的数字和事实,大数据语境下对数据的使用重在强调相关关系;信息则是指经过处理、专题化的数据,对于出版业而言,信息服务也能构成一种专业出版知识服务模式;知识则是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信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重要性越来越引起重视,而出版业对数据要素的认知、理解和运用还有不小的差距。正如《大数据时代》一书所指出的,(西方国家)出版社“没有把书籍的数据价值挖掘出来,也不允许别人这样做。他们没有看到数据化的需求,也意识不到书籍的数据化潜力。”[14]出版业在数据要素配置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数据理念缺失、数据思维薄弱、数据价值挖掘不充分、数据产业链缺位、数据治理缺失等。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对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离不开对出版业数据服务系统的构建,离不开集“数据建设、共享、开发、应用、维护”一体化的数据治理体系的建立。
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高数据要素生产率,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1)确立数据理念,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制定并落实“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据赋能为主线,以价值释放和创造为核心,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数字化转型、升级、重塑和再造”[15]的出版业数字化战略。
(2)推动数据赋能,建构和践行出版业数据价值体系,挖掘和实现出版业“图书价值、数字化价值、数据化价值”[16]三位一体的价值体系。
(3)完善数据流程,根据数据采集、数据清洗、知识标引、数据计算、数据建模、知识图谱、二次数据以及提供出版大数据服务的数据服务流程,建立和优化出版业、出版社数据服务体系。这方面,人民法院出版社的“法信”大数据平台堪称典范。
(4)推进数据治理,提升行业治理能力现代化,衔接国家文化大数据工程,通过出版业数据的分析、统计和整合,预测和预判出版业发展趋势和规律。
技术要素是指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因素。技术进步是出版业的高质量增长最重要的内生动力,是绿色增长的转换动力,也是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出版的发展史是不断应用新科技成果的历史,“数字技术赋能出版”[17]是当前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数字技术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主要包括:提供更好的内容呈现、更优的用户体验、更精准的出版服务、更高的生产效率等方面。
技术进步之所以是高质量增长最重要的内生动力,是因为:
(1)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增长是效率型增长,不是要继续增加要素的投入型增长。
(2)技术进步推动出版业经济增长是创新驱动的增长,不是主要依靠要素、投资驱动的增长。
(3)出版业系统吸收内化技术子系统的新要素所引起的出版新质态——数字出版、融合出版,是落实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的主攻方向,是出版业新的增长点、绿色增长点的重要标志。
历史也证明,王选先生激光照排的发明和推广,实质性地推动了我国出版业由“铅与火”走向“光与电”,是效率型增长的典型范例。
出版业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增长要重视和强化技术要素的运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转变思想观念,转换动力机制,由主要依靠内容资源的比较优势驱动增长转换为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增长。
(2)高度重视技术赋能价值,对内基于智能技术实现出版流程再造,对外提供数字化、数据化、智能化的出版产品服务。
(3)推进财政治理现代化,继续推进重大项目驱动战略,支持出版业数字化新基建的深入实施,发挥示范效应和引领作用,解决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问题。
(4)培育技术要素市场,以研发出版业自主技术为核心,加快数字技术在出版业应用的探索步伐,完善技术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的价格机制。
(5)建立出版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充分用好出版系统内外创意资源,发挥出版智库的作用,构建“出版企业-高等院校-技术企业”的产学研一体化机制,推动出版业科技研发与应用的开放创新和协同创新。
(6)贯彻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充分体现技术、知识、数据等要素的价值,充分尊重并用好科研型、技术型、创新型、全媒体型人才。
(7)坚定不移、全面贯彻出版业数字化战略,以数字出版和融合出版为重要抓手,以提高国有出版企业数字出版收入为重点,不断提高数字化收入在出版业产业中的贡献度,进而提高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
最后,再来谈一下出版业的特殊生产要素:书号资源。书号作为我国出版业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出版系统中扮演“身份证、指挥棒和准入证”[18]的角色,书号资源配置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出版业发展质量的好坏。
从历史维度来看,我国多次提出对书号加强调控,每次调控书号均与出版业发展质量相关。2018年机构改革以后,中宣部站在出版管理一线,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监管部门对书号总量进行了宏观调控[19]。
这进一步体现了书号配置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中的正向作用,应充分发挥书号治理的功能。出版单位也要充分认识和正确理解加强书号调控的初心,这是实现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和良性发展的契机[20]。截至2020年,新书品种数为21.40万种,较2016年的26.24万种下降18.44%,而营业收入、利润却分别增长15.77%、21.97%[21],应该说,出版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了相对明显的提升。
3 结构层面的多维重塑
如果说,出版业要素层面的问题主要是发展不充分,即要素配置没有被最优化、要素潜力没有被挖掘、要素价值没有充分实现等,那么,出版业结构层面的主要问题则是发展不平衡,包括宏观、中观、微观方面的结构都存在着比例失调、好坏不均、内部不协调等问题。
出版结构是指出版系统内部各要素、属性、子系统之间相互组成、结合的方式。出版结构是多维的,包括宏观层面的供需结构、出版物数量与质量结构、图书出版与新兴出版结构、出版业区域结构、出版业的销存结构等;中观层面的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大众出版等出版业态构成;微观层面的出版物品种结构、市场主体结构、出版单位内部组织结构等。
3.1 宏观层面的出版结构
首先,看宏观层面的结构,一是出版业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出版业的内容原创不足[22]、供给跟不上需求[23]、产能过剩[24]、精准匹配率[25]、在国际图书市场话语权及影响力弱[26]等供给侧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类型化总结如下:
(1)内容供给无法适配市场需求,原创度低,精品力作规模较小,“高峰”式作品仍然缺乏,同质出版、重复出版、跟风出版现象比比皆是,大大削弱了出版产品的原创竞争力,直接影响到整体图书产品供给侧的品质和评价,尚未能最大程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2)出版产品形态单调,供给跟不上用户需求。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广大读者数字素养的不断提升,对个性化、高品位、多样化的文化产品需求也日渐旺盛,而图书出版的供给仍然是以纸质图书为主,难以匹配用户需要。
(3)产能过剩惊人,存销结构失调,潜藏着较大风险。作为第一出版大国,同时,我国更是“第一库存大国”[27]。2018年调查数据显示:年销售数量小于5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34.5%,这意味着近三分之一的图书形成库存,面临报废[28]。这样高比例的存销比,正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所要解决的问题,高库存、高浪费潜在蕴藏着很大的经营风险,不符合出版业的安全发展要求。
(4)图书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结构不合理,国际贸易刚处于小幅顺差状态,“走出去”却没有“走进去”,图书出版的国际传播效能仍有待进一步提升。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版权贸易逆差从2005年的7.20:1[29]缩小到2020年的1.02:1[30],创下了版权输出和版权引进的最小逆差纪录;至2021年,实现出版物版权贸易顺差550项,其中输出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版权12 770项,引进12 220项[31]。从出版产业来讲,出版物版权贸易首次处于小幅顺差阶段,但出版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还比较弱,国际化收入需要进一步提升、国际化品牌需要进一步强化、国际化发展格局需要从点的突破向面的形成转化。由此,高品质的内容供给、立体化的产品形态、降库存补短板、走出版业国际化高质量发展道路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宏观结构方面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出版物数量和质量结构问题较为突出,这也是一直以来主管部门调控的重点所在。宏观方面,我国出版业年度总出书品种数一度超过了50万种,是美国的2倍以上、日本的近5倍,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出版大国。然而,数量上去了,整体的出版质量和相匹配的出版效益却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出版物供给结构不合理,面向特定区域、特定群体、特定行业的结构不平衡不充分[32],如少数民族出版基地的出版物数量和质量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内容质量方面,我国高水平的国际性学术期刊数量不足,期刊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仍有待提高[33],图书传世经典之作数量仍然不足,整体出版物内容质量尚需再提高一个档次。形式质量方面,在图书“质量管理”专项工作中对图书进行编校质量检查,结果显示出整体编校质量良好,但是仍有部分的图书编校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提高图书单品种效益,提升出版物内容质量,多推出精品力作,走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之路,是解决出版物数量与质量结构问题的关键所在。
再次,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二元结构。自2010年《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以来,历经“十二五”“十三五”10年的发展,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总体产值已突破1万亿元[34],推出了一批双效统一的数字出版精品。出版融合发展示范单位遴选推荐计划、出版融合发展优秀人才培养等项目的实施,使数字出版发展质量和效益也在不断提升,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二元结构基本形成。“传统、新兴两种出版的二元界分、二元并存状态将长期存在,直至出版机构完成从内容提供商向知识服务提供商的转变”[35]。“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新型出版传播体系有待加快建立。
二元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两张皮”“两股道”的问题: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在发展理念、产品研发、技术采纳、市场营销、业务流程、制度体系等方面均是各自独立,甚至还存在着相互质疑或对立的个别现象。这种问题的根源是发展理念的差异,是把数字出版作为战略方向还是作为战略补充甚至是战术任务的差别。
(2)融合不够、互动不足,合而不融、融而不深的问题也普遍存在于出版企业,基于文化、经济、技术子系统的三维协同体系没有构筑起来,诸多出版单位只是把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进行简单的线性相加,而不是推动二者产生吸收、内化、融合的相干效应。
(3)提质增效不足,质量效益不高:一方面,传统出版增长乏力,缺乏技术进步的支撑,全要素生产率不高;另一方面,虽然新兴出版总体产值持续上涨,但实质上国有数字出版的产值收入占比在持续下降,意识形态主阵地上的数字出版亟须做大做强。破除“传统出版-数字出版”二元结构的障碍,需以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这个“顶层设计”[36]来推进出版业的发展,实现发展的平衡、协调和可持续。
3.2 中观层面的出版结构
中观结构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对教育出版的太过倚重、高度依赖,教育出版占据了出版业的半壁江山及以上;而仍有广阔市场的专业出版、大众出版等业态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2000年我国课本出版比例占到全年出版的56.73%[37]。教材出版、教辅出版销售收入整体占比接近我国出版业年度销售收入的三分之二。这种一家独大的出版业结构,不利于出版业整体的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增长需要大力发展专业出版、大众出版,以形成更为平衡、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出版细分市场结构。
3.3 微观层面的出版结构
对于微观层面的出版结构,一是出版物品质结构,需以高质量系统的观念来解构和综合出版物品质,即出版物品质是由内容质量、载体质量、编校质量、设计质量和印制质量所构成的“内在质量、外在质量”双位一体的质量体系。要以提升出版物内在质量为关键,同时注重载体质量、编校质量、设计质量、印刷质量的提升,不断改善出版物的品质结构,进而提升出版物的整体质量。二是出版市场主体结构,以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来看,在严格做好导向管理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在网络出版领域对民营文化企业开放市场准入机制,以增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三是出版单位内部的组织结构要以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为核心,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增强出版企业创新活力,尤其是注重将“研发能力和策划能力”[38]作为出版业的核心竞争力,推进产品创新研发,推动出版技术进步,最终不断提高出版产品质量,实现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
4 功能视角的再度审视
如前所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是蕴含文化自信、高质量增长、技术赋能“三位一体”的协同创新发展。对出版系统要素的重构和对出版结构的重塑,旨在推动出版业功能的发挥,使之符合出版业高质量增长的目标。通过对出版发展系统要素的重构、结构的重塑,旨在解决出版高质量发展生产要素的不充分、发展结构的不平衡问题,从而服务于出版高质量增长、高质量发展功能的良好发挥。具体而言,出版业高质量增长功能可阐述如下:
首先,出版业的高质量增长可为出版政治功能的实现提供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出版政治功能是指出版“服务于社会政治建设的效用,是出版社会功能的核心意涵”[39]。出版业高质量增长本身就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成果,是新发展理念在出版领域应用的呈现,是高质量发展战略在出版范畴的体现。出版业的高质量增长,直接推动着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进一步巩固了文化产业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重要地位,为完成政治引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宣传引导等政治任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环境;出版业高质量增长依靠的是出版活动主体,其发展成果也由出版活动主体共享,出版活动主体通过高质量增长增强了人民幸福感,进而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出版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导向,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学习和阅读需要。
其次,出版业的高质量增长,较之于低质量增长、一般性增长,则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出版经济功能的发挥。一方面,出版业作为国民经济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直接做出经济贡献,创造出社会财富;其高质量增长、高质量发展,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出版领域起到推动传统经济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数字出版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技术进步、技术赋能出版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结果,客观上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此外,出版业的高质量增长为社会输送更多的文化、科技、教育价值,提供了丰富的出版产品服务,这些出版产品服务被消费的同时也提升了劳动者政治素养、文化素养、数字素养等综合素质,最终提高了社会各行各业的劳动要素生产率。
最后,出版业高质量增长,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出版文化功能的实现。高质量增长意味着技术赋能出版,意味着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选择、建构和传播提供更多的表达方式、更立体的呈现方式以及多样化的产品形态。高质量增长意味着出版经济处于效率型增长阶段,能够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地推动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和公共文化服务的稳定保障。高质量增长还意味着服务文化子系统是以文化自信为引领的增长和内容质量提升的增长,能够整体带动出版物文化质量的提高,进而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学习阅读需要、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
5 结语
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高质量发展要把发展的动力确定在“创新”概念上,以经济活动质量重新定义“结构”,把创新含量作为经济活动质量的衡量指标。依此,出版业高质量发展需“不断提升出版活动的经济质量,提高出版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动出版业发展质量、效益、结构、规模、速度、安全相统一,进而实现出版业整体平衡充分的发展”[1]。本文在出版产业的要素层面,分析了改造提升传统要素要以提高单要素生产率、培育壮大新兴要素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科学配置书号资源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而解决出版业发展的不充分问题。在出版产业结构层面,论述了出版业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结构优化,通过结构优化来解决出版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在出版功能方面,阐述了高质量增长能更好地服务出版业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值得一提的是,出版业这个复杂系统在要素、结构、功能方面走向“高级有序”的前提和基础是出版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作为基本细胞和最小单位的创新型出版企业的构建和实践。
作者简介
张新新,男,上海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数字文明研究院院长,国家新闻出版署可信数字版权与生态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方向:数字出版、人工智能、文化管理与服务。
孙瑾,女,新疆人民出版社数字出版部部长,副编审。研究方向:数字出版、出版运营管理。
参考文献
张新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界定与基本特征[J].编辑之友,2023(3):15-24.
张新新,敖然.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三维协同创新模型建构与分析:基于“文化—经济—技术”视角[J].中国出版,2023(16):21-27.
陈少志,张新新.出版业文化质量的提升向度与路径探析:基于编辑工作的视角[J].中国编辑,2023(7):32-38.
张新新.技术赋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技术蛙跳双案例研究[J].出版与印刷,2022(3):30-43.
罗紫初,吴赟,王秋林.出版学基础[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55-56.
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EB/OL].(2022-02-21)[2023-10-16].https://www.nppa.gov.cn/nppa/contents/279/102953.shtml.
杜大力,赵玉山,邢自兴.从大数据看新中国70年出版成就与发展历程[EB/OL].(2019-10-11) [2023-10-16].https://pub.bnu.edu.cn/xydt1/80116.html.
观研天下.中国图书出版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未来投资研究报告(2023-2030年)[EB/OL].(2023-09-06)[2023-10-16].https://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309/658135.html.
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13-20,90.
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EB/OL].(2020-04-09)[2023-11-01].https://www.gov.cn/zhengce/2020-04/09/content_5500622.htm.
朱晓峰,刘拥军.1978—1998中国出版业量化分析(上)[J].出版经济,1999(1):25-28.
张新新.我国数字编辑职业化历程回顾与价值分析[J].出版广角,2016(5):17-1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版系列职称评审条件(试行)[EB/OL].(2023-10-08)[2023-11-01].https://dwjsgzb.xju.edu.cn/info/1093/1309.htm.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12.
韩梅,张新新.出版业数字化战略内涵解读与路径思考[J].科技与出版,2021(5):53-59.
张新新.新闻出版业大数据应用的思索与展望[J].科技与出版,2016(1):4-8.
张新新,丁靖佳.立足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学科体系[J].数字出版研究,2022,1(1):17-31.
高海涛.我国书号管理制度:功能、效果及反思[J].编辑之友,2021(7):13-17,24.
陈香.2018年中国出版十件大事[N].中华读书报,2018-12-26(16).
尚跃平.合理配置书号资源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1-01-13(1).
观研天下.中国图书出版行业现状深度调研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22-2029年)[EB/OL].(2022-11-10)[2023-10-16].https://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211/616801.html.
谢清风.以供给侧改革提升出版社会效益[J].中国编辑,2017(1):6-9.
李晓晔.“供给侧改革”与出版创新[J].出版发行研究,2015(12):1.
周书灵.出版产业供给侧改革政策解读及其误区[J].编辑之友,2016(6):14-17.
冉梨,张洪建.深度融合发展视域下数字出版二元供给体系探索与研究[J].编辑之友,2021(2):38-46.
姚宝权.试论我国传统图书出版的供给侧结构改革[J].中国出版,2016(13):12-14.
刘彬,陈恒.第一出版大国的尴尬[N].光明日报,2013-04-18(16).
吴明华.立足专业细分领域 做强高端学术著作出版[J].出版发行研究,2016(7):42-43,65.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业输出引进这十年 版权贸易逆差正逐渐缩小[EB/OL].[2023-10-16].http://www.shsjcb.com/sjcb/bkview.aspx?bkid=217617&cid=665740.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五大看点!解读最新全国出版业统计数据[EB/OL].(2022-01-05) [2023-10-1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1069790435212183&wfr=spider&for=pc.
国家新闻出版署.2021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EB/OL].(2023-02-23) [2023-10-16].https://www.nppa.gov.cn/xxgk/fdzdgknr/tjxx/202305/P020230530667517704140.pdf.
方卿,张新新.推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几个面向[J].科技与出版,2020(5):6-13.
刘晶晶,李欣人,田宏.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我国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思考[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3,34(9):1097-1103.
王飚.新时代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前景探析[J].数字出版研究,2023,2(1):1-16.
张新新.基于出版业数字化战略视角的“十四五”数字出版发展刍议[J].科技与出版,2021(1):65-76.
本刊编辑部,赵慧君.出版融合新发展,破茧成蝶再辉煌:2023出版融合发展经验交流会暨专题研讨班综述[J].数字出版研究,2023,2(2):1-5.
代周阳.我国图书出版产业结构状况研究[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3,21(5):8-13.
辰目.再谈出版业结构问题[J].出版发行研究,2001(4):1.
方卿.关于出版功能的再思考[J].现代出版,2020(5):11-16.
Factors,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Analysis on Economic Dimens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shing Industr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ublishing Economic Activities
ZHANG Xinxin1, SUN Jin2
1.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nd Art Design,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093, Shanghai, China; 2. Digital Publishing Department,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830049, Urumqi, China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shing industry is inseparable from high-quality publishing economic activities. To improve the economic quality of publishing activ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reshape the factors,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publish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t the factor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raditional production factors such as capital and labor,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ynergistically allocative efficiency of new production factors such as data, information,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and make good use of the allocative efficiency of book number to improve benefit of the single variety of publications. At the structure level, it is committed to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structural imbalance, disproportionality, and internal incoherence in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realiz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publishing structure from macro-view, middle-view and micro-view. At the function level, through the high-quality growth of publishing economy, a solid foundation is laid for the realiz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publishing.
Key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shing industry; Data factors; Digital publishing; Development of publishing integration; Publishing economy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与考核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2BXW089)中期成果;2023年度第二批智力援疆创新拓展人才计划项目研究成果;上海理工大学人才项目科研资助项目“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