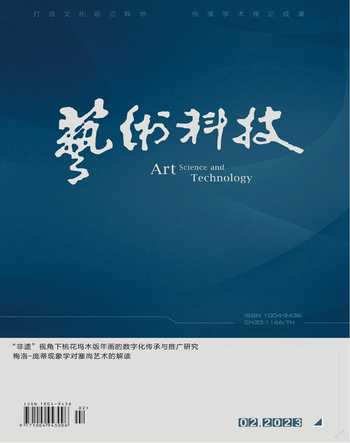论《在细雨中呼喊》的叙事艺术特色
2023-06-22贾云杰
摘要:在《在细雨中呼喊》这篇小说中,余华既保存了作为先锋小说作家延续下来的极具研究价值和探索意义的叙事方式和语言形式,又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极大的改变。尤其值得分析的是这篇小说独特的叙事艺术特色,无论是从叙述视点还是叙事顺序或是叙事技巧上,都呈现出复杂又有独特内在逻辑的特点。因此,文章主要探究《在细雨中呼喊》的叙事艺术特色。
关键词:余华;叙事视角;叙事时序;《在细雨中呼喊》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02-0-03
作为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不同于余华以往的中短篇小说的叙事手法,无论是叙事者的视点还是叙事时间,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这部小说开始,余华的写作由先锋主义小说向现实主义题材转型,他的作品中有了更坚实的现实基础,在叙述中投入了更多情感,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更重要的是在叙事方法上也不断突破。
叙述者和时间是叙事的基本特征。《在细雨中呼喊》这部小说不仅拥有复杂多變的叙事视角,在事件顺序的构造上也不同于通常以时间为线索而搭建起来的叙事小说,这使这部小说在叙事方式上十分灵活和特别。这部长篇小说主要依靠孙光林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辅之非聚焦型视角和不定内聚焦型视角穿插的形式,讲述了孙有元、孙广才和孙光林祖父孙三代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主要人物的故事。小说的叙事结构看上去是杂乱的,事实上,文中“我”对世界的独特情绪感受始终统摄着所有情节的顺序。
1 多重叙事视角的结合
1.1 第一人称叙事的客观性
小说通篇以第一人称视角叙事,故事的主人公孙光林以“我”的口吻讲述所有的故事。由于小说属于回忆性质的自传体小说,因此“我”这一人称其实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接受过良好教育、已经成年的“我”,在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另一个则是在过去的故事中充当角色的“我”,是6~12岁的孙光林。
主观叙事关注更多的是叙事角色的心理体验,容易让读者产生代入感,从而引发共鸣。然而这种手法又是一种主观性极强的叙事手段。余华在《在细雨中呼喊》中利用“我”的双重叙事视角,这两种身份交替出现的方式,既向观众展示在发生事件的当下,“我”的所看、所想和所感,又能从已经成年的“我”的角度复盘事件。两种不同的视角对比出在不同时段内,“我”对事件认识程度的差距。在第一章中,“我”回忆童年时候,每一次被父亲和哥哥殴打后都会在作业簿上记录,然而现在的“我”却难以清晰地感受当时立誓偿还的心情,紧接着成年的“我”继续感叹“也许是记忆吧,记忆超越了尘世的恩怨之后,独自来到了”[1]9。这种带有内省性质的叙述,以及对心理活动细致的描写,将个人体验传达给公众。同时这种叙事方式实现了对心理活动的长效和动态描写。因此即使以第一人称进行主观叙事,也显示出讲述者客观和冷静的态度,这样的视角与余华冷峻坚毅的语言描写相呼应,达成整体文风的统一性。
虽然小说通篇大多以第一人称为叙事主体,但事实上,这部小说的叙事视角非常复杂。胡亚敏提出的关于叙事视角的理论中,将其分为三类:非聚焦型即全知全能视角、内聚焦型视角以及外聚焦型视角。另外,她又将内聚焦型视角细致地分为固定内聚焦型、不定内聚焦型和多重内聚焦型视角。《在细雨中呼喊》集齐了非聚焦型和不定内聚焦型这两种叙述视角。并且,几种视角焦点的转换方式十分自然流畅。
1.2 非聚焦型视角
首先,故事主人公“我”——孙光林毫无疑问是主要叙事者。但是,小说中许多细节语句透露出全知全能的非聚焦型视角。例如,小说第二章中,讲述冯玉青被警察带走后,鲁鲁被送到福利院的经历,以及之后自己坐车去劳改场找妈妈的情节,就完全脱离了叙述者“我”的主观视点。作者是用一段简洁的叙述,完成了叙述视点的转换:“我全新的生活在北京展开,最初的时候我是那样的迷恋那些宽阔的街道,我时常一人站在夜晚的十字路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在家乡城里那栋破旧的楼房里,赤条条的冯玉青和她一位赤条条的客人,暴露在突然闯进来的警察面前。”[1]122通过“夜晚”这一相似空间的转场,完成了叙述视角由第一人称转向全知全能视角。描述王立强出轨被抓,杀人并自杀的一整段场景,同样是由全知全能的视角来展示,因为叙述者孙光林并不在场,即使是别人之后转述给他,但这些段落中大量的细节描述,也远非转述可以做到。
非聚焦型叙事中,叙事者像先知一样,对人物命运了如指掌,观察方式是居高临下的,可以轻易把握人物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在观察人物的同时,常常辅之以白描的写作手法,因此这种叙事视角笔调是客观而冷静的,并且具有全局性,将对未来命运的暗示藏在细节之中。例如,“我”祖母的婆婆让她的儿子选择是否要休妻时,三人来到大马路上,婆婆指示祖母向西边走去,自己则走向东边。“那个捍卫家族清白的女人走向旭日东升,而我祖母只能让背脊去感受阳光的照耀”[1]137,这句话暗含了祖母的命运从此背离了阳光,她走向了另一种人生,走向了逃难的人流,走向了贫困。
1.3 不定内聚焦型视角
除了零聚焦型视角和孙光林的第一人称视角外,小说中还出现了不定内聚焦型视角。不定内聚焦型视角是内聚焦型视角的一种,即在小说中采用几个人物的视角来呈现不同的事件[2]32-33。大多数故事都是通过孙光林的视角来叙述的,然而在小说中也有段落明显是通过其他人物的主观视角讲述的。
小说第二章“苏宇之死”这一段落中,对苏宇在将死之时的描写明显是从苏宇的主观视角出发的。“他感到自己化作了无数水滴,清脆悦耳地消失在空气之中”[1]109等语句虽然是第三人称的口吻,但采用的是苏宇的主观视角,叙述的是由苏宇个人的感官所感受到的信息和产生的内心活动。像这样的不定内聚焦型视角能使读者更好地关注不同人物的主观视角的表述,也能使读者与人物更亲近,真正体会人物的感受和心境。而流畅变化的视点,得以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感受一个事件。
通过这种不断的视角变异的方式,作者可以在叙述中向读者释放更多的信息,因此也被称为“扩叙”[2]35。叙述者得以突破單一的视角焦点,从而进入更广阔的视野,向读者提供超过叙述者或人物在某一焦点位置上所能了解的信息,扩展作品的深度和广度。
整部小说中,视角焦点一直在很自然和流畅地变化。这种多视角的叙述方式非常灵活,糅合了多种类型的叙事视角的优点,使叙事更加活泼多变,可读性更强,也避免了在长篇小说中因视角单一而造成的行文呆板。同时,故事的完整性得到了更好的展现。更重要的是,单独的主观视角叙事可能带来的“独断的和偏颇的”[3]感受,被多重视角转换的叙事策略冲淡。这样的方式使叙述既带有第一人称限知叙事突出主体审美体验的优势,又保留了全知全能视角注重客观性与事件全局性的完整。不难看出,作者通过娴熟地转换叙事视角,意图使事件和故事的展开显得更加可靠,并且将自我情感顺其自然地融入其中,让作品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
2 特殊叙事顺序的安排
2.1 特殊时序安排
小说在叙事时间的安排上也是特别的。整部小说并不是按照事件的发展顺序来讲述所有故事。小说在第一章中给整部书勾勒出一个框架,主要人物依次登场,但重要的情节几乎都是一笔带过。例如,第一章“南门”这一段落中就提到“我只能长久地去怀念在王立强家中的生活,还有我在孙荡的童年伙伴”[1]8,这里提到的“王立强家中的生活”和“孙荡”都是在孙光林6~12岁发生的事,按照整部小说故事发生的顺序本应该在第一章中就展开。然而事实是,直到小说的最后一章,孙荡的生活和王立强的故事才正式被展开。再如,在第一章的第二个部分“婚礼”这一节中,讲述了关于冯玉青的故事,然而她的故事并未立即讲完,有关她的命运在小说第二章第四节“年幼的朋友”中才得到继续。这种断裂式、碎片化和蒙太奇的叙事特点的优点是勾起读者对情节的好奇与想象,但在另一方面又使小说的叙事时间逻辑很难被把握。
《在细雨中呼喊》的整体结构是:回忆南门时光,祖父的记忆回溯,孙荡镇时光,再次回到南门。这四个阶段并非按照时间顺序或倒叙排列,读者无法简单地将每一章节排列组合以此捋清故事的发展顺序,每一个叙事单元可以独立,但叙述内容又互相渗透。这种时序状态可以称为“逆时序”,也就是说,“尽管故事线索错综复杂,时间顺序颠前倒后,但仍然能重建一个完整的故事线”[2]64。
事实上,小说中故事的发展顺序确实是有其底层叙事逻辑的。《在细雨中呼喊》意大利文版自序中,余华写道:“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重新选择,可以将那些毫无关联的往事重新组合起来。”[1]5余华确认要想打破传统的故事发生顺序,释放时间,甚至重建时间,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回忆来完成。而对于回忆,人们通常是不会按照时序完整地想起过去。就像这篇小说第一章的叙事布局,作者只是描绘了一个草图,并且告诉我们在那里会出现一些重要的人,在那里会发生一些事情。这完全符合回忆的特点。由此与真实回忆极其相似的体验得以传递给读者,进而使读者可以重新搭构起作者意图讲述的真实往事,支离破碎的经历将成为一个崭新的故事。
一段回忆有可能是另一段回忆的缘起,一个事件可能内在性地促成了另一个事件的发生。这样余华就在叙述中完成了死亡与降生、旧朋友与新朋友、意气风发与毫无尊严的轮番记忆转换,叙述在自然的转变中依然流畅。因此,虽然乍看之下小说的叙述时序是散乱的,但实际上,小说是基于叙事者对世界与记忆的独特心理体验而完成的对众多章节的把控。
2.2 重复闪前
作者在第一章完成了对回忆草图的勾勒,在之后的章节中,他反复追忆其实是在对草图中的残缺部分进行填充,直至刻意被制造的碎片和断裂在一次次的填补中得到重构。于是,在这篇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就是重复叙事和预序相结合,也可以被称为重复闪前。
书中在开头提到的弟弟孙光明的死亡,在第18页中一笔带过,一句话就在最开始交代了孙光明的悲剧结局,在第22页才正式开始讲述孙光明死亡的原因和经过。同样是对死亡的叙述,苏宇死亡的预叙则跨度更大,重复次数也更多。首先是在第9页就提到“苏宇19岁的时候,因脑血管破裂而死去”[1]13;之后在第12页再次提及“不到一年,他就死了”;在第13页再次重复叙事“我觉得已被人们像埋葬苏宇那样埋葬掉了”;直到第二章,“我”与苏宇的故事才正式展开,在书中的第81页,这一章节被命名为“苏宇之死”,这才详细地讲述了已经被预序和重复提示过的这一重要事件。然而,在利用数次重复闪前勾起读者极大的探究真相的意图之后,苏宇的死亡原因显得十分平淡。这一重复闪前不仅将作者的多次强调与苏宇平淡离开人世的方式作对比,显示出生命的无常,也体现出对作者而言,苏宇的离开是那么记忆犹新,无法释怀。
包括对在孙荡镇的童年和王立强、李秀英的数次提及,以及在整部小说的最后部分才真正将故事画轴铺展开来,这种重复闪前的方式不断重复重要的事件,加深了读者对重大事件的记忆,而预序的方式有意无意地露出下文的波澜,使读者不是抱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问题,而是“事情将会如何展开”的问题,更加注重过程和细节,对文字更专注。
《叙事学》一书中提到“在叙事文中,闪前这一叙述技巧的运用不如闪回普遍”[2]69,然而仅重复闪前这一技巧在《在细雨中呼喊》一书中就被频繁使用。因此,重复闪前的多次运用可以说是这篇小说叙事方面不可忽视的一大特点。
3 结语
除了叙事技巧之外,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对语言的精确把握都是余华作品中极具个人特色的文学表现方式。《在细雨中呼喊》尤其塑造出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父亲形象:在外懦弱,回家却耀武扬威,毫不避讳地与寡妇偷情,甚至对儿媳行为不轨,对父道尊严无情嘲笑的孙广才;与有夫之妇出轨,还无意杀害了两个孩子,最终不得善终的王立强;具有强烈反抗悲剧命运的信念和无畏无惧的阳刚之气的祖父孙有元。
孙有元这个男性形象几乎是余华笔下的独一份,相比书中的其他男性,无一例外,在青春年少时期都无法克制自己蓬勃的对女性身体、两性关系的欲望,甚至做出过许多过激行为。然而孙有元即使在物质最匮乏的时候,也没有被物质欲望或原始情欲夹裹着前进,他心中似乎一直只有生存的欲望,或许是生的欲望太强,以致压制了其他欲望。不过,这奇异的一笔却为《在细雨中呼喊》的叙事增添了关于生命的另一种色彩,仿佛是在阴暗天空中忽然亮出的一道闪电,让人眼前一亮。
余华在采访中也曾表达自己对文学作品的认识,他认为写作和阅读是在叩开回忆的大门,也可以说像一次重生。或许就是秉持这样的想法,才使他利用新颖的叙事方式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读者拉入自己创造的世界中,并在这个世界中构造出这么多有血有肉、形态各异、跃然纸上的角色和离奇曲折却又引人入胜的故事。
参考文献:
[1]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5,8-9,13,122,137.
[2] 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2-33,35,64,69.
[3] 徐怡.意识研究的第一人称方法论探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5:217.
作者简介:贾云杰(1997—),女,山西太原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影视文化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