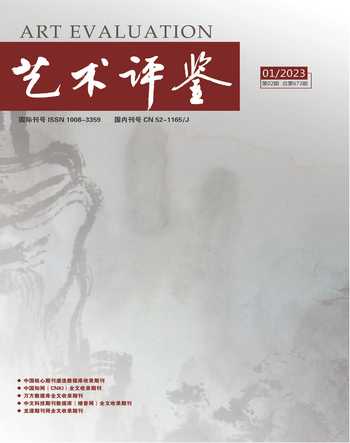解构主义视角下的舞蹈剧场《May B》解读
2023-06-21汤莹莹
汤莹莹
摘要:雅克·德里达基于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始创了解构主义批评学派,主张消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中心观念,颠覆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并推崇文本主题的多重意味解读。本文立足于德里达所提出的解构主义理论,从中心的瓦解、符号的延异与意义的播散三个角度切入,对法国舞蹈剧场作品《May B》进行解析,从中发掘该作品中所迸发的闪光点,并尝试将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运用于舞蹈作品的研究之中。
关键词:解构主义 《May B》 中心瓦解 符号延异 意义播散
中图分类号:J7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3)02-0036-05
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是由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所创立的批评学派,主张文本本身的矛盾性、丰富性以及阅读的多重性。它以质疑理性、颠覆传统为基础视野,推崇文本具有多重意味阅读的可能性,旨在打破结果的封闭性,消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中心观念,并颠覆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就德里达所提出的解构思想而言,它集中表现为对中心的分解、符号的差异与延迟、意义的播散等论点。
同样孕育于法国的舞蹈剧场作品《May B》,是法国当代舞蹈家玛姬·玛莲的神话之作。《May B》创作于1981年,时逢编导玛姬·玛莲的父亲逝世不久,受贝克特文学作品《等待戈多》的灵感驱动,她将戏剧、语言、生活化动作等非舞蹈元素融入舞蹈中,将舞蹈从芭蕾的权威话语下解放出,让身体真正成为表达思想与观念的语言,通过身体的魅力诠释出贝克特的文字与精神。本文基于德里达所主张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对《May B》作品中所体现的权威解构、符号能指以及意义播散进行分析,通过解构主义视野增强对该后现代作品的理解。
一、解构绝对中心
“解构作为一种阅读和批评的模式,首先是将反传统和反权威引为己任。”①德里达主张颠覆传统,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推崇万物背后都存在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一个支配性的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非平等并置的二元对立思维,即通过设立第一项的优先性而迫使第二项从属于它。因此,在传统权威的绝对话语权中,第一项是首位、中心的,第二项是次要、边缘的。而德里达的批判正是意于打破中心,消弭权威,通过颠倒、重构各种既有语汇之间的关系,促使原本等级对立的压制发生倒转,从而瓦解绝对中心的存在,模糊中心与边缘的地界。舞蹈剧场《May B》正是通过对传统叙事结构的颠倒与重组,对精英话语权的叛逆与挑战,公然放弃对中心、主体的绝对坚守,推翻了西方传统哲学所秉持的中心论与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
(一)重构传统叙事结构
德里达对西方传统哲学的解构,并非意味着赋予边缘性事物以重要位置而引向某个新的中心,而是从文本中抽取一个边缘性片段或是某个异质性成分,将它们置于整个文本的重要位置上,从而颠覆原先的等级秩序,向传统的中心论发起挑战。舞蹈剧场《May B》正是一反传统舞剧的主角叙事和线性叙事,抽离主角人物的领导存在,以10个互相平等、形态各异的舞者构成,并以“倒置”手法重构作品的发生,形成了叙事结构上的破而再立。
一方面,《May B》背离了传统舞蹈的主角叙事模式。在传统舞蹈叙事中,主要人物是中心焦点,次要人物和背景人物往往都是为烘托主要人物的饱满形象而存在的。而作品《May B》抽离了主次人物之分,10位舞者的地位互相平等,既是拥有共性的群体,也是形态各异的个体。当他们身着宽松质地的米白色衣服,浑身沾满灰白黏土的时候,这是一群抽离个性的群体。而当他们换上有色彩、有生气的日常服装时,这是一个个互相独立的具象个体,没有主次、高低、贵贱之分,虽然每个人物都拥有了自己专属的立场,或其乐融融地吃着蛋糕,或抓头发、掐脖子打架等,但他们之间都是互相平等的存在,没有谁是主宰,也没有谁是附庸。《May B》便是于10个既可模糊为集体,也可各自为自己人生主角的人物变换中,通过碎片、拼贴、重复的手法,编织起的极富戏剧意味的叙事模式。
另一方面,《May B》推翻了传统舞蹈的线性叙事结构。传统叙事性舞蹈通常采用“十字方针”编排,即按照引子、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脉络编织。而作品《May B》虽基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编创,却没有忠实依据文本自身的发展脉络进行,而是以“倒置”的视野组织叙事结构。在作品开始部分,舞者们簇拥成紧凑的队形,拖着急促的步伐,时而面向台口,时而又迈向上场口,不断地骤然转向,整齐划一却又单一重复,最后他们终于念出了“结束了,要结束了,可能要结束了。”这句台词将文学《等待戈多》的核心立意间接道明,因此它也应成为舞蹈编排的高潮基点。但该作品却一反传统的处理手法,将本需处处铺垫的高潮点直接倒置于开头部分,虽有开宗明义的效果,却也颠倒了原本的叙事脉络,衍生出更为戏谑的意味。此外,该句台词在作品的结尾处又再次出现,不同的是,这次只有一位手提箱子的男性,在像木偶般机械运动和四处张望后,缓缓道出法语台词。至此,全作终。《May B》正是在“倒置”与首尾呼应的叙事手法中,营造出了开篇即终局的深层意味。
(二)打破精英主义话语权
话语权作为一种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一定程度上掌控着社会意识形态。传统话语权往往是指在社会潮流中占有主导地位、权威影响的控制权,是等级秩序的直接体现。而德里达所推崇的解構主义正是反对强暴的等级制,旨在深度瓦解传统的权威话语权。舞蹈剧场《May B》正是以“逆向审美”和“小人物”为标签,挑战了舞蹈审美的主流趋向,打破了精英主义话语权。
一方面,作品《May B》对“舞蹈必须是美的”这一传统审美定式发出挑战,以直白的肢体动作、形态各异的身材形成直观的视觉冲击力,从而抛出灵魂深问:衰老或者不美好的身体就不配舞蹈吗?人们往往将舞蹈与惊险奇谑的技巧和细腻传神的表现力相联系,传统舞蹈审美更是要求舞者需具备独特的身体条件和出众外表,“三长一小”早已成为各专业院校和歌舞团挑选舞蹈人才的首要条件。而《May B》却打破了传统舞蹈对“美”的狭隘定义,10位舞者形态各异,高矮胖瘦,年长年少,没有挺拔、纤瘦的身材,也没有紧实、完美的肌肉,每一位舞者的形态都贴合普通人群最为真实的样态,与传统舞者大相径庭。玛姬·玛莲也曾表明,舞蹈的“唯美主义”要求舞者必须年轻漂亮,但不年轻或胖的人群就应该被关在舞蹈艺术的门外吗?因此,《May B》将舞者选择扩大至边缘化群体,无论高矮胖瘦均能在舞台上演绎,并非只有身形纤长才为唯美,存在即合理,每个人都可以舞蹈,在舞蹈中的每个人都是美的。
另一方面,当下社会的话语权往往掌握于上层的精英分子中,塑造英雄人物便成为主流艺术作品的发展趋向,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真实、普遍的人性。而作品《May B》打破了精英主义话语权,聚焦于刻画社会生活中的普通人物。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社会中最为普通、真实的人,他们模糊了各自的身份、年龄和职业,在舞台上抓耳挠腮,或集体过生日,或提箱匆匆前行等,有焦虑疑惑,也有丧失自主意识的,似乎在无目的地追寻等待着什么。这正映射着当下每一个普通的“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有节奏、无目的地忙碌奔走,认真生活却又茫然不知,有疑惑,也有焦虑,在无尽的追求中总好像在等待着什么。《May B》没有崇尚英雄主义,而是以“草根”视野发掘普通人一生的真实样态,经历着生活中乏味无聊的日常,忍受着潜在的欺凌与冷眼,一生都在无尽追逐着,也在苦苦等待着。因此,该作品瓦解了既有的精英话语权,打破了“舞蹈必然是美的”狭隘界定,用肢体展现了故事中的小人物,展现了真实生活中的每一个“我们”。
二、符号自由化指涉
能指和所指是结构语言学中的一对范畴,其中能指是指单词本身的词型或词音,所指则代表着单词表示的对象或意义。德里达以瓦解二级对立的等级秩序为出发点,认为能指并非比所指低级,能指的意义也非由所指赋予;能指单靠与其他同类能指的指涉便可以产生意义,从而产生由A及B、B及C、C及D这样一条无尽的能指链。因此,德里达主张能指自由,文本便成了“闪烁的能指群星”,意义便在能指和能指间的不断滑行中通过差异运动产生而出,衍生出多元意味。舞蹈剧场《May B》正是在对符号元素的能指处理中,通过怪诞化、延异化手法,消弭了传统“在场”赋予“不在场”固定意义的模式,让符号成为有意味的载体,为文本主题的多元性、散发性和不确定性埋下铺垫。
(一)符号元素怪诞化处理
怪诞化手法追求与和谐相反的美学效果,追求对等级制文本的解构和对传统权威的挑战。舞蹈剧场《May B》不拘泥于传统舞者配备的服化道具、所编排的肢体语汇,而是将它们怪诞化、夸张化处理,以猎奇的视觉效果解放观众对符号文本的固有理解,将能指自由真正释放而出。一方面,舞者们在外形上宛若一群“怪人”,他们穿着宽松、褶皱、沾满污渍的米白色衣服,浑身涂满凹凸不平的泛白黏土;惨白、诡异若丧尸般的妆容上,还顶着被夸张放大的鼻梁;泥泞的头发根根分明,与他们斑驳的皮肤互相映衬着。怪诞化的服化元素赋予了观众独特的视觉冲击,同时也为他们带来更为深刻的寓意启迪。
另一方面,《May B》对动作语汇进行夸张化、怪诞化的处理。它将日常生活中被遮掩的现实进行放大和变形,让它们光明正大地、直观激烈地呈现于舞台上,以异质化的视觉冲击来激发符号本身蕴藉的意义。如因争权夺势而产生的打架片段,互相抓头发、掐脖子、瞪眼示威等生活化动作不断呈现于舞台上,将日常中避讳的事夸张化和艺术化,让观者在符号传递的震撼之余不断直面心理,叩问灵魂。此外,作品中也融合了大量非传统舞台呈现的肢体动作。在作品伊始部分,舞者们不断用脚反复擦地板发出的“唰唰”声,不断从胸腔中挤出的呻吟声、呕吐声和狂笑声,以及第二段因争夺蛋糕而直接将其藏进衣服,徒手狂咽蛋糕,机械啃胡萝卜等等。这些视觉符号与听觉元素,在日常生活中均被视为背离“可舞性”,却被该作品直接搬上舞台,形成了怪诞化效果,并凭借符号本身播散出多元的理解意味。
(二)符号元素的“延异”运动
当一个概念需要区分与其他概念的不同时,其必须通过指涉他者来解释,而被指涉的所指又需引入另一批能指来进一步阐释,因此便构成了能指疯狂的、无止境的指涉运动。德里达将这种无尽的能指链称为“延异”,它既具有共时性层面上的差异区别,又具有历时性层面上的延宕,兼具空间与时间维度,与传统意义上的差异截然不同。因此,“延异”体现出一种对存在者的合理性,所有的在者都可以由差异来确定,同时这种差异又是无限性的,而非“在场”与“不在场”所形成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
舞蹈剧场《May B》打破了结构主义推崇的“不在场”通过“在场”留下印迹的观点。在作品的第一段,舞者们身着带有褶子与大团污渍的米白色衣服,类似于血迹的污渍凝结于泛白的衣服上,根根分明的头发仿佛正经受着泥泞的拍打,面容则若丧尸般惨白、惊悚。如若以“在场”与“不在场”的二元对立思维切入,辅以《等待戈多》的前文本设定,观众很容易跳入思维桎梏,通过血渍、妆容等服化元素,以及潦倒的神态等“在场”印迹,单一地界定:这是一群苟活于战争时代下的侥幸者。因此,观众的观演体悟与解读也往往会受限于此,思维无法发散。但作品《May B》并非意如此,它虽然呈现了仿若历经战争年代的人们,却没有赋予他们明晰的身份界定,唯一能明确的:他们是一群真实存在于社会中的人类。而其他所指都是开放的,需要观众凭借自己的即时感受与既有经验,对捕捉到的每一个能指进行自我理解,环环相扣,从而在不断延异的能指中品藉出无限运动的意义。因此,正如德里达提出的“延异是差异和差异之踪迹的系统游戏”,意义在延异中生成,差异的无限性便为文本主题的多元解读带来了可能性。
三、文本多元化解读
德里达认为每一个意义的产生都是延异的结果。一个能指所指向的所指,其实是由无数个与它有差异的其他能指不断“补替”构成的,而这些不断的“补替”使得语言符号本就对应的所指无法追溯,意义发生了延宕变化,从而形成了漫无边际的“播散”状态。“播撒”意味着意义不能被明确界定,任何事物都没有先验的主题和结构,文本内部意义的组合方式是多样、无穷的。因此,在解构主义视域下,由于文本的本质无法追寻,每一次对原文的理解都不能完整穷尽其本身的意义,继而形成了对原文的再次重构,让意义无限播散,使得文本主题因不同的解读而衍生出多元意义。
舞蹈剧场《May B》以荒诞派文学经典《等待戈多》为创作灵感,塑造了一群身份定位模糊的人们,泥泞、褴褛与落魄的服化元素,空洞、宣泄与孤独的神情样态,以及挠痒、疾走、打架、吃东西等片段,这些细碎又重复的符号元素,看似各自明晰地呈现而出,却被抽离了符号生发的先验结构,从而让能指不断延异,文本主题的意义不断播撒。每一位观者都可以依据既有的生命经验与现时的心灵触动,通过作品形塑出的符号能指,品藉出独一无二的深层意蕴。基于此,《May B》既可以是单纯地意于打破舞蹈与生活的边界,也可以是表达了战后幸存者的生活样态,还可以是对普通人一生所历经的苦难破碎后收获的小确幸的浓缩映照,甚至可以是对社会现象的深度反思,对生命意义的探求与思索。编导玛姬·玛莲并没有限定作品的主題立意,每一种文本意义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文艺作品的魅力正因意义的播散而绽放异彩。
作品《May B》可以划分成三个片段,即抽离个性的集体呐喊与宣泄本能片段、恢复日常生活的雀跃与恐惧片段以及不断游走的旅途与孤单片段。在第一段中,个性模糊的人们永远呈现着群体般的簇拥状态,整齐划一的动作,时而用脚用力擦地,时而面向各个方位发出呕吐声与狂笑声,似乎想申诉着、反驳着什么。此时,这群人体现的是集体共性,他们既可以是战争结束后的幸存者,也可以是社会生活中被抛弃的底层人民,还可以是每一个正在观看的“我们”所投射的镜像。而当人们开始拥抱和狂欢的时候,既能被理解成是人一生中对两性好奇的探索阶段,又能被解读成是对人性原始欲望的暴露与呈现。第二段,舞台上的人们穿上了各自相异的日常服装,代表着个体意识的回归。他们时而聚在一起过生日、吃蛋糕,以短暂的相聚促进情感的升温;时而又争权夺势、互相干架,呈现出最为原初的欲望与冷漠。其中,以生日蜡烛被吹灭为转折点,原本温馨的氛围骤然冷却,出现了大家因争抢蛋糕而引发的打架片段,此时的蛋糕既可以是物体符号本身,也可以是隐喻的权利、钱财等欲望。该片段既可以表达个人由懵懂无知的青葱样态不断经由社会的磨炼而成长;也可以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映射,是短暂幸福背后回归的破碎生活,也是戴着面具惺惺相惜的社会人群。第三段,舞者们开始以木偶般的步调不断行走奔波,一摇一摆,一颠一跛,或提着箱子、公文包,或啃着胡萝卜、苹果,机械单调地、周而复始地从下场门走至上场门。有时,某个人会脱离队伍,或是试图挣脱却失败地回归群体,或是被迫丢下却无人寻他。不断行走的群体仿若是某种无法逃脱的隐形力量,它操控着人们不断行走着,探寻着又等待着,人们丧失了个体自主意识却不自知。而这“隐形力量”与社会俗成的观念是多么相像,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都是其所身处的时代社会塑造的,无论追求自由与否、独立与否,都会经受社会时代的限制。而人们往往并不自知,一本正经地认真生活,随大流而奔波忙碌,一生都在追逐,一生都在等待,可到底追逐的是什么,等待的又是什么?只是因为“需要”从众。或许追逐的目标、等待的成果本身并不重要,真正产生意义的是等待过程中所历经的欢愉、苦痛、疯狂和释然。作品《May B》呈现的正是等待过程中的种种趣事,拥抱、欢聚、内讧、和解等。等待是我们不断追逐的期盼与动力,而体味等待过程中的趣事才是最终的意义所在,而这也是一次主题文本的意义播散。
解构主义是一种开放的阐释方式,它打破了文本原先单一、封闭、固有的状态,让文本的内在差异和意义不断展示,主张主题立意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正如舞蹈剧场《May B》所诉说的千姿百态的人类和辗转流年的生命,它没有限定观众解读的途径,也没有以编导的立意为绝对中心,而是让每一位观者通过作品去认识、去了解、去揣摩最为真实的“自己”,只有最真實的体验和感悟,才是作品《May B》真正想播散的意义。
四、结语
德里达作为解构主义的始创者,他瓦解了优先等级的统治支配权力,消除绝对中心的存在,并提出了无尽的能指链“延异”,在差异的无限性中形成意义的“播撒”状态,使文本主题具有多元解读性。在解构主义视域下的舞蹈剧场《May B》,既通过消除主次要人物的设定,以10位无身份界定的舞者“倒置”叙述打破了传统叙事手法,又以“逆向审美”为基点,向传统的权威话语权发出挑战。此外,作品抽离了文本发生的先验主题,通过符号能指的不断延异、补替,衍生出文本主题的多元意义,以开放性的结构、怪诞化的符号和疯狂化的能指,让观众既可以基于《等待戈多》文本的前理解,也可以结合个体的既有经历与现时感悟,通过符号元素的视觉捕捉与心灵触动,真正意义上与作品《May B》产生思想碰撞,情感共鸣,而这恰恰就是解构主义批评所独具的魅力与绵远意蕴。
参考文献:
[1]杨冬.德里达的启示——解构理论与文学批评[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5):17-21.
[2]杨晔.“延异”的应用:读过与未读过之后的批评[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02):101-103.
[3]朱秋兰,曾贤模.电影《无问西东》的解构主义分析[J].汉字文化,2020(24):136-137+145.
[4]吴珂璐.解构主义批评视角下的《变相怪杰》的解读[J].校园英语,2017(23):24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