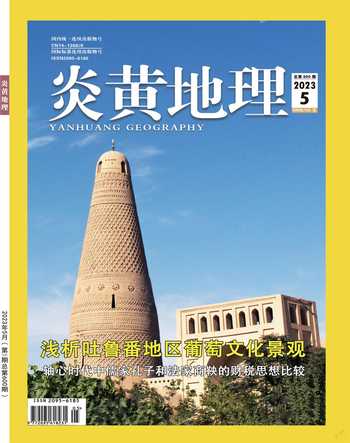苏州塘浦圩田探
2023-06-21李淑伟
李淑伟
太湖流域地势低洼,湖泊众多,河网密布,所以治水是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位于太湖流域东北部的苏州尤为倚重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的快速发展对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苏州水田以塘浦为界,横塘纵浦,筑圩围田。大约五代吴越时期,苏州塘浦圩田遍及东部水网平原,呈现“高无旱、低无涝”的农田水利格局。塘浦圩田作为中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典范,体现了先民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独特智慧,亟待进一步探讨与深思。苏州塘浦圩田历史沿革的梳理及其建设环境、管理制度的考察,有益于探索苏州地区水利社会的发展全貌,也对研究太湖水利史有积极意义。
北宋郏亶曾言:“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过于苏州。”[1]塘浦圩田是苏州水田的独特代表,其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独特智慧,成为中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典范。探求苏州塘浦圩田的历史,应突破单一的工程性理解局限,将其置于苏州的社会发展格局中,将其视作苏州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一。
苏州的水利环境
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时期,太湖逐渐成形,太湖平原初具形态,人类在环太湖一带定居和生活。太湖平原是典型的水网平原,以太湖湖盆为中心形成碟形洼地,西北和东北部略高,中部稍低,水网稠密,湖荡棋布。太湖流域以太湖为中心,分上游水系和下游水系。境内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望虞河等连接东西,太湖等镶嵌其间,将苏州河网分割为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的新沙、虞西、阳澄、淀泖、滨湖、浦南六个水网片区。
苏州拥有“一江、百湖、万河”的水系格局,共有河湖24643条(座),河道总长21638公里。“一江”为长江;“百湖”包括省级以上管理湖泊——太湖、鹅真荡等3个市际湖泊、阳澄湖等45个苏州市湖泊、巴城湖等22个湖泊属阳澄区湖泊群、陈墓荡等193个湖泊属淀泖区湖泊群、大龙港等137个湖泊属浦南区湖泊群;“万河”包括望虞河等4条流域性骨干河道、七浦塘等17条区域性骨干河道、东横河等9条跨县重要河道、一干河等52条县域重要河道,以及2万多条镇村级河道。
《尚书·禹贡》中有记载云“三江既入,震泽底定”[2]。“太湖三江”即娄江、吴淞江和东江,太湖水径由此三江泄入大海,故地位特殊。其中,吴淞江是沟通湖海的主要通道,有着“吴淞古江,故道深广,可敌千浦”的说法[3]。但由于泥沙淤积,三江壅塞严重,唐宋以后,东江、娄江先后湮废,太湖泄水仅靠束狭且有淤患的吴淞江,渠道不畅,水涝频繁。因此,太湖治理长期以吴淞江为中心,力求在解決太湖泄水的同时,实现治水与治田的结合。
苏州地区因灌溉和水运所需,不断开浚河道。春秋战国时期,吴地在自然河道基础上,以“通渠三江五湖”[4],实现了与外界的广泛沟通。胥浦等河道的开浚,为苏州水网奠定了重要基础。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水道开浚技术与农田水利工程相结合,苏州地区涌现出了众多农田水利工程,塘浦圩田逐渐兴盛。中唐以后,随着河道、塘浦的疏浚和修建,河、浦等交叉错杂的水系网络逐渐形成,塘浦圩田系统日渐成熟。但因高乡易旱,低乡易涝,高岗田的灌溉须开辟塘浦,深挖河道,从而引水灌溉;而低洼地与水争田,须筑岸围圩,以防洪水入侵。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苏州地区的人们深浚塘浦,高筑堤岸,筑圩围田,最终实现治水与治田的结合。
塘浦圩田的历史沿革
关于塘浦圩田的发展轨迹可以参考水田遗迹和《越绝书》等古籍。
新石器时期是苏州水田的发端期。于苏州草鞋山遗址发掘的水田遗迹,印证了苏州水田灌溉工程萌芽的产生。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水田遗址反映了农田水利的早期形态,田块之间有水井(坑)、沟洫等原始的农田水利灌溉设施。
春秋时期苏州围田成片出现。吴国在固城(今江苏高淳)筑圩为田,据《高淳县志》载:“吴筑固城为濑渚邑,因筑圩附于城,为吴之沃土。”此期,吴地围垦种植水稻,出现了大片农田。《越绝书》记:“地门外塘波洋中世子塘者,故曰王世子造以为田。”反映了当时有筑塘造田的迹象。“吴北野禺栎东所舍大疁者,吴王田也……吴西野鹿陂者,吴王田也。今分为耦渎、胥卑虚……吴北野胥主疁者,吴王女胥主田也。”其中以“虚”“疁”“陂”等命名的田段都反映了筑堤围田的迹象。
秦汉时期苏州圩田进一步发展。《越绝书》载:“立无锡塘……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大规模的治水围田,拓展了围田范围,又以筑堤、围圩、建闸完善了水利设施。至此,塘浦圩田进入滥觞期,据《越绝书》云:“摇城者,吴王子居焉,后越摇王居之。稻田三百顷,在邑东南,肥饶,水绝。”[5]汉代,吴地水田继续发展,据《吴都赋》记载:“屯营栉比,廨署棋布”“其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6]
魏晋南北朝时期,“塘浦圩田”形式初显。六朝时期,常熟地区大兴农田开发,改海虞县为常熟县,据《常昭合志稿》言:“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以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7]《宋史》载:“昔人于常熟之北开二十四浦,疏而导之江,又于昆山之东开一十二浦,分而纳之海。”[8]常熟、昆山一带,通过开浚塘浦,引水灌溉,筑圩挡水,保障圩田水利,实现旱涝保收。
唐代塘浦圩田进入系统化时期。唐代苏州地区修浚常熟塘等水路,建构了比较完善的水利体系,兼之海塘、湖堤及众多塘浦、泾河的开挖,奠定了塘浦圩田系统的基础。又因屯田发展,中唐以后形成规整的塘浦圩田系统,并引入大圩制。据当时官府要求,新开屯田每屯五十顷,一屯即一大圩,约一两万亩。唐贞元十二年(796),崔翰掌吴郡军屯,“凿浍沟,斩茭茅,为陆田千二百顷,水田五百顷,连岁大穰,军食以饶”[9]。塘浦圩田的建设,助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如韩愈言:“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五代吴越时期,塘浦圩田得以巩固发展。政府设都水营田司,置撩浅军,实现了治水与治田的结合。苏州境内有塘浦二百六十余条(座),在南北一百二十余里、东西一百里的区域内,形成了“五里一横塘、七里一纵浦”的格局。东太湖地区、吴江塘路、至和塘、元和塘、吴淞江一带,集中了大面积塘浦阔深、堤岸高厚的圩田,这些田块形状规整,规模巨大,被称为“大圩旧制”。
宋代,塘浦圩田系统积弊渐深。两宋时期,塘浦圩田虽继续发展,但由于长期水旱灾害,水利失修,塘浦河道阻塞淤废,圩岸渐趋毁坏。堰闸败坏,水溢农田,积水为灾,又因盲目围垦,泾浜不断分化,水系遭到破坏。至北宋,“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废”。塘浦间位位相承的圩田旧制不复存在,大圩逐渐被分割为小圩,泾浜小圩兴起,“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
元明清时期,“大圩毁坏,小圩发展”现象频出。两宋以后,水利问题恶化。塘浦愈修愈乱,河道常治常淤,终致塘浦系统崩坏。大圩体制遭到系统性破坏,逐渐分化为小圩。明代有治水官员提倡小圩形制,强调其益处,如工部主事姚文灏曾作《修圩歌》:“教尔分小圩,圩小水易除,废田苦不多,救得千家禾。”明万历年间,常熟知县耿橘设想联圩并圩,提出“联并小圩,分级排水”等治圩措施,但未能推广。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塘浦圩田提出了“复堤修圩、联圩并圩”的修复措施。新中国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开展了以复堤修圩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建设,河网圩田系统得以恢复和发展。一些地方还将联圩并圩作为圩区水利建设的重点,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圩工作,推动了当地农业发展。
塘浦圩田的管理制度
塘浦圩田发展的另一脉络,可见相关史籍中有关圩田管理制度的记述。水利管理是水利工程建设的基本保障。相传大禹受舜之命,为司空治水。随后,逐渐建立起了水利管理体制。秦汉时期,设都水长、丞,掌理国家水政,地方行政长官兼管水利。隋唐时期,设有水部,隶属工部,下设都水台、都水监等机构。唐代中期,形成了中央水官和地方水官条块清晰的水利管理体系。同时,针对圩田也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
圩田管理包括圩岸、塘浦、堤闸等农田水利设施的维修、养护和日常管理。太湖地域的圩田管理历来备受重视。五代之前已设圩长一职,负责修筑堤防、浚治浦港,如郏亶言:“田各成圩,圩必有长,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筑堤防,浚治浦港。故低田之堤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至五代吴越时期,《琴川志》记:“钱氏有国时,创开江营,置都水使者,以主水事。募卒为都,号曰擦浅。”吴越王钱镠为加强水利和农田管理,设“都水营田司”,专事兴修水利,创“撩浅军”,专事农田水利。范仲淹亦云:“曩时两浙未归朝廷,苏州有营田军四都,共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
宋元以后,圩长制度常态化。在大圩制向小圩制演变的转型期,江南地区设置水利的专职管理机构,敦促了苏州地区水利机构的不断完善。宋代圩田有官、私之分,官圩设“圩吏”,私圩设“圩长”,规模较大的官圩由国家直接派使臣管理,“陂塘”设有陂头(或陂正)、陂副,“堰”则设“堰首”,甲头、小工和水手不等。所谓“田各成圩,圩必有长”,依圩田大小,多数只设一人,大者设两人,“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筑堤防,凌治浦港”。圩长以分工出夫之法,率领农民浚河、取泥、做岸,在圩岸种植桑柳。
明代,塘长、圩甲制度正式设立。明初设置塘长制,据万历《青浦县志》:“国初……以里长、老人主一里之事;以粮长督一区之赋,而粮长之中有收有解;以塘长修疏河道,而塘长之中有总塘长,有塘长,制甚设也。”康熙《嘉定县志》载:“明初,塘长每扇止点丁粮多者一二人,后改每里一人。”塘长负责修疏河道、管理农田水利,按里甲编制,以区为单位设置,区以下有图(里),设“该年(圩长)”。圩户管修一段圩岸,圩长管修一圩圩岸,塘长管修一区圩岸,并向府县官员负责。塘长、圩长还负责日常巡察圩岸安全,“塘长圩长,沿堤分岸,纠察巡警。岸之漏者塞,疏者实,冲者捍,坍者缮,低者崇,隘者培”。管理的逐层细化和各级政府统管的实行,建构了完整的水利管理体系。“一圩沟岸,任在排年,一图沟岸,任在里长,此法之经也;百夫河港,任在老人,千夫河港,任在粮长,此法之纬也;一县水利,任在县佐,一府水利,任在府佐。”在政府领导下,建立了上至府县官员下至排年、里长的管理体系,自上而下,层层负责。
政府也颁行了圩田兴修的惩处办法:“有设圩甲以齐作止。其曰:兴工之日,塘长责令圩甲,躬行倡率,某日起工,某日完工,庶几有所统领,而无泛散不齐之弊。中有业户不听倡率,听其开名呈治。如圩甲不行正身充当,或至别行代顶,查出枷号示众。”未完成还有追责,“一圩不完,责在圩甲;一区不完,责在塘长。轻则惩戒,重则惩治……如一县中有十处不完,责在县官;一府有二十处不完,则官又有不得不任其咎矣”。
圩长在日常管理圩内之余,还涉及提督农务、催办税粮及田制管理等事务。《崔鸣吾纪事》记:“当每圩立一圩长,通计圩内田片若干,每片实田若干,某户田若干,庶便稽查,可无隐漏。”明宣德年间,苏州所辖各县均设有总圩长和圩老,全府圩长逾一千六百名。圩长深入基层,时有不作为及徇私舞弊,或有横行地方者。为革除此弊,苏州知府况钟发布《通禁苏民积榜示》《革除圩长示》,遏制圩长的权限。
清代,圩长制度迎来转型。明末清初,圩成为最终的划分单元,政府官署、民间杂居、官田民地都纳入了圩制的范围。圩长责任更为重大,职权更为广泛,对乡间民户的劳动力,圩长都要“酌量工力难易分别均派”,对地方财赋等诸项事宜,圩长也都负有相当的管理职责。政府对地方的各种杂役、摊收,往往直接由圩长牵头介入。清代水利建设主要靠地方官或士绅倡导,引领百姓自行修复。地方农田水利大多以按亩摊派、业食佃力的方法组织实施。圩长领头浚河修圩,自然能得到响应。“今当坐图开浚,令圩长作坝,坊长唤夫,业主给食,佃农出力。则土人休戚相关,自然踊跃从事。”同时,地方宗族亦参与水利建设和管理,除了自身的族田以外,对公田圩岸修葺等也有重要贡献。
苏州居于太湖平原碟形低洼区的中心,水网密布,河流纵横。春秋战國时期,吴国始筑圩为田,至唐代吴越时期,塘浦圩田渐趋体系化,呈现出理想的“大圩旧制”。而宋代以后,圩区失修,塘浦圩田系统紊乱,大圩毁坏,小圩发展。范仲淹提出“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并重” 的治水方略,旨在治水与治田相结合。应运而生的塘浦圩田,在实践中解决了蓄水与泄水、挡潮与排涝、治水与治田的矛盾,为太湖流域治水治田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照。
水利管理是水利工程建设的基本保障,唐代中期就已出现“中央—地方”条块清晰的水利管理体系。在苏州治水体系日渐成熟的基础上,圩田也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使得横塘纵浦井然有序,灌溉排涝自成体系,呈现“高无旱、低无涝”的农田水利格局。如吴尔成言:“吴中之财赋甲天下,而财赋之源在农田,农田之源在水利。”考察塘浦圩田建设发展史,有益于进一步理解苏州水利的经济文化格局,对于深化太湖地区水利史的认识也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范成大.吴郡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2]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袁康.录越绝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光绪.常昭合志稿[M].刻本.出版地不详:出版社不详,1904(光绪三十年).
[6]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韩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8]韩愈.韩昌黎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9]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李勇先,刘琳,王蓉贵,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