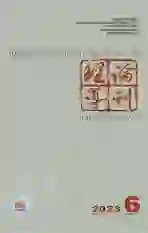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审美异化及批判
2023-06-19穆佳滢
摘 要:在图像丰富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们不再满足于“按图索骥”的文本信息,更倾向于追求活灵活现的图像美学。于是,“审美要素”成为资本牟利的一大动力。资本所有者既利用数字技术疯狂进行审美的大批量生产,形构审美商品,又在消费领域疯狂获取超额利润。在数字技术与图像资本的共同作用下,审美溢出固有的自律性边界,脱离蕴含着人性自由与理性复归的崇高意旨,沦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工具,遁入审美异化的困境。这就需要重思审美与技术的关系,实现审美对技术的超越,助力高雅艺术与大众审美的交织汇融,以重现美之“光晕”,使审美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重释“令人解放”之意蕴。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审美异化;赛博空間;数字技术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3)06-0060-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建党百年革命精神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21JDSZ3209);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百年奋斗经验及时代价值研究”(CYB22148);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关于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生专项课题重点项目“马克思需要理论与新时代人民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研究”。
作者简介:穆佳滢(1996—),女,河北邢台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与社会思潮。
一直以来,信息技术被视为推动时代进步的重要工具。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异军突起与广泛应用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渗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席勒笔下的“数字资本主义”①之样态得到了更为全景化和具体化的呈现。人们不仅对数字化发展抱有希望,更是寄希望于数字信息技术能够创设更加光明、自由、和平、正义的未来。正如比尔·盖茨所言,整个世界都可以“沐浴”在网络信息技术的包围中,构建“没有摩擦的资本主义世界”。但需要注意的是,数字技术在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亦造成了人们灵魂的空洞化与疏离化。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感知”幻化为存在,“虚体空间”侵占了“实体世界”,人从重“物”的时代,踏入“体验”的时代、“审美”的时代,“审美”成为一种拥有“巨大潜能的生产要素”,“审美商品”日愈显现。正如豪格所言:“美学革新向全世界抛出可以使用的东西,人们的需求在这些可以购买的物品中得以清楚地表达,这中间也包含着永不停歇的美学上的变化。美学革新承担着需求再生的功能,它简直成了影响人类的力量和机构。”[1]43相较于一般商品,审美商品更侧重于商品审美价值的呈现,即通过外部美化或内部赋值,展现出商品的个性化和特殊性,进而传达出更丰富、更灵动的生命力,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心理效应,唤起人们对审美商品的极大兴趣和热情。从表层来看,审美商品的生产与传播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正常进化需求;从更深层而言,审美商品的生产在资本牟利本性及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愈发偏离审美“令人解放”②的崇高意蕴,在向对立面转化的过程中,不断背离审美原则与价值准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审美异化之困境。为此,本文尝试通过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审美转向及异化原因的分析,审视其引发的诸多异化表征,为“可复制与可普及的‘审美,到底是人性的希望,还是人性的囹圄”[2]提供新的理论参考。
一、审美的“坠落”: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审美转向及异化原因
在传统美学视域下,美与艺术被限定在上层建筑领域,与资本互相抵牾,以崇高姿态与熟稔的日常生活保持安全距离、维持审美自律。“审美自律”与“审美无利害”作为传统美学中的核心概念,最早可追溯到斯托尔尼兹的《“审美无利害性”的起源》一文,主要针对的是当时泛滥于伦理学上的“利己主义”。后经由哈奇生、博克、艾利生、休谟等人的延伸发展,最终在康德处被擢升为一个经典概念。在康德看来,“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3]45,“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3]46。也就是说,人们在鉴美、赏美过程中所获得的愉悦感是无利害的,无关任何欲望与现实利益。审美活动以其摒弃个人化的特征,被视为一种无实用性目的的超验化的活动,旨在帮助人们从艺术品的“可见性”中洞见具有超越性的“不可见之美”,唤醒并激发感性幸福,将人与人性提升到可能的精神高度,通达更高层级的美与和谐之域[4],直抵自由王国。
需要注意的是,审美活动虽然是一种旨在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主体性活动,但其就本质来说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必然或多或少地介入日常生活。“审美无利害”等理论上的不自洽为审美与日常生活之暧昧互融提供了时空间隙和可能性。当然,审美与日常生活之互相渗透是一个递进过程,具体从诸多学者的研究中可见一斑。20世纪,德国思想家本雅明犀利洞见游走于“拱廊街”上的“闲逛者”,并将其视为迷醉于美轮美奂的商品橱窗前的资本增殖之工具。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德波视消费社会为虚拟的“景观社会”,人们于“景观”中驻足、鉴赏,可视化的景观图像取代抽象的政治意识,生活俨然成为“景观的庞大堆积”③。20世纪末,法国学者阿苏利指出审美已然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经久不衰”的重要动力,人们借审美品位这一形式,“以一种和平方式巩固自己的权利”[5]。可以说,在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鼓噪下,审美领域几乎发生了一场“哥白尼式”④的革命,审美的崇高追求跌落为取悦感官的短暂享受,审美热情“拥抱”了它曾“不屑一顾”的日常生活本身,与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贴合,“现实本身已经完全为一种与自己的结构无法分离的审美所浸润,现实已经与它的影像混淆在一起了”[6]。
审美与日常生活的交融加速了审美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应用,“助力”了审美异化,即审美向“推崇自由与解放的崇高审美”的对立面转化,成为异己的或敌对的力量,最终实现对人的统治与规训。谈及“异化”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形式。马克思在对“异化”作系统总结时指出,“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的”[7]。这一逻辑的关键在于,在雇佣劳动制下,工人在劳动中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属于他自己,而归属于资本家。劳动成为外部的存在,变为资本的附庸,成为主宰和奴役工人的异己力量。也就是说,工人的劳动变为异化的劳动,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成为异化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自身的生命循环活动无法完成,亦离完整的人类的类本质越来越远,只能宛若蝼蚁般苟活于资本家的游戏中,眼睁睁看着自身的对象性力量被无情占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之异化,一部分人成为另一部分人的统治者和控制力量。在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过程中,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亦产生了较大影响。卢卡奇在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基础上,通过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愈被冷冰冰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充斥和代替,人在劳动中创造的物反过来制约了人。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物化并非具体的物,而是具有衡量尺度的抽象的物,抽象为关系的物凌驾于一切之上,成为统治一切关系的“主”。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并未停留于工人阶级的异化劳动上,规限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中,在他看来,“商品关系变为一种具有‘幽灵般的对象性的物,这不会停止在满足需要的各种对象向商品的转化上,它在人的整个意识上都留下了它的印记”[8]。物化的原则被延伸至整个社会,包括统治者和资本家在内的全部人,均笼罩在巨大的物化关系网下无处遁行。
迈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伴随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异军突起,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加速扩散,对人造成了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上的围困与规制。这主要表现为,资本所有者洞察受众对审美的感性需求,借助数字技术,在创设大量有益于资本增殖的审美内容的过程中,使得审美愈发背离蕴意自由与解放的本性,遁入审美异化之困境。具体来说,资本所有者依据以下两个逻辑实现了对受众公开的或隐蔽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统摄与宰制。
其一,资本所有者将资本与审美相挂钩,将受众“打造”为资本牟利的工具。“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本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9]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主要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管理经营等手段完成资本积累和财富积聚,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在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生产的大量过剩,即日愈丰富乃至过剩的商品远远大于消费者的实际购买能力。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经济危机频发,致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岌岌可危”。如此,在追求剩余价值及摆脱内部矛盾的双重驱动下,资本所有者不得不以更新的增殖手段、更广的增殖范围突破发展瓶颈。步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在数字媒体技术的全方位操盘下,人们不再满足于墨守成规、按图索骥的文本信息,转而更倾向于清晰明了、活灵活现的视觉图像,而对图像的关注本就蕴含着对审美及美感要素的观照和追求。资本所有者洞察到人性中对美的神往,深谙受众对“时尚机制”的追求,察觉到审美是可以不断更新、始终保持生命力的因子,于是将其视为具有“巨大潜能的生产要素”,纳入资本运作逻辑,形构商品美学,重塑自身持续发展的动力。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通过赋予商品美感之形式唤醒并激发受众的快感,诱使其在对商品美学的追求中完成对商品的消费,又以美的无形特征为契机,助推美感充盈于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日益占领人的闲暇时间与消费空间。总之,审美与资本相勾连,审美消费逐渐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人际交往形式,受众浸沉于资本创设的审美幻境中“肆意享受”,被“降格”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其二,资本所有者利用数字技术,将审美与技术相连结,对受众施以公开的或隐蔽的全景式操控。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在将审美这一因子纳入资本运作逻辑后,便以数字技术筑牢并强化受众对视觉审美的兴趣和依赖感。一是鲍德里亚在对消费社会进行剖析时指出,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了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10]。置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则演化为受到“美”的包围。资本凭借数字技术搭建大量审美场景,促使各种新奇、有趣、好玩的视觉产品一波又一波,全方位、全面化地充盈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促使受众在快速更迭的产品的裹挟和包围下,发现、关注并逐渐喜爱此类产品,完成审美的一般吸引。二是资本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引诱受众达成审美崇拜。这主要表现为资本通过智能技术占有和分析大数据,对受众进行“身体解剖”“数据侧写”、动机挖掘,以察觉受众对视觉产品的不同偏好,有针对性地、不间断地向受众推送相关产品和服务,积极进行情感生产,为受众构筑“伪语境”与“伪需求”,将人们对审美的依附程度最大化。三是在审美消费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人际交往方式和普遍范式后,资本所有者更是借助数字技术,不断赋予审美商品新鲜意蕴和价值内涵,将审美追求与审美水平视为衡量现代人阶级归属的重要尺度,即对某种审美形态和价值观的认同与否成为某一阶层的划分标准。这种无形的技术力量无疑加剧了人们对审美的追逐,助力审美资本的不断积累,以致完成资本逐利本性的终极建构。可以说,商品凭借“强大无边的技术面”[1]50具备了“有魅力”的外形,受众将对这种商品的占有等同于自我价值的实现,视审美商品为自我的“倒影”。
不得不说,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得以迅猛发展,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改善,彰显了科技力量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现代社会日渐被绚丽多彩、眼花缭乱的审美景观包围,受众的消费需求已然从日常生活领域延伸至更深层的精神领域,消费对象也从对实物的消费变为了对符号、价值的追求。也就是说,只要事物(商品)所体现、象征的审美形象和价值观符合受众欲求,哪怕这一事物并非受众的真实需要,依然可以完成对消费的诱导。消费俨然成为一种迎合“身份彰显”与“快乐餍足”的“快感享受”,低层次的、浅显化的审美快感碾压了事物认知本应具有的深度和广度,受众沉湎于被建构的“真实”、被虚饰的“繁荣”之中,“背离理性的审美判断”,逐渐丧失分析、判断的能力,从而令审美异化现象愈演愈烈,日渐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之全面自由发展的桎梏。
二、审美精神的失落: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审美异化之表现形式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对全球资源要素的重组、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在助推整个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创造空前丰富产品的同时,亦构建了一个低时延、高仿真、精量化的现实世界副本,颠覆了人们传统的生存方式,促使人们从“文字生存”转向了“数字化生存”。需要注意的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并未减少,其以算法的形式精准捕捉受众的审美偏好,架构起以数字界面为场域、以身体需要为变量、以视觉叙事为形式、以美学体验为目的的全新美感制式[11],以期在对审美的操控中完成资本增殖之需要。与之相应,审美异化也呈现出更为普泛化、更加根深蒂固的样态。
(一)数字技术操控下的审美生产背离意义生产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是信息、科技飞速发展,从而带动整个社会方方面面迅猛发展的时代,其不仅以数字技术的强大威力构筑了图符数字化的“视觉盛宴”,更刷新了以审美体验、审美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新生存模式和新消费模式。从审美生产者角度看,数字技术的勃兴为寄居于数字资本主義时代的每个个体发放了程序简单便捷、创作门槛低、创作风格不限的审美生产“入场券”,每个人可依据个人偏好、社会潮流等进行自由审美创作。从审美消费者角度看,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快速更迭的信息科技笼罩下的生存压力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逐渐产生不适感、孤独感和悬空感,日渐丧失对生活的热忱和对生命的敬畏,似乎只有坦然接受数字化浪潮的“拍打”才能为自身赢得喘息的空间。如此,具备一定的审美价值,贴合大众图像接受需求,碎片化、即时性、便捷性的视觉审美体验成为弥合其现实生活疲乏、劳累的“止痛剂”,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审美生产寻觅到大量潜在性的消费对象。
不同于“生产什么,就消费什么”的传统生产型社会,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具备“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的消费型社会特点。审美消费者对新奇、便捷、冲击感强的视觉审美体验的需求替代了传统视觉体验的“静观”模式,审美生产者亦紧扣并迎合这一趋势,利用数字媒体技术创设新的视觉审美体验。如“好看即‘正义”的宣称及短视频中身体的狂欢与消费。这里的“好看”并非单指“审美”,也包括“审丑”,美丑在这里并不是划分“好看”与否的标准,具备吸引力、能够使受众产生强烈视觉快感的便可称为“好看”。再从身体狂欢与消费角度来说,无论是穿着打扮光鲜亮丽的俊男靓女,还是日常生活中简单的吃饭、睡觉,抑或是充满戏谑与怪诞的拌嘴打趣日常,审美生产者以身体的“在场”建构了新奇的视觉体验。受众在这种身体的狂欢与消费中,不仅获得了具有震撼力的视觉快感,更满足了自身的窥视欲与自恋情结。同时,点赞、评论、私信等功能也为受众实现即时互动,将自身视觉快感与满足最大化提供了可能性。然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审美奇观的缔造仅仅是在满足资本逐利贪欲前提下对受众窥探欲望与猎奇心理的迎合,是停留于表层化、浅显化、直接化的视觉餍足,文学性与艺术性在这种浅层次的审美奇观中遭遇极大的弱化,更无法提供深层的、沉浸式的审美体验。审美生产脱离了铸魂育人、启智润心的崇高功效,离“摆脱物质压迫和道德的强制,使人获得彻底的自由”[12]的深度意蕴愈来愈远。
(二)数字技术营设“虚假的需要”,削弱人的真实审美需求
德国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在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审视时,洞察到现代社会日愈显现的“加速”特征,提出了“加速社会”⑤的概念。资本的加速运动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加持下已然进入“超加速”模式,整个社会的各大行业均卷入了史无前例的高速运转中。资本主义在加速运动中占领先机的现实欲求与追逐资本增殖的本性需要促使其不断对产品进行更新换代。同时,在人人都可以成为审美生产者与创作者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审美活动日渐演化为纯粹批量化的、漫不经心的抽象性活动。为保证审美产品的生产在“超加速”的社会模式中不至于滞留和堆砌,资本所有者势必想方设法加速审美产品的流通与消费,正如鲍曼所言,“电子设备最大的作用就是把一种已经充分形成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和显著”[13]。这主要体现在资本家利用算法和大数据,对受众进行“数据画像”,以交互式、沉浸式的数字广告精准推送受众所需所想的审美产品,以刺激并激发受众的视听感官和购买欲望。同时,资本主义借助工具理性作用于人的心理层面。一是利用数字媒体技术,将象征着“权力”“尊严”“显贵”“成功”等意蕴的符号标签植入审美产品中,引诱受众竞相攀比、炫耀,创设“虚假的需求”。二是将有益于资本增殖的内容渗入人的自觉意识之中,在自觉意识否定、压制非自觉意识的过程中,以“虚假的需求”代替本真需求。除此之外,为了使这种审美消费合理化,资本所有者更是邀请明星、网红为其产品代言,吸引并诱导受众步入“竞相模仿”的陷阱。
如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审美消费活动俨然蜕变为“给予—接受”的单向度模式,审美商品成为一种“技术假体”⑥,在消解人的自然感官的过程中,遮蔽受众对商品的真实感受,代替消费者进行选择。受众亦浸淫于资本营设的“审美幻境”中,接受资本的规训,在“资本倡导什么,就消费什么”的循环往复中成为“提线木偶”,在符号魅惑的光影中丧失个性需求与审美追求,自主性在数字技术的规制下惨遭削弱。可以说,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们对审美商品的选择并非出自本真需要,且不断同占有的审美商品相异化,即占有消费越多,拥有的使用价值就越少,内心愈发感到彷徨和失落。人们看似是在“加速社会”中忙碌充实地生活,实则是在数字化洪流中被无情冲击,稍有不慎,则有可能被这场“加速”的资本游戏淘汰,因而无暇顾及自身感受,只能随波逐流于这场资本的游戏,“降格”为资本逐利的工具,失落在审美异化的泥沼之中。
(三)赛博空间中的虚拟审美体验与人际关系疏离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鉴于网络可移动性、虚拟性与交互性等特征,由“实体”架构的“实在世界”日渐被由数字“虚体”构建的“赛博空间”所代替,人们沉醉于数字技术创设的“虚拟幻境”中,热衷于在虚拟空间内进行交流和交往,“心甘情愿”沦为一串串算法数据,这已然成为现代人的生存常态。如在涌动的人群中,在行进的地铁上,每个个体的目光均关注于自己的手机屏幕,身体虽然处于地铁等“物理空间”中,“灵魂”却潜藏于手机屏幕后的由智能技术架构的赛博空间里,与其他虚体进行交流。也就是说,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与人的关系更倾向于表现为赛博空间中虚体与其他虚体的关系。同时,由于赛博空间的虚拟生存与交往能够产生大量的商业价值,因而数字资本并不会对其纠偏,反而会不间断操控,以牟取更大利益,最终造成审美异化与人际关系疏离。
赛博空间中的审美体验与消费,除却上述提及的关于短视频中身体的狂欢与消费外,还包括对数字空间中诸如游戏币、直播打赏等内容的消费。换句话说,受众可凭借自己的审美需求对游戏中的人物进行装饰,为其购买华丽的外衣;也可为喜爱、欣赏的主播打赏消费,满足自身的窥视欲。这种形式的消费的确能够为其带来即时的快乐与满足,于虚拟空间中凸显个人的品味与特性。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消费形式不仅会耗费大量时间、金钱、精力,并导致人们对赛博空间的过度沉迷,还极易导致自身与现实社会“脱域”,致使现实交往能力越来越弱。在罗萨看来,“在数字化的‘全球化时代中,社会亲近性与物理邻近性之间越来越脱节了。那些与我们有着亲密社会关系的人,不必然在物理距离方面也离我们很近,反之亦然”[14]。在虚拟空间中,我們可以是游戏主播,也可以是基于共同兴趣爱好汇集起来的亲密好友,而在现实中,仅仅具备物理邻近性的人不一定能够成为熟络好友,进入自己的社交圈子。可以说,在现实空间长期交往中形成的人际关系日愈被数字空间中的虚拟交往所代替。然而数字时代的虚拟性也为人际关系之构建埋下隐忧。以各类社交APP为例,在数字空间中,算法通过对受众精准分类与匹配,为受众推送符合其自身需求、满足其猎奇心理的社交对象,但在技术编码、变声器、美颜及团队包装等作用下呈现的美,并非真实之美,充斥着满是欺骗与谎言的异化人际关系,极易降低人们的信任感与安全感。
三、审美异化的突围:破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审美困境的路径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商业资本的生产、流通与消费需要利用审美图像,审美活动的实践性也决定了其与日常生活之交融,进而进入经济生活,在其中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然性。正是资本牟利本性与审美的日常生活性特征为审美商品凭借数字技术大批量生产与消费提供了可能。作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最为普遍化的审美娱乐方式之一,资本创设的视觉景观无疑为受众带来了新奇、震撼的审美体验,既表征了数字技术在审美层面的巨大潜力,又革新了审美观念,带来了新的审美形式。但是,当前审美消费呈现出来的大多是一种短暂的、浅层次的视觉狂欢,而非有深度的、人文性的审美体验,受众被“囚困”于单纯“快感享受”的乌托邦之中,消解着对人生应有的深度与广度的探寻,审美异化现象愈发严重。解决这一问题,相较于政策、措施等外部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实现审美对内容的净化,在技术批判中,审视审美异化的虚幻性与超现实性,缓解数字技术笼罩下审美精神式微与人道主义滑坡等社会问题,助力审美精神的理性复归,实现审美观赏性与价值性的和谐统一。
(一)数字技术的纠偏:探寻审美对技术的超越之路
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无与伦比的视觉奇观与科技审美新样态,人们也早已习惯于在赛博空间中感知新奇、震撼、多元的审美文化氛围。也就是说,人们在思想层面上已然接受了技术对生活的影响和改变,故而“返璞归真”、回到“审美无利害”的传统语境中解决问题显然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对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来说,无论是在现实空间还是赛博空间中遭遇审美困境时,都应该意识到“远离网络”“拒斥数字化”并非恰当的做法,既要避免理性的形而上的压抑,也要超越感性的形而下的异化[15]。因此,要在接受技术审美化的基础上,重释审美的解放作用,不仅要改变审美与技术的失衡状态,还要进一步达到审美对技术的超越。一是要正视数字技术笼罩下视觉审美的转向变迁。不可否认,数字技术对美的无限度挖掘与运用,构设了“引人入胜”的“审美幻境”,使得受众极易在光影交错的审美体验中陷入资本创设的“审美陷阱”,这无疑是应当否定与批判的。但同时,审美从“礼不下庶人”的高居态势降落至可供人人观赏、占有的“尘世凡间”,日常生活与审美的联系愈加紧密,技术不断为审美“赋值”,促使审美在一定程度上也涵育着启智润心、传播主流价值观等功能。因而,要正视数字技术加持下审美的转向问题,既不要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亦不应全然接受。二是要重构“图”“文”关系,减轻视觉图像对文字的“奴役”。数字技术的兴盛使得视觉图像开始流行,人们生存于高度密集且经由百般雕琢、精心设计的“美图”的簇拥之下,“心甘情愿”沿着“被预设”的轨道延续着对审美品味的追寻。既然无法改变数字技术愈发成熟的现实,则可以从减轻受众对视觉图像的依赖着手,利用数字技术“复活”以文字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引导人们在图文并茂中、在对文字的阅读中感悟生活悲欢、领悟生命真谛,以真正实现审美商品“真善美”的引领作用,通达审美“令人解放”的至高境界。
(二)生产消费环节的赋意:涵育审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批判精神
审美生产者与消费者是审美消费活动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因此穿透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审美异化迷雾,也必然要从这两个要素中寻求解决思路。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是“单向度的人”,犀利地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压制了人们的批判精神与否定精神,遏制了人们对不同生活方式的想象与期盼。这一警示在当代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从审美生产者的角度看,生产决定消费,审美商品的生产是审美消费异化的源头。伴随禁欲主义的旁落与消费主义的兴起,审美生产者为牟取更多经济利润,完成图像资本积累,利用算法与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为人们精准推送既符合社会趋势,又象征名誉地位的审美商品,不断攻破受众心理防线,引诱受众完成审美消费。这种罔顾受众真实审美需要,无视负面效应的做法不仅不会帮助人们形成健康、正向的审美观与消费观,还会导致受众沉湎于生产者创设的審美泥沼中,引发“审美精神的失落”。因此,在审美生产过程中,要将受众的“真实需要”与“主流审美价值”相结合,祛除审美生产过程中不纯粹的目的,弱化乃至消除低俗审美产品对人们的毒害。同时,赋予其具有历史厚重感与强烈人文性的审美价值意蕴,与碎片化、空洞化、平面化的低俗审美产品形成鲜明对比。
从审美消费者的角度看,凡勃伦与桑巴特将“奢侈”与资本挂钩,形象展现了美国在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背景下,消费者对商品之消费日愈与其内蕴的权势、尊严等相关联的社会现状。这种“凡勃伦效应”与当下审美消费者对审美产品的追求动机如出一辙。也正是在对审美产品象征的地位、权力等的追逐过程中,消费主体日渐迷失在绚丽多彩的审美迷雾中,沦为服务于图像资本增殖的“奴隶”。这就要求,一方面,审美消费者应从感性消费中挣脱出来,在面对各种“婀娜多姿”的审美产品的诱导时,保持理性,对各种直播打赏界面保持警惕,洞察自身真实审美需要,复归审美理性;另一方面,审美消费者也应主动学习审美知识,增强自身的审美品位与审美底蕴,在提高、夯实自身审美追求的过程中降低低俗审美产品对自身的侵害。
(三)审美理念的通达:在“审美令人解放”的意蕴下实现自我主体的确认
在传统美学视域下,审美有其特定的、独立的疆域,与功利主义的消费“水火不容”,是一对无法调和、相互对立的矛盾,且承担着将沉溺于消费泥潭中的人拯救出来的重任,完美展现着“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一说。人们亦在审美活动中以一种超越性生存的状态,不断完成由自在趋向自为、从自发走向自由的蜕变。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制造了大批量雷同的美,资本所有者更是不断为审美商品赋值,将其美化为自由、美好、尊贵的代表,诱导受众不断跟风消费。消费主体看似是在追逐蕴含着社会地位与身份象征的美,实则是沦陷在雷同的美中,成为同质化、伪个性化的存在。审美的神圣性、无功利性遭遇消解,审美走入异化困境已是不争的事实。需要明确的是,审美的异化说到底是人的异化。因为审美商品的消费活动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最终指向于人。在马克思看来,审美与人的本质密切相关,真正的美是实践基础上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16]。因而,解决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审美异化的根源在于消解人的异化,促使人实现个性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对自身本质和主体性的认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人摆脱异化枷锁、走向自由和解放的出路,即“个人在自己的自我解放中要满足一定的、自己真正体验到的需要”[17]。这种“需要”不是被资本特权或某种抽象存在物所裹挟的虚假的欲望,而是我们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切身体会到的且迫切渴望得到满足的需要,它既可以是劳动生产层面的需要,也可以是谋求尊重和认同的情感需要,还可以是追求自由个性的精神需要,且这种需要必须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现实的社会存在,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自觉发展,才能完成自我主体的确认,才能通达马克思视域下“完整的人”的生成,才能在破除人的异化的过程中消解审美异化之困境。具体来说,每个人既应提高审美意识、审美素质,又应观照现实、回应现实,涵育历史的使命感和时代的责任感,自觉将社会的和谐与人类的福祉相联结,秉承审美解放人性和复归自由之目的,既不做审美异化的助推者,也不沦为纯粹“欲望的动物”,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营设感性愉悦、领悟愉悦和精神愉悦共存的审美愉悦,创设自由、平等、轻松、欢快的审美文化氛围。
结语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以虚拟现实、大数据、算法推荐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在将审美要素运用于“生产—消费”环节,大力促进审美商品勃兴的同时,亦不可避免地使受众沉溺于审美商品的表象中,遭遇“视觉至上”的魅惑,造成了审美异化之困境,出现了诸如审美生产背离意义生产、“伪需要”取代真实需要、人际关系异化与疏离等现象。但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技术是如何完全取决于科学的一些客观的程式,技术本身不像整个宇宙一样,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它只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元素,它起的作用的好坏,取决于社会集团对其利用的好坏”[18]。数字技术在消费领域的运用并不是审美异化的原罪,科技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因而不能指望依托对技术的全盘否定走出审美異化之困境。赋予审美商品以审美愉悦与审美教育的人文内涵,助力高雅审美与大众审美的交织交融,实现审美对内容的净化,达到审美对技术的超越,才是走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审美异化迷雾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 “数字资本主义”是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丹·席勒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这样一种状态: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与工具”。
② 黑格尔指出,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要消除现代社会带给人类的这些负面影响,最好的方式和途径就是审美教育和情感教育。
③ 德波指出,“在现代生产条件无处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积。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部转化为一个表象”。
④ 审美不再单纯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主动加入、建构了社会现实。
⑤ 罗萨在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审视时,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时间维度出发,诊断出现代社会愈发显现的“加速”特性。
⑥ “技术假体”概念由维利里奥提出,主要强调技术加速塑造了人们新的感知方式,不可避免地强行消除人类自身固有的感知。
参考文献:
[1]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商品美学批判:关注高科技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美学[M].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杨震.审美经济现象的哲学意蕴[J].云南社会科学,2021(4):29-36+186-187.
[3]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崔健,穆佳滢.审美与资本的纠缠:审美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及批判[J].江苏社会科学,2022(2):43-51.
[5]奥利维耶·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M].黄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6.
[6]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00.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4.
[8]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64.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9.
[10]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
[11]崔健,李真真.数字资本主义的缘起、内症及迷局[J].学术交流,2022(5):5-17+191.
[12]弗里德里希·席勒.席勒经典美学文论[M].范大灿,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30.
[13]齐格蒙·鲍曼.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 44 封信[M].鲍磊,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8.
[14]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118.
[15]崔健,穆佳滢.虚假的现实:消费幻象中的视觉迷失[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42(2):205-212.
[16]陈东辉,王宇婷.泛娱乐主义思潮下青年审美能力的隐忧与解决策略[J].理论导刊,2022(8):91-98.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47.
[18]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M].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9.
【责任编辑:张晓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