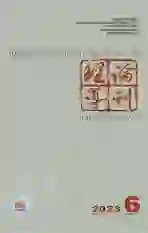《神圣家族》中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探论
2023-06-19钟启东
摘 要: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前奏”,《神圣家族》在批判国民经济学中揭露意识形态的辩护实质,在批判思辨唯心主义中揭露意识形态的抽象秘密,在批判抽象人权中揭示意识形态的生成变化规律,在批判空洞寓言中揭示意识形态的教化支配逻辑,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为即将到来的“意识形态的术语革命”(集中体现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清理了思辨的障碍、确立了群众的地位、提供了历史的肉身,做着“最后的理论准备”。
关键词:《神圣家族》;唯物史观;意识形态批判;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3)06-010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述原创性贡献及学理化学科化研究”(21VSZ001)。
作者简介:钟启东(1985—),男,四川内江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意识形态规律论。
关于《神圣家族》与唯物史观的理论联系,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经明确指出:“但是,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的观点,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1]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为了辩驳鲍威尔兄弟仍然给予费尔巴哈较高评价,但这既不表明他们这个时候还没有力求走出费尔巴哈的总问题及其哲学原则,也不表明此时的马克思没有在这种实际发生着的理论走出中意识到他同费尔巴哈的区别以及对这种区别作出阐明的必要性,因而更不表明《神圣家族》中意识形态批判的总问题及其哲学原则不是指向哲学革命、从属于新世界观的理论准备。在一定意义上讲,《神圣家族》正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前奏”,为“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做着“最后的理论准备”。这就使得一系列问题被提了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针对国民经济学和思辨唯心主义进行的副本批判,对于即将到来的“意识形态的术语革命”(集中体现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意味着什么?如果说《神圣家族》中的“副本批判”本质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那么它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及其批判内核的正式出场做了何种准备、清理了哪些障碍?鉴于学界尚未从这个问题视角来讨论《神圣家族》的意识形态逻辑,本文拟从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在该文本中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出发,梳理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辩护实质、抽象秘密、生成变化规律和教化支配逻辑的初步揭示,以期为学界深入研究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识形态逻辑问题尽绵薄之力。
一、在批判国民经济学中揭露意识形态的辩护实质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年发表于《德法年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都对国民经济学的逻辑悖论和现实矛盾作过批判,指出“新的经济学”和“自由贸易体系”,都是“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并“在一切领域中与自然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2]58,揭示了“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异化的本质”[2]158,这为《神圣家族》进一步揭露国民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辩护本质奠定了认识基础。
首先应当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批判国民经济学,直接目标是批判思辨唯心主义。既是为了批判思辨唯心主义对蒲鲁东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歪曲和责难,也是为了批判思辨唯心主义跟国民经济学共有的现实基础和理论错误。1840年6月,蒲鲁东的经济学著作《什么是财产》出版,他揭露了国民经济学掩盖着的私有财产经济事实,提出了“所有权就是盗窃”的著名观点。1844年4月,埃德加·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第5期发表评论文章《蒲鲁东》,通过“赋予特征的翻译”和“批判性的评注”两种手法发难《什么是财产》,批评蒲鲁东:在把贫穷跟公平对立起来的同时,“提出了历史上的绝对的东西”,坚持着“对公平的信仰”,成为“神学的对象”[2]258。在马克思看来,埃德加·鲍威尔既没有“根据国民经济学的观点”来理解蒲鲁东“对国民经济学所作的批判”[2]258,也没有“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2]255,仅仅满足于在宗教观念上大做文章,无法深入思想内部、不能切中理论要害,当然也就不会知道蒲鲁东国民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进路和现实意义,所以鲍威尔对蒲鲁东的经济学批判“根本没有谈到国民经济学,也根本没有谈到蒲鲁东的著作所具有的不同于他人的特点,而这种特点正是在于把私有财产的实质问题看作对国民经济学和法学生死攸关的问题”[2]258。质言之,鲍威尔对蒲鲁东的批判,除了表明自己与后者有着相同的观念论错误之外,不仅未取得实质进展,反而将后者的积极意义和理论不足统统忽视,导致“批判的批判”沦为“认识的宁静”和“思辨的胡说”。
不同于鲍威尔毫无批判原则的批判工作,马克思恩格斯既看到了“蒲鲁东则对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财产作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取得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在国民经济学中引起革命,并且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2]256;也看到了蒲鲁东的理论不足,由于蒲鲁东仅仅是从一般权利的角度来理解和说明私有财产,没有从生产关系总和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考察私有财产这个基本事实,没有“因否定私有财产而有了任何新的发现”,“不过是无意中透露了批判的批判讳莫如深的秘密罢了”[2]258,导致国民经济学成为真正科学的“可能”消失。从这也能看出,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蒲鲁东国民经济学批判的不彻底性,从理论上说是受到后者观念论哲学原则的影响,这跟鲍威尔兄弟的思辨唯心主义有着相同的哲学地基;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既是通过否定“批判的批判”来肯定蒲鲁东,又是通过肯定蒲鲁东来否定“国民经济学”,更是通过对“批判的批判”和“国民经济学”的共同否定来否定蒲鲁东,并将对这三者的根本性否定最终归结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否定。
这个批判思路也是在执行《德法年鉴》和《手稿》中确定的批判策略:先从“副本批判”上升到“原本批判”,再“联系原本”展开“副本批判”,立足市民社会及其政治经济学“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2]111。这个批判思路在《神圣家族》中得到完整体现,只不过是以论战方式呈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就在这种论战中激发并生长出来,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获得“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被科学地提出和建构起来。在此意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思辨唯心主义的直接揭露,以及对蒲鲁东国民经济学批判不彻底的间接批判,都属于意识形态批判,不仅内在建构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而且导向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真正批判的世界观”。
具体而言,既然对于国民经济学来说,私有财产、私有制是其“生死攸关的问题”,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批判,自然也要从这个问题出发来彻底击中国民经济学为资产阶级私有制辩护和祝福的意识形态本质。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民经济学的物质前提是私有财产。“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论述都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国民经济学把这个基本前提当作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作任何进一步的考察,甚至像萨伊所坦率承认的那样,国民经济学只是‘偶然提到这一事实。”[2]255-256私有财产作为前提在这里有两重内涵:一方面,私有财产是“主词”,国民经济学是“宾词”,前者决定后者,正如“颠倒的世界”生产“颠倒的世界意识”那样,国民经济学不过是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理论关系和精神表征;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私有制导致了异化劳动,才使得国民经济学所揭示的规律不过是异化劳动的规律,并用这个规律掩盖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要么绝口不提私有财产,要么把私有财产当成历史定在、逻辑前提,也就是“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终原因”[2]155。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关系当作合乎人性的合理关系。国民经济学研究问题总是从一定的虚构状态出发,既然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2]155,认为私有财产的存在是永恒真理,那它自然也会把这个永恒真理“当作合乎人性的和合理的关系”[2]256,并且在现实已经跟这个永恒真理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它不是反思这个永恒真理本身、不是说明私有财产的秘密,只是对某个资本家、银行家或者工厂制度这些私有财产“特殊的滥用行为”进行攻击和抨击,始终相信私有财产是合理正确的,始终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是最理想的历史形态。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指明,国民经济学为私有财产进行辩护。“以往的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运动仿佛为国民创造的财富出发,进行了为私有财产辩护的思考。蒲鲁东从国民经济学用诡辩掩盖的相反的方面出发,即从私有财产的运动造成的贫穷出发,进行了否定私有财产的思考。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批判,当然是从那种体现私有财产充满矛盾的本质的最彰明较著、最触目惊心、最令人激愤的形式,即贫穷、贫困的事实出发的。”[2]259这是对国民经济学意识形态辩护本质的直接揭穿。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不仅私有财产古已有之,而且只有实行资产阶级私有制,才能创造国民财富,才能推进人类文明,所以他们把工资看成天经地义的劳动成果,认为“工资和资本的利润彼此处在最友好的、互惠的、仿佛最合乎人性的关系中”[2]256,实质就是承认资本家通过工资购买劳动力进行的生产和分配剥削是天经地义、合乎人性的。质言之,国民经济学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真理,为“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个绝对利益和统治意志辩护,从而掩盖了“工人阶级没有可供侵犯的任何私有财产”这个异化本质和讽刺事实。国民经济学从不加反思的历史前提出发,又回到拒绝反思的现实前提,看似声讨了私有财产,实则捍卫了私有财产,而这不过是说明国民经济学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代言和思想专利。
二、在批判思辨唯心主义中揭露意识形态的抽象秘密
“批判的批判”之所以会误读并责难蒲鲁东对财产和贫穷作出的事实揭露,是因为它没有看到国民经济学的真正秘密是为私有财产辩护。正如它没有看到蒲鲁东批判国民经济学的真正问题不在于他否定了私有财产而在于没有在这种否定中得到“任何新的发现”,仅仅指责蒲鲁东对“公平的信仰”“成了神学的对象”,却没有看到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历史假定出发、蒲鲁东从否定私有财产的哲学原则出发,实际上同它自身坚持“从‘精神的绝对合理性的信条出发”[2]289没有根本区别,它们都不过是在说明——“当思辨在其他一切场合谈到人的时候,它指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观念、精神等等”[2]265。这就是意识形态模糊观念与现实关系,掩盖异化劳动本质并为私有财产辩护的抽象秘密。那么,意识形态的这个抽象过程是如何隐蔽着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思辨唯心主义的抽象原则,对这个意识形态加工环节的真相作了揭露。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对《巴黎的秘密》所作的批判性叙述的秘密,就是思辨结构即黑格尔结构的秘密”[2]276,“批判的批判”正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结构的具体运用。马克思恩格斯以“果品”抽象为例,说明了这个思辨结构的演化逻辑。首先是进行种属归类和概念提纯,从感性直观的苹果、梨、草莓、扁桃等具体的水果形态中,抽取出它们的普遍规定和共有属性,得到“果品”这个一般观念;其次是进行概念想象和本质设定,把“果品”这个抽象观念想象为“存在于我之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真正的本质”,进而宣布“‘果品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2]276。这是关键的一步,抽象造成的颠倒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思辨故意宣布,对于“果品”这个“真正的本质”和“实体”来说,“梨之成为梨,是非本质的”“蘋果之成为苹果,也是非本质的”[2]276,它们之所以是梨、苹果、扁桃等等具体样态,正是因为它们有“果品”这个“观念的本质”。也就是说,思辨把本来是从感性直观中抽象出来的观念当成了感性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和根据,不仅把这个观念想象成“本质”和“实体”,而且把这个想象设定为前提和现实,因而认为只有这个想象的“本质”和“实体”才最重要、最本质,至于梨、苹果、扁桃等等之间的“感性差别是非本质的、无关紧要的”[2]277。
但是,“思辨的理性”再怎么纯粹想象、再怎么创造奇迹,它还是“自己的抽象的理智”,感性存在再怎么不重要、再怎么非本质,它依然是“现实的果实”,以及肉眼可见的这些果实“现实的差别”。既然思辨声称作为本质和实体的“果品”取消了一切差别,创造了果实的具体形态,那么它就应该明确回答:一方面,“如果说苹果、梨、扁桃、草莓实际上无非是‘实体‘果品,那么,试问‘果品又怎么会忽而表现为苹果,忽而表现为梨,忽而又表现为扁桃呢?同我关于统一体、关于‘实体、关于‘果品的思辨观念显然相矛盾的多种多样的外观又是从何而来的呢”[2]277-278?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果品”是如何从“自己的抽象的理智”中创造出这些有着不同自然形态的现实果实的呢?换言之,思辨如何能够证明苹果、梨、扁桃等“现实的果实”是“抽象的果品”的创造物,而不是它们自身的产物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思辨的结构采取了第三步行动。“思辨哲学家回答道:这种外观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果品并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自身有区别的、能动的本质……‘果品把自己设定为梨,‘果品把自己设定为苹果,‘果品把自己设定为扁桃;把苹果、梨、扁桃彼此区别开来的差别,正是‘果品的自我差别,这些差别使各种特殊的果实正好成为‘果品生活过程中的千差万别的环节。”[2]278思辨的想象终于变成了思辨的胡说:苹果所以是苹果,是因为“果品”把自己设定为苹果,苹果之所以跟梨有区别,是因为“果品”的自我设定有差别,特殊果实的千差万别不过是说明“果品”的自我设定存在千差万别,但是唯一没有区别的就是“果品”既在设定区别,又在消融统一这些区别。于是,“果品”这个最高的统一体,“既把每一种果实全都消融于自身中,又从自身产生出每一种果实,正如身体的各部分不断消融于血液,又不断从血液中产生一样”[2]278,它造成差别又消融差别,它让差别仅仅成为自我的外化差别,因而它有多少个化身,就会有多少种事物,它的每一次思辨,就是“完成了一次创造行动”。到这里,思辨完成创世,从此历史只是思辨的自身循环史。
从特殊的果实中提纯“果品”到宣布“果品”是本质和实体,再到证明特殊形态的果实差别,不过是“果品”进行自我设定、自我外化的化身差别,每个环节都贯彻着思辨精神和抽象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2]280据此来看,抽象的秘密就是先从现实中造出“秘密”这个范畴,再从这个范畴中秘密造出现实世界。思辨之所以在谈到人的一切场合都只是在谈到观念和精神,不是因为思辨眼里没有人,而是因为思辨不理解现实的人,就像它不了解“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2]286那样,正是由于思辨总是从抽象的设定出发来抽象地创世,因而历史在它看来不过是本质和实体在自我运动中创造现实,导致“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精神的历史,因而也就变成了同现实的人相脱离的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2]292。
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民经济学同样遵循了这个思辨结构和抽象秘密,否则它就不能为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进行辩护和祝福了。国民经济学从市民社会中发现商品流通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私有财产,二是平等交换,于是将这两者设定为“本质”和“实体”,为了论证这个设定,他们又做了进一步的设定——理性经济人假设,并从“虚构的社会状态”中以“猎人和渔夫”的物物交换作为开端。一方面讲述交换原理和财富规律,另一方面讲述人类社会是如何在这种原理规律的支配下从传统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并由此得出结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都会趋利避害等等。国民经济学的核心要旨在于論证私有财产是财富和文明的秘密,如果说现实中还有“文明的野蛮化”现象,还有工人的贫穷和农民的破产,那不过是这个规律在展现自身秘密,不必大惊小怪,这是进步的代价,这是特殊的差异,这些代价和差异同私有财产的理性运动创造的巨大财富相比不值一提,前者终将被后者消融和克服,人类终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发现和确立起自己的“完美状态”。在国民经济学那里,私有财产不过是抽象的设定,正如根据这个设定提出的“天赋人权”同样抽象那样,这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抽象秘密,它“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2]179。
三、在批判抽象人权中揭示意识形态的生成变化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国家的抽象人权:“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具有同样的意义”[2]313,并强调《德法年鉴》就已指出这个实质。从《德法年鉴》到《手稿》再到《神圣家族》,马克思始终在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国家“普遍人权”的抽象性、虚假性、伪善性,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生成变化规律,说明了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革命利益是如何从起初的一致走向差异和对立,同时也就说明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如何走向根本对立,以及资产阶级为何要用抽象人权来掩饰并力求克服这种对立。
不管是《德法年鉴》,还是《神圣家族》,马克思都一再指出,鲍威尔对犹太人解放问题的讨论,以及在这种讨论中涉及的信仰特权和普遍人权,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是根本性的错误,鲍威尔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混为一谈,把“政治解放”当成了“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没有看到“政治解放”仅仅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2]32,也就是放弃了“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要求。这当然是由于鲍威尔抽象地谈论“人”(作为“观念”和“精神”的“人”)以及“人的解放”,正如他抽象地谈论“宗教解放”以及更加抽象、不加区分地谈论“信仰的特权”和“普遍的人权”那样,所以第二个错误不可避免地到来。鲍威尔把“抽象的人权”当成“现实的人权”,并错误地把“宗教解放”当成“人的解放”的前提和条件,一方面误以为只要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现实的人也就从宗教中解放了出来,另一方面误以为只要犹太教徒和基督徒放弃了他们“信仰的特权”,人们就“能获得普遍人权”。鲍威尔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只是在谈论“宗教解放”对“政治解放”的关系和意义问题,并“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2]25,结果导致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人的解放”问题,被当成了宗教信仰问题,既是在解决信仰什么宗教的问题,也是在信仰中解决宗教问题,却唯独没有解决信仰本身的问题,正如从来没有真正解决“人的解放”问题那样。于是,鲍威尔用“大胆、尖锐、机智、透彻,而且文笔贴切、洗练和雄健有力的”[2]23宗教批判和神学批判,移花接木地“把对耶和华的信仰变成了对普鲁士国家的信仰”[2]311。
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作了要点批判并明确指出:其一,“政治解放”只是“人的解放”的进步事件、中介环节,而非本质目的和最后形式,“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2]38。其二,致力于“政治解放”的“宗教解放”,只是把“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将“基督教国家”变成“政治国家”,把信仰从“公法领域”驱逐到“私法领域”,把现实的人从“信徒”变成“公民”,却没有把“现实的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2]38,不仅没有消除“实际的宗教笃诚”,而且也从不力求消除这种宗教笃诚。其三,这就说明,一方面“信仰的特权”跟“普遍的人权”并不矛盾,宗教信徒同时也可以是政治公民,“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仅存在,而且是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存在”[2]27;另一方面,且不讲“宗教的定在和国家的完成是不矛盾的”[2]27,即便政治国家终结了“天神信仰”,也会有“物神信仰”取而代之,就像“政治的权威”会代替“宗教的权威”那样,人们还没真正走出“人的异化的神圣形象”,马上又陷入“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2]4的抽象结构及其统治秩序之中。其四,这个抽象结构导致“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2]30,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的生活,人被看作社会存在物和公民,后一种是市民社会的生活,人被看作私人和工具,淪为“异己力量的玩物”。这种对立一方面表明正是市民社会“抽象的活动”造成了政治生活“抽象的痛苦”,另一方面表明政治国家赋予公民和法人的“普遍人权”不过是抽象的普遍性和虚假的自由性,是空洞的权利许诺和伪善的意识形态话语。政治解放的人权宣言和自由召唤,是有特定语境和时代规定的,因为“‘人权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2]313,我们在那些资产阶级“牧羊人带领下,总是只有一次与自由为伍,那就是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2]5。在资产阶级社会,真正自由的从来不是现实的个人,而是资本及其增殖运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政治国家承认人权不过是以公法形式在确认和保护市民社会的现代奴隶制:“这种市民社会的奴隶制在表面上看来是最大的自由,因为这种奴隶制看上去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个人独立,这种个人把自己的异化的生命要素如财产、工业、宗教等的既不再受普遍纽带束缚也不再受人束缚的不可遏止的运动,当作自己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运动实际上是个人的十足的屈从性和非人性。在这里,法代替了特权。”[2]316-317
实际上,以抽象的“普遍人权”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是这样构筑起来的,它构筑在“自由的假象”和“占有的幻象”之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市民社会的自由假象出发,从商品交换的平等规则出发,把市民社会的成员想象和设定为“原子”,然后宣布这些“原子”生而自由,声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享有自身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权利,每个人都有缔结社会契约委托监督政府行使国家权力的民主力量。总之,它在一切领域不失时机、不顾现实地骄傲宣称:“人权”取代了“神权”,“自由”取代了“强迫”,“民主”取代了“专制”,“文明”取代了“野蛮”,正是它复兴了文艺、启蒙了理智、解救了苦难、开启了现代……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个形成规律,实质就是“颠倒的世界”决定“颠倒的世界意识”。正是市民社会的颠倒本质决定了观念领域的颠倒幻想,正是市民社会的非人性现实决定了意识形态要在观念领域加以掩饰、标榜人性,因而不得不采取歪曲和虚假的意识内容,也就只能围绕抽象的人探讨抽象的权利了。在这种歪曲和抽象过程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把特殊利益说成了普遍利益,正如它把“资产阶级的法权”说成是“普遍的人权”那样,它将“宣言中的人权”当成了“市民社会中的人权”,所以它当然会把人想象成观念和天堂中才有的“原子”,并赋予这些“原子”各种神圣权利。但是由于“原子”本来就是想象的,“市民社会的成员决不是原子”[2]321,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赋予的普遍人权,看起来是一切都有,实质却是一切皆无,“绝对的权利”等于“绝对的空虚”。当然这是在本质上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权利许诺不会真正实现意义上的虚无真相,并不是说它所宣称的权利和自由全都没有得到任何实现,这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政治解放”当然是重大进步,“资产阶级的法权”当然也是重要宣言和现代通约,要不然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期又如何能够联合无产阶级共同反抗僧侣贵族阶级的封建统治呢?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体系中也有满足无产阶级利益需要的观念主张,只不过仅仅是一部分而非全部、是表象而非本质,但资产阶级却将之看成了全部和要旨,这既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意识形态基点,也是资产阶级在赢得政权、确立统治地位后背叛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证据。
对于这个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展示了他们批判工作的辩证风格。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非一开始就是完全抽象的,只有等它确立支配地位之后为了掩盖和歪曲市民社会中的异化本质,才跟无产阶级的利益原则和理论表征根本对立起来。正是因为这种对立暴露出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空谈甚至背叛,才使得人民群众看清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成色和利己本质,才决心走出资产阶级的思想秩序范围,并要用坚决的物质力量行动来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统治。所以当“批判的批判”责备“群众”由于没有“符合于一种思想”而不合时宜、肤浅庸俗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既说明前者没有看到“‘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286,也说明正是因为后者看到了资产阶级利益原则中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才会质疑并最终抛弃这“没有体现关于他们的现实‘利益的思想”[2]287,而去寻求和建构体现自己根本利益的思想体系与革命理论。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指出:“不难理解,任何在历史上能够实现的群众性的‘利益,在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在‘思想或‘观念中都会远远超出自己的现实界限,而同一般的人的利益混淆起来。”[2]286这当然是一种错觉,但也是一种符合革命需要的错觉,并且错觉里也有真实的东西,就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非纯粹的欺骗体系那样。封建统治确实需要推翻,法律面前确实应该人人平等,人民应该是国家和自己的主人等等,这些意识形态话语虽然没有真正实现,但它们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真正愿望。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还没有说明错觉是如何造成的以及为何必然出现这种混淆,但是到了《形态》中他们就已经为这个意识形态现象找到了答案:“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2]536可见,《神圣家族》中的意识形态批判成果,已经很接近最终由《形态》深刻揭示出来的这个意识形态规律了,前者为后者准备了问题和条件。
四、在批判空洞寓言中揭示意识形态的教化支配逻辑
“批判的批判”对“群众”表现出来的鄙夷和贬低态度,同样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以鲍威尔兄弟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由于对群众感到失望而放弃了对群众进行意识形态教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似乎他们批判群众纯粹是宣泄不满而没有支配企图,以致于认为对他们的“批判”只需要做出及时的揭穿和批判就好。“批判的批判”真的是在贬低和批评群众中放弃了群众吗?“批判的批判”真的就因此而忽视了对群众进行意识形态教化和思想政治教育支配吗?显然不是,要不然马克思恩格斯为何在《神圣家族》的序言中开篇就道出一个真相: “现实人道主义在德国没有比唯灵论或者说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2]253如果仅仅是理论荒谬,停留于纯粹思辨和学究讨论,那本身没有太大危险。但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在德国思辨唯心主义是现实人道主义最危险的敌人,这就意味着“批判的批判”达到顶点的“整个德国思辨的胡说”,并且不只是纯粹胡说,而且是已经影响和干扰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方向、路线与原则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思辨的胡说”面向工人群众进行的空洞“寓言教导”和“道德教化”,潜存着为资产阶级政治国家辩护、否定革命的意识形态教化支配逻辑。事情真相竟是如此:贬低群众是为了利用群众,醉醺醺的思辨表象之下是清醒的意识形态行动。
为了说明这个真相和逻辑,应先讨论“批判的批判”为何要对“群众”采取如此纠结复杂的态度和行动。根据《文献报》提供的材料来看,“批判的批判”把“群众”视为“精神”的真正敌人,他们认为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的“伟大历史行动”之所以会最终失败,正是因为重视物质利益的“群众”参加其中并阻碍了“精神”的发展,是因为“群众”自以为是地“占有真理”却不“追随真理”,导致革命行动在过分狂热的群众激情中断送了“精神”和“真理”的显圣事业。在“批判的批判”看来,“群众”是物质的、肤浅的、庸俗的、怯弱的、顽固不化的,是“精神的对立物”,是应该遭到“精神”和“真理”不断征讨的。“批判的批判”之所以会对“群众”大发雷霆,主要是因为他们颠倒了思想与利益、思维与现实、精神与历史的真实关系,而这又是因为他们站在黑格尔的哲学地基上空谈“思想的革命”和“真理的历史”,从不“面向经验的人”,只是面向“心靈的深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嘲笑它们不能自拔的“真理行动”,不过是把批判群众作为自己的绝对事业,“靠批判地贬低、否定和改变普遍的群众来取得自己的绝对荣誉”[2]282。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指明了“批判的批判”在群众问题上的矛盾性:一方面,它公然“贬低、否定”群众,把“绝对的批判的英明同绝对的群众性的愚蠢”彻底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它又期望能够通过“改变普遍的群众”来赢得“绝对荣誉”,于是“绝对的批判在对群众大发一通神圣的雷霆之怒的同时,又向群众巧言奉承了一番”[2]285,承认群众有权利“觉得真理一目了然”,因为“批判的批判”正在谈论的是“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真理”[2]285。
可见,“批判的批判”从“精神”绝对合理性的信条出发,一边把“精神”论证为“进步”,一边把“群众”变成“固定不变的本质”,并让两者彼此对立起来,进而宣布“精神”必须“征讨”和“改变”需要拯救的“群众”,让后者符合“思想的秩序”,聆听“批判的教导”。到这里,“批判的批判”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教化目标和思想政治教育支配逻辑已经表现得很充分了,虽然他们轻视群众、贬低群众,但并没有因此就“放过”群众、抛开群众。在一定意义上讲,“批判的批判”声讨群众,跟马克思恩格斯对“批判的批判”进行批判,具有相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都是为了争夺群众,只不过前者是在误导和分化群众、打击和愚弄群众,后者则是为了警醒和团结群众、维护和解放群众。
这就是鲍威尔及其伙伴在思辨唯心主义“批判的批判”中遵循的意识形态教化意志和思想政治教育支配逻辑:由于“批判的批判”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代言,所以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保守的,革命意志是软弱的,解放理想是虚幻的。尽管他们讲着“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他们不去反思“精神”缘何失去了“群众”,而是责备“群众”不追随“真理”。说到底,他们只是期望“群众”能够看清“思辨的英明”,能够追随“批判的批判”所揭示的“真理”。“只要他们在思想中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不再认为自己是雇佣工人,并且按照这种极其丰富的想象,不再为他们个人而索取报酬,那么他们在现实中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了”[2]273-274,“只要他们在思想上征服了资本这个范畴,他们也就消除了现实的资本”[2]274。为了达到这个真理宣教目的,“批判的批判”开始了用心良苦的外化之路:首先是没有任何例外地把人和现实抽象为“精神”,宣称“精神”总是按照自己的“真理”在创造奇迹和推动历史,再诬蔑“群众”是“精神”在思辨结构中秘密创世的“真正敌人”,责备物质的、肤浅的“群众”阻碍了“精神”的发展和“革命”的奇迹,最后把自身“绝对的批判”提升并宣布为“尘世救世主”,不仅批判和教诲“伤感的、诚恳的、需要解救的群众”[2]352,而且“凭借无限的自我意识,使自己凌驾于各民族之上,期待着各民族跪在自己脚下祈求指点迷津”[2]354,妄图用空洞的“寓言教导”和“道德教化”来支配“群众”、否定“革命”、拒绝“实践”。
遗憾的是,“批判的批判”的“如意算盘总是不如意”[2]289,因为在“绝对的批判”返回那个作为出发点的“抽象自我意识”之后,其全部运动就只剩下纯粹的“超越一切群众利益的自己体内的循环,因此,群众对它已经丝毫不感兴趣了”[2]347。“批判的批判”失去“群众”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视群众工作,而是因为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做好群众工作;“批判的批判”陷入空谈和妄想,不是因为他们满足于空谈和痴心于妄想,而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就是抽象。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就是幻想:以为改变了意识,其实是改变了意识的对象。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5.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