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论祖国作为“存有本身”的“大地和自然”维度
2023-06-17何光顺
何光顺
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存在着受希腊-德意志与犹太-基督教的两条对立文化路线所影响的德意志祖国的建构问题。前一条是明线,它提倡的是“祖国”作为“存有本身”建基的“大地和自然”维度,那是由诗人和国家创立者来实现的。后一条是暗线,特别是众所周知的海氏反犹太主义问题只是在近年出版的《黑皮本》中才得到进一步印证。对于海氏在祖国建构中所涉及的反犹太主义问题,《黑皮本》编者特拉夫尼(P. Trawny)将其描述为“存在史上的反犹太主义”(《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3—4)。国内学者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辨析,但都还未能就海氏的反犹主义与其“祖国”建构的关系作更多讨论。从现有资料看,海氏的反犹太主义,不能等同于纳粹的种族论反犹主义,这方面问题不大。我们要思考的是:海氏借助其否定形而上学的“祖国”,以建构出作为“存有本身”的“祖国”,这其中有怎样的致思路径?这种建构是否可能?它存在哪些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又当如何启示古老的华夏民族在今日建构我们的“祖国”?
一、 建构作为最高存在的祖国:两个开端之间的“大地和自然”
在《流逝中的生成》中,荷尔德林将“祖国”“自然”和“人类”三者关联起来,认为“这三者处于一种特殊的交互作用中”(转引自《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144),这隐含着对于形而上学“祖国”的否定和对于存有(存在)论“祖国”的重新发现。对于这两重意义上的“祖国”,海氏是从西方哲学的两个开端来展开诠释的。
(一) 祖国作为“存有本身”在“第一开端”中沦落
海氏所谈的祖国作为“存有本身”是在希腊形而上学的第一开端和德国克服形而上学的另一开端的意义上来展开的,它指向的是“民族的历史性此在”的“升起、高度和沦落”(《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62)。从希腊的形而上学的“第一开端”而来,就是“祖国”作为“存有本身”的沦落,是民族的历史性此在的非存在,是荷尔德林说的祖国、自然和人类的“沉落”。“‘祖国’乃是存有本身,它从根基上承载并构造着一个在此存在着的民族的历史。”(144)张振华指出,海德格尔将祖国与第一哲学的核心论题“存在”(存有)直接等同,表现了海氏哲学朝向实践的尝试及其存在着的双向运动:一是把存在论与现实政治拉近,令“存在”在“祖国”这里得到具体而明确的落脚点;一是把存在论与现实政治拉远,通过对“祖国”之本质发起存在论追问,暴露出当时现实政治在本质层面的追问不足与根基缺失(198)。这个说法是确切的,即海氏说的祖国既让“存有”在历史性维度实现出来,但又不是与当下政权等同的形而下的祖国,“诗人在一种源初意义上以历史性的方式看待祖国”(144)。张振华主要是从诗歌与民族共同体关系角度探讨祖国,但海氏的祖国否定着从第一开端而来的抽象的、超时间的祖国,而开启着另一个开端即源初意义上的祖国,则还需继续论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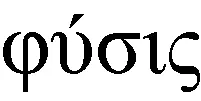
从希腊的“〈第一开端的历史〉乃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204)来看,“祖国”就是在希腊形而上学中伴随着技术对于存在者之自然的剥夺而走向没落的。这种剥夺被两种“袪自然化”(denaturiert)的陌异力量主导,“首先是经由基督教,自然第一次被贬降为‘受造物’”,其次是近代科学“机器技术的数学化秩序的力量”的消解(《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237)。海氏认为近代世界的本质是“‘制作性’的放纵”,它是由英国开始的,英国是美国主义和俄国主义的源头,犹太人则是“一切‘制作性’、‘计算性’的‘源头’、‘先锋’”(墨哲兰101)。当海氏将犹太人视作一切“制作性”“计算性”的源头,而有犹太主义之说时,他将英国视作“制作性放纵”的源头,也同样可以称其为英国主义。而海氏所批判的美国主义、俄国主义,都是从这种作为制作性或计算性的犹太主义和英国主义而来,是希腊形而上学第一开端发展而来的制作性与算计性垄断的结果。“沉落着的祖国、自然和人类”就是与犹太主义、英国主义、美国主义、俄国主义、基督教、自然科学的祛自然化相关。纠正这种从希腊第一开端形而上学而来的犹太主义的影响,就需要在德国作为另一开端中返回第一开端之前。
(二) 祖国作为“父亲之国”在“另一开端”中返回源初
海氏要克服荷尔德林所说的“祖国”的沉落,就必须到形而上学的终结处,到德国作为“另一开端”处去“经验存有之真理,并且追问真理之存有”(《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209)。希腊作为第一开端的形而上学导致了祖国的沦落,德国作为“另一个开端”的存有论真理和追问真理的存有根基,将重建一个全新的祖国,一个由诗人或国家奠基者创建的祖国。这个“祖国”不是宏大的爱国主义意义上的,“诗人指的是‘父亲之国’(Land der Väter)”,是“这片大地上作为历史性民族的民族,处于其历史性存在中的民族”。这个“历史性存在中的民族”就与源初意义上的“祖国”相关,是“植根于大地上的国家奠基者的行动和历史性空间”,“民族的这样一种历史性存有,祖国,依其本质始终锁闭于秘密中”(《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143)。海氏在此阐明了“祖国”和“民族”的关系,民族是一种历史性存有,祖国则是“我们”所指向的“历史性”“存有”的实现,是“自然”和“涌现”的“存有本身”,这样的“祖国”也才是诸神之到达和逗留的时机场所。祖国,即民族的历史性此在,才由此得以升起。
海氏从“另一开端”的存有之真理意义上返回源初的“祖国”建构,是具有艺术和审美意义的,它将与农人的生活、家乡的大地、诞生和涌现的自然的诗意相关联,打通了具体感受性的生存经验世界与超越性的存在本体世界的关系,回应着古希腊思想自身所具有的两重对立,即日神与酒神、明智与癫狂等诸如此类的对立。日耳曼德意志的祖国直接承继“前苏格拉底-赫拉克利特的基本精神”,它与犹太人所承继的“由巴门尼德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传统”相对立(倪梁康74)。海氏的“祖国”建构,批判了制作性、算计性和商业性思维,憧憬着在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开端之前的生成性、审美性和感受性的思想,那是和大地与鲜血所关联的令人悸动和震颤的力量。特拉夫尼指出,把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捆绑在一起的所有东西,都源自关于希腊的“第一次开端”和德国的“另一次开端”的叙事。这种叙事形成了海氏的“精神国家社会主义”,并与其所批判的“庸俗国家社会主义”相区别(特拉夫尼21)。
海氏在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后所作的题为《德国大学的自身主张》的讲演中,其所谈到的“领袖”(Führer)、“民族”(Volk)和“权力”(Macht)、“战斗”(Kampf)等纳粹流行语,既可看作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某种呼应,也体现出其在“另一开端”中对某种源初精神性力量的渴望。海氏看到,一种求知意志(Wissenwille)将民族带向一种最内在的和最极端的危险世界,“它乃是对一个民族的大地和血液之力量予以最深之保藏的权力,是对一个民族之此在予以最内在之激活与最辽阔之震动的权力”(《讲话与生平证词》143)。纳粹反对英国主义、美国主义乃至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技术和资本的文化,其与大地、鲜血和自然的内在相关性,或许让海氏看到了借此唤醒具有崇高性的德意志民族精神和国家的可能。当每个德国人都被这种崇高性和本根性精神震动,而一扫自一战战败以来的颓败和萎靡情绪时,它就与海氏把一般存在者的自我遮蔽/去蔽的本性转移到人或民族即“此在”这个特殊的存在者身上的思路契合了。海氏对民族本根性的推崇,也有造成一种“新形而上学”的危险,即过于强化一种扎根于血缘祖先的“民族性”,他把德意志民族看作扭转自古希腊以来沉落的“天命”(Geschick)的承担者,认为“德国人”就是“把西方历史的最内在的重担,掷于自己面前,并扛到肩上”(《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译者引言3)。海氏将这种源自“天命”意识的存有论的“祖国”建构,看作希腊作为第一开端的形而上学终结和德国作为另一开端的源初性返回,而这就或明确或隐蔽地否定着作为另一个欧洲传统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并导致它被纳粹利用的可能。
二、 从时间出发以寻找德国精神:海德格尔反犹主义的根源与危机
在早期的《存在与时间》中,海氏强调从时间来领会存在,指出生存论的本真时间与时间性相关,它不同于流俗的物理或钟表时间,而“是在此在的本真整体存在那里、在先行着的决心那里被经验到的”(《存在与时间》416)。在中后期,海氏更多从诗歌、艺术、民族和国家等来具体进入一种生存论的本真整体时间,探讨了“诸民族的历史性时间作为创造者的时间”问题,认为民族的历史性此在“乃是诗人、思想者和国家缔造者的时间”(《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62),“源初地经由诗人得到创建”,“国家创立者”“规定着民族之本质(seinem Wesen zu-bestimmten)”(171)。诗人、国家创立者,就是荷尔德林这样的哲人或诗人,是从古希腊-日耳曼德意志的“正传统”而来,是承继着赫拉克利特等前苏格拉底哲人的具有伟大开端性质的创造者。
(一) 创造者时间奠基德国精神
在海氏看来,诗人或国家创立者真正创立和奠定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性此在”,并确立着民族的“基础情调”。海氏关于民族的“基础情调本身必须首先得到唤醒”(《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173—174)的论说,在对历史性时间的自觉和反对算计性时间中,呼应了“祖国”作为“存有本身”的“大地和自然”思想,而犹太主义则被看作对这种“基础情调”的致命的威胁:“‘算计计算’(Rechnen)和‘倒卖放贷’(Schieben)的‘坚韧的熟练灵活性’(Geschicklichkeit)以及他们的混合。正是它们奠基了犹太人的无世界性。”(转引自特拉夫尼27)“基于他们强调算计计算的天赋,犹太人很早就按照种族原则‘生活’了”,但随后又“通过制造伎俩对生活的高度控制(Übermächtigung)”,“对人民进行的完全彻底的去种族化(Entrassung)”(25—26),让人民或种族弃绝了“父母之国”,失去了历史性时间,也即诗人和国家缔造者的时间。
海氏的“大地和自然”是对于历史性时间(创造者时间)的重新赢获,是回到非算计计算的第一开端之前。诗人、国家缔造者重建祖国作为存有本身的升起和沦落的历史性时间,于是,祖国作为民族历史性的此在,就不再是巴门尼德以来形而上学的存有/存在的那种绝对不变性,而是具有涌现和生成的生存论特征的整体性存在。荷尔德林在《大地母亲》中以“高耸而出”的“山脉”来比喻“创造者的时间”,也是作为祖国精神的时间,“超越于在日常的平面性中仓促时日的单纯相继”,“是从大地上高耸而出、有着本己的奔流和法则的时间。”(《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63)这种创造者时间孤独地直抵苍穹,直抵神性者的领域,它由此而成为一种内在时间。在另一首长诗《帕特莫斯》第3稿中,荷尔德林谈及“时间之巅”:“因此,那里常常[在明澈周围]环绕着/时间之巅”,这时间之巅有如山巅的聚集和指向穹苍,是创造者的居住地。在第2稿中,荷尔德林写道:“而至爱者[憔悴地]比邻而居在/相隔最远的山上……”(转引自《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63)海氏几乎是重述了这种至爱者的憔悴:“创造者立于山巅,肩负着使命及其创造之力——却‘憔悴地’处在相隔最远的山上。”(64)创造者退隐在至高的孤独中,不是在天赋平庸之单纯无能为力的意义上,而是在对独自承担的至高使命的完成或失败的意义上。
海氏所谈到的这种居于山巅的创造者“时间”是非大众化、非资本化的,它甘于孤独和憔悴,它与“神”比邻而居,是大地往下隐蔽(深渊)和向上显现(山巅)的一体性运作和聚集。诗人、创造者在这样一个时间维度上开展民族和祖国的创造,反对着犹太文化算计性的商业主义,渴望着生命力的一种强健和伟大。在海氏看来,世界犹太主义、英国主义、美国主义、俄国主义都是导致一种强健生命力量毁灭的毒素。犹太人不是具体现实的人,而是每个人都具有犹太人的元素,那就是:计算性思维、无根、无世界性;英国人就承继着这种犹太人的算计性基因元素:商业主义、贸易主义或货币主义。美国比英国更精于功利计算,科学技术更发达,故海氏干脆称其为美国主义,于是就有了英美和犹太的“犹太世界集团”之说,其核心标准就是“技术计算与制作”(墨哲兰44)。与犹太人、英国人的计算性、商业性不同的是,德国人的特点是:沉思性思维、家乡、本土性(74)。海氏反对犹太主义、英国主义、美国主义,重在批判资本、商业的算计性思维,有着在历史性时间中把德意志祖国孤独地隐藏于家乡和大地之纯洁的乌托邦梦想,而这也成就了海氏作为“存有本身”的“祖国”建构的审美性特征。
海氏认为,美国主义是犹太主义发展的顶点,而那种将世界(die Welt)视作资源的对象化的技术计算与制作的思维方式,将导致整个欧洲和德国精神的毁灭,其危害远甚于俄国主义。而这也就是海氏在1935年的一次讲课中所指出的:
如今,它遭遇来自俄国与美国两面的巨大夹击。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来看,俄国与美国二者是相同的,即两者对那无羁狂奔的技术和那肆无忌惮的庸民大众都有着同样的绝望式的迷狂。(《形而上学导论》44—45)
我们处在夹击之中。我们的民族位处中心点,正经受着最猛烈的夹击[……](《形而上学导论》44—45)
俄国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美国主义(资本主义)在本性上是一样的,即技术化的世界观,也就是犹太主义的表现形式,将造成攻击和摧毁欧洲中心点也即德国精神或某种基础情调的可怕危险。海氏期望有一种改变,即借助着从遥远的赫拉克利特等前开端的伟大希腊传统来对抗犹太传统,借助荷尔德林、里尔克、特拉克尔等作为先行者的德国诗人来对抗商业主义,正如其所言:“必须有先行者(Erstlinge)为这种改变情调的斗争而牺牲……那些诗人就是这样的先行者。”(《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174)诗人作为先行者的“时间”是“诸民族的源初时间”,它不同于“个体的可计算时间”(59)。个体的可计算时间是出生日期和死亡的数字的时间,但诸民族的源初时间是隐蔽的,它“超出而摆离(hinausschwingen)于他自己的时间及其可计算的当前(像诗人一样必须超出而摆离),并进入到自由域中”,而这就需要为了“本己的时间”而对“使自己出离于各个当前事物的时间”发起追问(61)。这样,海氏强调祖国的“大地和自然”主题,就始终有着一个返回神圣自然和历史性源头的向往,就是在反犹太化算计时间中复活一种作为存在(Sein)精神的德国精神,也实际就是一种乡土性的精神。
(二) 一双农鞋所隐含的创造者时间
海德格尔的“大地”和“自然”思想,作为一种以乡土性为特征的存在精神,在其将凡·高所画的其实是自己的鞋误认为农民的鞋而进行强制阐释时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积着那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眠。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的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这器具属于大地(Erde),它在农妇的世界(Welt)里得到保存。正是由于这种保存的归属关系,器具本身才得以出现而得以自持。(《林中路》20)
对于凡·高所画的鞋,海氏不是要进行文献学的客观考证,而是基于自身审美经验的鲜活艺术创造和生命时间的赢获。在海氏的阐释中,凡·高的鞋消失了,读者或观者被带到一双关于农妇鞋具的阐释中,这双农鞋赢得了其与大地和自然亲近的主人,不是作为主体论地位的主人,而是返回那种历史性此在时间和源初时间的成为世界守护者意义上的劳作者。凡·高的那两只鞋(甚至可能不是一双鞋),就被阐释为关联着穹苍、诸神和大地的农人的世界(Welt),它也是海氏后期思想关键词“Ereignis”所着重阐释的天、地、神、人的四元游戏,并由此而引入那种作为创造者时间的“存有本身”的“祖国”。这是一次成功的重释,它创造出了和凡·高的艺术品不同的另一个可能更为伟大的艺术品,它浸透着海氏所想象的德国农夫的世世代代的粗朴、原始、纯真和洁净,有着德国农民伫望田野的深情目光和坚实步履中的神圣祖国的到场,从而成为一种审美化虚拟性存在,也就是海氏所称道的:“一个存在者,一双农鞋,在作品中走进了它的存在的光亮中。”(《林中路》23)被海氏所阐释的一双绝妙的农鞋就在其进入光亮中照护着作为“存有本身”的神圣祖国了。
在对于这双农鞋的描述中,“时间”的维度异常丰富,那是诗人的时间、创造者的时间、历史性此在时间、生存论时间和源初时间的统一。海氏以“暮色”“冬闲”“分娩阵痛”“死亡逼近”等来标示一种创造者的时间。农妇的世界,就是诗人的具有历史性时间的创造,其中隐含着对于犹太主义、美国主义商业文化的警惕与对于德国的基础情调即大地和自然(德意志农人所象征的)的热爱。对于农鞋的诗意描述,就隐藏着欧洲文化内部的严重对立。当海氏从艺术和哲学上对于德意志农人的孤独的创造者时间和世界进行无限美化,而对于犹太主义、美国主义商业文化的可计算时间和世界抱持着无限恐惧之时,他就必然走入了他自己曾经所反对的二元对立的陷阱,而这种二元对立即使在他思想后期的“Ereignis”涵摄天、地、人、神的圆舞的世界(Welt)中也无法得到化解。资本和技术确然隐藏着危险,然而,难道只能通过回归大地与自然,才能消除这种危险么?与其螳臂当车式地反对资本和技术,为何不考虑何种资本和技术才当是更可以与大地和自然相亲,也与人相亲的?
海氏过于美化象征着大地和自然的德意志农人世界,寄望于反对犹太主义资本技术以实现对于祖国的存在论建构,实际是难以成功的。虽然,海氏将林中空地和敞显作为存在(指向此在、民族和祖国)的显现,强调从技术的对象化统治中解放个人,认识到形而上学是欧洲历史的根本特征,也期望从资本技术所腐蚀的危险中解放祖国,但这些言说都是植根于一个诸民族的源初时间和个体的可计算时间的严重二元对立之中。在这对立中,海氏所期望的个人和祖国的本质精神的自由,那存在的命运(Schicksal)或存在历史(真理的历史)就并不能真正自行发生。自由,作为林中空地的自身去蔽,就在海氏“大地和自然”与“资本和技术”的尖锐对立中被消解掉了,存在者进入匿名状态。海氏后期认识到其存在论哲学的问题,开始向东方哲学寻找资源,在老子和庄子那里找到了与敞显、林中空地相对或相反的阴性、遮蔽,他开始言说一种相反相成的敞显-遮蔽的双重运作。但因对东方哲学认识尚未深入,又无法将这阴阳对反相成的和谐思想用于其关于祖国的存在论阐释,这就导致了其关于祖国的审美化建构是无法完成的事业。
三、 缘在的牵挂:在希腊精神与犹太主义对立中建构审美化祖国的困境
缘在(Dasein)也译此在,其德语词“da”是个极为活泼和依语境而生义的词,有“那里”“这里”“那时”“于是”“但是”“因为”“虽然”“那么”“这个”多种意义,它“具有相互牵引、揭示开启、自身的当场构成”,它与其生存的空间和境域不可分,它是“有限的却充满了发生的契机等意义”(张祥龙94)。在《存在与时间》中,海氏指出:“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64)这个此在并不表达它是什么,而是表达其存在,总是我的存在,不是那种现成存在者,“此在总是从它所是的一种可能性”,从自身的存在和规定中领会到的一种可能性(66)。这就是海氏关于存在者存在的生存论建构,它不是那种日常的无差别相的平均状态。在中后期,海氏将“祖国”问题引入“缘在”或“此在”的基础存在论的分析中,强化了其在两个开端的对立中的不同的“祖国”阐释方向。
(一) 缘在重建祖国的基础存在论
海氏从此在或缘在基础上展开祖国的审美化建构,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其基础存在论抽空了生活和历史,造成了附着于大地和自然的德意志农人世界与掌握资本和技术的犹太主义世界的尖锐对峙。“世界犹太人”的“制作性”统治着这个世界。既然现代社会的本质就是被犹太主义或美国主义所导致的一种技术化或制作性宰制,从“存有本身”出发,海氏立足于其“大地”和“自然”思想以反对犹太-拉丁天主教对欧洲精神和德国精神的腐蚀,以重建德意志祖国的基础存在论,就水到渠成了。这样,海氏的德意志民族或祖国,就与其此在或缘在的基础存在论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密切关联了起来。
在海氏看来,“一个民族的真理乃是那种存在之敞开性,从这种敞开性而来,[……]它认识到它以历史性的方式所意求的到底是什么”(《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171)。这种历史性就是关联着从古希腊到德意志的一条隐秘的精神线索,海氏以希腊神庙为例阐发了一个历史性民族的世界(Welt):
正是神庙作品才嵌合那些道路和关联的统一体,同时使这个统一体聚集于自身周围;在这些道路和关联中,诞生和死亡,灾祸和福祉,胜利和耻辱,忍耐和堕落——从人类存在那里获得了人类命运的形态。这些敞开的关联所作用的范围,正是这个历史性民族的世界。(《林中路》29—30)
在这段话中,海氏彰显了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当他意识到德国民族的此在地基正遭受着来自俄国和美国的双重夹击时,他急切地希望唤起属于欧洲心脏地带也就是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性的精神力量”。然而,这种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性精神力量为何?它在抵抗资本和技术怪兽时,是否会变成另一头怪兽?当海氏呼唤这种历史性的精神力量之时,他强调人对其历史性生存的敞开与领悟,否定了古典形而上学的先于生存着的人的固定本质,看到了历史上关于人的本质主义的预设让我们陷入了泥潭。海氏由此提出了“领袖”的必要性问题,领袖似乎保证人在其历史性过程中展开和实现其本质。但作为历史性精神力量的“领袖”的规划,是否真能如海氏所愿,或者相反,即在一种现实政治实践中,实际的政治领袖却可能阻断人的本质的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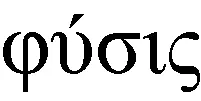
(二) 缘在将祖国召向幽然自闭的存在
在海氏那里,拉丁语和罗曼语及其关联的基督教中世纪,实际是犹太主义延伸出的产物。在诠释《加拉太书》第2章第16节时,海氏指出了基督教所蕴含的犹太或希伯来特征:“(基督教的律法)后来具有了一种新的基督教的含义。在此保罗的论证是希伯来的-犹太的-神学的。要把他的源本立场与这一观念区分开来。源于《旧约》的论证具有希伯来的特征。”(《宗教生活现象学》71)海氏声称要把受损害的欧洲精神重新“拽回”作为希腊形而上学的“第一开端”之前,认为犹太主义-基督教是希腊形而上学的延续,德国作为另一开端,是在形而上学终结处追问真理之存有,从而实现向古希腊哲学源头的返回,以对第一开端的形而上学误将“存在”(Sein)当作“存在者”(Seiende)的历史进行颠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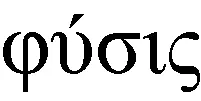
在这种强烈的外在区分中,海氏希望唤醒此在或民族的本己的良知,一种听的可能性,中断去“听”常人,中断去倾听美国主义和俄国主义(源自犹太主义)的声音。海氏指责“有些民族”的“蝇营狗苟”,“而却浑然不知其早已从存在处脱落”(《形而上学导论》44),这无疑表明了他对自己民族和祖国的伟大或精神性存在的肯定与自负,海氏借用里尔克等人的作品向我们揭显了德意志民族或祖国精神的“大地”和“自然”主题,强化了这种与外在敌人的对立。德意志诗人在这危机中以其本己的语言道说将人唤向本源的故乡,这就如诗人荷尔德林所吟唱的:“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出拯救。”(转引自《林中路》333)这种能自我拯救的唤向生命自身就是“良知”,是唤向人之存在或生存的此或缘,是与“敞开群山的脉络”和“它身后幽然自闭”的大地和自然对话。德意志祖国,于此就成为一个幽然自闭的存在,是在群山脉络里抵御着犹太主义、美国主义、俄国主义的孤绝之物。
四、 海氏“祖国”思想的伦理学反思:一种“大享”精神的缺失
海德格尔承接荷尔德林等诗人,从历史性和时间性维度上圣化着德国的大地、河流和森林。作为“存有本身”的德意志祖国,也由此成为人之最高存在的居所和庇护,是“父母之国”,是“家乡的大地”,是“民族的历史性时间”在诗人和国家缔造者创造中的实现。但海氏在否定犹太-基督教传统和肯定希腊-德意志传统中构建的历史性和精神性祖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对于家乡大地、本土性的退守和对于资本、商业和技术及其代表性文化和人群的拒斥,从而造成其通过两种开端重建审美化祖国的某种困境,即最终难以找到与具体他人或民族构建更大命运共同体的可能,也难以成就一种共享或大享文化精神。
(一) 在开端性建构中的伦理性不足
海氏在建基和开端意义上的“祖国”颇有近于汉语的“祖国”的含义。在汉语中,“祖国”的“祖”,从“示”,其表示与祭祀、宗庙有关。《说文解字》曰:“祖,始庙也。”段注:“始兼两义,新庙为始,远庙亦为始。”(4)这同样意味着双重开端,即故去的父母亲的新庙,是一个新的开端,它远绍那样一个最本源的开端,家族的始祖,第一个祖先。“祖国”的“国”,其初文为“或”,后写作“國”,本义为封邑、邦国。《说文解字》曰:“或,邦也。从囗、戈守其一。一,地也。”段注:“邦者,国也。盖或、国在周时为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既乃复制國字,以凡人各有所守,皆得谓之或。各守其守,不能不相疑,故孔子曰:或之者,疑之也。而封建日广,以为凡人所守之,或字未足尽之,乃又加囗而为國,又加心为惑。”(631)从文字演化看,“國”初作或,表示因始祖封邑而封邦建国。《说文解字》释:“國,邦也。”段注:“邑部曰:邦,国也。按邦国互训,浑言之也。《周礼》注曰: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国,析言之也。”(277)家族或始祖的封建,其小者为“國”,大者为邦,两者作为家族的封地,都是与祖庙的建制关联的,都蕴含有父母之邦、家乡的大地的含义,是子子孙孙应该守护和传承的亲缘土地和具有历史性的精神统绪。
于是,汉语的“祖国”虽是一个晚近概念,但从词源来说,却与祖先所居之地这样一个历史性时间密切关联起来了,它可以在宗庙和祭祀中被充分实现出来,它是血缘论、生存论和发生论的,又是在家族的精神性仪式中向未来延伸的,是自然性和精神性的统一。海氏所谈的德意志祖国却相对缺乏中国文化中源于祖先牵连着土地和历史的生存论维度,而只能相对抽象地言说“父母之国”或将德意志视作第一个开端终结中的“另一开端”。希腊-德意志这两个开端所缔造的传统实际遮蔽了犹太-基督教的传统,造成了德意志祖国在精神谱系上的断裂,导致了其“祖国”建构缺失了涵容具体“他者”的可能,从而成为抵抗资本与技术的幽然自闭的孤绝存在,它缺失了汉语哲学“祖国”概念的血缘性、发生性、绵延性和未来性维度的统一,更缺少了那种以“中庸”平衡“义”和“利”的和谐。
这样,我们就看到,海氏关于祖国作为此在(缘在)最高居所的阐释终究未能和具体生活事件联系起来,他将德意志的精神引向了希腊诸神、神庙和家乡土地、莱茵河、农夫所关联的那样一个不断涌现和沉落的神圣本真存在。但正如列维纳斯所言,这种存在论缺失了“面向他人之脸”那样一个难以被总体化的“无限”。海氏虽然也谈“共在”,但“它最终也是奠立在与存在一般的关系这个基础之上,奠立在(对存在的)理解的基础之上”,海氏把存在基础“确立为任何存在者都从中浮现出来的视域”,“交互主体性是共在,是一个先于自我和他者的我们,一个中性的交互主体性”(列维纳斯43)。在海氏那里,存在压倒了善,是中性化和无人称化的。列维纳斯将这一秩序颠倒过来,认为伦理学才是高于存在论的第一哲学,这就是“主体走向他人,超出自我主义的和孤独的享受”,“我对他者的欢迎,才是终极的事实”,物不再是被建造,“而是作为人们所给出的东西出现”(52)。
韩潮指出:“由于海德格尔让他人屈从于无名的存在,它‘无可避免地导致另一种权力,一种帝国主义的统治,一种暴政’”,“从列维纳斯对晚期海德格尔的批评可以看出,即便‘自我指涉’的嫌疑已经消除,海德格尔仍不得不为‘存在’的无人称和中性化而面临列维纳斯的指责”(153—155)。唯我论的影子在海氏的思想中始终挥之不去,他的诗意栖居似乎只是根本无“他人”在场的居留。列维纳斯从海德格尔缺失处开启他关于“家”和“居所”问题的思考,即人如何从自然的元素中退却,以自己的劳动享用这个世界,这种筑居会经历一个从占有(木材的获取),再到拥有(一个建筑成为我所属),最后到享有(我居于这样一个与世界的享用的快乐关系中)的过程。这种“享用”精神,在海氏的“Ereignis”的天、地、神、人的四元游戏中已然有所萌芽,但却还未真正成为海氏思想的主题,即当海氏的“此在”和“祖国”成为在群山脉络和家乡大地里幽然自闭的存在和孤绝之物时,一种面向他人的“享用”“共享”“大享”精神就难以实现。
(二) 一种“大享”精神的缺失
列维纳斯关于人的感性生命的“享受”和“享用”之思,海氏在“享用”或“共享”精神维度的缺乏,还可与中国文化中“享”的思想形成参照和互训。在汉语中,享的本字是“亨”,其字形像盛食物的器皿,意为进献,后写作“享”,表示享受。在《周易》中,亨也通于享。《文言传》受儒家影响,将《乾》卦卦辞“元亨利贞”释为四德(黄寿祺,张善文1)。20世纪,在殷墟甲骨卜辞问世以后,古文字学家发现了“贞”是卜辞前辞里的贞卜术语。易学家们遂重新释读了“元亨利贞”。较有代表性的是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释为:“元,大也。亨即享字。古人举行大享之祭,曾筮遇此卦,故记之曰元亨。利贞犹言利占也。筮遇此卦,举事有利,故曰利贞。”(1)元亨,也即大亨、大享。《周易》他卦如《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随》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益》六二“王用享于帝”,都是亨与享通,表示祭祀之名,既是人向神“献纳”“给出”美物和祭品,又是神“接纳”“享用”人之祭品(夏含夷4)。
易学重视人因敬畏天神、地祇、人鬼而心怀虔诚的献纳、给出以及神灵在与人往还中的接纳和享用,而人也在以神作为自己顶礼和敬畏的尺度中,反观自己与万物和他人的关系,而后可得自我所处的位置和秩序,而有伦理和礼仪的约束。故易之大亨、大享,就不单是世俗意义的享受,而是强调着人在祭祀神灵中的与其时位秩序的关联。由此,才有了儒家植根于仁义礼乐基础上的“大享”精神。同样,道家思想也有其大享维度,即重视人的无所为而沉浸于自然元素的感性满足,它以道和德为基础,而落实于现世人生长生久视的享用和享受,此即可谓道、德、享的三位一体。中国儒家和道家的“大享”精神充分体现了华夏民族较早走向人文自觉中对于“人”的现世生活的重视,学者常常将此视作实践理性或实惠文化,但我们在将其与西方哲学互训中,将其提炼为“大享”精神,从而可以避免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导往功利主义方向的偏弊,而凸显其天、地、人或道、德、享的三维关联。这种中华文化或中华美学的“大享”精神至为丰富,限于篇幅,当另文诠释。
海氏也曾经从老子和庄子那里汲取营养,如其1930年10月在不来梅所作题为《真理的本性》的演讲中就曾经引用德文本《庄子》中的“濠梁观鱼”,1946年又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张祥龙指出:“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观之间确有一个极重要的相通之处,即双方最基本的思想方式都是一种源于(或缘于)人生的原初体验视野的、纯境域构成的思维方式。[……]在世界思想史上,这种不离人生世间而又能构成尽性尽命、诗意盎然的澄明境域的思想方式是极罕见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引言13—14)“尽性尽命”就是“濠梁观鱼”中的鱼自得其乐和“大树无用”中的个体逍遥自得,它与海氏“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思想及其后期思想关键词“Ereignis”所蕴含的“天地神人”映射的四元游戏相通,已有近于中华美学的“大享”精神。这种“享用”精神也蕴含在海氏对于“祖国”的审美性建构中,如其引用荷尔德林《片断》:“对于至高者我欲沉默不言/禁果,如同桂冠,却/最是祖国。但每一个人/终会将其品尝”(转引自《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3)荷尔德林把“祖国”比喻为诱人的“禁果”,每一个人都将其“品尝”,这就是具有非常强烈的感性体验特征和“享用”意味。
从“禁果”之喻来看,“祖国”不能被庸俗化为某种宏大爱国主义或现世国家政权,而只能是精神之物,孤绝而只能被此在的最高精神抵达。“祖国”就被海氏视作“最高”“最艰难”“最终之物”“最初之物”,这样一个存在论上的祖国承载并构造着“在此存在着的民族的历史”(《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144)。但这样一个“祖国”因过于孤绝,因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拒绝和他人的缺失而呈现出新形而上学再本体论化的弊端。在晚年,海氏有重新理解犹太-基督教“上帝”的倾向,这就是他在最后岁月中接受《明镜》记者采访时所说:“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这里明确用了犹太-基督教的“上帝”一词,而不是希腊式的“诸神”,虽然海氏未予特别阐发,但或许,他在综合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化中尝试引入温润的精灵化元素:“留给我们的唯一可能是,在思想与诗歌中为上帝之出现准备或者为在没落中的上帝之不出现作准备;我们瞻望着不出现的上帝而没落。”(《海德格尔选集》1306)虽然还缺乏他曾经学习的东方文化中的那种“大享”精神,但也表明一种从思想和诗歌的双重维度来拯救存在的可能,意味着海氏开始超越德意志民族和祖国,而朝向人类之迷途及其拯救的未来之思。
小 结
综合看来,海氏的思想,虽然有从前期到后期的变化,有提倡此在(缘在)与他人共在,但终究缺少了某种具体性,缺少了在生活中与他人的共情基础。相较而言,海氏的思想还缺少了中国儒家和道家的“享”所关联的仁、礼、道、德的伦理性和普遍性,也缺少了列维纳斯从自我与他人关系中所阐发的筑造可亲的家和居所的享用精神。海氏的作为“存有本身”的祖国在农人、诗人的“自然和大地”中幽然自闭,自足圆满,这可能造成一种总体化和同一化以吞噬他人的危险。列维纳斯指出我们的存在就是一种占有,从而当深怀一种导致他人无法出场的“不安”意识,只有当我们面对他人之脸时,那种面对无限性无法被我们同化的“不安”意识,才会出现(朱刚114—124)。“面容抵制占有”,在面向他人之脸中,主体向着无法被同一化的无限超越,从而抹去自身、丧失自身,在家的筑居中,就不再是此在(缘在)的个体,而是一种父子关系的生成,作为主体的父亲在生育和超越中,转向了儿子,列维纳斯由此论证出了“我是我的孩子”的命题。海氏悬置了人与人之间那种相互亏欠着的、需要偿还的“不安”意识,也就缺失了人向着他人之脸的更为本源的伦理性关系,那种“我是我的孩子”的溢出我之现在的将来维度。故而,海氏的祖国和民族虽然建基于个体此在共属的自由之基础,但其关于人的伦理责任的实践却付之阙如,而该问题在我们当代中国民族文化的自我建构中无疑是应当予以警醒的。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Gao, Heng. The Book of Change:TheOldClassicwithaNewExegesis.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0.]
韩潮:《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
[Han, Chao.HeideggerandEthicalProblems.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07.]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Heidegger, Martin.BeingandTime. Trans. Chen Jiaying and Wang Qingji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ContributionstoPhilosophy(FromEnowning). Trans. Sun Zhoux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林中路》,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OfftheBeatenTrack. Trans. Sun Zhoux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张振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Hölderlin’sHymns“Germania”and“TheRhine.” Trans. Zhang Zhenhu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
——:《形而上学导论》,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IntroductiontoMetaphysics. Trans. Wang Qingji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宗教生活现象学》,欧东明、张振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PhenomenologyofReligiousLife. Trans. Ou Dongming and Zhang Zhenhu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
——:《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SelectedWorksofHeidegger. Ed. Sun Zhouxing.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讲话与生平证词》,孙周兴、张柯、王宏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SpeechesandOtherTestimoniesofaLife’sCourse. Trans. Sun Zhouxing,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
黄寿祺 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Huang, Shouqi and Zhang Shanwen.TheTranslationandAnnotationofThe Book of Change.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9.]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Levinas, Emmanuel.TotalityandInfinity. Trans. Zhu Ga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墨哲兰:《我对〈黑皮书〉事件的态度——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读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Mo, Zhelan.MyAttitudetowardstheBlack NotebooksIncident—ReadingsofPeterTrawny’sHeidegger and the Myth of a Jewish World Conspiracy.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9.]
倪梁康:《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关系史外篇:反犹主义与纳粹问题》,《现代哲学》4(2016):66—80。
[Ni, Liangkang. “Heidegger and Husserl: Anti-Semitism and Nazism.”ModernPhilosophy4(2016):66-80.]
夏含夷:《〈周易〉“元亨利贞”新解——兼论周代习贞习惯与〈周易〉卦爻辞的形成》,《周易研究》5(2010):3—15。
[Shaughnessy, Edward L.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Yuan Heng Li Zhen’ in the Zhouyi.”StudiesofZhouyi5(2010):3-15.]
彼得·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靳希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
[Trawny, Peter.HeideggerandtheMythofaJewishWorldConspiracy. Trans. Jin Xip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
许慎:《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1年。
[Xu, Shen.NotestoExplanations of Characters Simple and Complex. Ed. Duan Yucai.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1.]
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
[Zhang, Xianglong.Heidegger’sThoughtandChina’sCelestialWay:TheOpeningandIntegrationoftheUltimateVisio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张振华:《诗歌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与维系——海德格尔第一次荷尔德林讲课的核心问题与思路》,《文艺理论研究》3(2019):197—206。
[Zhang, Zhenhua. “Poetry and the Gen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National Community: The Core Issue and Line of Thinking in Heidegger’s First Lecture on Hölderlin.”TheoreticalStudiesinLiteratureandArt3(2019):197-206.]
朱刚:《不安意识作为原意识——再论列维纳斯的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哲学研究》11(2019):114—124。
[Zhu, Gang. “Bad Consciousness as Original Consciousness: On Levinas’s Ethics as First Philosophy.”PhilosophicalResearch11(2019):114-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