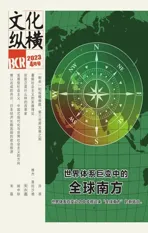脆弱的地区纽带
——石油租金与阿拉伯政治经济秩序的演变
2023-06-16李海鹏
李海鹏
作为全球为数不多的共享跨国民族认同的国家集团,阿拉伯世界既没有形成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经济地理单元,也没有出现类似20 世纪80、90 年代亚太地区“雁行模式”那样的产业分工体系,而是基于石油租金的政治性外溢形成了一个区域经济体系。[1]该体系对阿拉伯富油国(如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贫油国(如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的战略行为、国内政治经济和地区权力结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前国内外学界对阿拉伯地区秩序的研究多侧重于地缘政治博弈的视角,对区域经济影响的分析相对不足。本文以1971 年以来的油价波动周期[2]为时间线索,考察阿拉伯区域经济体系的起源、构成、演进,及其与地区政治秩序之间的互动。
阿拉伯区域经济体系的形成(1971~1997)
“阿拉伯之春”爆发前近四十年里,阿拉伯世界始终维持着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沙特-埃及政治轴心与石油租金的跨国流动,构成这一秩序的两大支柱。
“阿拉伯之春”爆发前近四十年里,阿拉伯世界始终维持着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沙特-埃及政治轴心与石油租金的跨国流动,构成这一秩序的两大支柱,其根源可追溯至冷战时期特定的地区和国际政治环境。
1973 年和1979 年两次石油危机、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等事件,大大提升了阿拉伯富油国对于西方战略、能源和金融安全的重要性。1967 年阿以战争埃及、叙利亚遭遇惨败后,沙特终于在1970~1974 年与埃、叙两国新领导层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尽管之后地区局势和阿拉伯国家间联盟关系经历多次波折,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富油国始终将埃及等核心贫油国视为平衡地区和国内安全威胁的重要合作伙伴,以资本优势弥补物质权力弱势,最终在冷战和海湾战争结束初期实现了两大国家集团之间权力的整体均衡。
在上述进程中,海湾阿拉伯富油国面向贫油国逐渐搭建起援助、侨汇、贸易三大经济纽带,以之为杠杆撬动与特定国家关系的调整和地区权力平衡的转移,也奠定了一种独特的区域经济体系。首先是以赠款和优惠贷款为主要形式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尽管不同时期有所波动,以沙特、科威特为代表的阿拉伯富油国始终是阿拉伯贫油国外部援助的主要捐赠国。1970~2004 年,官方发展援助平均占埃及、约旦国民总收入(GNI)的6.79%和15.36%,而阿拉伯国家分别占两国接收援助总额的30%和56%,在叙利亚则高达84%。同期,叙利亚、埃及、约旦三国分别吸收了阿拉伯捐赠国对外援助总额的24%、22%和16%。[3]
其次是阿拉伯外籍劳工及其侨汇收入。20 世纪70~90 年代,鉴于自身劳动力短缺的现实以及地区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改善,海湾富油国开始执行相对自由的劳工政策。从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前夕至1975 年,阿拉伯国家内部移民劳工数量由68 万猛增至130 万,1975 年阿拉伯移民劳工占海湾国家外籍人口的72%。尽管此后这一比重不断下降,但富油国内阿拉伯移民劳工整体规模仍呈上升趋势。[4]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是海湾国家阿拉伯外籍劳工的最主要来源国,侨汇收入在上述国家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埃及为例,1977~1999 年官方侨汇收入平均占埃及GDP 比重的8.89%,而1999 年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国家占据埃及全部侨汇收入的49%。[5]
最后,区域贸易的纽带。阿拉伯国家间贸易同样在20 世纪70~90 年代迅速扩大,但表现出低水平波动、地域集中和不平衡依赖等特点。阿拉伯国家间出口占其出口总额比重由1970 年的5.2%升至1990 年的9.4%,至1995 年又降至6.7%,明显低于其他重要的区域经济集团。1998 年阿拉伯国家间出口中约60%流向海合会国家,最依赖区域内贸易的埃、约、叙、黎、苏丹五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22.7%,其中10.2%流向了海湾富油国。[6]可见,至20 世纪末,阿拉伯世界已建立起一套独特的区域经济体系,石油租金通过上述三大纽带实现了从富油国到贫油国的“涓滴效应”。
基于援助、侨汇、贸易等纽带的区域经济体系,从三个层面奠定了当代阿拉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石。
基于援助、侨汇、贸易等纽带的区域经济体系,从三个层面奠定了当代阿拉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石。国际层面,冷战后期美国通过与海湾富油国之间的合作,成功分化和弱化了中东亲苏阵营,囊括了核心富油国和贫油国的亲美集团也成为后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地区单极霸权的支柱之一。地区层面,海湾富油国以经济权力优势弥补军事、政治权力弱势,最终围绕埃及-沙特轴心实现了两大国家集团间整体的权力均衡。国内层面,基于与贫油国的政治合作、盟友关系以及相对稳定的地区环境,富油国在20 世纪70~80 年代大大推进了国内的制度建设,也奠定了基于高福利体制的根基。对贫油国而言,海湾国家援助、侨汇的涌入和本国石油收入的增加,确保其在70 年代能够暂时回避结构性经济改革和人口控制的压力。80 年代中后期经济衰退、失业率、外债等问题在贫油国全面爆发时,又是海湾战争期间来自富油国的战略性援助以及随后的低油价,帮助埃及、叙利亚等国政府获得喘息之机,继续艰难维系着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7]

海湾资本与贫油国新兴裙带资本集团之间的共生关系,加剧了贫油国内部的不平等现象
然而,这一区域经济体系从一开始就显露出明显的内在缺陷。首先,富油国与贫油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这也决定了两者间经济关系易被政治化、安全化。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期间,海合会国家和伊拉克已开始将援助和侨汇用作向叙利亚、也门、埃及和巴解组织施压的权力资源。[8]
其次,在既有发展模式下,富油国和贫油国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的逻辑蕴涵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富油国的财政和国际收支平衡严重依赖油气出口收入,而贫油国政府对民众的巨额能源、食品补贴以及国内能源消耗的快速增长,决定了其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有赖于相对稳定的低油价。长期来看,依靠石油租金从富油国向贫油国的“涓滴效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
最后,外部强力支撑下的权力与财富失衡。1965 年埃及国民生产总值(GNP)是沙特的近3 倍,至1977 年埃及占阿拉伯世界GNP 的比重已从1965 年的23.4%降至7.9%。2004 年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四国经济能力都超过埃及,而同期阿拉伯世界军事能力最强的五国则是埃及、叙利亚、沙特、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9]非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可能有助于软化这种经济-军事权力的失衡,但正如海湾战争所揭示的,美国对富油国的安全保障才是维持这一状态的根本支柱。在海湾战争后近40 年的时间里,随着阿拉伯富油国与贫油国之间的经济纽带不断发展变异,既有地区秩序中的结构性缺陷也时隐时现,最终在“阿拉伯之春”中全面爆发。
富油国的财政和国际收支平衡严重依赖油气出口收入,而贫油国政府对民众的巨额能源、食品补贴以及国内能源消耗的快速增长,决定了其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有赖于相对稳定的低油价。
海湾资本扩张与阿拉伯地区秩序的崩塌(1998~2010)
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迅速席卷全球。不同于前一时期,外国直接投资(FDI)在阿拉伯国家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迅速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石油资本扩张需求与地区政商环境变化之间的契合与共谋。
1998 年以来全球油价进入新的上升周期,海湾富油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和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显著提升。考虑到“9·11”事件后西方市场的投资风险、投资回报率等因素,海湾富油国投资主体选择将相当一部分剩余资本投向阿拉伯贫油国。在富油国内部,20 世纪80 年代末期以来,不同海湾国家王室成员开始大规模涉足经济领域,海湾“国家资产阶级”和私营资本迅速扩大资本输出。在同期的贫油国,执政家族权力继承的考量逐渐主导了埃及、叙利亚等国的政治生活,新生代权力精英试图借助经济自由化改革巩固其社会支持基础,因此将吸引外国投资树立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在国际、地区和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快速变化的背景下,阿拉伯富油国与贫油国之间的非对称经济依赖在投资领域迅速深化。
2003~2009 年,海湾国家在约旦、黎巴嫩、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的FDI 总额高达692 亿欧元,同期欧洲和北美在上述五国的投资分别为229 亿和52 亿欧元。海湾投资在2007 年分别占埃、约两国FDI 的25%和35%,2008 年在叙、黎两国则占70%以上。[10]
从投资领域来看,海湾资本在阿拉伯贫油国的四大关键领域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第一,房地产及相关上下游行业。海湾财团通过直接参与竞标、控制投资对象国公司少数股份、参与公私合营(PPP)项目等方式,深度渗透埃及、阿尔及利亚、约旦、摩洛哥、黎巴嫩、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第二,通信服务业。上述八国全部26 家手机服务商中的14家全部或部分地为海湾财团拥有,海湾国家通信公司控制着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突尼斯等国移动通信市场的最大份额。第三,金融服务业。通过直接建立分支机构、企业并购等方式,海湾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阿拉伯贫油国的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业务。2006~2015 年,上述八国和也门金融部门接受的外国投资总额为143 亿欧元,其中海湾国家占据65%。在黎巴嫩、约旦、埃及、突尼斯、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海湾相关银行占据所有上市银行总市值的57%。第四,食品和农产品行业。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国企业通过土地收购、建立分支机构、合资或入股等方式,在苏丹、埃及等贫油国农产品生产、销售、物流、储藏等环节占据重要份额。[11]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投资深化的背后既有资本扩张自身的逻辑,也有权力精英政治考量的印记。无论是海湾国家出于本土粮食安全考量支持私营企业收购、投资邻国农业用地,海湾财团在房地产、通信等新的寻租领域与贫油国新兴裙带资本及其背后新生代权力精英的深度合作,还是海湾商业银行向埃及、黎巴嫩等国政府的大规模贷款,实际上都体现了资本积累与政治投资逻辑的相互补充。私人资本控制下海湾企业的投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都反映、顺应和利用了海湾国家王室的政治意志和现实经济利益。
对阿拉伯贫油国而言,海湾资本短期内的快速扩张配合其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共同催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经济后果,最终撼动了已维系四十年之久的阿拉伯地区秩序。
对阿拉伯贫油国而言,海湾资本短期内的快速扩张配合其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共同催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经济后果,最终撼动了已维系四十年之久的阿拉伯地区秩序。从受益者的角度来看,海湾资本与贫油国新兴裙带资本集团之间的共生关系,为后者的积累财富提供了便利,加剧了贫油国内部的腐败和不平等现象。在埃及,有政治背景的大型公司在银行信贷中占据绝对优势,22 家此类企业占据了全部122 家大型上市企业银行负债总额的92%。考虑到海湾资本相关的银行占据埃及银行部门总资产的约30%,其对埃及裙带资本集团的支持显然不容忽视。[12]除间接挤压中小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之外,沙特、阿联酋巨型财团还利用与投资对象国权力精英的关系,低价收购该国国有土地和资产,类似跨国权钱交易引发的民愤2011 年初就曾在埃及全面爆发。[13]
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海湾资本涌入为贫油国政府深化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提供了强大助推力,原来构成政权支持基础的中低收入群体则成为改革的最大受害者。为推动农业用地商品化,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埃及、叙利亚政府先后大幅修订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租赁相关的早期立法,导致大量小农失去土地。黎巴嫩、约旦政府则修订了一系列规管房屋租赁者与所有者关系的法律,通过默许驱逐租户为城市地产开发商移除了最重要的障碍。另一方面,海湾资本向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的聚集,加剧了阿拉伯贫油国产业结构的资本深化倾向,对相关国家就业和贫困问题的解决却贡献乏力。在埃及,海湾资本的涌入,并未推动埃及政府发展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并提供稳定就业机会的制造业。投资最密集的房地产业无法提供稳定就业,且难以吸纳受过高等教育的庞大青年群体,金融和通信服务业的创造就业能力则更有限。结果,海湾投资的受益群体高度集中,受害群体却非常庞大,催生的仅是相关国家“无发展的增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富油国油气收入的“涓滴效应”曾长期是贫油国维系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但同样来自富油国的资本扩张,却间接引发了贫富差距增大、弱势群体不满、特权群体腐败等问题,缓慢动摇了贫油国的社会稳定,最终导致冷战后阿拉伯地区秩序在其经济薄弱环节贫油国的崩塌。
海湾资本涌入为贫油国政府深化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提供了强大助推力,原来构成政权支持基础的中低收入群体则成为改革的最大受害者。
地区秩序主导权争夺战中的“经济大棒”(2011~2017)
2010 年末爆发的“阿拉伯之春”,暂时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以及海湾资本在阿拉伯世界的扩张势头。随着政治动荡迅速从突尼斯蔓延至整个地区,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富油国同时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和复杂机遇。
一方面,阿曼、巴林和也门政局的动荡乃至更迭,对海湾富油国政权安全构成重大威胁;重要的地区盟国埃及、约旦、摩洛哥、突尼斯前途未卜,西方式民主选举很可能会将这些国家的政治伊斯兰势力送上台;伊朗、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势力介入使得地区博弈复杂化;奥巴马在埃及抗议活动爆发尚不足一周时就抛弃了与美国已有三十年友谊的穆巴拉克政府,这一立场引发了沙特、阿联酋等国领导人的愤怒和恐慌。另一方面,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传统阿拉伯强国在此轮变局中遭受重创,阿拉伯世界出现明显权力真空;叙利亚政权的存亡则将直接决定伊朗及其地区阵营的影响力。2013 年10 月,长期主管沙特情报部门的图尔基·本·费萨尔亲王在一次讲话中表示,沙特将需要应对伊朗在伊拉克、巴林、科威特、黎巴嫩、也门、阿联酋和叙利亚等国“干预和破坏稳定的行为”。[14]2011~2017年,正是基于对上述新挑战与战略机遇的认知,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富油国一改以往维持现状的地区政策,转向更为积极甚至带有进攻性的现实主义外交。
经济权力优势一直是海湾富油国推行其外交政策的重要杠杆,这一轮政策调整也迅速反映在富油国经济外交政策的一系列转向之中。第一,与前一时期相比,“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富油国将与贫油国之间既有的经济纽带全面政治化,政治性转移支付的重要性空前凸显。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富油国通过“生存性对外援助”稳定海湾地区穷国(巴林、也门)和其他贫油君主国(约旦、摩洛哥)的政治社会秩序,避免动荡波及海湾地区。对突尼斯、埃及等转型中的共和制贫油国,富油国则通过许诺和控制“战略性对外援助”的流入,寻求影响两国转型进程,进而试图主导地区格局的重塑。2011~2014 年穆兄会候选人穆尔西当选总统、执政和被推翻前后,上述海湾富油国对埃及援助的流动变化,反映出该时期海湾国家经济外交的高度政治化趋势。[15]对黎巴嫩等立场摇摆国家,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巴林等国在2011~2016 年则多次采取中止军援、威胁驱逐本国黎巴嫩籍劳工、宣布旅行禁令或减少航班等措施,以外援、侨汇、服务贸易收入为杠杆向黎政府和真主党施压。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富油国将与贫油国之间既有的经济纽带全面政治化,政治性转移支付的重要性空前凸显。
第二,在政治性支付转移中,直接在央行存款超越传统的赠款、贷款、优惠能源产品等方式,成为这一时期海湾富油国向贫油国施加政治经济影响的最重要杠杆。这一点在埃及表现得最为明显。2011 年以来,海湾富油国不断承诺向埃及央行注资,2014~2016 年,海湾国家在埃及央行存储的金融资本已从70 亿美元猛增至168 亿美元。海湾国家存款占埃及政府外汇储备相当大的比例,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埃及政府在危机情况下进口商品、调节汇率、刺激流动性的能力;海湾国家一旦提取存款,必然导致埃及金融市场爆发严重危机。上述变化无疑大大强化了海湾富油国对埃及政府政治经济决策的影响力。[16]

“阿拉伯之春”暂时打破了海湾资本在阿拉伯世界的扩张势头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的最初五年,海湾阿拉伯富油国表面上提升了自身在地区政治中的影响力,但它们对贫油国政治进程的深度干预,却使贫油国、阿拉伯世界乃至海合会国家内部呈现出弱化和分化的态势。在“阿拉伯之春”爆发的几年里,国际油价仍处于上升阶段,海湾国家得以将大量资源投入地缘政治博弈,却因此错过了对国内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又一窗口期。地区权力结构失衡的潜在风险,也终因油价在2014 年后进入下滑阶段而全面爆发。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的最初五年,海湾阿拉伯富油国表面上提升了自身在地区政治中的影响力,但它们对贫油国政治进程的深度干预,却使贫油国、阿拉伯世界乃至海合会国家内部呈现出弱化和分化的态势。
阿拉伯区域经济何去何从?
2014 年下半年起国际油价开始经历断崖式下跌,自2016 年跌至最低点直至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长期在低于80 美元/桶的低位徘徊。油价暴跌和前一阶段扩张性财政政策叠加导致的财政压力,地缘政治博弈带来巨大的资源消耗,美国政府在中东地区收缩态势的延续,以及全球能源转型的根本挑战,迫使海湾富油国自2015 年起整体将政策重心转向国内经济改革,在地区军事和政治博弈中的经济资源投入趋于减少。在这一背景下,既有区域经济体系中的联系纽带、经济关系的强度乃至整个体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海湾富油国间的同质化经济竞争正愈演愈烈
单纯从数据来看,2015 年以来,阿拉伯富油国与贫油国之间的四大传统经济纽带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波动和弱化。其中,侨汇和贸易的总体波动较小,投资和援助的波动或降幅较大。其一,侨汇方面,从海湾几个主要侨汇寄出国的侨汇外流规模来看,沙特在2015 年后明显减少,阿联酋在2010~2019 年持续增长,科威特和卡塔尔平稳波动。从贫油国侨汇流入规模来看,埃及侨汇收入在2015 年后继续增长,但约旦、黎巴嫩侨汇流入在2015~2016 年后明显减少。[17]其二,贸易领域,贫油国向富油国的出口出现波动,进口基本平稳。2011~2019 年,向海合会国家出口占埃及、约旦出口比重,相比前一时期(2003~2010)显著增加。[18]尽管2016 年后出现明显下滑,但贫油国的非石油商品出口、服务出口和石油产品进口的需求,继续将其与富油国经济密切绑定。[19]其三,阿拉伯国家间外国直接投资波动较为明显。经历前期的平稳增长后,阿拉伯国家间FDI 项目投资由2016 年的202 亿美元猛跌至2017年的106 亿美元,2018 年迅速增至253 亿美元,之后再次回落。同期,埃及、约旦等贫油国获得的投资份额基本保持稳定。[20]其四,富油国对贫油国官方发展援助明显下降。如沙特对外援助和贷款自2015 年起明显减少,2020 年规模仅为2014 年峰值时的33%。沙特、阿联酋两国对外赠款也从峰值骤跌,并直接反映在埃及等地区受援国获得的官方赠款数额之中。[21]
上述变化,是2014 年下半年油价进入下降阶段后,阿拉伯区域经济中两个相反的发展趋势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一个趋势是地缘政治博弈驱动下区域经济的碎片化和“去区域化”。一方面,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严重动摇了海合会国家的政治互信与经济一体化进程。海湾地区原本是阿拉伯世界内部经济一体化相对较为成功的次区域,2001 年海合会经济协议第3 条规定了各成员国公民、货物、资本可在地区内部平等地自由流动。然而,2017~2021 年沙特、阿联酋等国针对卡塔尔的全面封锁,严重破坏了海湾经济一体化的既有成果,也动摇了成员国尤其是小国对海合会政治和安全机制有效性的信心。尽管危机在2021 年初告一段落,海湾富油国间的同质化经济竞争却愈演愈烈:海合会国家纷纷投资油气新产能,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布局,争夺地区金融、航运、娱乐、旅游业中心地位,抢占外国投资和就业机会。
海湾富油国延续高度政治化、竞争性的经济外交,也造成阿拉伯区域经济网络的割裂和阵营化。
另一方面,海湾富油国延续高度政治化、竞争性的经济外交,也造成阿拉伯区域经济网络的割裂和阵营化。在突尼斯、埃及等重要转型国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三国继续在经济外交领域进行缠斗。2021 年7 月突尼斯总统赛义德宣布暂停议会活动后,阿联酋、沙特开始挑战卡塔尔在突尼斯经济中的主导地位。2022 年4 月,卡塔尔则连同沙特、阿联酋向埃及政府承诺提供220亿美元援助,试图平衡后两国对埃及影响力。[22]在黎巴嫩等立场摇摆国家,海湾富油国继续采取惩戒性经济外交,如2019 年对黎巴嫩经济危机持消极观望态度,2021 年10 月对公民赴黎巴嫩旅游和进口黎巴嫩商品采取限制措施。对面临战后重建但被敌对阵营主导的叙利亚,海湾富油国则拒绝任何实质性的经济投入。经济关系的高度政治化,显然不利于阿拉伯贫油国管控经济危机、启动战后重建或平稳推动经济改革。
第二个趋势则是资本逻辑拉动下区域经济秩序的“再区域化”,表现为海湾大资本回归贫油国。为吸引海湾资本注入、推进经济改革进程,以埃及塞西政府为代表的贫油国政府迅速推翻了“阿拉伯之春”初期的多起反腐败、反资本垄断诉讼,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政策法规。这一转向也为富油国政府和大资本集团向贫油国的回归或扩张铺平了道路。2013~2017 年,在埃及、约旦、黎巴嫩、苏丹等国最大的投资项目中,沙特ACWA 国际电力集团、阿联酋Majid Al Futtaim Group、Al Habtoor Group 财团,科威特Zain 移动通信集团等海湾私营或国企巨头仍赫然在目。从产业分布的角度来看,2018 年阿拉伯国家间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63.6%)、油气煤(12.6%)和食品烟草(9.3%)等领域。[23]
可以说,当前阿拉伯世界的经济秩序仍在这两股力量——“去区域化”的地缘政治逻辑和“再区域化”的资本逻辑——的拉扯和重塑之中。
当前阿拉伯世界的经济秩序仍在这两股力量——“去区域化”的地缘政治逻辑和“再区域化”的资本逻辑——的拉扯和重塑之中。
结语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阿拉伯知识分子曾多次哀叹“泛阿拉伯主义”的衰亡,亦即阿拉伯政治精英在地区核心议题——遑论政治统一——上已不可能形成共识或合力。但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富油国石油租金通过多种渠道向贫油国的转移,让阿拉伯区域经济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整合。富油国和贫油国借此各取所需,维持了近四十年的脆弱地区平衡。然而,“阿拉伯之春”触发的安全危机和权力失衡,推动了地区国家间经济纽带的政治化和安全化,让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整合进程趋于停滞,在某些层面甚至发生倒退。长远来看,全球能源转型与美国从中东地区战略收缩的大势,意味着阿拉伯地区政治经济秩序未来可能面临推倒重建的灾难性挑战。2022 年初以来的俄乌冲突导致国际油价再次进入上涨和高位期,但只能延缓,而不可能逆转这一长期趋势。当然,阿拉伯富油国作为食利经济体的性质在中短期内不会改变,富油国与贫油国之间相互的政治经济安全需求仍在。考虑到地区权力格局达到新的平衡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阿拉伯区域经济体系不会完全“去区域化”,但“再区域化”逻辑在短期内也很难逆转区域经济碎片化、阵营化、政治化的趋势。
阿拉伯区域经济体系转型可能触发怎样的政治效应?假使海湾富油国在地区博弈中继续坚持当前“本国优先”的竞争性政治经济政策,帮助其贫油国盟友重建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放任战乱和摇摆国家沦为失败国家,后两组国家将很可能酝酿新的地区政治风险,富油国最终能否独善其身也存在疑问。
注释:
[1] “石油租金”(oil rent)的说法源于食利经济或食利国家(rentier state)理论,该理论是当前学界解读中东和非洲产油国政治经济的主导性范式。与依赖国内税收维持国家运转的大多数国家不同,食利国家政府在非常大的程度上依赖从外部世界直接获得的租金,这种租金可能来自石油天然气或其他矿产资源、战略资产、毒品生产和贸易等。
[2] “二战”结束后国际油价波动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1945~1971 年是稳定的低油价时期,1971~1981 年油价整体上行,1981~1997 年油价整体下行,1997~2014 年油价整体上行,2014~2022 年油价剧烈下行、短期震荡后趋于平稳。参见管清友:《国际油价波动的周期模型及其政策含义》,载《国际石油经济》2008 年第1 期。
[3] UN-ESCWA,Economic Trends and Impacts: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rab Region,2007, pp. 12~13; World Bank,“Net ODA received (% of GNI) - Egypt, Arab Rep.”; World Bank,“Net ODA received (% of GNI) - Jordan”.
[4] Saad Eddin Ibrahim,“Oil, Migration and the New Arab Social Order,”in Malcolm H. Kerr &El Sayed Yassin, eds.,Rich and Poor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Egypt and the New Arab Order,Westview Press;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82, pp. 23~25.
[5] World Bank,“Personal remittances, received (% of GDP) - Egypt, Arab Rep.”; M.I.T. El-Sakka,“Remittances of Egyptian Migrants: An Overview,”Middle East Institute, April 18,2010.
[6] Hassan Al-Atrash and Tarik Yousef,“Intra-Arab Trade: Is It Too Little?”IMF Working Paper, No. 00/10, 2000.
[7] Onn Winckler, “The ‘Arab Spring’: Socioeconomic Aspects,”Middle East Policy, Vol. 20,No. 4, 2013, pp. 69~71.
[8] Sonoko Sunayama,Syria and Saudi Arabia: Collaboration and Conflicts in the Oil Era,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07, pp. 122, 219~222; Helene Thiollet,“Migration as Diplomacy: Labor Migrants, Refugees, and Arab Regional Politics in the Oil-Rich Countries,”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Vol. 79, No. 1, 2011, p. 108.
[9] Paul Noble,“From Arab System to Middle Eastern System? Regional Pressures and Constraints,”in Bahgat Korany and Ali E.H. Dessouki, eds.,The Foreign Policies of Arab States: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8, pp.116~118.
[10] Adam Hanieh,Capitalism and Class in the Gulf Arab States, Palgrave Macmiillan, 2011, p.151.
[11] [16] Adam Hanieh,Money, Markets, and Monarchies: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pp. 139, 157, 164~168, 186~188;pp. 260~261.
[12] Ishac Diwan, Philip Keefer, and Marc Schiffbauer,“The Mechanics, Growth Implications,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Crony Capitalism in Egypt,”in Ishac Diwan, Adeel Malik and Izak Atiyas, eds.,Crony Capit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Business and Politics from Liberalization to the Arab Spr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77.
[13] Yasmine Farouk,“More than Money: Post-Mubarak Egypt, Saudi Arabia, and the Gulf,”GRC Gulf Paper, April 2014, p. 13.
[14] Turki Al Faisal bin Abdul Aziz Al Saud,“Saudi Arabia’s Foreign Policy,”Middle East Policy,Vol. 20, No.4, 2013, pp. 38~39.
[15] 张帆:《海湾君主国对中东国家对外援助动因的发展变化》,载《西亚非洲》2016 年第1 期;Yasmine Farouk,“More than Money: Post-Mubarak Egypt, Saudi Arabia, and the Gulf,”GRC Gulf Paper, April 2014, p. 15。
[17] Central Bank of Egypt,Economic Review, Vol. 58, No. 4, 2017/2018, p. 66.
[18] WITS,“Egypt, Arab Rep. Export/Import Partner Share by country in percentage 2011-2019”, “Jordan Export/Import Partner Share by country in percentage 2011-2019”.
[19] Central Bank of Egypt,Economic Review, Vol. 58, No. 4, 2017/2018, pp. 74~75; Central Bank of Egypt,Economic Review, Vol. 59, No. 4, 2018/2019, pp. 78~79; Central Bank of Egypt,Economic Review, Vol. 60, No. 4, 2019/2020, p. 91.
[20]The Arab Investment & Export Credit Guarantee Corporation (Dhaman), Investment Climate in Arab Countries, 2021, p. 42.
[21] Central Bank of Egypt,Economic Review, Vol. 54, No. 4, 2013/2014, p. 89; Central Bank of Egypt,Economic Review, Vol. 59, No. 4, 2018/2019, p. 85.
[22] Amr Adly,“Egypt’s Renewed Dependency on GCC States’ Largesse,”The Arab Gulf States Institute in Washington, April 15, 2022.
[23]The Arab Investment & Export Credit Guarantee Corporation (Dhaman), Investment Climate in Arab Countries, 2018, pp. 43, 61, 77, 79;The Arab Investment & Export Credit Guarantee Corporation (Dhaman),Investment Climate in Arab Countries, 2019, p.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