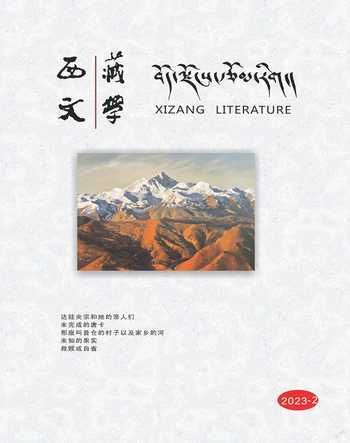那座叫普仓的村子以及家乡的河(散文组章)
2023-06-15杨乐

杨乐,内蒙古巴彦淖尔人。西藏成都办事处下属企业西藏饭店职工。自治区第八批驻村工作队员。驻村期间开始文学创作,所创作的散文《高原的影子》《灰布口袋》《老肖的青藏线》等作品刊登于西藏日报等刊物。
多少年前的梦里,我可曾来过这里?那雪山、草原,风里卷带的砂石,都好像是为我悉心准备的。我应该出现在这里。没有刻意的寻求或是反抗,于时光流年中,远涉千里地来了。
多少年后的我,是否还会回到这里?看村外的小河,夕阳下的牛群,和那远处挥舞皮鞭拥有明媚笑容的少年。这会出现在我未来的梦里,在匆匆而过的岁月里,忽而调转马头,飞奔向你。
普仓,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就跟这个屯、那个沟一样。群山环抱之中一股细流顺着山势缓缓流淌。夜晚停了电,你只能对着村子的方向扔两块儿石头,循着狗吠才能找到回家的路。我爬过村子周围所有像样的山,从不同的方位端详过它。说实话,它的气质配不上4600多米的海拔,看上去太过温顺和安详。
清晨的炊烟,像是村子长起来的头发。丝丝缕缕,在海蓝色的天空下,隨风变幻着形状。云也只是在半山腰上挂着,但它却不屑与炊烟为伍,还未靠近,便匆匆忙忙化作一阵雨、一场雪落在了地上。
牦牛却早已闻惯了自己粪便燃烧的味道,它亲眼看着女人们将那一坨坨堆砌成墙。有些牛已经活得老态龙钟,可仍旧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每当我清晨蹲在河边漱口,总会有那么几头围在我身边若有所思地打量着,那一颗颗硕大的脑袋在过去一年的时光里,仍旧以为我在做着什么奇怪的事情。
“休巴德嘞。”村长的弟弟是每天第一个看到我的人。
“休巴德嘞。”我嘴边还挂着牙膏的泡沫。
“德嘞、德嘞。”他叫罗布,40多岁了仍然未娶,早晨将牛群赶到山上,晚上再从山上赶回来,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德嘞、德嘞、德嘞。”再多的藏语我也没学会。
“德嘞、德嘞、德嘞、德嘞。”他不会先比我结束这段顺畅的交流。
旁边村长家的“二狗子”在晨光中微微抬起头看了我们一眼,然后换了个姿势继续睡了。这条傲慢的獒犬在我来到这个村子之前并没有名字,甚至人们给它喂食的时候,都没有跟它说过一句话。而我每天都要过去跟它打招呼,教导它不要成天只知道睡觉,要做些有意义的事。自从它的野狗“女朋友”被村民扔到了几百公里外的班戈县,它便再没什么盼头。我很同情“二狗子”,它挣不开这胳膊粗的铁索,我们有时候是一样的苦楚与无奈。
正午的阳光,把躲在村子角落的雪融化进了土里。阳光下的玻璃房子,一只慵懒的狸猫四仰八叉地睡在窗台上。兔子、黄鼠狼、狐狸也都停止了追逐,凑到村里的石板路上晒太阳,偶尔还会看到一群白屁股的藏羚羊从村子里一闪而过。牦牛对此甚至都来不及反应,只感觉到一阵风和一带而过的羊骚味。
白玛曲卓的阿妈又送来了酸奶,流着鼻涕的普布次仁偷偷给我手里塞了一块糖。五岁的英秋在前些日子也上了幼儿园,不会再拎着半条胳膊的玩具熊每日跟在我屁股后面。那天中午她还兴冲冲地跑过来对我说:“你在做什么?谢谢。”红彤彤的小脸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我以前总觉得自己必须要生个儿子,女儿太娇贵,让人担心。就在那一瞬间,我似乎改变了主意。
傍晚的夕阳,像是山的另一边有无数宝藏迸发着光芒,阳光将最后的余晖洒向了草原,所有的一切都染就了一身金黄。人们把小牛拴在了桩子上,整个村子也跟着奶声奶气地呼喊起来。没过多久,山头上便涌起一阵黑压压的“泥石流”,边跑边低沉地回应着。人类特别喜欢用这样的招数,屡试不爽。
黑夜总是早早地降临,在风起云涌下,它与白天“判若两人”。风从四面的山谷里像驱使着千军万马嘶鸣而来,暴雪在无数股力量的撕扯下疯狂地挣扎却怎么也落不到地上。沙石拍打着四周的墙,似乎在告诉我,这才是它原本的模样。
羌塘高原的夜晚,大自然在独自 狂欢。
这样的夜晚我惶惶然穿过了四季,经历了一个轮回。以前所有的日子却从未有过这样的深刻。我被放逐在夜晚辽阔的草原,任思绪飞舞到千万里。我看到浩瀚星河下村子的一头连着府南河,另一头长出一棵棵参天的杨树。数不清的梦境,整个村庄的夜晚都是我躺在床上听着风声肆意构想的。那日日夜夜憋在肚子里的话,都从半开的窗户飞离而去。
我从没想过会在老家之外的另一座村庄待这么长时间,长到我几乎熟悉了这里的一切。每一张和善的面孔,每一处歪歪斜斜的房子,甚至是河里每一块漂亮的石头,都深深地浸入了我的脑海里。
而我似乎刚刚才被这座村庄所接纳,人们看到了我坏脾气背后的好心肠,习惯了无数寒冷日子里并肩站在一起的那个人。我们共同喊着“二狗子”,身上混合着糌粑酥油味儿。阳光更加温暖,就连村里的风刮在我身上也温柔了许多。
然而,我终将会离开这里。在我们熟络的时候。
就像是生命中的一场境遇,村庄上空飘过的一片云,我只是这里驻足停留的过客。然而,生活在一寸寸的光影中走到了现在,每一阵风、每一场雪都在我生命中留下了该有的印记。我在辽阔的草原上尽情呼喊过,在巍峨的高山下仰望星河,在每一个无眠的夜里,思考着这困顿的旅途和平凡的人生。
只是想在后来的某一天,再次穿过那条熟悉的山路出现在你的面前,那时的我能否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那时的你会不会依然留在这里,任岁月更替,神态安详。
热塔的鹰
我在普仓到热塔自然村的那段崎岖的土路上,走过七十多个来回。我总是独自一人带着一盒剩饭,迎着下山归家的牦牛群上山。
在那半山腰上,有一栋破败不堪的石头房,屋里住着的光棍男人听说多年前去了比如县挖虫草就再也没有回来,只留下一条脖子上系着红布的獒犬。我每次路过那里,它都会对着我咆哮不止,揪扯着红布下包裹着的铁链,惊起阵阵黄土。它身后守护的是一座已经没有了门框的黑森森的洞穴。人们说这条可怜的狗是靠所有路过那条路的人养大的。因此,我便想在有限的时间里朝那个方向多走几趟。
我站在阳台看着窗外翠绿的五面山,高大的白杨树在风中微微地晃动着。制造航天发动机的厂房里寂静无声,有一两只麻雀从里面飞了出来。疫情又一次迫使这座城市安静了下来。之前,我似乎从没有这样认真地端详过窗外的景色。不知为何,此刻它让我想起了一段离我生活已经远去的时光——连一棵树都难以寻觅的藏北高原。
从那栋石屋再往前走有一个岔路口,右边延伸进一座山谷,谷里零星散布着十几户人家。左边通向一座高岗,那是一片被铁丝围起来的废弃牧场。人们说石屋前的那条孤零零的狗经常会被这山上住着的一只老鹰所欺凌。抢夺它来之不易的食物,撕咬它身上已经打了结的皮毛回去修整自己的巢穴。人们不能忍受生活不幸的人再蒙受屈辱,更何况这条狗身上有着多数人格都无法企及的 忠诚。
村民们也曾设法围捕过那只可恶的鹰,像扑小鸡一样扑过去,像管教牦牛一样用鞭子将石子飞掷出去。可那只狡猾的禽兽似乎轻而易举就能洞察人类的企图,总是在不高不低的半空中盘旋,让地下躁动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体会自己的无能为力。
清涼舒爽的风从窗口吹进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将身子探出窗外。空荡荡的街道、低矮的草丛树林,还有几只松鼠和梅花鹿样式的雕塑立在马路中央的绿化带里。当初那只鹰大概就是在这样一个高度俯视地面的景象。我紧紧抓住阳台的护栏,生怕自己像一块笨重的石头一样,掉落下去。
那只獒犬用爪子在地上挖出一个西瓜大小的坑,平常积攒雨水,路过的人们也会将食物投放进去。我每次都会看着它把我带来的东西吃干净,才会起身登上那座热塔高岗。我要去捣毁那只鹰的巢穴,让它无处安身,不得不离开这里。
然而,我来来回回在那座山峰上搜寻了几十次,却连一只鹰的影子都没有碰到。山上有时会刮起猛烈的风,气流如同湍急的浪花拍打在我脸上,使我不得不俯下身体才能正常呼吸。风又从我的领口钻进衣服,我便像只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而有时登上去却一丝风也没有,只有脚下的云海像白色的轻舟缓缓向一个方向浮动。远处一座又一座的雪山在湛蓝的天空和耀眼的阳光下,仿佛助跑几步就能轻松地跨越过去。我如果是那只鹰,一定会选择栖息在这里,一遍遍贪婪地俯瞰着这片广阔的天地。
终于,我在一处隆起的巨石上发现了它留存的印迹,一道道清晰的爪痕和风干的鹰屎。我爬了上去,竟一眼看见山腰上那栋破败的石头屋和屋前模糊得像一只黑点的獒犬。我似乎还能隐约地听到那狗的咆哮声。
天空一片寂静。我要是那只鹰该多好啊,此时就可以从这狭窄的窗口滑翔出去,驾驭着这股清凉的风,到达所有我想要到达的地方。我应该会在对面的五面山盘旋片刻,接着就展翅飞跃秦岭,回到九曲的黄河。我要饮一饮那橙黄色的水。我要实现当初在热塔高岗上所有的幻想后,再飞回那高岗的巨石之上。啊呀呀,啁啁。
后来,守护在石头屋前的獒犬突然消失不见了。村里的人说:是那房子的主人趁着夜晚回来带走了它,他们一人一狗,翻过了热塔的高岗,沿着蜿蜒的河道朝更加荒芜的双湖县去了。也有个别人说:是山上的那只老鹰干的,这么多年来它根本不是在欺凌那只可怜的狗,而是一次次用自己坚硬的喙,企图啄开那红布包裹着的铁索。
我个人更愿意相信后者。整个热塔,可能只有那只鹰听懂了獒犬疯狂的咆哮声中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河
小时候生活的村子被四条水渠围在中间,那里面日夜奔流着浑浊的黄河水。我最喜欢到西边的三岔口玩耍,因为只有那里的水可以没过我的头顶。父亲总是在日头最盛的时候,强迫我静下心来睡午觉,可那几百米外的河水像是光着身子的女人跑到院门外使劲向我招手。我为此常常要受到父亲的追打,庄稼地里拿起什么都可以教训自己的儿子,葵花杆、玉米棒子,甚至抠起地里的泥也能从后面掷在脸上。但我从来都不觉得疼,黄河水将人的头发一根根地指向天空,这让我奔跑起来十分畅快凉爽。
我口渴的时候会像狗和牛一样匍匐在岸边,张开嘴让河水自然地流进我的咽喉、鼻腔,清凉芬芳的泥土味驾着一朵朵小的浪花尽情地拍打在我脸上。我便索性将整个头颅都伸了进去,像白杨和红柳的根茎一样,吸收着水里的养分。我看见了金黄的鲤鱼、光滑的泥鳅,一群只长出两条后腿的蝌蚪,还有一个满脸惆怅的成年男人站在河的尽头。突然间,我又想起上游的放羊老汉会对着这条水渠打开自己的“闸门”,便像是吃了人生大亏一样,猛地从那水里扬起头来。泥沙和水堵住了我的耳朵,我却发现面前挂起一道若隐若现的彩虹。
人终归要长大,要告别村子里青梅竹马的女孩,自从我离开了那片黄土地,梦里流淌着的水声就渐渐消失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去了很多个地方,见过无数条河,那些水流大多清澈见底,那岸边也总有人倚着栏杆深情地望着水面。可我那时候并不知道,这只是他们的河,与我无关。
在这波光粼粼的世界里,在这纷繁复杂的时光中,我跟随每条遇见的河流都要走上一程,然而当时间在我面前化作一个个浪头又四散奔逃时,我已经无法分辨自己到底是那水里的鱼,还是一颗顺流而下的石头。
直到若干年后,我来到了另一座村庄。黄土地变成了千年的草皮,平原上隆起了高耸入云的山脊,方圆几百公里连一棵像样的树都没有,空旷的天地间我像是一件被遗落在山谷中的铁器,是河套平原耕地的犁,或是城市外墙剥落的铁皮。晴朗明媚的白昼,皓月当空的夜晚,世界上所有蜿蜒浩荡的河流都被阻隔在群山后面,只有一股细流从村庄的腹地欢快地奔涌而过。
时间从天空中落了下来,陪同我沿着这条小河一直走向山的最深处。我将几十年的心事与不甘统统地告诉了脚下的河水,它便一路喋喋不休地流向远方,并把我所有的秘密公开给岸上的青石、水中的鱼虾,还有几头驻足饮水的牦牛。它们都认识了我,漫山遍野的鲜花一夜之间铺满了整个草原,风温柔得像少女的头发,和升腾的炊烟紧紧地缠绕在了一起,雄鹰也从云层中滑落到人间,整理着自己骄傲的羽翼,望着我会心地点着头。我开始在万事万物面前渐渐恢复了儿时的知觉,在某个寂静无声的夜晚,仿佛又听到了西边三岔口的流水声。
暴雨将小河变得汹涌澎湃,激流翻卷着浑浊的泥沙,像是一位不远千里专程来探望我的伙伴。原来所有的河流在某一时刻都会变成故乡的黄河水,而多年背井离乡、飘来荡去的人呐,才需要放下山外的风景找回自己。我站在石桥上看着两个村庄的河水重叠在一起,中途的旁枝末节都被淹没在杂草丛中。时间将我放在一个刚刚好的位置,能够一眼望穿来时的路——那条漫过我青春岁月的长河。
我还看见了那个将整个头颅都伸进水中的少年,他眼中藏着我人生初始时最纯真的梦想。
土 路
这条两旁长满了芦苇和狗尾巴草的乡间土路一直可以延伸到很远,它跟随着人工渠里橙色的黄河水逆流而上。我小时候常常坐着大爷爷的自行车到前面不远的民富小学上学,他在坚硬的后座上为我加装了一件用灰布包裹着的海绵垫。风此时就从那个方向吹过来,我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路中央,坐在草丛间。
有蚂蚱和蜻蜓从我身边掠过。我站起身来试图抓住它们,却听到自己的膝盖发出一连串沉闷的响声。这些年来,我已走过很长很远的路,一闭上眼周围就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嘈杂,像暴雨拍打在玉米和葵花展开的叶片上。我曾在无数个夜里想起这条宁静的小路,坑坑洼洼的地上全是黄土和红泥。大爷爷总是沉默不语,身上永远散发着一股陈年的烟油味,仿佛他那干瘦的身体就是一支燃烧着的巨大的纸烟。
昨天是我的婚礼。我和父亲在当天清晨露水还未散去的时候,开着车沿着这条小路来到大爷爷的坟前。家中有了新进人口,按照习俗要过来告诉他一声。每座坟茔都长得一样,隆起的虚土上泛着白色的盐碱,低矮的石碑淹没在了荒草之中。后人们全凭记忆祭奠。父亲和大爷爷一样沉默,他用地上的树枝将带来的纸钱烧尽,又将两包烟扔散给了周围同样荒凉的土堆。
这些年来,父亲总是开着他那辆破旧的长安奔奔行进在这样的乡间小道上,屠牛宰羊,收售皮货。他身上总是带着一股浓重的羊油的味道。回去的路上,车斗上那一排锋利的铁钩在颠簸中像是奏起了一段奇妙的乐曲,叮铃铃、铛铛……我从当初只有野草那么高,到今天即将要步入婚姻的殿堂,时间像只奔跑的兔子从这路上一闪而过。父亲还是双手紧握着那只满是油污的方向盘,从始至终没有半句叮嘱的话。风吹进车窗,带着升腾而起的泥土和青草的芳香。我看着后视镜里摇摇晃晃的路,远处有一个戴着草帽、穿着破烂衬衫的稻草人,正站在树荫下侧着身子向我们挥动着手。
爆竹声散去,还有鲜艳的红花和洁白的纱裙。我也不知为何独自一人又来到这里,看着这条蜿蜒崎岖的土路上碾过的一道道车辙。它们有的狭窄细长,有的宽大厚重,深深嵌入土里,没有人打扫,只有雨水偶尔下来冲刷冲刷。两边的庄稼不紧不慢地生长着。沉静的土地,低垂的白云,哗啦啦的黄河水和轻轻抚过青草的风声,还如我孩提时一模一样。
我用一块土坷垃将身上脱下的衣服压在地上。只穿着一条代表新婚的红色内裤,奔向河水上游的闸口。一群麻雀和两只喜鹊叽叽喳喳地飞在我左右两边的草丛上。野鸡、兔子,还有翠绿如芭蕉的玉米,也跟着我一起向前涌动着。我将脚趾头抠进温热松软的泥土,接着一头扎进了芬芳冰凉的黄河水里。是土壤、草根、树叶和麦芽的味道。它们一瞬间便涌入了我的耳朵、鼻孔和嘴巴。我仰面看着金色的阳光照射在自己溅起的晶莹的水花之上。我看见那条土路下边是丰茂的水草和纵深蜿蜒的根茎。两岸的花草树木在那一刻像是弯下腰也想跳进来,而我却只想成为一截木头,顺着河水,紧挨着这条土路,一直飘下去。
酸 枣
在我老家的村东边曾经住着个放羊老汉,名叫迎喜。他打了一辈子光棍,未能成就一件喜事。
每天天不亮他就赶着一群羊钻进了村外的芦苇荡,那芦苇浩瀚无边,连着阴山脚下千里的戈壁滩。村里的老人说:“这里面住着九尾狐狸,迎喜出出进进肯定是有啥想法哩。”待到日落西山,那金色的芦苇丛中就会跳出一头头吃得圆滚滚的羊,而迎喜老汉有时背着一捆打来的嫩草,有时只扛着一截死去的胡杨木。
剩下漫长的夜晚,他会在那间漆黑的小屋里点起一盏煤油灯,盘腿坐在土炕上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那屋中所有的陈设都跟他本人一样,像是泥巴做的。唯独油灯下摆着一盘火红色的酸枣,颗颗饱满,在闪烁的烛光中,像是黃土堆里长出了一窝新鲜的花骨朵。
他的口袋里也装满了这样的红果子,在清晨或是傍晚的路上分发给遇到的每一个小孩。那时我为了能多讨几颗,便一个劲儿地喊他:“迎喜爷爷,迎喜爷爷。”他高兴得鼻孔里的毛都露了出来。我看见那杂乱无章的花白胡子里只挂着一颗孤零零的黄牙。
如樱桃般大小的枣子,酸甜可口的味道里还带着一股特殊的烟草香。
从那以后,我便一次次翻上他的院墙,像窥探一座破败的寺庙和寺庙里六根清净的老和尚。我把耳朵贴在那扇笨重的木门、糊满报纸的窗户上,甚至是房顶隆起的烟囱。我像一只猫头鹰一样,盯着烟雾缭绕下那张长满荒草的脸,还有那盘火红火红引人直流口水的酸枣。他无儿无女又没牙齿,这么好吃的果子难道就这样跟着他一起风干吗?
我开始每天在村口等他回来。吃过口袋里的酸枣,还要继续爬上墙头观察他重复地点烟、抽烟、熄灯、睡觉。他从不跟任何人说话,只是偶尔会喊骂那群边走边拉屎的羊,像在喊骂自己不争气的孩子。
从麦苗只有韭菜高到地里的葵花结出了籽盘,我把迎喜的那面墙生生地坐下了个凹槽。在这段时间里,那扇严密的窗户下又多出了一把火红的酸枣,院门也不再像往常一样紧闭,我甚至看见他离开时把钥匙插进了墙面的缝隙里。
那是一个刮着大风的黄昏,风把窗台上留给我的枣子不知吹向了何方。我像一条被喂熟了的狗,四处寻觅无望,竟爬上窗户打起了屋里的主意。
我把手伸进了墙缝。
屋子里漆黑一片,一股浓重的烟油味像是已经浸透了整个世界。我慌忙地将盘中的酸枣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还把剩下的塞进了嘴里。正当我准备逃离这间让人窒息的小屋时,借着门口投射进来的光,一口巨大的棺材赫然出现在 眼前。
与此同时,我听到有无数的脚步声从院门外涌了进来。我被吓得嚎啕大哭,像是一只慌不择路的兔子冲了出去。那迎喜老汉又背回了一截胡杨木,那群肥硕的羊被突然出现的我吓得四散奔逃起来,院子里一片黄尘。我拼命地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墙,越过一片又一片的麦地,总感觉自己身后还跟着一只九尾狐狸。
一直跑到精疲力尽,我瘫倒在了一片麦地里。我看见一轮明月挂在半空,慢慢地只剩下风掠过麦穗的声音。
醒来时,我竟然躺在自家的土炕上。两只口袋里的酸枣已散落殆尽,却单单还留下一颗。
待到阳光直射大地,我又回到了昨夜拼命奔跑过的麦地,却见那片压倒的麦子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金黄的土地上没有一星半点的红色。难道这只是一场梦吗?我不敢确定,也再没敢爬上村东头那座孤寂的院墙。
半个月后,迎喜老汉的那群羊饿得从圈里跳了出来,跑进了别人的庄稼地。村里人这才发现他已死在家中多日,躺在了自己打造的胡杨木棺材里。这口棺椁太过巨大,人们只好将整个门框都拆卸下来。当刺目的阳光照进这间被旱烟熏得漆黑的房子,人们又一次惊奇地发现,屋子里陈旧的家具、地上的砖头,甚至是整整齐齐码在角落里的被子,都是火红色的。
又过了些年,村里为了增加耕地面积,一把火将那片绵延不尽的芦苇荡烧成了灰烬,有没有九尾的狐狸没人知道,人们只是说起芦苇丛中有一片人工栽种的酸枣林,大火烧了九天九夜,那挂在树上的酸枣却像不灭的炭火一样,仍旧闪闪发光。
编辑导语:这组散文语言很有特色,有泥土味道,又有思想力道。作者将思想和情感融入生动物象中,写鹰,写藏獒,写河,写小路以及酸枣,都仿佛是从事物内里发出,带着对象鲜活的个性色彩和温度,活泼、自然而又意味深长。
责任编辑:子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