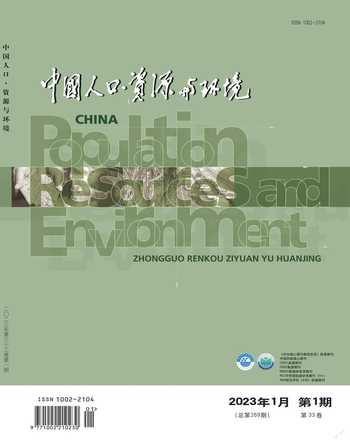环保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2023-06-12罗理恒
罗理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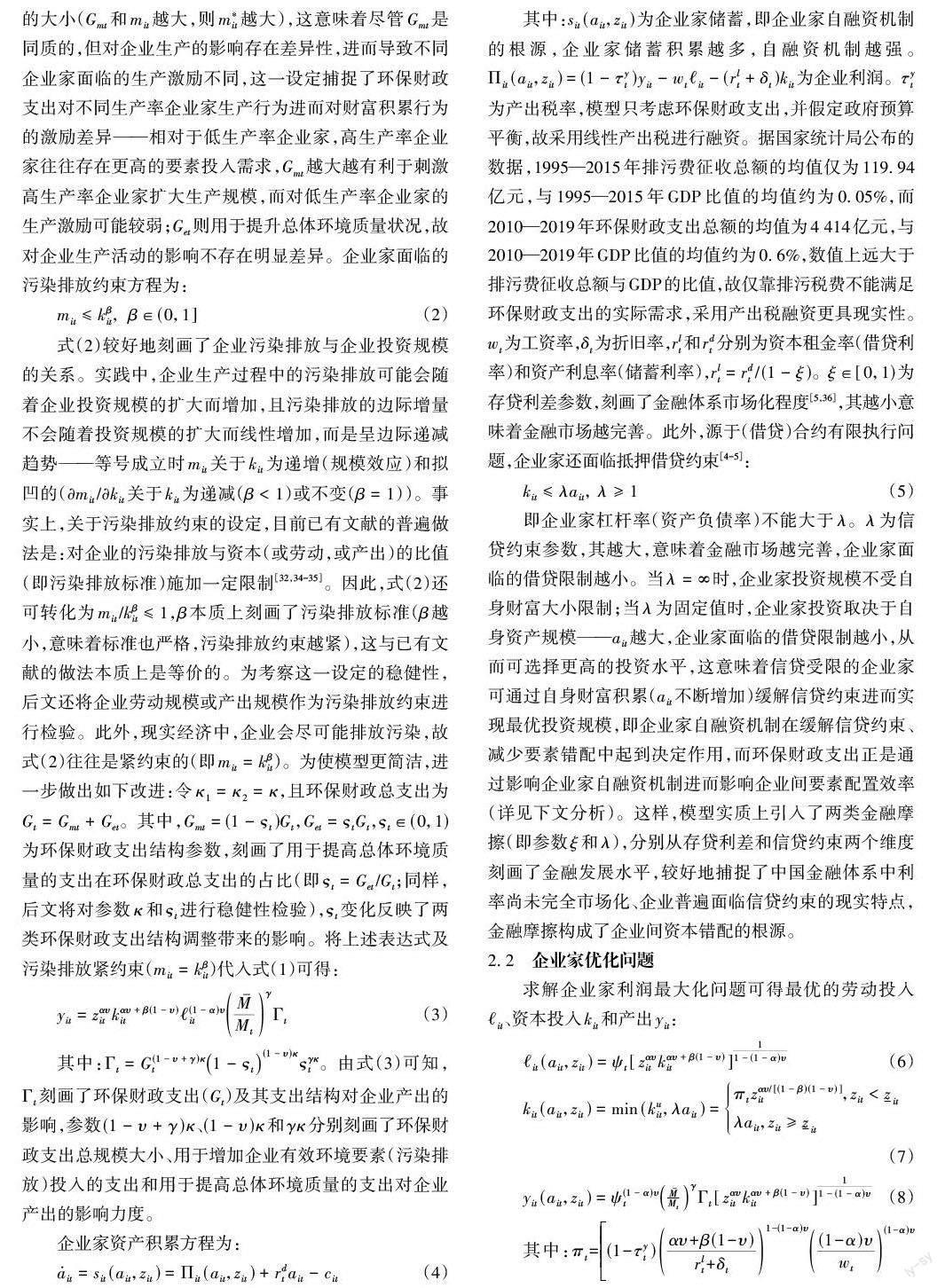

摘要 环保财政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及其作用机制如何?为回答这一问题,该研究提出一个环保财政支出影响企业间要素配置进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中国现实经验数据为参数赋值依据,利用数值模拟方法,从要素配置视角剖析了环保财政支出对TFP的影响及其核心机理。研究表明:环保财政支出对TFP和总产出具有较弱的负影响,作用机制源于环保财政支出可通过影响企业家自融资机制进而影响企业间的要素配置。环保财政支出结构中,用于提升总体环境质量的支出占比越大,会加剧TFP的损失,而提高用于增加企业有效环境要素投入支出的占比则有利于提升TFP,但二者的TFP效应较弱。利用排污税费为环保财政支出融资对TFP具有较弱的正影响。信贷约束对环保财政支出的TFP效应具有非常突出的影响,信贷约束越紧,企业间资本错配程度越高,环保财政支出对TFP的负影响越大。环保财政支出明显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和提高总体环境质量。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扩大环保财政支出规模,同时优化调整环保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健全环保财政管理体制、加强环保财政职能对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协同调节机制,完善金融市场机制、提升金融市场资本配置效率。
关键词 环保财政支出;全要素生产率;要素配置
中图分类号 F812. 45;X3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3)01-0038-12 DOI:10. 12062/cpre. 20221010
尽管近年随着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大,中国各类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呈现出下降趋势(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SO2排放数据为例,排放总量从2010年的2 185万t锐减至2019 年的457. 29 萬t),但总体环境质量状况仍不容乐观[1]。同时,自上而下的环境治理困境及财政工具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治理的难度[2]。增强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手段[3]。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环保财政支出便是国家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所需财力投入最直接的体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环保财政支出为2 441. 98 亿元,2019 年则增加至7 390. 2 亿元,增长了约2倍,呈现出明显的递增态势,政府财政支出在环境治理中持续发挥积极作用。尽管如此,环保财政支出在经济总量和全国财政支出中的占比依然很小:2010—2019年,全国环保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均值仅为0. 6%,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的均值仅为2. 6%。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环保财政支出规模还具有较大的扩张潜力。但现有研究对以下几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尚缺乏深入探讨:环保财政支出规模扩张的经济影响及其内在理论机制如何?是否有利于持续改善环境质量?环保财政支出结构变化的经济影响如何?运用环保财政手段能否有效实现环境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推进?从理论上深刻解答上述问题无疑对“环保财政支出规模是否应当持续扩大”“环保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调整方向”“环保财政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等一系列重要议题的探索和实践具有极强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为此,该研究提出一个环保财政支出影响企业间要素配置进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的理论分析框架,在Moll[4]和贾俊雪[5]研究的模型基础上进行拓展,构建一个连续时间的随机异质性企业家模型,以中国现实经验数据为基础,利用隐性-迎风算法(Implicit?upwind Scheme)进行数值求解[6],深入剖析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间要素配置进而对TFP的影响及其核心机理,并细致考察环保财政支出结构、支出融资方式、信贷约束变化的TFP效应及环保财政支出的环境效应。
1 文献综述
环保财政支出直接目的在于减少环境污染,其本质上属于更广义的环境规制范畴[7]。长期以来,环保财政支出的经济环境影响及其影响机制一直是学者们研究关注的焦点,且目前该领域的相关成果多以实证研究为主,理论研究相对较少。
目前学界对环保财政支出的经济环境影响展开了大量研究,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观点。在环保财政支出的经济影响方面,部分学者指出,环保财政支出是公共支出的一部分,在短期内通常会刺激经济,并在较长时期对经济增长具有稳定的促进作用[7-8]。Krajewski[9]利用中欧11个国家经验数据发现,环保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但也有部分学者研究发现,环保财政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10-11]。黄菁等[12]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来度量污染治理投资份额,研究发现,污染治理投资份额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负影响。陈思霞等[13]利用中国城市经验数据发现,现阶段环保财政支出并没有促进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反而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另一部分学者着重探讨了环保财政支出的环境影响,并认为环保财政支出有利于提升环境质量。Ruffing[14]指出,环保财政支出是环境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能有效减少空气污染。López等[15]利用欧洲12个国家经验数据发现,环保财政支出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Czy?ewski等[16]证实了欧盟国家环保财政支出规模与PM2. 5排放量之间的相关性:支出越高,PM2. 5的排放量就越低。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对环保财政支出的正向环境效应提出了质疑。Bernauer等[17]利用跨国经验数据发现,政府财政支出规模越大的国家,环境质量反而越低。环保财政支出并不必然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18-20]。
已有文献对环保财政支出的影响机制也进行了丰富探讨。大部分学者认为,环保财政支出通过引致环保投资、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增强健康资本积累等机制促进经济增长,但同时对私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及导致行业成本增加从而阻碍经济增长[9,11,13]。而财政政策工具对环境保护的有效性源于环保财政支出的直接减排作用及对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绿色技术创新等机制的间接影响,总的环境效应不仅取决于环保财政支出规模,还与支出结构、环境保护税收手段的组合形式密切相关[2,21]。但已有文献忽略了环保财政支出影响经济的一个重要机制:环保财政支出影响企业间要素配置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目前鲜有文献从要素配置视角深入考察环保财政支出对TFP的影响。事实上,近年来大量文献强调企业间要素配置对TFP的决定作用[4-5,22-23]。Moll[4]、贾俊雪[5]构建一个异质性模型,深刻揭示了企业家自融资机制(企业自身财富积累)是缓解信贷约束下企业间要素配置扭曲导致的TFP损失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企业间要素错配导致的要素价格扭曲和要素利用效率低下被认为是加剧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24-26]。牛欢等[26]构建一个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进一步指出信贷约束下要素配置扭曲和污染的负外部性双重加剧了TFP损失。上述几位学者的观点为后续学者深入探究要素配置、环境污染、TFP三者之间的内在理论关联提供了契机,也为该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路借鉴,即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隐含的倒逼驱动机制:环保财政支出在降低环境污染的同时也会影响企业间的要素配置进而对TFP产生重要影响。
与已有研究成果相比,该研究在如下两个方面进行探索:①提出一个环保财政支出影响企业间要素配置进而影响TFP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Moll[4]和贾俊雪[5]研究的模型基础上进行拓展,将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和环境质量的外部性纳入企业生产函数[26-33],并引入污染排放约束和两类金融摩擦(存贷利差和信贷约束),构建一个连续时间的随机异质性企业家模型,其优势在于能够从更微观的层面捕捉环保财政支出对不同企业家生产行为(包括企业产出、要素需求、自融资机制)的影响,从而刻画环保财政支出对不同生产率企业家财富积累行为的激励差异,及对企业间要素配置进而对TFP 的影响。同时,借鉴Achdou 等[6]提出的隐性-迎风算法(Implicit?upwind Scheme),将该理论方法运用于数值求解分析中国的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问题。由于理论模型最终推导出的TFP表达式较为复杂,仅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无法全面深入考察环保财政支出的微观影响机制,而隐性-迎风算法则能够以中国现实经验数据为基础对模型进行数值求解,进而从数值上清晰揭示环保财政支出对TFP的影响及其核心机理。②引入环保财政支出结构参数,从理论上清晰刻画环保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对TFP的影响。依据财政部公布的环保支出项目明细将环保财政支出分为两类,即用于提高企业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的支出和用于提高总体环境质量的支出。前者可以更直观地理解为治污技术及清洁生产技术研发、低碳循环经济发展等既有利于增加企业实际产出又能减少企业实际污染排放量的财政投入,主要包括污染减排(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等支出;后者主要包括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江河湖库流域治理与保护、环境监测与监察等支出。虽然已有国外文献普遍采取的环保财政支出设定亦主要分为两类:一类针对个体企业而言,引入污染排放扩大技术资(Pollution?augmentingKnowledge Capital)投入[29],用于增加企业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另一类针对整体自然生态而言,引入政府减排支出[27-28,31],用于提升总体环境质量。但上述文献都只侧重考察了环保财政支出的某一方面,该研究则将两种类型的环保财政支出同时纳入企业生产函数。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环保财政支出虽然在改善总体环境质量和提高企业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方面具有积极影响(详见下文分析),但这是直接以牺牲企业产出(即缴纳产出税,往往远大于排污税费)为代价的,因此相较于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产出的正向激励,产出税具有更为直接的负影响,故对企业家财富积累进而对TFP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黄菁等[12]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包括企业环境支出和政府环境支出,后者占主导地位)占GDP比重来度量污染治理投资份额(可近似理解为前文理论模型中的产出税率),研究表明,污染治理投资份额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负影响,也可更直观地理解为以“增长换环境”,短期内资源总量不变的条件下,用于污染治理资源的增加会挤出直接用于生产的资源,从而减少了产出。鉴于环保财政支出数据的可得性,该研究以2007—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索洛残差法[42-43]测算出TFP,在控制了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人口密度、R&D支出规模等一系列变量后,利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保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环保财政支出规模)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导致TFP和实际GDP分别显著下降0. 0 756%、0. 0 763%,意味着当前中国的环保财政支出对TFP和经济总产出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影响力度较弱。这很好地契合了前文理论分析的结论——就前文理论模型而言,环保财政支出增加与环保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增加及产出税率增加本质上是等价的(源于政府预算平衡条件的假设)。理论机制分析表明:产出税率增加对企业产出具有抑制作用,而环保财政支出通过影响环境质量和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对企业产出还具有正向激励(但较弱)。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产出税率增加对企业产出的负影响,要大于环保财政支出增加带来的正影响。基于省际数据的实证结果证实了该研究数值模拟结果的准确性,为理论分析的结论提供了良好的经验证据,增强了结论的可靠性。
3. 2. 2 要素配置机制验证
前文理论模型较好捕捉了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间要素配置的影响机制(式(4)—式(8)),定性分析了环保财政支出通过差异化影响异质性企业生产、财富积累行为进而影响企业间要素配置。为进一步直观揭示环保财政支出影响企业间要素配置进而影响TFP的作用机制,本部分利用数值模拟对这一机制进行验证。具体而言,引入如下两个变量刻画企业间的资本错配程度(二者的值越大,则企业间的资本错配越严重,TFP损失越大)[5]:一是两类企业资本产出比的比值Δ(- z )(即非信贷受限企业与信贷受限企业资本产出比的比值);二是信贷受限企业家累积资产损失份额Ω(- z )。
图2给出的数值模拟结果显示:随着环保财政支出G增加,Δ(- z ) 和Ω(- z ) 的值都增大,且这一递增趋势相对平缓,这意味着环保财政支出加剧了具有不同生产率的企业在生产要素选择上的扭曲和偏差,从而不利于提升TFP(但这种负效应较弱)。上述機制分析很好地契合了环保财政支出对TFP的影响(图1(a)),进一步证实了环保财政支出通过影响企业间要素配置进而影响TFP的作用机制。
3. 2. 3 支出结构及支出弹性变化的TFP效应
图3(a)给出支出结构参数? 不同取值下环保财政支出G 变化对TFP的影响,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在一定范围内改变? 的取值,环保财政支出对TFP仍具有负影响,这与基准结论保持了良好的一致性。同时注意到,? 取值为0. 4时的TFP曲线略处于? 取值为0. 8时的TFP曲线的上方,这说明? 越小,越有利于提升TFP(虽然这种正效应很弱)。原因在于:理论模型中,环保财政支出包括用于提高总体环境质量的支出Ge 和用于增加企业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的支出Gm,故在环保财政总支出不变条件下,用于提高总体环境质量的支出在总支出的占比?越小,则1 - ? 越大,进而意味着Gm 越大。由前文分析可知,Ge 对企业生产活动的影响不存在明显差异,而Gm 对企业生产激励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越大越有利于刺激企业家(尤其对高生产率企业家而言)扩大生产规模(式(1)和式(3)),故对企业家财富积累(进而企业间的要素配置)具有正影响,有利于提升TFP。这里之所以要强调环保财政总支出不变条件,是为了比较静态分析仅由环保财政支出结构? 变化对TFP的影响。事实上,Gm 增加还可能是由G增加(而非? 减小)导致的,但这并不有利于提升TFP(详见基准结果及下文支出弹性变化的TFP效应)。在经验分析上,陈思霞等[13]指出,现阶段中国环保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影响,环境科研、环境生态信息建设、环境技术研发等用于增加企业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的财政支出较少,中国的环保财政支出结构有待调整优化。
图3(b)给出支出弹性参数κ 不同取值下环保财政支出G 变化对TFP的影响,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在一定范围内改变κ 的取值,环保财政支出对TFP仍具有负影响,与基准结论一致。同时注意到,κ 取值为0. 15时的TFP曲线略处于κ 取值为0. 005时的TFP曲线的下方,这说明κ 增加对TFP具有较弱的负影响。原因在于:κ 越大,既增加了G 对产出的正影响(式(1)和式(3)),进而有利于企业家的财富积累;但同时又推升了要素价格(工资率和资本租金率,式(17)和式(18)),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对企业家财富积累产生负影响。正是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κ 增加对TFP具有负影响。
但现实经济中存在一个典型客观事实是:尽管全国排污费征收总额逐年增长,但相对于全国经济总量发展水平,排污费的征收规模依然占据较小的比例,且远小于环保财政支出规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995年全国排污费征收总额为37. 1亿元,2015年排污费征收总额则为178. 5亿元,相较于1995年增长了约3. 8倍。可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排污费征收总额快速增长;但相对规模依然较小,2015年全国排污费总额占GDP比重为0. 026%,1995—2015 年该比重的均值为0. 05%,而2010—2019年环保财政支出与GDP比值的均值约为0. 6%。因此,实践中,仅靠排污税费本身远远不足以弥补中国环保财政支出的需求,从而造成了“牺牲企业产出”“以增长换环境”的局面。上述分析进一步增强了基准结论的可信性和现实性。
3. 2. 5 信贷约束变化的TFP效应图4(b)给出信贷约束参数λ 不同取值下G 变化对TFP的影响。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在一定范围内变化λ的取值,环保财政支出对TFP仍具有较弱的负影响,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而且λ 越大,TFP的总体平均水平越高——λ 取值为1. 5时的TFP曲线远处于λ 取值为1. 05时的TFP曲线的上方,这很好地证实了“λ 越大越有利于减少信贷受限企业进而改善资本配置效率进而提升TFP”这一作用机制。但值得注意的是:λ 越大,环保财政支出的TFP效应就越弱。原因在于,λ 越大意味着企业家受到的信贷约束越宽松,企业家的财富积累(自身融资机制)对于缓解信贷约束的作用相对减弱,企业间的资本错配程度较低,从而“环保财政支出影响企业家财富积累进而影响企业间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而影响TFP”的这一作用机制减弱。因此,λ 较大时,环保财政支出的TFP效应减小,对应TFP的曲线变得更平缓(λ 取值为1. 5时的TFP曲线更加平缓)。可见,信贷约束对环保财政支出的TFP效应具有非常突出的影响,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有利于缓解环保财政支出扩大导致的要素配置扭曲和减少TFP损失。
3. 3 环境效应
图6给出环保财政支出G 变化对污染排放总量和总体环境质量的影响。不难发现,随着环保财政支出增加,污染排放总量减少,总体环境质量显著提高,污染排放总量(或环境质量)的减少量(或提升幅度)的绝对值会随着环保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增加,具体表现为:污染排放总量的递减趋势随着环保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变得更加陡峭(图6(a)),总体环境质量的递增趋势随着环保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变得更加显著(图6(b))。这较容易理解:在环保财政支出用于环境污染治理的初期,由于执行成本、污染治理与清洁能源技术研发等因素的制约,导致环保财政支出的环境效应存在时滞,故随着环保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加,其对环境污染治理和环境质量的积极影响才会凸显出来,而且环境质量的持续提升进一步增加了环境自身的净化能力(即对污染物的吸纳能力),进而加强了环保财政支出的环境效应。这与臧传琴等[46]利用中国省际环保财政支出数据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类似。同样,该研究以2007—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47]估算了环保财政支出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环保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环保财政支出规模)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导致SO2排放显著下降0. 326 2%,这为上述数值模拟分析的结论进一步提供了经验证据。
当然,上述环保财政支出边际递增的环境效应是短期且不持续的,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在实践中,环保财政支出不会无限增加。就中国现实经验数据而言,2010—2019年环保财政支出与GDP比值的均值为0. 006(据此将理论模型中产出税率τy 设为0. 6%),此时G 的模型预测值为0. 008 9,而G 的模型预测值为0. 45时,其对应产出税率τy 为40%,此时环保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影响,但这一情况在现实中往往不存在。其次环境质量越好,越难以维持,继续再提升的空间就越小[29]。
4 结论与政策建议“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推动绿色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十四五”时期的工作重点领域之一。如何运用财政手段赋能环境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推进,对于落实“十四五”时期工作重点领域的目标显得至关重要。环保财政支出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对中国环境治理成效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故厘清环保财政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及其作用机制是实现环保财政职能优化的重要突破口。
研究表明,环保财政支出对TFP和总产出具有负影响,且环保财政支出的TFP效应和总产出效应较弱——这源于环保财政支出可通过影响企业家自融资机制进而影响企业间的要素配置,虽然环保财政支出增加,有利于改善总體环境质量和提高企业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但这是直接以牺牲企业产出(即缴纳产出税,往往远大于排污税)为代价的,因而相较于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产出的正向激励,产出税具有更为直接的负影响,可理解为以“增长换环境”,故对企业家财富积累进而TFP呈现较弱的负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环保财政支出可通过影响企业间要素配置进而影响TFP,环保财政支出加剧了企业间要素错配程度,从而导致TFP的损失。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财政支出结构中,如果用于提升总体环境质量的支出占比越大,就会加剧TFP的损失,而提高用于增加企业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支出的占比则有利于提升TFP,但二者的TFP效应较弱,这源于两类环保财政支出对异质企业家的生产激励差异;环保财政支出弹性增加对TFP 具有较弱的负影响;利用排污税费为环保财政支出融资对TFP 具有较弱的正影响;信贷约束对环保财政支出的TFP效应具有非常突出的影响,信贷约束越紧,企业间资本错配程度越高,环保财政支出对TFP 的负影响越大,反之亦然;环保财政支出明显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和提高总体环境质量。
上述结论对于如何通过优化环保财政职能以践行“两山”理念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良好的启示意义。
首先,从环境治理角度环保财政支出规模应当进一步扩大,以持续发挥环保财政支出在提升总体环境质量、减少污染排放方面的重要作用。但环保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落在优化环保财政支出结构上,政府应当注重环境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供给方向:污染减排技术投入比公共污染治理投入更有效率,即环保财政总支出中应当增加用于企业污染治理与清洁生产等方面的技术研发投入,而适度减少用于公共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更具体来说,环保财政支出应当更多向绿色技术研发、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利用、环境管理创新、资源综合利用等用于提升企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减少企业污染排放的支出领域倾斜,从源头上减排降污,实现绿色增长、高质量发展。同时,也不容忽视环境监管、公共区域的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等用于公共环境保护或末端治理方面的适度财政支出,以提升总体环境容量,避免出现“公地悲剧”。
其次,应当进一步优化环保财政管理体制,强化环保财政职能,加强环保财政“收与支”对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协同调节机制。当前中国环境保护领域的税收规模总体较小,以排污收费和资源税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995—2015年中国排污费征收总额和资源税征收总额占GDP比值的均值分别为0. 05%和0. 1%,占环保财政支出比值的均值分别为6%和25%(其中,与环保财政支出比值所用样本期为2010—2015年),二者与经济总量及环保财政支出规模相去甚远,即使依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2020年9月1日施行)规定针对原油、天然气和煤等具有高排放特征的化石能源矿产的税率区间也仅为2%~10%,依然具有较大上调空间。现行环境保护领域的税收手段对经济和环境应有的调节作用难以得到发挥,因此,应当适度提高环境保护领域相关税种(如环境保护税、资源税)的税率,以此扩大环境污染治理专项资金池,充分发挥“庇古税”对污染负外部性的有效矫正作用,确保政府环境支出与环境税收的基本平衡,从而尽可能避免出现“以增长换环境”的现象,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双赢。此外,还应当进一步健全中国的金融市场体系,例如,深化金融市场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机制、提升金融市场资本配置效率,解决某些(尤其是高生产率)民营企业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以缓解环保财政支出扩大导致的要素配置扭曲和减少TFP损失。
参考文献
[1] WENDLING Z A, EMERSON J W, DE SHERBININ A, et al.__ 2020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R]. Yale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Law & Policy, 2020.
[2] 张莉. 财政规则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以环境治理为例[J]. 中国社会科学,2020(8):47-63,205.
[3] 陈诗一, 陈登科. 雾霾污染、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经济研究, 2018, 53(2): 20-34.
[4] MOLL B. Productivity losses from financial frictions: can self?fi?nancing undo capital misalloc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 3186-3221.
[5] 贾俊雪.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异质企业家模型的理论分析[J]. 经济研究, 2017, 52: 4-19.
[6] ACHDOU Y,HAN J Q,LASRY J M,et al. Income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in macroeconomics:a continuous?time approach[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22,89:45-86.
[7] 原毅军, 孔繁彬. 中国地方财政环保支出、企业环保投资与工业技术升级[J]. 中国软科学, 2015(5): 139-148.
[8] BLANCHARD O J, LEIGH D. Growth forecast errors and fiscalmultiplier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 117-120.
[9] KRAJEWSKI P. The impact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on economic growth[J]. Problemy ekorozwoju?problems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6, 11: 99-104.
[10] JOSHI S, KRISHNAN R, LAVE L. Estimating the hidden costs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1, 76(2): 171-198.
[11] BARMAN T R, GUPTA M R. Public expenditure, environment,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2010, 12: 1109-1134.
[12] 黃菁, 陈霜华. 环境污染治理与经济增长: 模型与中国的经验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 2011(1): 142-152.[13] 陈思霞, 薛钢. 地方环境公共支出如何影响了经济增长: 技术效率与健康资本的视角[J]. 中国软科学, 2014(5): 173-181.
[14] RUFFING K G. The role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making[J]. Review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2010, 4(2): 199-220.
[15] L?PEZ R,PALACIOS A. Why has Europe become environmental?ly cleaner:decomposing the roles of fiscal,trad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14,58:91-108.
[16] CZY?EWSKI B,MATUSZCZAK A,KRYSZAK ?,et al. Efficiencyof the EU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struggling with fine particulatematter (PM2. 5):how agriculture makes a difference[J]. Sustain?ability,2019,11:4984.
[17] BERNAUER T,KOUBI V. Effect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n airquality[J]. Ecological economics,2009,68:1355-1365.
[18] HALKOS G E, PAIZANOS E A.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the environ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3, 91: 48-56.
[19] ABID M. Does economic, financial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matter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EU and MEA countr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7, 188: 183-194.
[20] GHOLIPOUR H F,FARZANEGAN M R. Institution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expenditure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evidencefrom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J].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18,29:20-39.
[21] POSTULA M, RADECKA?MOROZ K. Fiscal policy instruments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J].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review, 2020, 84: 1-9.
[22] HSIEH C T, KLENOW P J.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in China and India[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124: 1403-1448.
[23] CHOI B. Productivity and misallocation of energy resources: evi?dence from Korea s manufacturing sector[J].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2020, 61: 1-22.
[24] ANDERSEN D C. Do credit constraints favor dirty production:the?ory and plant?level evidenc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7, 84: 189-208.
[25] 宋马林, 金培振. 地方保护、资源错配与环境福利绩效[J]. 经济研究, 2016, 51(12): 47-61.
[26] 牛欢, 严成樑. 环境税收、资源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 世界经济, 2021, 44(9): 28-50.
[27] NIELSEN S B,PEDERSEN L H, S?RENSEN P B. Environmentalpolicy,pollution,unemployment,and endogenous growth[J].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1995,2:185-205.
[28] BOVENBERG L A, DE MOOIJ R A. Environmental tax reformand endogenous growth[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7,63:207-237.
[29] LANS BOVENBERG A,SMULDERS S. Environmental qualityand pollution?augmenting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a two?sector en?dogenous growth model[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5,57:369-391.
[30] COPELAND B R,TAYLOR M S. Trade,growth,and the environ?men[t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4,42:7-71.
[31] FULLERTON D, KIM S R.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and policywith distortionary taxes, and endogenous growth[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8, 56: 141-154.
[32] TOMBE T, WINTER J.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misallocation:the productivity effect of intensity standard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5,72: 137-163.
[33] 陈素梅, 何凌云. 环境、健康与经济增长: 最优能源税收入分配研究[J]. 经济研究, 2017, 52(4): 120-134.
[34] HELFAND G E. Standards versus standards: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ollution restriction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2,82:369.
[35] HOLLAND S P. Taxes and trading versus intensity standards:second?best environmental policies with incomplete regulation (leak?age) or market power[R]. 2009.
[36] SONG Z, STORESLETTEN K, ZILIBOTTI F. Growing like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 196-233.
[37] SCHOU P. Polluting non?renewable resources and growth[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0,16: 211-227.
[38] GROTH C, SCHOU P. Growth and non?renewable resources: thedifferent roles of capital and resource tax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7, 53: 80-98.
[39] BELLA G, MATTANA P. Policy implications in an environmentalgrowth model with a generalized hotelling depletion of non?renew?able resourc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2019, 8: 179-192.
[40] WANG J.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evi?dence from Chinese municipaliti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3,101:133-147.
[41] BAI C E,HSIEH C T,QIAN Y Y. The return to capital in China[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006(2):61-101.
[42] 郭庆旺, 贾俊雪.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1979—2004[J].经济研究, 2005(6): 51-60.
[43] 张军, 吴桂英, 张吉鹏.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1952—2000[J]. 经济研究, 2004(10): 35-44.
[44] LI Z,SUN J F. Emission taxes and standards in a general equilibri?um with entry and exit[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2015,61:34-60.
[45] LI Z,SHI S Y. Emission taxes and standards in a general equilibri?um with productivity dispersion and abatement[J]. Macroeconom?ic dynamics,2017,21(8):1857-1886.
[46] 臧传琴, 陈蒙. 财政环境保护支出效应分析: 基于2007—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J]. 财经科学, 2018(6): 68-79.
[47] STERN D I, COMMON M S. Is there an Environmental KuznetsCurve for sulfur?[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management, 2001, 41(2): 162-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