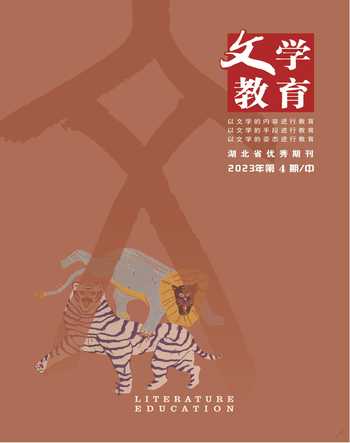契诃夫《变色龙》中的多种形象变色
2023-06-12李渊
李渊

内容摘要:在契诃夫的短篇讽刺小说《变色龙》中,奥楚蔑洛夫、赫留金和群众都是“变色龙”。小猎狗随着奥楚蔑洛夫的“变”而“变”。奥楚蔑洛夫、赫留金、群众及小猎狗的“变”展现了契诃夫对病态社会的讽刺和俄国“国民性”的批判。
关键词:契诃夫 《变色龙》 形象 奥楚蔑洛夫 赫留金 群众 小猎狗
伊凡·卡皮统内奇是契诃夫塑造的第一个“变色龙”形象。伊凡·卡皮统内奇在未见到上司之前是高谈阔论、振振有词的,而见到上司后立马变得唯唯诺诺、卑躬屈膝,这前后截然不同的表现,如同变色龙般的变,揭示出了他的奴性以及社会的弊端。“您不要相信那些犹大,那些变色龙!”[1]“经历过这样的事以后,看你还相信不相信这些变色龙的可怜相!”[2]契诃夫在《一个人两副嘴脸》的开头和结尾都明确的指出了伊凡·卡皮统内奇是“变色龙”。虽然伊凡·卡皮统内奇这一人物形象没有奥楚蔑洛夫典型、意义深远,但它特有的幽默讽刺的手法以为《变色龙》奠定了基础。“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是联系在一起的,文学从来不是一种无倾向、纯客观的文本,必然有作者主题的加入。有些作品看似荒诞不经,却能真切地表现出在某种社会条件和生存状态下的人们的真实感受。”[3]变色龙原本指自然界的一种神奇的动物,皮肤的颜色能随着四周的物体的颜色而改变。但随着契诃夫《变色龙》的发表,“变色龙”一词逐渐演变成为被社会符号化了的指代,成为了见风使舵的小人的代名词。
一.奥楚蔑洛夫
作为《变色龙》的主人公,奥楚蔑洛夫毋庸置疑的成为“变色龙”形象的代表,在“变”中将沙皇走狗的见风使舵、趋炎附势和阿谀奉承的特点展现的淋漓尽致。
1.五次“变色”
作为一名警官,最重要的便是实事求是,用证据说话。而作为警官的奥楚蔑洛夫却大相径庭,在“狗咬人”的事件中,根据狗主人的不同而数次改变立场。
奥楚蔑洛夫从人群里听到“这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狗”[4]时,立马转变自己的态度,从扬言要“拿点儿颜色出来给那些放出狗来到处乱跑的人看看”[5]到指责赫留金异想天开,想得到一笔赔偿费,这是奥楚蔑洛夫的第一次“变”。当巡警叶尔德林依据将军家的狗都是大獵狗而指出“这不是将军家里的狗”[6]时,他第二次转换嘴脸,对赫留金进行安慰,又一次扬言要“好好教训他们一下!是时候了。”[7]在奥楚蔑洛夫还没付出实际行动时,巡警和群众又提出可能是将军家的狗的结论,奥楚蔑洛夫便进行了第三次的“变”,再一次对赫留金发出指责“你这混蛋,把手放下来!不用把你那蠢手指伸出来!怪你自己不好!……”[8]将军家厨师的出现促使奥楚蔑洛夫完成了最后两次的“变”。当厨师否认是将军家的狗时,奥楚蔑洛夫进行了第四次的“变”,“这是条野狗!”“弄死它算了”。[9]但在得知是将军家哥哥的狗时,奥楚蔑洛夫对小狗的态度发生大转弯,由“这是一条野狗”转变为“好一条小狗”。
契诃夫让身为警官的奥楚蔑洛夫在同一件事情上自相矛盾足足五次,接连不断的极度反转增强了人物形象塑造的夸张与讽刺效果,增强了文本的张力。五次“变”不仅显示奥楚蔑洛夫见风使舵,更将社会人云亦云,恃强凌弱的风气通过“变”展现出来。
2.“变”的工具——军大衣
奥楚蔑洛夫那崭新的军大衣,让人不禁联想到契诃夫的另外一篇讽刺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中别里科夫的“套子”。虽然在很多方面别里科夫的“套子”和奥楚蔑洛夫的军大衣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它们却殊途同归,它们都能够成为解读主人公内心的切入点。
契诃夫认为:“简洁是天才的姐妹。”在文本中,军大衣仅仅出现四次,每一次的出现都是寥寥几笔,简洁明了。那军大衣是如何作为奥楚蔑洛夫“变”的工具展示其内心的呢?
军大衣首次出现是随着人物的出场而出现在读者眼前。“警官奥楚蔑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提着小包,穿过市场的广场。”[10]奥楚蔑洛夫的军大衣是崭新的,从物质层面看,奥楚蔑洛夫是不愁吃穿的,从侧面表明奥楚蔑洛夫是沙皇忠实的警犬。当将“新的军大衣”与随后的“盛满了没收来的醋栗”联系起来时,奥楚蔑洛夫的欺凌弱小、装腔作势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并为下文奥楚蔑洛夫利用军大衣进行“变”埋下了伏笔。
军大衣的第二次出现是人群中有声音说狗主人是将军时,契诃夫的描写是:“席加洛夫将军?哦!……叶尔德林,帮我把大衣脱下来……真要命,天这么热,看样子多半要下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还不懂:它怎么会咬着你的?”[11]“脱”是一个关键的字眼,表现出了奥楚蔑洛夫内心的害怕和慌张,仿佛狗就是“将军”一般。其次,天并非是真要下雨,而是奥楚蔑洛夫为了掩饰自己的出尔反尔的行为找的一个借口,也为自己后面的态度的再次转变争取时间。最后,脱军大衣为后面穿军大衣埋下了伏笔。此外,在脱军大衣这个细节上,契诃夫采用短句加省略号的形式展现奥楚蔑洛夫语言的简短,话题转换的迅速,这恰恰将语气中的恐慌和害怕呈现出来。“真要命”表面上是指天气,实际上表明得罪了将军,是真的要了自己的命。奥楚蔑洛夫那副谄媚之像活灵活现。
军大衣第三次出现是在奥楚蔑洛夫发生第三次变脸时,再一次从群众处得知狗是将军家的时。“哦!……叶尔德林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吧……好像起风了,挺冷……”[12]奥楚蔑洛夫的由穿到脱经历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同样奥楚蔑洛夫的语言简短,换题快转,但是与语气中的恐慌和害怕却愈加明显。与“脱军大衣”相同,奥楚蔑洛夫穿军大衣这一行为同样是在为自己的变脸找一个台阶,分散群众的注意力。“挺冷”的“冷”不在起风了冷,而是奥楚蔑洛夫内心的寒冷和颤栗。军大衣一脱一穿的细节将奥楚蔑洛夫趋炎附势的走狗形象表现的淋漓尽致。
军大衣的第四次出现是在人物离场时。“‘我早晚要收拾你!奥楚蔑洛夫向他恐吓说,裹紧军大衣,穿过市场的广场径自走了。”在这里,同一件崭新的军大衣,契诃夫对其描写不是“穿”,而是“裹紧”。在经历了五次变色之后,奥楚蔑洛夫不再是刚刚出场那般威风凛凛、盛气凌人,而是灰溜溜的,不得不用军大衣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慌乱和狼狈。军大衣这一工具随着人物来,又随着人物去。契诃夫用军大衣这一简单的工具,刻画了奥楚蔑洛夫在“变色”过程中内的心恐慌和害怕,可谓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二.赫留金
在《变色龙》中,不仅仅是主人公奥楚蔑洛夫在变,其配角赫留金也在“变”。
赫留金表面上是一个受害者,实际上却是一个勒索者。赫留金的出场是伴随着“探”“扑倒”和“抓住”这三个动作,动作熟悉连贯得根本不像一个被狗咬伤的病人。赫留金为何对一只咬伤他的狗如此紧张且拼了命也要抓住它?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社会,沙皇的反动高压政策使整个俄国笼罩在军警宪兵的白色恐怖之中,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商店和饭店“面对着这个世界,就跟许多饥饿的嘴巴一样;门口连一个乞丐也没有。”[13]连身为沙皇警犬的奥楚蔑洛夫都要靠着“没收来的醋栗”果腹,何况身在底层的赫留金。因此赫留金拼尽全力也要抓住小狗,不管狗是不是主动咬伤自己,其最终目的是向狗主人索要赔偿。在赫留金在讲述事情的经过时,“用手罩在嘴上,咳嗽一下”[14]这和奥楚蔑洛夫用脱军大衣和穿军大衣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慌乱有异曲同工之妙,均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慌张和害怕,掩盖自己说谎的实质。而在奥楚蔑洛夫揭穿他是想得到一笔赔偿金时,立马从受伤可怜变得强词夺理,恶狠狠的骂拆穿他的独眼鬼,又搬出法律,又找当宪兵的兄弟做靠山,其最终的目的依旧是讹诈狗主人的赔偿金。
赫留金也是这场“狗咬人”事件的主导者。回到“狗咬人”事件的最初,“伙计们,别放走它!这年月,咬人可不行!逮住它!哎呦……哎呦!”[15]当赫留金被狗咬伤,他的第一反应是要抓住它,再通过两个“哎呦”表达自己的疼痛感,显然是故意为之,想博得别人同情赫留金陈述事件时,他“半醉的脸”是有“神气”的,更表明“狗咬人”这个事件是赫留金为骗取赔偿金而自编自导的一出闹剧。
赫留金是一个无聊自私粗鲁的人,一方面口口声声的宣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另一方面又欺凌弱小,谄媚权势。而这样的性格特征又是赫留金在那个社会环境下追求生存的手段,在本质上是和“变色龙”奥楚蔑洛夫的“变”相同的,其区别在于赫留金是被统治的阶级,是属于底层人民,而奥楚蔑洛夫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三.群众
不仅拥有姓名和职业的奥楚蔑洛夫和赫留金在“变”,没有姓名和职业作为“看客”的群众也是在“变”的。
契诃夫对作为“看客”的群众,未进行详细的划分,将其融为一个整体。他们和赫留金处于相似的环境和地位,本来应和赫留金同仇敌忾共同对抗沙皇的封建专制统治,然而他们却站着了赫留金的对立面,选择取笑灰溜溜的赫留金。他们与鲁迅笔下的各式各样的“看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麻木不仁、冷漠无情的。
在“狗咬人”事件尚未发生时,广场上本是没有人的、空荡荡的,是寂静的。但是当“狗咬人”这个琐事发生之后,人群立马“钻”了出来,有人甚至是睡意正浓,这明显是放弃了休息来围观发生了什么热闹。人群这一静一闹的对比,揭示出人群的浑浑噩噩,他们就喜欢看热闹,似乎看热闹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唯一乐趣。
作为看客的群众,他们围观了奥楚蔑洛夫的断案过程。契诃夫对群众的描写并不多,却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这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狗。”人群里有人说。[16]
“没错儿,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人说。[17]
从“好像”到“没错儿”,群众的态度的变化说明他们并没有证据证明狗的主人是将军,他们并不在乎奥楚蔑洛夫的判断是否公正,是否有依据,他们最终的目的在于看热闹。这两处对群众的描写看似无关紧要实际上直接促使了奥楚蔑洛夫的两次“变”。奥楚蔑洛夫的断案过程无疑是在群众面前进行的一场喜剧表演,为了向“观众”展示自己的公正无私,事实上,却在“观众”的眼前自相矛盾一次又一次。在群众的“看”中将奥楚蔑洛夫的虚伪和谄媚展现的淋漓尽致,将其势力虚伪的丑恶形象栩栩如生的展示在读者眼前。身为“看客”的一群人是无聊、愚昧、冷漠、麻木的,然而这些都是沙皇专制下的病态社会所给予的。人群似有似无的从事件最初一直贯穿到最后对赫留金的嘲笑,承载着契诃夫对俄国社会更深刻的思考即对俄国“国民性”的批判。
四.小猎狗
除了人物在“变”,文本中唯一的动物——小猎狗也在“变”。与奥楚蔑洛夫、赫留金和群众的“变”不同,小猎狗的“变”是被动,是通过奥楚蔑洛夫之口发生变化。
在奧楚蔑洛夫发生的五次“变色”中,小猎狗也发生了“变”:从“这多半是条疯狗”到“它是那么小”到“完全是个下贱胚子”到“这是一条名贵的狗”再到“那它就是一条野狗”最后到“好一条小狗”。小猎狗出现这些“变”的原因在它的主人到底是不是席加洛夫将军,同时也是促使奥楚蔑洛夫发生五次“变”的直接原因。契诃夫将奥楚蔑洛夫的“变”和小猎狗的“变”放置于同一平行时空,使奥楚蔑洛夫这一人物形象与沙皇忠实警犬合二为一,更将奥楚蔑洛夫处处维护封建官僚阶级利益的丑陋形象展现出来。在一只小猎狗面前,奥楚蔑洛夫已丧失尊严和人格,不断自相矛盾,不断推翻自己的结论,那在统治者面前,奥楚蔑洛夫的谄媚与阿谀奉承可想而知。奥楚蔑洛夫“变色龙”的性格本质在小猎狗的一系列变化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换言之,小猎狗如同一块镜子,使奥楚蔑洛夫见风使舵、欺下媚上、势力虚伪的走狗嘴脸和丑恶卑鄙的灵魂一览无余。
文本中的狗本来是“一条白毛的小猎狗”,“脸尖尖的,背上有块黄斑”[18]只有三条腿还一瘸一拐。因其主人的身份地位和权势的改变而受到了不同的对待,奥楚蔑洛夫所关注的不是小猎狗这个动物的本身是否需要公平正义,而是关注其所附带的社会属性与社会价值即主人的身份地位及其权势。换句话,只要小猎狗的主人是将军,那么小猎狗就是“小的”“名贵的”“伶俐的”“好的”;反之则就是“疯狗”“下贱胚子”“野狗”。咬人的小猎狗被宣判无罪,灰溜溜的进场,神气的离场,而赫留金却被奥楚蔑洛夫威胁,这仅仅是因为小猎狗的主人是将军的哥哥。通过小猎狗富有戏剧性的“变”,契诃夫揭示了奥楚蔑洛夫之类人,是沙皇专制豢养的忠实走狗,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沆瀣一气欺压鱼肉百姓,不顾百姓死活。
契诃夫在《变色龙》中,幽默巧妙地将典型的“变色龙”形象——奥楚蔑洛夫刻画得鲜活生动,此外又赋予赫留金、群众等配角“自私自利、事故圆滑、欺上媚下”等诸多“变色龙”的品质特征,进而把对沙皇专制统治的黑暗与腐朽以及社会麻木不仁、宠媚权贵的风气的讽刺推向了高潮,也展现出契诃夫对俄国民众愚昧无知的“国民性”的批判。
参考文献
[1]契诃夫著,左少兴译.契诃夫作品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5-7.
[2]契诃夫著,汝龙译.契诃夫短片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2-16.
[3]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90.
[4]陈长卫.《变色龙》之“变”微探[J].语文天地,2018(08):11-12.
[5]刘军.人群:《变色龙》中的别样风景[J].语文学习,2020(03):51-53.
[6]邱水灵.还原:从“警官”的身份说起——《变色龙》中奥楚蔑洛夫形象再探[J].语文教学之友,2020,39(05):29-31.
[7]孙绍振.《变色龙》:喜剧性五次递增[J].语文建设,2014(13):42-45.
[8]王明.从人物话语的断裂解读《变色龙》[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7(26):63-64.
[9]王飞.用题目延伸的方法解读《变色龙》[J].中学语文教学,2019(05):60-62.
[10]于秋潭.《变色龙》的创作风格与人物语言特色[J].语文建设,2014(29):41-42.
[11]张建生.《变色龙》的人物形象及讽刺艺术探析[J].語文建设,2016(30):37-38.
注 释
[1][2]契诃夫:《契诃夫作品集》,左少兴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5,7.
[3]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90.
[4][5][6][7][8][9][10][11][12][13][14][15][16][17][18]契诃夫:《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4,13,14,15,15,16,12, 14,15,12,13,12,14,15,13.
(作者单位:重庆开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