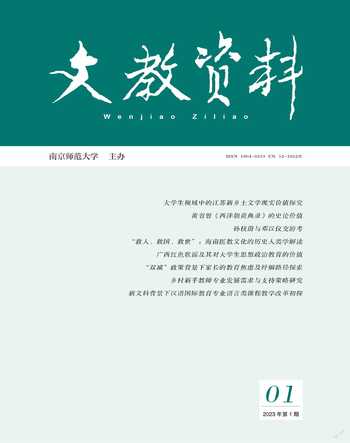论梁启超《管子传》中的管子研究
2023-06-11王春龙
王春龙
摘 要:梁启超是近代管子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成书于1909年的《管子传》是其研究管子的代表作。梁启超的管子研究深受康有为的影响,早年的独特经历也使得梁启超的研究兼具中西学术特色。其管子研究一开始便着眼于国际,在“西学中源”说的基础上对管子其人其学在历史中的误解进行澄清并给予积极评价,注重阐发管子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价值,同时在今文经学“通经致用”思想的主导下,对管子法治主义思想进行详尽的阐释,并借以构建起颇具近代色彩的社会改造理论体系。梁启超对管子的研究代表着戊戌思潮下仁人志士对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使命的努力与思考,尽管其研究具有一定的时代性的局限,但其理论价值和现实影响同样值得今人重视。
关键词:近代哲学 梁启超 《管子传》 管子 法治主义
纵观梁启超有关管子研究的著作,其于1902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对管子其学派归属、《管子》作者进行明确说明。梁启超与汤学智1903年在《新民丛报》上合撰《管子传》,据学者王学斌考证,文章具体内容多与1909年版的《管子传》重合[1],可视为1909年版的最初版本。1906年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和《开明专制论》中,对管子的研究涉及不多。1909年版的《管子传》不仅对管子其人、其学、其功绩做出了正面的评价,还以今文经学的角度和国际化的视角对《管子》本身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挖掘,着重阐发了管子思想中的法治主义思想。但自1909年完成《管子传》之后,梁启超便不再对管子进行过多的关注,无论是1922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社点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讲演,还是1924年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表明梁启超晚年仅在原先研究的基础上对以往的部分研究进行了考证和辨伪,对管子思想价值则一直保持着认同态度。总之,在梁启超管子研究的诸多著作中,只有1909年版的《管子传》最为详尽、全面且深入地对管子进行了专门研究,因而1909年版的《管子传》对梁启超的管子研究以及近代管子研究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梁启超管子研究的缘起与旨趣
回顾近代百年的历史,中国出现数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无数仁人志士奋起以自强。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的一名学者,其思想颇具有时代特征。独特的经历塑造了其独特的学术视野,旧学和新学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使其學术兼具中西特色。管子研究是梁启超学术思想的一部分,而究其源流则来自其老师康有为的影响。
首先,康有为系统地传授了梁启超今文经学的知识,奠定了梁启超管子研究的中学基础。今文经学自东汉以后不断衰微,至清代中期由庄存与重新提倡,又经刘逢禄、宋翔凤等人的努力,今文经学形势渐好,到康有为将今文经与近代变法联系起来,今文经学才得以复兴。从学海堂求学到万木草堂拜师可谓梁启超整个学术生涯中的一大转折点,意味着梁启超学术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转变。梁启超在学海堂苦读三年后,便转头拜今文经学大家康有为为师。在康有为的言传身教下,梁启超较为系统地学习了今文经学的知识,广泛地接受了康有为所述的孔子改制、新学伪经、大同三世等理论,并参与《新学伪经考》等书的编写工作,及至后来时务学堂讲学时期,还写成了《春秋界说》和《孟子界说》等作品,为康有为托古改制鸣锣喝道。
其次,康有为彻底激发了梁启超对西学的兴趣,开启了梁启超管子研究的国际化视野。梁启超真正开始对西学展开学习应始于万木草堂学习时期,这源于康有为对学生的影响及严格要求。早年的康有为对西学兴趣颇多,曾大量购入西学著作进行阅读和学习,因此在万木草堂讲学期间也常常要求学生广泛阅读各类西方著作。正因如此,梁启超对西学的兴趣被彻底激发起来,乃至于后来流亡日本期间,在见到诸多西方著作的日文译本后刻苦学习日文,以期对西方的学术思想拥有更多的了解。这一期间的大量阅读,为梁启超日后的学术研究及在报刊上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宣传奠定了坚实的西学基础。
再次,康有为引导梁启超关注学术史,奠定了其日后管子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思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课过程中强调对“学术源流”的关注,梁启超也曾正面表示出对“学术源流”的浓厚兴趣。据梁启超回忆:“先生每逾午则升坐讲古今学术源流,每讲辄历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每听一度,则各各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退省则醰醰然有味,历久而弥永也。”[2]后来梁启超关于学术史研究的关注也应来源于此。此外,在康有为讲述“学术源流”过程中,也一度表示出他对管子的好感与推崇,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第一,康有为对《管子》的文采、管子“言治”和“言法”的思想价值以及管子的生平功绩进行了充分肯定;第二,将管子纳入法家谱系,尽管“在康有为那里,‘法家是不存在的,因为法家不是独立的学派”[3],但是仍然肯定了管子思想与法家思想之间具有某种联系;第三,判断《管子》成书年代为战国时期。康有为对于管子的基本论断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梁启超管子研究的理论基础。此外,康有为对管子的重视更多来源于对现实救亡图存的思考,在这一点上也推动了日后梁启超对管子思想中法治主义的关注。
总体而言,梁启超的管子研究思路源于其师康有为的管子研究:其于1902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将管子归为法家;对《管子》一书的价值进行积极肯定,赞其为“实国家思想最深切著明者”[4];判断其书非管子所作,乃战国时期管子后辈所纂述;指出管子所属北派学术精神具有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明政法等特征,均可见到其师康有为的影子。而在研究旨趣上,梁启超与其师皆基于现实的需求而关注管子,这在1909年版的《管子传》中得到具体体现。
二、梁启超对管子其人、其书的考辨
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旧与新、中与西交汇的时代,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以及如何守卫本土文化,成为整个时代急需回答的问题。“风行一时的‘西学中源说正是那时主张学习、引进西学的中国人对这一问题所做的回答,这种视中学为源、西学为流的文化观的提出,显然是为了消解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即中学与西学之间的紧张关系,既疏通西学东渐的渠道,同时又维护中国本土文化的地位。”[5]因此“西学中源”说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色彩,梁启超在《管子传》的例言中也曾说道:“时以东西新学说疏通证明之,使学者得融会之益。”[6]故而梁启超的管子研究,实际上是在西学中源说的基础上展开的。
首先,梁启超对以往学者关于管子的误解做出解释,并以国际化视角阐释了管子研究的价值。梁启超指出传统儒家中对管子产生误解的源头在于后世“陋儒”对孔孟之言的误解:孔子对管仲的不满更多是针对其“器小”,对其事业仅限于齐国而不能广施于中国表示惋惜,然而却也赞许管子之仁,对管子的功绩进行了正面肯定。孟子论管子时常常透露出轻薄之意,而梁氏指出孟子对管仲的不满仅是有为而发,因为管仲的学问虽不及孟子,但是管子之事业却也有孟子所不能及的地方,并以此反驳了后世陋儒批判管子的迂腐末论。为了更好地说明管子研究的价值,梁启超从国际化视角出发,将管子与西方思想家们进行比较:其一,西方的自由与民权之学起源于18世纪末,而管子的自由与民权之学其提出更早且更中正;其二,西方政治根据政治主张的不同分为君主派、人民派和国家派等三派,而其中国家派的提出不超过二三十年,然而管子却在几千年前就已提出;其三,西方政治家和政治学者二者分立,而管子却兼具政治家和政治学者的双重身份,由此凸显管子研究的价值。
其次,梁启超对研究管子的方法进行了说明,并对《管子》其书真伪及成书年代做出基本判断。梁启超指出目前为管子立传的文献仅有《史记》一本,《史记》本为别裁之书,其文中的敘述往往不依照常用规格,况且司马迁常常掺杂个人情感于其中,因此《史记》中的管子传必然不能体现出管子全貌,因而想要真正了解管子之全貌必然要深入对《管子》的解读。对于《管子》一书,后人多认为是战国时人假托管子所作,原因在于《管子》书中记载了管子去世后的部分事件,因此梁启超也认为《管子》其书并非全部都是管子所作,还有一部分可能为齐国稷下先生所作,但是这部分作品仅占十之三四。而且非管子所作部分也大体上由管子思想衍生而成,因为自管子去世后,齐国沿用其政治思想长达数百年,所以齐国的稷下先生们的讨论与记载也多受管子影响。况且作于战国时期的《墨子》也有类似情况,《管子》的这种状况也并非独例。
再次,梁启超通过对管子所处时代背景及其生平经历的考察,对管子研究的现实意义进行了说明。在梁启超的视野下,进行管子研究有两种现实意义。其一,管仲之事功为后人所难及,其治国思想值得我们重视。春秋时期的齐国是管子的母国,地理位置上自建国之初便远离王室而与戎狄相接,经济上虽有姜太公之鱼盐政策却还是收获未丰,内政上自建国至桓公即位三百年间内乱不止,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不断,然而这样的国家却在管仲的治理下富强起来。其二,管子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自信值得国人学习,梁启超指出:“中国人爱国心颇弱,苟不得志于宗国,往往北走胡南走越,为敌国伥以毒同类。”[7]然而管子却虽知死而不受鲁政,虽死君而侍于桓公,可见管子之爱国非忠于君而忠于国,其爱国心之昭昭,当为国民的典范。管子之自信也非常人所能及,他超过其他政治家之处,不单在于他敏锐的眼光、高明的手腕,还在于他的自信。管子“不名一长而能尽众长”,其用人之自信以及对自己之自信都尽数显现。
三、梁启超对管子法治主义学说的研究
梁启超对法治主义的关注由来已久,其早在1902年的《新民丛报》中便对西方有关政治、法理、经济的学术思想进行过介绍。所谓“法治主义”即以法为治,强调“要之不离乎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奋迅振厉,严肃而整齐之”[8]的法治精神。梁启超指出一个国家的存在有三个要素,即土地、人民和主权,只有三个要素兼具,一个国家才能够形成。法是一个国家主权外显的表现,无法也便无国。法治作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手段,无论是过去、现在又或者是将来,也定然不能为国家所抛弃。梁启超将管子视为法治主义发明的“始祖”,其目的并非将管子的法治与近代西方的法治进行比较,而是向中国民众阐释二者之间一以贯之的法治精神。
首先,梁启超对管子推行法治的必要性进行了说明。法治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国家是应人民的现实需求而出现的。而国家之所以能够满足于人民的需要则全赖于法,法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法的本质天然具有干涉性的成分,国家若是一切放任,则是自荒其职。梁启超对西方干涉主义更为青睐,并断言干涉论的胜利是时代的大势。梁启超对同为“纯主干涉者”的法家进行肯定,认为唯有对国家进行干涉方能成就功业,中国也唯有实行干涉主义方才能救亡图存。
其次,梁启超对管子法治与君主、人民、政府的关系进行梳理。对于法治主义与君主的关系,梁启超认为管子所处的时代贵族势力极大,管子通过立法“增益君权”实际上是出于压制贵族的现实需要,而且国家所立之法,君主与臣民皆要受其限制,非为一家之私。对于法治与人民的关系,管子认为爱民莫若爱法,因为爱法可以使民“辑和于内而竞胜于外”[9],对内民众可以安居乐业,对外足以自保自养,人民是国家统治的客体,为法必严方能取信于民且使人民的利益达到最大。对于法治主义与政府的关系,梁启超认为“凡法治国,莫贵乎有责任大臣”[10],管子所发明者,君主无责任而臣有责任,因为君主有责任便会导致无人问责,纠问伤损君主威严,不纠问则国危,因此君主委权于大臣,使臣下代负责任,君主不可以随意侵其权,这与近代内阁制颇为相似。
再次,梁启超对管子法治的目的进行了论述。梁启超指出管子之所以远贤于商鞅,就是在于其除富国强兵外还有一大目的:“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11]管子并非不重视德治,而是认为“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12],先有法治而后才能有德治,法治的目的是更好地进行德治。梁启超对管子的这种德法兼用思想甚为推崇,认为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单纯地去讲道德感化并没有多大成效,因此一国之中有道德责任心薄弱者的必须借助法令才能改正,使奸邪小人不敢违背,而民众自然会日益进于德而习于礼。当然,管子对于法治的运用仅仅是定分以止禁,并不排斥道德本身的感化力,而是希望化民成俗于无形之中。
四、梁启超对管子经济政策的诠释
梁启超所处的时代面临的是救亡图存的问题,人们关注更多的是社会制度变革的方法。梁启超对管子经济政策的展开,实际上是戊戌思潮下仁人志士对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使命的努力与思考。
管子的内政大体上可分为教育、理财、治兵等三大方面,梁启超对管子的教育、治兵等方面所述不多,但对管子之理财的论述则颇为完备。
其一,提出奖励生产之政策。梁启超指出凡言经济当以生产为首务,许多不明经济的人往往将金银与财力相等同。但是管子认为,“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13],金银仅仅只是操控百货的工具,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真正的富足,而想要国家真正富强则必须使全国之国民都变为生产者,主张通过法治对生产进行干涉。
其二,提出均节消费之政策。梁启超认为管子在意识到奢侈的危害的同时,也看到适当奢侈的好处,“俭则伤事,侈则伤货”[14]。过分节俭会对商品的再生产产生损伤,不利于市场健康有序发展;而过分奢侈则会伤及资本,使各种产业不能兴盛。
其三,提出调剂分配之政策。西方对分配政策的重视起源于近代,然而管子早在数千年前便已提出。管子认为所有的政治经济上的弊端都是因贫富不均所致,政府必须对财富分配进行一定的调节,因此提出轻重之说,即通过对金属货币和具有一定货币功能的谷物操控进而达到平衡经济目的的手段。这种手段必须由国家来进行,以防止豪强进行垄断。梁启超认为这与近代社会主义学说颇为相似。
其四,提出财政政策。管子所提倡的财政政策被梁启超称之为“无税主义”,据梁氏考察其理由有三:“其一则以为租税妨害国民生产力也,其二则以为租税夺国民之所得也,其三则以为租税贾国民之嫌怨也。”[15]然而一个国家的发展必然需要以一定的财力来支持,管子主张通过将盐铁收归政府专卖、由官方经营商业两种方式作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
其五,提出国际经济政策。梁启超对此极为重视,他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至关重要,“若夫经济力之一消一长,能影响于一国之兴亡”[16]。梁氏指出我国的管子最早提出商战,主张通过利用本国优势特产形成价格垄断,以此操控天下物价。西方近千年来对于商战一直颇为重视,而我国自秦汉以后政治家们在这方面却少有重视,梁启超对此深感遗憾。
五、结语
梁启超对管子的研究源于现实政治的訴求,而非学术研究的需要。《管子传》的出现,一方面客观促进了西方学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另一方面深入挖掘了管子思想中的现代性价值。不可否认的是,为了以一种易于国人接受的方式更好地宣传西方学术思想,梁启超在对管子进行解读过程中加入了一些个人的附会和改造。张锡勤曾指出:“在戊戌前后,捍卫中国本土文化的问题虽已引起关注,但时代的需要则主要是引进、吸收异质的西学。”[17]这就注定了梁启超的诠释天然地具有某种时代性的局限。
参考文献:
[1] 王学斌.梁启超管子研究之肇端——1903年《管子传》考析[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17-20.
[2] 梁启超.南海先生七十寿言[M]//饮冰室文集:第12册.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34.
[3] 魏义霞.康有为视界中的管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5):154-160,176.
[4]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饮冰室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190.
[5] 张锡勤.“西学中源”说漫议[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13-16.
[6] [7] [8] [9] [10] [15] [16] 梁启超.管子传[M].饮冰室文集:第5册.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3,10,13,22,27,42,60,64.
[11] [12] [13] [14] 管子[M].李山,轩新丽,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1:2,696,239,77.
[17] 张锡勤.论康有为对儒学的改造[J].哲学研究,2004(5):4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