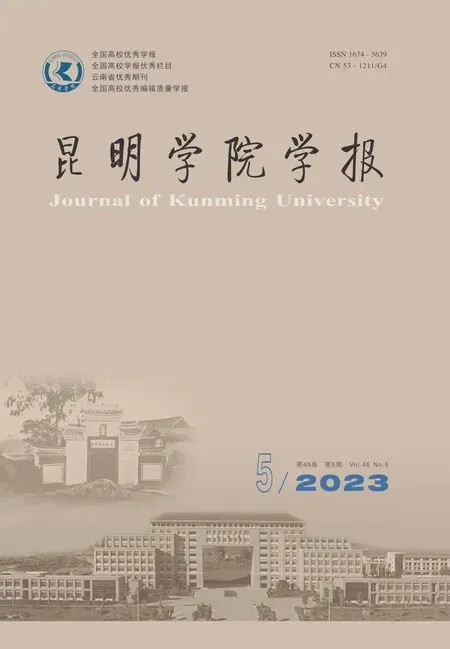社交媒体如何影响自主性:基于哲学和伦理学的思考*
2023-06-07郭佳楠陈婉莹
郭佳楠,陈婉莹
(1.郑州工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2.中国人民大学 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一、引言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数字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对用户自主性的影响研究,同时社交媒体平台也日益成为信息交流传播的重要渠道。与传统媒体不同,社交媒体内容广泛,通过平台全球传播,网络环境复杂,为信息操控提供了可能。在当下,虽然不少学者就新技术对自主性的影响已在人工智能与社交机器人等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例如琼·恩东古(Joan Ndung’u)等人通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了社交媒体的使用对肯尼亚私立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社交媒体的使用会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影响。其中,人们的社交和认知与组织公民行为呈正相关,享乐与组织公民行为呈负相关。此外,马尔辛·弗朗茨凯维奇(Marcin Frackiewicz)也指出,社交媒体的使用对用户行为自主性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一方面,社交媒体可以帮助用户找到更多相关内容,提高内容审核的准确性,并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广告;另一方面,社交媒体还可以用来操纵用户的行为,传播错误或虚假信息,尤其是对于弱势群体而言,社交媒体可以用于跟踪用户行为并引导用户做出违背其自主性意愿的行为,从而引发人们对隐私和数据安全的担忧。我国学者代宝和罗蕊等人从社交媒体倦怠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社交媒体对用户行为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价值、感知效用满足等认知性后果的影响。然而,笔者通过整理发现,多数研究社交媒体对自主性影响的文献都未能从哲学层面对该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这导致学界很可能忽视社交媒体对自主性在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全方位影响。因此,从对作为一种道德概念的自主性以及社交媒体作为当代生活重要表征工具的理解出发,需要深入探究这些影响及其成因,从而为人类社会交往指明道路。
基于此,文章首先对相关哲学文献中关于自主性的不同概念进行系统分析,并认为自主性在广义上是指人们能够发展自我的能力、具有拥有真实目的性并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关键性特征,而不是被他人操纵、威胁和控制。其次,本文立足于数字化的时代背景,详尽阐述社交媒体的内涵意蕴,并重点探讨社交媒体对用户数据、注意力与行为等方面的影响与控制。笔者试图概述这种控制可能对社交媒体用户造成的3种具有相关性但却截然不同的自主性危害:(1)不尊重用户的自主权;(2)干涉用户合理正当地行使自主权;(3)损害用户的自主性能力及其发展。最后,在实践层面上,针对社交媒体对用户自主性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出新时期社交媒体治理与监管的模式和路径。
二、关于自主性的哲学思辨
实际上,关于自主性的哲学文献不但涉及的学科领域广泛,而且还包含多个方面的内容。相关研究对自主性已有了一些基本理解,并通常从程序性、实质性、关系性3个维度意义上系统地回顾自主性理论的相关研究。
关于自主性的程序性理论认为,特定的内容中立程序是实现自主性的充分必要条件。根据这样的观点,“一个人为自己所决定的东西即可以包含任何特定的内容。”[注]孟玺.社交媒体用户虚假信息识别意向影响机制研究[J].现代情报,2023,(4):39-42.相较于此类观点的自主性而言,重要的是无论人们选择何种内容,在选择的过程中都必须遵循适当的程序,并且通过考量人们在处理所谓的压迫性社会化案例时所面临的挑战,能够对理解这些观点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注]袁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的虚假信息研究[J].国际安全研究,2022,(3):32-56.自主能力则是代理人能够自主行动所需的那些技能和权力。例如,那些推理和批判性地反思他们的价值观、想象不同的选择、发展善的概念以及将自己视为值得尊重的、能够实现自我指导的代理人的能力。此外,压迫性的社会环境也可能影响自主性代理人在做出和反思自己的选择时使用的批判性反思与推理技能。[注]CHRISTMAN J.Autonomy and personal history[J].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1991,(1):1-24.
相比之下,关于自主性的实质性理论认为,社会个体及其选择只有在满足某项实质性条件下,才能被看成是自主的。自主性的实质性理论可以进一步分为弱理论与强理论。弱理论通过设定某些条件来实现社会个体的自主性,而这些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被限制并告知”了其要选择的内容,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的选择可以算作是自主的,同时仍要保持最大限度上的内容中立。而强理论则完全决定(或至少更严格地限制)人们自主选择的内容。在社会个体自主性较弱的情况下,选择被视为实现自主性所必须满足的条件,这些条件通常包括“自尊、自爱以及对自尊的评价态度”[注]BOSNJAK M,AJZEN I,SCHMIDT P.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Selected Recent Advances and Applications[J].Europe’s Journal of Psychology,2020,(3):352-356.。我们可以将这些自我态度视为一系列广泛的自主能力的一部分,这些能力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及其选择算作自主。虽然强自主性的实质性理论可以通过提供独立于压迫性环境的、标准的客观规范条件来解决压迫性社会化问题,但它们却仍然面临着要识别与证明客观的良好目的和价值的问题。
关于自主性的弱实质性理论则更多地专注于一套社会个体自主能力、相关技能以及自我态度的满足与实现。自主性的关系性理论认为,自主性及其相关能力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能力”,因为社会化在其发展与使用过程中发挥着必要的作用。然而,如果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和政治结构是压迫性的、剥削性的或不公正的,那么这种对该能力的开发与使用就会受到破坏。卡特里奥娜·麦肯齐(Catriona Mackenzie)认为,自主性应该具有的3个维度,即自我决定、自我治理以及自我授权。其中,自我决定指的是一个人做出相关选择的自由,这些选择反映了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控制。自我治理关涉一个人的决策能力,反映了一个人的身份与价值观,即通过做出反映代理人真实偏好的决策。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决策,我们要么在批判性反思后认可它们,要么承认它们并为它们负责,这样我们的偏好与价值观才“真正地”是我们自己的。自我授权则需要对一个人的身份、价值观和选择拥有权威。因此,自我授权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它要求我们将自己视为一个值得尊重的代理人,有权在其他代理人社区中确定我们的目标。
为了厘清这些对自主性实现的不同维度的影响,在下文中笔者简要地区分关于自主的纲领性或全球性与情节性影响将如何更有效地从哲学的语境中去重新认识社交媒体的存在。纲领性或全球性自主更侧重于一个人的整体生活和执行其生活计划的能力。相反,情节性自主适用于“特定情况”并且“仅限于单个行为或动作”。通过分析二者之间的区别,能够帮助人们评估个体自主性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仅在一个领域或选择中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
三、社交媒体对自主性实现的负面影响研究阐释
尽管关于社交媒体概念的研究已取得较多共识,但有关怎样看待“社交媒体”与“自主性”的关系等具体问题仍存在较大的分歧。一种声音如克里斯蒂安·富克斯(Christian Fuchs)在《达拉斯·斯麦兹的今天——受众商品、数字劳工辩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理论》中指出的那样,社交媒体的范畴应该包括“相关的应用程序,如博客、Twitter、社交网站或视频、图像、文件共享平台”,它们将提供“使两个或多个社会群体能够互动的数字基础设施”。[注]FUCHS C.Dallas Smythe today—The audience commodity,the digital labour debate,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tical theory[J].TripleC,2012,(2):692-740.同时,社交媒体也是一种数字环境,个人、团体或组织可以在其中通过共享文本、照片、图像、视频或其他数字格式的内容和信息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应该说,社交媒体平台是根据个人用户的数字足迹对内容进行个性化设置,并能够根据数据分析针对特定人群。这使得社交媒体公司及其客户相对于传统媒体具有更显著的优势,因为它们可以定制消息和广告,以适合其想要接触的用户,而不是像传统媒体那样——所有消费者都会收到相同的内容、消息或广告。
此外,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另一个区别是社交媒体公司及其客户有能力进入“私人的、无形的社会领域”,通过不断涉入“越来越个性化的、私人的交易”,使得这种交易被从一个可能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共领域中移除,从而避免了传统媒体以往受到的大部分公众监督。而社交媒体这样的特性可能会产生一种“相关性维度”,正如哈佛大学学者约凯·本科勒(Yochai Benkler)等人所说的那样,“在当代领先的互联网平台上,虚假信息活动和合法的广告活动实际上无法区分,这不但是因为恶意行为者传播(错误)信息和内容的手段越来越复杂,而且还由于用户与社交媒体平台之间关系的个性化和私密性而导致其相对缺乏公众监督。”[注]BENKLER Y,FARIS R,ROBERTS H.Network propaganda:Manipulation,disinformation,and radical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102-105,117-120.
正如前文所述,社会化将对自主性的实现产生关键性影响,特定的社会化模式不但存在于社交媒体的背景下,而且可以说会因社交媒体的发展而加剧。例如,无论是社会向往的美丽的标准、成功的定义,还是理想的职业道路,社会化往往会影响社会代理人对世界的观点与看法。这种倾向在社交媒体领域也日趋明显,财富和物质财产的展示通过社交媒体中存在的“喜欢”和“分享”等系统影响人们对美感、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的看法。此外,社会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教育与知识,它允许社会化的人做出明智的决定。随着社交媒体上错误信息和假新闻的兴起,使得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错误信息成了当今社会面临的风险之一。为了应对并纠正社交媒体在数据、图片和统计结果中的错误信息,就需要考虑社交媒体如何通过控制用户数据、注意力和行为来减缓或消除对自主性的负面影响,因为自主性可以被理解为需要不受他人控制的自由,这也就要求人们在未来更多的地关注对信息与数据质量的有效控制。
四、社交媒体对用户数据的控制
一般而言,当用户在社交媒体上浏览信息并进行互动时,在这个过程中会生成数量惊人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则由平台所有者予以记录与存储。[注]ZUBOFF S.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M].New York:Profile Books,2019:205-210,79-100.在平台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用户及其活动为这种发展提供了相关的材料与数据,从而带来了更多的利润。实际上,平台资本主义是指一种专注于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即平台)的资本主义形式,它使两个或多个群体之间能够实现互动与交流,并且通常建立在网络效应之上以试图将其用户留在平台内。当前,平台已经成为“垄断、提取、分析和使用越来越多的正在记录的数据的有效方式”,这些数据在随后会被社交媒体公司用来产生利润,通常是通过销售广告来获得相应收益。[注]FUCHS C.Web 2.0,Prosumption,and surveillance[J].Surveillance &Society,2011,(3):288-309.在下文中,笔者将进一步深入分析用户在失去对其数据的控制后,可能由此产生对自主性的重要影响。
于是,在社交媒体与人的世界的交织中促生了关于自主性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即社交媒体公司似乎(至少有可能)在剥削用户。富克斯认为,剥削的概念延伸到社交媒体用户,是因为他们参与了数据和用户生成内容的生产,然后社交媒体公司使用这些内容来产生利润。这应该算作剥削,原因在于尽管社交媒体公司“不(或几乎不)向用户支付内容生产费用或数据,但他们却从中产生、获取利润或剩余价值”。[注]FUCHS C.Social media:A critical introduction[M].Newbury Park:Sage,2014:256-260.虽然资本所有者对剩余价值的任何榨取都可以算作马克思主义技术意义上的“剥削”,但这种剥削似乎只是在满足进一步条件时不尊重自主性的道德问题表达。当剥削未能将其他代理人视为平等的一方来确定双方同意的互动条款,而是利用漏洞过度使自己受益时,那么剥削就会被视为不尊重个体的自主性。
针对这个问题,有些人可能会辩解称,用户事实上是以“免费”服务的形式获得了合理的利益,以换取从他们的数据中产生的价值。然而,富克斯认为社交媒体用户并没有获得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通用交换媒介”,社交媒体只是为用户提供了“使用特定通信方式的途径,其使用符合他们(公司)自身追求利润的目的或利益”。另外,针对用户拒绝使用该平台的能力也存在合理性的隐忧,因为他们“可能会错过某些社交接触机会”,并因此“在社会上遭受迫害”。[注]JESSE F,JENNIFER J M.The dark side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An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ors associated with Facebook use and affordances[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9,(45):168-176.换言之,如果至少在某些社交圈中,人们拒绝使用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是不合理的,那么某些社交圈的人拒绝同意社交媒体公司提供的任何条款可能都是不合理。此外,人们对社交接触的需求和对错过机会的恐惧(FOMO)[注]错失恐惧症(“Fear of Missing Out”,简称“FOMO”),特指那种总在担心失去或错过什么的焦虑心情,也称“局外人困境”。具体表现为无法拒绝任何邀约,担心错过任何与有助人际关系的活动。面对“错失恐惧症”,要学会做自己的主人。,以及他们在不阅读隐私条款的情况下接受隐私条款的脆弱性都表明了特定的人类脆弱性的存在,社交媒体公司可能会利用这些脆弱性来剥削他们的用户,从而选择不尊重他们所拥有的自主性。
然而,即使用户明确“同意”使用社交媒体,这也不意味着他们已经自动同意这些条款,因为他们可能会因受到剥削而被迫同意,或者他们可能没有得到适当的通知。[注]NISSENBAUM H.A contextual approach to privacy online[J].Daedalus,2011,(4):32-48.此外,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对许多专业活动来说变得至关重要,与社交媒体平台相比,其中还会产生进一步的财务与经济成本,这意味着用户可能会认为他们将别无选择,只能加入或使用该平台。而这种别无选择的加入或使用可能是因为害怕错过了关键信息或新闻,因为这种错过涉及来自家人和朋友的个人新闻或时事新闻,或者害怕因为不属于社交网络而在社交或职业上被排斥。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用户加入社交媒体平台的决定,如果是被迫的,一开始是否应该算作自主决定?
当然,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因为这限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知情同意标准。欧若拉·奥尼尔(Onora O’Neill)认为将其与以知情患者同意为中心的医学伦理学进行比较,将有助于人们淡化社交媒体对自主性影响的模糊理解而产生的朦胧感。在这里,“我们不希望患者像他们的医生一样详细了解他们提议的治疗方案,以便他们的同意被视为知情。但是,自主性问题的根源在于患者对他们同意的内容缺乏完整的理解,因此需要信任来支持医疗环境中的同意”[注]O’NEILL O.Autonomy and trust in bioeth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172-175.。而二者关键的区别在于患者可以有充分的理由信任他们的医生,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医生对他们有照顾的责任以及对他们有保持医疗能力的专业义务。但这恰恰是社交媒体用户与其提供者之间的关系中缺乏的注意义务与专业义务,因此在缺乏强有力的信任基础的情况下,知情同意就必须完成所有的范式工作。
对于社交媒体来说,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在大数据时代下匿名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梭伦·巴罗卡斯(Solon Barocas)和尼森鲍姆认为,“匿名化是不可能的”,因为由于平台控制着大量数据,它仍然“可以区分一个人的信息,并足以将这些记录关联到特定的个人”。[注]BAROCAS S.NISSENBAUM H.Big data’s end run around anonymity and consent[J].Privacy,Big Data,and the Public Good:Frameworks for Engagement,2014,(1):44-75.也正是出自多个来源的数据的组合导致了这种隐私的丧失,并且从数据组合中进一步提取信息不太可能得到知情用户的自主同意。这也将引向本文下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监视。
祖博夫将监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它声称人类经验是用于提取、预测和销售的隐藏商业实践的免费原材料”。他强调,虽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过严厉的批判,并将其描述为“以劳动为食的吸血鬼”,而不是以劳动为生,但“监视资本主义却是以每个人经历的各个方面为食”。[注]ZUBOFF S.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M].New York:Profile Books,2019:205-210,79-100.监视导致的主要后果之一是社交媒体用户体验到隐私的丧失,尤其是在他们认为自己正处于孤独和私密的时刻。具体来说,它会导致“失去外在自由的风险”,即用户的行为容易受到他人控制以及“失去内在自由的风险”,这意味着用户可能容易受到社会压力的影响,从而无法为自己做出重要选择。[注]REIMAN J H.Driving to the panopticon[J].Santa Clara Computer and High-Technology Law Journal,1995,(1):27-29.此外,用户对监视的担心是由于他们受到监视而会限制和阻止其在社交媒体网站上真实地行使他们的言行自主权。另外,对政府监控社交媒体的担忧也可能限制人们自主性的实现。
同时,失去对私密数据的自主控制也会影响人们自尊、自爱的自主能力。此外,在一个人认识到社交媒体网站可能会通过利用个人作为获取数据的手段来表达对其自治权的不尊重,这样会使他更难保持应有的自尊。而最后一点特别涉及自主性的自我授权内容,即人们认为自己有权设定自己的价值观和目的,因为当人们受到剥削性条款的约束时,很难用这些条款来正确看待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每个人并不是自主同意,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也无法合理拒绝。这些不同维度的负面影响既可以在自主性的情节性层面上发挥消极作用,通过干扰人们对监视的关注而做出的个人选择,也可以在纲领性的或全球层面上产生不良影响,从而破坏人们作为具有强大自尊和自尊水平的自我授权代理人的整体意识。
五、社交媒体对用户注意力的控制
在数字化媒介技术开始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社交媒体通过控制人们的注意力来影响或操纵它的用户,甚至还会以这种方式来潜在地贬低和干扰人们自主性的实现。如果要批判性地分析社交媒体通过控制用户注意力来影响自主性的实现方式,那么重要的是要了解其吸引和利用用户注意力的运作机制。伊夫·西顿(Yves Citton)通过将注意力置于“注意力经济”的经济模型中,提供了对注意力概念的全面阐释。在这种情境下,“我们看到了从控制生产方式到控制注意力方式的转变,注意力成为一种备受追捧的稀缺资源。而这一理论被称为‘有限资源假设’,它进一步指出‘人类可获得的注意力总量在任何给定时间都是有限的’”。[注]CITTON Y.The ecology of attention[M].Oxford:Polity Press,2017:101-107.当在社交媒体的情境中考虑自主性问题时,注意力的稀缺会变得更加明显,内容与信息的流动几乎是无限的,而人们可以用来消费这些内容的时间和注意力显然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戴安娜·祖利(Diana Zulli)将“一瞥”定义为“一种快速、转瞬即逝、不分青红皂白地观看”,是“驱动我们注意力经济的关键特征”,并使我们能够检验“数字技术是如何重构用户及其经济行为的”。[注]ZULLI D.Capitalizing on the look[J].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2018,(2):137-150.这也意味着社交媒体公司正是通过不断竞争以吸引尽可能多的用户注意力来产生利润。
目前,算法被认为是社交媒体控制人们注意力的重要工具,因为算法会对社交媒体用户在平台上消费和参与的内容产生重大影响。[注]MYLLYLAHTI M.An attention economy trap?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four news companies’ Facebook traffic and social media revenue[J].Journal of Media Business Studies,2018,(4):237-253.社交媒体也正是通过使用算法来控制用户在订阅源上看到的内容,这样社交媒体公司及其客户就控制了用户的注意力,而且还通过控制他们有限的注意力,以他们不会在反思后认可的方式控制着用户。而以这种方式破坏政治话语的一种方法就是创建“回音室”,[注]MITTELSTADT B.Auditing for transparency in content personalization system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6,(10):4991-5002.它会让用户缺乏不同的想法与信仰,导致用户只接受某种特定的政治观点,从而不接受或排斥其他观点,这实质上会对自主性的实现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同时,社交媒体的应用也造就了人们对个性化的担忧。在社交媒体的传播环境中,这种个性化可能会通过使人们增加接触极端与非理性观点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激进化。马克·阿尔法诺(Mark Alfano)等人指出,在2018年一份关于YouTube的研究报告中称,“在该网站上花费的所有观看时间中,大约70%是由推荐系统驱动的。”[注]ALFANO M,FARD A E,CARTER J A,CLUTTON P,KLEIN C.Technologically scaffolded atypical cognition[J].Synthese,2020,(199):835-858.最令人不安的是,YouTube的算法正在努力让一些用户接触可能导致社会激进化的阴谋内容,从而尽可能长时间地让人们参与该平台的运作。[注]BHARGAVA V R,VELASQUEZ M.Ethics of the attention economy[J].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2021,(3):321-359.正如Facebook的告密者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所言:“我在Facebook一次又一次看到的是,对公众有利的东西和对Facebook有利的东西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Facebook……选择为自身利益的实现而进行优化。”[注]PAUL K,MILMO D.Facebook putting profit before public good,says whistleblower Frances Haugen [EB/OL].(2021-10-03)[2023-05-26].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1/oct/03/former-facebook-employee-frances-haugen-identifies-herself-as-whistleblower.当涉及用户的自主性时,激进化是一个阻碍其自主性实现的重要原因,这是由于激进化可以向用户灌输他们在知情反思后不会认可的价值观与目标。
除了关于个性化的讨论,社交媒体带来的另一个有可能抑制自主性的主要挑战是“假新闻”,由于社交媒体公司对用户注意力的控制,“假新闻”可能成为用户关注的内容的一部分。假新闻以合法新闻的形式描述有关世界的错误信息和不准确信息,确保遵循传统可信媒体来源的呈现方式与格式。对此,尼尔·莱维(Neil Levy)不但承认假新闻在政治领域颇具影响力,而且他还强调假新闻的消费性。这是由于知识的来源与知识的内容分别存储在人类的记忆中,因此,当知识的内容被带到有意识的意识中时,在记住知识来源的同时可能会导致记忆错误,这反而使得人们可能将假新闻归因于可靠且可信的新闻来源。基于此,假新闻就会对人们的自主性实现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它可能导致用户错误地认为他们正在使用可靠的信息来源,他们可以安全地根据这些信息采取行动。
最后,社交媒体上的个性化广告是这些公司影响用户注意力与行为的另一种方式,这在根本上影响用户自主权的行使。在这里,可以以埃莉诺·M·温佩尼(Eleanor M Winpenny)在《儿童和青少年接触社交媒体网站上的酒类营销》一文中的调查结果为例,调查显示英国的Facebook平均每个月都会向15~24岁的“89%的男性和91%的女性”展示酒类营销媒体广告,考虑到这个样本中的许多人都是未达到法定饮酒年龄的儿童,这种营销广告显然是不道德的。对此,有人可能会争辩说,通过禁止让未成年人接触有害产品的广告就可以很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然而,这种做法恰恰忽略了关于社交媒体上定向广告的潜在性问题。此外,个性化广告还可能导致用户部分失去对自己的控制,因为他们无法专注于他们最看重的东西,同时他们的注意力也会一直被社交媒体公司有意且持续性地劫持。
总之,这些负面影响以及控制方式在自主性实现的纲领性与情节性层面均发挥一定的消极作用,其中社交媒体破坏情节性自治的最明显例子就是有针对性的广告形式。根据对社交媒体公司可以访问的大数据的分析,并通过将用户定位在其某个特定的脆弱时刻,就可以迫使用户做出他们在不那么脆弱的状态下不会自主做出的决定。[注]SUSSER D,ROESSLER B,NISSENBAUM H.Technology,autonomy,and manipulation[J].Internet Policy Review,2019,(2):11-15.从广义上说,激进化、错误信念的形成以及某些理想的放大不仅会在个人选择层面上影响用户,还会在纲领性层面上影响他们如何成为想成为的人和实现他们想要的生活类型的价值生活。可以说,这在更深层次意义上改变了他们作为一个“人”的身份,从而对他们的全球自主权产生了负面影响。另外,由于抑郁症和焦虑症会对一个人在全球范畴内的代理能力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也间接凸显了人们因社交媒体网站而产生的抑郁和焦虑情绪对全球自治的消极影响。
六、社交媒体对用户行为活动的控制
关于对人类行为操纵的文献也非常广泛,丹尼尔·苏塞尔(Daniel Susser)认为“从本质上讲,操纵是一种隐藏的影响——即暗中颠覆他人的决策权。”对这一权力的运作,可以通过“利用被操纵者的认知(或情感)弱点与脆弱性来引导他或她的决策过程朝着操纵者的方向或目的”来实现。[注]SUSSER D,ROESSLER B,NISSENBAUM H.Technology,autonomy,and manipulation[J].Internet Policy Review,2019,(2):11-15.操纵可以发生在理性与审慎两个层面上,通过影响信念、欲望、价值观和批判性思维来控制他人的行为;也可以发生在情感层面上,通过利用恐惧或厌恶等情绪来控制他人的行为。而另一个对操纵而言比较重要的观点是,操纵通过隐藏或隐蔽的手段来利用代理人的漏洞,导致被操纵的代理人由他人控制,这显然不是代理人的自主行动。
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需要将操纵与其他形式的影响区分开来。而发挥影响力的两种主要形式是说服与胁迫。其中,说服是通过影响“他们有意识的深思熟虑与选择的能力”来公开呼吁某人做某事或不做某事。胁迫,如对“你的钱或你的生命”的威胁,也是对他人的明显影响。然而,胁迫是通过撤销选项来完成的,从而让胁迫者的选择成为决策者剩下的唯一(合理)选择。在这两种影响方式中,代理人的决策能力都没有受到损害,因为它们是公开的影响方式。这些形式的影响不同于操纵,因为“操纵人们就是取代他们作为决策者”,并且“如果他们以清晰无误的方式考虑问题,就会破坏或破坏他们自己会批判性认可的选择方式”。[注]STEINSBEKK S,WICHSTRM L,STENSENG F,NESI J,HYGEN B W,SKALICKá V.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use on appearance self-esteem from childhood to adolescence[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21,(114):106528.
实际上,以上关于操纵的3个维度都能够在社交媒体的应用中得到体现。首先,通过虚假新闻或误导性广告来欺骗用户,导致用户形成影响他们决策的错误信念。其次,对用户的诱惑是通过长期使用通常不合理的成功、财富和美丽标准来实现的。通过算法以及“喜欢”“分享”和“评论”等机制传播成功、富有或美丽的某些表现形式,使得社交媒体可以产生某些不真实的欲望,但这会影响他们的自主决策。希埃拉·里夫斯(Shiela Reaves)等人认为,社交媒体有意识地对照片进行编辑和“修饰”的结果——“暴露在苗条中的理想”——会操纵女性的自主决策,因为它“往往会降低女性对身体的满意度,增加自我意识,并降低自尊”。[注]REAVES S,BUSH HITCHON J,PARK S-Y,WOONG Y G.If looks could kill[J].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2004(1):56-71.这意味着不断暴露在这种(不切实际且通常不健康)理想中的女性会感到自尊心降低,因为她们认为自己不符合那些公认的美丽标准。最后,社交媒体通过让用户接触旨在引起极端情绪反应的内容,使得其可以在情绪上操纵或煽动用户改变他们的行为。本科勒指出,“收入低于40,000美元的家庭最容易成为关注移民和种族冲突的广告的目标。通过专门针对低收入人群,广告商可以引发恐惧和厌恶,或恐吓选民不要投票。”[注]BENKLER Y,FARIS R,ROBERTS H.Network propaganda:Manipulation,disinformation,and radical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102-105,117-120.这是社交媒体中的一个常用且显著的机制,它可以通过情绪操纵来控制用户的行为,而不是实现一些用户的真实目的(即他们在知情批判性反思后会认可或承担责任的目的)。
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是关于Facebook如何对其用户的情绪进行操纵的研究。亚当·D·I·克莱默(Adam D.I.Kramer)与杰米·E·吉洛里(Jamie E.Guillory)等人在这份研究报告中指出,“用户们情绪感染的产生是通过操纵 Facebook用户的动态消息上的内容所导致的……当积极情绪表达减少时,人们发表的积极帖子就会减少,而消极帖子就会增加;当负面情绪表达减少时,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注]KRAMER A D I,GUILLORY J E,HANCOCK J T.Experimental evidence of massive-scale emotional contagion through social networks[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4,(24):8788-8790.因此,他们得出结论,Facebook用户在他们的动态消息中接触到的情绪会影响他们自己的现实情绪。此外,一些记者的调查发现,Facebook曾建议其广告商如何在年仅14岁的弱势青少年感到“毫无价值”与“不安全”的时候来“瞄准并操纵”他们的情绪。而这种操纵正是通过“实时监控的帖子、图片、互动与互联网活动”来实现的,这使得 Facebook能够知道青少年何时会“感到‘压力’‘被挫败’‘不知所措’‘焦虑’‘紧张’‘愚蠢’‘没头脑的’‘无用’和‘失败’”。[注]VALDMAN M.A theory of wrongful exploitation[J].Philosophers’ Imprint,2009,(6):1-14.通过这样的方式,社交媒体公司不但通过主动操纵用户的情绪反应来控制用户的行为,而且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暗中利用这些脆弱的情绪反应来操纵用户购买其客户的产品。
此外,成瘾是社交媒体控制用户行为的另一种重要方式。一般而言,社交媒体公司会利用3种机制来助长人们的社交媒体成瘾。第一个是间歇性变量奖励的使用。这是在人们电子产品的主屏幕上加载以及社交媒体平台(如Twitter)的“拉动刷新”[注]BOND R M,FARISS C J,JONES J J,KRAMER A D,MARLOW C,SETTLE J E,FOWLER J H.A 61-million-person experiment in social influence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J].Nature,2012,(7415):295-298.功能中发现的一个设计特征,这两种功能都是为了在用户内部产生间歇性可变奖励而设计的,类似于“老虎机”的一种奖励刺激。第二个是社交媒体平台利用人们“对社会认可和社会互惠的渴望”,引导大众通过“喜欢”按钮或“分享”功能等“社会奖励计划”来实现吸引更多新用户。第三个是社交媒体平台通过使用“无限滚动”消除了任何自然的停止提示,从而剥夺了用户可能让他们有机会做出暂时离开平台的决定。这样,社交媒体不但能够利用通知系统来诱发人们患上FOMO(因为用户们觉得他们必须在通知弹出时立即关注每条通知)[注]KUSS D J,GRIFFITHS M D.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nd addic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17,(3):311-315.,而且这种通知系统已经成为一种将用户的注意力从其他活动吸引回社交媒体平台的重要方式。
当社交媒体平台利用用户的弱点暗中操纵用户的信念、情感和决策过程时,这显然已经构成了对用户自主选择权的不尊重。不难看出,社交媒体的操纵或控制会对自主性实现的所有3个维度都产生负面影响。首先,自我决定是被这样一个事实所破坏,即操纵的唯一原因是引导用户做出适合社交媒体公司及其客户而非用户的选择。因此,用户就无法做出反映当时对他们生活自我控制的选择。其次,自我治理会受到以下事实的影响:即社交媒体上的操纵不仅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并且可能发生在用户的意识之外,从而削弱了他们批判性地反思他们正在做出的选择的能力。再次,当用户的言行被社交媒体操纵时,自我授权就会被完全破坏,因为当用户的决策能力被劫持并通过秘密利用其漏洞进行操纵时,用户对其身份、价值观与选择就会缺乏权威性。最后,社会个体的整体生活的全球自主性会最明显地受到成瘾的影响,成瘾是社交媒体通过实施导致社交媒体成瘾的机制以及用户们对错过关键和重要事件或内容的持续恐惧、始终被迫要求在线和可用需求增加而助长,这样用户的整体生活就会受到社交媒体及其行为控制的影响和塑造。
七、结论与应对策略启示
信息化时代催生了媒体化,迎来了今天的“泛媒体化”时代。一方面社交媒体能够通过与人们真正重视的其他人的社交互动来帮助人们实现自身的目标并行使自主权,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对人们自主性的实现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由于社交媒体的形态仍在不断更新,这里存在的3种类型威胁不仅引发了学界围绕社交媒体监管的相关讨论,还使整个社会开始关注自治性实现的重要性以及社交媒体可能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使其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话题。基于此,本文提出的应对策略也将更多地从抽象的哲学或伦理学语境去消解社交媒体对自主性实现产生的负面影响。
首先,就社交媒体的最终用户而言,尤其是要不断强化对用户个人或隐私数据的科学监管与保护。一方面,通过顶层设计推动法律规范与伦理框架协同发展,进一步明确数字经济时代下个人数据和隐私的范围。例如,数据的归属和权利、数据的类别和价值等基础问题,并敦促社交媒体平台对其所使用的用户数据保持透明,以及保证其算法的设计尊重用户隐私和自主性。此外,社交媒体平台应对人工智能的任何不道德使用负责,如针对弱势群体的不公正使用或传播错误信息。另一方面,推动社交媒体进一步保障数据隐私的安全,需要围绕社交媒体的相关知识开展对用户进行数字教育,并培养用户的数字道德规范与认知警惕意识,预防社交媒体用户陷入由于害怕错失机会的脆弱性而使得自治权受限的困境。通过提高社交媒体用户的数字素养,可使用户重新认识并提升其对主观规范、感知行为以及数据的控制能力。这些美德以及道德规范可以通过“持续性、有意识的”监测与自我教育方式进行培养,从而使得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社交媒体对用户个人信仰、价值观与目标的影响。
其次,在重新认识社交媒体可能以潜在的方式对用户自主性的实现产生负面影响后,就需要深入地了解社交媒体如何影响用户自主能力或注意力的发展,尤其是它对用户的自我态度的影响。主要包括用户信仰的真实性、推理与思考的方式、用户重视和关心什么、用户与谁互动和受谁影响以及他们做出的选择等,从而有针对性地为社交媒体的规制提供实证论据。在深入考量这些影响用户注意力的因素后,社交媒体应该通过正确的互动引导方式,构建一种具有价值性、互动性、整合性的信息交流与传播形式,而不是以诱导性或强制的宣传来控制或操纵用户注意力与关注度,从而消除算法黑箱容易引起的算法操纵现象。同时,社交媒体平台运用算法进行自动化决策时还应保证某种程度的透明度,使得社交媒体给予用户对自身注意力控制的足够自主性,允许用户以自我目标为导向,自由选择信息内容和进行自我注意力的操控,激发社交媒体用户控制自身注意力的积极性,从而避免用户注意力失控带来的对政治自由与平等的曲解、对科学的信任危机以及社会群体撕裂等不良影响。
最后,应加强对社交媒体应用的评估与监管。虽说社交媒体的算法黑箱容易导致对用户自主性行为操纵现象,但算法黑箱也有其自己的积极价值并且是一种值得受到法律保护的事项,要求所有社交媒体中的算法都公开透明也是不切实际的,因其成本相较于收益而言过于巨大。那么在适当保留其算法黑箱的前提下,就需要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进行相应的评估与监管。由于对社交媒体的评估与监管连接着伦理道德、技术手段和法律规范等相关方面,是硬托底和软治理之间的桥梁衔接部分。因此,一方面,制定社交媒体的相关监管规范,应争取覆盖社交媒体更多领域,加强国内社交媒体监管规范与国际规范的衔接,在技术应用、数据标准和自主性保护方面达成一致。同时,在此基础上构建必要的安全控制评估体系,建立评估专家库和评估机制,提高对社交媒体的评估评测能力,以技术手段为支撑,切实规避因社交媒体产品和应用而产生的行为操控缺陷与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在评估关于社交媒体的拟议法规时,需要全面考量社交媒体对用户的剥削与操纵行为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尊重、干扰甚至阻碍用户的自主性实现以及相关自主能力的提升,从而形成评估共享数据集,研发评估测试工具集,将对社交媒体技术评估的道德伦理框架和价值选择内化为法律规范中的原则,通过科学合理的立法评估实现包容协同发展。
综上所述,社交媒体对人的经验世界、精神状态、意义价值的影响,以及它对当下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都呼唤着与这个媒体化时代相匹配的自主性研究。事实上,在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的规制性与人的自主性并不互相排斥,人难免要在一定的算法规制性中学习与发展,而社交媒体规制性的实现又离不开人的发展需求,两者相互影响、共存共生。在具体的“用户-社交媒体-用户”这一信息生产和传播实践中,要动态博弈与权衡社交媒体规制性的工具理性与人的自主性发展的价值理性二元关系,在协同共生中实现价值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