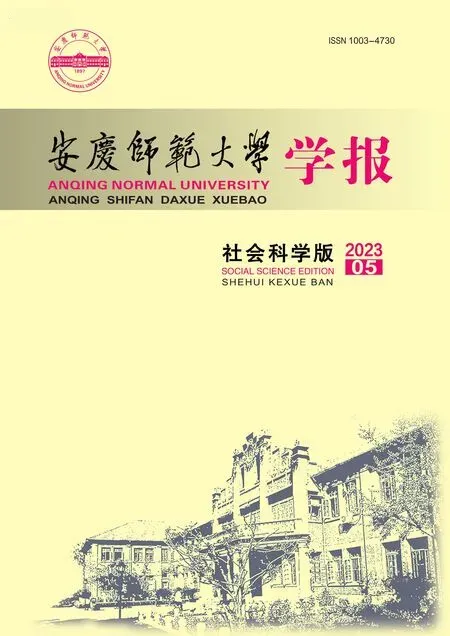清末民初译诗体式论
2023-06-07李向阳
李向阳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一、引 言
文体变革是文学变革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变革进程中,翻译文学充当了桥梁。而在诸种体裁的文学翻译中,译诗的难度往往为人所提及。这是因为,除了翻译活动通常会遇到的困难——在译诗中更多地表现为如何准确传达原作的神色韵味及词藻句法,译诗还要考虑形式的因素,包括外国诗的形式和中国诗的形式,以及两种形式之间的转换。清末民初这样一个新旧杂处、中西混融的时代,译诗对诗体的选择也呈现“律古”与“趋时”的不同倾向。除中西、新旧的立场对译诗诗体的制约外,外国诗,即原作本身,也会对译诗的诗体起到调节作用,促使以“中国调”译“外国意”的译者不能尽焉削足适履,而以分行白话体译诗的译者亦不能全然无视原诗格律。关于清末民初译诗的发展脉络与基本特征,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连燕堂《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已有论述和总结①详见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上篇之三“中国近代翻译诗歌鸟瞰”、下篇之四“苏曼殊、马君武及其他诗歌翻译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9-103页,第304-344页。连燕堂《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第三章“近代的诗歌翻译”、第十三章“新一代翻译家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在近代翻译转折期中的独特作用”,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9-90页,第319-350页。。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查阅《新小说》《竞业旬报》《中华小说界》《新青年》等报刊,《马君武诗稿》《德诗汉译》《拜轮诗选》等(译)诗集,《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三》《胡适留学日记》等文献,发现本时期译诗在译法上可以概括为四种类型:古体诗译法、近体诗译法、杂言体译法、白话自由体译法;相应地,在诗体上呈现六种体式:诗经体(四言体),楚辞体,五七言(古体、近体),词曲体,杂言体,白话自由体。基本涵盖中国诗史上各占一代之所胜的所有重要诗体。作为“五四”新诗孕育生成的试验场和参照,清末民初译诗的诗体递嬗,折射出中国诗歌革故鼎新的痕迹和步履。总结清末民初译诗体式,正是探究该时期译诗诗体演变,进而考察新诗生成过程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步。由于学界目前尚无专文综论该时期译诗体式,本文拟就此问题略陈知见,以就正于研究者。
二、诗经体
诗经体通常可以被理解为四言体,但“四言体”表达不出“诗经体”所具有的“经典”意味。这种“经典”意味并非可有可无,更多的时候,它都暗含在译者对所译诗歌的文化定位中,作为一种隐性因素被读者感知。换句话说,大多数译者将外文原诗译为四言体,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尊体”考虑的,比如借重中国诗体传达外国诗的宗教属性。诗经体或四言体因而成为一种“有意味的译诗形式”,其“意味”来源,指向《诗经》作为六经之一的崇高文化地位。
以《遐迩贯珍》中的译诗《自咏目盲》为例。弥尔顿(Milton,1608—1674)在原诗中抱怨地自问道:“难道上天不给光明却要向我论工计数?”“忍耐”回答道:“上天不需要人的服务,也不要你还给他什么礼物;好好负起轻松的轭,就是最好的服务。”[1]《自咏目盲》的对应译文为:“嗟彼上帝,既闭我瞳。愚心自忖,岂责我工”“苍苍上帝,不较所赐。不较所赐,岂较作事。唯与我轭,负之靡暨。”[2]《自咏目盲》本是诗人在领悟上帝旨意时的精神自释;对照今译,发现《遐迩贯珍》译文不仅辞义准确,而且四字句所营构的整饬紧凑的阅读效果,更将原诗浓厚的宗教氛围恰当地烘托了出来。译作中“静言思之”的诗句,表明译者对《诗经》句法的直接借鉴。由此可知,《自咏目盲》在汉译过程中是以《诗经》作为文本参照的。《诗经》儒家经典的身份和中国诗歌源头的地位,使它在诗体上与西方宗教诗歌的互译,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共通性。
带着这种认识理解严复在《天演论》中翻译的《尤利西斯》片段,和刘半农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号的译诗《我行雪中》,对这两首诗四言体的形式就会更加了然。尤利西斯是罗马神话中的人物,也即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奥德赛;《我行雪中》是一首宗教颂诗,为印度著名歌者Sri Paramahansa 所作,刘半农“尝以诗赋歌词各体试译,均苦为格调所限,不能竟事”,最终以“译经笔法写成之”[3],直译为四言体。严复和刘半农对四言体的选择不是偶然的。《尤利西斯》对神话英雄暮年心灵的刻画,《我行雪中》对宗教情境的知觉感悟,均使它们与《诗经》或在英雄题材、或在颂诗风格上相契合。诗经体或四言体所独具的古朴诗形和韵出天籁的自然音节,也使其比较适合用来翻译神话或宗教题材的诗歌,而较少受到人为设置的诗歌格律束缚。
保证辞达以及追求不同的诗歌节奏和阅读效果,是诗经体或四言体译诗的又一原因。此时,在理解原诗风格和情感内容的基础上,译者主观倾向起到很大作用。在没有其他因素牵制的情况下,当译者认为四言体更能传达原诗神韵,且能达到良好的翻译效果时,往往就会采用四言体。叶中泠发表在《华侨杂志》1913年第2 期的译诗《矢与歌》,苏曼殊收在《拜轮诗选》中的译诗《赞大海》,就更多地属于这种情形。试读《赞大海》中的诗句:“摇山撼城,声若雷霆,王公黔首,莫不震惊。赫赫军艘,亦有浮名,雄视海上,大莫与京。自公视之,藐矣其形,纷纷溶溶,旋入沧溟。”[4]相较于他以五言体翻译的《去国行》和《哀希腊》,别有一种气势在。
三、楚辞体
楚辞体也可以称为骚体。在中国的文学地理中,《诗经》《楚辞》一北一南,构成中国文学的两个源头,形成对后世诗歌发展影响深远的“诗骚”传统。得益于楚文化哺育,以《离骚》等为代表的楚地文学展现出强烈的浪漫抒情色彩。《离骚》作者屈原“美政”的理想追求和九死未悔的爱国热忱,更是中国文学爱国主题的重要组成。清末民初译诗对楚辞体的选择,爱国情感的表达是其中一项相当重要的因素。
马君武翻译的《非律宾之爱国者》开篇写道:
去矣,/我所最爱之国,/别离兮在须臾。/国乎,/汝为亚洲最乐之埃田兮,/太平洋之新真珠,/惨怛兮舍汝而远逝,我心伤悲。/我命甚短兮,/不能见汝光荣之前途[5]!
情辞哀切,颇足感人。借助楚辞体深长咏叹的语调和节奏,《非律宾之爱国者》传达出深沉浓烈的爱国情感,这种爱国情感在本质上与屈原对楚国的眷恋并无太大的不同,但黎沙儿将菲律宾放在“亚洲”和“太平洋”的视野中来赞美,就显示出崭新的时代内涵。
更典型的莫如对英国诗人拜伦诗歌的汉译。胡适翻译的《裴伦〈哀希腊歌〉》和刘半农翻译的《弔希腊》都是以楚辞体结构。借助楚辞体,诗歌翻译者表达着对东西方爱国诗篇共通性的理解,这当然也基于拜伦与屈原在文学想象和浪漫风格层面的相似。《裴伦〈哀希腊歌〉》第一节写道:
嗟汝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诗媛沙浮尝咏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今唯长夏之骄阳兮,纷灿烂其如初。/我徘徊以忧伤兮,哀旧烈之无余[6]161-162!
《弔希腊》中的诗句也是直抒胸臆:
思勇士兮不能忘,慕遗风兮弔旧邦。/平原如锦兮直抵山之岗,是为自由之故乡。/荣名沉没兮塚中藏,庙堂遗迹何堂皇。/览此遗迹兮,物是人非我涕滂[7]。
无论是《非律宾之爱国者》,还是《裴伦〈哀希腊歌〉》和《弔希腊》,抒情主体均为第一人称。同样在楚辞体译诗中突出“我”的,还有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第1卷第2号的《亚美利加》;作为美国国歌,《亚美利加》对“吾土”“吾宗国”和“自由乡”的讴歌,其神圣感、自豪感更是充溢在字里行间。
除国家情愫的表达之外,诗人气质的张扬是译者采用楚辞体的另一原因。鲁迅、周作人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在翻译小说《红星佚史》和《灯台守》中的几首楚辞体译诗,呼应鲁迅对摩罗诗力的倡导和吁求,也是鲁迅“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8]主张的诗学践行。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在突出作家主体精神、彰显高标独立的人格特质等诸多方面,都与鲁迅对诗歌的期待相契合。这一时期,鲁迅对楚辞体译诗有着明显的偏好。除了前面提到的译作,他还在《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2 期翻译了两首海涅的诗。楚辞体以其鲜明的风格特色,成为译诗内容的重要构成。
此外,叶中泠发表在《华侨杂志》1913年第2期的译诗《云之自质》,同样以楚辞体传达出独特的诗歌韵味。胡适翻译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的《乐观主义》后曾言:
此诗以骚体译说理之诗,殊不费气力而辞旨都畅达,他日当再试为之。今日之译稿,可谓为我辟一译界新殖民地也[6]160。
流露出译诗成功后所体会到的精神愉悦。胡适的感悟可视为从文学翻译角度选择楚辞体的例证。
四、五七言
关于五七言译诗,可从戴宗球和胡适的体会谈起。戴宗球在一段“译者附识”中,道出了他对中英诗歌韵律的理解,以及他之所以选用五言古体翻译《隐士吟》的原因:
英文诗歌之讲“feet”与“rime”也,一如中文之律诗,种类繁多,兹不备述。其在中国,《诗经》为言诗者所祖,其诗不究平仄(feet),而韵(rime)则出自天籁,未尝有误,寻常四句一章,章各有韵。其为韵也,或二、四两句,或一、二、四三句,如《卷耳》首章属前说,其次属后说。魏晋宗之,而多五言,如刘越石《扶风歌》,魏武帝《短歌行》是也。本诗窃效斯体。至唐宋始有律古之分,律则平仄不容或误,而同韵之章,不止四句矣[9]108。
胡适在《译德国诗人亥纳诗一章》的“序”中,说明他对该诗的感受道:
德国诗人亥纳(Heine),……生平长于短章、小诗,其诗亦敦厚,亦悱恻,感人最深。即如此诗,相思之词也。高松苦寒,诗人自况;南国芭蕉,以喻所思;冰雪火云,以喻险阻,颇类吾国比兴之旨。而其一种温柔忠厚之情,自然流露纸上。信笔译之,以寄吾友[6]159。
戴宗球肯定《诗经》“为言诗者所祖”的诗歌史地位,却最终选择了继承《诗经》“不究平仄”“韵出天籁”传统的魏晋五言体。在戴宗球的权衡下,五言古体显然更适合传达原诗神韵。《诗经》文学地位虽高,其四言一句、四句一章的基本体式却未必适合用来翻译《隐士吟》。胡适的考虑同样如此。从“序”中可知,他对亥纳(海涅)此诗的理解,是“颇类吾国比兴之旨”,并有“一种温柔忠厚之情”,按照字面的逻辑,似乎应该把这首诗译为诗经体,但胡适没有这么做,他的《译德国诗人亥纳诗一章》是两首七绝的形式,原诗与《诗经》艺术手法或诗歌风格的相似,是通过化用《诗经》现成的句子体现出来的,比如“脉脉无言影寂寥,欲往从之道路遥”[6]159,后一句就是对“欲往从之”“道阻且长”的整合。促使戴宗球和胡适放弃诗经体而选择五七言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后者具有的更大收容量,而更大收容量意味着更丰富的表现力和更准确的句意传达。相较于诗经体译诗,五七言在表达原作句意方面无疑具有明显的优势。
清末民初译诗发展史上,五七言译诗占据的分量较重;这不仅因为它同时包含多种体式——五古、五绝、五律、歌行、七绝、七律,更为重要的是五七言的诗体特征所具备的更大可操作性。比如,译为诗经体就不免缩长为短,译为楚辞体又不免延短为长,两相综合,五七言往往成为折中的选择,其中又尤以五古为多。199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三》,共收录近代各体译诗58 首(不计散文诗),其中五七言译诗就有37首,占总量的63.79%;在这37首五七言译诗中,五言体有22 首,七言体有15 首。《翻译文学集三》共收英国诗27 首,其中的21 首均为五七言,占总数的77.78%,而这21 首五七言译诗中,五言体有17首,七言体只有4首。《翻译文学集三》收录的近代译诗虽然不全,但还是基本能够反映出清末民初译诗诗体选择的总体倾向。证以胡适译诗亦然。胡适“五四”前的译诗有13首①数字根据王新禧编注《胡适翻译小说与翻译诗歌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统计得出。,其中五七言译诗7首,占二分之一强;7首之中,五言体5首,七言体1首,剩下的一首《军人梦》共分三节,一、三两节为七言,中间一节为五言。胡适清末民初的译诗中,《军人梦》的诗体是比较独特的。
民初译者李思纯曾在《〈仙河集〉自序》中总结“近人译诗”的范式道:
近人译诗有三式:(一)曰马君武式,以格律谨严之近体译之。如马氏译嚣俄诗曰:“此是青年红叶书,而今重展泪盈裙”是也。(二)曰苏玄瑛式,以格律较疏之古体译之。如苏氏所为《文学因缘》《汉英三昧集》是也。(三)曰胡适式,则以白话直译,尽弛格律是也[10]。
诚如李氏所言,马君武能以“格律谨严之近体”译诗,如他译嚣俄(雨果)的《重展旧时恋书》;但这样格律谨严的近体译诗,即便在《君武诗集》中也并不多见。马君武的译诗,《哀希腊歌》为歌行体,《缝衣歌》为五古,《阿明临海岸哭女诗》为歌行体,《米丽容歌》为杂言体,近体译诗的占比并不是很大。不过却可以说,五七言是马氏译诗的主体。在清末民初译诗的家族中,近体译诗只是一个小分支,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该时期译诗对格律的规避,而这种情形,直到李思纯发表《仙河集》的1925年,也仍在延续。
五、词曲体
梁启超是词曲体译诗的先行者。扪虱谈虎客(韩文举)在《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旅顺鸣琴名士合并榆关题壁美人远游》的一段眉批中,透露出小说作者梁启超的译诗设想道:
著者常发心,欲将中国曲本体翻译外国文豪诗集。此虽至难之事,然若果有此,真可称文坛革命钜观。吾意他日必有为之者。此两折亦其大辂椎轮也[11]83。
“此两折”所指的,即梁氏以《沉醉东风》和《如梦忆桃源》翻译的拜伦诗歌《唐璜》的两小节。现将其译文迻录如下,代表一种译诗体式:
(沉醉东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两神名)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如梦忆桃源)玛拉顿后啊,山容缥渺。玛拉顿前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11]83-84!
对梁启超这两首译诗的理解,无论是从原诗的角度,还是从曲牌的角度,均“宜勿徒求诸字句之间,唯以不失其精神为第一义”[11]105。这两首译诗是否为“曲本体”译诗之“大辂椎轮”,也许会有不同的理解,但眉批中所说以“中国曲本体翻译外国文豪诗集”为“至难之事”,却不是信口大言。这也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清末民初的“曲本体”译诗并不多见。事实上,以曲牌或词牌翻译外国诗,遇到的格律障碍更多,操作起来也更难。像梁启超这样几乎不顾曲律的“豪杰译”,使论者很难按照曲牌的规范评判其好坏,只好从诗歌的“精神”上感受其价值。梁启超自己也知道这样译诗不免为人指摘,所以他说:
刻画无盐,唐突西子,自知罪过不小,读者但看西文原本,方知其妙[11]84。读者如果能看“西文原本”,自然能领略原诗的妙处。遗憾的是,当时的大多数读者是看不到或看不懂“西文原本”的——这也正是翻译的价值所在。不过话说回来,梁启超通过译诗,为读者指示一条通过阅读“西文原本”感受西诗之妙的路径,态度开明而通达,也符合译诗的初衷。
与梁启超“曲本体”译诗的“豪杰译”不同,陆志韦以词体翻译的外国诗倒很能符合词牌的要求。比如他发表在《东吴》1913年1卷1期的《野桥月夜·调寄浪淘沙》四首,以及发表在《东吴》1914年1 卷2 期的《译彭斯诗·调寄虞美人》,均是相当规范的词体译诗。《野桥月夜·调寄浪淘沙》译自美国诗人朗费罗的作品,其一为:
夜静小桥横,远树钟声。浮图月色正三更。桥下月轮桥上客,沉醉金觥。
潮水打空城,举目沧瀛。浮萍逐浪野花迎。两岸芦花斜月影,似溯空明[9]195。
每一句的平仄均合乎格律,可谓颇费匠心。陆志韦的词体译诗不仅代表一种译诗体式,而且本土化色彩浓厚,在中西诗意的转换上也有他独到的体悟。清末民初译诗诗体的多样尝试与探索中,陆志韦该占有一席之地。
总体而言,清末民初的词曲体译诗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我们也很难说它们对原诗的翻译是完全忠实、准确的。梁启超、陆志韦等译者的大胆尝试,毕竟给清末民初译诗演示一条他途,无论通与不通,它都为“五四”译诗在观念上同时也在方法上,提供着经验与镜鉴。
六、杂言体
杂言体译诗往往是因句意表达的需要,不得不突破整齐句式的束缚。这也容易理解:假如原诗句仅有一个或两个单词,译诗要想把它扩展成五个或七个汉字,难度可想而知;而且扩展之后的句意与原诗能否保持一致,也很值得怀疑,反不如直译其意简洁明了。还有一种情况,译诗已达五字或七字,但原诗的意思未能完全释放,此时译者在意犹未尽处酌添二三字,也都有明证可举。杂言体在句式上参差错落的特征,是中西两种诗歌在翻译过程中“张力互较”的结果。中国诗体对诗歌的形式要求,与西方诗歌的内容表达之间,存在以中纳西时产生的诗学张力;相应地,西方诗歌对形式的要求与中国诗体的现成规范,也并非完全对等。杂言体译诗长短不一的诗句正是两种诗歌的“张力”在翻译时“互较”留下的痕迹。译者没有完全按照中国诗的体式将西诗“削足适履”,而是为它留下较大的弹性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末民初译者忠实于原著的译诗精神。
以马君武翻译的《阿明临海岸哭女诗》为例。现依照《马君武诗稿》,各取原诗及译诗的一部分对照如下:
Why dost thou awake me,O gale?
风若有情呼我醒,
I'm coverd with dew-drops,it says,
风曰:露珠覆汝,此非汝眠处。
But the time of my fading is near,
噫!吾命零丁复几时?
The blast which my faliage decays。
有如枯叶寄高枝。
To morrow the traveller shall come,
或者明日旅人从此过,
Who once saw me comely and bold,
见我长卧海之湄。
His eyes shall the meadow search round,
吁嗟乎!海岸寥空木叶稠,
But me they shall never behold。
阿明死骨无人收[12]。
原诗中的“it says”被译为“风曰”,“I'm coverd with dew-drops”被译为“露珠覆汝”,都是按照直译的方法,但是译句中的“此非汝眠处”却是译者在原诗基础上的合理发挥。除了二、五两句和译诗中的“噫”“吁嗟乎”等语气词外,这一节译诗基本是每句七个字;第五句中的“或者”对应原诗中的“shall”,“从此过”对应原诗中的“come”。马君武没有将该句译为七字句“或者明日旅人来”,而是译为九字句“或者明日旅人从此过”,句意表达的准确性显然要超过他对句式整齐的考虑;而经此一译,从模糊的“来(come)”,到具体的“从此过”,原句的意思也更加明朗。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马君武这节译诗虽短,却同时采用了直译意译两种译法——前五句基本为直译,后三句为意译。而且,马君武将“But me they shall never behold”译为“阿明死骨无人收”,要比原句的字面意思“但他们永远不会看到我”,情感表达更为强烈。由此可知,马君武译诗在手法上是灵活机变的,他可以把外国诗译为谨严的近体诗,也可以直译意译两结合,将其译为杂言体。通过解读一首译诗,可以惊喜地看到“马式”译诗在内涵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叶中泠发表在《华侨杂志》1913年第2 期的《战死者之孀与孤》,应时《德诗汉译》中的《义士歌》《乐师诅咒》《骑士朝歌》等篇,《大陆报》1903年刊登的《威拉下民境遇歌》,马君武收在《君武诗集》中的《米丽容歌》等,同为清末民初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杂言体译诗。《战死者之孀与孤》叙“战死士”的妻子对丈夫与幼子的爱,动人以情;《义士歌》对救人急难的义士的歌赞,《乐师诅咒》对耀威黩武的“独夫”君王的诅咒,《骑士朝歌》对沙场捐躯的骑士视死如归形象的塑造,在不同的内容中共同体现出德国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英雄义士的崇敬;《威拉下民境遇歌》是为底层劳动者发声,《米丽容歌》则表达了对家乡的思念。清末民初的杂言体译诗,以“杂言”所具有的相对自如的表现力,丰富着读者对这一时期译诗阵营的认知。
七、白话自由体
白话自由体译诗在清末《圣经》翻译中就已出现。《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三》收录了1908年圣书公会发行的官话本《旧约全书·雅歌》二章。语言白话,句法欧化,与“五四”新诗在形式上已无太大不同。圣书公会翻译《旧约全书》使用的是官话,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翻阅张美兰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晚清民国间新教传教士中文译著目录提要》可以发现:晚清民国间新教传教士翻译的200多种《圣经》译本中,除了采用官话,还采用了粤语、潮州话、客家话、上海话、宁波话等,远远超过为数不多的采用文言的译本。晚清民国间的《圣经》翻译使用官话和地方方言,其利于传教的目的十分明显。以今天的眼光回望,可以说《圣经》翻译使用白话和土语的选择虽然符合后来语言文字改革的大方向,但传教士的考虑显然不在语言和文学改革的层面。事实上,《圣经》的白话体译诗对诗体解放和白话新诗创作的影响相当有限。本文探讨清末民初译诗的白话自由体式,主要还是聚焦“五四”新诗运动对诗体解放的推助。
这就要说到李思纯总结的“胡适式”译诗。所谓“胡适式”“白话直译,尽弛格律”的译诗,指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学家的白话自由体译诗。胡适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的译诗《老洛伯》,是他个人白话自由体译诗的开始,也是民国初年白话自由体译诗的开始。1919年3月15日,《新青年》第6 卷第3 号刊发的胡适译诗《关不住了》,被他视为是自己“‘新诗’成立的纪元”[13]。先实现语言的白话化,后实现形式的自由化,“五四”时期的译诗在新诗运动理论指导下,通过解放自身诗体参与到新诗诗体的建构进程中,并发挥重要的引领与示范作用。“五四”时期,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是重要的白话自由体译诗实践者;《新青年》则是推动译诗实现白话化、自由化,并且是发表白话自由体译诗最重要的阵地和平台。
白话自由体译诗并不是无视格律,只是这个“格律”不再是旧体诗的格律——“平仄粘连”“四声八病”之类,而是一种宽泛的整体的格律。所谓旧体诗格律,与李思纯所说马君武译诗“格律谨严”、苏曼殊译诗“格律较疏”之“格律”,表示的意思一致,而这正是主张诗体解放的胡适想要努力打破的。胡适试图建立的新诗规范,正如他在给侄儿胡思永的遗诗所作“序”中说的: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14]。以此衡量,我们或许就能明白,为什么胡适会以《关不住了》而不是《老洛伯》作为他新诗成立的纪元:《老洛伯》虽然也是白话自由体,但形式较乱,《关不住了》则被译得很整齐,显得有组织、有格式,也符合原诗作为格律诗的特征。所以说,在胡适的意识里,白话自由体译诗乃至新诗,都并不完全排斥格律。我们在看到胡适为诗体解放所做努力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他对新诗“有组织、有格式”的期望。
八、结语
清末民初译诗的六种体式,基本概括出本时期译诗的诗体情况。原诗属性及题材会影响到译者对诗体的选择,译者对原诗的文学感受及个人偏好,也会影响到译诗体式。从横向角度看,这六种体式代表了译者对外国诗向中国诗转换的六种理解;从纵向角度看,六种体式显示出由文言向白话、由整齐向自由的演进,准确地说,是中国传统诗体——诗经体、楚辞体、五七言、词曲体、杂言体,共同向白话自由体演进。在此过程中,“五四”新诗运动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它使得清末民初译诗在诗体上明显地区分为两个阵营——古典的和现代的。从古典走向现代,中国诗歌借助译诗建构起新诗体;从清末到民初,两个阶段的译者以一种历史接力的方式共同促成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其中作为一种隐性力量存在的,是清末民初两代译者思想意识、文学观念、翻译理念等层面的代际更新。
长期以来,关于清末民初译诗的研究,诗体问题一直未能获得足够的重视。其实,探究该时期译者选择何种诗体,为何选择某种诗体,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对中国传统诗体作出的调整和改变,是我们理解“五四”时期胡适为何以“诗体大解放”为突破口掀起“诗国革命”的重要视点。通过本文具体的案例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梁启超还是刘半农,当其运用古典诗体译介外国诗时,均会感受到相当的矛盾和困难;他们的感慨,从翻译的角度论证了诗体解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对清末民初译诗各体式的分析,一方面可以展示译者的翻译策略,另一方面也可使外国诗内容与中国诗形式之间的张力效果得以生动呈现。在以西方近代文学为范型构建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潮流中,不仅本土文学创作在一步步探索转型的方向,翻译同样以自身努力试验着多种可能。译诗在成功与失败交织的尝试中,最终找到通过白话化、自由化来准确传达原诗形与意的途径,也由此建立起可供新诗参照的诗体形式。可以说,在此之前的译者的每一次思考和努力,都值得纪念。本文对清末民初译诗体式的总结分析,正是想填补既有研究对诗体问题着墨不多的遗憾,垫厚这块在以译诗为视角考察新诗诗体建构的研究领域略显薄弱的“砖石”,从而使相关研究的视角能够更加丰富而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