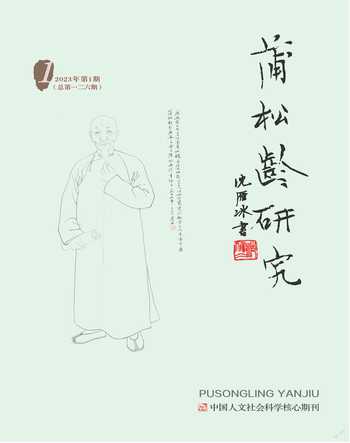《聊斋志异》中再婚与继母现象
2023-06-07于天池李书
于天池 李书
摘要:《聊斋志异》有三十余篇反映妇女再婚,可称是明清之际再婚问题的风俗画卷。站在男权和宗法的立场上,蒲松龄是那个时代的代言者,但在前房子女的教育问题上,蒲松龄表现了教育家特有的关注和视角。
关键词:《聊斋志异》;蒲松龄;《吕无病》;《细柳》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志码:A
再婚,是人类婚姻史上正常之事。《聊斋志异》中的婚恋篇章约有一百余篇,其中涉及再婚的有三十余篇 ① ,约占百分之三十。比如《冤狱》篇中结合的男女皆是再婚者,即是这种正常社会现象的反映。
《聊斋志异》反映再婚的篇章不仅多,而且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不仅涉及继母道德问题,而且探索了前房子女的教育问题,简直是明清之际关于再婚问题的风俗画卷。
一
在明清社会,男性再婚,天经地义,无拘束无限制,不存在任何道德争议。所以《聊斋志异》对男性再婚也从无微词。女性的再婚就不一样了,不仅为主流观念所不容,认为是“失节”“失贞”,实践操作中也形成严重困扰和麻烦。上述涉及再婚的三十余篇故事中,凡再嫁的女性几乎无一不是被鞭挞的人物。最能反映这一社会问题在男女性别上的差异的故事是《牛成章》篇:
牛成章,江西之布商也。娶郑氏,生子女各一。牛三十三岁病死。子名忠,时方十二,女八九岁而已。母不能贞,货产入囊,改醮而去。遗两孤,难以存济。有牛从嫂,年已六袠,贫寡无归,送与居处。
数年,妪死,家益替。而忠渐长,思继父业而苦无赀。妹适毛姓,毛富贾也。女哀婿假数十金付兄。兄从人适金陵,途中遇寇,资斧尽丧,飘荡不能归。偶趋典肆,见主肆者绝类其父,出而潜察之,姓字皆符,骇异不谕其故。惟日流连其傍,以窥意旨,而其人亦略不顾问。如此三日,觇其言笑举止,真父无讹。即又不敢拜识,乃自陈于群小,求以同乡之故,进身为佣。立券已,主人视其里居、姓氏,似有所动,问所从来。忠泣诉父名。主人怅然若失,久之,问:“而母无恙乎?”忠又不敢谓父死,婉应曰:“我父六年前,经商不返,母醮而去。幸有伯母抚育,不然,葬沟渎久矣。”主人惨然曰:“我即是汝父也。”于是握手悲哀。又导入参其后母。后母姬,年三十余,无出,得忠喜,设宴寝门。牛终欷歔不乐,即欲一归故里。妻虑肆中乏人,故止之。牛乃率子纪理肆务,居之三月,乃以诸籍委子,取装西归。
既别,忠实以父死告母。姬乃大惊,言:“彼负贩于此,曩所与交好者,留作当商,娶我已六年矣。何言死耶?”忠又细述之。相与疑念,不喻其由。逾一昼夜,而牛已返。携一妇人,头如蓬葆,忠视之,则其所生母也。牛摘耳顿骂:“何弃吾儿!”妇慑伏不敢少动。牛以口龁其项。妇呼忠曰:“儿救吾!儿救吾!”忠大不忍,横身蔽鬲其间。牛犹忿怒,妇已不见。众大惊,相哗以鬼。旋视牛,颜色惨变,委衣于地,化为黑气,亦寻灭矣。母子骇叹,举衣冠而瘗之。忠席父业,富有万金。后归家问之,则嫁母于是日死,一家皆见牛成章云。
在法律的层面上,牛成章和郑氏都是再婚,并无异样。作为男性,牛成章的再婚(尽管是在非人间)顺理成章,心安理得;但作为女性,郑氏再婚就被戴上“不能贞”的帽子,蒙上了抛弃子女的恶名。更令人惊讶的是,宣布罪名,执行判决惩罚的,竟然是有着同样再婚问题的丈夫!
女性再婚,虽然普遍不被社会认可,但也有潜规则,那就是当丈夫去世或已解除婚约之时,如果女性“齿太幼”,“又无出”,就可以再婚,社会也可以容忍,因为这是“恒情”。比如《吕无病》篇中的王天官女21岁“新寡”,再嫁孙麒。23岁时被孙麒休弃,延宕了多年,仍然可以再嫁。比如《金生色》篇中的金生色死后,婆家和娘家对于她的去留发生了不快地争议,等等。在正常情况下,女子死了丈夫再婚,一般由婆婆而不是母亲操作,虽也征求本人的意愿,但大权掌握在婆婆手中。《金生色》篇就体现着婆婆控制着寡媳的再婚的权利,并深刻反映了勉强妇女守节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为什么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普遍对妇女再婚持负面态度呢?除去对于妇女贞操上的偏见外,也还源于社会和家庭中的实际问题的某些考虑,并不能一概以落后观念视之。在这些方面,《聊斋志异》有多方面的反映,比如丈夫死后,年迈的公婆有养老的问题:《耿十八》篇中的耿十八之所以耿耿于妻子不应承守节的承诺,原因在于“老母腊高,妻嫁后,缺于奉养”;有家族财产的流失问题,比如《大男》篇中申氏再嫁过程中,“田产为子侄所阻,不得售。鬻诸所有,积数百金,携归兄家”。《牛成章》篇中郑氏“货产入囊,改醮而去”。再比如,《吕无病》篇中的王天官女在被孙麒休弃之后,回到娘家已无立身之地,因为出嫁之女并无财产继承权,没有财产继承权也就意味着没有了生活的来源。孙天官女之再嫁也就成为必然。
不过,社会对于妇女再嫁的负面态度,也包括蒲松龄的态度,更多指向了有年幼子女的女性。因为有子女的女性再嫁,不外抛弃年幼子女离去或者携带子女进入新夫家两个途径。抛弃年幼子女另嫁,为古今社会所不齿。《牛成章》篇中的郑氏之所以被当众指责处死,不是因为“货产入囊,改醮而去”,而是因为抛弃子女!《金生色》篇中的木氏最后家破人亡因奸而死,本质上也是因为放弃教养子女而另嫁!另嫁不守乃至被處死,这是《聊斋志异》中对于再婚女性最重的惩罚了。不过,《聊斋志异》中没有携带子女再婚的女性的故事,不知是因为此类事情在明清时代绝为罕见,还是蒲松龄有意回避了此类题材。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中,子嗣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男性之所以堂而皇之地再婚乃至娶妾,女性之所以不能轻易再嫁,都同这一问题关联。女性抛弃子女再嫁固然受到谴责,而男性的再婚使得前房子女受辱在《聊斋志异》中也不乏啧有微词的作品,比如《黎氏》《恒娘》《吕无病》《细柳》《张诚》等篇,在这些作品中,往往是男子懦弱,女子泼悍(或强势)而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蒲松龄对此类问题颇为关注,并有意通过小说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除去在《黎氏》篇有“再娶者,皆引狼入室耳”这样的较为偏激的话外,其中《吕无病》和《细柳》最为值得注意。
二
《吕无病》篇写洛阳孙麒在妻子病故后,先是与“微黑而多麻,类贫家女”的吕无病同居。吕无病待前妻之子非常疼爱,但因出身微贱,无法与孙麒结为伉俪;后来孙麒娶了有势有貌的王天官女为妻,王天官女骄奢悍泼,虐待前妻之子,孙麒不堪其扰,远避京都。此期间,孙天官女虐待孩子,逼走吕无病。吕无病托梦孙麒回家救回儿子,孙麒始知吕无病为女鬼。悲愤之余,孙麒休弃了王天官女。王天官女被弃后在娘家悔悟,历尽苦难,争取与孙麒复婚,终为贤妻良母。
就本篇故事写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感情纠葛而言,《吕无病》篇与《香玉》《小谢》《陈云栖》《莲香》《嫦娥》等在结构上颇为近似,但又有很大的不同:《吕无病》篇中的主人公全为再婚。男性孙麒是丧妻者,吕无病虽为“年约十八九”,而观其行事,似非少女;另一位王天官女则明言其为“新寡”。这在《聊斋志异》的性爱篇章中可谓绝无仅有。更值得注意的是,《吕无病》篇所写感情上的纠葛更多体现在婚后的日常生活上而非婚前的缠绵恋爱上。
《聊斋志异》中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感情纠葛里女性都很漂亮,性格各异,互相映衬,最后善始善终,共侍一夫;《吕无病》篇的两个女性则反差极大,不是美貌善良相得益彰,而是美丑善恶呈强烈对比状态。就貌而言,吕无病“微黑而多麻”,王天官女美艳青春。就家世而言,吕无病“类贫家女”,而王天官女家世显赫,扬言“即杀王府世子,王天官女亦能任之”。就性格言,吕无病知书达礼,温婉贤淑,在家庭中“俯首承睫,殷勤臻至”。甘于婢妾地位。而王天官女骄奢淫逸,“衣服器用,多厌弃,辄加毁弃”;“怒迁夫婿,数相闹斗”。尤其是两个女性在对待前妻的子女上有极大反差:吕无病善待孙麒前妻许氏的子女阿坚,“爱抱如己出”。阿坚“从无病宿”,连许氏都“唤不去”。许氏死后,吕无病与阿坚相依为命。而王天官女则折辱虐待阿坚:“无病鞠躬屏气,承望颜色,而妇终不快。夜使直宿床下,儿奔与俱。每唤起给使,儿辄啼。妇厌骂之。无病急呼乳媪来抱之,不去,强之,益号。妇怒起,毒挞无算,始从乳媪去。儿以是病悸,不食。妇禁无病不令见之。儿终日啼,妇叱媪,使弃诸地。儿气竭声嘶,呼而求饮,妇戒勿与。日既暮,无病窥妇不在,潜饮儿。儿见之,弃水捉衿,号咷不止。妇闻之,意气汹汹而出。儿闻声辍涕,一跃遂绝。”最后吕无病拼死去给孙麒报信,挽救了阿坚。阿坚被救活后,王天官女依然悍泼,“盛气奔出,将致诮骂”,“儿方啼,开目见妇,惊投父怀,若求藏匿。抱而视之,气已绝矣。急呼之,移时始苏”,以致孙麒怒骂说:“不知如何酷虐,遂使吾儿至此!”
吕无病和孙天官女的强烈对比,表达了蒲松龄对于男性再婚时对于女性选择标准的看法,那就是必须能够善待前房子女,而吕无病和王天官女分别代表了继母中的好坏典型。
再婚不同于初恋初婚。再婚大都失去了初恋初婚的浪漫,变得更加注重生活的实际。对于嫁给再婚的男性而言,女性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前房遗留的子女问题,而男性所考虑者则在女性的容貌、财产、身世地位之外,也加进其对待前房子女的态度。——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婚姻的目的是子嗣,子嗣是宗法社会家庭的底线。孙麒面对王天官女的“数相闹斗”,可以闪避,“托故之都,逃妇难也”,可是面对王天官女把自己的孩子置于死地,则忍无可忍,“立离婚书”。
就小说的艺术而言,《吕无病》并非十分优秀的篇章。吕无病死后,孙麒“题碑曰‘鬼妻吕无病之墓”,小说已经结束,卻添加上王天官女被休弃之后的悔悟,不仅累赘生硬,而且复婚后王天官女的悔过不近人情,乃至预言自己“某日当死”,死之日,“颜色如生,异香满室”,更是荒诞之极。不过,蒲松龄在“异史氏曰”中说“心之所好,原不在妍媸,焉知非自爱之者美之乎”,却极有道理,含有美学意蕴。它包括两层意思。其一是美丑的判断具有主观性,所谓“情人眼中出西施”。其二是相貌的美丑只是表面现象,无关乎人心,而人心的好坏善恶,才是最根本最切实际的择妻标准。
三
如果说《吕无病》篇给人的启示是如何从道德层面选择继母的话,那么《细柳》篇则提供了继母应如何教育前房子女的范例。
细柳是“中都之士人女也”,与吕无病同样都是知书达礼的女子。大概蒲松龄认为好的家庭教养是好继母的必要条件吧。与吕无病“微黑而多麻”不同的是,细柳长得“眉细、腰细、凌波细,且喜心思更细”。在丈夫去世之前,小说主要突出了细柳心思缜细,擅于相面的贤妻形象,写她善于持家,“晨兴夜寐,经纪弥勤。每先一年,即储来岁之赋,以故终岁未尝见催租者一至其门”;写她对于丈夫去世未卜先知,提前做好各种准备。同时写她对于前妻之子长福“抚养周至,女或归宁,福辄号啼从之,呵遣所不能止”。而在丈夫去世后,小说充分展示了她善于教育子女的好母亲的特质。
子女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亲生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打,可以骂,可以做想做的一切,社会舆论没有异议;但假如是继父母,社会舆论就比较苛刻了,正如蒲松龄所指出的:“日挞所生,而人不以为暴;施之异腹儿,则指摘从之矣。” [1]1024“比如有一个前窝儿,若是打骂起来,人就说是折蹬;若是任凭他做贼当王八,置之不管,人又说是他亲娘着,他那有不关情的:谓之左右两难。” [2]882
作为继母,虐待前房子女的只是少数,能够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前房子女是大多数。假如细柳对待前房子女长福只是“抚养周至”,细柳也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好继母,小说也就是一个普通的道德小说而已。作为教育家的蒲松龄,在《细柳》篇则增加了如何教育前房子女的内容,因为这是继母更难面对的问题,也是继母细柳更难能可贵更光彩照人之处,其笔力较之前代小说显然深入了许多。
《细柳》写长福在父亲死后,“娇惰不肯读,辄亡去从牧儿遨”。而且任凭细柳“谯呵不改,继以夏楚,而冥顽如故”。小说写在此状况下,细柳毅然决然采取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让长福在经历磨难后自己幡然醒悟:“母无奈之,因呼而谕之曰:‘既不愿读,亦复何能相强?但贫家无冗人,可更若衣,便与僮仆共操作,不然,鞭挞勿悔!于是衣以败絮,使牧豕,归则自掇陶器,与诸仆啖饭粥。数日,苦之,泣跪庭下,愿仍读。母返身向壁,置不闻。不得已,执鞭啜泣而出。残秋向尽,桁无衣,足无履,冷雨沾濡,缩头如丐。里人见而怜之,纳继室者,皆引细娘为戒,啧有烦言。女亦稍稍闻之,而漠不为意。福不堪其苦,弃豕逃去,女亦任之,殊不追问。积数月,乞食无所,憔悴自归。不敢遽入,哀求邻媪往白母。女曰:‘若能受百杖,可来见,不然,早复去。福闻之,骤入,痛哭愿受杖。母问:‘今知改悔乎?曰:‘悔矣。曰:‘既知悔,无须挞楚,可安分牧豕,再犯不宥!福大哭曰:‘愿受百杖,请复读。女不听,邻妪怂惥之,始纳焉。濯发授衣,令与弟怙同师。勤身锐虑,大异往昔,三年游泮。”
与教育长福的方法同样但作为陪衬情节的,是细柳自己的孩子长祜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游闲惮于作苦”,甚至“淫赌”。细柳也采取了同样的“磨砺”教育方法,使长祜改悟。在她的耐心教育下,两个孩子都长大成才,最后一个当官,一个经商,一富一贵。细柳追忆教育孩子的经历时说:“汝弟今日之浮荡,犹汝昔日之废学也。我不冒恶名,汝何以有今日?人皆谓我忍,但泪浮枕簟,而人不知耳!”
细柳教育孩子采取的“磨砺”方法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尤其按照现当代如何对待处于“逆反心理”期的青少年的教育理论,蒲松龄提供的范例简直可以说荒谬至极。因为在这种挫折和磨砺下,孩子固然可以按照小说家的浪漫意愿走向悔过自新,却更可以按照现实生活中更多的破罐子破摔的方向发展。不过,《细柳》篇的意义,不在于提供这种“磨砺”式教育方法是否正确,而在于它超越了以往小说关于继母道德的讨论,探索了继母与前房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并塑造了有胆有识,关爱并善于教育子女的继母细柳的形象,这才是它超越前人和创新之处。
参考文献:
[1][清]蒲松龄.细柳[M]//《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清]蒲松龄.慈悲曲[M]//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
Remarriage and Stepmother Phenomenon in
Liaozhai Zhiyi: Together with Lv Wubing and Xi Liu
YU Tian-chi1 LI Shu2
(1.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2.Central Committee of Jiu San Society,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 Liaozhai Zhiyi has nearly 30 chapters reflecting women's remarriage,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a custom picture of remarriag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atriarchy and patriarchal system,Pu Songling was the spokesman of that era, but on the issue of the education of the children in the front room,Pu Songling showed the special attention and perspective of educators.
Key words: Liaozhai Zhiyi;Pu Songling;Lv Wubing;Xi Liu
(責任编辑:李汉举)